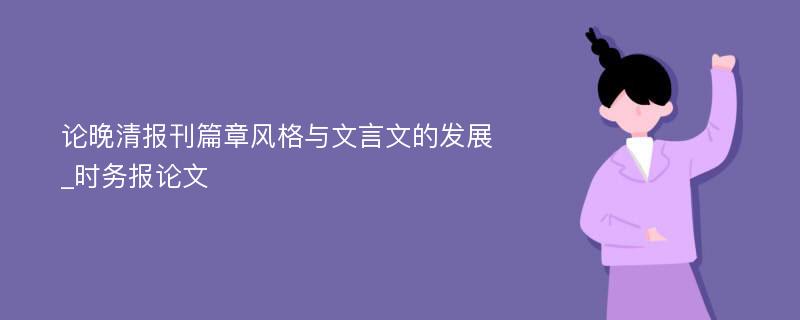
论晚清报章体与文言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章论文,晚清论文,文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7)02—0122—04
“文言”的概念,是中国古代雅文学一个庞杂的经验式书面体系的集合,难以精确定义。并且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甚至在其内部还包括了许多相异与冲突文学语言的实践,如古文与骈文。晚清以降,在现代媒介基础上产生的“报章体”,代表了近代以来文言发展的趋势。如同麦克卢汉在现代媒介研究中认为,新的媒介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它们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世界”[1](P7)。“报章体”的文言表达,以载体的现代传媒形式,带来了创作主体身份的调适、文学传播的市场化、阅读群体的扩大、俗文学的兴起等变化,促使文言发展形成了清末民初浅近文言的种种特质。
一
文言发展到晚清时期,与报章体共时性存在,最值得关注的“文”的历史事件和现象,一是八股文与科举制的废除;一是颇具文学色彩的桐城派古文占据的统治地位。二者对于当时文言书写的面貌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十八九两世纪的中国,文学方面是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的时代”[2](P39)。
从明代的科举考试,八股文就成了专用文体,内容是不离《四书》的代圣贤立言,形式上必须写成“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到了晚清,在改良主义的思潮下,将颓败的国势与八股文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废科举、兴学校”成为一种士大夫普遍的改良共识。1905年,中国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科举取士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科举制的废除、八股文的逝去在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影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和诸多领域。简而言之,一方面“学”、“仕”合一的传统终结了,读书人不再会有“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为新思潮的引进扫清了障碍,促进了现代意义上各类学科的兴起。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读书人社群在社会学意义上边缘化,预示了中国数千年士大夫阶层终结的命运。反映在“文”上,必将造成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文”与“道”既有意识形态关系的模糊,在缺乏如科举这样的制度性依托下,文言将逐渐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
关于桐城派古文,它集中国古代文论之大成,是在晚清古文中占有正宗和统治地位的流派。它笼罩和影响了这一时期整个古文创作的面貌,其深层文学观念是道统文学观的典型代表——力图以孔孟程朱的“道统”融合韩柳欧苏的“文统”。不少论者都罗列过晚清时桐城派古文的“负面影响”,从而后见之明地说明桐城派古文的“腐朽性”。其实,晚清时期的桐城古文经过曾国藩改造与努力,确切说仍有着生命力,并极力与社会保持同步的发展,甚至在特定时期中用来翻译西方小说。桐城派古文一直得以延续发展,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才在“桐城谬种”恶谥下遭受到迎面打击,成为历史的名词。因此,并不像某些论者的看法,在清末民初时期,报章体面对桐城派古文时,是绝对对立之下的摧枯拉朽。实际上,其时报章体文言与“桐城派”古文同时存在,二者都没有一统天下。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不同的载体,新文体更多出现于具有现代传媒意义的报刊杂志,它所引起的舆论关注与轰动是远非“桐城派”古文能比拟的。
二
早期的中文报刊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如1815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创办了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查世俗每月统纪传》,后来有较大影响的如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1874年由《中国教会新报》改名的《万国公报》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报刊中语言的使用已有新的特点。如《申报》创刊伊始,报刊用语要求即为“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皆能通晓者”[3]。
在戊戌变法之前,具有初步维新变革思想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办报,一般认为国内第一张报纸是在1873年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王韬在1874年于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早期中国报刊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在早期报纸实践的基础上,已有人对文言提出了新的看法,把矛头直接指向其时正统的桐城派古文。王韬认为:“知文章所贵乎在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敢谢不敏。”[4](P1) 冯桂芬认为:“顾独不信义法之说。窃谓文者,所以载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具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有能理而董之,阐而明之,探其奥赜,发其精英,斯谓之佳文。”[5](P399) 后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报章体”基础上发展成为“新文体”,即在一定程度上顺延和提升了这些观念和实践。
戊戌变法时期,随着改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报章的兴起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事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与它们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这些报刊的出版地区遍及全国沿海和内陆的许多城市,打破了外报在华出版的优势,它积极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一支主要力量。”[6](P539) 相应地,以“开民智”和启蒙宣传为目的的报刊,其巨大社会功能已经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的重视——“时时轰动我耳膜,击醒我眼球,洗刷我脑筋,灌输我智识,教导我改革者,翳何物?翳惟十九世纪第四种族之报章。”[7] 于是,我们看到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带来政权的频繁转换与动荡中,报刊媒介的发展在政治缝隙中可能有更多的弹性空间,更容易在公共领域形成有力量的话语权,甚至一度成为时代精神的风向标。
对于晚清时期的报刊,研究者多注意这一浪潮中的民间力量参与,特别是在野改良派的倡导。近年来在清末民初文学方面,研究者多重视文本的制造方式和传播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似乎也加深了对报刊就是由民间力量主导的这一印象。如李怡认为:“报纸特别是非官方的报纸的问世,一般被视作是消解传统专制权威,建立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空间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报纸常常充当着公共利益的监察者,而报刊言论也自然反映了社会公众的权利与意愿。报刊文体的写作既不是为了‘上书’,也主要不是为了文人间的学问交谊,它第一次使得我们的文章必须面对普通的读者,这样的写作必然是‘务实’的,也必然是表述自然而有说服力的。”[8] 在这种描述中,当然包含有客观的情况,但似乎又给人这样的感觉——晚清报刊就是民间倡导的产物,但是语言文字的变革发展仅通过民间就能完成吗?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辨析晚清报刊产生的动力构成和参与,以及所能开拓的有效语言文字变革空间。实际上,在晚清稍具开明意识的士大夫都倡导办报,无数史料表明官方也曾积极介入。如晚清重臣张之洞就曾在经费上支持过《时务报》,他对报刊有一个“官方版”的全面理解:“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情,以后更无有继之者。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乙未之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土、三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9](P47) 张之洞的观点与当时报刊兴起的主流看法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时人们对报刊功用的认识。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也说道:“今请于京师及各省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译成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其各省政俗土宜,亦由各报馆派人查验,随时报闻,择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才日出矣。”[10] 后来总理衙门对此折奉旨议准,这实际上是官方承认了现代报刊的合法性,并参与到其中。因此,稍微扩大视野,注意到晚清报刊传播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晚清报刊的兴起不仅是民间力量的努力,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朝野的共同推动。
再以《时务报》为例,加以具体说明。《时务报》发行于1896—1898年的短时期内,它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社会各阶层的“普天忠愤”和要求变革的氛围中,创造了一个空前成功的传媒典范。“《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1](P477) 在《时务报》上,还载有很多政府官员饬令订阅《时务报》的消息:在第6册上,有湖广总督张之洞《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札》;在第18册上,有浙江巡抚廖丰寿《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在第25册上,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这非常能说明问题,《时务报》所开创的公共空间绝非限于民间,也不仅仅是由民间人士推动的。大量的官销事实表明《时务报》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明士大夫阶层——无论朝野,共同建构的一次救亡图存的努力。《时务报》是民报,但也有被政府官员推销中误视为官报的。如广西巡抚史念祖称:“今京师首辟官书局,上海《时务报》,皆以官报广行天下。”[12] 再来看《时务报》的受众,阅读者基本为士绅官员。如裘廷梁对无锡一地《时务报》读者的估计:“以无锡言之,能阅《时务报》者,士约二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分之一,农工绝焉。推之沿海各行省,度不甚相远。”[13]P(2625) 因此,我们很难说,类似《时务报》的晚清浅近文言报章,就已经是面向了“普通读者”。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想表明这样一个观点:晚清报章的蜂拥,不仅是民间推动的结果,报章体的兴盛也不仅是民间行为,它广泛影响至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在当时对文化仍具主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同时官方也予以了积极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章体所代表的文言发展,获得了社会文化上的广泛的合法性,具有了普遍意义,成为其时重要的文化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报章体”为代表的文言发展,就成为在现代媒介参与下完成的一种全局性汉语书面语的突破。
如果将这一观点再作延伸、提升,我们认为:作为民族书面语体系的现代转换,民间力量以其新锐姿态介入,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语言文字变革又不是仅由民间的倡导就能完成的,它必须与政权的力量相结合,在一种政府力量的支持与推行下才有可能彻底完成。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书面书写系统的变革,真正能成为全民性的重要成就,在其背后都可以看到政府力量的参与和推动,如五四白话文与民国时期教育部的努力,如汉语拼音、简化字运动与1949年后人民政府的大力倡导。反之,较为纯粹的民间语言文字运动,如世界语运动、汉字拼音化运动等,虽然影响可能显赫一时,但其成果最终难以真正地融入到新的书面语体系中去。
三
由于报章是以传达信息为目的,之于读者需要表述上的明白晓畅,而在其时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信息传达的繁复也需要大量引入新名词,所以晚清报刊的当事人即已自觉认识到报章与“新文体”的必然联系。唐才常在对《湘报》的期许中,包含了行文的要求:“义求平实,力戒游谈,以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所不逮;亦以使圆颅方趾,能辩之无之人,皆易通晓。”[14](P137) 梁启超则进一步看到:“自报章兴,吾国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15] 于是报章体对中国既有文言格局发起了全面的挑战。
谭嗣同是晚清对“报章体”有重要认识的人物之一,他撰有专文《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以细致辨认报章文体,高度评价报章体的价值。谭嗣同驳斥对报章体的种种批评:“若夫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宏史官之益而昭其义法,都选家之长而匡其阙漏,求之斯今,其惟报章乎?咫见肤受,罔识体要,以谓报章繁芜阘茸,见乖往例,此何异下里之唱……”[16](P375) 同时,他还将“天下文章体例”分为“三类十体”,在超越文言的各类文类中,探讨报章体的合法性和丰富性,报章文体包括了“纪体”、“志体”、“说体”、“注体”等等。再就具体的种类来说,简直是无所不包:“又以及于诗赋、词曲、骈联、俪句、歌谣、戏剧、舆颂、农谚、里谈、儿语、告白、招贴之属,蓋无不有焉。”[16](P377)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璀璨者也。”[16](P377) 谭嗣同对报章兼容性的强调和赞同,对报章所载俗文学的正视与认可,实际上已极大地背离传统文言书写体系和中国古代文学的雅俗格局,表明了报章体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格局的突破与冲击。
谈及“报章体”带来的新文体发展,必然会面对的是梁启超——这位近代文化与文学中的巨人。梁启超在晚清以报章体为代表的文言发展中的地位,如同胡适在现代白话文倡导中占有的地位。从早期在《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的活动,到正式承认“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报》”[11](P2508),《变法通议》系列影响深远的煌煌大文开始诞生。作为近代传媒界中的“Charisma”人物,梁启超以其杰出成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舆论界之骄子”。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浅近文言的文风也风靡大江南北,被认为是新文体中“时务文体”最杰出的代表。在其“三界革命”的实践中,梁启超在与其直接相关的“文界革命”中,浅近文言散文创作数量最为丰硕、成就最为惊人,并最充分展现了自身的个性和才华,以至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将梁启超的散文创作等同于“文界革命”的主要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界革命”主要是以实践确立的,它以实绩对中国古代文学格局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并形成了实质性的深远影响,代表了清末民初文言发展的主要面貌。
因此,我们说晚清报章体的文风一般都是条理明晰、平易晓畅,倾向于浅近化。它突破了文坛的种种定则,在中国古代文言的诸多“宗派家法”的陈规下,极大解放了文言文体的种种束缚,也埋下了日后“文体解放”的逻辑。基于信息传达的功用,报章体对文言的突破与发展,较少考虑审美方面的精雕细琢,这表明出晚清以降语言文字变革的主要着力点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强调语言文字的实用性,而不是在语言文字系统自足的内部中,去思考艺术性的建设。这样时代性的文言发展与实践的趋势,必将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固有的雅俗界限,从而为中国语言文字变革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收稿日期:2006—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