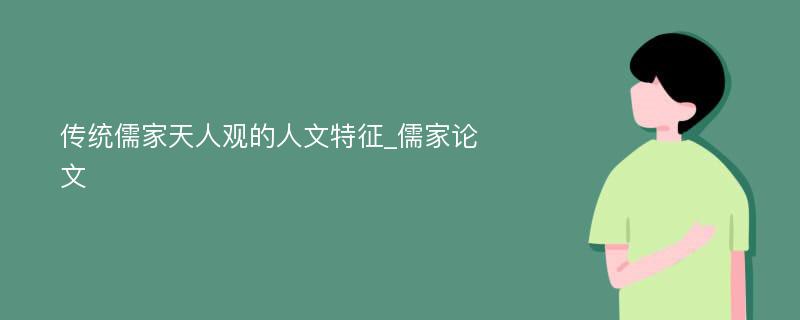
传统儒家天人观的人文主义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人文主义论文,天人论文,特征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人观作为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从天人相与的思想方式出发,论证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以及君权天授的理论。但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学的,并没有走上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那样的道路。究其原因,是儒家的天人观具有人文主义性质。
一、在本体论上,传统儒家学说中的天,兼具人格化的天与自然的天
双重含义
在中国文化史上,《尚书》所保存的周初几篇文献中,“天”、“天命”的概念多见,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天的朦胧认识。商周之际的天人观,孕育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路向。当时人们所说的天,往往是上帝的同义语,却又不是一个完整的至上神的形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科学地认识自然和解释人类社会,认识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天”和“天命”常有神与自然的双重特征。第一,强调天的意志,亦即天命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法则,“时惟天命,无违”[①],即使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君主,也必须“恪谨天命”[②];第二,天人相与,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历史沿革决定于天的意志,另一方面,从民情中又可体察天意,“天畏忱,民情大可见”。[③]可见,商周之际的思想家们把天命系于人事,以人类社会作为认知天命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这种重于人事而虚于敬天的认知路线,便决定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人文主义发展路向。
对于天与天命的认识,儒家更多地接受了商周之际的思想遗产。在先秦儒家那里,天同样是一个不很清晰的概念。《论语·公冶长》载:“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可见孔子及其门人也很少谈及天。从孔子及其门人关于天的一些言论来看,天依然是自然和神的混合体。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④]又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⑤]前者完全可以理解为自然的天,而后者则是人格化了的天。到了战国,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对于天作了各不相同的解释。虽然孟子在解释天命时曾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⑥]从中可以看出其自然主义倾向。但是,孟子更倾向于把天理解为人格化的,如《孟子·滕文公上》:“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与孔孟相反,荀子则强调天的自然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⑦]在荀子的思想观念中,天只不过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客观存在,天人相分,“大天而思之,熟与物言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⑧]荀子对于天的认识,显然比孟子的天人观更接近于事实。在尔后的思想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思孟学派的天人观。总之,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儒家是不可能走向神学道路。
汉代是儒家天人观发展的重要阶段。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继承了战国思孟学派的思想方式。董仲舒对于天的描述比先秦儒家更为细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董仲舒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的观点对天作了比孔孟更为详尽的解释:“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其天之序也。”[⑨]“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天之数也。”[⑩]这是把五行配以方位四时。董仲舒的发明在于把阴阳、五行与天道、人伦、五德结合为一体。如其谓“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11)“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事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12)其次,董仲舒所说的天更具人格化的特征。从先秦儒家天人相与的认识出发,董仲舒进一步论证说:“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3)这种认识的核心是承认天有意志,能够对于人的某些行为行赏罚。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解释天,得出天人感应论,是在论证现实社会的君主制度以及申述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用天来论证君主权力的至上性。汉代儒家的立足点依然是人类社会。
汉唐时期,从先秦延续下来的儒家思孟学派天人观和荀子的天道自然的思想被思想家们继承下来,天究竟是人格化的天还是自然的天,一直没有停止争论。东汉初期的桓潭、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都曾尖锐地批判过天人相与的思想。如,王充详尽地阐明了“天地合气、万物自然”的观点,强调“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14)刘禹锡则更进一步提出“天与人交相胜”(15)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推向一个高峰。
宋明理学扬弃了已往思想家对于天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从而使传统儒家的天人观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宋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由太虚,有天之名。”(16)“天道不穷,寒暑也”。“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17)张载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天人观,说明其思想只能是人文主义的。
在程朱理学看来,在天地万物之前,存在一个形而上的理或道,或称天理,理是宇宙万物本原,“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18)理与万物,是“理一分殊”的关系,所谓“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19)“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居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20)宋儒论述天理,其特征就是把儒家倡导的伦理政治原则赋于天,以此来说明封建的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天人本无二”(21),“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2)程朱理学关于天的解释,依然立足于人类社会。
汉儒重天命,宋儒论天理,其特征都是把儒家倡导的伦理政治原则赋于天,传统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中的天,从来都是人格化的天和自然的天的混合体。正是由于儒家学说中的天具有上述双重特征,儒家的天人观和政治哲学才不可能走向宗教神学的方向。
二、在认识论上,传统儒家始终认为天是可知的,不是神秘的
天与天命具有可知性,这一认识也发端于西周初期。《尚书·大诰》说:“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这句话说的是天命的可知性,人能知天。这也就在认识论上一开把天引向与人相结合的方向。
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23)这句话,足以证实孔子承认天与天命是可知的。在孔子看来,致知是个人知识和经验积累的过程,这样知天命在逻辑上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可能的。《孟子·尽心上》说:“尺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孔孟在人所以知天这一点上的差异在于,孔子认为人知天的根本途径是个人不断地向外部世界认知,而孟子则把知天作为道德的自我修养的结果。如果说在孔子那里,知天是人认知客体,那么在孟子的认识中,则是把天与人的道德看成是一体的,知天是人性自我修养的道德境界。天与天道的可知性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即使汉代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多有阴阳五行家的神秘色彩,依然承认“天命成败圣人知之”。(24)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即是人们必须遵行的外在必然准则,又始终被作为人的认知对象,“知天命”被历代儒家学者看作是格物致知或道德修养以成圣的最高境界。这正是儒家的天人观与宗教神学的差异之所在。宗教神学的基本精神是对于偶像的无条件崇拜和信仰,神或上帝是绝不允许人们认知的,并且也不承认人具有认知上帝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少在中世纪以前如此。这是传统儒家的天命观所没有的。传统儒家的天人观是人文主义的。
三、在天人关系上,传统儒家就人事而论天道
从先秦到宋明的历代儒家学者,虽然对于天道与人道的理解各异,而在逻辑上莫不以人道作为其思想学说的核心,这主要体现在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上。
历代儒家据人事而论天道,首先表现在对天命与君主权力的关系的认识上。前面说过,传统儒家把君主权力的来源归结于天命,所谓“天生民而立之君”,(25)君主权力是天的意志的体现,是代天行道,按照天的意志行赏罚。这一认识在理论上是君主权力本于天,王道、君道本于天道。但是,天道如何,历代儒家学者只具其言而未及其详,而现实社会的君主权力却是实在,具体的。用未知其详的天道说明现实的君主权力,事实上只能是站在君主权力的立场上来论天道。如《礼记·坊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这句话似乎是说“天无二日”是“土无二王,家无二主”的原因,但是仔细推敲则可发现,问题不在于“天无二日”这一前提,只是由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土无二王”的政治现象。“天无二日”这一前提是根源于“土无二王,家无二主的”。
传统儒家据人事而论天道的另一方面,是其天意与民情相统一的观念。传统儒家在理论上把天命赋予君主,而把天的意志的一部分赋予民众,往往以为民情察视天的意志。宋人张载说:“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过于耳目心思。天视听以民,明威以民,故诗书所谓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26)张氏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对孟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7)的诠释。这是把民众当作天的耳目,同时又把民众作为天的意志的载体。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孟子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28)在天、天子、民众三者的关系上,传统儒家认为,天以天下授予天子,但天子能不能常有天下却取决于民众,二者是相反相成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儒家对于天及天人关系的认识,具有典型的古代人文主义特征。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宗教神学统治的历史阶段。正是由于儒家的天人观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人文主义路向。
在世界文化史上,曾经存在过古希腊的古典人文主义、欧洲近代的人文主义和古代中国儒家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人文主义。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延伸,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传统。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家开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先河,而传统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却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附翼。人文主义思想与不同的政治传统的结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差别,就在于在天人观上的认识不同。
在天人关系上,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按照这一思想,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人在自然状态下所享有的诸如追求自由、享受、生存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当这种权利受到统治者的破坏时,人民有权推翻其统治,恢复自己的天赋人权。在中国传统儒家那里,不是天赋人权,而是天赋王权。传统儒家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自然权利。
在儒家的政治学说,君主是天子,天的意志、天命只是赋于了君主,广大民众全无权利可言,至于察民情、恤民生只不过是由君主权力派生而来的政治责任。虽然传统儒家如孟子等人也主张暴君无道人人得而诛之,汤放桀,武王伐纣等等,是所谓“诛其君而吊其民”;(29)但是,伐暴君、诛无道的结果不是恢复被统治者破坏了的“天赋人权”,而是修复和完善由于暴君统治行将倾覆的君主权力和专制统治。中西思想家在天人关系上的不同认识,导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只能走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人文主义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尚书·多士》
[②] 《尚书·盘庚上》
[③] 《尚书·康诰》
[④] 《论语·阳货》
[⑤] 《论语·子罕》
[⑥] 《孟子·万章上》
[⑦][⑧] 《荀子·天论》
[⑨][⑩]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11)(12) 《春秋繁露·阴阳尊卑》
(13) 《汉书·董仲舒传》
(14) 《论衡·自然篇》
(15) 见《柳宗元集》卷十六附刘禹锡《天论上》
(16) 张载《正蒙·太和篇》
(17)(26) 《正蒙·天道篇》
(18) 《朱文公文集·岭黄道夫》
(19)(20) 《语类》卷九四、卷十八。
(21)(22) 《遗书》卷六、卷五。
(23) 《论语·为政》
(24) 《春秋繁露·随本消息》
(25) 《左传》襄公十四年
(28) 《孟子·梁惠王下》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君主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董仲舒论文; 孟子论文; 天道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