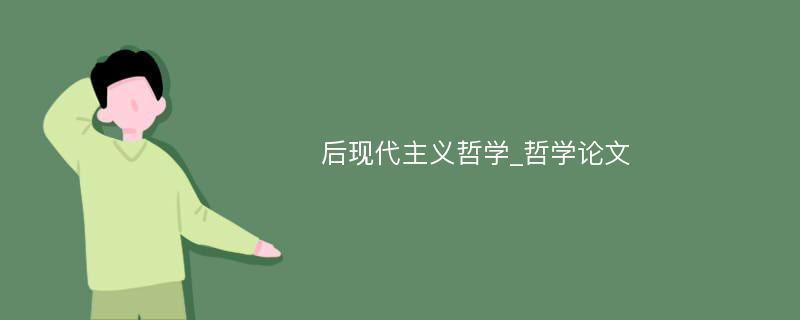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在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中,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即抛弃柏拉图以来的科学主义的哲学传统模式,转向一种更加开放的哲学立场。为了彻底扭转当代哲学的颓势,罗蒂提出了哲学的三个根本转变:一是从系统哲学走向教化哲学,二是从认识论走向解释学,三是从正常话语走向反常话语。可以说,罗蒂的主张反映了本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哲学的新动向,那就是将欧洲大陆的哲学同英美国家的哲学综合起来,克服它们各自的偏狭之处,最终实现一种多元的和平等的“后哲学文化”。
本世纪以来,英美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为了找到哲学的出路而费尽心机。然而,无论是哲学的科学化还是哲学的人本化,都没有达到重振哲学的目标。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哲学(包括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之所以屡试屡败,究其原因是没有跳出西方哲学传统的窠臼,徒劳地寻找着终极基础和绝对真理。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哲学面临的生存危机,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 )提出用“小写的哲学”取代“大写的哲学”,用“启迪的哲学”取代“系统的哲学”,在摧毁西方哲学传统的前提下重塑哲学的形象。从他的“后哲学文化”的设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以及后现代主义所反映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的深刻变化。
一、走出传统哲学的误区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始终有一种超越时空而进入永恒的企图。差不多所有的哲学派别都在重复柏拉图的思想,即建立一个不受历史限制的知识构架,为人类的文化提供一个终极的基础。二元论、再现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这些由柏拉图遗传下来的哲学思维原则,长期占据着西方哲学的活动舞台,并且成了主导性的东西。在西方传统哲学的风景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由柏拉图主义、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构成的一个坚固的哲学传统,这就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科学主义的哲学模式。
从柏拉图开始,哲学被看作是追求绝对真理的化身。关于心灵的学说(即认识论)成了哲学的核心所在。人类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用心灵去映照外在世界,“人具有一个本质,即他必须去发现各种本质。”(R·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文1版,3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这种认识论哲学将人的心灵视为一面可以映现外部世界的镜子,将认识活动看作是在心灵中发生的事情。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继承和发扬了柏拉图的哲学传统。他把认识论(关于心灵活动的学说)作为哲学的中心部分,通过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来建立他的第一哲学。他把心灵和外在对象作了二元论的区分,并且将柏拉图的视觉中心主义发展成一种典型的表象理论。在他看来,“去认知,就是去准确地再现心以外的事物;因而去理解知识的可能性和性质,就是去理解心灵在其中得以构成这些再现表象的方式。”(同上书,1页)
罗蒂认为,笛卡尔提出的类似镜子的心的观念,产生了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传统。“从作为理性的心转向作为内在世界的心的笛卡尔转变,与其说是摆脱了经院哲学枷锁的骄傲的个人主体的胜利,不如说是确定性寻求对智慧寻求的胜利。从那时以后,敞开了哲学家去达到数学家或数学物理学家严格性,或者达到这些领域严格性外表的大道,而不是敞开了帮助人们获得心灵平和的大道。科学,而非生活,成为哲学的主题,而认识论则成为其中心部分。”(同上书,43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西方近代哲学的图画,是一幅巨镜式的心灵的图画。对于这幅图画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可以凭借纯粹的和非经验的方法来加以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学被当作是知识的典范,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要依从于这个典范。
在罗蒂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是由康德所开创的。康德旨在把旧的哲学概念改造成一种最基本的学科的概念,在他看来,哲学的首要性不再是因为它站在最高的位置上,而是因为它站在最基础的位置上。换言之,哲学的首要性在于它是一门基础学科,其他学科都要从哲学这里获得自己的知识合法性,因为一切知识都产生于认知精神并且要从认知精神的秩序中获取自己的法则。在康德这里,人的心灵是任何先验认识的基础。从前的哲学把人的心灵看作是一个消极的容器,康德把人的心灵(尤其是人的想象力)视为创造的主体。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的,即我们只能先验地认识对象,因为认识对象是由我们构成的。人不仅为社会立法,而且还为自然立法。不是我们的认识应当与对象相一致,而是对象应当与我们的认识相一致。人类理智是预先构筑好的结构(时空等范畴),经验感觉材料只是砌在这种结构网眼上的砖块。当人类的理智之光投射出去,杂乱无章的感性世界顷刻就变成了一个有序的理念王国。近现代以来的主流哲学,大体上都是按照康德的这种思路发展起来的。
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和超越处在危机之中的传统哲学。不同背景的哲学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济世良方”,由此而形成了派别林立的现代哲学景观。从这些众多的哲学流派中间,罗蒂归结出三种最基本的思路。第一种是实证主义(包括语言哲学)和胡塞尔的思路,体现了一种科学主义的追求(建立一门严密的哲学科学);第二种是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思路,体现了一种艺术化或诗化的倾向(向往本原性的文化);第三种是实用主义的思路,体现了一种政治化和民主化的立场(崇尚平等的和多元的文化)。在罗蒂看来,胡塞尔和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完全以科学为样板,远离艺术和政治,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而海德格尔以及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则要求回到人类的现实,放弃科学主义的哲学模式,让哲学关注生活。
正是从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尤其是从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威那里,罗蒂找到了走出传统哲学误区的思想道路。在海德格尔和杜威看来,为了彻底摆脱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羁绊,我们必须向外转而不是向内转,必须走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哲学应该放弃它的“科学皇后”的幻想,从绝对真理的梦境里走出来,自觉地成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罗蒂认为今天已经没有人再相信,有朝一日,人类可以最终找到绝对真理,然后安定下来不再向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说明了人们对于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不信任。事实上,“考虑大写的真理,无助于我们去说某种(小写的)真的东西,考虑大写的善,无助于我们去做(小写的)善的事情,考虑大写的合理性,无助于我们变得(小写的)合理”。(R·罗蒂:《后哲学文化》,中文1版,3~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西方传统哲学固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形而上学信念,那种统辖一切和穷尽一切的图谋,实质上导致了人类文化的冻结。因为它不仅限制了思维活动的范围和方向,而且致使精神远离现实的东西。罗蒂认为,实用主义以它独有的理论魅力,为我们真正走出传统哲学的误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二、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
对于许多当代哲学家来说,实用主义不过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哲学,是一种不够规范的理论体系。尽管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有过一个繁荣的时期,但它很快被许多专业哲学家抛置在一边,被当代的众多哲学流派所轻视和贬斥。在分析哲学家看来,实用主义的反形而上学主张还不够严密和精致;在非分析哲学家看来,实用主义的反科学主义又不够彻底和激进。实用主义为什么不被人们所重视呢?原因可能是它用非哲学的语言阐述了反哲学的观点。正如美国学者S·罗森塔尔指出的,“实用主义并不想对传统的哲学问题提供更完美的解答,恰好相反,它打破了这些问题赖以生存的整个构架;而在打破这种构架之时,它也就拒绝采纳任何一种传统哲学立场,不管是二元论还是还原论,实在论还是唯心论,客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如此等等。”(S·罗森塔尔:《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中文1版,10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
罗蒂发现,实用主义在被埋没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开始在欧洲大陆和英美国家得到复苏。“哲学家们总是想提出新的观点。说英语的哲学家们往往在他们的思想源泉干枯的时候,希望从欧州大陆那里找到一些新的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过的。”(R·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英文版,6页,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和福科关心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数学和科学问题;德里达探讨的是哲学与小说、戏剧、电影的关系,而不是哲学与数学或物理学的关系,欧洲大陆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思潮的出现,显然影响到英美国家复兴实用主义的哲学运动。为了走出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的困境,戴维森、普特南、蒯因等人已经开始用实用主义来改造分析哲学,力图跳出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框框。
在罗蒂看来,复兴实用主义哲学是开创新哲学的正确选择。实用主义已经为我们扫清了传统哲学的尘埃,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武器。杜威等实用主义者告诉我们,哲学不等于认识论,哲学不是为了穷尽真理而存在的。哲学应该放弃追求永恒真理的奢望,回到可错的和暂时的现实生活。“人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休息,而是更丰富、更好的人类活动。我们应该认为,所谓人类的进步,就是使人类有可能做更多有趣的事,变成更加有趣的人,而不是走向一个仿佛事先已为我们准备好的地方。”(R·罗蒂:《后哲学文化》,中文1版,84~8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出于抛弃科学主义的哲学模式的需要,罗蒂极为赞赏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在《实用主义的后果》一书中,他对实用主义采取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方式。在他看来,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是由三个根本性的主张来体现的。首先是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按照詹姆斯的观点,真理不是那种具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在本质和现象之间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区别。“那些希望真理具有一个本质的人,也希望知识,或理性,或研究,或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本质。而且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运用他们对这样的本质的认识来批评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观点,并为发现更多的真理指明前进的方向。詹姆斯认为,这样的希望是徒劳的。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本质,也没有任何普遍的认识论方法来指导或批评或保证研究过程。”(同上书,第246页)简言之,“真”是我们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我们不能去问为什么是真的,因为真理没有本质;真理是一个用来表示赞许的词,而不是一个表示说明的词。
其次,实用主义反对把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在传统哲学的图画中,凡是没有达到与实在相符合的观念,就是丧失了合理性的个人谬见,就是一些私人的情感和意欲而已。柏拉图主义不仅用科学的程式来限制人的行为,而且要求人类服从于非历史和非人类的实在。科学真理被抬高,人性欲求被贬低;认识论哲学被视为中心的中心,非认识论的东西被当作无关紧要的边缘之物。因此,当实用主义者攻击那些作为精确表象的真理观念时,也是在攻击理性与欲望、理性与意志之间的传统区分。他们认为,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道德判断,都是对各种具体经验的思考。它们之间并无高低和大小之分。
再次,实用主义主张除了对话的制约以外,不要再设置任何外在的和人为的制约。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总是希望找到一种先天结构,由此而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固定化。似乎有了一个普遍的和不变的形而上学规定,人类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周围的一切了。在实用主义者看来,重要的不是追根究底地抓住某个本质,而是如何团结一致来对抗黑暗的现实。“我们与我们的共同体、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治传统、我们的思想遗产的认同,只要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我们的而不是自然的,是形成的而不是发现的,是我们构造的很多种中的一个,就会得到加强。”(同上书,251页)当我们看清人类的计划是可错的和暂时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偶然性的事实,而不再求助于必然性的设定。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命定的,而是存在着不断改善的诸种可能性。
同杜威等实用主义者一样,罗蒂宁愿要一个可错的和暂时的生活,而不愿要一个绝对的和不变的世界。他主张放弃思辨的理想,不要再去解答柏拉图主义的问题。哲学的思考应该从属于生活的实践,应该去追问社会政治问题和人类的历史遭遇问题。因此,他从传统哲学和现代分析哲学中冲杀出来,力图传承和复兴实用主义的理论主张,最终实现哲学自身的彻底转变。“实用主义者乐于见到的不是高高的祭坛,而是许多画展、书展、电影、音乐会、人种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等等。总之,是许多文化的选择,而不是某个有特权的核心学科或制度。”(同上书,153页)正是从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中,罗蒂找到了一个重塑哲学自我形象的理论模型。
三、后现代哲学的三个转向
“哲学的终结”是后现代主义者大谈特谈的一个思想转向问题。罗蒂也在大谈“哲学的终结”,但他的意图不在取消哲学本身,而是在于彻底改变哲学原有的形象和地位。罗蒂认为,哲学只有实现三个转向,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在后现代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首先,哲学要实现从系统哲学到启迪哲学的转向。罗蒂将哲学家划分为两个类型:一类哲学家的思想活动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另一类哲学家的思想活动基本上是破坏性的。前者以认识论为中心,后者以怀疑认识论的主张作为出发点。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代表前者的系统哲学家成了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哲学家,代表后者的启迪哲学家始终是处于边缘的外围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康德等哲学家的思想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固守着心灵的镜式本质,固守着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元哲学。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则是我们时代的启迪哲学家。他们都取笑关于人的古典图画,摈弃绝对真理和形而上学。他们更加注重人类的对话,反对用最终的词汇去追求普遍的公度性。
在罗蒂看来,从系统哲学转向启迪哲学,是走向一条非认识论哲学的道路。离开科学主义的元哲学之后,哲学既不想发展一种“先验解释学”,也不想建立一种“普适语用学”。哲学不再以发现永恒不变的研究构架为己任,不再去模仿科学的一举一动。在哲学自觉放弃了文化的特权之后,它可以充当一个“文化批评者”的角色。人们不再相信系统哲学的“绝对观念”,但可以接受启迪哲学的扶助。如果说系统哲学是在禁锢人类的精神活动的话,那么启迪哲学则是在激励人类的思想潜力。哲学应该推动人类去创造,而不是去停止人类的思维活动。
其次,哲学要实现从认识论到解释学的转向。罗蒂认为,认识论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探究(inquiry),并且只关心终极性的原理。相反,解释学以对话(conversation)为目标,旨在达到人类的相互理解。在放弃认识论而走向解释学的过程中,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不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而且真理这个概念只适用于古典哲学中的人的图画。我们应该用“自我形成”(Bildung)的概念来取代作为认识论目标的“知识”这个概念,正确地获取事实,只是发现一种新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的准备;谈论事物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罗蒂以极为赞赏的口气说道:“于是伽达默尔摆脱基本作为本质认知者的人这幅古典图画的努力,也是摆脱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从而使我们把‘发现事实’看作教化的诸多规划之一的努力。这就是何以伽达默尔如此不惜笔墨地摧毁康德在认识、道德和美学判断之间所做区分的理由。”(R·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文1版,31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再次,哲学要实现从正常话语到反常话语的转向。在系统哲学的支配下,属于认识论问题的正常话语(或正常研究)压制着非认识论问题的反常话语(或反常研究)。从笛卡尔以来,“有关科学话语是正常话语、而一切其它话语都须以其为模式的假设,成为哲学研究的标准动机”。(同上书,336页)凡是符合形而上学传统的理论研究,凡是服从于绝对真理体系的思想主张,都是可以大行其道的正常话语。相反,凡是背离了正常话语的思考和问题,均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贬斥。当然,反常话语受到的压迫和监禁,不仅来自科学的昌盛发达和认识论哲学的霸道横行,而且也来自食物匮乏和秘密警察。罗蒂提出,“如果有闲暇和图书馆,柏拉图所开始的谈话,将不致以自我客观化告终,这不是因为世界和人类的万事万物逃避了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可能,而只是因为自由的和悠闲的谈话,如自然规律那样确实无疑地产生了反常话语。”(同上书,338页)
从正常话语走向反常话语,也就是从统一性走向差异性,从中心性走向边缘性,从一元性走向多元性。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只是人类对话的一种声音。人类的对话更象是一种多声部的大合唱,而不是一种独唱或小合唱。我们接受反常话语,意味着接受不可公度性的原则。不可公度性包含着不可还原性,但却有着一种相容性。追求真理固然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但是,如果把人生等同于追求真理,无疑是对人类的歪曲。如果哲学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把它得到的绝对真理强加到每个人的头上,那么它将会窒息人类社会的活动。哲学应该是有助于个体和群体不断完善的一种工具,它行使着“文化批评”的职能,可以起到启迪人心和激活社会的作用。
“民主先于哲学”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罗蒂的自由主义理想。他反对认识论哲学及其再现论,是因为再现论束缚了人的心灵的活动;他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是因为这些形而上学的原则阻碍了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他看来,民主政治是首要的,哲学则是次要的;哲学只是为人的自由服务的,而不是为超验的绝对真理而存在的。抛弃柏拉图以来的认识论哲学传统,是要为不同的思想活动提供一个自由对话的空间,为不同的文化团体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机会。在后哲学文化中,再也不存在跨学科的和超文化的标准,再也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一个绝对的样板。
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不是要终结哲学本身,而是要重塑哲学的自我形象。对罗蒂来说,哲学在失去了它的贵族特权的今天,非但不会走向衰亡,反而会成为一朵“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当我们用一种平凡的心境去看待哲学时,哲学就不再是高深莫测和神秘玄妙的东西,而是变得亲切可爱。因为这种(小写的)哲学不是在那里命令我们和教训我们,而是在那里倾听我们大家的声音。
在彻底抛弃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的呼声中,罗蒂所采取的“解构”策略是拆除旧庙另辟地基来重建哲学的住所。罗蒂没有完全接受利奥塔德等人的虚无主义立场。他所提出的“团体中心主义”(或译“种族中心主义”),就是用来避开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理论选择。一方面,他赞同利奥塔德等人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寻求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因此,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带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他把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揉合在一起,把古典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揉合在一起,着重探讨了当代西方文化的转型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理论主张标志了当代西方思想的走向。
标签: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柏拉图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哲学史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