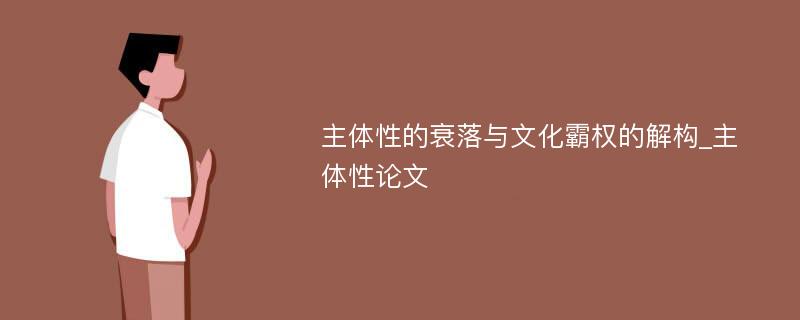
主体性的式微与文化霸权的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霸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044-06
对文化霸权的分析和批判是后殖民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后殖民主义崛起的时代正是主体主义哲学式微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对其大加讨伐,而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又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主体性批判问题上,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相同的旨趣。在后殖民主义的文本中,我们看到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主体主义的二元论、本质主义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可以说,从主体性的角度解构文化霸权是后殖民主义的应有之义。文化霸权问题是在主体性式微的背景下凸显的,文化霸权与主体性具有密切的关系,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解构文化霸权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相当必要的。
一、文化霸权与主体性的内在关联性
文化霸权与主体性是内在契合的,这一契合体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霸权的产生有其重要的主体性根源、文化霸权有其一定的主体性表现以及基于交互主体性基础上的反文化霸权机制(策略)的建构。为了厘清这三个问题,“自我主体”、“权力主体”、“身份主体”是需要我们非常关注的三个因素。从理论逻辑上看,文化霸权与主体性的内在关系,主要集中在西方的“自我主体”、“权力主体”、“身份主体”等方面。
“自我主体”是文化霸权与主体性关系中的核心,“权力主体”、“身份主体”实际上是“自我主体”在不同领域的另一种呈现,“权力主体”是对“自我主体”的另一种观视,“身份主体”是“自我主体”与“他者”试图建构的同一性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主体。实际上这几种主体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绝然分开的,它们是统一在一起的。西方作为主体,既是“自我主体”,又是“权力主体”、“身份主体”。作如上的区分只是一个“理论模型”而已,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来讨论问题的需要。同一个西方主体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呈现:“自我主体”是文化霸权的逻辑起点,文化霸权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自我与他者存在二分的逻辑前提;文化霸权之所以能够得以实施,是因为西方是“权力主体”,西方的“权力主体”是文化霸权的动力和源泉;而“身份主体”是文化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争夺的主要领域,后殖民主义谈论的身份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境遇中的身份建构、身份认同、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等问题。视自我主体为文化霸权的逻辑起点,由此既可看到文化霸权的主体性根源,又可看到文化霸权的主体性表现。西方把文化霸权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分之上:西方是“自我”,东方是“他者”。西方为什么把自己定位为自我、主体,把东方定位为他者、客体?这与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西方建构自我主体的哲学理据是同一性思维。同一性哲学是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它设置一个本体作为同一的支点: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这种思维把同一性当作目标,并绝对化,形成了绝对的专制性的同一性逻辑。这种逻辑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把自我看作是本,两者的同一以自我为支点。因此,同一性思维是归并性思维:把客体归并于主体、把他者归并于自我。同一性思维也是一种奴役性思维、专制性思维、极权性思维。在同一性思维中,同一化等于同质化、极权化、独裁化、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排他主义等,同一性逻辑中的总体化、普遍化必然排斥非同一性逻辑中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同一性思维必然导致唯我论,以自我为中心;也必然导致二分思维:西方/东方、主体/客体、自我/他者、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并把后者还原于前者。
正因秉持这种同一性思维,文化殖民自始至终贯穿着西方自我中心主义、东方的“他者”性。文化殖民主义者还把文化时间化,在文化的进化问题上采取历史线性进步观,认为自我是“源”,他者是“流”,他者永远跟在自我的后面追赶现代性;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上游,而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下游;有些文化属于文明,有些文化属于野蛮。主体(自我)和客体(他者)的关系被表述为一种时间上的距离:野蛮是过去的标志,文明是现在的标志,其目的就是要在西方人的时间与他者的时间之间拉开距离。于是,时间被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时间关系被看成是排斥性的关系,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在文化霸权主义的境遇中也存在启蒙问题,文化启蒙的过程也伴随着文化殖民。启蒙开启了现代性,现代性是启蒙的结果。与此同时,启蒙自身已日益具有意识形态性,启蒙与统治、极权、独裁、霸权、殖民的关系已从幕后走向前台,“启蒙变成了神话”。西方一直以启蒙主体自居,认为它有资格、能力和义务来“使东方明亮”,使东方摆脱愚昧、野蛮的境地,从而使东方得到拯救,使东方具有理性。实际上,这种启蒙“拯救”是虚,“殖民”是实,“拯救”的葫芦里倒卖的是“殖民”之药,启蒙成了蒙骗和欺骗。
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很多哲学家强调“我”是我们中的“我”、“自我是一个他者”来解构“自我同一”。黑格尔认为,“我是我们,我们是我”,他把主体间性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勒维纳斯和拉康在解构“自我同一”、批判自我主体方面更是具有釜底抽薪般的震撼力量。勒维纳斯提出“无脸的他者”,拉康提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不仅否认自我的中心性,而且认为根本就没有自我,他者是“我”的“无意识”,“我”只是他者的影子。
权力主体是文化霸权的基础和源泉。西方之所以能对东方实施文化殖民,就在于西方是一个权力主体。这里所说的权力是一个具有广阔涵盖性的概念,它既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治、法权中的权力、宏观权力,又指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话语知识权力、微观权力;既指政治、军事、经济等所谓的“硬权力”,又指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软权力”。权力具有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形态的权力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媒介权力、知识权力、软权力、微观权力是依附性权力,总体上是供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硬权力驱使的,但后者在要求前者依附的同时,也深深依赖于前者,前者装饰了后者的社会形象,证明着后者的合法性。正因为西方具有权力,它才能够“表述”、“建构”东方,表述、知识与权力具有内在的关联。
身份主体是文化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争夺的主要领域。如今,身份已日益意识形态化了。以意识形态化的身份认同观看文化身份,就不可避免地把文化人种化,认为一个种族一种文化,种族决定文化,人种间的差别决定精神、能力和习俗等的差别,并把这一差别绝对化,对混血现象加以排斥,反对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混合,表现出对玷污的焦虑,害怕失去血统的纯洁性,从而强调身份的纯粹性和同质性。这正是文化殖民在身份主体上的逻辑。实际上,身份不是静态的,而是构成性和流动性的。针对西方对东方民族文化的“妖魔化”,我们认为重建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是文化非殖民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但这种重建并不是“本土主义”的重建,不是基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之上的重建。这些所谓的重建仍然是二元对立、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的体现,我们要强调的是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本土”建构。
还有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明确的是,反对文化霸权,不能完全消解主体性。事实上,主体性是无法消解的,它是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维度,要消解的是传统的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是承载着本质主义观念的主体性。在整个反文化霸权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主体性重建,重建交互主体性,重建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主体性。这就要求我们彻底转变思维方式,从二分思维走向间性思维,以构建平衡的文化生态。
二、主体性的式微:后现代主义对主体主义哲学的批判
20世纪中晚期,西方思想界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并进而对现代性中的主体主义展开“狂轰滥炸”。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主体性的解构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当属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全面反思了现代性的理性启蒙假说、线性发展观、技术主义等,犀利地批判了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等在场的形而上学。
主体主义哲学先设定一个高高在上的万能的主体——无论其为逻辑主体、言语主体、实践主体还是其他性质的主体,再设定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和人不存在,而主体是作为提问者的存在,并由主体的存在颇费周折地论证自然和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主体主义哲学中,客体的命运是由主体决定和操控的。不仅如此,主体主义哲学还是将自我当作主体,主体当作本体的哲学。主体主义哲学强调万物的本体必须以自我存在为条件,自我是感性流变万物中的有限性的同一本源。主体自我是本体的拟人化变种,它保持着本体论所要求的同一性、现存性或在场性。所以,主体主义哲学也是自我中心主义哲学。
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达说,主体主义哲学是一种“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我们惟一所知的一种形而上学。也许可以这么讲,那种基础、原则或中心的所有名字指称的一直都是某种在场[艾多斯、元力、终极目的、能量、本质、实存、实体、主体、揭蔽(aletheia)、先验性、意识、上帝、人等等]的不变性”。[1](P504)而逻各斯中心主义“与作为在场的一般存在意义的历史规定相融合,与取决于这种一般形式并在其中组成它们的体系和历史系列的所有次要规定(事物向视觉显现为本质,作为实体/本质/存在的显现,作为此刻或瞬间的暂时显现,我思、意识、主体性的显现,他人与自我的共现、作为自我的意向现象的主体间性,等等)相融合。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支持将在者的存在规定为在场”。[2](P16)这样的动机、在场的权威性,被德里达视为哲学上的极权主义。
后现代主义所意欲解构的就是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就是主体主义哲学的这种极权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中心主义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而主客二元对立的实质,就是要毫无节制地提升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凸显人的主体性,为人在世界中的统治、占有权提供内在根据。主客二元对立作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式,被后现代主义看成是西方哲学步入迷途的根源,它不仅为人们设定了一个确定的客体,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去达到对客体的控制与征服。后现代主义从现代社会中二元论与主体性的互动以及在互动中相互论证、相互激发的逻辑事实出发,认为解构了主客二元对立结构,也就颠覆了主体中心主义,从而也就使主体失去了藏身之处。
主体主义哲学也是理性霸权的最终决定性的表达,即理性对于“强力意志”(尼采)、“存在”(海德格尔)、“差异”(德里达)、“非同一”(阿多诺)、“疯癫”(福柯)等的一个强权过程。人的主体性,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人的理性至上性所决定的。在笛卡尔以降的西方哲学世界中,理性是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主体,非理性始终是一种“他者的行为”,一种“他者语言”,凭借理性力量,人最终会走向自由的王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变成了工具化的理性,变成了极权主义理性。随着20世纪主体性的高扬,理性成为人类所引以自豪的、独一无二的征服一切的工具,成为人凭借权力控制一切的基础。理性中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滥觞,使理性这把威力无穷的双刃剑,既拓展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也开掘出人类所面临的陷阱。因此,解构理性中心主义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反思现代性的重要任务与必然走向。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性追求理性的普遍性是极其迂腐的,因为以理性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将其作为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的个性的发挥,束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绝对理性统治是对现代的有缺陷的设计”。[3](P23)费耶阿本德指出:“理性不再是指导其他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他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4](P3)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中,理性不再具有什么优势地位和中心位置,理性中心主义的基础被粉碎了,现代主体性瓦解了。
主体主义哲学还对线性进步观予以极力推崇。线性进步观强调历史进化的线性连续性,连续的历史“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并许下诺言,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恢复对他们的支配,并在他们中找到我们可以成为主体意识场所的东西。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想系统的两个方面”。[5](P15)福柯认为,线性进步观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达,这种进步观其实是传统思想家杜撰的一个神话,这种相信历史的连续进步的思想是“乌托邦式思维”。线性进步观是现代主义粉饰现代化进程,张扬主体中心主义的借口和根据。
在福柯那里,批判历史连续性与解构主体主义哲学是相互关联的。他通过强调断裂,倡导间断性、界线、裂口来解构历史连续性的神话,借助“考古”,通过剖析“知识型”的断裂性来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在1983年与C·罗莱的关于结构主义论题的一次谈话中,福柯解释使用考古一词,“是为了指示我所用的是一种错位的分析类型,即不是在时间中,而是根据对象所处的地位来进行分析。我的问题不是在演变中研究思想史,而是从思想的底下研究这样那样的物怎样成为认识之可能的对象,例如,研究疯狂何以在某个特定时期成为与某种知识类型相应的知识对象。这样,就存在着在关于疯狂的思想与把疯狂作为对象进行建构之间的错位”。[6](P497-498)知识考古学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分析,它不仅要分析知识的表层,而且要分析知识的深层,就像考古学家发掘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一样,去发现历史演化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显示:从一种知识型到另一知识型的转变是一种突然和完全的断裂。 “知识型”是断裂的,历史是非连续的,作为“主体的奠基功能”的连续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主体主义是虚妄的。
三、从主体性角度解构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的中心议题
后现代主义对主体主义哲学的解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解构,是一种旨在动摇现代社会理论基础的解构,其目的是导致“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7](P13)反对主体的权威性、专制性和压迫性,进而反思现代性,重写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这一致思路向无疑深深影响了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是继后现代主义之后在西方“横空出世”的一种极有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其理论观点的形成得益于后现代主义所提供的重要理论资源。正如琳达·哈琴所看到的,“在把价值给予(中心所称的)边缘或他者的过程中,后现代向任何敢于充当中心的霸权力量挑战,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在于‘拒绝把他者变成同一的那种思想’,而这当然是它对后殖民主义的意义所在”。[8](P494)德里克在一次访谈中也指出,后殖民主义采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并认同了它们的观点。后殖民主义的这种后结构主义倾向,在后殖民主义的“神圣三位一体”——即赛义德之于福柯、斯皮瓦克之于德里达、霍米·巴巴之于拉康的著述中仍清晰可辨。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声名显赫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思潮出现了。在80年代以前,人们还很少能看到后殖民主义这个词;而到了90年代初这个词就成了学术界的常用词了。[9](P24)
后殖民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赛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为标志,它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殖民主义崛起于20世纪末期,形成于主体主义哲学被无情解构的理论氛围中,受主体性式微时代理论氛围的“浸染”,其在解构文化霸权时对主体主义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从主体性角度解构文化霸权是后殖民主义的应有之义,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就充分肯定了主体性视角对分析东方学、文化殖民主义等问题所起的作用。他说,“我们无法否认霍米·巴巴、盖雅特莉·斯皮瓦克和阿希斯·南迪以殖民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有时令人极为困惑的主体关系为基础的作品,对认清东方学这样的体系所设置的人文陷阱所起的作用”。[10](P437)因此,要理解文化霸权的实质,真正达到反文化霸权的目的,从主体性角度来解读文化霸权就显得尤为必要。
如果说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是在谈论主体,那么,后殖民主义对主客二分本质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在批判主体性。而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就是西方主体对东方客体的建构、想象、表述、歪曲,讨论的是西方主体对东方客体的文化殖民。实际上,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在其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对文化霸权的主体性根源、主体性表现以及基于文化“杂交”、“模拟”(这实际上就是文化间性思维)等反文化霸权策略基础上的对文化的非纯粹性、互融和共存等问题都有论述和强调。
赛义德提出的一个“重要性”问题是能否有真实的、不带偏见的表述“他者”的知识。对此问题,赛义德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东方学对东方的表述是一种建构、类型化、妖魔化,东方学家眼中的东方是“东方化”了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东方。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的主要方式是,使东方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一种加强西方作为一种优等文明的自我形象的策略,其目的是使这个世界上的东方部分和西方部分之间的差异根深蒂固。结果,在东方学的话语中,东方被标以消极的客体性特征,而西方的特征则以积极的主体性词语来表达。通过这种主体主义的建构和表达,东方学就为西方的霸权主义行径提供了合法化的借口。赛义德《东方学》的理论旨趣就是对东方学家的主客二分的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在东方学家的眼中,西方是“自我”、“主体”、“中心”,东方是“他者”、“客体”、“边缘”,东方需要得到西方的关照、教化、启蒙和拯救才能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性。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详细的分析了西方对东方的“建构”、“表述”、“想象”、“妖魔化”和“类型化”,阐释了东方是如何被西方人所观看、凝视(gaze)的。为此,他对西方人对东方以及东西方关系所作的抽象概括和类型归纳提出强烈质疑,将西方/东方、我们/他们等二元对立的主体主义观念视作“帝国主义文化的标志”,[11](P178)从而对此进行抨击。
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基本上是立足于文化间性思维来展开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的。我们从其章节的标题就可看到赛义德的主旨。 《文化与帝国主义》共有四章,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标题分别为“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和“融合的观念”。赛义德把基于传统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身份认同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他反复强调东方民族文化的重建并不是建立一个类似于传统西方自我中心式的文化,不是摧毁一个西方中心后再树立一个东方中心。赛义德反对传统的将东西方文化作绝对对立的二元区分的观念,认为东西方文化实际上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东方文化是与西方文化“杂交”中的文化,东西文化是互渗的,文化是不纯的。R·拉德哈克瑞希南恰当地评价了这一观点。R·拉德哈克瑞希南认为,赛义德并不注重那些根深蒂固的盲目意识形态化的“我们与他们”式的区别,而是运用地理空间想象域来表明在那些各个不同的、经常彼此敌对的历史之间存在交叠现象。[11](P303)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女权理论家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后殖民主义女权理论,以消解潜存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西方(主体)中心主义观念和帝国意识,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女权理论家促使学术关注点转向女性主体,探讨了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如殖民主义的社会性别特性,帝国主义语境中的社会性别动态,殖民背景下社会性别、种族、阶级的互动,边缘化妇女的能动性等等。他们特别关注冷战以后由文化霸权主义、非殖民化、全球性移民浪潮及其文化后果引发的一些紧迫的当代问题,从而建构起一套相关的女权理论特别是反霸权性的女权主义读写活动。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女权理论家,斯皮瓦克将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理论紧密相联,运用女权主义去分析东方女性所遭受的权力话语剥削处境,运用解构主义去透析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权力的形成及其构成进行重新解读,以消解权力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真相。
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大特色在于她积极参与“属下”或“非主流研究”(subaltern studies),长期从事诸如第三世界女性和文化等“属下”话语研究,所致力于的就是要使这些第三世界的,“属下”、“非主流”社群喊出自己的声音,以便削弱帝国的文化霸权和主宰地位。在斯皮瓦克看来,在父权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压抑下,第三世界女性完全丧失了主体地位和自我表述的能力,沦为被动的客体和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变成为一个虚构的“他者”。“女性”这个符号之所以“空白”和“不确定”,是因为它触及到有关所有权的文本暴政,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她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家不自觉地复制出的帝国主义话语表示不满,主张重新构建第三世界女性的文化历史,“重新命名”、“重新书写”第三世界女性的文化身份,摆脱“边缘化”地位和处境走向“非边缘化”境地。作为“属下”的第三世界女性的“边缘性”正如东方文化的“边缘性”一样,不能被理解为与身俱来或固有的,而应理解为被推论建构的,是长期以来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帝国主义霸权造成的。但即使如此,这一边缘地带也是不可征服的,它会抓住一切适当的时机进行“非边缘化”和“非领地化”的尝试,进而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以便最后消解中心/边缘这一人为的二元对立。
后殖民主义的一大亮点就在于它对“边缘”、“他者”、“属下”等予以特别的关注。而在殖民主义话语中,“边缘”、“他者”、“属下”是作为主体的对象化的客体形象出现的。斯皮瓦克最关注的是“属下”能否为自己说话,或“属下”是否只能以扭曲的、“引起人们兴趣的”方式被别人表述和代言,她由此意欲对主流观念和属下地位进行质询。赛义德坦言《东方学》是对“弱者”悲惨境地的一种展示。巴巴在《献身理论》一文中也流露出对“他者”是被征引、被引用、被框定、被曝光、被打包的对象,是注解差异的一条边线,从来不是主动的表达者等自我中心主义观念的质疑。后殖民主义对“边缘”、“他者”、“属下”等“弱者”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向世人描述这些“弱者”的悲惨境地,也不只是表示对这些“弱者”的同情和怜悯,其目的在于揭露文化霸权主义话语对于“弱者”话语的压制和剥离,展示这些“弱者”的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所说、自我生命表征与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它直面西方的权力话语,从不同层面进行权力控制和社会压迫进行分析,以向中心话语挑战的姿态,以其“边缘”话语的特殊视角解构“中心”话语掩盖下的话语暴政和文化霸权。
标签:主体性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 自我中心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