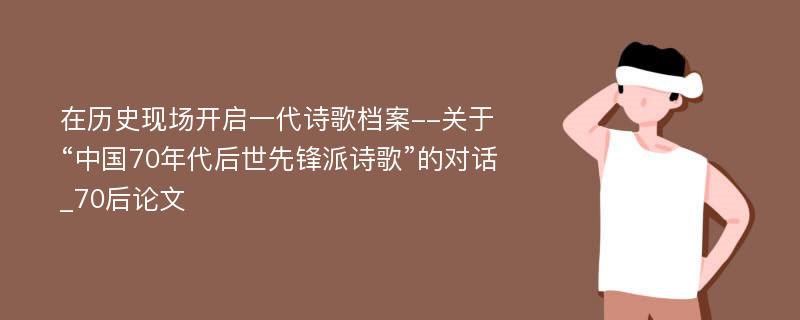
在历史现场打开一代人的诗歌卷宗——关于《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卷宗论文,先锋论文,中国论文,代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2009年12月9—10日,深夜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杨庆祥:首先我想祝贺你《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这本著作的出版发行,说实话,虽然也偶尔涉足诗歌圈子,但是对于你书中提及的诗人、作品、刊物、现象等等还是比较陌生,很多的名字还是第一次看到。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本很及时的书,所以说阅读这本书等于是一次补课。从整个诗歌研究现状而言,这么系统的全面梳理70后诗人的专著我觉得是一本开拓之作,填补了诗歌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盲点,而从更长远的意义来说,它又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我相信,以后无论是谁来研究70后的诗人或者诗歌现象,这都是一本绕不开的书。从这些方面来说,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无论何种溢美之词都是不为过的。当然,这本书引起我更大兴趣的与其说是它的贡献,不如说是它所涵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象本身的问题,也就是70后作为一个诗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另外是这本书写作的问题,也就是诗歌史如何去写的问题。我想就这几个问题和你进行一次对话,我们之间或许观点相左,认识不同,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正是我们进行这项工作的有趣之处。
霍俊明:我非常看重我们之间的这次对话。关于《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从目前看来可能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憾,但正如你所说这本书因为带有“第一次”的性质,所以我也格外珍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从2006年冬天在内蒙古的额尔古纳订下写作计划到此后三年时间的践行,我都感受到写作和阅读的巨大快乐和痛苦。给很多读者包括评论家的印象是除了断代史意义上的建构和理性的学理分析和阐释之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大开大阖的酣畅淋漓的散文化的、“激情”化的言说方式。据说有一个70后女性诗人是用一个晚上读完这本书的,当时她正发着高烧,可她后来说拿起这本书之后就不想让它再放下了,她觉得书中燃烧的情绪让她体会到久违的文学批评的热度和体温,同时也因为一代人的共同情感、体验甚至是写作生活让她重新在往日和现实中获得了感动。我感谢人们对我这本不成熟的书的关注甚至是肯定,我也深知这本书因为带有了“第一次”的性质自身不可避免的缺憾和问题。尽管这本书罗列了643位70后诗人的名录,但是我在近半年来翻看杂志的时候仍然看到了一些我所陌生的但是诗歌写作确实不错的同时代的诗人,可能他们的写作时间较短,在刊物上“谋面”的机会不多,所以这也是我不小的遗憾。当然也有一些同为70后的诗人为未能进入这本书而对我心存不满。这就是文学批评的矛盾与尴尬,而历史叙事总会呈现出一些人,也会同时在减法规则下“湮没”一些人。实际上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让那些正在坚持诗歌写作的70后一代人对自己的生存背景、历史记忆、写作状况和精神图景有一个初步的整体性的认识,能够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一代人包括每个个体写作的特点和差异,能够让这一代人在纷繁的后社会主义时代不仅能够坚持写作,而且能够拿出成色够好的文本给读者甚至留给将来的历史。至于这本书自身的不足我想今后的相关研究会很好地弥补它。
杨庆祥:我还是从你这本书的几个关键词谈起吧。首先自然是“70后”这个核心概念,一般来说文学史上对代际的认定是非常严格的,比如必须有稳定的创作队伍、有独特的审美理念、有重要的经典(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埃斯卡皮认为一个站得住脚的作家应该在去世20年以后还没有被遗忘,这是一种时间上的限定了。在你的著作中,很显然你都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进行了大量的界定,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在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的时候,你最不放心、最没有底气的是哪一方面?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你觉得70后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思潮、现象、群体等等说法),它最容易被人“证伪”、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在哪里?
霍俊明:关于代际概念和相关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事甚至已经成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显豁的诗学话语方式,关于代际命名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我想包括韦勒克、沃伦、埃斯卡皮、刘晓枫、刘再复等人都有非常精彩然而又各执一词的阐释。实际上包括“70后”在内的代际概念作为一个诗歌群体甚至诗歌流派都不能不呈现出巨大的悖论和文学批评界自身命名的乏力和面对着纷繁的诗歌写作现象和现场的无以置喙之感。我曾经在最近一期的《星星》诗刊上有一篇关于诗歌命名和代际概念的文章《“朦胧诗”之后:错乱的诗歌史命名》。从“朦胧诗”这个意味深长的带有强烈的历史问题的诗学概念起,此后中国诗歌界的批评与命名就陷入到极大的错乱甚至是无力之中。我粗略估算了一下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给1978年以来的中国诗歌写作命名了不下60个诗歌概念,而今天看来它们大体都是短视、短命和失效的。而“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新生代、第四代、中生代、70后、中间代、新世代、晚生代、“85一代”、80后、90后甚至“00后”都呈现了研究者们投机取巧的平庸和无奈。实际上我在写作《尴尬的一代》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长时期处于困惑之中,以什么视角和方法来呈现一个代际概念和相应的写作事实一直在困惑着我。甚至我们一直都听到有些诗人和批评家对代际研究的不屑一顾。我想更为值得反思和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代际研究就不能具有自己的合理性和文学研究价值呢?我想人们对“70后”和我这本书存在的一个争议就是认为70后如此庞大的一个诗歌群体他们的写作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如果光以一个时间性的代际概念来整合和分析肯定会有不小的问题。但是我想人们可能忽略了我这本书的副标题“中国70后先锋诗歌”。之所以如此,我正是在回应人们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对“70后先锋诗歌”有一个特殊的界定,而这就与泛泛的更为庞大也更为庞杂的“70后诗歌”群体有了差异和比照。换言之,在我看来一些很早就进入了70后的相关诗歌选本甚至在诗文学刊物上频频露面的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不具备“先锋”的性质而被我搁置。实际上“70后”无论是从早期的带有明显的抢占和焦虑性质的文学登场,还是作为一个代际概念甚至是像黄礼亥早年所称的一个诗歌流派确实带有着两重性。因为代际概念强调的是同一性,但是事实上我们无论是面对当年的“第三代”还是今天的“70后”和“80后”他们的个体写作的事实是明显的带有不可辩驳的差异性的。这就会引起人们“证伪”的冲动,既然写作存在差异那么笼括性的取消差异的代际命名和话语方式很明显带有不攻自破的矛盾性和自我否定性。这种长期以来对代际命名和评论的“证伪”不可否认肯定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但是我想我在《尴尬的一代》中所能做到的一点就是要强调代际命名的不可证伪性和自身的合理性。在这本书里,我能做的并不是大而无当的整体性、归纳性的诗学报告,而更多是一代人犹如胎记的历史境遇和思想印痕。尽管我在这本关于70后先锋诗歌的系统论述会中会反复强调每一个诗人不可规约的写作个性和各自不同的写作方向,但是作为一代人,一些共性的关键词还是在我个人的思考中以强烈的历史性作为思想史而不单单是诗歌史最终袒露了出来。就70后诗歌而言无论是男性诗人还是女性诗人,无论是面对城市还是面对城乡接合部和乡村,是面对现实、历史、生存还是知识和经验都在写作个性之上呈现出了强烈的普遍性特征,比如焦虑、尴尬的两难、漂泊、外省、广场意识,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等都有着一代人的共性。换言之,这一代人在诗歌的语言、结构、技巧和想象力以及先锋的探索性上都是在一代人共有的经验和历史背景上展开的,正如我们所烂熟于心的那句话,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一条路一样。基于此,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底座,在看到一代人丰富多样的充满了个性化言说方式的前提下我更想看清的是一代人带有共同精神履历的历史面影和一代人不无尴尬的隐忧和灵魂。
杨庆祥:在你的著作中,与70后这个概念一样,“尴尬”也是一个核心的概念,而且实际上构成你整个论文的逻辑出发点,这可以说是一个创造。在我的理解中,你是把“尴尬”这个词放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概念中来进行界定的,比如“乡村”和“城市”,“故乡”与“外省”、“个体”和“集体”,在这种情况下,“尴尬”就是一种身份意识、审美观念上的不确定状态,一种犹豫和游离,那么我感兴趣的是,“尴尬”到底有没有一种自主性?它是否可以跳出那些“二元对立”的界定而自己生产出意义?并进而为70后的诗歌美学进行命名和概括?
霍俊明:我想我并没有将“尴尬”或为了突出“尴尬”性特征而有意设置二元对立的方式,我更想做到的是一种比照或互文性的呈现,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故乡和外省,我想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都是以相当复杂的视角来审视的,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尴尬”在我看来正是这一代夹缝中生存的显豁征候和身份烙印,但这并不是说“尴尬”也一同导致了诗歌写作和审美观念的游移和不确定状态,而是恰恰相反。这种“尴尬”作为一种自主性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代人诗歌写作的理想,也是这一代人的现实和写作背景的直接显现。在70后这一代人不乏戏剧性的登场中,在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纠结的时代氛围中,我注意到了这些“红旗下的蛋”集体尴尬的身影和一颗颗永远追寻又似乎永远无所适从的灵魂。我发现在这一代人身上,普遍有一种对广场等宏大的集体或政治事物的疏离、不屑一顾甚至反拨,在这代人身上,革命、政治、运动的“广场”和“纪念碑”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但是这股烟云作为潜意识里一种病灶,却时时刻刻在血液循环并发生着足以致癌的基础效应。无可辩白70后一代人无论是在历史遭遇、生存经验乃至诗歌写作都呈现出显豁的“尴尬”特征。这种尴尬性给他们的诗歌文本带来了无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杨庆祥:你提到70后的时候,实际上也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整体中的差异性,而且你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差异实际上也就没有整体,这两者是很辩证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你把1976年作为70年代生人的重要节点,为什么是1976年?或者说,你觉得1976年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何在?仅仅是“文革”的终结吗?仅仅是阅读谱系的改变吗?你这么处理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经验?
霍俊明:70后诗人内部的生存体验、精神型构,外部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尽管是大体一致的,但是70后的内部仍然充满甚至掺杂了两个甚至多个声部。分割这两个声部的年份大概是1976年,1976年明显属于加上着重号的一年,显然带有历史节点的性质。实际上,80后诗歌同样如此,不是有人将1985年作为这一代诗歌写作的分界线吗?在研究70后诗歌的过程中,我甚至有将1977年至1979年出生的人划入下一代人的冲动。因为在我看来同样是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稍后出生的一部分诗人,他们在作品中所陈述、表达的心理特征、文化、社会背景、写作精神却与稍前几年出生的诗人有着不可否认的一些差异和不同。在我看来出生于1970至1976年间的诗人较之1977年后出生的诗人显然要更为复杂也更为沉重,历史无意识的呈现更为突出。在他们身上具有一定的“60”年代出生诗人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和红色历史的集体情结。这主要是因为文革后期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教育等强大的带有宏大的集体主义色彩的影响甚至是负面伤害都相当有力的在70后一代的生活、思想和写作上留下了永远难以消泯的时代符码和沉痛印记,而这种时代符码和印记更像是纪念碑在广场上投下的巨大阴影。尽管因为年龄的原因对于文革不可能有多少感同身受、刻骨铭心的像第三代诗人那样的记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革语境对于这些70年代初、中期出生的诗人而言,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在此后这代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这种影响的遗传因子时不时的甚至相当强烈地呈现出来,无论是在生活、学习还是在写作当中无不如此。换言之,1976年之前的一代人承继了前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所以这代诗人的写作照之第三代诗人、中间代诗人和80后诗人而言,都显得那么不够纯粹,照之此前要么政治、运动到底,照之此后要么娱乐至死、要么时尚前卫的精神,总是令70后诗人欲言又止、遮遮掩掩,来不得全面的皈依、解放或是放纵,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状态。基于此70后一代诗人,尤其是1976年之前出生的诗人不能不处于政治话语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巨大影响之下。广场上狂欢的巨浪、亢奋而盲目的激情,翻卷不息的手的海浪和绿色军装、红色旗帜的波涛,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铺天盖地的豪言壮志注定没有随着1976年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记忆与胎记。尽管可能这种红色的记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已经遭到了他们的质疑甚至一定程度的颠覆。所以无论如何70后诗人集体主义特征的成长背景已经成为永远不能抹掉的“虚幻之门”。政治狂欢的年代结束了,集体主义的农场和村庄消失了,疯狂奔跑的红色卡车瘫痪了,然而这些都一起作为70后一代人的整体性胎记都如冰冷的黑夜里的那只幽灵一般的“红色田鼠”钻进了血管、融入了血液。不管你在生存的路上是迎合还是拒绝,政治年代的晚照和集体教义的时代阴影都牢牢地印刻在你的灵魂深处和生活的细节当中,而这一切在此后商业社会中不能不以最为尴尬的状态呈现出来。70后尤其是1976年之前出生的一代人是名副其实的“红旗下的蛋”。
杨庆祥:我还想和你讨论诗歌史写作的一些问题。我记得你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新诗史写作的问题,你对建国以来中国新诗史的写作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学理化的梳理,并提炼出了一些不同的写作范式。在我看来,你的这本著作似乎和你以前归纳出来的那些范式都不太一样,既不是非常随性的,即兴式、印象式的点击和鉴赏,也不是非常严格的学术化的考量,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既有资料的收集整理,也有诗人诗作的分析批评,亦有对文学史的周边,包括历史语境、生产机制和文学场的分析概括。这种杂糅式的写作方式形成了一个“复调”意义的文本。我不知道你是否对你的这种写作方式有一种自觉的考虑?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
霍俊明:我曾一次又一次想到了马尔科姆·考利和他为同代人和自己所撰写的影响深远的《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文学流浪生涯》。而考利所做的正是为自己一代人的流浪生活和文学历史所刻写的带有真切现场感和原生态性质的历史见证。我想我应该做的也是一个类似的工作。那纵横交错的原野和地层下的河流与岩层正是我所要勘测和挖掘的,尽管这种勘测和挖掘只是初步的。《尴尬的一代》确实是我有意为之的一部带有个人性的断代诗歌史写作的尝试,但是它的整合方式、历史构架尤其是叙事方式明显与我们所熟悉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写作有着很大的区别。我更想写出的是一部不仅有着历史框架和脉络,而且更想写出“有血有肉”的见证和细节式的新诗史。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很长时期内成为集体性的一哄而上的配合各种教材和教学科研任务的相当浮躁、粗糙、浮光掠影的文本,这些文学史除了在不同时期和板块中填入诗人、作品和简单的评价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甚至这些集约化的历史呈现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的原貌,尽管我们并不能完全的呈现和复原历史。我曾长时间沉浸于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大量的、华采的、美仑美奂的散文诗般的带有修辞性和想象性的散漫的文学史书写体式。这也引发了我关于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本体性思考,例如体例、叙述语言、结构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对于文学史写作的认知,文学史家长期是将其看得相当神圣而严肃,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体式严谨、书写规范的与历史联系紧密的“求真意志”的客观再现式的写作。然而文学的历史真实或原貌是否一定按照文学史家所设计的体系性和体例在写作中依次显现?答案显然不是。而当后设史学将历史著作仅仅视为一种由书写者写出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修辞性和想象性时,我们看待文学史写作也就不必定于“常识”。当文学史的写作被我们看成是一种普通的文本操作时,我们就有可能看到文学史的书写本来就不必拘于格套而应是具有个性丰富多彩的。翻开几百部现当代文学史,“复写”的痕迹仍相当明显,尽管著者有别但叙述方式、基本结构雷同,资料重复、评述相仿,结论也相差无几,它们最终呈现的文学史状貌也多大同小异。作为“70后”的同代人和诗歌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更想在文学史叙事中强调现场感和鲜活的资料的呈现。所以我想当年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而是以“史人”和见证人的身份叙述所经年代的文坛景像。《文坛五十年》由于是当事人色彩的见证叙述,就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家隔着遥远的年代仰视或俯视文坛的视角不同,而是采取了一种平视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使得曹聚仁笔下的文坛更为真切、平和甚至有些“闲话”色彩,没有一般文学史写作中的强烈的经典化和贬抑化的倾向。《文坛五十年》所叙述的历史对于当代人而言已经模糊遥远,但是曹聚仁带给我们的叙述却使我们相当真切地透过历史纷乱的烟云看到了一段文坛历史的鲜活细节和本真纹理,遥远纷繁的历史仿佛就在昨日刚刚发生。这不能不与曹聚仁作为见证人所不可取代的独特视角和真切体验有关。所以我更喜欢《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旁观者》、《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等这些带有个人性、现场感和见证色彩的“另类”的历史叙事。这些带有见证色彩并提供大量新诗史细节的新诗史著作显然作为一种个人化的述史方式参与到新诗史的构建。由于多为当事人的回忆和评说,所以在文体上更接近于随笔和回忆录,且因为明显的个人好恶和价值取向而引起关注甚至争议。当然如果以目前传统的对文学史著作的认识,这些是很难归入到文学史写作(“大历史”)当中去的,但这些带有见证色彩的边缘化的新诗史叙述看作新诗史也自有其道理。这些细节新诗史的写作者基本都具有当事人的亲历者身份,对于各自的那段新诗发展历史也较为熟悉,他们提供了很多一般新诗史写作和研究中没有提及的重要历史细节和相关资料。而这些新诗史著作由于与教科书和正统新诗史写作大有差异,所以它们的面目都呈现出了日常的、芜杂的、丰富的、散漫的、质感的、细节的、鲜活的、生动的、跟踪式的特征,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得以凸显。这些另一类的或边缘的新诗史叙述,大都是由对当事人的访谈以及回忆文章组成,更像是回忆性随笔的结集或资料汇编。但是由于书写者都有着相当强烈的文学史意识,并且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被以往的文学史所遮蔽和遗漏的历史真实和一些细节,而成为带有边缘化性质的新诗史写作模式。这些细节新诗史尤为强调历史细节和见证者知冷知热的贴心式的呈现,从而使叙述带有真实的现场感和清晰可辨的细节化,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新诗史所不可能做到的。这些感性而生动的文字颠覆了以往历史叙述的条分缕析、体大虑周的叙述格局。这种开放的充满张力的冲突可感的文本,让读者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侧面,对被历史叙述中减法原则所遗漏部分的强调和重视。所以我想提供的也应该是一本见证式的“另类”的历史叙事。
杨庆祥:这几年我渐渐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充满了怀疑,一来是怀疑批评究竟与写作能否发生有效的关系,二是怀疑现有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能够建构出一个更具有历史感和意义感的文学史谱系。对当代文学史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严重,甚至一度有当代文学究竟能否写史的争论。当AI写作史有当代的有利之处,比如它的现场感和及时性,但也有不利之处,那就是在价值判断上往往容易受到自己以及社会环境的局限,不一定很准确。你的这本专著写的是最当下的文学现象,估计也一定受到上述问题的困扰。我在读你的这本专著的时候,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你投入了非常多的个人的感情,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自我建构的动机,这是无可厚非的,为一代人命名肯定要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如果你在写作的时候能够再拉开一些距离,把自我的历史同样放入一个对象化的位置来进行反思、重组和再读,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是不是就更具有“史”的价值?
霍俊明:我想“当代”写史和写作“当代史”永远都会因为时间性的问题和写作者的姿态成为聚讼纷纭的话题。新诗史写作由于都是“当代人”对前此或当下的文学史现象进行叙述,那么时间问题就是任何文学史家都难以回避的。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莱曼的调查认为由“历史记忆”(文学史,百科全书,教科书,学术论文等)所记住的作家,大概只占发表作品的人的百分之一;而“当代”(近30年左右)与过去的作家被记住的比例则大抵是一比一。因此文学史叙述的现象越靠近文学史家所生活的年代,就越有可能成为一大篇作家作品的目录。这无疑给“当代”写史提出了挑战。但是回溯文学史写作历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新诗的草创和发展,带有见证者色彩的批评性质的当代人写作的“当代”新诗史写作与研究也一直与之相伴而行,如闻野鹤的《白话诗研究》(1925年)、胡怀琛的《新诗概说》、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第四章《诗》(1929年)、草川未雨(张秀中)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1929年)等。值得强调的是写作当代史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上“宜”与“不宜”的问题,而是史家是否具有一种对文学现象进行历史观照和情感上、精神上的优势,也即他是否具备对历史进行合理审视的能力。所以即使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家或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的后设性叙述,也同样会遭受质疑。研究者通常是以当下的立场和现在所遵循的文艺或史学观念来反观历史,这些观念在现代性话语系统中自有其合理性。文学史的写作实际上是“历史”与“现时”之间相互往返的过程,既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又要从现实出发予以对历史的理解。实际上在写作《尴尬的一代》的时候我也确实准备了两套叙述话语,一个就是尽量客观的、中性的、审视的甚至是旁白式的写作方式;另一个就是目前所呈现的带有明显的个人化、散文化、情绪化的介入式的写作方式。但最终我放弃了前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前者的历史叙事会更客观也更符合读者对历史叙述的阅读习惯,但是我们司空见惯了那么多的貌似客观的文学史叙事,但是它们真的是客观和真实的吗?我想作为“当代人”写作正在进行的文学史现象,审视和积淀历史的时间肯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深处现场和当下的涡漩之中,很多现象和文本我们个人的认识肯定会有诸多缺陷甚至偏见,但是我想这些悖论性的问题正是写作当代史的“宿命”性伦理。在我看来既然当代人呈现当代史都很难说服当下的读者和研究者,很难不带个人情感的“意气用事”,很难做到所谓的冷静和客观,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用那种刻板的、僵化的、线性的毫无生机和生命感的干瘪说教式的写作方式,不如选用个人化的、情绪化的、散淡化的方式来呈现后来者所不能具备的现场感和介入式的体验。当然并不是说在现场和交往、介入中进行文学史叙事就不具备历史感。恰恰在我看来历史感应该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这种历史感的具备甚至一定程度的完善再加之鲜活的现场感和见证者式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更会以个性和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出历史的原生状态,也可能会更为传神的在某一个方面更为深入地呈现历史,哪怕这可能只是历史原野上的一个小小的地貌。
杨庆祥:最后我想说的是,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70后先锋诗歌(如果这个概念能够在文学史上立足的话)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作为一个整体缺乏意识形态的自觉,其二是作为个体还缺乏更“强力”的诗人,当然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也有的“世代”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然后就被历史“屏蔽”了,这是历史上常见的事情。当然这不是70后存在的问题,80后的诗人,还有即将登场的90后,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你似乎对80后有点偏见,这个偏见就像50后、60后对70后的偏见一样,我觉得都是没有必要的。我想你也一定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并一定会在将来的研究和写作中对此进行更有力的开掘。
霍俊明:时间是伟大的,写作有时候不能不是脆弱的。只有“坚硬”的诗歌和“强力”的诗人才能够扛住这个严峻的考验。我曾将70后一代人正在进行的诗歌写作比喻为一座生长着各种树木的森林,它们各自奇异的姿态一起呈现出这座森林的影像,在这隐现的森林中我在不同的树身上感受和觉察到一些共同的姿势和声响。在森林蜿蜒的小路上,我发现了落叶,发现了根须,也发现了新蕊;我发现了日益茁壮的物种,也发现了日渐萎缩的躯干。确实,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都要经受时间的筛选和历史的减法规则,曾经在各种报刊媒体上显豁的诗人最终昙花一现,也有默默坚持修成正果的“强力”诗人。在关于70后一代人诗歌的大量文本细读之后,我想无愧地说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差,相反我会相信注定在这代人中间会默默走出几个高大的诗人,虽然和任何一代人一样,可能是极少数的几个;不但如此,他们,她们,还最终会站在时间档案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实现自我的历史陈述。实际上我写作《尴尬的一代》的目的也正是要让这一代人正视自己的诗歌写作,能够在持续和坚忍中把诗歌写作作为一种信仰,因为包括70后在内为数众多的诗人将诗歌看成了名利场上的敲门砖,诗歌作为个人乌托邦似乎已经成为后工业时代齿轮和商业吧台上抬高的大腿们所不屑的“过时”的举动。但我们知道这种信仰对于诗人的写作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你说我对“80后”和“90后”可能存在着一些偏见,确实代际上的原因我可能曾经会认为这两代人从物理年龄和写作年龄上较短尚需时间的锤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这些诗人的文本阅读的理解我越来越对他们的写作刮目相看,因为他们的写作照之“70后”可能更为自足、更为纯粹,甚至在语言和想象力上他们更为出色。当然这两代人的写作也有自身的问题。我希望作为一个诗歌阅读者和批评者我尽量减轻我的盲视。最后谢谢庆祥,占用你这么宝贵的时间,冬天的这次谈话我们无比贴心。谢谢!
标签:70后论文; 诗歌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写作细节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