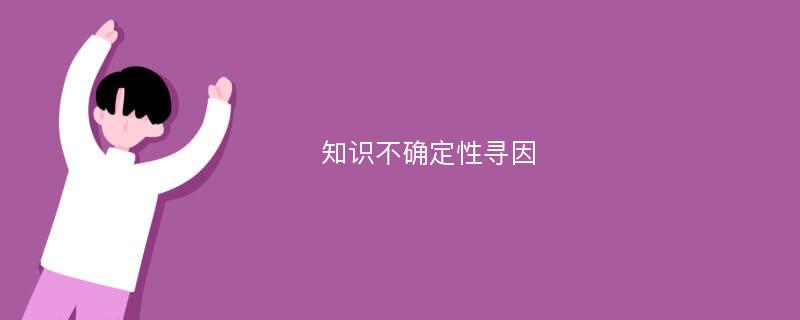
知识不确定性寻因
胡 潇 李金梅
内容提要 不确定性问题,久为哲学家们关注。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90年前由海森堡在其量子力学中实证性地做出了研究和说明,形成“测不准关系”的著名命题。此后,它日益广泛地为不同学科采用并不断延伸。今天,这一问题已多维度地溢出量子力学世界,进入众多科学领域,并与上世纪后期兴起的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发生对接,用以说明日益增多的社会行为不确定性现象。这使传统哲学关于必然和偶然,进而决定性与随机性、认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等范畴理论有了新的变革。在对实际生活的不确定性解释中,添加了一种自然与社会贯通、不确定性的认识与认识的不确定性理论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的思想景观,这为人们积极探索、妥善处理知识不确定性问题产生诸多助益。
关键词 不确定性 认识论 归因
不确定性理论源出于量子力学中对量子运动认知的不确定。这一现象的理论概括是1927年3月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一篇《关于量子论的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觉内容》论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微观世界具有一些不确定的关系,一个微粒子的某些成对的物理量,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时间与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测得愈准确,另一个量的误差愈大。而对于这些物理量分别进行测量时,则可以得到精确数值。这一理论显然构成了对经典物理学解释范式的根本性挑战与解构。在经典物理学中,宏观物体的运动可以用质点的位置和动量精确描述。同时测定了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就可以预言之后其运动在任意时刻的位置和动量,从而描绘其轨迹。而在微观物理学中,如果要更准确地测定质点的位置,那么测得的动量就可能更不准确,因而不可能用轨迹来描述粒子的运动。这是不确定性的原初意义。
但对于微粒子某些成对的物理量之不确定关系,以及由此做出的不确定性原理之概括的根据,又界说各异。有些学者认为,不确定关系是微粒子的存在方式即“波粒二象性”的必然结果,为存在论命题。另一些学者认为,对微粒子某些共轭量不可同时测定,是由于观察仪器、活动对被测量对象的干扰,影响了其本真态,因而无法与其他相关量被同时测准。海森堡认为:“在原子物理学中,观测者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引起受测系统不可控制的、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够将一次观测结果完全客观化,我们不能描述这一次和下一次观测间发生的事情”。①这深刻而多方面地涉及观测主体、仪器与对象之间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故不确定性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它们成为不确定性理论的初始叙述。而当量子力学揭示的客观事物现象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被人们转换成从主体对客体所施干预而形成认识不确定性的知识论命题时,不确定性问题在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的深化与拓展中,向更多学科与实践领域扩散。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出版过《确定性的终结》等一系列著作,系统深入而卓有创见地探讨了这一问题。甚至连最讲究精准性的数学研究也深刻触碰到这一问题,美国数学哲学研究者克莱因于1980年出版了《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从数学与物理、逻辑与直觉的可变关系中系统解释了数学确定性的诸多困惑。当代高新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双重推动,人类的认知因素通过科学技术广泛深入地介入社会生活,主体精神力量的任性实践加剧了客观事物运演的摇摆与动量涨落;全球化进程的急剧提速,亦使社会冲突泛化、激化,焦点转换迅速而风险加大。因之,不确定性问题频繁出现在社会行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中,客观事实倒逼认识论,日益强烈地要求人们从哲学视角来审视不确定性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因而,从认识论角度关注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无论对于顺应社会变迁而调适、优化认知方法与行为方式,还是助推哲学理念的变革和思维范式的创新,都是一件充满时代气息的大事件。
主客体互动是知识不确定性的始因
知识是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的结果总和。关于知识不确定性的研究,必须在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论探讨中实现。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强度改变着客观世界,把人的主体性力量深深嵌入对象世界中。物质世界更多方面、更深程度地丧失了它的天然性。因而,我们更需要秉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主张的,对环境、现实、客观对象的理解,必须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对象,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主体性理念。②同样,科学技术广泛深刻地介入认识活动,影响认识对象的持存与呈现机制,造成了大量测不准关系。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也更需要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关于在对象的本质力量与人的本质力量相互作用、彼此建构、互相规定中考察认识活动主体性的思路③,去进行不确定性问题的认识论研究。值得欣慰的是,复杂性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以科学事实深化、丰富、实证了马克思上述的元哲学理念。对象事物的不确定性,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理解,除了它有类似于微粒子运动那样一种天然的波/粒二象性的原始内容之外,还有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随机性。量子力学揭示的“测不准关系”,除了因微粒子本身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存在论特征外;还在于认识主体及观测仪器对被测对象本真态的干扰,导致所测结果的部分失真、失准。后者蕴含的认识论意义,从哲学界面更广泛地引发了人们对观测对象并非纯然客观的理解。可以逻辑地认定,马克思1844至1845年提出的关于对象世界的主体性理解的深刻思想,是对后来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理论的先见或哲学预兆。而复杂思想则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把马克思揭示的关于认识对象主体性解释的理论,进而对主、客体在认识中的相互作用关系之焓变性、非恒稳性,给予了当代版的深入阐发。
复杂理论的系统阐发者莫兰认为:由于主、客体的辩证互动及其相关律,“世界处于我们精神的内部,而我们的精神又处于世界的内部。主体和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是建构者。但这并不导致一个统一的和谐的观点。我们不能摆脱普遍化的不确定性的原则。如同在微观物理学中观察者干扰着对象、对象干扰着观察者的知觉一样,对象的和主体的概念同样地互相干扰,每一方都在另一方中打开一个缺口。我们将看到,在主体和环境的关系中存在着根本的、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只有关于对象的实在性或主体的实在性的绝对的(也是虚假的)本体论的规定能够了结这个不确定性。从主体和对象的复杂的关系中,也从这两个概念的不充分和不完整的特性中,一种新的观念涌现出来。主体应该保持为开放的,在它本身不具有决定性的原则。对象本身也应该保持为开放的,一方面对于主体,另一方面对于它的环境。而环境也必须是自我开放的,在我们的知性的认识极限之外继续自我开放。”“这种概念的局限性,这种本体论的裂缝,这种客观性,决定论的倒退,似乎作为第一个收获带来的是认识的普遍倒退,不确定性。”④
认识为何向不确定性倒退呢?因为在人所处的世界中,“主体是与世界同时涌现的。它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出发点涌现出来,在那里某些人类主体特有的特点(目的性、程序、通讯等等),被包含在对象—机器中。它特别从自组织出发涌现出来,此在那里自主性、个体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多义性变成了对象具有的特点。在那里尤其是构词前缀auto(自我),在其本身中携带有主体性的根基。”⑤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主张,不仅主体、客体是相互开放的,一方作用于对方的同时接受着对方的作用,在自我规定的同时包含着与对方的相互规定,因而它们都不是单纯自足的;而且,主、客体还与其所处环境相互开放并彼此互动。因而单纯主、客体是不存在的,主体不能在自为的意义上自外于世界、社会、他人;客体不能在自在的意义上孤立、独存、自绝于主体和环境。主体把自身不确定的作用加予客体,引发和加剧客体的不确定性;客体之间、客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成的不确定性又反馈给相关主体,也培育和强化了主体及其认知的不确定性;最后,是在这一系列不确定性的联动中构建和激化了主、客体关系的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些互动、复合的不确定性互关律,莫兰认为不确定性既是由主、客体互规定机制造成的,反过来,它又分别给主体、客体的性状及其界说、理念以不确定性的规定。它使那种只是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对象或主体的概念成为不完满的概念。“纯粹客观的世界的概念不仅被剥夺了主体,而且也被剥夺了环境、超出它的东西。从而它变得极端贫乏,关闭在自己本身中,只建立在客体性的公设上,被不可探测的空虚所环绕。同时在它的中心——应该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思想的地方,存在着另一个不可探测的空虚。主体的概念的状况是:不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极其渺小,就是在超验的层次上过度膨胀;现在轮到它失去环境,在消灭世界之后自我封闭在唯我论中。”⑥这些论述似乎在主、客体关系中表明了一种机理性的反讽:不确定性的关系才可能是确定的。离开主、客体及其与环境之间多变的互动关系,不啻说客体无法认识和被理解,而且作为认识者的主体自身也将无法认识和被理解。他们既有沉入经验世界而失去“自性”即丧失其内在统一、组织和秩序之原型的危机,更有因脱离经验世界、主观极度膨胀,最终失却其本真而无从自持与把握的危机。这样,主、客体双双陷入神秘的不可知境界,成为无规制的不确定性事物。事实上,主体对自身的认识论确证,不能脱离主体所处环境和面临对象及其作用的受动性考察而完成。因为“考察社会环境系统对我们的影响使作为观察者的我们与我们自身拉开一定的距离,亦即从外部看待我们自己,把我们对象化。这同时意味着认识我们的主观性。”⑦人的自我意识,从来都只能是对象意识、环境意识与主体意识的涵化、复合与结晶。主、客体及其环境在实践生活中的相互规定,派生也隐匿着一条对象意识、环境意识与自我意识相互建构的秘道。诚如马克思说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因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⑧不仅主体、客体、环境的事实关系制约着主、客体各自的确定性,而且三者相互建构、规定的情形之具体变化,以及主体对这种作用机制的测度和理解,还会多方面地影响主、客体及其关系的确定性,使之带来由诸多元素相互作用、随机生成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基于这诸多致因生成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思想认为,“偶然性打开了人类精神面对世界现实和面对它自身的现实的不确定的难题。昔日的决定论是对现实的本性的本体论的断定。偶然性则只是引进了观察者对现实的关系。昔日的决定论排除组织、环境、观察者。被丰富了的有序概念和无序概念彼此相互引进。它们两者都要求科学少简化一些和少形而上学一些。”⑨由此可见,复杂性思想对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分析,进而对必然/偶然、确定性/不确定性关系的深刻解释,必定多方面地延伸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人们对于决定论/必然性/确定性,与非决定论/偶然性/不确定性,以及两系列范畴关系的理解,出现了由传统到当今的认知—思维范式的创新性发展与历史性转换。这种关于主、客体及其关系的认识论复杂思考,很吊诡地表明了一种不确定性思维的狡黠:确定性关系存在于不确定性关系中,只有经过对不确定性关系的探察和说明,才能形成对确定性的理解与把握。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页。
关于人与对象世界的相互建构,我们必须区分人为过程的作用机制与自然过程机制的不同特点,关注两者互动的合力效应。总体来讲,人为过程是追求决定论的和可逆性的;自然过程则包含着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基本要素,具有丰富的、自发的活性力量。这一方面,是自然以其自在的可变性影响着人对自然的认识与实践关系;另一方面,它又能以自变与因变的方式承受人类的作用,形成自然回应于人的“生动对话”。基于这种主体与对象、环境之间复杂的物质、能量、信息变换关系,今天人们的认知“兴趣正从‘实体’转移到‘关系’,转移到‘信息’,转移到‘时间’上”。人们关注世界的方式与内容,以及对待世界的总体态度,有了诸多的随机灵动,放弃了以往的那种机械与刻板。对人为干预认识对象所造成的认知的不确定性给出的解释,使认知主体面对着一种地位推升和理性贬抑的悖论:一方面强调认识的主体性,极端重视人为影响对认识过程及其知识结论的作用,并把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为科学活动的中心环节对待;另一方面,又在充分估量认识主体性意义的同时,弱化了认识的客观性、实在性、真理的绝对性与稳定性,使认识的结论处于认识主体之干预客体这一前设的逻辑证伪之中,增加了主观任性、非恒稳性和不确定性色彩。就像普利高津在“终结确定性”的讨论中对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做的结论那样:“纳巴科夫的信念仍然正确:‘凡是能被控制的决不会完全真实;凡是真实的决不会完全被控制。’”以操控认识对象的胜利,换来认识失真的回馈。成败、得失之间,全在于主体性!
知识不确定性的文化致因
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通过对量子运动不确定性的说明,揭示了认识不确定性的主客体互动的始因。虽然它的解释很到位,但并没有从主体侧把导致认识不确定性的众多原因引入视域。从认识的主体性而言,即使在非量子世界,因为主体始终处于向现实、向社会、向历史高度开放的态势,主体外的各种因素作为认识客体的旁系力量不断嵌入认识活动中,不断刷新认识者的主体性,影响其作用的具体发挥,从而在直接的主客体关系外大量生出认识不确定性的致因来。它们的作用机制是研究认识不确定性需要深刻关注和说明的。
①转引自李庆臻编《简明自然辩证法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谈到认识的主体性时,费尔巴哈曾给出了一个双重自我的说明:在思维中我与自己同一,我是法官又是诉讼人,是绝对的主体,不容异己;反之,“在感官活动中……我容忍对象像我自己一样,是主体,是实在的,自己活动的实体”。他把现实存在这一有众多他人参与其中的对象世界,当做有“主体性”意义的事物,即表明自我向对象世界的开放,对自身釆取一种接受、容忍对象事物给予刺激、制约的受动性立场。正是这样一种感知的开放性,让主体的认知必须承受现实对象本身不确定性的制约。对象事物不是线性持续运动的,不是单向守恒的,它有非对称性、非一贯性、非周期性等多相性特征,要求主体对其多相进行选择和研判。这一智慧焦虑过程将会因为主体内在性因素的紧张调动、内在尺度的大量比照而激发自身的多元文化要素非齐一地参与其中,从主客体之不确定因素的互动中加剧认识的不确定性。恰如美国关于知识不确定性的研究者沃勒斯坦所说:“如果现实是不确定的,那就不得不进行选择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那分析者的价值取向、偏好、假设等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分析过程了。我们即使有意排除这些要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也会无意识地出现……因为无意识构成了分析家的灵魂。”现实事物有发展阶段性、随机性和展示的概然性,因而人们必须选择。选择和评价难以价值中立并一以贯之,主体有目标预设、知识背景和好尚诉求,它们往往以沉入无意识深处的隐性文化力量左右主体的选择、评价和取舍,并且常常是以随机而发的应激行为方式无序地表现出来,形成人在认识中难以觉知和自控的主体性。这些又再次构成难以数学化计量的主客体关系非对应的混沌性,而导致认识的不确定性。人们在不确定性的认识论研究中发现,正是因为认识主体的这种文化多样性、思想差异性,决定着人们在认识世界时总是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且能够看到的东西,而不一定都是主体理解和把握对象事物需要人们如此去看到的东西。因而认识具有强烈主体性造成的“人差”现象,以致同样事件在不同主体那里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论。这些结论不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在特定时期内其真理性是很不确定的。而认识主体这些方面思想和行为的难可控、不确定性,随着认识的拓展与深化会以十分复杂的作用机制反馈于对象世界,更深层次地引发主客体互动的复杂性而导致认识不确定性的强化。如人们在对环境科学反思中所发现的,“由于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以及自然环境和人类对它施加影响之间互动的高度复杂性,环境科学的不确定性被加强了”。就此而言,人类因主体不确定性带来的思维非至上性,与事物发展要求非对称的局限性,以及实践验证的非现实性,都从不同方面给认识带来了不确定性。这样,“关于人类,决定论无情地宣称:不存在自由意志。人的意志受外部物质和生理原因的支配”的机械决定论及其认知确定性的理念,都是站不住脚的。“鉴于不确定原理,因果性和决定论变得无意义了。”这是承认知识的不确定性,必然向传统科学观的确定性、决定论发起的挑战。
2.主体的社会品格制约思想方法和认识定势,催生知识的不确定性
四是在情境化的认识中,知识、理论与思想的共识往往是短暂的,这降低了认识的可靠性和主体的坚定性,强化了认识的随机性、从众性和应景性,不确定性因此大增。瑞士的知识社会学家海尔格发现,在科学研究中人们达成的某些共识,“只要这些共识是临时的,它们的可靠性就会降低,但是降低到何种程度,并且以何种方式降低,都无法确定。科学共识的变动来源于科学的暂时性(也可以说是科学的不可靠性),这种暂时性反映出科学的动态特征,反过来,动态性又反映了科学对自然与社会世界的更深刻理解,这种理解本身就是可靠性业已提高的一种形式。但是,在共识的广度和可靠性的深度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可被说明的关系,尽管按照学科划分进行的研究,本质上并不更加可靠。”虽然,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和确定性不能靠主体的共识来维持和保障,但认识主体的共识却能在认识对象、方法、结论的一致性研判中深刻而广泛地影响认识的确定性。所以,共识的短暂而不稳定,既是认识不确定性的情境化致因,又是认识不确定性造成的情境特征,其内在的互动机制尤需关注。
太和医院在规模、技术、人才队伍等综合实力方面,当属鄂西北地区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而且,经过多年经营,医院也是周边地区急危重症患者就医的首选医院。
人们在科学的反思中发现,认识的“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科学和社会之间高速互动的必然产物,正在不断加强;的确,不确定性可以说是现代性在现阶段中的标志”。当代社会的认识与实践,各自既有自变与因变双重的不确定,又共为不确定性的复合体。一方面,人们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支持下,实践更多地成了科学技术行为,社会和自然的现实成了科学技术的造物,这使认识的不确定性转换成了现实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反过来又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影响认识主体,形成新一轮的认识不确定性。故而主体向社会开放的过程,在特定意义上成了不确定性在认识和实践中循环往复的过程。以致人们要探讨和排除认识的不确定性,就是要切断不确定性的循环链,把对社会、现实的不确定性研究直接当做科学技术的反思,直接从认识中揭示和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要有效地展开这一工作,必须在承认主体与社会相互开放、彼此互动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让认识主体从社会纷扰中超拔出来,维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品格,以客观、冷峻、独立思考的态度去接近现实,发现真理。人们普遍认为,“学术自由首先是去探索、发现和坚持真理的自由”。科学研究者对学术事业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越是不断增强,他们在科研中就越能选择和坚持特定的路径、立场和方法,而不必顾及任何权威的干预。任何理论都非尽善尽美,但并非可以将所有命题、理论都理解成同等合理或不合理的。这要求科学探索者秉持严格的是非标准,机敏的好奇心,不避艰险的求知动力,强烈的批判意识,大胆地主张所是、攻击所非,在众多求是剔非的努力中增进认识的确定性和真理的客观性。作为科学殿堂的“大学在社会中受到敬重,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严肃’、根本问题的知识得以发现、阐释和教授的所在。它们还由于一个循环过程而受到敬重,因为它们是与权威和正义、秩序、生命、死亡等‘严肃’问题紧密相关的专业和职业的源头。”基于此,我们在反思认识的确定性时,一方面要看到社会对认识活动的影响,它们形成了“动机性的或构成性的意见”;另一方面要看到科学研究的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它们“是人们对各种整体所形成的推测性或解释性的观点”。对两者我们应仔细区分,才能既清晰意识到认识不确定性的社会原因,又寻找到一条走出困境的主体性之路。
3.认识的情境化加剧知识的不确定性
[瑞士]海尔格·诺沃特尼、[英]彼得·斯科特、迈兜尔·吉本斯:《反思科学》,冷民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204、149、203、192页。
一是科学探究中,“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植根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各种前提和偏见,而这些前提和偏见会干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中立的’学者。我们也同意,对社会现实进行照相式的再现是不可能的。一切数据都是从现实中挑选出来的,这种选择要以某一时代的世界观或理论模式为基础,要受到特定群体所持立场的过滤。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的基础乃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因而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我们所说的客观性是指绝对中立的学者再现了一个外在于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这一人尽皆知的事实背后,便深深藏匿着包括社会认知在内的知识不确定性的致因。无论是历史建构的认识前提或选择基础,还是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深刻制约认识能否稳定推进的因素,本身都是不断变化且难以确定的。它们的不确定性从社会文化情境方面,必然给人的认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即使是非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也概莫能外。科学史上经典力学的决定论受到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学说的挑战,并且后两者也是在长期的论争中才得到科学界的确认,其漫长认识过程无不是在社会文化思想的僵化和变革的激烈斗争中完成的。科学研究中谬误的维持和克服,真理的发现和确证,总是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更新,是认识和社会情境双重不确定性交互运动的过程和结果。
(3)另取0.1 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2mL,滴加2滴1%的酚酞溶液,用水稀释至20mL,将0.1 mol/L的盐酸改为0.01 mol/L的稀盐酸重复上述实验操作,直至溶液的pH为2.00为止,用蒸馏水冲洗pH电极。
由图4可知,漂烫温度与冷冻时间交互作用无显著性关系,漂烫温度和冷冻时间对脆度和含油量影响较大。当漂烫温度与冷冻时间大于90 ℃和2.9 h时,产品标准化综合得分降低。
[美]M.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4页。
三是认识的情境化、语境的历时性演绎,需要特别关注,即社会知识的高度不稳定性。在这方面,诚如哈耶克所说:“指导任何人类群体的行为的具体知识,从来就不是作为一个稳定而严密的体系而存在的。它只以分散的、不完美和不稳定的形式,存在于众多个人的心智中,一切知识的分散性和不完美性,是社会科学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经常作为‘仅仅’是人类心智的不完美因素而不屑一顾的东西,在社会科学中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事实。”人们的社会认知,之所以如此难以确定,就在于它们难以获得自然科学那样一种超越利害关系的公允性。社会生活本身是由各种权益关系建构起来的,对于社会的真善美规律和价值的探究、诠释、确证,从来不能超越利益关系,认识的确定性直接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利的制约,走向真理的确定性十分艰难、曲折。同时社会生活及其规律以人的实践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认知是主体对自身认识与实践的自我意识。其中的主观性、“人差”性、价值冲突性等超不确定的因素难以排除和克服,其可逆性和证伪性等支持确定性的途径同样难以展开。再加上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恒稳性弱,社会认知的不确定性必然大大超过自然科学。
认识的不确定性在主体侧因开放而致,也来自主体对社会的开放,主体受到社会的诸多规定。而且社会情势不确定,以诸多不稳定的矢量干扰人们的认识活动,引发对事物关注和探索的热情涨落、方向摇摆和意见分歧。认识论的研究者曾以理想主义的立场确认,知识是构成人类智慧的最根本因素,知识具有一致性、公允性,判断其真伪要施以实践与逻辑验证,而非立场取舍和好恶勘判。这种理性主义态度相对于真理客观性的最终确认,自然是合理合法的,但相对于认识过程和某些具体的知识结论,情形却未必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事物的秩序,知识场,权力,等等。它潜藏在我们通常称为知识的边缘地带……它是一股潜在的力量,使得概念的形成成为可能。但它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之外。此外,它不仅仅是人性的构成成分;在某种意义上,它决定了所有的人性,因为它告诉我们知识……我们所有人都置身其中,依靠它来了解关于任何事物的任何事情。”这种认识论的社会文化机制赖以发生作用的基础是:“人们根据信仰、传统、社会制度、权力机构、教育、政治、灌输、对财富和媒体的控制来安排自己的实践。人们通过自己的创造、犯错、沉思、发明等等来改变某些实践。”这就是知识不确定性之认识论研究和解析需要特别关注的个人与社会、认识与实践的多边互动关系。
生17:这道题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后面一个都与前面一个有关系,是建立在前面问题的基础上的,所以解答这类问题时我们要回头看一看已经求解的内容,从中获得启发.
Inclusion criteria:(a)age 22-45 years;(b)history of an active sexual life without any contraceptive measures for more than 1 year;(c)female partner with normal fertility;(d)provision of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1.文化差异加剧主体对不确定性现实所做选择的多样性,在主客体错位中孕育知识的不确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在强化主、客体相互作用,因而强化认识对象的主体性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客体本真态如实把握之非精确性的追问,进一步增强了对认识活动开放性、认识结论相对性的理解,亦即知识不确定性的理解。包括科学家、哲学家在内的人们,几乎形成了一种基于对不确定性原理的复杂思考而达致的共识:“自然界不可能听任摆布地说那些我们要它说的话,科学研究不是独白。”⑩“科学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的结果不可预知。”人们从认识活动中主客体的相互开放、相互作用、相互规定中,进一步揭示和理解了要真实地认识对象事物,必须认识到认识活动中人与客体的相互干预和搅动,必须认识到认识主体的地位、作用和文化规定性,正是这样一些复杂因素的多相互动,影响了认识活动及其知识本身的确定性。
③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129、127~129页。
④⑤⑥⑦⑨[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陈一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5、36、42~43、158页。
⑩[比]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1页。
[比]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3页。
在闽西北地区洋桔梗常见的病害有叶斑病、立枯病、霜霉病和灰霉病[5]。叶斑病用80%戊唑醇水分散粒剂6000~8000倍液喷雾防治。立枯病用3%甲霜·噁霉灵水剂(甲霜灵0.5%+噁霉灵2.5%)兑水喷雾。霜霉病可用增威赢绿杀菌剂+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连续喷施2~3次。灰霉病可连续喷施20%腐霉利400~500倍液,每5~7 d喷1次,连续2次。平时要加强通风,降低棚内空气湿度,减少类似病例发生。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5~156页。
[美]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8页。
认识论所谓的情境,是现实生活中各类背景、事件、人物、行为、环境、语境等因素的综合体,它是主体进行认识活动必然关注的一切条件。主体在认识中通过对情境的体验形成自己与环境关系的基本判断,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反馈,展开与情境的互动,与他人的对话,与语境的意会,使情境成为认识产生和主体理解、交流的背景、“前结构”、潜台词、中介等支持和规范系统。因而,情境不仅影响认识主体对客体的理解与把握,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主体对认知本身的自我研判和相互交流与理解。它不仅作为场所因素制约着认识的验证、确定性与发展,而且更会以自身的不确定性直接给认识带来深刻影响,衍生多重不确定性。人们在对科学活动的反思中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认识的情境化机制:“情境化依赖于科学家与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他者’之间的长期对话。这是多层次的。清晰的信息得以交流、诠释和再诠释,隐含的或尚未被阐明的偏好、需要和愿望也是如此。”科学认识中主体的相互对话,既是上下文历时态的言说,也是共时态的彼此争鸣,它们作为语境给认识造成深刻社会文化影响。尤其在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中,“为什么两个历史学家虽然拥有同样的材料却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们。……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其作者的个性,也取决于其宗教社会或民族社会环境。”认识论上的主体个性是个体社会化的特殊方式、特殊路径、特殊嵌入点造成的文化人格,它给诸多认识结论带来由情境—主体性造成的“人差现象”。它们在主体对大量问题追求共识的过程中形成彼此抵牾、相互疏离、缺少内聚力的非确定性。这类问题的诠释,有以下几个具体情境机制值得关注。
二是情境中内含的语境成分,它们以认识发展、传承的历时态机制,让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语境中积淀,以上下文叠加的方式嵌入认识活动与结果之中。尤其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的知识与行动之间的间隔变得如此之短,以至于人们再也无法从时间上或者从组织上把它们分离开来。相对于日新月异的创新,知识和行动的结合显得更加激进。这一结合造成两个结果:第一,过去科学创新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不再是未来的事件和遥远的预感,可以通过之后的调整来修正。现在,从新事物诞生的那一刻起,不确定性就内生于其中,成为一种即时的体验和瞬间的现象。第二,新事物—不确定性的即时性引发了人们的抵触情绪。”以上这样两种情境,既会加剧认识主体对不确定性的厌恶和拒斥,引发对它们的简单化处理;同时也会造成对认识活动与内容的不自信,加快试错的频率,造成认识的摇摆和应激反应,而增加其不确定性的几率。
M.克莱因:《数学与知识的探求》,刘志勇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
对于新型的设备的导入以及相关的技术的运用,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投入使用,推动施工现场的效率的提升以及要需要建立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培训机构和研发机构需要相关的技术人员对其新型设备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掌握其利用规律以及设备使用的最大化效用,在全面提升企业施工的工程进度和节省成本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也是对现场的施工人员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加强对相关的设备的技术参数方面的学习以及相应的规范使用设备的手法等方面的学习与宣导,让全员形成一种自主学习和自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升施工的工作效率和企业方面的效益。
[加]弗拉第米尔·塔西奇:《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蔡仲、戴建平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136页。
[美]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李家永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0、217页。
本次研究搜集所获数据均采用SPSS21.0软件实施统计学处理,其中的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分别以(%)和(±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取χ2检验,α=0.05作为其检验水准。
[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5、26页。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8页。
书须“善读”方有益。读书多不等于知识多,更不等于各方面能力都很强。一个人能力的提高,一部分得益于书籍,一部分得益于实践,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方法不对头,思维没跟上,日日与书为伍又何益?以为多读了几本书就可以包打天下,成为“万能之士”,那可真是冤枉了书籍。那种以为读了几本书就必须达到某种效果,万一不如意就迁怒于书籍的人,我看还不如别去读书——书可担当不起这个罪责。
作者简介:胡潇,1947年生,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金梅,1992年生,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