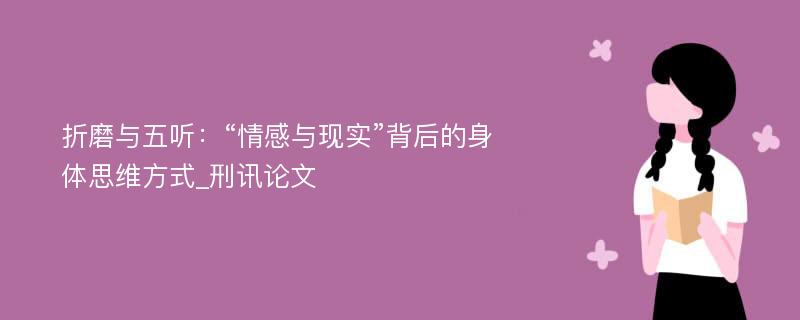
刑讯与五听:“情实”背后的身体思维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模式论文,身体论文,情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205(2014)03-0025-(010) 对于刑讯制度的荒谬洞识,再也没有像福柯所揭示的那样淋漓尽致了。福柯指出,刑讯是一种产生事实真相的机制,也是一种通过被告会说话的和必要时受折磨的肉体所呈现的司法仪式。在刑讯的拷问中,痛苦、较量和真理联系在一起,调查与惩罚交融在一起。值得玩味的是,人们怎么能够将一种惩罚手段当作一种证明方法呢?[1]38-51比福柯更早时期的贝卡利亚更是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刑讯从对真相的调查莫名地转向对被告体质和感觉的衡量,那么,一个数学家应当会比一个法官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他依据一个无辜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计算出会使他认罪的痛苦量。[2]37-38对于刑讯制度的存在,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追溯到古老的神裁法机制。 对刑讯制度荒谬性的批判,绝不仅是一二智者的洞见。问题是,刑讯制度长久诟病在身,却又能“金身不毁”。涂尔干说:人类制度是绝不能建立在谬误和谎言的基础上。那么,刑讯制度与加诸其身的毁誉长久并立,这是如何可能的呢?——问题的焦点是:刑讯通过制造身体的疼痛,却要纾解心灵的秘密,何以可能? 在古老的中国,五听亦与刑讯长久并存,并有论者认为其比之于夏商的神明裁判制度更为进步,而且认为它是现代心理学运用于司法实践的先声。[3]562-563 刑讯与五听,境遇尽管有别,但在中国法制史上却经历了类似的跌宕起伏。刑讯在制度上的明确废止始于晚清修律时期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该法第326条规定:“凡审讯一切案件,概不准用杖责、掌嘴及他项刑具,或语言威吓,交逼令原告、被告及证人偏袒供证,至令淆乱事实。凡刑讯逼取口供者,降格治罪。”这条规定亦得到了之后不久制定的《大清新刑律》的支持。但随后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即又对此采取含混和回避的态度。[4]尽管晚清立法大都没有正式施行即告流产,但这种在立法层面对待刑讯暧昧不明的态度却沿袭至今。 2013年生效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50、54条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及类似的取证方法(威胁、引诱、欺骗及其它),并将这些由非法方法所取得的证据排除适用。但又没有规定侦查人员有将此规定如实告知当事人的义务,以至于在实践中缺少必备法律知识的当事人很难充分利用该权利;并且,该法第118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义务,紧接着在第2款中规定,如实供述有争取宽大处理的权利。这被学者讥评为不自证其罪和如实供述的“对冲规则”,[5]更有学者从目前中国公检法非平行的司法结构现状推论出,要真正落实将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排除于非法证据之外,有相当的难度。[6]这些隐忧形成了我们窥视司法实践中各种刑讯逼供现象的“暗窗”。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及其修订案实施以来,各种“躲猫猫死”、“开水死”、“洗脸死”、“做梦死”等令人匪夷所思的疑似刑讯致死案件仍层出不穷,佘祥林案、张高平叔侄案等因刑讯诬服的冤案更是比比皆是。更曾有学者从道德和实用主义的角度为刑讯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正名”。[7] 五听制度的命运大略近似。五听制度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连同刑讯制度被作为封建统治的象征而被整体性否定。[8]2013年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将证据的概念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列举了8种法定的证据形式,而在证据学理论上被界定为情态证据的五听制度则付诸阙如,亦有学者为之叹惋①。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视为与五听制度具有形似原理的测谎仪却也有限度地被用于侦查活动中,虽未达到证明方法的基本可信度,但也可以认作侦查线索,对有效证据的获得起到辅助作用。 刑讯与五听,作为获取“情实”证据的两种并行手段,在中国法制史上和人们的心理层面长期维持了一种“欲拒还迎”的暧昧姿态。这使我们产生了进一步探究的兴味。 对此,我们拟按以下步骤进行探析:首先,刑讯与五听,均是古代中国司法官吏在讯狱时达致“情实”目标的两种手段②。其中,“情实”究竟何指?它与我们今天证据制度中的“证据事实”、“待证事实”和“案件事实”这些概念有何不同?其背后依存的是什么样的认知(思维)模式?这构成了本文的第一部分。其次,五听常被现代学者类比为英美法上的情态证据,更有甚者,将五听的原理与现代心理学所研究的“微表情”进行比附,它们之间究竟能否等同?抑或存在实质上的差别?这构成本文研究的第二部分。再次,刑讯作为中国古代司法官吏获取供辞的手段,其本身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那么,中国古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及司法官吏的讯狱活动是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这构成本文的第三部分。本文的最后,将探讨刑讯和五听制度及其背后的独特思维模式与原始初民社会神判活动的巫术行为中所包含的原始思维模式之间的渊源关系,并与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抽象逻辑思维模式相对照。 一、“情实”与真相 (一)刑讯与五听的对立和统一 在中国古代的狱讼中,刑讯与五听常被视为得“情”的两种对立手段。沿袭自西周以来的五听狱讼审判方式,是通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的情态观察,来判定狱讼两造“情实”的真伪。而据说与神判有着渊源关系的刑讯,却是以折磨拷问的方式,通过制造肉体或精神的极度痛苦而强力逼迫出“情实”。相较而言,五听更倾向于受讯供者身体情态的自然流露,刑讯的强力逼取,显然违背了身体情态表露的自然之理。因此,历代狱讼中以“得情”为宗旨的司法官吏,往往对刑讯的“上干天和”持批评的态度。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汉书·路温舒传》:“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陈书·沈洙传》:“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清末深受西学影响的维新派理论先驱郑观应质疑道:“至今法审犯,必取其口供为凭,致问官动用非刑逼供,痛昏之下,何求不得?若确已知情,又焉用招?”[9]319 刑讯会导致诬服的可能后果,它与五听手段相比,高下立判。不惟如是,受讯供者的面目表情往往会因遭受刑讯所施加的痛楚而扭曲痉挛,反而会破坏五听手段对其身体情态的判断,这使得有经验的讯问者更倾向于将二者对立起来看待。[2]38清代名幕汪辉祖曾有由衷之论:“狱问初情,人之常言也。盖狱之初发,犯者不暇藻饰,问者不暇锻炼,其情必真而易见。威以临之,虚心以诘之,十得七八矣。稍萌姑息,则其劳将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狱,圣人惟与乎子路,其难可知矣。”论中所谓“问者不暇锻炼”,即是防止刑讯对五听所判断的“初情”的破坏,这被视为“人之常言”③。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而忽略了二者的统一:刑讯与五听,尽管手段上有高下之分,但在求“情”的总体目标下,二者却又显现了思维原理上的一致性;并且,在历代的立法实践中,刑讯往往成为五听求“情”的强力后劲。秦律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知)其施(诈),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勿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又尽听书其解辞,又视其它毋解者复诘之。诘之极而数訑(诈),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治(笞)讯某。”[10]246北魏《狱官令》亦云:“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唐律疏议》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征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11]592《宋刑统·断狱律》除了规定“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方可拷掠外,太祖建隆三年(962)又敕曰:“如是勘到宿食行止,与元通词款异同,或即支证分明,及赃验见在,公然抗拒,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仍须先申取本处长吏指挥。”④宋律对于“支证分明,赃验见在”而“不招情款者”,仍须拷掠刑讯以取得犯人的服辩供辞。明清法律基本沿袭了这一做法。这些立法实践表明,刑讯在“尽求情之意”方面,实在是与五听手段保持了更多的一致性。 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模式,使得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在追求“情实”的总体目标下,二者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思维原理上的一致性?在证据学原理上,其所追求的“情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又维持了怎样的关联? (二)“情实”、事实与认知模式 现代诉讼证据理论中存在着三种事实:证据事实、待证事实和案件事实。事实是对呈现于感官之前的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某物具有的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的一种断定或陈述。[12]38事实以命题的形式存在,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在事实之前,是物和事件,它们属于本体论范畴,也就是说,在人的意识之前就以“物自体”的形式客观存在着。物具有空间上的三向度和时间上的延续性,能够通过观测手段把握。事件也称事情,是围绕物发生的,物和事件都是事实的载体,事实是从物和事件中截取的命题。 证据事实就是由证物或某个案件中截取的命题,至于由何处截取、截取的长度以及要证明什么,完全取决于证明者的主观意识,大陆法系又称作“心证”。不同的人主观意识各不相同,因此由证物和案件中所截取的证据事实也不尽相同。从一个证物或事件中,可以产生几个版本的证据事实,也会形成截然相反的证据事实。由证据事实推出的结论称作待证事实,二者之间具有唯一确定的关联性。保证此关联性的,取决于现代形式逻辑推理,尽可能将矛盾的可能性排除,二者关联性的程度决定着证据事实证明力的大小。 案件事实由证据事实和待证事实合成,并与法律规范相关,受法律规范的制约。案件事实都是制度性事实。[12]22法律规范是大前提,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是小前提,通过演绎推理,最终形成案件事实,也就是判决认定的事实,它又是确定案件当事人承担法律后果的前提。 现代诉讼证据理论中的事实认知,是一种主客分离的模式。事实以一种对象化的客观形式,与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衔接二者的,主要是形式逻辑链条。证据事实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自由心证的思维模式,也即取决于证明者个体的经验感知。在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中,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证据事实和待证事实作为小前提,尤其体现了形式逻辑思维模式中的演绎推理的特征。 与此相对,古代狱讼活动却是以“得情”为宗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条曰:“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此处“得人情”的“情”字何解?籾山明先生认为,不能解释为“人心”或“人的本性”,按《睡虎地释文注释》列举的《周礼·小宰》的疏文,当为“情实”的训诂,应理解为“察得犯人的真情、真实、真相”。只不过,这里的“真实、真相”是通过“书从迹其言”也即是记录口供的方式获得的。[13]78-79《唐六典·刑部员外郎》规定:“凡察狱之官,先备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14]190《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唐律疏议》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证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11]592贾公彦《周礼注疏》云:“以囚所犯罪附于五刑,恐有枉滥,故用情实问之,使得真实。”[15]2766这段文字表明,刑讯和五听是获取情实的手段,贾公彦的注解表明,情实与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过情实,可以达到真实。要获得情实,首先需要讯囚者本人“以情察辞理”,这里的“情”,当指常识性的情理。宋代郑克在《折狱龟鉴》卷六言道:“尝云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固当兼用之也。然证有难凭者,则不若察情,可以中肺腑之隐;情有难见者,则不若据证,可以屈其口舌之争。两者迭用,各适所宜也。”郑克的这段话表明,察情可以“中肺腑之隐”,其含义显然不是指肺腑生理性脏器隐藏的病痛,它实际上表达了“内心隐含真诚”的隐喻含义。“察情”与“据证”并列,并能够相互补充,彼此印证,表明此“情”当与“据证”一样,具有证据的地位。特意将“察情”和“据证”分列,又表明二者具有明显的不同。 宋代郑克在《折狱龟鉴·释冤下》总结道:“按凡察狱者,或以气貌,或以情理,或以事迹。此三者皆足以知其冤否也。”在其列举的事例中,气貌基本上属于五听查证的范畴,应属于查案线索;情理当是判案者根据个人的经验推理出的事实;事迹则是由证物获得的证据事实。[16]110-111清代名幕汪辉祖在其著述《学治臆说》中言道:“古人云:‘狱贵初情。’一犯到官,也必详慎推求,必得其实,然后酌情理之中,权轻重之的,则犯自服输。”此处“情”有两处:“初情”之“情”,“情理”之“情”。——如许多“情”,“情”字何解?据欧阳祯人的考证,“情”的本字为“青”,本义指草之青色。与“性”结合,“性”的本字为“生”,草生于地,说明“性”、“情”相关。“性”是根本,“情”是其外化的表现。“青”字添“心”,“从青从心,上青下心”,“情”由此获得了心理情绪的内涵。[16]81-88《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荀子·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可见,“情”字第一义,是反映人之本性的自然情感。 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情”字,既能“抒情”,也可“载道”。而古典文艺所载之“道”,无非来自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既有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另外主要有兄弟、夫妻、朋友、邻里乃至四海之内),亦有将父子之“孝”移作君臣上下的忠诚之道。此是“情”字第二义,是属于家族化、伦理化了的道德情感,[17]10我们通常所谓的情理、真诚、诚信也属于此层含义。 李泽厚先生在对传统中国乐感文化“情本体”的核心特征进行概括时指出:此“情”者,既是情感,也是情境。[18]55-56欧阳祯人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包括:初始、实质、情实、情理、真诚和诚信。其中,情理、真诚和诚信,已包含“情”字第二义。“初始”一词有二义:一指人,当作“情”字第一解;二指事物发展的最初状态,尤其指没有人为羼杂前的事物的本来的样子。“情实”一词的概念比较复杂,在后面的证据原理分析中,它可以根据不同情形,表达“情”字的四重含义。“实质”一词则很少在中国古代狱讼证据概念中出现,因此不作分析。那么,“情”字第三义,指情境,也指“初始”的第二义。 我们通常所讲的事情,与“事件”一词同义,已如本节之前的分析。“情”字第四义,与“事情”相组合,是指有待主体认知的、围绕着物发生的客观自在的事件。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狱讼活动中的“情实”具有多重含义:当作为五听的手段所获得的“情实”时,既指人的内心情感,也指向一般的经验情理,两相验证,以此获得狱讼证据的线索,由此,指向“情”字一、二义;当作为刑讯手段所获得的“情实”时,刑讯以逼取口供为旨归,口供应与内心的真实情感相一致,所以此处的“情实”反映出口供与内心情感的匹配度,这里的情感也包括了“情”字一、二义,它与言辞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不可分离,因此属于言辞证据⑤;当指“初情”一词时,包含了情境的内涵,大概近似于英美法上的情势证据,这种情境更多地受到判案者经验性情的塑造,不具有独立的客观性。 当“察情”与“据证”并立时,“据证”更倾向于人证以外的证据,主要是与人的主观情感无关的证据。“察情”在此更倾向于与人的内心情感相关的内涵,在此它更像一种查案线索;当“察情”通过人的言辞形式表达出来时,情辞就成了言辞证据,属于证据事实中的言辞证据;“察情”当然也可指向“据证”,也即所谓客观性的人证以外的证据。试看下面一例: “前汉时,沛县有富家翁,赀二千万,一男才数岁,失母,别无亲属。一女不贤,翁病困思念,恐其争财,儿必不全,遂呼族人为遗书,悉以财属女,但余一剑,云:‘儿年十五付之。’后亦不与,儿诣郡诉。太守何武因录女及婿,省其手书,顾谓掾史曰:‘女既强梁,婿复贪鄙。畏贼害其儿,又计小儿正得此财不能全护,故且付女与婿。此实寄之耳。夫剑所以决断,限年十五,力足自居,度此女婿不还其剑,当闻州县,或能明证,得以申理。此凡庸何思虑深远如是哉!’悉夺其财与儿,曰:‘弊女恶婿,温饱十年,亦已幸矣。’闻者叹服。”[19]386 本案中的遗嘱显然属于人证以外的“据证”,形式上已具备客观证据的效力。然而,太守何武却根据遗嘱所产生的情势以及“将心比心”的情态判断,最终得出了与遗嘱记载内容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表明,即便是具有客观形式的物证(包括书证),也必须通过裁判者道德情感的涵化,才能成为“真实”的证据。因此,所谓“情实”,实质上是经过认知主体道德情感化的身体感知后,涵化到其身体认知结构中的“事实”。这是一种主客同构的身体思维认知模式,迥异于现代性的抽象形式逻辑思维模式。 我们下面通过五听和刑讯手段中的身体思维模式的介绍展开论述。 二、五听中的身体思维模式 在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五听常被看作现代心理学应用于现代司法实践的先声,更有论者将其与目前心理学上方兴未艾的微表情研究挂起钩来,认为类似于英美法上情态证据的五听制度,“是人类本能和心理的一种司法运用,是基于压力而导致人的情绪发生变化时,并由植物神经系统作用而引起的动作或生理变化”。[8] 将五听所反映的情态归结为“人的植物神经系统所引起的生理变化”,这一结论是否符合五听作为情态证据判断的真实思维模式,是本节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对该问题的探讨分为两层:其一,对微表情在现代心理学上的研究现状及其内涵做一简要介绍,分析微表情作为谎言测试的运作原理,并对测谎仪在目前证据制度中的局限作一反思;其二,揭示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五听的,其背后所依存的身体思维模式,在历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又是如何具体展开的。 (一)微表情与谎言识别 微表情(microexpression)属于面孔认知的研究范畴,与普通表情和弱表情(subtle expression)相对,在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交叉领域被广泛地进行实证研究,[20]并在精神分裂症的临床医学、情绪智力、谎言识别、国家安全、政治心理学等领域进行着尝试性的应用,目前已在很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1] 微表情之所以被应用到谎言识别领域,是因为现代心理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微表情与自我(ego)防御机制有关,表达了被压抑的情绪。它与普通表情一样,反映着人类自身的情感信息,可被视为人类心理活动的晴雨表。与普通表情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十分快速以至于难以被察觉的表情,维持时间仅为1/25秒至1/5秒。它往往在人撒谎时出现,表达了人试图压抑与隐藏的真正情感。这种表情动作是自发性的,表达了诸如高兴、厌恶、愤怒、恐惧、悲伤、惊讶六大基本表情。[22]面孔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表明,这六大基本表情分别对应于人脑的不同区域,受到神经子系统的处理和控制:恐惧和悲伤面孔主要涉及杏仁核区,快乐面孔涉及扣带回区,愤怒表情涉及前额眶区,厌恶表情能激活前基底核和岛叶,这些脑区在进行不同情绪的处理时会有重叠。[20]在生物机理上,研究者普遍假设(假设尚无实证检验),它与控制面部肌肉运动的两条通路相关:一是皮质运动通路,控制随意的面部肌肉运动;二是皮质锥体外系通路,控制自发的面部肌肉运动。[21] 与微表情的谎言识别相比,测谎仪(lie detector)已不再局限于面部表情,它的正式名称是“多参量心理测量仪”(polygraph)。顾名思义,这种仪器是以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阻等受植物神经系统控制的多种生理变量作为参照依据,用以识别言辞的真伪。而将微表情的研究引入到测谎技术中去,对于提高测谎仪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也是面孔认知研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20] 二者之所以能够相互结合,是因为存在共同的运作原理基础:微表情能够自发性地表达被压抑的心理情绪,并受到人脑神经子系统和面部肌肉生物机理的控制;测谎仪所依据的生理变量同样是受到植物神经系统的机能控制,这种神经系统又名内脏运动神经,由脑和脊髓发出,分布于躯干和四肢,司理运动和感觉,因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因此又称自主神经⑥。何家弘先生将测谎原理的核心总结为“心理刺激与生理反应的对应伴生关系”,[23]这一总结同样适用于微表情原理。而对于同样具有“对应伴生关系”的一些在说谎时伴随着的下意识习惯性动作,比如说话结巴、连续眨眼、吐舌头、摸鼻子、挠耳朵、搓手掌等,因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被排除在微表情和测谎仪的测量范围之外。 从二者共同的运作原理,我们可以在此总结一下微表情和测谎仪的思维模式。在刑事诉讼中,微表情和测谎仪也常被作为测量言辞证据的真伪,为案件事实的判定提供参考依据。在整个测量过程中,人的身体结构犹如一个较为复杂的机械组织,观测者运用综合性的科学手段,可以对其生物机理和神经系统的运作进行精细的测量和分析,通过反复的实验和总结,特别是计算机科学的运用,这种观测的结果可以进一步抽象为数字化的识别系统。 由此,人的身体成了一种抽象性的存在,成了可供科学实验和技术测量的客观对象。构成身体的肌肉组织和神经系统虽不像机械零件那样可以任意拆解和操控,但仍然可以被测量和分析。在刑事诉讼中,嫌犯或证人的言辞真伪被判定,言辞之下的思想情绪被换算成表达各种生物体征的数据,呈现在借助各种仪器实施观测的专业人员冰冷的理智之下,观测者的个人情感被假定丝毫不掺杂其中。与数据库的样本相矛盾的个人体征被小心地排除在外,更多的具有相同原理的新型样本被充实到数据库来,由此使得测谎仪的测量数据在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中越来越趋向于重要。在整个测量过程中,既有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又有通过计算机的数字化处理的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因此,微表情和测谎仪,完全成了科学演示的理智活动。 (二)五听与情实 五听求“情实”,但并不借助任何科学仪器和标准化的数据样本(条件也不具备)。五听的操作无须假手于人(法庭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它完全由主审案件的司法官吏一体承担,并且仰赖于司法官吏本人的睿智和人格魅力。谙熟五听审断的司法官吏不仅需要有一副“哀敬折狱”的悲悯心肠,还需要通过礼典的熏陶和世事的历练,以获得洞悉人情物故的经验支持。明代惠帝为太孙时,“捕盗贼七。太孙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盗,其一非也。’讯之,果然。帝问何以知之?对曰:‘《周礼》听狱,色听为上,此人眸子了然,顾视端详,必非盗也。’帝喜曰:‘治狱贵通经,信然。’”[24]1252治狱不求明法而贵通经,《周礼》作为儒学的经典,渗透了儒家的义理,惠帝幼年即受其润泽,时人认为,这便是他小小年纪能够谙熟五听,明断盗案的原因所在。 清代名幕汪辉祖似与明惠帝有共同心得,在其著述《学治臆说》中有“治狱以色听为先”条:“《书》言五听,非身历不知。余苦短视,两造当前,恐记认不真,必先定气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虚者良久即眉动而目瞬,两颊肉颤不已,出其不意,发一语诘之,其真立露,往往以是得要犯。于是堂下人私谓余工相法,能辨奸良。越年余,伪者渐息,讼皆易办,盖得力于色听者十五六焉,较口舌争几事半而功倍焉。”[25]2 通过眉动、目瞬、两颊肉颤不已而判断其“情虚”,与微表情的判断方法迹近相似。然而色听似乎没有像微表情判断那样,将人的心理情感分解成人体肌肉和神经的生理性机械共振现象,而是更强调心-身整体性的有机互渗。孟子也很重视以眸子配合言语的观人之法:“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26]离娄上台湾学者祝平次就此论道:“这种由人的一部分以断定人的全体,逻辑上还是整全和分殊的关系。分殊和分殊的关系构成整全(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而整全既成,也可由分殊加以反溯证实。分殊的目的既指向整全,则没有单一的分殊完成(成则具成);故胸中正则眸子瞭焉,由一在内的分殊的完成可以推知另一分殊的完成,反之亦然(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27]292 人的眸子的清浊与其胸中掩藏的善恶情感具有一种有机互渗的联系,这里的身体已不再是单纯生理性的,它与道德情感化的心灵之间互相渗透,形成了具有实践倾向性的“整全”的身体。这正是身体隐喻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 色听仅是五听方法中的一种,它尚包含辞听、气听、耳听、目听等单一或综合的手段。汉代郑玄在对《周礼》作注时有详解:“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 事实上,五听在实际运用中远不止这五种手段。“郑子产闻妇人哭,使人执而问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问曰:‘何以知之?’子产曰:‘夫人之于所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哀。今且夫已死,哭不哀而惧,是以知有奸也。’”[19]25郑国的子产只通过妇人“不哀而惧”的哭声即辨识出其中隐藏的奸情。五代和凝父子的《疑狱集》和宋代郑克的《折狱龟鉴》搜录了大量通过五听相类似的手段侦破隐情,从而获得破案线索的例子⑦。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五听作为一种查案手段,其所获得的线索远没有达到证据证明力的地位,因此也不可能等同于英美法上的情态证据概念。 我们看到,五听及其类似手段所观察的诸如声音、眸子、语气等各种肢体性的情态,恰恰是我们之前讲测谎仪所认为不稳定而予以舍弃的观测对象。测谎仪更注重具有稳定性和一般性的血压、脉搏、呼吸、皮肤电阻这些能够形成仪器测量参数的生理体征。与此相对,五听观察的身体更为具体,它不可能形成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数据指标;同时,五听观察的身体更具有整全性,它虽不能脱离生物性的身体,但也无须借助仪器将其分解成生理性的身体体征。 对于微表情和测谎仪苦于无法通过营造高风险撒谎的实验情境,以激发受测对象强烈的撒谎动机,并且仪器与人体的接触,也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情绪唤醒,从而干扰到测试结果,由此使得人们对其实验的效果多持保留的态度。[21]五听及类似手段却可以通过灵活的钩距讯问和擿奸钩慝术⑧,营造出针对被测对象的虚假情境,以使其产生误判,从而轻易解除掉其内心本有的强烈防御机制,然后突然间回马直切主题,破解掉其精心营造的谎言。试看一例:“元绛字厚之,钱塘人,为上元令。有甲与乙被酒相殴击,甲归卧,夜为盗断其足。妻称乙,告里长,乃执乙诣县,而甲已死。绛敕其妻曰:‘归治而夫丧,乙已服矣。’阴使信谨吏迹其后,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绛命絷僧庑下,诘妻奸状,即吐实。人问其故,绛曰:‘吾见妻哭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污,是以知之。’”[28]171-172元绛诈称案已告破,使疑犯放松警惕,再暗中派人尾随,见其“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遂暴露真情,一举告破。这是典型的擿奸钩慝之术。随襄州总管裴正云:“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19]313据证者核奸用之,察情者擿奸用之,盖证或难平而情亦难见,于是用谲以擿其伏,然后得知。 五听察情,没有指标,没有量化,没有样本数据库可供参照,完全是一对一的心理攻防战术。每一个观察的对象都是与自己一样整全的身体,这更加要求讯问者需要关注个殊化的身体。因此,五听的思维模式首先是一种具体思维模式。要想完全发挥这种思维模式的功效,首先需要讯问者要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被讯问者的身体情境中去,设问一下:如果自己处于对方的情境之下,该会作何抉择?这种推心置腹、移情换位的思考模式正是我们所讲的身体思维模式。《晋书·刑法志》云:“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使然。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 这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模式,正是身体思维模式的隐喻类推形式。它以自己的身体的功能和结构为论证推理的基点,并假定其能够与所要认知的宇宙万物的结构彼此类通,互相感应。讯问者在启动自己的身体思维模式时,首先要抱持“哀敬折狱”的虔敬心态,相信仁爱至诚之心能将自己欲认知把握的对象涵摄到自己情感化的身体中来。 三、刑讯中的身体思维模式 正如之前所论,五听和刑讯,作为获取“情实”讯供证据的手段,具有自然表露和强力逼取的相异特征。因此,为了保障“情实”讯供证据的真实性,历代法律都有意识地将五听手段置于刑讯之前。秦律规定较为详尽:“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知)其訑(诈),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勿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又尽听书其解辞,又视其它毋解者复诘之。诘之极而数訑(诈),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治(笞)讯某。”[10]246北魏《狱官令》亦云:“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征诸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 直至清末法律改革前,五听都是作为刑讯的前置程序规定在历代律典中,以此限制刑讯所可能造成的冤滥。同时,通过五听和“验诸证信”后,在被指控事实具有极大可能性的情况下,受讯供者仍不“首实”的,方可拷掠刑讯。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证据理论,没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划分,也没有半个证据、一个证据这样的数量标准划分。因此,对于“事多疑似”的判断完全有赖于主审司法官吏的情理推断。而对于证据确凿犯人却拒不招供的情形,是否还需要刑讯呢?秦律“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似乎并不以刑讯供辞为必然。而《唐律》第476条明确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 所谓“赃状露验”,据《疏议》曰:“谓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检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据状科断。”可见,唐代法律以“赃状明白”为已足,并不必然要通过刑讯获取犯人的服辩供辞。然而,这种情形在宋代以后即有变化,《宋刑统·断狱律》除了规定“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方可拷掠外,太祖建隆三年(962)又敕曰:“如是勘到宿食行止,与元通词款异同,或即支证分明,及赃验见在,公然抗拒,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仍须先申取本处长吏指挥。”⑨宋律对于“支证分明,赃验见在”而“不招情款者”,仍须拷掠刑讯以取得犯人的服辩供辞。明清法律基本沿袭了这一做法。在此情形下,刑讯的服辩供辞基本上在获取破案线索和证明犯罪事实方面已无实质意义。若说有意义,或许是在“情实”上进一步增强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29] 刑讯使受讯供者陷入进退维谷之地: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告无罪释放。但不管哪一种情形,都会使无辜者遭受比真正的罪犯更坏的境地,从而使获得“情实”的目标更难实现。[2]38这个问题早已被历代立法者所隐约察觉,因此,历代法律都曾对刑讯手段采取了一些限制,以尽量避免屈打成招的恶果。唐代法律对此规定详尽,比如: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每次拷囚须间隔二十日,笞杖部位分臀、腿、背均受(笞以下允许背、腿分受;殿庭刑讯,皆在背部),刑具的材质和规格规定详细,刑讯期间不得中途易人以及对于不依法拷决而刑讯致死的官员要依法追究责任等等⑩。明清律典在刑讯方面,尽管增加了一些刑具的种类,但总体上对刑讯采取限制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11)。某种意义上,刑讯手段的限制本身即是仁爱德性的体现,这反而模糊了刑讯在人们心目中本来的面目,仿佛度量适当的刑讯是可以接受的,只有过度冤滥的刑讯在道德评价上才是负面的。然而试想一下,刑讯若不达到超越人的皮肉忍耐极限的程度的话,又如何让罪犯“自动”招供呢?因此,无论如何,刑讯的限制本身即是一个悖论。 刑讯要获得供辞,言为心声,因此实际上总是要得到受讯供者内心的“情实”。既要获得“情实”,最好像五听手段那样,通过情态的自然流露,而刑讯给身体造成的痛苦却让整个面目表情因痉挛而扭曲,这反而难以获得“情实”。那为何还要通过刑讯手段获得“情实”呢?贝卡利亚展示出了这样一个迹近荒唐的理由,即洗涤耻辱。将痛苦作为试金石,以肉体痛苦的手段洗刷道德上的耻辱。[2]40而作为司法术语的“供辞”的“供”,与普通意义上关于客观事实的“陈述”一词相比,本身已具有主观上大奸大恶的伦理倾向。[30]35-36因此,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也包含了通过制造肉体的痛苦从而使得受讯供者内心产生愧辱,从而“自动”招供而产生“情实”这一层含义在内。它不像五听手段那样,还需要借助身体情态的外部呈现,而是由受讯供者衷心地直接表露出来。 基于这种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刑讯作为一种“最为伤和害理,有悖民牧之义”的不道德手段,[31]194却能追求道德性的“情实”目标,这一内在关联是如何可能的。既然刑讯是追求道德“情实”的目标,那么,与道德相抵触的一些客观事实就自然要排除在“情实”证据的内涵之外了。 《唐律·断狱》“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条(474)、“拷决孕妇”条(495),将年龄过老过小、身体异常、孕妇(包括未产及产后未满百日)以及身份特殊者,都排除在拷讯范围之外。另外,从汉代以来,儒家“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在历代法律中都有体现,一直到《大清律例》“老幼不拷讯”规定:“其与律得相容隐之人,及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若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笞五十。”沈之奇就此论道:“此皆本乎人情,原乎天理,所以厚风俗以正伦纪,律之精义也。”而对于以卑告尊者,清律称之为“干名犯义”,规定:“子孙告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但诬告者,绞。”清代立法甚至对妇女作证也多有限制。这些现象被蒋铁初先生总结为“伦理与真实的冲突”。[32]事实上,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主要是跟中国人特殊的身体思维模式有关,在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客观证据事实必须要经过道德化身体感知的涵化成为“情实”后,方可作为支撑案件事实真相的关联性证据。简言之,所谓“情实”,是经认知主体道德涵化了的“事实”,这种主客同构了的认知模式的结果,便是古代中国人眼中的“真实”。 四、巫术渊源中的原始思维 的确如批判者所论,刑讯逼供渊源于古老的神裁法机制。沸水、烈火、热油、潜水、毒药、动物等等,是原始初民时代神裁法机制所使用的手段,千奇百怪,花样繁复,[33]1-94但都遵循着同样的原理,即将案件中的疑问交给明鉴的神意来裁决,而神意则是通过各种残酷的手段测试被验者的身体呈现的。当神意明鉴的权杖掌握在具有世俗司法权威的古代官吏手中时,便是刑讯制度了。 在古老的神裁法机制中,必须要有能够与神意相沟通的媒介,并且需要展示这种沟通媒介的现场仪式。于是,负责主持神裁法的人就兼具了巫师和法官的双重角色,神裁法机制巧妙地将法律的裁判功能与巫术的仪式功能融合在一起,双方各自借助彼此的力量充实着自己。[34]14-26在整个仪式中,巫师/法官借助自己的身体的动作、姿态、容貌、语言等一系列繁细且高难的技巧以完成既定的巫术礼仪,并且通过这些狂热的身体举动呈现出敬、畏、忠、诚的主观情感,以迫使神意降临到自己的身体。[34]14-26同时,在神裁法机制中,被裁判者的身体同样是仪式的一部分,各种酷烈的手段既是在考量筋骨皮肉忍耐痛苦的程度,同时也是检验神意对罪之有无的钧鉴。由此,裁判者和被裁判者的身体和情感,在神裁法机制的真相熔炼炉中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在整个巫术—司法仪式中,裁判者与被裁判者的身体被一种原始宗教性的神圣敬畏情感所充斥着,是一种主客同构的认知状态,已不再是作为认知主体纯然客观的对象化存在。这种认知模式就是布留尔所总结的具有身心互渗、人神杂糅的原始思维模式。[35]94-95 巫术礼仪到了商周时代逐步衍化为宗法政治社会世俗性的生活礼仪,进而成为儒家礼制的一部分。儒家礼制不仅承继了古老巫术的外在仪式——也即是规范身体容貌行止的各种礼仪、礼数——而且巫术活动中,巫师身体所呈现的敬、畏、忠、诚的内在情感也转化为儒家所强调的仁爱、诚信的道德理念。而在神裁法机制中,借助裁判者和被裁判者的身体共同完成的仪式,也被后世司法中的刑讯制度和五听制度沿袭了下来:司法官吏“哀敬折狱”的道德情感正是来自于古老巫师在巫术活动中所表达的与神意沟通的敬、畏、忠、诚的神圣信念;司法官吏以至诚的情感对案件事实的体认,也沿袭了巫师利用仪式性的身体与神意的耦合;神裁法机制中的各种酷烈的考量成为了后世所司空见惯的刑讯场面,巫术中的“神意”演化成刑讯所求索的“真相”,而无论是“神意”抑或“真相”,都是借助裁判者和被裁判者身体的仪式化形成的。“神意”和“真相”都不是脱离认知主体的身体之外,而是涵摄在认知主体的身体结构之中,人神杂糅的巫术最终演化为儒家身心互渗、主客同构的身体思维模式。 在神裁法机制下,针对被讯问者身体的残酷手段是探知神意的途径,本身并无价值上的判断。而在刑讯制度中,刑讯手段本身同样是探知真相——“情实”的手段,本身也没有价值优劣可言。历代所针对的是刑讯冤滥所导致的“伤和害理”,不仅有违“民牧之义”,也是对古老神裁法机制中“神意”的滥用。其结果是使得滥施酷刑的司法官吏首先丧失了作为至诚道德主体的前提。而“神意”在身体上昭示的另外一种方法,即通过身体的动作、姿态、容貌、语言等所显现的“情实”,反而是更为可取的方法。 尽管儒家门徒深受孔夫子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诲,但受儒家至诚道德精神理念感召的循吏们往往会深信,至诚的精神信念甚至能够与天地神明的力量相感应,进而使得欲探寻的情实“自动”浮现出来。清代胡文炳在《折狱龟鉴补》一书中颇多记述,试举一例:“田滋字荣甫,开封人,累拜浙西廉访使。有县尹张彧者,被诬以赃,狱成,问之,但仰手泣不语。滋大疑,明日斋沐,诣城隍祠祷曰:‘张彧坐事有冤状,愿神相滋,明其诬。’守庙道士进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状到祠焚祷,火未尽而去,炉中得其遗稿,今藏壁间,岂其人邪?’视之,果然。明日,诣宪司诘成等,不服。出火中誓状示之,皆惊愕伏辜,彧遂得释。”[28]791-792 整个案件告破过程之离奇,匪夷所思。只因怀疑当事人有冤状,便斋沐祷神,竟意外寻到人赃证物。这难免让人疑惑,是否是因为田滋精诚招致神意所致。这种事例在《折狱龟鉴补》一书中多有记述,可见它在中国人的精神情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这正是我们所论述的身体思维模式演绎的当然结果,也充分表明身体思维模式与原始初民社会巫术中所包含的原始思维之间所具有的渊源关系。 ①“情态证据”属于英美法上的概念,是指证人在作证时的非言语情态,包括证人的姿态、外貌、面部表情、声音语调等,事实认定者可以借助情态证据对于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作出判断。参见龙宗智:《进步及其局限——由证据制度调查的观察》,《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②古代中国官制分官设职但不分权,司法行政合一。即使国家层面有专职司法官,如西周的司寇、秦汉的廷尉、唐宋的大理寺、明清的刑部等,但地方州县行政长官却都将司法审判纳入自己的日常行政工作。另外,唐代的三司推事、明清的会审制度,都有大量行政官员参与司法审判的事实。因此,本文所论古代中国凡参与审判工作的官员都以“司法官吏”来称谓,甚至也包括明清时代像汪辉祖那样的、以私人幕宾身份与主人共进退的人员,以示与现代意义上的专职法官的区别。 ③“锻炼”一词,杨奉琨先生解释为“罗织罪名,制造罪证,使成狱案”。由于古代刑事诉讼需要“据供证定罪”,而从通常疑犯的心理角度出发,没有人会自动招供,因此“锻炼”二字不免会有刑讯的意涵。参见《疑狱集折狱龟鉴》,杨奉琨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④[宋]窦仪等:《宋刑统》,卷29“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门”,引建隆三年(962)十二月六日敕节文,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礼记》曰:“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急救篇》:“词穷情得具狱坚。”师古注:“既穷其辞,又得其情,则鞠讯之吏,具成其狱,锻炼周密,文致坚牢,不可反动也。”都反映出“情”与“辞”的不可分离。 ⑥植物神经,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IkVGvB2N9InCa9cgCvrhqa29BiNAfmVmO_M2mJIA8NjpAG6kL6w-2YCxYdMp1W1,2013年9月24日访问。 ⑦如“严遵疑哭”、“高柔察色”、“周纡尸语”、“韩滉听哭”等故事中查案的手段都类似五听。参见《疑狱集折狱龟鉴校释》,杨奉琨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6、22、40页。 ⑧钩距”讯问法,是指辗转推问,侧面迂回以便查明案情。《汉书·赵广汉传》云:“(广汉)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叁伍其贾,以类相推,则知马之贵贱,不先实矣。”“擿奸钩慝”,按照杨奉琨先生的解释,是指“揭露巧诈的犯罪和勾出隐晦的犯罪”。参见《疑狱集折狱龟鉴校释》,杨奉琨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 ⑨[宋]窦仪等:《宋刑统》,卷29《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门》引建隆三年(962)十二月六日敕节文,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⑩《唐律·断狱》“拷囚不得过三度”条(477);另外,参见仁井田陞著:《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27页。 (11)明清的刑具在笞杖以外增加了掌嘴、跪链、夹棍、拶指等。参见《大清律例·断狱》“故禁故勘平人条”。另外,美国学者马克·P·唐纳利和丹尼尔·迪尔合著的《人类酷刑史》一书中,形象描述了20世纪初的清代中国一幕“跪铁链”的刑罚,并配有生动的图片,同时也提到了针对妇女的拶指刑。这些刑罚既用于惩罚已决的囚犯,同时也用于拷讯未决的疑犯。参见马克·P·唐纳利、丹尼尔·迪尔著:《人类酷刑史》,张恒杰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3页。标签:刑讯论文; 微表情论文; 心理学论文; 法律论文; 刑事诉讼法论文; 周礼论文; 测谎仪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证据规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