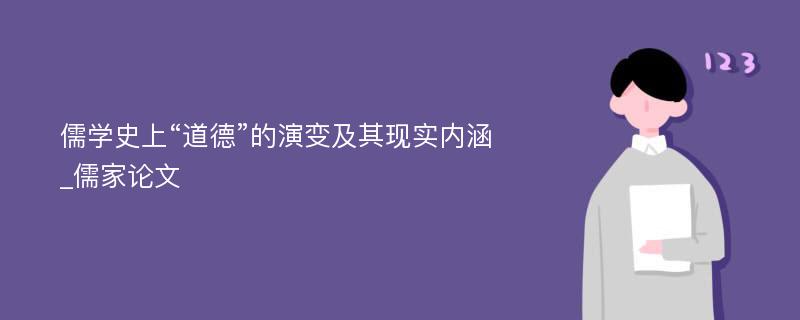
“德”在儒家学说史上的演变及真实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史上论文,学说论文,内涵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07)01-0036-04
“德”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似乎可以不必做任何解释。但是,这种熟知往往只是局限在“德”作为一般伦理原则的层面上,而对于“德”的历史沿革及由此蕴含的丰富内涵却缺乏深入探讨。笔者认为,“德”开始只是作为天地的品格、自然之性,为人们所效仿;后来逐渐跃升为政治范畴,成为对“王者”的特殊要求;最后才成为后世广泛使用的伦理范畴。儒家对“德”的阐释包含着对自然、社会、人性的整体感悟,其中蕴含的天人一体、天性和人性的差别等思想,对于解决现代自然环境危机,加强道德修养,提高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水平,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德”是天地的品格、自然之性
天的信仰和观念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信仰和观念。
在中华初民看来,“天生烝民”[1]、天生万物,即人是从属于自然的,大自然生养人,生养万物。“天之大德曰生”。天养育万物,庇护万物,促成万物的和谐生存,这就是天的大德或天性。这种天性没有自私狭隘、亲疏远近的算计,而是对万物一视同仁。“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正是由于天的至诚无欺的品格,人们才会产生尊天、敬天、畏天、应天、法天、顺天、知天、事天、乐天、配天的态度,保持对天地自然的敬畏、顺应之情。
人既然为天所生,又对天如此顺应尊崇,也就自然秉承了天性,即天性为人性。这种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故“生之谓性”(告子语),“天命之为性”(《中庸》)。人拥有了这种秉性,就是“德”。《管子》和《礼记·乐记》中都说:“德者得也”,《广雅·释诂三》也有“德,得也”的解释。“得”是什么呢?“得其天性谓之德”,“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1]。“德”即天性,这个结论是符合逻辑的:人既然是自然的产物,就必然拥有自然的属性,即特殊中蕴涵一般。有了这样的“德”,人就会像天地一样,对别人、对事物抱着亲善关爱之情,并通过行动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这样,“德”就有两重表现:在内为性,即德性,指亲善的感情;在外为行,即德行,即亲善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儒家的观念里,天(自然)和社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不是对立的。社会来自于自然,自然的法则同时也就是社会的法则,自然的法则中包含着伦理的品质,这种自然伦理也就是社会伦理。社会要良善发展,就得师法天地,师法自然,秉承天地自然的博厚、久远、无私的品格。
在儒家思想中,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大自然既是人类的养育者,又是人类的伙伴。因此,人类应当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但人类在近代以来工业化过程中不顾一切地追求发展速度,大规模地开发资源,造成大气污染、森林减少、土地沙化等全球环境的恶化。现代化过程中人对自然的无情剥夺,缘于对西方现代精神——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极度尊崇。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在破除愚昧迷信、高扬人的价值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反思中,儒家“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思想受到人们的关注,绝不是偶然的。
二、“德”成为政治范畴——“有德者王”
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夏商时期,已经出现了“德”的观念。不过,这一时期的“德”似乎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品质和行为,还没有上升为普遍的人格规范。到了西周时期,德的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跃升为政治文化范畴。在这种跃升中,德的主体主要是君王,“德”指君王的人格品性和统治方式。这一变化有其社会历史原因。本来,殷商乃至其他邦国都相信王权天授,天命是王权的依据。殷商作为天下共主,深信天命认准殷商为王,永远不变。可殷商到了后期信奉鬼神,在统治方式上则实施刑政,残酷暴虐,结果众叛亲离,“小邦周”灭了“天邑商”。
西周成为天下共主之后,总结了商灭周兴的经验教训。西周统治者认为,天命靡常,并非永远不变,“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书》),周人的胜利主要胜在周人的“德”上,即周王有“德”,因而赢得了天命。天下共主就是天子,天子在统治天下的活动中,应当养育和保护民众。这种认识促使周人调整统治思路,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并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周公因势利导,创建了分封制、宗法制,并制礼作乐,注重对人民的教化。这就是西周的所谓“德治”或“文治”,它区别于殷商的暴政和刑政,意味着政治和文化的重要变革。《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就是这场政治变革和创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德”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概念。
“德治”思想后来成为儒家的主要思想,是儒家伦理政治观的具体体现。把道德视为政治的基础,强调当政者的道德品质对政治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从历史上看,这种思想曾造就了一批开明君主和清官贤臣,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即使在今天,强调当政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政治中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毕竟混淆了政治和道德的差别。这种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它把整个国家的兴衰治乱完全寄托在个人尤其是当政者的道德水平上,从而造成中国历史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恶性循环。
三、“德”普遍化为一般伦理范畴
既然德是天性,德就是人所共有的秉性,并不限于君王,也不限于政治生活领域,而应该存在于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样,“德”就由政治范畴扩展为一般道德范畴,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格追求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德”作为人的普遍的天性并不仅仅从“天生烝民”中得到解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得到充分的经验印证。在家庭中,父母养育儿女、祖先繁衍后代的行为,体现了“德”的品性,它和上天养育万物的行为所包含的品性是同质的。这才有了儒家“亲亲”、“别爱”观念的产生。孔子的“仁”就是指“德”在家庭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具体表现。
“德”作为人人具有的人格品性,到了战国时期的儒家那里进一步泛化开来。尤其是在孟子的思想中,“德”不仅变成了人人皆有的“善端”,而且人人都有可能在道德修养上达到完美的境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也”[2]。这就在天性和人性之间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联系,“德”也就成为人的本质特征。同时,“德”也成了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成为衡量理想人格的核心指标。人生的价值在于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其最高境界是成为圣人,“圣人,德之至也”。至于君王,孟子认为,则要把“不忍人之心”表现在政治统治上,推行“仁政”。而对普通人来说,“德”又具体化为“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3]。
孟子的性善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人为什么并没有都成为君子、圣人,而是常常表现出“恶”,天生具有的“德”为什么还要靠修行才能获得等问题。为此,后来的儒家对人性又引入了诸如情、欲、心、义理、气禀一类概念,甚至将人性分出善与不善,分出品级,认为下品性恶,不可改变。其实,先儒(主要是孔子和孟子)虽然认为人人都秉有天的德性,但又深知人性并不等于天性。因此,他们只是在天性和人性之间建立起了必要联系,并没有否认二者之间的差别,从而为强调修身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因为人人都是有善端的,才可以通过学习、修炼等方式提升道德境界,否则善如何无中生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每个人的道德状况,关键取决于个人后天努力的程度。
按照先儒的思维方式,虽然人人都有天性,但人人并非天地,而只是构成天地的一个分子。这样,人在得天之性的同时,还存在着天地和小我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在小我身上,就是天性和小我之性的冲突。当一个人蔽于小我之中,就会违背自己的天性,失去从天性出发看待得失的立场,导致小我膨胀而走向“恶”。比如,一个人是家庭之人,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可是一个人不仅是家庭之人,也是社会之人、天地之人,因而也要对社会、天地承担起应有的义务和责任。
显然,儒家的思想必然内在地蕴涵群体本位的思想,排斥狭隘的个人本位。但是,儒家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完全否认个人价值,他们提倡的恰恰是道德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所追求的自由权利不是与共同体相对立的,而是通过与共同体的合一来获得的。儒家没有把个人之间互不干涉的状态当成社会理想,而是把伦理共同体之内存在着的道德规范与自身道德意识的统一作为个人追求的理想。在儒家看来,人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就在于克服利己的本性实现道德本性、天地本性。程颢认为,仁者就是识痛痒、具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觉悟,即“仁者,公也”[5]。朱熹用天理解释天性,强调“私欲净尽,天理流行”[6]。由于天理是天地的本性,是生养万物的原则,自然允许包括人在内的生命拥有情欲,只是要求这种情欲限制在保证生命健康成长的范围内。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情欲,就是泛滥荒淫的情欲,即朱熹所谓的“人欲”。
正是由于人性中有“私”的、“欲”的成分,有不符合天理、天性的方面,所以才会有修“德”的问题。追求“德”的过程就是发扬孟子所谓的四种善端的过程,也就是恢复人的天性的过程。人只有把这些善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会有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升华的无上愉悦。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7]“诚”即诚实无欺,是就人恢复天性的真伪而言的。“德”是指人的天性。人恢复了自己的天性,就活得真诚,就是有“德”,就是“善”。天从来都最真诚,因此能够养育万物,生生不息。人只有像天一样为人做事,才可以消除私欲、小我,得其天性。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7] 后来有“不诚无物”的说法,“诚”得到了后世儒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发挥,成为儒学又一个重要的范畴。
由此可知,古人所谓的知天、乐天、事天,都不是空泛玄远的话,而是真切的人生感悟,真正追求的人生境界。用冯友兰在《新理学》中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天地境界”。可见,一个“德”字,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竟有着如此高深宏大的内容。《中庸》中有一段话,可以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德”(不论是天的“德”还是人的“德”)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就是说,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是与天地并立的。人生的使命,就是和天地一起,共同促成大自然化育万物,从而实现大自然的和谐。而这样的人生正是以修身为起点的。
儒家修身非常注重日常养成,注重人成长阶段的规律性把握。一个人只有学会日常生活的洒扫之类,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才算具备了起码的道德修养,将来才可能成为一个对他人和社会有用的人。正所谓“修身”以后才能“齐家”,“齐家”以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修养方式平实自然,符合人的成长规律。相反,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通过个人践行形成最起码的道德,那么,不论以后的道德教育如何强化,也难以使他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德观念的人。
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恰恰只注重较高精神境界的教育和培养,忽视了做人的基本教育。与此相对应,往往只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的外在灌输,却忽视了对学生日常道德养成的引导,忽视了对学生内心世界的塑造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能力的培养。这就容易导致学生道德观念的确立缺乏一个自然而然的自我认同过程,结果把道德视为在我之外的东西,而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并对空泛的道德教育产生逆反心理。我国目前教育改革提倡素质教育,尤其注重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的养成教育,既是源于对道德教育现状的清醒认识,也是对儒家修“德”思想批判继承的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高21世纪教育报告也强调,不仅要使学生有知识、会做事,更重要的是会做人。可见,修身做人已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儒家的修身理论可以为此提供重要的启迪。
四、儒家的“德”和现代的“德”
以上论述了儒家“德”的丰富含义,它的许多内容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的“德”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现实中来。对儒家的“德”,必须批判地继承,既要吸取其积极因素,又要剔除其消极因素。
首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法律与道德,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支撑,但在不同经济条件下,它们的地位和关系又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当社会处在自然经济发展阶段时,人们世代聚居,彼此熟悉和依赖,道德在社会中居于主导规范地位,法律要根据道德原则来建立,并为维护道德秩序服务。如果法律条文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法律必须服从道德原则。在传统社会,这种亲情大于王法的伦理至上主义合乎伦理纲常,顺乎人心民情。我国古代法律就是以维系伦理纲常为目的的,传统道德在古代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
当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阶段时,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人际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和交往对象的频繁变化,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转变成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时社会已很难依靠传统的权威和道德舆论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也不能指望处在物的依赖关系中的个人仅仅通过加强修养来自觉践履道德义务,因为处在物的依赖关系中的人有着作为“经济人”的特征,只要社会存在利益差别,他们就会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倾向。虽然“经济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要受到起码的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然而“经济人”并不必然是有道德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会损害他人利益。而且,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即使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也难以保证他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会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可见,适用于小农社会的纯粹道德约束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是脆弱的,它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人们强烈的利益驱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法律这个普遍而又强硬的监督机制,才可能保证人们遵守道德规范。法律地位的上升,使道德开始以法律为根据,即道德规范根据法律义务而建立,并为维护法律秩序服务。这样,当道德原则与法律条文发生冲突时,道德原则往往要服从法律。我们现在强调以德治国也是建立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之上的,现代道德是作为法律的辅助手段参与国家管理的。
其次,正是社会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区别。
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区别,概而言之,就是所谓私德与公德的差别,表现为它们与公正的关系不同。具体说来,植根于我国小农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的土壤之中的传统道德,大体上属于个人伦理和私德的范畴体系,其根本特征是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等级服从的义务,维护少数人的特权而无视绝大多数人的权利。由于身份、等级等是社会基本价值准则得以形成的根据,使得社会生活领域被极端泛化的亲情关系所挤占,“公共生活”领域极度缺失,公德意识淡薄,所有的价值标准都难以超脱于亲情私德而存在。而这种基于私人亲情关系的私德常常是与公正对立的。孔子曾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8] 在“其父攘羊,其子证之”的道德判定上,孔子认为,隐匿才是合乎道德价值的。很明显,这种道德价值是有违公正原则的。
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现代道德,突出的是社会伦理和公德的范畴体系,它以社会公正为要旨(所谓“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罗尔斯语),推崇一切社会成员的权利平等,张扬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契约精神,其根本特征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因此,我们现在的道德建设既要服务于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变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道德取向为法治取向,又要符合现代的平等精神,剔除儒家“德”的等级服从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合理地吸取儒家“德”的有价值的思想,既有利于我国的道德文明建设,也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