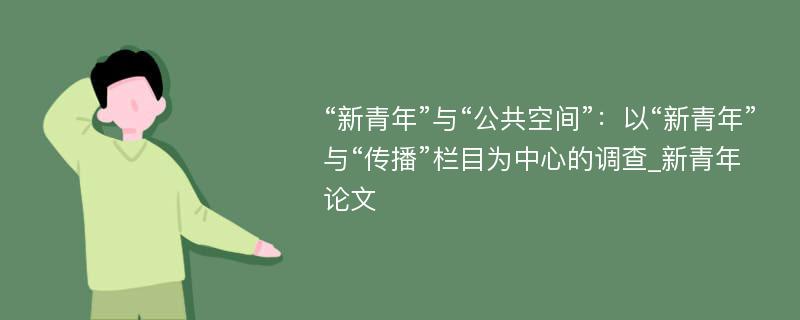
《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青年论文,栏目论文,通信论文,中心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3)03-0079-05
1 引论:近代报刊的民间化和政党化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兴。“凡具数百元之资本,即可创设报馆”,[1]于是,各种新 创报刊层出不穷,成一时之潮流。仅上海一地,1901年~1911年10年间就出版各类日报 和期刊一百多种,这当中还不包括数十种小报和一些仅知其名但已无从详考的报刊。[2 ]“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然 犹茶后之消遣品也。共和告成以来,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近则上海各马路之烟 纸店,均有报纸出售,于是报纸有渐与日用品同其需要之趋势矣。”[3]戈公振这段话 ,从报刊发行的角度清晰地描述了百余年间,报刊如何一步步地由一种不被理解的新鲜 事物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出现的大量报刊基本都是民办报刊。办报人大都没有官方背 景,报馆运营以民间资本为主体,报刊的预想对象也是一般的社会民众,甚至连印刷、 发行都体现了明显的民间色彩。民报勃兴打破了甲午之前官报和外报对报刊传媒的垄断 ,反映了从晚清开始的大众传媒的“民间化”趋势。“相对于官报和半官报,民间化即 是非官方化;相对于外报,民间化则意味着本土化。”[2]民办报刊的相对独立性,使 得它在政治国家之外逐渐开拓出一个新的自主性的社会空间。这是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组 织起来的阅读和交谈网络,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民众都可以在其中方便地获取信息, 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过去只是“一姓之私”的国家大事 ,这时也被当成关乎所有人的“公共”事务接受普遍的关注,承受“公众舆论”的批判 和监督。正如戈公振所描述的那样,“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 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3]在这个意义上,民办报刊 实际成为一种沟通社会民众和政治国家之关系的公共机关,它所拓展的社会空间,正类 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批判性的“公共领域”。
辛亥前后,由于报律松弛,民间报刊的发展更加迅猛,但有相当数量的都是政党报刊 。有的直接以某个政党的“机关报”面目示人,有的虽然自诩为“公共舆论机关”,但 实际上在人事组成和资金来源上都和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 每次论辩实践的交往前提都在于参与者消除和超越党派偏见与自身的特权。这两个前提 必须得到实现,这甚至应当成为辩论的成规。”[4]在他看来,政党组织的偏狭眼光和 固执态度,会破坏公共讨论得以实现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前提,从而瓦解“公共领域”的 “公共性”。民初众多的政党报刊,大体分成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阵 营,它们尖锐对立,为各自的政党利益互相攻讦征伐。再加上每个阵营内部还有派系分 化以及其它一些小政党的刊物,整个报界几成“混战”之势,不只人身攻击,甚至还发 生了殴人毁报的事件。在此背景下,“报纸之功用,纯为私党之利器,互相攻讦,互相 诋諆,而全国报纸,遂无复虚心讨论之心矣”。[5]而一般读者想借报刊自由发表意见 更是不可能,“于是‘议论公开’之说,在我国遂未由实现!”[3]因此,后来罗家伦在 讨论“公共舆论”的建设问题时,第一条就是“报纸公开”:报刊“不但不能受政府或 社会的干涉,而且不能为私人所独占,为党派作机关”。[6]报刊的民间化和政党化两 种趋势的并存,显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公共空间”拓展过程中的内在悖论:一方面, 大量民办报刊的出现为形成一个以公众讨论为核心的社会交往空间提供了可能;但另一 方面,报刊不断增强的党派意识又妨碍着理性的公开运用,使平等、开放的公共讨论很 难展开。“公共空间”在凭借报刊得以建构的同时又在自我瓦解,既不断扩张又处处自 我设限,呈现出特殊的中国的现代性状况。
作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青年》(注:本文讨论的《新青年》指 《新青年》月刊,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终刊于1922年7月1日,共9卷54期,不涉及后 来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新青年》第一卷时称《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 《新青年》。)即在此背景下诞生。从它恰逢其时的创刊,到最后颇具吊诡意味的终结 ,其间戏剧化的演变历程,也正清晰地展示了这种悖论和紧张。本文既不着重关注近代 基层组织和地方精英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也区别于哈贝马斯本人从政治功能角度强调“ 公众舆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而是赞同李欧梵先生的策略,即把整体性的“公 共领域”(public sphere)分解可为复数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把它看做是 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注意对报刊这一文化形式的演变作单独的考察。通过对“ 通信”栏目由“大众”而“精英”而“政党”演变历程的梳理,本文试图廓清《新青年 》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如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发生器,最终 又是如何被政党意识形态所瓦解,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利用报刊这一印刷媒 体,营造自己的言说空间,发出一种既不同于官方又不能归入私人的“社会”的声音等 种种问题。
2 前期:《新青年》与“公共空间”的建构
《新青年》创刊伊始即设立了“通信”栏目,并在创刊“社告”中特意说明:
本志特辟通信一栏,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 ,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
虽然刊物初创时表现出某种明显的“圈子色彩”,但设立“通信”栏目意味着对读者 参与权利的承认和鼓励,使刊物一开始就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而“质析疑难发舒意见 ”云云,则是想把散漫自由的书信往来导向严肃的讨论,但这个规划很快就落空了。
《新青年》第一卷的通信数量、篇幅俱少,第五号甚至付诸阙如。观其性质,大多是 对读书、就学等实际事务的咨询,比如上海有何好学校,自修“中文洋文及算学”应如 何着手等等。本卷通信总共14封,这类书信就占了七八封之多。不过陈独秀倒不以为意 ,有信必答,态度平等而热情。一卷二号上李平投书询问上海的法文学校事,顺便提及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一书,陈独秀就在回信里用了不少篇幅引经据典地比较克鲁泡特 金的“互助论”与达尔文的“竞争论”之异同,以至于后来李平不禁称赞道:“谆谆不 倦,足见记者之热心教诲。”[7]虽说这个时期的“通信”未能成为“质析疑难发舒意 见”的园地,但其事务咨询的功能,倒也与既“改造青年之思想”又“辅导青年之修养 ”的刊物宗旨[8]颇为合辙,更重要的是,编者、读者之间平等开放的交流形式已经确 定下来。
相对于第一卷的冷清,《新青年》的“通信”栏目在第二三卷开始“热闹”起来。这 一方面表现在通信的数量和篇幅都成倍增加,三卷三号一期“通信”的分量(占28页)就 几乎是第一卷全部通信的两倍;另一方面,“通信”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务 咨询类来信越来越少,而各种讨论性质的通信大量出现,占据了“通信”的主导,使“ 通信”栏目的功能开始由“事务咨询”向“编读讨论”转型。这些“讨论”涉及的话题 各种各样,争论最激烈的“焦点”当然是孔教问题和文学革命,它们本身也是同期《新 青年》最为注重的两大主题。
这一系列的变化并非是杂志刊行日久、读者渐多的一种“自然”现象,相反,它是陈 独秀有意为之的成果,反映的是这一时期《新青年》编辑方针的调整和自我形象的重构 。在二卷一号上,陈独秀表示:“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 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真理愈辩而愈明也。……以后如有析理辩难之文见 赐,必当照录,以资讨论,否则无取焉。”[9]这里对“析理辩难”因素的强调,其实 是对自己设立“通信”栏目初衷的重申,它意味着陈独秀开始有意识地试图削弱“通信 ”栏目在前一个时期“事务咨询”的色彩,转而为“析理辩难”的“讨论”开拓更大的 空间。与此相适应,《新青年》从第二卷开始新设“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 ”,“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10]进一步向读者开放刊物空间。
这一时期的《新青年》通过对一系列刊物策略的运用,一方面拓展了读者对刊物的参 与空间,另一方面也把这种读者参与导向一种更加严肃的公共讨论。也就是说,这个交 往空间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就读书、上学等“私人”事务交换信息,而是要对人们共同 关心的“公共”话题展开论辩,以期“真理愈辩而愈明”,最后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 为,“公共领域”的成败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 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当时在“通信”里,与陈 独秀展开讨论的读者大多已不可考,就能确定的而言,既有青年学生、教员、学者,也 有银行职员、军人、工人,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职业,具有相当的包容性。陈独秀对 来信也一体对待,对旧朋新友固然热情,就是素昧平生的一般读者也决不慢待,还常常 以“连环通信”的方式和他们耐心讨论,既坚持己见,又大方地接受批评。周策纵据此 认为,《新青年》的“通信”一栏,“在许多方面成了中国杂志上第一个真正自由的公 众论坛,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思想都在这里得到认真的讨论和发展”。[11]就这样,一个 平等开放的公众讨论空间逐渐建构起来了。
从第四卷起,《新青年》改组为北大的“同人刊物”,“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 ,公同担任,不另购稿”。[12]刊物的编辑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改之前由陈独秀独立 “主撰”的样式,成立了由北大同人为主的“编辑部”,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 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然后再由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刊物性质以及编辑方式的变化,使 《新青年》刚刚建立起来的“公共”形象呈现出某种微妙的张力。
《新青年》在四到六卷里,登载了大量同人及其朋友之间的通信,占到通信总数的一 半以上,而一般读者的来信则明显减少,使得这一时期的“通信”栏目更像是个“同人 论坛”,而非第二三卷时那样的编、读讨论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刊物对这两类通信表 现出的“内外有别”的态度,事实上造成了“通信”栏目的形象分裂。对刊物同人而言 ,它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论坛,在其中,大家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互相质疑甚至激烈争 辩。由于具有接近的文化取向、知识结构和社会身份,以及彼此相熟的人际关系,同人 之间的讨论往往可以在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中进行,也更具建设性。比如围绕“世界语 ”的问题,同人们就分成赞同和反对两派,在“通信”栏里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论战, 针锋相对,全无之前“小批评大捧场”的默契。虽然最后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无 疑大大深化了对世界语问题的思考。但是对一般读者的来信,同人们就不复以前的热心 ,往往不屑耐心讲理,只用“恕不奉答”四字便打发过去。鲁迅的态度很有代表性,他 在给钱玄同的一封信里说:“《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爱看。但据 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以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 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 。”[13]对读者的商榷意见,不少同人更是没有以理服人的气度,动辄冷嘲热讽,甚至 以“野蛮人”、“尊屁”、“粪”等粗语相赠。其蛮横的态度不但遭到很多读者的批评 ,就是在新文化阵营内部也不被认可。罗家伦当时就曾委婉地批评道:“虽然对于现在 顽固思想,应当极力扑灭;但对于非绝对不可救药的人,总当予以回头的路。我们言词 之间,苟能‘哀矜勿喜’,那我们革新的事业,更容易推广得多。”[14]
这种“内外有别”的态度,反映了《新青年》同人日渐浓厚的集团意识和精英意识, 显然破坏了保障公共讨论得以展开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原则。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 同人内部每个人的态度并不一致,胡适就很“特殊”。五卷一号的“通信”里登有汪懋 祖的一封来信,批评《新青年》“如泼妇骂街”、“似不容人以讨论”的霸道作风。胡 适在回信里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表示:“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 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在胡 适轮值主编的六卷四号上,蓝公武来信直言批评《新青年》随意谩骂的态度,认为“令 人看了生厌”,甚至点名批评了刘半农、胡适都不以为忤,还引用上次答汪懋祖的那段 话,再次表明自己主张平等讨论的态度。放在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常与读者“对骂”的 背景下,胡适的“特殊”姿态表达了他对同人的异议,以及试图扭转刊物形象的一种努 力。这使得我们很难用封闭——开放、霸道——平等这些截然对立的措词来简单描述这 个时期的《新青年》形象。
这种情形的出现,根源于“集体讨论-个人主编”这种特殊的编辑方式,它既可以避免 刊物成为个人意志的宰制对象,又给每个编辑同人表达自己的立场保留了余地。本着“ 各就所能,各尽厥职”的共识,同人之间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制衡,从而避免了由(个人 或集体的)偏激化带来的单一和封闭。除此之外,《新青年》同人的激烈态度多少也是 对新文化运动在当时遭受种种压力的防御性反应,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在私下 里,他们未必不认同尊重读者异议的道理。钱玄同曾经就戏剧改良问题给胡适写过一封 信,在信里他表示,“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 ”,但马上他又补充道:“如其通信,却是可以”。[15]后来在给周作人的两封信里, 他又对陈望道等人擅改读者来信里的用字一事大表愤怒,甚至说:“我现在对于陈望道 编辑《新青年》,要看他编辑的出了一期,再定撰文与否。”[16]激进如钱玄同都如此 替“通信”栏目的独立性辩护,也可以反过来证明,《新青年》的“同人刊物”性质虽 然不利于普遍讨论的展开,但它本身并没有瓦解和取消读者参与空间,甚至在某种意义 上还为公众讨论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可能。《新青年》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真正瓦解 ,是从七卷以后开始的。
3 后期:《新青年》与“公共空间”的瓦解
从第七卷开始,《新青年》发生了某种“转折”。先是结束同人“集体讨论-个人主编 ”的模式,改由陈独秀独立主编;接着从第八卷起,刊物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作为党的机关刊物。
在此期间,曾是《新青年》上最生动最丰富的部分之一的“通信”栏目急剧萎缩,先 后有8期没有“通信”,而这种情况在前六卷一共只出现过两次,而且还都是一些外在
因素使然。后三卷一共只刊登了30则通信,平均下来每卷只相当于前两个时期的几分之 一,甚至少于刚创刊时的第一卷。而且来信常常不复,复信率之低(3∶2)是以前没有出 现过的。即便回信,陈独秀也往往是寥寥数语,心不在焉,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热心。与 此同时,《新青年》上另一个对读者开放的讨论空间“读者论坛”,从第七卷开始也取 消了。而在另一方面,当初众声喧哗的“随感录”这时成了陈独秀及其党内同志的“专 栏”,新开的“俄罗斯研究”,每期都会用大量篇幅翻译各种关于苏俄的文章,以致于 胡适批评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了。随着陈独秀的 个人意志和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越来越深的左右刊物,《新青年》已经变得“色彩过 于鲜明”了。
迄今的研究,常常把“谈政治”——前期不谈政治,后期要谈政治——看成是《新青 年》前后期转向的标志,也把在“谈不谈政治”问题上的分歧——陈独秀等人主张谈政 治,胡适等人反对谈政治——看做是《新青年》同人圈子分化解体的原因。虽然陈独秀 在创刊伊始就宣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这多少有迫于袁世凯政治高压的苦衷, 而且,刊物“国内大事记”一栏持续关注“国体问题”,实际上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暗 寓褒贬,抨击袁世凯的专制政权。到第二三卷,袁世凯倒台,陈独秀就开始大胆论政, 连续在刊首的醒目位置发表《对德外交》、《时局杂感》等文章,介入当时的“府院之 争”。当有读者为此投书表示不满时,陈独秀回答得理直气壮:“本志主旨,固不在批 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17] 文意直启后来那篇著名的《谈政治》。变成北大的同人刊物之后,由于胡适“二十年不 谈政治”的承诺,《新青年》的内容大体“趋重哲学文学”,但在一战结束后仍然刊登 了《去兵》、《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和平会议的根本错误》等和当时政治形势直 接相关的评论文章。这样看来,“谈政治”其实是《新青年》一条一以贯之的思路,只 是有时彰显有时隐晦罢了。事实上,《新青年》后三卷与前六卷的真正区别,不在“谈 政治”本身,而是谈论政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开始以一种“政党”的立场来谈论政 治。
出于对辛亥以后党争纷乱的反省,陈独秀有意识地标榜《新青年》的非党派姿态,主 张“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认为“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 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18]作为一份典型的民办刊物,《新青年》在前期一 直恪守自己的非党派立场。从第七卷开始,《新青年》重归陈独秀独立主编。这时的陈 独秀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来越多地注入刊物 之中。等到开始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出版,《新青年》正式变成了一个政党 刊物。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前期《新青年》其实是以一个普通“公众”的身份谈论政 治和监督政府,这正是建构一个批判性“公共领域”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种论政方 式不会影响公共交往的开放性。比如陈独秀在鼓吹“对德宣战”的时候,“通信”栏目 里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正趋热烈,并不受其影响。陈独秀一直心仪“法兰西文明”,感 叹“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19]但也登载过多篇刘叔雅等人鼓 吹铁血政治和军国主义的文章。然而,刊物一旦以“政党”的身份参与政治论争,就会 使“批判的公共性遭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从而瓦解这个公共交往空间。在哈贝马 斯看来,政党的言论只是一种“宣传”,其目的是想“加强自己立场的声望,同时又使 要妥协的事情本身不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它以一种“展示机制”替代了公共领域的 “批判原则”,相对于公共讨论的开放和自由,它却想把人们不同的意见整合成一种声 音,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服务。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通信”栏目为什么会在这 个时候突然萎缩。作为政党的机关刊物,它的任务就是要宣传和灌输某种特定的政治主 张,不但不需要而且还要努力制止各种不同的看法的公开讨论。像“通信”栏目这样不 能由编者完全控制的杂语之地,往往会对意识形态权威构成潜在的挑战,因此必须小心 地加以整肃、削减乃至取消。“通信”栏目的萎缩和终结,表征了由《新青年》所建构 起来的那个“公共空间”的衰落和解体。
4 余论:“公共空间”与中国现代性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近代报刊民间化和政党化两种趋势都在《新青年》( 也包括“通信”栏目)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其间的相互纠缠和此消彼长,正从一个特 定角度投影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公共空间”的伸缩历程。正如哈贝马斯本人所强调的, “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 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 中”。[20]作为一个带有强烈西方经验色彩的概念,它并不能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找到 自己完美的现实范本。因为它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某种“第三领域”,所以无论从 逻辑上还是历史上讲,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市民)社会二元对峙的格局都 是其存在的前提,但这种清晰的分化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反而总是陷于哈贝马斯所担 心的国家社会化、社会国家化相互混杂的困境之中。就文化观念而言,中国人对“公” 、“私”关系的理解也极其暧昧,既有“大公无私”的说法,又有“一姓之私”的传统 ,与西方的“公私分明”的观念大相径庭。这种种因素,加上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 的过度焦虑,使得现代中国的“公共空间”始终在建构、解构之间转换挣扎,成为一个 总在进行之中的未完工程。这与个人的作为无关,而是某种历史的“宿命”使然,反映 的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历程。或许真的如帕克所说,“报刊的存在,不像我们的道 德主义者有时想象的那样,是由一些活跃的人们所组成的小组织的任意产物。相反,它 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有许多人参加进来了,而同时又不曾预见他们各自 的劳动的最终产物是什么。”[21]
收稿日期:2003-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