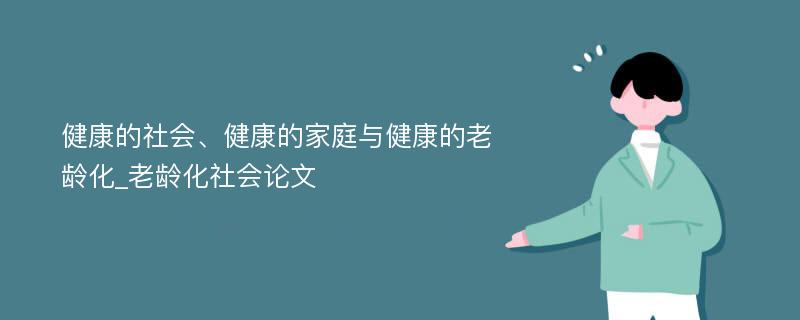
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家庭与健康的老龄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健康论文,家庭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昌明,人类在延长寿命和节制生育两个方面都不断地取得成功,老龄化现象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跨入了老年型行列,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朝着老龄化的方向前进。1982年维也纳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会议宣称21世纪为人口老龄化时代。据专家学者预测,我国也将于2000年成为老年型国家。
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它关涉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值得广大的专家、学者、政治家及社会活动家认真研究和对待。
健康的老龄化,这不仅是一个崭新的重要的观念,也是一个迫切需要积极解决的现实问题。当然,健康的老龄化跟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会又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着的。对此,笔者愿意发表一些自己的浅见。
一
老龄问题作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在本世纪才逐渐明显起来的。在上世纪,人类还没有意识到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因为那时各国的平均预期寿命都还不高。19世纪末,日本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为42.8岁,女为44.3岁。192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为53.6岁,女为54.6岁。时代更早一些,或者发达程度更低一些,那么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就更短。据记载,在青铜器时期(希腊)是18岁,距今2000年左右(罗马)是22岁,中世纪(英国伦敦)是33岁,1789年(美国麻省)是40.9岁。[①]在1900年以前,只有欧洲的少数国家跨入老年型的行列。1866年法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7.2%,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老年型的国家。到19世纪末,也只有瑞典、挪威成为老年型国家。[②]进入20世纪后,人口老化的速度逐渐加快。到1950年,全世界有15个国家和地区跨入老年型行列。到1988年,跨入老年型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已有57个,其中欧洲国家有43个,比例最高。[③]
在世界上,我国人口最多,老年人口也最多。但是,在80年代以前,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大,增长速度也不快。1953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是4.41%,1982年是4.91%,30年只增长0.5%,都还处在成年人口型的初期。从80年代开始,由于有效地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而且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医疗卫生日益进步,死亡率大幅度降低,老年人口比重逐渐上升,人口趋于老化。从1980年到199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7364.4万增加到10115.8万,增长率为37.4%,而同期总人口增长率为12.8%;同期全世界老年人口增长率为27.2%。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比总人口增长速度快24.6%,比世界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10.2%。据有关学者测算,从1990年到1995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要上升到6.4%;从1995年到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上升到7%,开始成为老年型国家。而且,接着将有近40年的高速老化期。预计到2040年,我国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17%,成为一个成熟的老年型国家。如果我国措施得力并有效,也许2030年可以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而到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才有可能开始逆转,老化程度有所下降。
显而易见,无论从全世界看还是从我国看,从现在到下世纪初,都处在人口老化的进程中,银发浪潮正气势恢宏地汹涌而来。
面对着滚滚而来的银发浪潮,我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采取了积极迎接的态势。1980年第35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把1982年召开的老年人世界大会定名为“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同时还要求各国成立老龄委员会,从而在国家范围内广泛开展活动。我国积极响应,198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接着,1983年4月,又成立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随后,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地方的老龄问题委员会,而且深入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公司、商店等,很多单位也陆续建立了老年工作机构。1983年10月,我国第一个以老年人为对象的全国性杂志《中国老年》创刊。而且,一些省市也纷纷办起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报刊,全国陆续出版发行了大量有关老年方面的读物。1983年,我国的第一所老年大学——山东老年大学创立,接着,很多省、市、县、区,甚至机关、学校、企业、街道、乡村都纷纷建立老年大学或老年学校。这些学校能把老年人更好地组织起来,发挥特殊的教育功能,积极的保健功能和养老功能,能帮助老年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振奋精神,再造辉煌,提高生活质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要,很多养老、敬老、乐老,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和设施纷纷建立。我国紧密联系实践,确立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这五个“老有”为中心的老年工作原则。以中央电视台的《夕阳红》为代表的一些老年节目专栏也在若干个电视台陆续开播。现实生活及各种传媒,都显示出我国老年人金光灿烂如瑰丽红霞的美好晚景。
二
离退休后的老年人应该如何对待社会活动?这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最基本的有两个路数:一种主张休闲;另一种主张继续积极活动。前一种认为随着年岁的增长,老年人逐渐不像过去能干或可以依赖,因而必须由年轻的人来代替,并且老年人自己也会感到精力衰退而选择退隐和休闲。后一种观点认为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是维持充沛精神状态的重要手段。老年人在离退休后会脱离若干年来一直对自己的生活极为重要的角色,缩小社交范围,降低活动水平,产生失落感,甚至动摇或丧失自我认识。为了弥补这些损失,继续保持充沛的精神状态,维护自我认识,就需要一种以补偿性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复原。这就是说,老年人可以通过继续积极活动在社会和心理上保持适应,可以由于继续保持适度而积极的生活方式而显著地维持自己的幸福观念。总之,积极地保持适度的活动水平,会使老年人所要求的角色认同更能得到有力的支持;而稳定的角色支持有助于确保稳定的自我认识;老年人的自我认识越明确越稳定,生活的满足程度就越大,也就越会感到幸福。
当然,休闲论与活动论这两种似乎互相对立的观点,很可能实际上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不过,笔者更倾向于赞同活动论的观点,主张老年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该继续积极活动。如果有条件,更应该适当地再参加工作,因为这有助于使老年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保持健康;有助于为社会作出贡献,增加社会效益;也有助于老年人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作为我国老年工作的根本原则的五个“老有”中,“老有所为”处于重要的地位。全国老龄委名誉主任陈丕显讲过:“解决老龄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五个‘老有’中养,医、学、乐都是要消费、要花钱的,而‘为’是积极的,最活跃的因素,它能体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创造社会财富……发展老有所为应当是老龄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积极对策。”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切实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离退休干部,使他们老有所为,安度晚年。”老有所为,也就是要让老年人再造辉煌,作出新的贡献,更有意义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二次青春。老年人不应该消极地面对着苍凉晚景而无能为力,却应该积极地自觉地自为自助,再造辉煌,健康地、潇洒地走过生命中又一段路程,再一次奏响生活的华采乐章。
三
按退休年龄划线,我国以年满60岁算进入老年期。但是有的学者把人的60岁到90岁这一阶段称为第二青春期。1990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正式提出“健康的老龄化”这一目标。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健康的老龄化要求人们在第二青春期都处于健康的状态。
那么,什么叫“健康”呢?《辞海》认为,健康是“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劳动效能的状态。通常用人体测量,体格检查和各种生理指标来衡量”。这是纯粹从生理上讲,没有考虑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健康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安全安宁状态。”[④]或者说:“健康是指一种完美的身心和社会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不生病或不虚弱。”[⑤]这样定义的健康包含着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包含着老年人的快乐和幸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是以婚姻或血缘(包括领养)关系为基础,由共同生活并有相互责任的人们组成的单位。就家庭基本构成的主体而言,婚姻关系是建立家庭的基础和核心。家庭是人们特别是老年人生活起居的主要处所,因而健康的家庭跟健康的老年生活是紧密地联系着的。这不仅对那些完全或主要依赖家庭赡养的老年人是如此,而且对那些在经济上摆脱了家庭赡养的老年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老年人不仅需要物质赡养,尤其需要精神赡养。在健康的家庭中,老年人得到健康的爱情和亲情的滋养,就能更好地享受健康的老年生活。当然,这一方面需要老年人善于正确地协调夫妻关系与代际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婆媳关系或翁婿关系、祖孙关系或外祖孙关系,等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年轻的一代和年幼的一代正确地对待老年人,奉献给爱心和孝心。
总之,健康的家庭为健康的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环境,而且又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健康的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又是健康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广大的众多的健康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就构成了整个地区、整个国家或整个社会健康的老龄化。
全面的完整的健康概念,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不仅仅是不生病或不虚弱”,它还应该包含着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因此,健康的社会与健康的老龄化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古代思想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他们所理想的健康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者皆有所养。”[⑥]这也就是所谓的“大同”社会。我国历代很多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都曾受过“大同”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即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毛泽东就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⑦]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解放以后,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我们走了不少弯路。例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很快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而一举解决包括“养老”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结果造成了三年大冒进,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从60年代到70年代,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弄得民穷财尽,使国家和社会处于动乱之中。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积极而稳妥地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老年事业方面,积极完善离退休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福利事业,大力兴办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加强尊老、爱老的立法工作和社会舆论,为健康的老龄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创造健康的社会环境。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贯彻和实施,全国各地“助老工程”的启动,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正根据江泽民总书记“重视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创造积极迎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这样,我们在建设、健全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时也就在切实努力地实现健康的老龄化。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出现的客观现象和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日益逼近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我国,银发浪潮在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在更多的地方正迎接它的到来。健康的老龄化是有科学根据的,可以实现的崇高目标。实现健康的老龄化又是跟建设健康的家庭和健康的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的老龄化而奋斗。
注释:
① ② ③《老龄化对中国的挑战》,袁缉辉、张钟汝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2页。
④《普通逻辑》(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3版,第291页。
⑤《金色晚年——老龄问题面面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⑥《礼记·礼运》。
⑦《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2版,第四卷,第14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