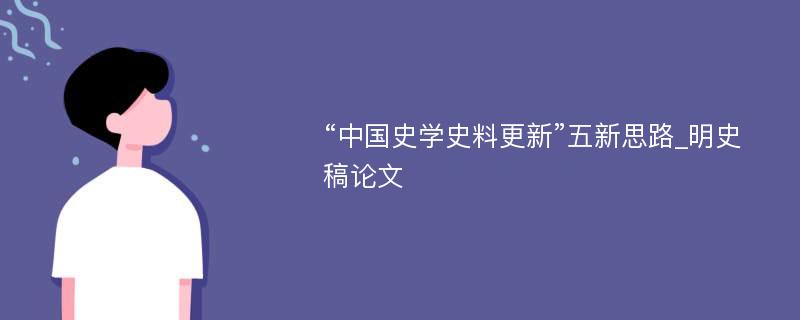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新识五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资料论文,史学史论文,新识五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2-0019-08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四卷本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之后,有多篇专题书评予以肯定,指出“本书用第一手资料勾勒出中国史学的博大画卷”①。而学术探讨永无止境,史料的发掘和考订也是持续推进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必然会留下还未理清的环节,存在尚须阐明的内容。这里谨述重读本书的几点新思考、新领悟和新考核,以求中国史学史学界同仁的指正和切磋。 一、《宋书》、《魏书》均为官修史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下简称《增订编年》)承袭杨翼骧先生原书的布局,在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一册)对于沈约《宋书》、魏收《魏书》,收录资料较多,使其编纂状况能够较为清晰地显示出来。众所周知,《宋书》、《魏书》后来纳入正史系列,且部帙较大,资料丰富,值得重视。对此二书,历来研究者多有评述,但大多没有明确地判别是属于官修史还是属于私修史,甚至缺乏这种区分官、私的意识,实际多是将之等同于私家修史来议论的。一般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似乎不一定非要区分官修史与私修史,但假若将中国传统史学置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而又互有排抑的双轨发展中予以考察,辨别重要史书是否属于官修史就十分必要了。 一种古代史籍是官修史还是私修史,有时特征明晰,容易划分,有时则比较模糊。唐朝之前,史馆制度尚不完善,官方修史的情况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有明确、允当的判断标准。在中国史学史上,官方史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项内容:1、官方切实控制和管理下的史籍编纂;2、制度化、规范化的记史和修史机构;3、官方编辑的史料和官修史书;4、官方历史观与史学思想;5、官方史学的学术地位及其政治性的作用。其中第1条是判断一部史书是否属于官修的主要依据,如果一部史书在其编纂过程中,历史观点、史书体式、内容取舍等主要问题受到官方切实的管控,那就属于官修史。这里的“官方”指的是政权组织或机构,官员发出的指示必须代表和执行一个政权的意志,而不是他个人的意愿,才可认为是官方,但皇帝的谕令,则可以代表朝廷意志,即为官方的干预。 关于《宋书》,《增订编年》依照杨先生原书第一册,载有南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沈约开始著作《宋书》”条,而次年即载“沈约著成《宋书》纪、传七十卷”,并且将之进呈齐武帝,《进书表》中较为细致地列举了自刘宋以来,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多人主持编纂此书的状况。沈约乃是修订前人之稿,故于一年内即写定纪、传七十卷,此乃官方修史活动积累的成稿。沈约做出较大贡献者,是进献《宋书》纪、传之后,修订和撰写“八志”30卷,这一编纂事项,虽然于梁武帝天监年间才最终完成,但主要工作也应当是在南齐时期基本就绪。②有记载表明,齐武帝对《宋书》的编纂是很有干预的,如《南史》卷七二《王智深传》记述沈约编纂《宋书·袁粲传》,就曾送齐武帝审阅,被指示要按“宋家忠臣”来撰写。沈约“又多载(宋)孝武、明帝诸亵黩事,上遣左右语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③可见沈约是在朝廷的直接管控之下修史,因此《宋书》应该定性为官修史书。 关于《魏书》,情况与《宋书》类似,魏收虽然是主要编纂成书的作者,但第一,魏收主持的《魏书》编纂,是承袭了前此官方纂修的既有史稿;第二,魏收等人在朝廷切实的管理、控制之下进行编撰。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很早就开始了本国史的编纂,虽因公元450年崔浩史狱的发生,中断了10年,但至公元460年,即恢复史官建置。此后持续未断,魏孝文帝时期更有发展。著名史家高允、刘模、李彪、崔光、高祐、崔鸿等历经任职,魏收则自东魏时参与编修,北齐时主持其事,另有多名史官协助,承接前此成果,裁定成书。这在《增订编年》中历有载录,线索明晰。《魏书》载笔多有揭发北朝土族丑事,引起众口喧嚣,曾导致朝堂辩论,由北齐文宣帝亲自裁定是非,制裁了攻击《魏书》的势力,同时也两次命令魏收修改《魏书》,这些情节皆载于《北史·魏收传》,而《增订编年》按时间将载录析出,分别于公元560年和566年专立两个题目:“魏收奉命修改《魏书》”和“魏收再度奉命修改《魏书》”④,彰显朝廷对纂修《魏书》的干预。魏收于公元572年卒后,次年北齐又曾“诏史官更撰《魏书》”⑤,总之《魏书》乃在朝廷的切实控制、管理下编纂,属于官修史性质。 一部古代史书是否属于官修史,有时因资料的残失或缺载而难于辨别,其判断的标准,不能根据史书的思想倾向,也不论官方是否予以支持和资助,只应当考察该史书纂修进程之中,官方是否切实施行了管理和控制,这是最允当的衡量尺度。 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条目遗留的问题 朱熹《通鉴纲目》一书,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著述,影响深广。南宋之后,直与孔子《春秋》并称,曰“《春秋》大义,《纲目》大法”,视为历史观念之圭臬。《增订编年》于公元1172年立“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条,⑥基本依照杨翼骧先生原书资料,篇幅已经相当可观,未多做补充修订。然而这遗留了一些史学界意见分歧,且尚未解决的问题,十分需要进行学术研讨。 第一,《通鉴纲目》何时完成初稿?汤勤福先生根据朱熹于淳熙九年(1182年)十一月上书宋孝宗,说到《通鉴纲目》“数年之前草稿略具”,认为:“《通鉴纲目》的初稿至少完成于淳熙七年(1180年)二月之前”⑦。其实早在1994年,叶建华先生即已发文考订这个问题,引证朱熹《答吕伯恭》书中“《纲目》草稿略具,俟写校浄本毕,即且休歇数月,向后但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劳心也”,指出《通鉴纲目》初稿完成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⑧这个考订是成立的,后来郭齐先生为驳汤文,再次引用同样史料重申以上结论,⑨此项史实已能得以确认。 第二,关于曾经单行的《通鉴纲目凡例》,争议颇大,汤勤福先生直指现存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为伪造,而且是与所谓朱熹致赵师渊的“八书”(八封书信)联结一起,原因是现存《通鉴纲目凡例》与“八书”,早年无人知晓,据称都是几十年后朱子后学王柏从赵氏家中得到,二者来源一致,故同是伪造。⑩朱熹撰写《通鉴纲目》先成《凡例》,这在他与门人、友人的书信中多次谈到,若断定现存本是伪书,须有确证,郭齐先生的文章指出汤文的辨伪,缺乏可以成立的理据。对于朱熹的文集何以未曾收录“八书”,郭文解释为“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种种复杂情况,是常有的事”,直至现代,还曾发现朱熹的佚文。(11)但他却未解答汤文的质问:在朱子后学编纂朱熹文集之时,作为朱熹弟子的赵氏,为什么不提供这八封书信? 第三,赵师渊在《通鉴纲目》的编纂中有何作为?一种意见是认为朱熹定“纲”,弟子赵师渊撰“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即如此论述。又一种意见则强调赵师渊不仅撰“目”,而且参与定“纲”,应当是主要作者,刊印此书应该题写赵师渊之名。(12)而认为“八书”本是伪造的学者,自然就否定了赵师渊曾经参与《通鉴纲目》的编纂工作。 根据现存资料以及对史学界不同观点的清理,《通鉴纲目》编纂状况可以概述如下: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决计编纂《通鉴纲目》,首议《凡例》,且随即开始编辑。有蔡季通、李伯谏等多人协助,朱熹本人裁定。至乾道八年(1172年)《通鉴纲目凡例》已经完成,史稿正文也进展迅速,初具规模,朱熹此时信心百倍,故撰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序》一文。至淳熙二年(1175年),已然“草稿略具”,即完成初稿。这在前揭叶建华之文章中有所考述。 此后,朱熹对书稿开始做全面的修订工作,淳熙三年至五年颇有成效,但淳熙六年以后,由于官职外任,修订之事有所因循,而且越来越感到艰难。其原因是全盘修改此书,不仅要使内容和表述符合自订的《通鉴纲目凡例》,而且史事考证、文字校订,不胜其烦,故每有“大惧不能卒业,以为终身之恨”(13)的感慨。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上书提到修订《通鉴纲目》事,意欲争取朝廷给以大力支持,然而希望落空。因身体多病,缺少助手,其后史稿的修订使朱熹更为力不从心,常常在信件中叹息缺乏专力助手,难于进展。 朱熹的学生人数甚多,但其中缺乏史家,修订《通鉴纲目》又难度极大,任凭朱熹叹息,仍无人敢于应承。迨至晚年,终于有赵师渊领受了《通鉴纲目》的修改工作。那么赵师渊是哪一年开始承担此务?笔者认为绝不早于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理据有二:赵师渊先曾为官,不可能承当修史之任。庆元元年(1195年)才免官东归,不再复出,此其一;庆元二年朱熹在《答辅汉卿》书信中称:“诸书无人整顿,抄寄然改处亦不多”(14),可知赵师渊此时尚未担负“整顿”《通鉴纲目》之事。 赵师渊作为朱熹的学生和朱家的亲戚,可能出于对老师的同情而担负修订《通鉴纲目》的重任,无奈其见识、能力不佳,结果不仅未能完成,而且颇多舛误。赵氏仅从事修订工作三年,朱熹即已逝世,此后不了了之。朱熹后代与众多朱门后学,也必定对此大不满意。赵氏心有赧然,自然不好意思公布朱熹关于修订《通鉴纲目》的“八书”,而朱熹后人编辑朱熹文集,也对这样的书信不予重视。又因《通鉴纲目》之文远不能契合《通鉴纲目凡例》,后来刊刻全书便舍弃了《凡例》。孰料几十年后事过境迁,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却钩沉发隐,令《通鉴纲目凡例》与朱熹“八书”再现于世,且引出种种误解,这是《通鉴纲目》整个编纂、流传过程中的一场尴尬。赵师渊于《通鉴纲目》贡献不大而疏失颇多,历代不少学者对本书多所指摘,赵氏难脱缺欠史才、修订不力之责。 三、《咸宾录》撰成之年及刘坦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 《增订编年》元明卷收录明代江西豫章人罗曰褧著《咸宾录》一书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乡人刘一焜所撰《〈咸宾录〉序》,其文篇幅较大,评介详细,而且说明了本书撰写的时间问题: 《咸宾录》者,录四夷之事也。曷取乎四夷之事?胪列众卑以承一尊而已。……《录》之创造,岁在实沈,成在寿星,在大火阏伯之辰而授之剞劂,传之博雅君子。万历辛卯仲夏月,豫章刘一焜元丙父撰。 “实沈”、“寿星”、“大火”,都是星岁纪年的术语,需要转换为确切的明朝帝王纪年和公元纪年。我在家乡天津市武清县读中学时,就听到本县人物刘坦的传奇故事,据称在古年代的考证上大受郭沫若的赞赏。1978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居然从图书目录中发现有刘坦的著作《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至1996年前后,杨翼骧先生编著第三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需要判定《咸宾录》的撰成之年,而一时无法措手,遂将此事对我谈起,认为这种星岁纪年问题,很需要可资参考的书籍。于是,我说起中学时期所闻之事,建议杨先生是否参阅《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可能有所裨益。过了一段时间再与杨先生会面,先生十分高兴地告诉我,参考刘坦的这本书,问题已经解决,年代可以确定,并且拿起书桌上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盛赞其学术精深,指示应当认真阅读。我接过来予以翻阅,如若天书,茫然若坠五里雾中,竟然搁置多年未读。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出版,见书中“罗曰褧著成《咸宾录》”条目有案语曰:“罗曰褧《咸宾录》之著作年代,刘一焜序称‘《录》之创造,岁在实沈,成在寿星。’据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推算,实沈当为万历九年辛巳,寿星当为万历十三年乙酉,故编于此。”然不解杨先生究竟如何推算出结论。笔者近年从容阅读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及相关论著,终于稍可了解其中奥秘。 刘坦(1910-1960),武清县王庆坨镇人,潜心研究古代纪年问题,早年撰有《〈史记〉纪年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1950年代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著有《论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5年)、《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其中《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近27万字,内容丰富、功力深厚。刘坦是值得关注的历史年代学家,但因独自于乡间研究学术,并且早逝,于今知之者甚少,应当彰显其人其事。 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木星大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为此将天空划分12个星区,称为十二次。木星每行经一次,古人曾经以其所处星次位置纪年,故称木星为岁星。但岁星并非正好12年运行一周天,而是11.8622年,这样对于观测者而言,经历若干年后,岁星就会超过一个星次,是谓“超辰”。而且岁星的行进方向,与日月及其他恒星运行方向相反,也使观测纪年有所不便,于是又想象出一个的星体,取名曰“太阴”,后改称“太岁”,按照12个地支标识的天宇区域(即“十二辰”)顺序运行,速率类似岁星但与之方向相反。按照西汉末年刘歆《三统历》的设定,岁星从“星纪”位次起始,太岁从甲子位起始,二者相邻,相对运行,岁星每到一个星次,就以太岁同时到达的地支标记其年,当然也可以用星次名称表示纪年。12年一周期,若配以天干,运行五周乃一个甲子。此外,还有将天干、地支皆按先秦的岁阳、岁阴名称,用以纪年,亦源于星岁纪年法,例如甲寅年写作“阏逢摄提格”。这与《三统历》不同,也与本问题无关,且不具论。 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详细地梳理了《三统历》纪年法,列出其唐尧至东汉光武帝的年表,画出其星岁运行与纪年的多幅图表,显示出岁星星次与太岁地支的对应是确定的,这12个对应关系是:星纪——子,玄枵——丑,娵訾——寅,降娄——卯,大梁——辰,实沈——巳,鹑首——午,鹑火——未,鹑尾——申,寿星——酉,大火——戌,析木——亥。(15)即在纪年上凡言“星纪”,必是子年,凡言“实沈”,即为巳年,依此类推。 东汉时期逐步摈弃了星岁纪年,独立地使用干支纪年法,与岁星、太岁全然剥离,大为便利,后历朝历代沿袭。但是,有些学者为示古雅,仍故意使用岁阴岁阳纪年或用星次名称表示纪年,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全书皆以岁阴岁阳名目配合帝王纪年,偶用星次名称标识年代者也时有出现,刘一焜《〈咸宾录〉序》即为一例。但是,东汉之后的这种岁阴岁阳纪年以及星次“示年”的做法,仅仅将干支进行固定对应名称的转换,并非对岁星有什么观测,也是与当初的星岁纪年法脱离了干系。刘一焜《〈咸宾录〉序》所谓“《录》之创造,岁在实沈,成在寿星”,不过是说此书始修于巳年,完成于酉年,“大火阏伯之辰而授之剞劂”是戌年开始刊刻。这里只有地支而无天干,但撰《序》时间已写明为“万历辛卯”即万历十九年,而同乡友人撰《序》,一般不会距成书之年过于久远,于是从《中国历史纪年表》可以查到万历十九年之前最近的巳年是万历九年辛巳,酉年是万历十三年乙酉,遂知成书之年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当然付刻时间是在次年即丙戌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刘一焜标识的星岁纪年乃是依照《三统历》的现成说法,若依取其他典籍例如唐朝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三对星次对应地支的解说,则不着边际,无法解读刘一焜之《序》。因此,细读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对《三统历》的深入研究,实为推定《咸宾录》成书之年的关键。 四、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书名说起 《增订编年》于元明卷补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修成”条目,事在公元1636年,(16)其中节录了《满文老档》与康熙朝所修《清太宗实录》的记载之文。于是呈现了一个问题:这部清入关前修成的实录,书名究竟是什么?其称谓有何演变?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原始性资料,在书成进呈表文中的全称是“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太后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实录”,这样一堆庙号、尊号、谥号构成的书名,只是在进书仪式和重大典礼上应用,一般提到之时皆用简称,此一条记载的标题即为“(十一月)十五日,《太祖太后实录》告成”(17)。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实录的名称乃“太祖”与“太后”并列,所谓“太后”,即清太宗生母叶赫纳喇氏。她于戊子年(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嫁与清太祖(18),年十四,于辛丑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即已死去(19),年仅二十七岁,其死时距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天命政权尚有十五年,对清太祖一生创基立业活动关系甚微,而实录修成后竟以太祖、太后并列于书名,违背历代纂修实录的体例规则,显然是阿从清太宗私意。这部实录用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分栏书写,并且配以插图,行文用语,也不合传统的皇帝实录体式,是当时清廷虽立意仿从汉人政权纂修实录,但纂修上既不深知、也不想完全取同于传统的实录体例,我行我素,遂编成这部独有特色的实录之书。 清入关后的顺治时期,因欲纂修清太宗的实录,必当参考此前的太祖实录,但感知入关前所修实录很不规范,为了与新修清太宗实录稿本格式一致,于是将满、蒙、汉三种文字分栏书写的体式,改抄分为三种文本,删去书名中“太后”之称,厘为四卷,舍去图画,在每卷正文之前都加上书名、卷数,其形式向传统的实录体例有所接近。此书满文本、汉文本皆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当然正式全名仍然依从入关前文本所拥有庙号、尊号、谥号。另外,顺治新抄写的实录汉文本,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封面题为“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书内各页边幅的书名则删去“努尔哈奇”四字,这比封面的题名允当。 康熙朝纂修发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顺治抄本)仍然大不符合传统实录的体例,决定重修,并于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成书,按照康熙朝对清太祖新增改的谥号、尊号,称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简称《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朝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与入关前《太祖武皇帝实录》相比,面目已彻底改观,单就体例而言,御制序、凡例、目录、进书表、修纂官职名等一应俱全,列于书首。文中统一了年月日书法,日期皆系以干支,人名、地名的翻译已趋于文雅,而且连努尔哈赤的谕令、话语也修改的文绉绉,体现了清廷趋于“汉化”的文化取向。全书避讳了帝、后之名,对清太祖一律书之为“上”,这些都符合历代实录纂修的通例。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成为清朝皇帝实录体系中的第一部,原入关前所修实录已经摈弃。 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之际,从宫廷内发现入关前写定的太祖实录原本,得到乾隆帝的推崇,认为其中古朴、勇武的精神值得提倡,遂下令依据此书编撰《皇清开国方略》,随即又下令将入关前所修实录原本复制2份,以期长久保藏。乾隆帝《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自注言:“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因命依式重绘二本”(20),即完全按照三体文字分栏书写和带有插图的样式复制。但乾隆朝对于入关前实录原本和重新复制本的名称,则相当多样,例如称之“开国实录”、“图本”、“太祖实录战图”等等,前两种用以指入关前之本,后一种兼指乾隆重新复制本,皆为权宜之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康熙朝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乃清帝实录体系的正本,“高皇帝”的谥号不可再改称“武皇帝”,所以不能依正式书名称呼入关前的实录原本,更何况该书还有大不符合规范的“太后”书名。因此,只能代以别称、简称,当事人心知所指也就可以了。至于后来乾隆重新复制本的名称题为《满洲实录》,乃是在书册贴签粘补,这最早也在乾隆四十八年之后,该书已制成好几年了。(21) 清朝官修史有时在书名上伸缩灵活,并不固执。例如乾隆十一年成书的《明纪纲目》,有时写作“明通鉴纲目”、“明史纲目”,刻本有称《御撰通鉴纲目三编》者,《四库全书》录入时名为《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乾隆三十三年成书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多处文献和刻本题为《御批通鉴辑览》,简称《通鉴辑览》者亦每每可见。因此,今人对此不必处处胶柱鼓瑟,更不要因书名之称谓不同而多生臆想。近代以来,学术界在事关清太祖一朝实录问题上,误解联翩,其中多有因书名称谓歧异而大加发挥者,如将《太祖实录战图》与入关前《太祖太后实录》说成两书,将顺治朝分文本抄写《太祖武皇帝实录》说成是重修等等。而其极端者,甚至妄言乾隆朝重新复制的《满洲实录》一书,是清廷君臣合伙的伪造。此说荒唐谬乱,却竟然得到某种赏识,这需要另文驳正,在此暂且不议。 五、戴名世文字狱与王鸿绪进呈《明史列传稿》 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是康熙朝后期一个很大的案件,《增订编年》立有条目录入相关资料。其事起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22)。这明显地是要兴起文字之狱,经刑部查议,则定性为“察审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内有大逆等语”(23),实际上涉及的罪状主要是私修、私论明史而触犯清廷禁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名世本人问斩,牵连多人处以刑罚。 康熙帝以“宽仁”为标榜,自称“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此心此念,恪守五十年,夙夜无间”(24),“朕治天下、惟宽仁是务”(25)。康熙后期可以说是“宽”到法制松弛的地步,所以才会有雍正朝的刑罚严苛,矫枉过正。戴名世的罪过并非太重,可以坐实的“悖谬”,只不过是早年间撰文、书信,偶用了南明政权的年号,事隔多年,仍不姑息,将此钦点一甲二名进士处以死刑,而且牵连多人入罪,是几十年来少见的严厉之举。或许有人认为刑部原议之处罚更为严酷,康熙帝已经予以大幅度消减。但这在清廷结案机制上,乃常见的双簧式戏剧而已,不足为“宽仁”之据。学术界对戴名世被严加治罪的原因,有多种解说,但皆未注意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康熙帝对私撰明史问题,具有极度的敏感加极度的反感心理。 自康熙四十年之后,康熙帝因册立太子等问题的挫折,心理失衡,政务颇受影响,对史学的态度也由高度重视转变为一种虚无情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就批评《明史》馆:“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26)后来还说过诸如“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皆纸上陈言”,“书中之言,多不可凭。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阅,悉属笔底描摹,无足徵信”,“大臣虽奏请速成《明史》,朕明知其无实,速成何为”(27)等厌弃史学的话语,官方纂修的国史、《大清一统志》、《明史》都半途而废,起居注馆随后也被撤消。在官修《明史》废弛境况下,清廷就会对私修行为倍加反感,若有违碍之处,则更不容忍。戴名世案发恰遇此时,无怪乎在劫难逃。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名世被处斩,令休致在乡正纂修《明史稿》的王鸿绪格外惕厉,他于次年进上《明史列传稿》205卷,且撰《进呈明史列传稿疏》上奏。查王鸿绪因结党钻营,康熙四十八年被免职休致,回乡时将明史馆内史稿尽数携走,所有文献中皆无朝廷特许他在外修史的记录。“书局自随”是一种荣耀,倘若有此经历,王鸿绪康熙五十三年的进书上奏岂能只字不提?可知携稿回乡乃是私自行为,但因康熙朝后期修史废弛,竟然无人过问。《南山集》文字狱之后,王鸿绪用一年时间抓紧整理和誊写《明史列传稿》,进上朝廷,此非偶然,乃是唯恐追究,谋求规避。如若不然,为何全书远未完成就急忙进呈列传?以书局自随的官员,或书稿完成后进呈,或朝廷讨要而进呈,或身故之后由家人献出,从未见王鸿绪这种做法。王氏的行为乖巧有效,康熙帝虽未因此而重视《明史》纂修,但起用王氏编纂《省方盛典》,重新获得信任。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氏再进《明史稿》,据其上疏称:“今合订纪、志、表、传,共三百零十卷,谨录呈御览”,并且自注为“全史八套”(28),说明对原进呈的《明史列传稿》又作了修改。可见康熙五十三年所进《明史列传稿》乃仓促凑成,未为定稿,印证了乃是另有动机。王鸿绪巧于避过,得益于戴名世之案的警醒,否则迨至雍正元年,假若王氏仍未上交《明史稿》,雍正帝正雷厉风行地全面恢复康熙朝废弛的起居注、国史、《一统志》纂修,焉能忘记《明史》?岂不严厉追究王鸿绪盗取史稿之罪!陈梦雷手中《古今图书集成》稿,就被雍正帝强行夺取,改由官方设馆纂修,并且将陈氏严加惩治,即为显例。 黄爱平教授《王鸿绪与〈明史〉纂修》(29)一文为王氏辩白,认为历来指责王鸿绪攘窃《明史稿》之说不能成立,王氏虽自刻《横云山人明史稿》,但在清代这种情况多有,并不违规。所言自是合理。但王鸿绪的行径,确有将《明史稿》据为私有的不良动机,私自携去史馆史稿与私刻史稿,都是这种私欲的痕迹,虽无可加罪,但品行却为有识文臣、学者看透,故雍正朝就有史官杨椿,对王氏予以贬抑,影响深远。 平情而论,王鸿绪纂修《明史》很有业绩,在康熙朝后期官方史学废弛之际,以个人之力延续了《明史》修订,尽心尽力,大为提高了史稿质量,贡献不在万斯同之下。雍正元年进呈全部史稿两月后逝世,功成而善终,是他个人幸运也是《明史》之幸运,而这其中却还有戴名世罹难事件的历史性补偿。 ①张越:《跨三代学者,筑学术基石——简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7日。 ②《梁书》卷30,《裴子野传》载有范缜上表称“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是《宋书》已在南齐时流行,疑改朝换代为萧梁后,沈约仅以改动萧梁避忌处为重点略作修订而已,主要撰著工作当是在南齐时完成。 ③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0页。 ④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189页、190页。 ⑤《北齐书》卷8,《后主纪》,《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194页。按:从现有资料看来,此次对《魏书》并未完成多大改动。 ⑥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第273-276页。 ⑦汤勤福:《朱熹与〈通鉴纲目〉》,《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⑧叶建华:《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39辑,1994年3月。 ⑨郭齐:《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⑩汤勤福:《朱熹给赵师渊“八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1)见郭齐《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2)见严振非《赵师渊与〈通鉴纲目〉》,《文史哲》1991年第1期。 (13)朱熹:《答李滨老》,《晦庵集》(《四库全书》本)卷46。 (14)朱熹:《答辅汉卿》,《晦庵集》卷59。此信系年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三联书店2010年版。 (15)见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 (16)《增订中国史学资料编年》元明卷,商务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17)《汉译满文老档》崇德朝第36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册,第1698页。 (18)《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戊子年九月。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后同。 (19)《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辛丑年九月。 (20)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第1册,《满洲实录》卷末第423页。 (21)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南开学报》1992年第6期。 (22)《清圣祖实录》卷248,康熙五十年十月丁卯。 (23)《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丙午。 (24)《清圣祖实录》卷245,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 (25)《清圣祖实录》卷264,康熙五十四年六月戊辰。 (26)《清圣祖实录》卷218,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壬戌。 (27)以上依此见《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癸未,《康熙起居注》五十六年八月初四日乙酉、五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庚戌。 (28)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第255页,雍正元年“王鸿绪再进《明史稿》”条目。 (29)载《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