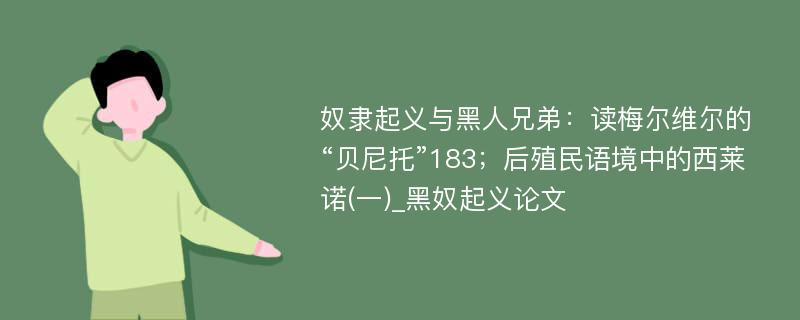
黑奴暴动和“黑修士——在后殖民语境中读麦尔维尔的《贝尼托#183;塞莱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奴论文,修士论文,暴动论文,语境论文,维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赫曼·麦尔维尔的中篇小说《贝尼托·塞莱诺》(“Benito Cereno”)于1855年10-12月在《普特南》月刊连载,1856年收入包括名篇《书记员巴特比》在内的《回廊故事集》。(注:《回廊故事集》(The Piazza Tales)收了麦尔维尔在《普特南》上发表的七篇故事中的五篇,麦为之写了自传性的故事《回廊》作为序。参看willard Thorp, Afterwold, Billy Budd and Other Tales, by Herman Melville (New York: Signet, 1979)325;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st] ed.), vol. 1 (New York: Norton, n. d.)2148 n. 1(以下提到该版本,均简称《诺顿美国文学》Ⅰ,在文中给出页码)。)
《贝尼托·塞莱诺》(以下简称《贝》)取材于一艘贩奴船上奴隶暴动的真实事件。1799年,智利船长贝尼托·塞莱诺驾驶“圣多米尼克”号贩奴船从智利出发去利马,航行7日后,黑奴在一个叫巴波的小个子黑人的领导下起义,先后杀死三四十名白人船员和奴隶主等高级乘客,强迫塞莱诺将船驶往塞内加尔。几经变故,不堪重负的起义船在南美洲南端的圣马利亚岛抛锚,被一艘靠岸加水的美国捕海豹船“快乐的单身汉”号发现,古道热肠的德拉诺船长给他们调拨了紧缺物资。为了向外来者隐瞒真相,巴波亲自导演并胁迫塞莱诺一起上演了一台大戏,让塞莱诺扮演专横跋扈、喜怒无常的船长,而他本人则扮演塞的贴身侍者,寸步不离主子。他们将船上的令人生疑的情况归于接踵而至的海上灾难和疾病爆发,而起义船上的白人在黑人的严密监视下没有任何办法向美国船长传递和暗示事情的真相。巴波还密谋夺取美国船以完成去非洲的计划。傍晚德拉诺船长准备离开西班牙船,塞莱诺突然从大船跳进德的小艇,致使黑人的起义行动暴露。德拉诺一旦明白西班牙船发生了哗变,立即展开追捕,终于制服了起义船。两船一起开往利马副王总督辖区受审,(注:关于南美洲西属殖民地的状况、副王总督辖区(viceregal intendancy)这个译名、从西非到加勒比海一带及南美洲的贩奴路线、姓名称呼法等,北京大学的赵德明教授给了我不少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小说中基本上用同辈但关系不亲密的尊称“堂·贝尼托”指称主人公,在更正式的场合则在后面加上姓氏;较早的评论沿用这两种称呼,本文参照当下一些评论文的做法,依照英美习惯,直接使用其姓氏塞莱诺。此外,当时南美洲大部分地区仍是西属殖民地,还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当地的白人是西班牙人或他们的后裔,所以本文也按小说中的说法,称智利人塞莱诺为西班牙人,他的船为西班牙船。)巴波被判枭首示众,塞莱诺则进了利马附近一所修道院,三个月后郁郁而终。
麦尔维尔并没有选用按时间顺序描写事件始末的叙述方式。《贝》分为两大部分,“顺序”的详尽叙述只出现在故事的后一部分,采用的形式是利马法庭审理时,塞莱诺所提供的第一人称的证词。然而占小说五分之四篇幅的前一部分则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limited omniscience),基本局限于德拉诺登上西班牙船后一天内的经历和心理活动。《贝》具有明显的悬疑、惊悚故事的特征,麦尔维尔让读者和德拉诺一样,一头扎进扑朔迷离的情境。德拉诺不断地起疑,释疑,又起疑,再释疑,又冒出新的疑问,这个过程构成了循环推进故事的节奏。富有戏剧性的格局更因德拉诺的性格特征而产生特殊的张力。他和《白鲸》中的亚哈船长的性格正好相反,却是一类美国人的典型:达观,乐于助人,随和,好奇,但并不多疑,不大相信身边有大恶,幽默,好用比喻;同时恪守航海业规范,是纪律与秩序的化身。他的随和及善意特别表现为对黑人(尤其对塞莱诺的“忠仆”巴波)的喜爱和同情,他不时闪出的疑问则主要针对塞莱诺:塞不是暴君就是海盗,冒牌货,冒险家,要抢夺他的船。他被对方有一个针对自己的“阴谋”的情结攫住了,于不知不觉中扮演了自作聪明的无知者角色,潜在地“配合”了起义者的计划。甚至当塞莱诺跳进他的小艇,巴波持匕首跳下欲向塞行刺时,德拉诺仍然认为这位护主的“忠仆”要刺杀的是他德拉诺,可谓愚钝到家了。
这就是说,在小说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里,德拉诺始终蒙在鼓里。但文本外的读者在故事过半处,尤其在读到巴波为塞莱诺剃须的情节时,一般都会猜出塞莱诺受到黑人控制的基本真相,这是因为麦尔维尔在叙述视点人物的视角与误导性的解读时,利用德拉诺好用比喻的特点,对隐含读者进行了大量的暗示。对文字高度敏感,懂得聆听多重叙述中的不同声音的读者,便会在阅读过程中接受暗示,捕捉住言外之意。
“剃须”的片断集中了几个有强烈暗示作用的比喻,而德拉诺对比喻的拒斥,则清晰揭示出这一类“美国人”的盲信。当富有航海经验的德拉诺的提问就要让塞莱诺露馅的时候,巴波立即以恭顺的姿态提醒主子,每日剃须时间到了。他当着德拉诺的面,将剃须刀的钢刃磨得锃亮,架在瑟瑟发抖的塞莱诺的脖子上,巴波那乌黑的皮肤与白色皂沫衬托下塞莱诺那张格外苍白的脸形成鲜明对比,一时竟让德拉诺“看出那黑的是刽子手,那白的是砍头木砧上的人”。读者随着比喻进入了塞莱诺的“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心境,但德拉诺却在一瞬间就将这个“滑稽可笑的奇想”赶出了自己“有条有理”的头脑。(186页)(注:Herman Melville, "Benito Cereno", in Billy Budd and Other Tales (New York: Signet, 1979) 186.本文所引《贝》的文字,若不加说明,均引自该版并直接在文中注页码。)当德拉诺不经意地提起另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时,巴波的剃刀在惊跳起来的塞莱诺的脖子上划出了血口子。德注意到,哪怕“剑在英王詹姆斯一世眼前抽出,暗杀当着这胆小国王的面完成,”也不会出现塞莱诺那么难看的脸色。(注:詹姆斯一世(1566-1625)的母亲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信奉天主教,他本人是苏格兰长老会(新教)信徒。他刚出生父亲就被炸死,后来母亲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他继承英国王位后不久,就遭遇针对他的、准备炸议会大楼而未果的火药案(1605)。《诺顿美国文学》称他一生“生活在被天主教暗杀的恐惧中,在火药案和1610年法王亨利四世遇刺事件后恐惧尤甚。”(Ⅰ,2185页,注释6)法国的亨利四世是支持新教的,后被一个天主教极端狂热分子拉韦拉克用匕首刺死。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8卷,第507页、19页。)然而他立即如释重负地嘲笑自己疑神疑鬼,竟然怀疑这个被剃刀弄出血就吓得要命的人是“想溅洒我的一腔鲜血”!与其说塞像个谋杀犯,“不如说更像他自己要被干掉呢!”(187页)接着德拉诺心情愉快地欣赏巴波娴熟的理发技巧,看他的梳子剪子在塞莱诺的头部舞动,觉得真是“巧匠的好手艺”(“the hand of amaster”也指“主子的手”);理发完毕,仆人细察主子,那“克制着的自得的神情”活像在看着自己“那双有品味的手塑造出来的作品”。(189页)在此前大量“怪事”的铺垫下,德拉诺脑中闪现的这一系列比喻无疑明确地告诉了读者,谁是西班牙船上真正的主宰。
剃须前,巴波围在塞莱诺脖子上的围布抖落开来,展示出令德拉诺惊叫起来的西班牙王室旗帜的图案——“城堡和狮子!”“在大量的纹章条纹和黑蓝黄的底色中所显露的,是血红的地面上封闭的城堡,对角则是白底色中的一只立狮。”(186页)城堡喋血记与非洲立狮之间的联系旋即由德拉诺的系列比喻凸现出来,读者也开始体会到塞莱诺的真实处境,并从对这面王室旗的描写中隐隐闻到了船上的血腥味。不过,读者此时还不大会联想到,理发的围布其实呼应了故事开头提到的、作为圣多米尼克号船艉饰的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的椭圆盾形纹章(144页),(注:卡斯蒂利亚与莱昂(Castile and Leon)是古西班牙王国。卡斯蒂利亚一词的意思是“城堡之地”,莱昂的意思是狮子,故纹章中有城堡和狮子的图案(狮子是纹章中常出现的lion rampant,即后腿着地、前爪扬起作扑击姿势的狮子)。参见《诺顿美国文学》Ⅰ,2151页,注释①。)更不会料到白色背景中的立狮也就是那位黑奴雕塑家巴波,早就将奴隶主阿兰德杀死,并将其骷髅制成了“一尊白色的雕像”,代替哥伦布做了船艏饰。(203、212页)事实上,小说第一部分的结构和文字几乎就是由嵌入人物,场景、物件、行为、气氛描述中的层层叠叠的明喻、暗喻、借喻、象征所营造的迷宫,它们互相勾连,互相呼应,迷惑读者也引导读者进入表象之下的另一个文本层次,另一个世界。
德拉诺本人并不领会自己的比喻的指向,他也从未怀疑过白人被黑奴控制的事实,这当然是麦尔维尔的精心安排。如前所说,来自新英格兰的德拉诺具有一般美国人自以为崇尚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特征。尽管他后来帮助镇压了起义,但他未见得赞成蓄奴制。他不断表示对船上黑人的好感和善意,说自己遇到黑人水手,“总爱同他拉闲话,逗乐子,”因为他喜欢黑人,“就像别人喜欢纽芬兰狗(注:产于纽芬兰的黑色、壮硕、灵敏并善于游泳的狗。)一样。”(185页)正是将黑人等同于纽芬兰狗的比喻,暴露了德拉诺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的种族优越论思想,揭示出他始终看不清真相的根本原因。
小说中的起义领袖巴波具有惊人的智力和组织能力,但这是戴着种族主义有色眼镜的德拉诺所看不到,无法想象,也不愿承认的事情。登上圣多米尼克号以来,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塞莱诺一直赞扬黑人,对白人船员却颇有微词?他推测说,“白人天生就是更加精明的种族,”假如塞莱诺想阴谋抢夺美国船的话,就一定要防着能看穿他目的的聪明人,而黑人则很“愚钝”,“对他的邪恶视而不见,”所以塞才会抑制白人而褒扬黑人。但这么说岂不是只能假定塞莱诺与黑人联手了?德拉诺糊涂了,他觉得黑人“太愚蠢了,再说,谁听说过这样的事,一个白人背信弃义到如此地步,竟然与黑人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同类?”(175页)就这样,他的疑问和解释疑问的方式使他陷入越来越深的种族主义泥淖。对于这个主张善待黑人的美国人来说,即便是搞阴谋的白种坏人,败类,也不可能做出纠集黑人反对自己族类的事情,因为那不符合基本人性。可以说,德拉诺从骨子里感到黑人是低于白人的下等族类,智力低下,并认为不同的种族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线。(注:真实发生的事情(姑且称其为“历史事实”)和顽固地存留在人们观念形态中的认识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就以德的这段疑惑的推理来说,他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不久前就发生过。在《塞》所述事件之前一二十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在当时的新斯科舍(Nova Scotia)集合了一批反独立的保皇人士,其中就有很多黑人。在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有一大段被国民大会删去未用的文字,谴责贩奴勾当“违背人性”,指责英国国王以给黑人自由为诱饵,挑动他们站在英国一边反对殖民地人,那无疑是以挑动黑人夺取白人殖民者性命的犯罪方式来“偿还他们从前剥夺一个民族的自由的罪行。”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中也谈到英国“那野蛮的地狱般的政权挑动印第安人和黑人来毁灭我们”。参看Funk and Magnalls New Encyclopidia, vol. 19, 237;《诺顿美国文学》Ⅰ,476、498页。尽管如此,在一般美国人的观念中,像德拉诺那样的想法应有一定的普遍性并延续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
出现在德拉诺思绪中的“纽芬兰狗”的比喻,如剃须情节中的一系列比喻一样,也承载着隐含作者对读者的暗示。小说结尾处,第三人称叙述者完全脱离了德拉诺的视角,夹叙夹议地描述巴波及起义的终结,反讽语调格外清晰,着重点出的正是有关黑人智力低下这种观念之荒唐:
至于那黑人——阴谋策划并领导了这场叛乱的是他的头脑,而不是身体——他那瘦小的体格与其所支撑的脑袋根本不成比例,在船上他一下子就被那个强健无比的抓他的人制服了。……黑人无言而终。他的身体被焚烧成灰,但那颗蜂巢般精妙叵测的头颅,却一连多日悬挂在广场的示众柱上,毫不羞涩地迎着白人盯望的目光。(222-223页)
读者在这样的文字中,似不难感受到麦尔维尔对白人优越论,对蓄奴制和镇压黑奴起义的愤怒和否定。
但以上的阅读似乎又引出了矛盾的理解和阐释。剃须情节对塞莱诺真实处境的暗示让读者将同情心转移到了塞莱诺身上;作品第二部分的庭审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它以仪式化的权威性和终极性还原了曾被几重相互矛盾的叙述所涂抹和覆盖的圣多米尼克号事件的真相;塞的证词中,那位“忠仆”巴波的残暴简直可以说令人发指。这样的阅读关注表象与实质的巨大差异,它所看到的“翻案”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将起义领袖巴波与罪恶和阴谋相连,备受德拉诺怀疑的塞莱诺却为了救德的性命,在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危跳船,成了英雄。然而,读者的基本良知、正义感以及在近一二十年关注政治、意识形态、种族和族裔话题的批评语境中培植起来的对种族主义话语的高度警惕,却让我们难以接受这种“政治不正确”的阐释;更何况文本内同样有许多细节、比喻批判了德拉诺所代表的种族主义态度,肯定了起义者的智慧、组织性以及争取自由的大无畏精神;文本内的空白(“庭审”未给予起义者发言权),巴波在法庭的“失语”(“见一切都完了,他一声不吭,谁也无法强迫他开口。他的神态仿佛在说,既然我做不成事情,我就不开口说话”,222页),他那悬挂在广场上的头颅对白人目光的无声蔑视和具有威胁性的反凝视——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将前面的定案再次翻过来,重新认识巴波这位反抗罪恶制度的足智多谋的黑奴领袖。实际上,这也正是晚近后殖民批评对《贝》的认识的主调,尽管它无法解释文本的另一些复杂倾向。
本文正是试图解释这种矛盾。在细读《贝》的真实“原型”和另一个对麦尔维尔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的“底本”的基础上,将它们和《贝》的文本进行仔细比对后,我认为当下的政治性阅读对小说文本的阐释基本上是服从现行理论的需要,虽然有进行文化反省的积极意义,但对于《贝》中黑人形象的复杂性,尤其是麦尔维尔对玄学意义上的“黑暗”和“邪恶”的持久关注,则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过,在进行这种比对前,有必要对历史上和当下的后殖民批评语境中对《贝》的批评做一些概略的分析。
二
一个半世纪以来对《贝》的批评,尤其是对巴波和黑奴起义的看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最初的70年《贝》默默无闻,尽管作品发表时美国内战在即,但当时的评论几乎都没有表现出对黑奴造反的特别警觉,甚至根本没有将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注:参看〈http: //www. melville. org/hmpiazza. htm〉,其中列了1856年6-9月间各美英的报纸杂志对《回廊》的短评9篇。)从20世纪20年代麦尔维尔研究复苏,到80年代中后期这六十多年中,《贝》的主题、人物、风格等方面得到一定关注,对巴波形成过很不同的意见,这从收入《短篇小说批评》的文章(注:Short Story Criticism, ed., M. Detroit (Gale Research, c. 1988-)。这是一套工具书,按时间顺序收集对中短篇小说的论述。我在第1、17卷中查到《贝》的16篇评论。以下简称SSC。)和约翰·朗敦选编的《麦尔维尔的〈贝尼托·塞莱诺〉——供研究用文本》(1965)(注:John R. Runden, ed., Melville's Benito Cereno: A Text for Guided Research(Boston: D. C. Heath, 1965).这是一种案例研究性质的书,集《贝》文本、素材、评论、版本校注和研究书目于一体。以下引用该书简称Runden并注页码。)可得出大致印象。大约从1990年开始,对《贝》的评论激增,而且几乎一概以认识德拉诺船长的种族主义观念、起义领袖的智谋、以暴抗暴的合理性等内容为主。与此同时,大学课程也纷纷采用《贝》作为阅读和讨论的题目。(注:2003年从在线的《学术期刊集成全文数据库》(ASP,即Academic Search Premier)搜索“Benito Cereno”,发现各类杂志的电子版文章33篇,其中25篇是1990-2002年间发表的文章,标题中含有巴波、种族、(反)蓄奴制、社会性别、政治、历史、静默、黑色等字眼的就有21篇(基本出自1990年以后),其余也同当下政治化的研究有关。这些虽远非几十年间有关该小说的全部评论文,但从几率看,仍能说明近十几年来批评界的集中关注点。总的来说,1980年以前的文章关注叙述、语言、自我、词义、意象等问题为多,标题显然没有突出政治。见〈http://search. epnet. com〉。)这个阶段,对《贝》的意见出现了惊人的趋同,评论者不仅赞扬巴波是英雄,批判德拉诺和塞莱诺所代表的种族主义,而且认为麦尔维尔本人在《贝》中表明了反对蓄奴制的立场,含蓄地歌颂了暴力起义的黑奴领袖。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治正确”论者对塞莱诺相对肯定的态度。小说结尾处写道,在黑人被制服后,德拉诺一如既往,只看到阳光、碧空、湛蓝的大海、和煦的贸易风(the trades)(注:此处指“可靠的、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吹的风”(《诺顿美国文学》Ⅰ,第2213页,注6)。贸易风和其他各种风的名称在《贝》和麦尔维尔的其他航海小说中都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此外,该词一般用复数形式,而下文中的“贸易,买卖”一般用单数。)——好用比喻的他将好风比做航海人“温暖而坚贞的好朋友”:一切不都好起来了吗,为何塞莱诺仍然愁容满面,究竟“什么东西在你心头投下如此阴影?”塞答道,“那黑人”(“The Negro”)。他不仅在去利马途中不能面对巴波,连法庭请他协助完成对巴波验明正身的要求都坚决不允,甚至晕死过去。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如他对德拉诺说的,贸易风“只稳稳地吹着送我进坟墓罢了。”(222-223页)这个结尾,被一些人理解为塞莱诺在失去人身和精神自由的数月中,尝到了当奴隶的可怕滋味,由此对奴隶产生深刻的同情并反思罪恶的蓄奴制度,却终因无力公开对抗制度,郁闷而死。例如,有人望文生义地将“贸易风”一词读作贸易、买卖,从而发挥说:“我们必须也将它读作‘奴隶贸易’。德拉诺坚定地相信奴隶买卖是‘温暖的朋友,忠贞不渝的朋友’”。而塞莱诺则不同,他“刚刚当过奴隶,无法忘记一个人被囚禁时是什么滋味。贝尼托·塞莱诺不能忍受(live with)‘[奴隶]贸易’”。(注:此文应为学生作业,标题是“Captain Delano's Ugly Passion,”(《德拉诺船长的丑恶感情》)(〈http://sketchbook. sbc. edu/sidestreet/papers/benito_cereno. html〉)。方括号为原文所有。)奇怪的是,这种生硬的逻辑甚至出现在一些深思熟虑的评论中。早在1978年,格里南达在《〈贝尼托·塞莱诺〉与合法压迫》一文中,几乎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了塞莱诺最后的忧郁:熟悉了奴隶社会之黑暗的他“现在终于能理解哗变者的行为了。这是使他无法存活下去的(live with)知识。”他之所以“无法朝巴波看一眼”,是因为他在“道德上的两难”处境:一旦认清“自己对奴隶的压迫性关系”后,有良知的奴隶主应解放自己的奴隶,但是,在一个贩奴、蓄奴合法的社会中,这样做却会使他“被自己的社会阶层所唾弃,承受经济的压力或受到人身骚扰,或两者皆有”。(注:M. E. Grenander, "Benito Cereno and Legal Oppression,"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2. 4(1978): 137-342 (〈http://www. szasz. com/grenanderbenito. html〉.页码可能指该期杂志的始页和终页。电子版介绍说,作者是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校区的资深退休教授。)这两篇文章都从对巴波的肯定和对德拉诺的否定,推论出塞莱诺的态度,在发表作者本人对蓄奴制等问题的见解。对于这样的推论,我们可举出文本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来发问:如果塞莱诺因做黑人囚徒数月而获得了换位思考的能力,那他如何能做长篇证词,详细控告黑人虐杀白人船员乘客的血腥行为?他又为何一提自己的好友、被巴波制成白骨雕饰的阿兰德就悲痛欲绝?更何况圣多米尼克的黑人能顺利地起义,一个客观条件是奴隶主阿兰德说他的黑人“温顺驯服”,不必像“几内亚贩奴船”那样将他们上镣铐扔到舱底,于是塞莱诺一直让他们在甲板上自由活动。(153-154、209页)
格里南达的文中有一句话,倒是基本符合《贝》批评的历史实际:“直到上个年代(指20世纪60年代)之前,《贝尼托·塞莱诺》一直被人误读……《贝》不得不等候一个多世纪才迎来对它的真知灼见。”事实上,从当下“一边倒”的批评回到前面所说的第二阶段的评论,结果同样令人吃惊:认定故事中巴波和黑人代表“恶”的,并非只是个别人。(注:格里南达文中提到,“1960年,莫林·波恩(Merlin Bowen)仍视巴波为存在之恶的邪恶表现……即使今天仍可读到关于这个故事的种种奇怪的解释。”)在对这部“见仁见智的作品”(注:Runden, Preface, vi.)的多元化的阐释中,专门关注起义本身的并不多,(注:对朗敦书中9篇评论(其中3篇与SSC节选的作者与篇名重合)、15种带简要评注的书和文章目录(其中4种亦见SSC)的粗略统计表明,除了在“蓄奴制问题”专题中长篇节选的2篇,比较突出废奴和起义论题的篇目有2种,作者用“英雄主义”、“英雄”等字眼肯定了起义及其领导者。见Warren D'Azevedo (1956), Joseph Schiffman(1950), in Runden, 197。)然而对巴波的负面意见却时而浮现,例如套用麦尔维尔的作品《骗子》(The Confidence-Man),称巴波为“黑骗子”(“a colored confidence-man”),说他的“精心策划不仅为敲竹杠,还要伤人”;(注:James E. Miller, Jr. (1962), in Runden, 196. )又如称“巴波是纯粹的恶,以施加‘凶暴的恶行’为乐”。(注:Stanley T.Williams (1947),in Runden,198.)对此,我以为应该做实事求是的辨析。首先,必须分清所谓“巴波=恶”的说法究竟是论者对黑奴争取自由的政治问题的表态,还是在阐释小说文本?(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关注文字符号本身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巨大影响,绝不亚于今天政治话语对文学批评的渗透。)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麦尔维尔批评中,“恶”往往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或至少含有这样的层次,它与纯粹政治观点的表达是有区别的(这也是本文将重点论述的观点)。再者,如果认定“巴波=恶”的提法反映了种族主义意识,那么,美国在法律上取缔蓄奴已大半个世纪后仍有这样的言论,只能说明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很缓慢、很复杂的过程,何况从19世纪50年代的历史语境看问题,反对蓄奴制度并不必然等同于赞成用暴力推翻这个制度。最后一点,不少人理直气壮地论述起义领袖之“恶”,毫无不自在的感觉,这本身也说明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文坛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政治话语。
历史地看,对于《贝》中的贩奴、蓄奴制及其相关问题,大致形成过四种意见:
1.以温特斯和费尔顿斯坦为代表,认为《贝》不涉及蓄奴制的是非问题,这类批评家一般将巴波阐释为代表玄学和道德意义上纯粹的、绝对的恶。(注:Yvor Winters, "'Benito Cereno': A Late Masterpiece," (excerpted) in Runden, 118; SSC, vol. 1, 299 (1938). Rosalie Feltenstein, "Melville's Use of Delano's Narrative," (excerpted)in Runden, 124-133(1947).与蓄奴制无涉一句见第132页。Winters所说的“The morality of slavery is not an issue in the story”经常被人引用;他接着说作品描画的是“横行的恶”和恶行的后果,分别表现在黑人和塞莱诺身上。)
2.以麦修逊为代表,认为作品“提出了没有回答的问题”:黑人实行了“野蛮的报复”,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是奴隶,因此首先是别人对他们施行了恶。”(注:F. 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1941),转引自SSC, vol. 1, 300.麦是较早触及奴隶问题的著名批评家,他有关《贝》中的黑奴既是恶的表征也是恶的牺牲品的意见对后来人产生了影响,如Harter Richard Fogle和Allen Guttmann,而下文要提到的Sidney Kaplan则用之作为反面教材,分别见Runden, 196, 180, 173, 177-178。)麦修逊显然认为蓄奴制度本应认真对待,起义的正义性应该更加突出,但在作品内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处理。换言之,在现有的文本中,麦修逊没有体会出麦尔维尔对黑人有明显的同情。
3.认为《贝》是麦尔维尔从前卫的反种族主义立场的倒退,表现出害怕、仇视奴隶造反的情绪。
4.表达了类似当代评论的意见,认为《贝》表现了起义领袖的英勇和智谋,赞扬了麦尔维尔反对蓄奴制的态度。
上述第三类意见中,朗敦选本所节选的卡普兰的文章《〈贝尼托·塞莱诺〉:蓄奴制的辩护词?》(1956-1957年)尤其值得注意。(注:Sidney Kaplan, "'Benito Cereno': An Apology for Slavery?", in Runden, 167-178.下文提到的颜色象征的分析见174-175页。该文原文见“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会”的刊物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41 (1956): 311-338; 42(1957): 11-37。)作者以翔实的资料说明,从18世纪30年代起的一百多年中,在贩奴船上不断发生黑人起义、杀死船长和船员乃至全体白人的事件,从而使我们对小说描写的圣多米尼克号起义的深广的背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卡普兰提到的著名事件中有后来拍成电影的1839年阿米斯泰德号(Amistad)起义,美国最高法院曾对此案做了历史性的结论,“首次从法律上声明,当黑人被当作奴隶从自己的家乡贩运出来的时候,他们有权利为了争取自由而杀死任何企图剥夺他们自由的人。”(注:Sidney Kaplan, "'Benito Cereno': An Apology for Slavery?", in Runden, 169页。关于历史上真实的贩奴船上奴隶起义的论述见第168-170页,特别是168-169页中的两条详尽注释。)有人曾用“1856年的奴隶起义大恐慌”、“反蓄奴制斗争白热化的10年之中段”来形容《贝》和《回廊故事集》发表的岁月。(168页)卡普兰与持对立意见的人有共同的认识前提,即根本不相信麦尔维尔在创作时会脱离自己时代的具体的政治、文化关怀;这一点在当今批评中已被普遍接受。但值得我们深思的倒是,在《贝》发表100年之际,这位在黑人历史研究刊物上撰稿的、旗帜鲜明地反种族主义的卡普兰,通过对《贝》的文本细读及其与麦尔维尔先前作品的比较,竟然也在其中分析出黑人和黑色与“恶”的联系,从而将麦尔维尔推入“蓄奴制的辩护士”行列。(177页)这提醒我们,故事本身可能比我们所想的复杂得多。卡普兰的愤怒在当代亦有回响。有个美国白人教师在多族裔学生参与的课堂上讨论《贝》这篇“内战前的反蓄奴制的杰作”,期待班上的非洲裔学生起来驳斥白人学生无意中流露的德拉诺式种族意识,可非裔学生中有的竟“和巴波的态度一样,宁可愤怒地保持沉默,”还有的干脆课后去老师的办公室“气愤地质问[他]为什么要教这样的种族主义的文本”。(注:Robert S. Levine, "Reconsideration: Teaching in the Multiracial Classroom: Reconsidering Melville's 'Benito Cereno'," Melus 19. 1(1994): 111-120. (〈http: //web20. global. epnet. com/〉)文中所说的情况发生在马里兰大学。)
目前对《贝》持赞扬或批评的正反方论者似乎都未举出麦尔维尔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日记、信件、创作笔记等材料作为佐证,证明他在创作《贝》的时期密切关心废奴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黑奴以暴抗暴的行为表示过明确的态度。(注:一卷本《诺顿美国文学》第四版在1820-1865年文学的引言中提到,麦尔维尔称黑奴制度是“人类最无耻的罪行”,但未说明此言的出处,尤其未注明时间。同一引言还提到,1851年麦尔维尔的岳父、麻省首席法官在波士顿强制实施了(1850年)逃奴法,对此梭罗曾在日记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854年更发表辛辣的演说《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见The Norton Anthology: American Literature, Shorter 4 th ed. (New York: Norton, 1995)396, 769, 772。
19世纪50年代反蓄奴的斗争已白热化,美国北方废奴的呼声十分高涨,言论已经相当公开,尤其是在麦尔维尔生活的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除梭罗的演讲外,1855年F.道格拉斯发表自传第二版,对第一版(1845)进行了大量扩充修改。我没有读到麦尔维尔本人有任何支持黑奴暴力起义的言论。相反,倒是有论者在谈论艾米莉·狄更生与美国南方的关系时指出,南方读者视爱默生、梭罗和斯托夫人的作品如毒物,而狄更生则不然,“她同麦尔维尔和霍桑这些南方人喜爱的作家一样,采取了哀婉的默认态度。”见Christopher Benfey, "Emily Dickinson and the American Sout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y Dickinson, ed. Wendy Mart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2002) 48。)不过,《贝》所依据的真实原型,却能从一定意义上弥补上述材料的匮乏,我本人在对小说和原型进行仔细比对后,认为指责麦尔维尔为黑人的暴力起义张目的观点根本就站不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