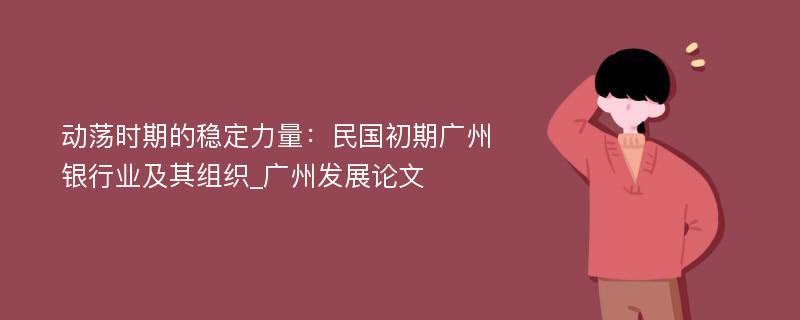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钱论文,民初论文,广州论文,乱世论文,稳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072(2004)06-0092-08
粤省近代金融业以广州为中心,主要有银号、当押店、银行、保险及信托公司等类。由于历史的原因,银钱业虽是一种传统的金融行业,但在民初仍以经济实力长期居于商贸中坚之地位,其公共组织具有良好的管理效能和权威,与政府财政当局处于既抗争又合作的互动关系,并在本地商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社会变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行业同业公会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本文主要以广州银钱业的公共组织银业同业公会为个案,在此领域开展一些探讨。
一、广州银钱业的经营种类及经济地位
银钱业是我国封建社会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旧式金融行业,起源于铸币的交换。广州银号(在上海等地称为钱庄)产生年代久远,向乏调查,不见于野史稗官,不详于志书传记,但据银业界老行尊口述,其实滥觞于清康熙朝前。当时除以放款、揭项为主体的忠信堂各会员银号外,尚有以开炉倾销为业的“五家头”(即裕祥、大昌、德昌、宝源、阜安五家,由藩署批承开设,专铸藩库银)、“六家头”(即永安、谦受、厚全、宝聚、泗隆、慎诚六家,由盐运司批办,专铸盐库银)银炉,以及以汇兑与存储官款为主要业务的“西号”(以山西人经营的票号为主)等。这几类银号各有团体组织,不相统属,何者先创尚难确断。其业务虽各有特殊范围,但皆经营放揭款项。至清末,因银行业务兴起,银钱业的经营受到影响。进入民国后,山西票号因放出款项不能收回,周转不灵,多行倒闭。倾炉业则因改用铸币,也相继停顿。仅忠信堂属下各银号,因资本宏大而得以继续营业。[1]
广州银号向为顺德人所经营,后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归侨亦向此发展,因之业内遂有顺德帮和四邑帮两大集团势力。前者执银业之牛耳,成立最早,地位亦最重要,放款多以丝业为对象,营业方针略为守旧,保持百年银业固有的色彩;后者实力稍弱,且经验较浅,经营除仍具银号原有之特点,并兼新式银行之制度,作风较为革新。
民初广州银钱业行计分两大类型,虽是同属一行,而营业却颇异。一称做架(即附揭生息),此类银号早期俱入银业行会组织忠信堂。其资本较雄厚,专做汇驳按揭、丝偈买卖单口生意,年营业额多则上百万,少亦数十万。款项之存放,大多为相识主顾,或经由中间人介绍,一般客户綦难请求通融资金。银号对于存放款之利息,向无定率,须视顾客之关系、信用及银根之宽紧为标志;一称做仓(即代客买卖货币),此类店铺除找换金银货币、买卖有价证券外,多从事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特别是炒卖铺,其盈亏实不可测,金融上愈多风潮就愈多机会,同时亦愈危险。
虽自近代以降,银号不论资本还是经营方式都远不能同银行相比,但因其熟悉地方情况,经营灵活自由(银号向能适合商人之心理,如注重信用放款,借款不需抵押,不限营业时间,力求办理手续简便;又以票据运用,活泼资本,使中小商人亦得便利等),并专设“行街”(银号派出探查行情的人员)终日来往于各店号以招揽生意,故仍在粤省金融界拥有极大势力。直到20年代,尽管广东银行业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真正起到工商银行职能的仍旧是银号,尤其是正当银号经营方针稳扎稳打,恪守信用,为全省金融之中坚。工商界一般较少与银行打交道,平时市上各行商凡有进出口货买卖者,更是多与银号保持来往关系(因有汇划制度,可省去现金),如花纱、煤油、钢铁、油豆、海味及米面等杂行,无不赖银业之汇驳附揭兑换,以资周转流通。尤其当夏季蚕丝出产极盛时期,所有出口丝价之汇驳和毛单之买卖,年达8000万元(粤币,下同)之巨,全赖银业为之周转。此外,秋、冬两季之侨汇回粤,岁逾亿元,亦多靠银业转驳,故可谓其“实居商场上最重要之地位”。[2]广州银钱业虽不发行纸币,但大银号都代收捐商捐官的税款,发给收条,凭此可作缴款入库之凭据,国库及省库在此类收条上盖章,银行即当缴过款之凭证。银行凭收条入帐,而钱仍在银号手中。如霍芝庭的福荣银号、邹殿邦的广信银号、植子卿的胜兴银号等,所发收条,在商场上几等于银行本票,信用不下于银行纸币。[3](P322)
银钱业曾被称为广州“百业之首”,如1918年市面不景气,“盈余者寥寥,亏折者指不胜屈,能获厚利,则以银业行为首屈一指”。[4](P2216)不过广州银钱业自身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多数企业规模小,经营者个人及字号的信用,亦缺乏确实之保障。银号为无限责任性质,股东的资产是银号的后盾,而许多银号股东并无雄厚的资力,一遇风吹草动,担负不起他们应负的无限责任。故银业界的兴替变化节奏较快,很难准确统计实数。30年代初全行业店铺达540家,资本总额约700万元(实际数额应高于申报额,因为各号为减轻纳税,在开始营业注册备案时即未实报,有些竟数倍于申报资本总额)。[5](P95)另有估计广州银钱业资本当在2000万元以上,全行业资力约值1亿元。[6](注:广州银业资本难以确实统计,因股东负有无限责任。全市银号资本额估计约当在2000万毫元以上,至于吸收存款,至少应4倍于营业资本。)如此巨额资金,足可左右金融。
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港币与大洋价格猛涨,做投机营业者惨遭失败。又因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以及白银大量外流所引起的金融危机,致使大批店号倒闭。4月1日,广州合德、宝华两大银号因资金周转不灵倒闭,亏欠各户存款百余万元。风声所及,存户纷纷向各银号提款。[7](P2)金融界与官场皆蒙受重大影响,仅1个月倒闭银号即达20余家,造成全市性金融恐慌,[8]乃广州银业界数十年未见之险象。30年代中期,广东银行业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受此影响,广州银钱业经营多趋收缩,获利较少,在惨淡经营中求生存和发展。1935年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产生更大影响,店号数量剧减。[9]
二、广州银钱业的组织及其管理
(一)广州银钱业的组织演变。近代以后,“五家头”、“六家头”及山西票号因行业不存,难稽沿革。而忠信堂(会员为以放款为主体的银号)之历史证诸碑志,发源于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前,假银行会馆为会址,作为银业行商们开会议事的地方,其主要职能是共同订立行规,维护同行利益和限制不正当竞争。[10](注:据忠信堂重建银行会馆碑志所记,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广州众多银号自行捐资重建银行会馆,可证该堂之组织当在此之前。)会馆屡经重建,会务日渐发达,入会者日增,至1873年时,已拥有会员68家(不包括找换店)。[11](P76)1917年2月,北洋政府农工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后,广州忠信堂同全国各地旧有工商行会一样,进行改组,逐由传统的行会演变为近代新式团体。
1923年广州市银业公会成立,这是依照政府法令而设的工商团体组织,加入市商会为会员,选出代表参加商会的会员代表大会和选举商会的理事。忠信堂原有的同业公共组织之职能移交,变成主要是承办厘金的机构。银业公会初假忠信堂为会址(在西关珍巷连珠里),后迁西荣巷绸缎行会馆地址。银业公会成员既有“做架”的银号,也有“做仓”的找换店。1931年时,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所颁之工商同业公会法,又改组为广州市银业同业公会。[12]
(二)广州银业公会的业务管理。在形势动荡的年代,经济风险很大,做架银号特别是顺德帮惯做信用放款,每遇客户营业失败,无力偿还,首先既受拖累,甚而倒闭者亦属不少。1927年,广州银业公会以年来行中放出款项迭遭倒挞,为维持同业公共利益计,拟就规则8条,作为信用放款之保障。主要内容为:凡同业有被外行挞欠者,即宜将该挞欠行股东及司事经手人姓名标贴于会内,使众周知;凡同该挞欠围内字号有连带关系者,同业亦一律宣告停止其交易及买卖汇驳一切交收;凡挞欠号的股东及司理经手人,各债务未清而再行另改字号营业者,亦一律宣告停止其交易买卖及汇驳交收;凡本会同业内有故意抗众,对于已宣告停止交易及买卖汇驳交收之店号,而仍与之交易者,一经查出有据,每次罚款500元以示惩戒。如不遵罚,即行革除会籍,不得入市买卖,会底充公。[13]
在银钱业“做仓”投机活动中,“好友”(买入方,亦称多头)、“淡友”(卖出方,亦称空头)揸扎(意即买入)期西(指港币期货)租仓订有规则,做仓银号旁观胜负坐收渔人之利。另外做仓银号与同业交易,亦订有仓务规则,由银业公会自治课颁订,会员均须遵守,[14]因投机事业极复杂,故订立游戏规则以保同业利益底线和平衡。
由于省内伪劣币混杂纷乱,忠信堂和银业公会为鉴别真赝以息纷争起见,于1928年联合成立毫币鉴用委员会,附设于银业公会内。另又在银业公会内设收条清理处,以忠信堂董事和毫币鉴用委员会委员组织之。[15](P29-30)该处作为银钱业的汇划机构,其性质类似于票据交换所。每周各银号将所接收的银票、汇票或受同业委托代交收款项之收条,及买卖时找结数尾所发给的收据等,依时汇集携赴该委员会办理,以免纠葛。同时亦有利于减少现金使用和同业间的资金占用,减少凭证递送环节,缩短递送时间,节约人力,加速资金的流转。
(三)广州银业公市。广州市银业公会成立后,创办了广州市惟一的综合性金融贸易市场——银业公市(与香港的金银业贸易场相似,设在银业公会内,1930年后改称银业交易所)。公市的日常管理工作亦由银业公会所设的自治课负责,凡属银业公会的会员,缴纳会费和厘金,并凭公会发给的证件,即可入市。公市有警察把门,凭证进场,可进行买卖香港汇单、港纸、中纸(泛指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广东革命政府中央银行及其后续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及有价证券的交易。公市买卖,每日分早、午两市,交易方式极为独特,双方以手势议价,然后多互拍对方肩头表示定交。成交后不须立据,多守信用,不得反悔。[16](P11)参与交易的银业公会会员均依时齐集,平时约有三三百人,济济一堂,喧呶聒耳,其叫嚣之声不亚于纽约、伦敦及巴黎等交易所,初入者朦胧如坠云雾之中。[17]银业公市之买卖,基本全属银业行商人,虽有三几间商办银行参加,然而各种货币的“众盆”(即公价),均为银业行所操纵。
广州金融市场由有影响的大银号担任理事,为了剂盈酌虚,因应缓急,联合组成银业集团操纵银市。由于省港金融行市息息相关,港币控制了华南的进出口贸易和货币金融,并又是粤人的交易媒介、保值手段和投机对象,故广州银业公市受到香港金融市场的操纵。广州市外汇汇率均由银市根据香港行情发布,这同旧中国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外汇汇率由汇丰银行挂牌有所不同。
广州银市在30年代中后期屡闭屡开。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局势动荡,金融投机商因买卖期货(广州银市上交易的外币俱属期货,多为港币)而致亏数百万元,银店倒闭100余家,影响社会经济。财政当局派员制止期货买卖,以免发生金融大波动。银市停业数月后,商人以长此停止期货贸易,妨碍外汇之流通,请求复市。翌年4月中旬,广州市银业公会奉财政厅令草拟新银市规约,严格规定入市经纪资格,并加强组织管理。改组后新银市复开,市内允买卖各国货币(期货)及国内一切有价证券,经营业务与金融交易所无异。[18](P7)
当时广州银市对社会有着两重性影响:(1)积极方面。首先是它有利于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中国尚无外汇管理,港粤人员来往自由,货币携带不受限制,走私盛行。有了银市后,期货、外汇买卖可以使进出口经营商把用外币计价结算的交易在进行实际结算前,先将汇价定下来,从而避免日后计价波动的危险,有利于确定成本和销售价格,保障预计的利润。其次是它可以沟通异地金融,调剂余缺,促进物资交流,帮助吸收侨汇,从而推动工商企业的发展。(2)消极方面。主要指金融投机性的严重危害。参加投机者,表面上是银钱业界的人物,但其背后有政府官员染指。投机商力图拉拢官僚政客,以利了解时局发展的“行情”。于是,官商勾结,哄抬市价,牟取暴利。
三、广州银钱业与财政当局的互动关系
广州银钱业与历届财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基本上表现为抗争与合作的两面性,集中反映在货币和捐税等问题上。对于政府强制行使缺乏信用保证的纸币和滥征苛捐杂税,银业公会所采用的对策往往先是消极的通电或请愿,力争对话协商妥善解决,若不奏效,难免也会发展到抗税、罢市的地步。
民国时期广东纸币花色种类繁杂,各个不同年代印发的钞票大都属于所谓“官纸”,而且发行量相当大,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元。但这些纸币缺乏信用基础,其发行不过借以弥补统治当局财政之不敷,毫无例外都经历过贬值、低折、拒用、挤兑、停兑等恶劣局面。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正是由于政局动荡,政权更迭过速,必然导致金融不稳,经常发生纸币风潮,辗转循环,为害极烈。广州银业公会成立伊始,即要面临如此严峻之局面。究其根源,纸币挤兑,或因官方银行缺乏发行准备,纸币不敷信用,遭到银业店号拒收;或因银钱业操纵纸币市价,利用其低折投机图利。故官商既相对抗,如银业罢市和政府强制开市;又相妥协,如共同维护和解决纸币问题,并支持币制改革等措施。
货币经常贬值,必然引起市面恐慌,造成民众的严重损失。因此,纸币问题可谓真实反映商民对待官方态度的晴雨表,而银钱业资本家无疑是充当了领头的角色。民初广东官营银行曾发生过无数次纸币挤兑风潮,银业店号深受其害,被迫承受纸币低折之损失。官厅强令十足兑现纸币,曾引致银钱业以罢市相对峙。如1922年3月广州纸币风潮爆发,政府一筹莫展,授意工界出面维持,工人纠察队四出捕拿银业“败类”。4月2日晚,各银业商在银业公会集议,决定于次日罢市抗议。罢市后,“一切汇兑交收,概行停顿,全省商场,大受影响。”工商对立加剧,财政厅长惧酿事端,遂请出广东商会联合会调停,银业罢市才得以解决。[19]6月陈炯明叛孙事件发生后,粤省纸币价跌,民心不安,11月4日,新任省长陈席儒邀请商会及银业行会商维持办法。[20](P261)1923年初,孙中山利用各路军阀驱逐陈炯明,在广州再次建立革命政权。9月上旬,财政当局为整理全省金融,召集工商各界代表筹备成立整理纸币委员会,银业界代表梁祖卿当选为委员长。[21](P20-21)
由于孙中山革命政府和广州驻军发行货币过多、抽收税捐过重,与商界之关系极为紧张,罢市潮迭起。如1924年3月30日,广州银钱业为抗议省财政厅增抽“银业买卖捐”而全体罢市1天,财政当局“深恐钱业罢市,影响甚巨,其他各业亦将受其牵动”,遂回复银业公会会长杜琯英,被迫取消之。[22](P12-13)6月初,广东造币厂开工鼓铸钱毫,广州银业公会反映民意,通过总商会致函该厂监督梅光培,要求其“依照部章,严定成色……以释群疑,而维币政。”[23](P31)7月24日,广东政府大本营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省财政厅长和广州总商会提出的《维持省行纸币之办法》,决定由广州总商会、银业公会等和政府共同组织“整理维持纸币联合会”,[24](P28)但并未解决问题。10月广州第二次罢市,银钱业亦参与,迨商团事件被处理后,风潮平息,才先后复业。[25]镇压商团一案使各银号损失极大,所借出之款项殊难收回。因各商号店铺或被焚,或为兵掠劫而无力经营,故专营放款的银号损失最为惨重。事后银号的复业亦为最迟。[26]翌年宋子文致函省财政厅维持纸币,令所有政府收入机关应限尽收中纸,不得再收毫银及银号凭单。财政厅遂电饬各厘税收入机关,一体遵办,[27]此举对于银号的营业亦为不利。
财政当局时有勒索认债之举,这种作风严重伤害了银钱业商的正当经营活动。如1927年8月下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古应芬为应付中纸挤兑潮,以“非常手段”举借临时公债1000万元,规定广州市银业承担400万元,各银号按商业牌照资本额的44%缴纳。由于银业界未刻按期限缴纳借款,古氏认定为故意稽延,遂采取强硬措施,令军警于9月1日查封市内银业店号,并拘禁胡颂棠等6名商董,限即日缴足借款。至次日各行号多遵令缴款后,才撤封和释放人质。此举招致商界强烈不满,迭由国民政府查究,终致古应芬引咎辞职。[28](注:40年代末,广州银钱业在呈国民政府财政当局函中曾云,该业往昔“共负担北伐公债八厘库券四四借款等约数百万元”。可能即与正文所提到的款项有关。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6),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6页。)
20年代后期,粤省各属发生拒用1924年所铸银毫(因疑其私铸及滥铸)的大风潮,对政府形成很大的压力。1928年3月31日,广东中央银行奉命召集各商会、银业公会及各大公司代表开会,协商办法,达成共识,遂使该币复归流通。由于拒用银毫风潮与银业界投机分子炒买炒卖亦有密切关系,故广州总商会于7月11日召集各商会及银业公会联席会议,讨论救济金融办法。会后根据议决办法,由商会和银业公会各推举委员5人组成救济毫币委员会,并在总商会内设立临时鉴定处,由银业公会派出精干人员负责秉公鉴定,处理所有交收之纠纷。[29](P239-240)翌年2月,市面又突起拒用1928年所铸毫币的金融风潮,国税公署于21日特召开官商联席会议,决定由省市商会、广州银业公会及各商民团体,会衔通告各地民众使用新毫币。[30](P9-10)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确立后,广东“小洋”(又称“毫洋”,为清末民初粤省本位币)的兑换行情起伏相当大,人民多次吃到纸币发行过多而价值贬低的苦头,要求改进币制的呼声高涨。1929年3月12日,广州市银业公会和忠信堂开会议决:(1)改两为元,以后买卖港单港纸,一律通用元数,废除两数;(2)推行纸币,维护“中纸”,以巩固摇摇欲坠的市面金融。[31](P38)此举得到财政当局的支持,财政厅发出布告,称经过省政府会议议决,决定废除天平制度改两为元(因以银两交收须用天平,而平银时,有大小平之称,元、两杂出,计算纷纭,奸商乃借机牟利),[32](P34)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直到1933年,中央政府才公布废两改元的法令,规定从4月6日起,禁止银两交易,确定银本位币以银元为单位。
1931年发生的几件事,明显地反映了政府同银钱业界间的控制与反控制较量。如3月4日,广东中央银行忽然挤兑,舆论认为起因于某些银铺操纵纸币市价,造谣图利。[33]4月23日,中纸因遭银业店铺拒收而发生挤兑,次日即平。[34](P3)同月27日,银号反对财政厅取缔(实为整顿,因银业公会制订流通收条办法,以港币为本位,有歧视国币之嫌;又有某些银号资本不实,故财政当局对二者皆予以取缔)银业办法,拒用中纸,致银行再生挤兑。次日又派代表请愿,官商双方态度均甚强硬,财政厅长范其务允延期一月施行。[35](P7-8)
1932年2月,陈济棠将广东中央银行改组为广东省银行时,派定广州各界代表组成广东省发行纸币监理委员会(负责银行新纸币基金之保管及副署签发),植子卿即为委员之一,该会在此后省银行遭遇挤兑时为其支撑了门面。同时,省政府亦应银业公会的要求,同意贷款给银铺,以应付存户提款。[36](P2-3)翌年福建事变的消息传播后,广州人心突生浮动,广东省银行自11月16日发生挤兑,纸币风潮影响商场,银钱业首当其冲。广州银业界于28日召开大会商讨维持办法,决定全市同业一致联络,相互支援以防店号倒闭。银业公会并经呈准财政厅,通令限兑到期存款,以谋救济。[37](P77-78)1935年11月初,财政当局实行币制改革,组织广东省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由省银行、广州市立银行、省市商会、银行公会及银业公会之代表组成。植子卿和邹殿邦均列为委员,各大银号在收购白银(币制改革章程规定以所谓“法定”纸币即省银行、市银行兑换券收兑民间存银)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3](P316)此后不久,外间盛传陈济棠已将收得的白银运到香港卖光。省政府为了辟谣,特邀省市参议会、省市商会、银业公会、忠信堂以及其他民众团体前往检查。[38](P26)
1936年“两广事件”爆发后不久,省内形势紊乱。7月1日,广东省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对于保管准备金安存问题,开会议决将其中一部分运付香港或广州沙面租界存放,同时关于仓库问题,派定由邹殿邦等赴香港调查。[39]同月6日,该会又讨论维持金融办法,决定分函广州市商会、银行公会、银业公会及忠信堂等,转知所属各商,勿助港币市价高涨,禁止买空卖空。[40]陈济棠下野后,随着时局逐步发展,广东金融渐呈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整顿粤省纸币,以俾统一币制。财政厅亦召集银行公会、银业公会、银业找换业公会等各代表开会,宣传解释意义。[41]8月,广东法币准备管理委员会成立,财政部指定宋子良为主席,邹殿邦列为委员之一。[42](P27)
当然,这并不预示着新政府与商界从此就和谐共处了。1937年1月中旬,作为广州市商会主席的邹殿邦率领120余同业公会之代表结队赴省财政厅举行大请愿,要求取消营业税课税新标准,表示将“誓死力争”。刚上任不久的财政厅长宋子良因群情激昂,恐生事端,预先飞往上海,暂避风潮。[43]
上述事例充分表明,尽管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银钱业界和财政当局仍尽量寻求妥协与合作,以达共存。
四、广州银钱业在本地商会中的地位
晚清以降,我国时代的主旋律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寻求近代化发展道路,商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承担者。广州商会的建立,是当地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反映了社会组合的必然趋势,它负有“联商情、开商智、扩商权”之使命,领导工商业资本家追求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和军阀割据,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致力于“实业救国”,成为推动近代岭南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广州商会具有凝聚、沟通、促进、调和、慈善公益、地方自保等诸多社会功能,由于其法定职责得到商界的承认而发挥领导作用,并因拥有相对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而成为本省社团网络的聚合中心。由于近代产业的不发达,广州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商会成员的构成亦显示如此特点。[44](P173、P546;P71-75)(注:例如1910年时改选的广州商务总会共有会董57人,其中商业资本家49人,占总数的86%;工业资本家5人,仅占8.8%。1928年时,广州总商会有同业公会会员66个,1937年增至108个(其中工业行业仅10余个)。1946年广州市商会重新成立时,有同业公会会员115个,其中仍以商业同业公会最多,达93个,工业同业公会其次,为22个。)金融资本家在广州商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银业公会是商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其领袖人物以经济实力和较高的威望在商会权力机构中占有一定的优势,有些还曾数度担任商会负责人,长期执掌会务。
早在清末,广州银钱业店号即是本地商会重要的始创成员。如1905年初,广州商务总会由七十二行商发起组织时,集款之法定由各号公摊,计每股10银元,各银号即允承担了2000股。[45]
民初广州总商会被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所控制,1924年商团叛乱被镇压后,陈氏逃往香港,但商会的实权仍握于金融商手中,继任会长和12名会董中的4人,都是银钱业界的代表。[46](P201)1927年1月中旬,广州总商会选出新任正副会长邹殿邦(广州银业公会主席、广信银号经理。曾兼任广东省议会议员、广州电力公司总经理、国华银行董事。1936年又开设盐号,转营盐业)、胡颂棠。正由于银业公会及其领导人在广州市商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某些重要问题尤其是有关金融货币方面的情况,商会经常联络银业公会一致行动。如1929年爆发粤桂战争,中央银行纸币低折。广州总商会为安定人心救济金融,于9月24日召集有各商会、银业公会及忠信堂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请财政当局官员报告时局真相和金融状况,并建议政府收预饷以减少流通额,并重申投机之禁令,另又劝各商照常通用纸币,[47]使纸币价格旋即回复原状。
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后,逐步在“整理商人团体”的名义下取消原有的总商会,以期统一成立由官方直接控制的商会。192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令全国商会限期改组。广州总商会决议先成立改组筹备处,举行会员总登记。旋奉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民训会指令,将广州总商会、市商会、市商民协会合并,重新组织一个市商会,“以谋商运统一”。[48]1931年2月23日,召开了广州市商会会员代表大会,有60个工商同业公会的846名代表参加。越2日,选出邹殿邦等22名执行委员会及候补执行委员。新广州市商会依法成立,邹殿邦任主席。[49]此后几年间商会内部舶来货商派(以何辑屏为首)和国货大联合商派,死力竞争,邹殿邦遂利用矛盾,保持其在商会中的领袖地位。但部分行商认为邹氏领导下的商会殊无建树,且会务废弛,于1936年发起联署,强烈要求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派员改组整理之。[50]翌年7月中旬,邹氏被迫赞成广州市商会改组,并宣布辞职以谢商人。[51]实际上,此后直至民国末年,广州商会的领导权大部分时间里仍被控制在植子卿、关能创等银钱商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济棠统治时期,广州许多大银业商都有官僚的背景关系,如邹殿邦以财政厅长区芳浦、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霍广河等为后台,谈国英(银钱找换业同业公会主席)的祥兴、关能创的国源、植子卿(金业同业公会主席)的胜兴等银号,都与达官贵人及其太太宠妾打通渠道,以作靠山并利头寸调拨,更设法贿赂电报电话局、警察局及法院等部门的权势,故消息相当灵通,有时竟甚于军政机关之情报,据称不论发生什么天大的案子,都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52](P44-45)
综上所述,由于民初新兴的金融机构银行实力未能超越和取代银号,故广州银钱业及其同业组织仍能在经济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忠信堂和银业同业公会有着延续和并立的关系,而该业公共组织的重心显然是向更具现代色彩的后者倾斜;银钱业公共组织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利益,由此而决定了其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广州市商会历来内部矛盾十分尖锐,而银钱业的领导层则比较协调一致,这有助于其长期控制商会的实权,以反映和维护商民的利益,并扩大了金融资本家的社会影响和地位。
[收稿日期]2004-10-13
标签:广州发展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纸币论文; 银行论文; 工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