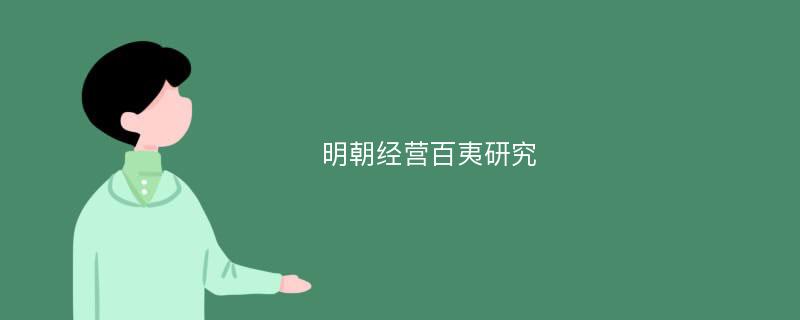
于秀情[1]2003年在《明朝经营百夷研究》文中指出在学术界,傣族历史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有关历代中央王朝经营傣族的历史研究鲜少。本文试就明朝经营百夷的政策进行较全面的论述,以丰富傣族历史研究的内容。 在元朝,傣族被称为“金齿百夷”,简称为“金齿”或者“百夷”。百夷归附元朝以后,元朝在百夷地区一方面继承历代中央王朝经营南方民族地区的成果施行郡县制,以百夷聚居地区为单位在百夷地区设置路、府、甸,另一方面元朝在百夷地区施行土司制度。 明朝时期傣族被称为“百夷”。明朝继承元朝经营百夷地区的主要政策——土司制度,并且使这一制度得到完善与发展。明朝还制定了其他政策、采取了其他措施加强明朝对百夷的统治。百夷地处西南边疆地区,因此,明朝经营百夷的政策与明朝的西南边疆的形势发展息息相关。本文将综合运用历史学、结合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论述明朝经营百夷的政策及其措施,揭示这对百夷社会和明朝的影响以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有助于祖国各民族的团结与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本文根据明朝经营百夷的政策与措施发展、变化的特点,分五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概述13—14世纪百夷地区的形势,其中主要地追述了叁个方面的内容:元朝在百夷地区所施行的主要政策——土司制度;元朝晚期,平缅思氏的扩张、对元朝的反抗以及元朝为此所采取的政策。 第二章论述明朝经营百夷的主要政策——土司制度。明朝先后在百夷地区建立了大小近30个土司区。明朝在百夷地区土司区的建立是这一制度的基础和重要反映,也是明朝经营百夷的各项政策具体内容的载体,因此,本章首先概述明朝在百夷地区设立土司区的概况。明成祖建立了明朝征调与控制百夷土司的制度——金牌、勘合、底簿制度,从而加强了明朝对百夷土司的控制。百夷土司对明朝的贡、赋制度是明朝经营百夷的主要政策——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百夷土官承袭制度也经历了一个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因为百夷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XL俗与汉族完全不同,百夷与汉族语言不通,因此,明朝在百夷地区又施行流、上参用制度。这加强了明朝对百夷土司的控制,也为明朝最终实现流‘会统治百夷地区作准备。本章对这四项制度逐一进行了论述。总之,明朝时期,上司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巩固了明朝对百夷的统治,维护了西南边疆的稳定,客观上也促进了百夷社会的发展。 第叁章论述明朝解决百夷土司反抗明朝的政策。百夷封建领主制的社会特点决定了各上司扩张领土的要求。但是明朝经营百夷的目的就是要使百夷上官通过世袭制保守其境土,供明朝征调。这样,百夷土司与明朝之间发生了对抗性矛盾。明朝采取兵威镇压、“以夷攻夷”、严禁云南边民与百夷人民往来等政策来平定百夷土司的反抗。这些政策巩固了明朝对百夷的统治,巩固了明朝西南边疆的安定,维护了百夷社会的稳定。 第四章论述明朝经营百夷所采取的其他举措。为了巩固对百夷的统治,明朝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其他有效的举措,其中,招机、分化较大百夷土司势力、加强西南边疆的建设是较为重要的举措。这些措施巩固了明朝对百夷的统治。 第五章论述晚明经营百夷的政策。晚明时期,与明朝前期相比,百夷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百夷地区的土司制度的实施严重受阻。缅甸宣慰使司。缅中宣慰使司(即阿瓦)先后大肆扩张领土,反抗明朝,很多百夷土司依附缅甸、阿瓦。面临这一变化,明朝采取了严厉的镇压与招执政策,并且制定了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与募兵制度,有效地巩固了明朝对百夷地区的统治,巩固了西南边疆的安全。 结语部分评述明朝经营百夷的得失。总的来说,明朝经营百夷对百夷社会)“‘生了积极而且深远的影响,巩固了中央王朝对百夷的统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
伍洲扬[2]2016年在《明代中国云南与缅甸的文化交流研究》文中提出14-17世纪是中国云南和缅甸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在明朝、缅人势力、百夷土司叁者遭遇过程中,以朝贡交流为背景,缅甸所产大象、马匹、金银器皿等土产方物经云南进入中国,而中国的丝绸也作为回赐物通过云南流入缅甸。伴随着傣、缅先民之间的互动,缅甸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百夷地区的影响逐步加大;金银器物、贝叶经、贝叶文书和佛教建筑文化也随宗教和政治途径在滇缅之间发生交流。综上,族群互动与政治交往是明代滇缅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精神和物质互嵌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呈现方式:区域内的资源、财富的争夺,宗教、政治秩序的重构则是滇缅文化交流的主要影响。论文第一章首先介绍历史上中国云南和中南半岛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明代滇缅地缘格局所带来的影响。接着介绍明代中国云南和中南半岛的政治秩序,并在一系列连锁反应中揭示明缅关系的演变过程。通过前两节的铺垫,第叁节和第四节主要是对明代滇缅文化交流的主体与文化交流的实现途径进行界定。第五节则从滇缅地理联系及交通网络的角度呈现文化交流的物质基础。第二章,第叁章进入论文主体部分,介绍明代滇缅文化交流的条件、过程、内容、途径、制约因素及其影响。具体来说,第二章主要介绍明缅朝贡交往下的大象、马匹和丝绸等物质文化交流,及朝贡交流背后的礼仪秩序的确立和文化意义的传播。第叁章主要以缅甸东吁王朝北扩,傣缅王族联姻及缅甸上座部佛教入滇为历史背景,讨论滇缅之间金银器物、寺塔和贝叶文化的交流过程,以及物质交流背后蕴含的王权与宗教之象征意义。第四章为明代滇缅文化交流的特征归纳及理论分析部分。第一节指出,滇缅先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及族群社会发展是明代滇缅文化交流先在的条件,或者称为文化交流的内部动因。第二节论述滇缅族群互动与政治交往如何成为文化交流的实现途径,或者称促使交流达成的外部力量。第叁节通过借鉴人类学领域关于礼物交换,物质文化等相关成果,从物质与精神互嵌的角度论述滇缅文化交流的内容及性质。最后一节则从长时段的角度阐述滇缅文化交流的多元层次及意义。综合以上讨论,本研究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整体观为方法论指导,力图揭示出14-17世纪滇缅秩序重整、文化碰撞、物质流动、价值传播的复杂过程及动态历史图景。
杨林兴[3]2015年在《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文中认为学术界对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的研究较为关注,而对于当代云南民族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发展作长时段综合研究的更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云南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历史过程的考察较多,但是对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基本类型、特征和格局及形成原因研究不够,特别是关于云南各民族长期保持友好和谐的内外因素探讨相当不足。继承民族关系和谐的传统因子,促进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实现意义。云南民族关系主要由国家政权与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云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民族内部的关系叁个维度组成。古代云南民族关系是由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与云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云南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融、云南各民族内部之间的互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因素使这些关系得到发展和稳固。而近代云南民族关系由古代云南民族关系发展而来,同时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密切相关,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重要内容。云南各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国家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指导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重构了当代云南的民族政治、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关系,各民族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将走向更高层次的多元一体格局;同时,民族关系趋同性和趋异性两种趋势的发展规律,也将影响着云南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总之,云南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本文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发展作深入系统的探讨,可为深刻认识与理解云南民族关系发展的复杂历程与基本规律提供借鉴或参考。
李文颖[4]2017年在《明代四夷馆新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四夷馆是明朝中央政府负责教习周边民族和国家语言文字,培养翻译人才,同时专门处理朝贡文书的机构。明朝与周边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往来频繁,边疆民族与周边诸国向明朝进献表文,明朝也向他们回赐敕书,由此产生大量非汉文文书。翻译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口译由通事负责,但他们在文字翻译方面并不擅长,明朝因此急需一批通晓交往双方语言文字并能准确翻译的人才。四夷馆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自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设立,到明清鼎革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四夷馆作为专门机构实际存在的时间超过叁个世纪,乾隆年间才与会同馆合并而失去独立地位。四夷馆作为研究课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关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前辈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着眼于四夷馆整体,探讨四夷馆在招生、教学、考核等方面的各项制度;一类深入研究其中某一馆,通过对一馆的全面考察与细致分析,揭示四夷馆的部分面貌,这类研究通常也对本馆所用教材即某馆《译语》的文本作出深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前一类即针对四夷馆各项建制本身的研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考察还不够细致。例如生源前后变化的过程、生徒不断流失的原因与去向等;对四夷馆各分馆的讨论也并不均衡,回回、鞑靼、暹罗等馆已有相当充分的考察,缅甸、百夷等馆则尚无专门讨论。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一些讨论尚不充分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更为细节的描摹,补充其中模糊或缺失的片段。清初四夷馆被继承并改名四译馆,后于乾隆年间遭到撤并,本文也试图对这段时期四译馆的发展情况作出跟进,并探讨撤并的缘由。全文分为叁章,概述如下:第一章讨论四夷馆的设立、方位与招生情况。第一节讨论四夷馆的设立,主要关注到前八馆设立并非同时,而有先后顺序,并试图对此作出解释。第二节考察四夷馆的方位,分迁都前后讨论,尤其注意考证迁都北京后的方位,从四夷馆与翰林院位置关系的角度,探讨其位置变化,另外对南北两馆共存的时间作出探究。第叁节主要考察招生情况,分为招生次数与生徒来源两方面,前者重新考订有明一代四夷馆见于史料记载的招生共计十二次,后者重点考察明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生源的变化过程,并指出天顺年间恢复专收监生的旨意并未实际执行。在生源变化部分,考察了监生所受待遇,并对他们离开四夷馆后的去向作出跟进。第二章讨论四夷馆的教师,探究他们身份、事迹及在四夷馆发展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分为叁节考察,基本遵循四夷馆发展进程展开。第一节关注设馆之初教师多为担任通事的民族人士,有赖于元朝的多民族遗产;第二节明廷不断征集外籍教师以使新增馆所的译学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与本馆培养的汉族教师配合以加强各馆教学水平;第叁节集中讨论了数名起到负面作用的教师,以期揭示明中后期四夷馆管理的松懈与译学的荒疏。第叁章集中讨论了四夷馆内各馆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种不均衡与不同语种或文种的应用范围及使用人数有关,同时与交往民族或国家同明朝的关系亲疏密切相关。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各馆实际承担翻译事务的繁简不均,并由此导致各馆师生人数多寡不一。本章第一、二节内容围绕馆务不均和师生人数不一两点讨论。第叁节则是对四夷馆被清朝继承改名四译馆后情况的跟进。明清鼎革后,四夷馆虽被清朝继承,但明后期以来形成的"废冗闲曹"局面已无法扭转,乾隆年间裁撤四译馆,将其与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在明朝中央官署中,四夷馆的多民族、多元文化面貌表现突出,考察四夷馆的师生群体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多元文化交往的真实状况。同时,四夷馆在教学、招生和日常管理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暴露的不足,对当下外语和民族语言教学也应有重要借鉴意义。
王春桥[5]2015年在《边地土司与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云南边疆的形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并有歧见的重大问题。当今滇西边界的形成与明清两代对边地土司的管理不无关系。清王朝为加强对边地土司管理,依据地理远近,将边地土司分为“内”、“外”之分。土司虽有“内”、“外”之分,但同属中央王朝则无二致。随着清王朝在缅甸建立藩属体系并趋于完善,内外土司的区分消失。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的侵入,逐步将“外”土司沦为其控制下的殖民地。十九世纪晚期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英两国就滇缅边界进行无数次谈判,终未能解决滇缅边界问题。深入探讨明清两代西南土司问题有利于正确认识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有利于正确认识中英滇缅边界谈判的复杂性,揭露英帝国主义侵略缅甸和中国边地的罪行,有利于正确理解百余年来滇西和缅北的形势,对国家治理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对元明清时期云南边地土司的历史发展、云南西部疆域的变迁以及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的考究,探讨云南西部边地土司辖区从“边地”到“国界”的历史过程,分析边地土司与中国疆域变迁的关系,阐释边地土司自身历史发展、藩属体系、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等因素对近代中国边界形成的影响。主要探讨如下问题,并提出本人的独立见解:首先,论述元朝统一云南及控制金齿地区以后云南西部边疆的局势,分析土司制度建立之前,元朝对云南西部边疆的控制,在缅甸建立行省,与缅甸蒲甘王朝的冲突以及麓川兴起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其次,阐述明中前期中央王朝在云南西部边地经营和拓展版图的详情,考证景泰以前云南西部疆域的范围,指出明朝以广置土司的方式使云南西部疆域到永乐时达最广。正统年间,明朝又通过“叁征麓川”及善后措施,完全控制了潞江以西的云南西部边地,但因对缅甸、木邦等边地土司处置不当,为后来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的纷争埋下了隐患。通过对明代中后期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纷争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考究,探讨缅甸东吁王朝兴起和明朝“内忧外患”下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由纷争而致离析的过程,论证明末云南西部疆域内缩的原因及影响。指出了中国王朝的边疆是流动的弹性地域,边地土司为王朝的藩属,有远近亲疏的关系,但同为王朝天下并无二致。在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后,土司去留向背决定着王朝国家疆域的外扩或内缩的结论。第叁,讨论清朝对滇西土司的统治,清缅藩属体系确立的过程及其对滇西传统边界形成的影响,探究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由离析而致内外分野的历程以及滇西传统边界线的形成,指出清朝将归属王朝、接受“王化”的土司称为“内土司”,将明末以降,附缅甸的土司称为“外土司”。这是清朝对“中华秩序”中“我者”与“他者”的区分,是元明以来云南西部边地自身历史发展及其与王朝国家互动的结果。当清缅藩属体系确立后,边地土司内外之分消失。第四,以全球史的视野阐述清朝和英国关于缅甸“存祀入贡”及滇缅划界等问题的交涉及结果,认为清缅藩属体系崩溃后,中英开始近代滇缅边界谈判,并最先划定了滇西土司段的边界,在中缅之间首次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界,这标志着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意味着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地从“边地”到“国界”转变的完成。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地从“边地”到“国家”的转变是中国从“天下”(王朝国家)到“国家”(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转型在边疆问题上的体现,是云南西部边疆自身历史发展脉络和连续性、中央王朝和缅甸势力盛衰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妙[6]2013年在《明清时期永昌、普洱两地百夷发展差异探究》文中指出明清时期的永昌、普洱两地均为云南百夷的主要分布区,两地虽是同一民族的聚居区,但各自百夷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却不尽相同,使得两地百夷的发展轨迹不同。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部分,概述明清时期永昌、普洱两地政区沿革,比较两地地缘政治的差异,分析两地百夷分布区域的特点;通过比较两地百夷土司制度的差异,以及两地百夷对改土归流的不同应对手段,说明两地百夷在政治发展上的差异。第二部分,概述两地明代以前的交通状况,探讨交通传统的不同所造成两地在对外交往中的差异性;通过分析明清时期两地移民在类别、空间分布的不同,使得两地受移民的影响不同;最后对两地经济发展作出比较分析。第叁部分,比较两地宗教信仰类型、外来宗教传入时间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等方面,探讨宗教在两地百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分析两地儒学以及寺庙教育的兴起、发展、数量上的差异,说明两地百夷文化发展的不同。第四部分,通过比较明清时期与两地百夷密切相关的军事冲突,分析与两地百夷有关的事件对疆域变迁、社会发展的影响,表明两地百夷在边疆中的重要地位。最后指出两地百夷发展差异的原因:在于地理及政治环境不同,从而导致两地百夷在各方面的发展上有所不同;而中央王朝廷对两地不同的治理策略和方式则直接影响着两地的发展与变化。
朱迪[7]2016年在《耿马摆夷土司及其与国家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要探讨耿马摆夷土司与国家的关系,从横向上来看,土司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从土司的治理手段、政权组织、当地的社会文化等部分表现出来的,研究二者间的互动关系,要从耿马摆夷土司本身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层面入手;而从纵向上看,耿马摆夷土司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历史中的“国家化”的进程中,这部分既有国家对该土司掌控的层层深入,又有耿马摆夷土司对国家认同的逐步加深。因此探讨二者的关系,首先要从该地区摆夷的源流谈起,在文献记载和历史记忆之中探讨该地区摆夷对自己族群身份的认知以及树立起中华民族认同的进程;其次重点研究耿马摆夷土司的行政架构和发展历史,探讨在它的施治手段和历史事件,在这些行为中其“国家化”过程如何被体现和实现;最后,被耿马摆夷普遍信奉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相比内地汉文化是一种“异文化”,它与该地区摆夷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在当地佛教信仰与摆夷土司这一地方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耿马摆夷土司和国家的关系中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通过历时和共时对该地区宗教信仰的研究,考察地方社会的变迁以及与国家关系的变化。
胡鹏飞[8]2017年在《孟密土司与明代云南西部边疆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明代,因为土司的兴废,今云南边外地区作为明王朝的西部边疆地区,局势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后,尤其自永乐以降,明王朝在这一地区建立起了颇为完备的土司体系,将今缅甸大部,泰国、老挝北部纳入了朝廷的版图;嘉靖以后,由于这一地区土司的纷争、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明朝在此区域的土司体系崩溃。不但此地尽失,还进一步危及到今云南边境以内地区。因此,土司因素,使明朝西南边疆的盈缩兴衰,呈现出与北部边疆不同的“风景”。很显然,对这一地区土司发展历程、朝廷对土司的制度管理及相互关系、土司的利益诉求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不但是研究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探析西南边疆发展及其规律的重要切入点。孟密土司,作为这一地区的土司个案,在土司纷争的夹缝中,从安抚司上升为宣抚司,再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为缅甸东吁王朝灭亡。孟密的兴亡,折射出此地区土司之间的复杂关系,孟密还因宝井问题与明廷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关系,并且孟密与缅甸土司的矛盾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嘉靖、万历时期边地土司崩溃的导火线。因此,孟密土司与明代西南边疆关系的研究,是我们认识明代西南边疆大变局的重要因素。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孟密在从属麓川、木邦土司时期的滇西边地的基本情况:在明王朝统治滇西边疆地区初期,通过对麓川问题的解决,明王朝建立起相应的边地土司体系,维护其统治,保障滇西地区的稳定。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孟密脱离木邦宣慰司管理时期的滇西边地形势:孟密在曩罕弄母子的领导下,凭借宝井之利,取得中央王朝的认可,从而被立为安抚司,直接隶属于云南布政司。孟密安抚司的设置,是明中期滇西边地土司体系的重大调整,导致边地土司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是该地区由治到乱重要的转折。第叁部分主要探讨了孟密土司同其他边地土司的纷争仇杀的概况:弘治年间,孟密同木邦、孟养等土司在滇西边地展开大规模仇杀,明廷通过武力胁抚的方式解决边疆争端。正德至嘉靖初期,滇西边疆地区战火重燃,孟养与木邦联合攻灭缅甸宣慰司,而明廷则不顾土司间争端,继续采买孟密宝石,导致滇西边地局势持续动荡。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孟密在明、缅之间的发展情况以及明王朝滇西边境大规模内缩的过程:孟密在明、缅两大势力之间左右摇摆,最终为缅甸所占有。明廷由攻转守,筑八关以御敌。明王朝开采孟密宝井,引发阿瓦的入侵,致使八关外大量领土丧失,最终使得云南西部边境内缩至腾越至叁宣一带的八关地区,明、缅双方沿此地带对峙。
毕奥南[9]2005年在《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文中认为麓川王国在元末已摆脱元朝控制自治一方。当明朝接替元朝在云南的统治权时,要求麓川服从。麓川不愿受明朝控制,并在兼并同族以扩大势力时与明朝发生冲突。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制服麓川,将其分解为数部,这对明王朝控制当地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本文通过对这段史事的分析,着重指出,明朝对麓川的控制是分阶段完成的。由于形势不同,双方关系各阶段变化各有原因;某些史书为强调明朝统治合法性而忽略各阶段具体情节的做法,是将事情简单化,有碍后人认识真实史实。
胡绍华[10]2004年在《从《百夷传》论傣族封建领主制社会的形成》文中认为《百夷传》是明朝初年钱古训、李思聪所着的一部见闻录。此书重点记载了今天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傣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同时也记载了车里(西双版纳)等地傣族情况,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该书成书的历史背景是在明初洪武末年,由于百夷(傣族)与缅甸(明代时的缅甸宣慰使司,是明朝云南边境所设置的"六慰"之一)经常发生纠纷,明朝中央派遣行人钱古训、李思聪出使缅甸和百夷,调解相互之间的纠纷,归后所写的一本见闻之
参考文献:
[1]. 明朝经营百夷研究[D]. 于秀情.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2]. 明代中国云南与缅甸的文化交流研究[D]. 伍洲扬. 云南大学. 2016
[3]. 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D]. 杨林兴. 云南大学. 2015
[4]. 明代四夷馆新探[D]. 李文颖. 南京大学. 2017
[5]. 边地土司与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D]. 王春桥. 云南大学. 2015
[6]. 明清时期永昌、普洱两地百夷发展差异探究[D]. 张妙. 云南大学. 2013
[7]. 耿马摆夷土司及其与国家关系研究[D]. 朱迪. 云南大学. 2016
[8]. 孟密土司与明代云南西部边疆变迁研究[D]. 胡鹏飞. 云南大学. 2017
[9]. 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J]. 毕奥南.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
[10]. 从《百夷传》论傣族封建领主制社会的形成[J]. 胡绍华. 民族史研究. 2004
标签: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明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云南发展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