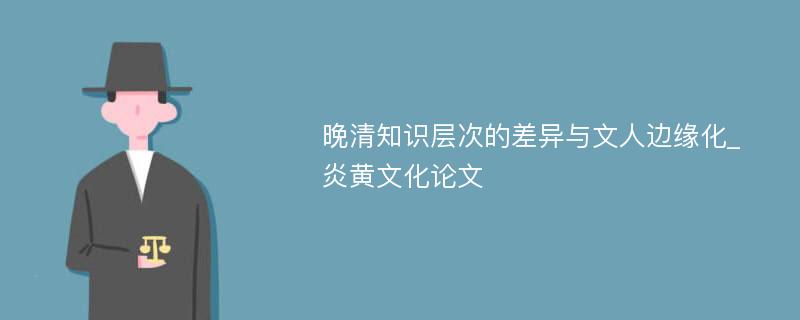
晚清知识层的差异及士人的边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晚清论文,差异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锢蔽者自锢蔽,开通者自开通”,这是晚清社会的一个有趣现象。它反映着知识群体既有思想方面的分歧又存在风尚的差异。①晚清时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又由于西方器物、思想对各地区、各阶层的影响不一样,所以在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风尚等方面形成了不小的地域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晚清社会风尚的这一特点,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晚清政治变革、社会变动不同的认知;造成了一部分人思想很新,而另一部分人思想偏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却几乎处于静止的状态。
一般地说,近代以来人们的信息源大体一致。“大众传播工具同时向社会每一成员传布同样的思想”,②在传媒作用下,大众的喜好、审美观点、价值取向无不受到它的导向而趋于一致,易于表现相同或近似的价值观。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使得各地区不仅在大众传播工具的发展利用上不同步,而且在同一地区能否成为新媒体的受众也很不一样。再加上人们的生活环境、物质生活状态相差悬殊,导致人群与人群之间即使在媒体“同样的思想”影响下,也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差别。这里仅就晚清时期知识层的不同风尚做具体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
19世纪50年代以后,当沿海通商口岸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时,知识层的风尚差异渐次形成。其中,上海知识层率先在人际关系、风气方面有了新的趋向。50年代末,有人议论说:“今之交友者,意气伪也,学问谬也。广通声气者,以喧寂为轩轾;趋慕势要者,以荣悴为亲疏。故以势交者,势败则散;以利交者,利尽则疏”。“今之士子,贬气节、慕势利。”③交谊以财以利,这在一贯崇尚清高的士夫文人,实在是一种就俗趋下。王韬感慨说:“古之所谓名士者,怀抱经济以待时,植立型坊以励俗;世不我用,则食贫终老而无悔,人不我师,则返躬自修而益勉。岂有仆仆求人,孳孳牟利,刻数卷诗词以为乞钱利器,假当道柬札以为调金要符!”知识层做人的气节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变质,甚或到了“偶得一友,则遽述其吹嘘;乍觐一人,且暗审其贫富。周旋揖让为谋食具文,谈吐诙谐皆求钱地步”。④而且愈到后来,风气愈趋之于下,以至报纸在总结申江陋习时说,衣冠取人成了商品经济发展之后上海出现的坏风气,而且发展到“新交因狐裘而订”,“旧友以鹑结而疏”的程度。⑤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重商的社会风气,转而导致士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为师者日益众,延师者日益轻。其诗书士族之家,犹知重传,而市井之中,欲以经管贸易之余为设一席,无怪饮食起居视如伙友,即学俸之间,亦必握算无遗。……师至今日其自待亦太薄矣,迩来课读者流,大抵以求馆之艰难吞声下气,惟恐明年又在何处无以为糊口之谋,而隐忍之苦衷,实有不可明言者”。⑥以课授为生者斯文扫地,反映着深刻的时代变迁。它既说明士人地位的动摇、耕读传统的失宠,也说明时代转向,重商风气渐次形成,价值观念发生了嬗变,社会评价标准随之发生了变化。⑦耐人寻味的是,90年代,内地乡间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1893年,一直居住在乡间,对士人生活状况有切身体验的刘大鹏这样写道:“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就商者。”次年年初,他再次感叹说:“世风之凌夷,不可言矣。邑人之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1896年,“事态”的发展似乎更为严重,“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做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至此,已经与7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差不多了。以后几年,这里读书人的地位持续恶化。 1898年,“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 1903年,“竞尚财利,凡聪慧子弟,均弃读书而为商贾”,1904年,士“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读书之士往往坐困,并无生路”。到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前夕,“读书一事人皆视之甚轻”。
事实上,“读书无用”风气源于晚清谋生、发展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拓宽。废科举以后,社会评价标准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人们不仅可以从商事贾,另外还有学新学新知、选择新谋生出路的可能。正因如此,旧时士人的优势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刘大鹏感叹道:“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为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近年来新学之兴,以能洋人之学为高。”⑧
时代的变迁不仅使士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也迫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为适应变化而不断趋新。于是,一个新知识群体渐次产生。就新知识群整体而言,他们对西方文化和西化的生活方式采取了宽容、欣赏甚至是接受的态度。当然这里存在着程度的不同。有人只是试图了解、认识西方文化。而另一些人则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表现出一种钻研精神。1889~1893年,上海的格致书院举行特课考试,由热心科学与洋务的中国官员命题。命题的范围从时政(铁路、轮船、电报、丝茶贸易)到国策(军事、人才、利权),再到科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化学原质名称中译问题”、“金属性质及导体阴阳极问题”、“大洋海、大西洋海、印度海、北冰海、南冰海考”)等,考察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参加考试的人不仅有格致书院的学生,还包括各地的读书人,总人数虽不可稽考,但获超等、特等和一等以上奖的共有1878人,他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获奖者身份,至少包括府学生、县附生、县生员、县附贡生、监生、举人、候选县丞、县学增生、府学优贡生、廪生、拔贡生等,⑨差不多都属于城乡中下层知识分子。与全国4亿人口相比,这几千乃至几万关心西学的知识分子可能不算太多,但是与全国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以及几十万绅士相比,这一数字又不能忽略不计。它至少给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时代信息:晚清社会不再是旧学一统天下,新的文化讯息、求新的知识风尚已清新吹过。
晚清知识层明显地分属新旧两种文化圈。一种文化圈“尚洋”,这部分人多数生活在通商口岸,外国的器物文化以及西风西俗对他们影响很大。他们的知识结构也比较新,至少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甚或有一定的研究。由于长期受商品经济、商业化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与旧士人阶层相比有明显地区别,不那么看重中国传统的为人、为学、“穷达”之道了。就他们从事的职业而言,多数与外国人开办的文化教育机构有关,如教会的书馆,中国人自办或外国人办的新闻机构,如报馆、翻译馆,还有一些属于自由撰稿人。这部分人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有淡化的趋势,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在生活上接受了西方样式。1859年,与王韬时相过从的徐同柏(号春甫)以西法结婚,王韬在日记中写到,“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⑩当然,这类新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的亲疏决定了他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的疏密,并不是一新全新。
另一个文化圈更靠近传统,无论生活状态还是思想方式都明显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他们在思想感情方面,与传统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中的一部分对于晚清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全然不知,有些甚至和西学完全不沾边。山西举人刘大鹏的日记反映出,1897年之前,他的主要关怀还是自己和儿子怎样读书应试,对乡间偶尔刮过的“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的“坏风气”并没有切肤之痛。1897年之后,他得知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读“时务书”。为了赶上时代,他千方百计托人从京城买回一箱时务书,而他眼中的时务书仅仅是“御篡七经共十六套,御批通鉴辑览两大套,皇朝经世文编四套,皇朝经世文续编二套,康熙字典一部,洋板”(11)之类的旧式经世书,与通商口岸知识分子所读的时务书有不小距离。与刘大鹏境况相仿的乡间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属于旧文化圈的文人在人数和地域分布上,远比新知识分子群大,大都市有他们的身影,广阔乡镇是他们的天下,连城市生活最接近西化的上海也有不小的一股势力。以名望而言,刘熙载、俞樾当是他们的代表。
群体的不同归属造成了他们思想观念、政治态度乃至人格的分裂。19世纪70-80年代,郭嵩焘“力主中国当亟办火车、轮船、电报三事,长沙人士,皆目笑腹诽,不与往来”(12)。这时候在内地大中城市,洋务没有什么市场,趋新风尚当然更没有市场。甲午以后,情况不同了,西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旧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总理衙门不无忧虑地说:“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相互攻讦的结果是,“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13)群体的不同归属不仅造成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观念,而且“终不能合”,分化是相当明显的。
二
知识层的风尚变化缘于晚清社会变迁。晚清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就大局而言,至少存在几种发展趋势:其一,由于帝国主义不断侵略,国家政权呈现不断衰弱的趋势。其二,社会经济表现为一种变化发展的趋势,其表现是传统农业经济既不断衰退又缓慢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新经济因素不断长成;近代工业企业相继出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渐替代了前近代商业经济;近代工商业城市迅速发展等。晚清社会经济的种种变化,引起了社会生活的连锁反应,造成各种社会结构的变动,引起风尚变化和差异的产生。
19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由于上海租界外国资本主义的“示范”作用,使这里的社会风尚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许多旧式的人际关系被商品经济的金钱关系所取代。“沪上习尚奢华,仪文放废,而洋泾尤不可问”,最让文人“不堪回首”的几种关系,是“德重才优,桃李春风次第收。师道尊无右,忠敬宜深厚”的师生关系,变成了“脩膳薄云秋,防先虑后,呼马呼牛,眉眼谁甘受”的雇佣关系,致使读书授馆之人的地位大不如前。原来理想中的生意买卖关系,是“生计营求,术学陶朱雅谊留。真货公平售,价弗欺童叟”,如今却变成“虚伪日相投,鬼谋白昼,较尽锱铢,情面无亲旧”,前近代社会那种靠地域、血缘、宗法形成的富于人情味、重乡情的人际关系,被金钱、狡诈无情地剥夺。传统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高下尊卑本可以从人们的穿着打扮上一眼洞悉,“丝缎绫绸,锦绣章身尽上流。品重衣宜美,下贱人难比”,如今变成了“仆隶偶盈余,全忘法守,艳服华冠,绅宦同行走”,等级秩序、社会群体的组合形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动,风尚在这种变动中也发生着历时性转移,原来在四民社会中居于较高地位的旧式的文人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情绪。(14)
风尚转移以口岸城市为中心呈水波状缓慢地向外扩展。紧邻上海的定海县,中外通商之后商品经济发展,引起“风俗丕变,不重儒,应科试者少”。不应科试的人们多半“志在通晓英算”,“相率趋沪若鹜”,经商牟利成了一时的风气。与上海朝发夕至的江苏六合,“自轨舶纷驰,商场集中沪镇”后,“渐染仿效,不揣本而齐末,消耗之途多而殷实之户少,曩时朴厚之风一变而为奢靡,生计艰窘,诈伪滋多……”(15)。传统农耕时代提倡的那种重农抑商、甚至贱商的社会风尚被轻而易举地破坏了。19世纪末,内地一些地区,士人重商轻儒现象也次第出现。据刘大鹏观察,当时的祁县、太谷一带,为商者十之八九,读书者十之一二,经商成了一时风气。理由很简单,有些人“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更多的人则“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16)再往后,知识层中为官的那一部分兼营工商,志在牟利的情况多了起来,不仅成为一时的风气,而且带动了社会风尚的转移。有论者说:“甲午战争之前,盛宣怀等一批洋务官绅经营近代企业,是由绅向商流动的开始,而在1895年1913年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创建热潮中,官、绅向商人(企业主)的流动已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了。”(17)“1895年之后,许多中上层文人虽未完全放弃追求学问,但也开始参与现代经营活动。他们不仅进行投资,而且也开办和经营各种企业。借助于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工商业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视的行业”。“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内地最富饶的省份也是如此”。(18)弃儒经商的最典型例子是张謇以状元身份办厂,这不仅是以学人商的典型,而且也是千年科举历史的绝唱。
士人经商、官商合流对商人来说,不仅是名誉地位的提升,归根结底是为了有所依仗,有靠山,这样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就有优势;对官吏和知识层来说,则可以通过这条捷径迅速地积累大量的财富,实现仅靠权力不能带来的生活享受。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价值取向的改变,人们头脑里原有的“文化崇高感”轰然倒塌,在普通民众眼中,甚至把“穷困潦倒”与“耕读”划了等号,这样的变化何其深刻。职业的分野是导致知识层风尚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晚清时期以职业划分社会群体替代了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知识层的队伍明显多样化起来。从大的职业分工来看,晚清时期文化人的主要谋生之路,除传统的读书出仕(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即知识层中的官吏群体)之外,还可以经商办厂,成为工商阶层;可以“投笔从戎”,成为新式军人;可以在新式文化机构就职,成为记者、律师、医生、新式学堂教员等。就职方向的不同,导致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境况迥异,同样也导致他们所受风尚影响的差异。新的职业分野打破了士这一“特权”阶层,造成四民社会的解体。一方面,新的职业形成新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传统士人以新式教育为媒介向社会其他阶层流动,其方向有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甚至还有进入军队,以举人、秀才的身份效命沙场。柏文蔚曾经举例说,合肥的翰林周维藩进了南京的陆军师范学堂;三河的举人汪承继自费入江北陆军师范学堂读书,每月要花10两银子;而江北陆军师范学堂学习的廪贡秀才差不多有180人之多。(19)除此以外,绅的称谓也多样化起来,像绅商,官绅,军绅等,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组合的大致方向。经历了这样的重组,旧士绅阶层渐次消亡,晚清知识层因而有了多样化这一特点。
知识层的分化伴随易位与流动而发生。知识层变化的一个突出结果,是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既有文化知识,又有官的显赫地位,还有商场奋斗的经历,同时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所以他们在晚清以及民国以后的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衍化成日后的官僚资产阶级,在清王朝倒台以后成为新的统治阶层。由此观之,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知识群体的变化,从而引起知识层风尚的差异。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了晚清政治的变化。
新式教育的出现是知识层风尚变化及差异的另一个动因。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1902年,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是6912人,而1909年,数猛增到1,638,884人,到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学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大中城市,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与旧士大夫群体有很大不同,“近代学生群的地位与前途,以带来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文明的近代化变革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一趋势看,他们大都不是依附于旧的阶级,而是追随进步势力的旗帜,政治上要求变革专制制度,经济上要求发展工商业,使国家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理想”。(20)新知识结构带来新的思想风貌,它不仅改变了新知识群体风尚追求,而且对各阶层民众起着移风易俗的倡导作用。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上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如唱歌课、体育课和各种活动课。这些新型的教育内容成为社会新风的“导体”。晚清文人去中小学参观体育、唱歌课是很流行的一种带有观赏娱乐性的活动,也使社会各界人士开阔了眼界。(21)学生们常常把在新式学堂中学到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首先是介绍到自己的家乡,从而推动那里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
三
知识层的风尚转变以及差异带来一定的社会震荡。首先,趋新与守旧在思想观念、社会风尚的差异导致知识层中的官吏队伍出现趋新与守旧两个阵营,造成统治阶级的分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晚清时期统治者的力量。一部分官吏群体成为新风尚的响应者和倡导者,成为趋新力量的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开风气之先,助长了近代新思想观念的成长,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1840年以后,连续两场战争的失败,终于使一部分人觉悟,这种觉悟便是正视世界。有学者做过统计,1840-1860年的20年间,只有一个人明确表示过中国遇到了“变局”,而1860-1900年的40年间,至少有43人正式发表过这样的认识。(22)这一认识使一部分士大夫的视野扩大到世界,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国家和认识自己。洋务时期中央与地方的洋务派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议论,这里不赘述。洋务派的这些认识使他们同世界接近了许多。举例来说,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成为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亲历西方,使他对世界的认识比国内的洋务派更为深刻。他知道了除技艺之外,西方还有一套政治制度、法律、思想文化。(23)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了解它并介绍给国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想把中国形象介绍给世界。(24)
19世纪80~90年代,国内的一些洋务派高级官员参与了普及科学的活动。1886~1894年之间,上海格致书院搞了一系列考试活动,特别邀请了一批略知西学的督抚大员和知名人士参与命题。有案可查的命题人包括:邵友濂、薛福成、周馥、龚照瑗、许星台、盛宣怀、胡云楣、李鸿章、曾国荃、傅兰雅、聂辑椝、刘坤一、郑观应等,他们所出题目从治国方略到科学研究,几乎无所不包。比如,1887年的“中国近年丝茶贸易问题”,1888年的“收回被洋人所夺工商利权问题”,1890年的“化学原质名称中译问题”,1891年的“食物、环境与人身关系”,1891年的“物体凝流二质论潮汐应月说”,1893年的“整顿中国教务策”等,(25)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和自然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近代科学知识是通过怎样的轨迹在中国普及开来,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洋务派地方大员们在近代社会风尚变迁中所起的积极推进作用。
对晚清社会而言,这些开明官吏所倡导以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接受的乃是一种时代新风尚。这种新风尚总体上说有利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变化,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在这个意义说,他们已经在同一个社会等级中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了。这一结局使统治阶级形成了实际上的分裂,因而从另一个方面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至少,他们对国家出现的重大问题有了不一样的、甚至带有原则性的分歧。当然,统治阶级的这种分化在开始时只是一个趋势,真正形成分裂,至少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也就是晚清最后的四、五十年。把它的影响估计过高同样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
统治阶级中不同群体在晚清政治、文化等方面不仅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还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风尚。中央和地方都形成了思想开明、行为趋新的一部分官吏和相对保守、言行守旧的一部分官吏。愈到清末,趋新的阵营就愈显得声势浩大。像端方、锡良等人,显然属于前者。他们在自己统辖的范围内,或者对学堂学生采取了奖掖、优容的政策,或者在清末立宪、开国会问题上态度积极。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一定程度与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从而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
与上述开明派相反,洋务运动及其以后一段历史时期,特别是戊戌维新失败、义和团运动以后把持政权的顽固派,则是中国社会极端守旧、顽固的一派。他们以道义鸣高,在对待西学问题上,坚持守旧立场,提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以为这样便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就可以保持中国文化传统不变。还有的人拒绝外来文化竟然到了把自己家面对使馆区的大门封死,路遇洋人以扇掩面的地步。更有甚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不惜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赌注,把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不管晚清时期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不必去考察实际生活中的他们是否接受了新的物质生活条件,只从他们的观念、作为和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就可以知道他们距离时代多么遥远。
思想守旧的官吏对新风气看不惯,他们对新风尚的不满和议论相当激烈。以湖南为例, 19世纪70-80年代“风气未开,向来最恶洋务”,以至于郭嵩焘1879年卸任回乡时,由于乘火轮船而遭到绅民的拒绝。郭嵩焘在日记里写到:长、善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地方官员“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26)直到20世纪初年,湘籍驻外公使罗丰禄死时,“其丧归里,卞宝第为总督,佯语藩县司道,问罗丰禄为何人,群知卞意,答以不知,故延宴阖城文武,不许往吊”。(27)晚清新政和预备立宪活动中不仅各地区普遍设立新学堂,连各部委也开设相关学堂,比如,户部成立计学馆,刑部开设兵学馆,工部设艺学馆等,未设学馆的部门便产生一种危机感。吏部官员们说:“今新署林立,我而不开学馆,将无以自存,渐为他部所并。”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偏激,也不管学堂与国家管理部门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产生这种认识显然迫于一种改革的压力,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胡思敬等思想相对保守的人物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部办学堂是“保全禄位”的卑鄙行为。(28)对于一种新生事物,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理解抱有不同的态度,时有抵牾发生,这种状况不但使晚清社会呈现五色斑斓的局面,而且也使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复杂多变,社会革命曲折艰难。
其次,风尚差异还导致知识层的另一种分化,一部分知识群体成为社会主流阶层,另一部分越来越边缘化。因晚清政治变革而形成、对中国发展之路影响甚大的知识层,逐渐成为主流阶层。换一句话说,他们成为晚清社会思潮的主要承载着。这部分人构成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以及晚清社会持各种变革主张的政治团体,他们是时代新风的积极倡导者。尽管洋务三十年并没有把中国引上独立、富强之路,但是,洋务派的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历程中却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由此而兴起的思想维新潮流一发而不可收。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政治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康梁维新派汇集了一个时期以来的新思想,形成了完整的变法主张并付诸行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主张革新政治,而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和思想解放运动,还搞了大规模移风易俗的社会改良。尽管这些活动随着维新运动被镇压而夭折,但是带给社会的冲击却是长久的。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他们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一起,展开宏大的宣传攻势,尽管他们的思想主张不尽相同,采取的方式不尽一致,所走的道路也大不一样,但是他们对清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其中,倾向革命的知识群体在思想风尚方面最为激进。他们在清末十几年间,除了主张民族主义,建立共和民主政治和提倡民生之外,还倡导颇为激进的风尚,诸如昌言革命排满,掀起革命之风;主张军国民教育,提倡尚武之风;反对旧伦理,力主去除大家庭等,这些新主张有些成为时代之风,也有些仅仅是个别人的激进思想,远没能形成一时的社会风尚。但他们的这些思想主张,激起波澜壮阔的时代风潮,正是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才使条件并不充分,时机不很成熟的革命成功了。
总起来说,晚清知识层分成不同的社会政治群体,趋新的那一部分在政治主张上可能不那么一致,可是在提倡社会新风尚方面都十分积极。当然,晚清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种种社会变革包括政治变革在社会上层或知识层身上容易形成各种烙印,很多人因风云际会而显赫一时,不论是统治集团中的名臣重将,还是改良、革命的领袖式人物,他们曾经对近代社会转型以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又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政治动荡中跟不上时代步伐甚或有所倒退。在很多时候,知识层内部趋新与守旧的矛盾和斗争甚至十分激烈。以群体而言,戊戌维新时期湖南的知识层发生了趋新的变化,“贤士大夫,渐谙外情,竞购新政”,(29)使其走在各省之先,成为维新先进省份之一。与此同时,湖南知识群体的内部斗争也是最为惨烈的省份之一。热心新政的谭嗣同、林圭等与坚决的反对派王先谦、叶德辉、王闿运之流形同水火,(30)当然,他们争执的焦点不一定是维新与守旧,这一点早有学者详论。
一部分士人逐渐边缘化。这部分人主要是旧学培育出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应该称传统士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谋生之路皆因旧学内容定型或基本定型,因而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面对传统儒学的没落他们一时难以适应,甚或困顿竭厥,挣扎在生活贫困线上。晚清士人边缘化是一个过程,开始是缓慢的,至少在戊戌维新之前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到 1905年宣布废科举前后,边缘化过程加快,颇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势。同时,边缘化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问内容的边缘化,二是因生计问题引发的社会地位的边缘化。
据总理衙门奏报,“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因在于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学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顾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其真有旧学者又往往不通新学,辄与新理相忤而为众所鄙弃。”(31)这是说“中学”的先生为学生看不起。(32)1905年,刘大鹏观察到“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33)宋恕则说:“中学教员类被轻贱者,虽薄俸之所然,亦斯习之愧。”(34)也就是说,中学边缘化还因为这些人没有真正掌握学问。当然,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解释了。
学问内容不合时宜是困顿的一个方面,学无用武之地则是困顿的另一方面。某种意学无用武之地、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比学问内容的边缘化来得早,影响也大。废科举前,旧士人“坐困乡里”的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废科举后,问题愈加突出。来自江苏学务会的一份文件这样说:“科举既停,凡国文确有根柢,无论已得科举、未得科举而心志、年力愿观新学之全者,一省岂无三百人。能慰其愿,则事半功倍,尽成有用之才;不能慰其愿,将终身废弃,反受兴学之困。故兴学所宜首及者,端在科举既废又无合格学堂可就之人矣。已仕者犹开法学堂以课之,未仕者岂不同是国民而恝然置之欤!”(35)怎样才能将这些学问内容已经定型,又明显地不适应新时代的人利用起来,起码也应有所安顿,成为废科举之后的严重问题。
废科举的一个直接措施是将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这样就迫使原先“除教读外,兼以各书院为生计”的“大多数之寒士”无以为生。(36)出路问题不仅困扰着有边缘化之虞的旧士人,而且困扰着清末各级政府。于是,安置他们、怎样安置,成为时论焦点。如山西的刘大鹏,无助之时也去“经营小煤窑”,贩运煤炭;民国后还出任县立小学校长。总起来看,他们的生活但求温饱而已。这样的生活景况,要想保住四民社会中至高的社会地位几乎没有可能。
第三,风尚差异进一步促成上下悬隔,加剧了社会的不平衡。中下层士人知识分子丧失生计还直接带来另一个结果,民间贫苦百姓读不起书的现象也一时严峻起来。科举即废,“无力读书者,送至不入学塾,或且以为科举已废,读书无用,乡僻之区,竟有十里二十里之间,并私塾而无之者。若不就现有私塾之处,急先设法整顿,力予扶助,将朝廷日言兴学而草野不识字之人日多一日,讵不与朝旨大相背谬,是以当道之忧也。”(37)
这样的忧虑相当普遍。刘师培说:“夫学堂之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若学堂既兴,无论其为公立为私立,入校肄业,莫不索费,购书阅报,所费滋多。彼乡野贫民,仰事俯蓄,尚虞缺乏,子弟虽有求学之心,亦以无资而中止。是则享学校出身之荣者,均富民子弟。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无阶级制度之名,具阶级制度之实。若官立学校,虽免纳费,然舍达官荐达外,鲜克入校,白屋之民,望学校若阶天。岂非科举之弊,作弊者仅数人,学校之弊,则所在皆然,较科举为尤甚!其因有以为利者,则牧令援以超升,绅耆因之以敛费,少数新党恃为糊口之资,富室子弟恃为进身之路,不独使昔日之儒生失业已也,即在下之民,亦以兴学之故,增加赋役,既吸其财,并妨其学。由是而降,贫民永沦于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也。”(38)刘师培所忧的“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的现象在晚清相当严重。其原因不仅在于下层百姓失学,更在于世局的动荡,此当不言而喻。而知识层的风尚差异也直接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果,趋新与从旧越来越成为两种世界。
未变的这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还不同程度影响着普通民众。这可以从民间百姓的好恶中曲折地反映出来。读西书而获功名的新知识分子不为乡间社会所容,是晚清社会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1906年,太谷城一读书人,“从英人学已三年矣,业既毕,给举人。去冬诣上海,欲游日本,因东洋学生之哄遂归,而服色竟易洋装。近日归乡,人皆目为洋夷,宗族亦待为异类,此华人变为夷者也”。(39)太谷小城的宗族、百姓视穿洋装的为“洋夷”,而大城市的普通百姓也看不惯行为和思想太新的人物。据当时的报道,街道通衢大凡有着洋服者过,总能听到几声打“假洋人”的呼声。上海各种小报把剪发、西装者嘲讽为“狮头驴足”,也是看不惯的一种反应。尽管办报、投稿等形式是很新的时代风尚,但是撰稿者却不一定是新人物,所以报章上的议论各式各样。
总之,晚清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诸种变迁导致了晚清知识层的分化组合,使原本简单得多的社会群体构成复杂化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另一部分却基本保持着原来的风貌。变与不变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有些是因为思想观念问题,也有些是因为经济条件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晚清知识层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侧面,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民国以后社会风尚变迁而继续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风貌不断趋新。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风尚差异主要指知识层的生活意趣、喜好、价值取向等,有别于学术风气。
②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王晓毅、王地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③《王韬日记》1858年11月21日、1859年3月2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④《王韬日记》1859年5月13日。
⑤《申报》1872年4月7日。
⑥《申报》1872年8月17日。
⑦当然,严格地说,这一时期上海发生的变化,既有商业化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恐怕也和教与学的比例失衡有关系,不能简单下结论。
⑧以上史料均引自《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8、65、78、118、131、133、140页。
⑨上述资料参考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8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⑩《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1页。
(11)《刘大鹏日记》,第62页。
(12)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08页。
(13)“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页。
(14)《瀛壖杂志》卷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15)《六合县续志稿》卷三,1919年本。
(16)《退想斋日记》,第17页。
(17)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18)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8、619页。
(19)吴长冀:《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20)以上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
(21)参见《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三十三年二月四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2)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81页。
(23)他在日记中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日记》第3册,第439页。)
(24)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详细记录了郭嵩焘在英国召开的大型招待茶会,全部规格比照外国类似的招待会,邀请了英国外交部官员、社会知名人士和一些国家驻英使节,不少外国人以被邀请为荣。
(25)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八,第373-385页。
(26)《郭嵩焘日记》第3册,第853-854页。
(27)黄濬:《花随人圣庵摭记》,第76页。
(28)《国闻备乘》卷一。
(29)《知新报》,1897年4月12日。
(30)至于说他们“新中有旧”,“旧中存新”是不言而喻的。在现实生活中,思想极端僵化,甚至冥顽不灵、顽固到底的人毕竟少而又少。
(31)《四川提学史方旭致叙永厅劝学所札》(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转引自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2)《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页。当然,这里所指是说中学教习质量差,但是亦可以窥见中学学问不适应时代,逐步开始边缘化。
(33)《退想斋日记》,第143页、145。
(34)《上东抚请奏创粹化学堂议》,《宋恕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2页。
(35)沈同芳:《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上,《马观察良拟江宁省城设立出洋及专门预科说帖》,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第128-132页。
(36)《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卷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37)上海私塾改良会编:《私塾改良总会章程》,《论私塾改良会急宜由官绅提倡》,北京师范大学馆藏铅印本,第9-10页。
(38)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第969-970页。
(39)《退想斋日记》,第149页。
(40)《汪穰卿笔记》卷三。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晚清论文; 读书论文; 边缘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