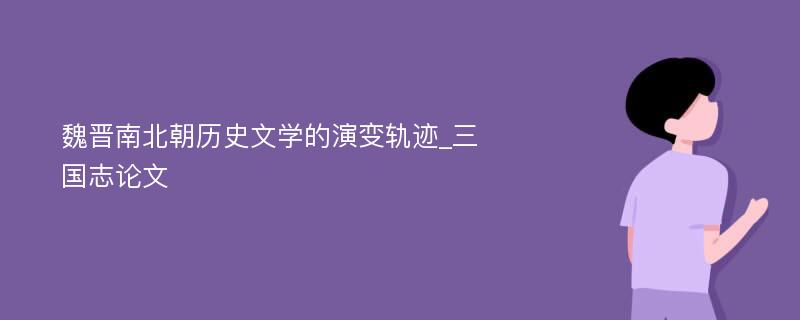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史传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4-0005-07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修史十分重视,每个政府(包括北方各族建立的短期割据政权)都注意设立史官,撰写国史,史学出现了繁荣局面。仅据《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通计亡书共874部,16550余卷,其中只有几十部是汉代以前和隋AI写作成的,其余都是这一时期作品。而且史学已逐步从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自成一派。但从史传文学角度来看,很少能与《史记》、《汉书》相抗衡。这里,我们以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
一、人物范围逐步缩小
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文学,总体上人物类型由上层向下层逐步扩大,而此期的史传文学人物类型逐步向上层转移。
《三国志》、《后汉书》的人物类型还比较广泛。《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比较全面地选取了魏、蜀、吴三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以三个国家的君主为核心,形成了三大政治集团、军事集团以及人物集团。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指出:“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三国之主都很重视人才。三国时期的争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争夺战,各种人物纷纭而出,给《三国志》的人物类型增添了不少色彩。以曹操为例,《魏书·武帝记》记他多次下求贤令,如建安十五年令: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由于强调“唯才是举”,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人才,有的出谋划策,有的冲锋陷阵,有的能文能武。三国时代,军事争夺十分激烈。所以,《三国志》特别着眼于军事家、外交家,展现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相对而言,下层人物入选较少,可以说是一种局限。
《后汉书》的人物类型显得比较突出。在《史记》、《汉书》的类传之外,范晔又创立了7个新的类传, 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东汉一代的历史。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野共愤,形成了批判宦官的一股强大力量,矛盾激化的结果,导致了党锢之祸,《党锢列传》通过李膺、杜密等人与宦官的斗争,真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宦官由来已久,但到了东汉时期,势力强大,炙手可热。他们专权跋扈,干预朝政,“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1] (《后汉书·朱穆传》),为非作歹,使社会陷入黑暗之中,《宦者列传》对这一特有的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东汉时期,还有一些特立独行之人,如谯玄、李业处乱世而守志不移,范式笃于友情,戴就刚直不屈等,范晔统摄于《独行列传》之下。《后汉书》还设《逸民传》,专门反映地主阶级中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妇女在正史中争得一席之地,《后汉书》特立《列女传》,认为“才行高秀者”皆可立传。东汉以来,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家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于是,《后汉书》在《儒林列传》外,又立《文苑列传》,专门记载东汉一代文学家。此外,《方术列传》记载医药、占卜和神仙怪异,共20余人,其中确有像华佗这样的名医,但也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总之,《后汉书》创立的类传,是它人物类型扩大的一个重要表现。每类人物的出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
《宋书》、《南齐书》、《魏书》的人物类型则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步向上层集中,这与当时的门阀制度有很大关系。门阀士族的发展,自汉代开始,到了曹魏时期进一步发展:“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矣。其州大中正主簿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矣。”[2] (《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门阀制度使许多有才能但出身寒微的人受到压抑,以至于左思在《咏史》诗中大加抨击:“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东晋时,门阀士族制度发展到极盛,南北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3] (《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正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史传人物,大都集中在大家世族,下层人物难以入传。如沈约《宋书》,高门士族占了半数,像王、谢两大家族,《宋书》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十多人。而像鲍照这样有才华的人也只能附见于临川王刘义庆的传记之中。对于士族,作者总是以“前代名家”、“风格高峻”等大加称赞。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都是士宦显赫,故而《宋书》为豪门贵族立传也就不足为怪了。萧子显的《南齐书》,人物由皇帝到皇后到皇子到宗室,还有士族,尽管也有高逸、孝义、文学等人物,但只是一种点缀,基本上仍是以上层人物为核心。萧子显是南齐开国君主萧道成的孙子,父亲豫章王萧嶷在南齐也煊赫一时。贵族中的人来写史传,无疑要“走上层路线”了。再看《魏书》,由于北魏政权是门阀化鲜卑族和汉族门阀地主的联合统治,因此,《魏书》中的人物也主要集中在上层,由帝王到皇后到帝王子孙,到士族。《魏书》在写开国君主拓跋珪之前,专列《序纪》,追溯拓跋家谱。书中竭力宣扬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那些高门大族的家诫、门风,称赞“德洽家门,功著王室”。尤为突出的是,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那些高门世族的谱系和亲戚关系,旁及疏支远族,无论有功无功,都要记上一笔。如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鲜卑贵族穆崇,传中列举66人。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北史·魏收传》载:“(杨)愔尝谓收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魏收要以史传当家谱,所以,选入的人物也只能是大家世族了。
另外,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也使作者难以有自己的选人标准。史传成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重要工具,也就难以顾及下层人物了。
二、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
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到《史记》、《汉书》达到高潮,既有生动的叙事,也有个性化的人物。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格化逐步减弱。
《三国志》、《后汉书》已透露出这个信息。《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三国志》简质有法”,可见《三国志》以简约爽洁见长。如被人称为传记中第一的《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白帝城托孤”、“出师表”等事件,叙写了这位政治家、军事家的一生,线索清晰。但由于简约,也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刘备为招纳贤才,去拜见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只用“凡三往,乃见”5个字叙述, 没有具体过程,流于平面化。而小说《三国演义》将这5 个字演义为“三顾茅庐”的故事,是多么生动,当然小说有虚构之处。由于《三国志》在叙事方面以简约为主,省去了许多过程,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裴松之的注来了解详细过程,乃至于反过来借助小说来想象人物的风采。如《文帝纪》写曹丕登基:“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一场登基大典,就这样简单,曹丕的心情就这样平平淡淡。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仅一句独白式的话语,将曹丕的喜悦之情展现出来。由于《三国志》只是略记了人物做过了几件事,而没有写出怎么做和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有的人物只是粗线条的几笔,缺乏具体的行动、言谈、神情的描写,如《文帝纪》、《吴主传》等,大部分篇幅都是按年月次序,简单记录一些诏令、文告、任命之类,而人物的风采没有很好地显示出来。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曾说:“承祚(陈寿)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三国时代,风云人物不少,如果让司马迁来写,肯定会出现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当然,《三国志》也有些传记写得生动,如《张辽传》、《周瑜传》、《吕蒙传》、《关羽传》、《张飞传》等,或用细节展现人物个性,或用人物的神态举动表现个性,或在动态发展中写出人的性格变化。总体上《三国志》已经向着简略叙事方向发展。
《后汉书》在人物刻画方面比《三国志》稍强,它往往“举其大略”而又“诸细意甚多”[1](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如《班超列传》写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的奇特经历,其中有不少生动的描写。试看其年轻时的一段故事:“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当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闲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这个故事,奠定了班超的个性特征,给人以形象之感。《马援列传》写出了一个经历奇特、老当益壮的名将形象,其中也以他的豪言壮语表现他的个性,等等。《后汉书》在新创立的7个类传中, 写了各种各样有特异性的人物,在刻画人物时也注意选择一些典型事例表现人物形象,并以他们的语言展现个性,比《三国志》在写人方面有较大的进展。但范晔写《后汉书》,目的在于“正一代之得失”,所选的人物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所以,在人物刻画方面也往往流于简略叙述。如《张衡传》:“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擒,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气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这种叙事方法,对人物的活动作了概括介绍,但缺乏生动性,人物形象不够鲜明。
如果说《三国志》、《后汉书》已由性格化向叙述化方面转化的话,那么,《宋书》、《南齐书》、《魏书》就已完成了这个转化。人物传记大都变成了叙述性的概要介绍,具体过程和人物形象看不到了,甚至有些传记只是简单地罗列履历。《宋书·武帝记》写刘裕代晋的过程:“(晋恭帝下诏禅让,刘裕)奉表陈让,晋帝已逊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上(刘裕)犹不许。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固请,上乃从之。”简略叙写了代晋的过程,而刘裕当时如何想以及幕后的刀光剑影怎样,都无从看到。《南齐书》也是如此。《高帝纪》上下两卷,写萧道成一生,按日月次序,一一叙述,不见事件经过,甚至不见一句有个性的话。这里,我们录《魏书·李宝传》,以见这三部书写人方面的共同之处:
李宝,字怀素,小字衍孙,陇西狄道人,私署凉王暠之孙也。父翻,字士举,小字武强,私署骁骑将军,祁连、酒泉、晋昌三郡太守。宝沉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伯父歆为沮渠蒙逊所灭,宝徙于姑臧。岁余,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乐为用,每希报雪。属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世祖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诏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宣。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这样的传记,是南北朝史传的主要形式,从人物的籍贯字号起,一直到死,以及子孙,是一个人一生的完整记录。但人物形象不像《史记》、《汉书》那么鲜明了,甚至没有清晰的人物形象,读这样的传记,读者与传主根本产生不了共鸣。
在叙述方法方面,《宋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方法——带叙法。即在原来附传的基础上,把附在最后的有关人物插入到正传之中,暂时打断正传人物事迹,等插入人物的事迹结束后再接正传人物。后来的《南齐书》也用这种方法。带叙法的好处在于避免了呆板,使叙述变化多端,并增大容量;但用得不当,会使传记显得松散拖沓。如临川王刘义庆传中,写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列为佐史国臣。”紧接写鲍照事迹,而鲍照传中又收录了《河清颂》一文,文章本身也较长。这样,刘义庆传就显得松散了。类似的例子不少。
魏晋南北朝史传走向以简略叙事为主的道路,有许多原因。就外部因素来说,此时文学与史学分道扬镳。人们的观念中,史学已从文学中独立出去,如曹丕《典论·论文》列举文学四科是“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萧统《文选》也把史传排除在文学之外,只收录了一些史传的论赞。此种情况表明,史学著作走上了纯粹的记事道路上去了,至于用文学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倒是次要的事了。因此,此期的史传大都以记事为本,而且大量收录经世之文,愈显出历史文献的特征了。就个人因素来说,是作者对传主缺乏深入研究。官方著作为人立传,一般无暇对传主进行研究,甚至对传主一点都不熟悉。韦勒克(Wellek)和沃伦(Warren)在《文学理论》中指出:“一个传记家遇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家所遇到的问题。传记家要解释诗人的文献、书信、见证人的叙述、回忆录和自传性的文字,而且还要解决材料的真伪和见证人的可靠性等类的问题。”[4]传记的写作如此复杂, 而我们的史传家,第一,大都根据现成的资料加工而成史传,缺乏对传主个性研究;第二,即使注意到了第一手材料——传主的大量诗文,也很少去挖掘,充其量是把他附于传内。正因此,写出的人物给人的只是一种表象。
三、思想感情由浓而淡
此期的史传作品,由于以叙述历史事实为主,加之统治者的干预,作者的思想感情也逐步由浓而淡。此期的史传著作,思想感情最为突出的是《后汉书》。据《宋书·范晔传》,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后,“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众多的《后汉书》中,范书能独占鳌头,就在于它有独特之处。范晔对自己的著作非常自负,说“序论”“皆有精意深旨”,尤其是“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后汉书》爱憎分明,笔挟风雷。范晔把自己的爱憎感情寄寓在字里行间,如对于建功异域的班超,忠心为国的马援、敢于与权豪作斗争的范滂等,都予以热情的称赞。我们看《党锢传》中李膺的一件事:
(李膺)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李膺捕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不畏权势,勇气过人。作者在叙事中渗透着对李膺的钦佩之情。《后汉书》对于那些身居高位而腐朽无能的达官贵人,对于那些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的外戚、宦官等豪强势力,也都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像《梁统列传》,对于外戚梁冀,作者历数其令人发指的罪状。他依仗其妹梁太后的权势,专横跋扈,不知杀害了多少人。他的从人也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梁冀还肆意掠夺人民做奴婢,多达数千人。作者对梁冀的凶恶、贪婪予以强烈的斥责、鞭挞。当然,《后汉书》的感情色彩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传论直接体现出来。如《党锢传》的论赞中称李膺的斗争“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染,波荡而从之。”《陈藩列传论》说:“桓灵之世,若陈藩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对于正直官吏予以高度评价。而《宦者传论》则对宦官横行霸道、为害天下的丑恶行径予以强烈的抨击。《独行传》对于那些假借“独行”以抬高名声的伪君子,予以无情讽刺,而对真正的独行之士以及隐逸高人予以赞扬。总之,《后汉书》的感情色彩是可以与《史记》相媲美的,尤其是类传中表现的褒贬之情,在本时期内是独一无二的。
《三国志》作者陈寿处于三国入晋时代,魏已灭吴和蜀,晋又代魏,实现大一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尊魏为正统,但并非随意贬抑吴蜀而颂扬魏国,褒贬比较公允,如《先主传》评刘备“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吴主传》评孙权“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对于三国时一些重要人物的记载,基本上也是带有感情色彩,如对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及关羽、张飞、赵云、张辽等英雄人物,都予以赞扬。《董卓传》对董卓残忍的个性描述中带有愤慨之情,而论赞中又评道:“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足以显示作者的感情色彩。从总体上说,《三国志》由于叙事简略,作者的感情难以在叙事中完全表现出来,大部分显得隐蔽一些,而传后的论赞,基本上弥补了传记中的感情色彩,使人对作者的态度还能比较清晰地辨析出来。它不像《史记》那样火山爆发式的感情,也不像《后汉书》那样笔挟风雷,而是在论赞中一显个性。
相对来说,《宋书》、《南齐书》、《魏书》的思想感情愈来愈淡薄了。上文说过,这些著作在写人时大都是粗陈梗概,甚至罗列履历,很难看出作者对人、对事的态度,他们的感情藏而不露。当然,对于皇上君主、世家贵族的歌颂是明显的,这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感情,并无多大实际价值。我们从传记中,再也感受不到感情的力量了。再看这些著作的论赞,已和“前四史”不大一样了,因为“前四史”的论赞,基本上是作者态度、感情的表现,而此期的论赞,大多是虚夸、不务实的,是一种表面文字,与传记并无多大内在联系。刘知几《史通·论赞》尖锐地批评道:“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而且,这些论赞,也大都不敢以个人思想去评价人物,只能依统治者的思想为标准,对人、对事进行评论。
此期史传感情的淡薄,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史学走上了纯史的道路,作者只要把历史事实记录下来即可,无须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这样做,也符合统治者对修史的要求;而且,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史家也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思想感情。如《南齐书·王智深传》载: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史者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吗?北魏太武帝诛杀史官崔浩,对修史者不能不是一个警告。尽管北魏文宣帝对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5](《魏书·自序》), 但此话又何尝不是一个委婉的警告呢?所以,史传只能依统治者的意愿行事罢了。
四、语言向骈俪发展
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语言由《尚书》的诘屈聱牙逐渐变得生动形象,长短句结合,参差不齐,适合于刻画人物。从《汉书》开始,史传语言已向着整齐方向发展,出现骈偶倾向,但总体上还是以散为主。
到了魏晋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促进了骈文的大发展。骈文反过来也影响了史传文学,使魏晋以后的史传明显带有骈偶特点,刘知几《史通·叙事》批评这种倾向:“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史传中的这种倾向,以论赞文字最为突出。《史记》文章的“太史公曰”纵横驰骋,风格多样,长短结合;到了《汉书》的论赞,往往变单为双,整齐划一。此后,不断发展,到了《三国志》又出现了新特点,试看《诸葛亮传》的“评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可以看出,《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比《汉书》前进了一步。
再到《后汉书》,形式更趋完美,可以说是骈文的成熟阶段了。如《宦者传论》一段:
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从《后汉书》开始,每篇除了有“论”之外,最后还有整齐的四言句作为“赞”,这个赞语,更是典型的骈偶句式。沈约《宋书》的论赞,代表了此期骈俪语言的最高成就。如《谢灵运传论》中的一段: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这段文字是从声韵的角度讲文学发展的情况的,其本身又是一段精采的骈体文。沈约本人擅长音律,所以,写出的骈文又具有声韵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大量收载诗赋、诏令、表奏、祝颂、书信、问论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以骈偶为主,这也是史传骈俪化的一个方面。《三国志》中已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如《诸葛亮传》载《出师表》,《吴主传》中载孙权称帝时吴蜀盟誓文等等。《后汉书》更显其能,仅以《文苑列传》中的人物传记来看,杜笃传载《论都赋》、傅毅传载《迪志诗》、黄香传载《上和帝疏》、崔琦传载《外戚箴》、赵壹传载《谢恩书》、《刺世疾邪赋》、刘梁传载《辩和同之论》、边让传载《章华赋》、郦炎传载《诗二首》、高彪传载《长乐观箴》、祢衡传载《孔融荐祢衡疏》,这些文章文辞华美,骈偶倾向十分明显。此后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收文更多,骈俪倾向也更加明显,有些传主就是骈文高手,如谢灵运、孔稚珪等。
此期的史传文学在叙事时基本保持散文的语言特点,有些作品在句式上也有明显的整齐趋向,有些甚至也有骈偶特点,但不是主流,故不再一一赘述。
收稿日期:2000-06-20
标签:三国志论文; 后汉书论文; 魏书论文; 诸葛亮传论文; 三国论文; 汉朝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史记论文; 宋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