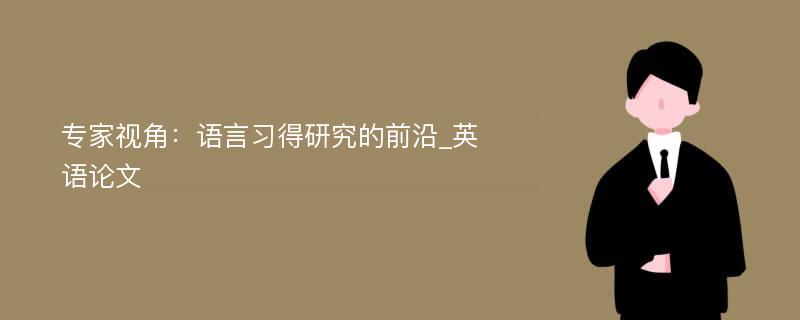
专家视点:语言习得研究前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点论文,习得论文,语言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袁博平(剑桥大学): 二语习得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在围绕“成人二语习得为什么不成功?”“为什么儿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能掌握自己的母语,而成人花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学习二语仍然无法达到母语者的水平?原因何在?”等问题展开。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二语研究人员大多从宏观角度来探讨以上问题,其中包括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在成人二语语法中是否仍然存在?成人二语学习是否受到语言学习关键期的影响?成人二语习得中语言参数的重新设定是否能成功?这些都是当时的研究热点。但是自本世纪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一些微观的问题,正在从宏观方面转向微观方面。在对“关键期”问题的讨论方面,许多研究显示,“关键期”对第二语言各个范畴的影响不同,比如,语音习得与词汇习得相比,后者受“关键期”影响就小得多。因此,笼统地讨论“关键期”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已开始受到质疑。 在二语习得参数重设方面,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微观参数(micro-parameter)而不是宏观参数(macro-parameter)。微观参数指的是语言中的各类特征(features),二语习得涉及语言特征的重新组合。以汉语为例,汉语“是……的”句型中“的”的使用对句子时态起重要作用,比如: (1)张三是这个月结婚。(“结婚”这一事件是否发生不确定) (2)张三是这个月结婚的。(加上“的”后,“结婚”这一事件已经确定发生) 当母语是英语的人学习汉语时,他们必须把“过去时态”这一语言特征从他们母语动词时态上重新组合到汉语“是……的”句型的“的”上(详细研究请参看Mai & Yuan(2016))。这类语言特征重组是否会对成人二语习得带来困难?这是目前许多研究人员所关注的问题。 近几年二语习得领域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接口问题,包括句法与语义的接口、句法与语篇的接口、句法与语用的接口等。 先谈句法与语义的接口问题。 不及物动词有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之分。 (3)a.一条船沉了。 a’.沉了一条船。 b.一棵树倒了。 b’.倒了一棵树。 c.一个老人笑了。 c’.*笑了一个老人。 (3a-b)中的动词表示某种“变化”,而(3c)中的动词表示一种方式,不表示“变化”。它们虽同为不及物动词,表达的意义却不同,因此,这里的句法结构受到动词语义的制约,从而构成了一个句法与语义的接口问题。成人汉语二语习得是否能在句法与语义上接口,这将是汉语二语习得的一个关键问题。 再看句法和语篇的接口问题。 我们都知道,汉语中疑问句的疑问词没有显性移位,是wh-in situ语言,与语篇无关的wh词不能前置,但与语篇有关的wh词可以前置,比如: (4)a.*什么你喜欢? b.什么菜,你没吃? (4a)里的“什么”与语篇无关,所以不能前移,而(4b)里的“什么菜”是听话人和说话人共享范围内的信息,可以前移,这里表现出语篇对句法的牵制。我们的问题是:语言学习者是否能对这种句法-语篇进行成功接口?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二语学习者达不到母语的水平。 再讲句法和语用的接口问题。以汉语“都”的使用为例: (5)a.我把那个苹果都吃了。 b.*我把一个苹果都扔了。 “吃”可以一口一口地吃,可以切分(segment),但“扔”不行,是一次性的动作。这与语用现实有关系。我们要研究的是成人如何进行句法与语用的接口,儿童又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不会告知我们“这里有句法-语义接口,那里有句法-语用接口”等等,那么是什么语料激活了这些接口? 因此,如何解释这些接口问题成为近年研究的重点。研究人员正在从宏观向微观转移,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细致。 研究人员认为不仅在语言习得问题上存在接口,在方法论上也要接口。在语言习得方面,我们现在有大量的量化研究,比如借助ERP、眼动仪等技术在心理语言学及神经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这些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科学的研究手段。虽然这些技术很有用,但研究人员语言学的功底同样也很重要。语言学是做语言习得研究的重要功底,不管采用什么技术,研究人员要有目的语和本族语的扎实功底。现在大家都在做量化分析,但仅仅对量化分析数据的描述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提高解释力。由于在方法上有技术上的接口,设计必须要严谨,如果变量控制不妥,很难得到有效的证据。 此外,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神经学等还要进行跨学科的接口。最后,还有研究人员的接口,现在大量的研究都是合作进行的,单一作者的文章越来越少,因此研究人员要有合作。也就是说,要进行全面接口。在中国,从事二语习得研究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在研究队伍扩大的基础上,要在研究质量上下功夫,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学派,希望这次“全国外语教学与研究中青年学者论坛”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张辉(南京师范大学): 我以前一直从事汉语习语的认知与神经机制研究,2013年起开始关注二语习得,尤其是二语句法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我注意到,二语习得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行为实验和问卷调查,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二语习得的许多理论在影响因素对最终习得状态(ultimate attainment)的预测和证据上有分歧。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新的方法。目前关于二语习得句法加工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尤其是ERP的研究方面,国际SCI和SSCI期刊大概有四十余篇论文,这说明国际学术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Hernandez(2013)在其专著The Bilingual Brain中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提到二语习得研究的三大支柱问题(three pillars in SLA)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第一是习得年龄或最初接触外语的年龄(age of acquisition,AoA),关注二语习得的年龄和关键期问题。关键期到底影响有多大?ERP的第一个句法加工实验是Weber-Fox & Neville(1996)发表在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论文,她们发现越是习得早的,越接近母语。但此实验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控制外语水平。后来的实验基本上都是控制了外语水平,考察不同习得年龄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或者控制习得年龄,看不同外语水平对习得结果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习得年龄关键期问题仍存在争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的学者如Steinhauer(2014)提出,较晚接触外语的学习者(12岁以后)也可以达到接近母语的水平。 第二是外语水平(level of proficiency),研究不同外语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对二语的加工是否与母语者相同。国外对二语句法加工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英语母语者学习西班牙语或德语母语者学习英语等,这些研究都是在印欧语系内进行的,其习得的语言与其母语相似。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母语汉语缺乏印欧语丰富的形态,其在句法上的加工是否表现出特殊性?例如,耿立波、杨亦鸣(2013)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加工英语主谓一致时出现了失匹配负波(MMN)。这一发现在国际期刊的二语句法加工的论文中从来没有报道过,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才能确认。 第三是二语的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研究,研究学习者大脑认知的控制问题。健康的双语者能控制语言的使用,在说一种语言时,他可以控制不说另一种语言,但大脑损伤者则失去了这种控制的能力。双语的认知控制是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国内对认知控制的神经机制研究还很少,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以上三个支柱问题,本人近年来一直关注着。2014年我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就是要运用ERP技术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句法加工的时间进程和神经机制,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能做更多有价值的研究,获得更有价值的发现。 卢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是世界上学习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有世界上最多的英语学习者和最庞大的英语教师队伍,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背景和特点丰富多彩,因此,中国是二语习得研究的富矿,有着数量可观的研究对象及与之相关的最为多样化的研究问题,可以从多方面和多角度探讨二语习得的相关问题和机理。 1)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学生成长。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极为重要,研究者要从教学实践中观察学生、研究学生、发现问题,运用二语习得理论来分析和研究问题,把研究结果反哺于教学,做到教学相长,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随着教育理论中人本主义思想的普及,外语教育和教学越来越多地关注学生和学习者,外语教育和二语习得研究中以学习者为中心(learner-centered/oriented)渐成趋势。要在教学的实践中观察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特殊表现,从中发现问题,查阅文献,进行研究。比如,我们曾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到粤语方言区的一些学生在英语口语中会有吞音或增音现象。一个看似简单的二语者的语音现象,其实蕴含着二语音位习得的深刻道理,可以从母语影响、语言迁移、语音习得、二语水平、交际能力等各个维度进行科学严谨的实证型研究,从而深入分析和理解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习得规律和特点(卢植2002),这样的研究所得的结论才是有意义的。立足和扎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的二语习得研究才能服务于中国的英语教育和教学,以中国外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二语习得研究也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2)跨学科和超学科的方法论在二语习得的研究中日益重要、渐成热点。二语者或双语者处理两种语言的神经机制仍是未解之谜,是目前国际上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需要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对于语言学习的认知过程及其机制,过去多从行为科学的层面进行研究,而且获得了众多极有价值的成果,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二语习得的规律性认识,受心理学等认知科学分支的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的二语习得在本质上具有极高的实证性和多科性。目前,随着人们对二语习得认知神经机制的深入研究,二语习得研究的跨学科特色更为明显,多学科跨学科的团队型研究更为普遍。比如,二语习得研究中著名的“关键期”假设的研究,在美国曾经有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二语习得等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目的就是发现二语学习起始的最佳年龄。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人们更是从认知神经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借以分析不同习得起始年龄二语者的大脑神经机制的差异。二语习得中神经机制的研究实际上也体现了当前国际科学界的热点问题,即脑科学的研究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 3)二语学习者如何将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认知心理学很早就提出人类记忆系统有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两大系统,相应地,人们头脑中的知识有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之分。这两大记忆系统在学习和处理信息上既相互合作又互相竞争,在掌握相同或类似的知识如语言序列和语法规则知识时相辅相成,其中一个系统的低效会引发另一个系统功能的加强。最新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经验水平较低时更多地依赖陈述性记忆,随着二语学习者经验水平的提高,他们会更多地依赖程序记忆,并且其语言水平提高的几率很大(Ullman 2013)。这一过程由一系列因素决定,如二语者开始学习二语的年龄,接触二语的时间,个体差异尤其是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容量,等等。在这方面,以我国外语学习者为对象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不同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的路径和机理值得我们去研究。 4)二语习得的复杂动态系统研究,这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桂诗春教授就提出外语教学是一个大系统,包含各种各样的参数(桂诗春1994),这一观点受到许国璋先生的认可和赞扬。这一观点是中国学者对二语习得研究学科的思想和理论贡献,需要我们的系统阐发和阐述。而Larsen-Freeman于1997年才提出二语习得中的复杂理论(Complexity Theory in SLA),认为二语习得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自适应系统,二语习得领域的著名期刊Language Learning于2008年编发专刊探讨语言的复杂自适应特征。也有国内学者注意到了二语习得复杂理论,问题是介绍者有之,而实验性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还有目前国际上较新的二语习得中的认知控制及认知负载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等,国内研究者跟踪的步伐较慢,较少有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 5)关于二语习得研究难点问题。首先是问题意识,一项研究要有好的创意和研究设计,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者能够发现问题所在,切中问题要害,精心设计研究框架和程序,从而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需要跨学科多学科的团队合作,随着科学研究的分化和整合双向趋势日益明显,任何科学问题的探讨都需要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尤其是二语习得研究有时会涉及学生、教师及管理人员,学科方面除了语言学,还可能涉及教育学、数学、统计学甚至计算机科学、医学等等,因此,团队合作就尤为必要。其次是研究手段的问题,目前虽有大量运用ERP,fMRI等技术手段的研究,但传统的纸笔实验并未过时,好的设计和研究思路才是一项研究的灵魂所在,我们常常可以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读到运用传统方法做出的高水平研究。最后,是文献的查阅和获取,这涉及对国际学术动态的了解和把握。 蔡金亭(华南理工大学): 我主要谈谈对语言迁移问题的研究。“语言迁移”又称为“跨语言影响”,在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中如影随形,时刻存在。语言迁移研究作为二语习得的核心课题之一,不仅研究内容广泛,而且受到了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的高度重视。 语言迁移研究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富矿,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探索。纵向来看,它跨越四个研究阶段(Jarvis & Pavlenko 2008:4-8)。第一个阶段只把语言迁移看作一个可能影响二语习得、语言使用及其他语言、心理、认知和文化过程的自变量。现在则倾向于把语言迁移看作因变量,不仅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多种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迁移从正向、反向发生的情况,而且提倡运用新方法对新兴话题进行深入挖掘,呼吁新的理论框架。 今后语言迁移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首先,要加深对语言迁移的理解。语言迁移不仅是结果,还是过程;不仅涉及语言层面,还涉及概念层面;不仅有显性的,还有隐性的;不仅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仅是正向的,还可能是反向的。 其次,要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前人对语言迁移提出了不少有启发的观点和假说,但很少有人将其体系化,形成理论框架。张会平、刘永兵(2013,2014)做了大胆尝试,提出了概念迁移理论框架。近来,蔡金亭、李佳(2016)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提出了“语言迁移的多维动态理论框架”。但该框架是否合理,还需要实践检验。 再次,要重视研究方法。针对许多语言迁移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不够严谨的现状,Jarvis(2000,2010)提出了“统一框架”和“基于比较的取向”,已有人将其运用到实证研究之中。近年来,本人受动态系统理论的启发,在批判性吸收上述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母语迁移的比较-归纳方法框架,并将其应用于课题组的系列研究之中。但上述框架只是依赖语言证据,更为科学的研究还应同时分析内省证据和副语言证据,从而形成研究方法的三角论证(trianglism)。但目前做到这一点的研究极少。 第四,要紧扣前沿课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概念迁移(conceptual transfer研究,但须注意它与语言层迁移(linguistic transfer)密切相关,还要用严谨的方法判断概念迁移及其子类——纯概念迁移(concept transfer)和概念化迁移(conceptualization transfer),避免把语言层迁移过度解释为概念迁移。2)反向迁移和双向迁移。3)一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包括其中母语对二语的影响、母语对三语的影响、二语对三语的影响等。4)语言迁移与其他因素的互动,需要考察的因素包括语言水平、跨语言客观异同和主观异同、语言普遍因素、个体差异因素等。5)二语产出和理解中语言迁移的表现和运作机制的异同。 最后,要重视对研究结果的理论解释。可以吸收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结果,从二语产出和理解心理过程角度予以解释(参见Cai 2015)。 张萍(华南师范大学): 纵观《外语教学与研究》近三十年来所刊发文章目录的关键词,从1995年的“话语分析、语言测试理论、词汇研究、文化定型、功能语法、主位推进”,到2005年的“写作、外语教学改革、语法隐喻、语言学史、二语习得、教学信念”,再到2015年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实证对比、语块、句法分析、词汇化、语用特征、语法能力”等,可以看出,三十年来中国二语习得研究有几个变化趋势:一是研究内容从综述、总结式的理论述介扩展到二语习得句法、词汇、语用等诸多层面;二是研究对象从曾经的“仰望”本族语者到“青睐”中国英语学习者;三是研究方法从非实证、偏主观分析大幅推进到量化和质化行为研究。中国虽然是做二语习得研究的大国,也具备各种有利条件,但我们离国际水准、与国际接轨、发国际声音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二语习得研究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一、研究内容。比如词汇研究。王立非、江进林(2012)的统计结果发现,国际二语习得研究近10年来(2000-2009)词汇习得的研究最多(116次),词汇习得也是语言学习者最常问及的话题(Cook & Singleton 2014)。词汇习得中涉及词形与概念的输入加工、不同语境下的词汇习得、母语知识对词义和搭配习得的影响、心理词汇与使用中的词汇接口、英汉双语词库对比等。再比如语言的磨蚀研究,包括汉语和英语的磨蚀,还有语言的加工研究等。有些是热点话题,比如语言与大数据,牵涉到语料库、翻译、网络语言使用等研究;有些是经典话题,没有结论,仍是热点,比如母语迁移、习得年龄等,需要更多深入的探索。 二、研究对象。“二语习得者”在中国习惯上被理解为英语作为二语的中国学习者,是外语界的地盘。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常常叫做“对外汉语学习”,归汉语界研究。我们其实还有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英语作为第二、第三语言。个人觉得,二语、三语者群体日益壮大,英汉两界应联手研究,至少我们可以将汉语二语学习者作为CFL/CSL(Chinese as foreign/second language)学习者一起纳入我们的二语习得研究对象范畴。去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召开的对外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上,蒋楠教授也曾提出这样的建议。“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心理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吸纳了研究汉语的心理学研究者和研究英语二语习得的学者,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融合。两界联手一可以更好地传播母语习得的成果,二可以做两语习得的比较研究,这是双赢的事,我们应该去做。 三、研究方法。二语习得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而成,其研究方法也理应多样,更需三角验证。离线式的语言学本体需要研究,在线式的心理学视角的加工实验研究、厚描写的社会学视角的动态建构、互动等质化研究同样不可或缺。还有将英语作为外语(EFL)和将英语作为世界语(ELF,English as lingua franca)态度的不同,多了一种解读二语习得的视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的地方。 四、研究理论。二语习得是一头巨象,不同视角对它的解读必然产生不同的理论(Van Pattern & Williams 2014),过度依赖单一理论和语言研究必然无法描绘二语习得全景。语言社会化理论、会话分析路径、动态系统理论、身份建构视角等社会文化理论和计算、心理、认知语言学理论将会作为传统认知理论的有力补充,丰富英、汉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解释,其对比研究成果又将增强中国二语研究者的理论建构意识和能力。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这次会议的报告内容,也应该能够看到既有经典话题的研究,也有对新理论的探索,也有各种交叉(研究视角、英汉受试、研究方法等)。希望在今后的二语习得研究中,我们能从各自为营、盲人摸象式的研究过渡到团队作战、多靶位聚焦,全方位、多视角地将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从点慢慢连成片,希望将来在勾勒出二语习得这头大象的全貌中有我们中国学者的贡献。 曾涛(湖南大学): 我起初从事母语习得研究,现在也兼做一些心理语言学研究。现在跟大家分享几点研究体会: 1)语言习得研究是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母语习得、二语习得,还是双语习得、方言习得等研究都是为了揭示语言普遍性规则,为了探求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为了客观描述和科学解释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发展过程,因此学科之间相互交流与借鉴非常重要。国内母语研究的群体涉猎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相关学科的紧密支撑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母语习得一直是理论语言学的支柱学科之一,很多语言学的理论问题都需要母语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证据。只要有好的选题,好的研究范式,传统的母语习得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2)语言习得要突破语言本身的限制,不管是一语、二语还是对外汉语学习,都需要在更大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目前,国内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英语为二语的研究中,小语种、对外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些研究都还没有真正融入二语习得这一统一范畴。此外,当前的习得研究大都没有考虑社会语言环境的复杂性,儿童所处的语言环境往往是双语或双方言的,而二语学习者也同样如此。因此,今后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突破语言本身的局限,既保持各自研究领域的目标与特点,又把母语习得、外语学习、对外汉语、方言习得等纳入统一理论框架,从而真正推动我国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 3)语言习得研究越来越借助心理学与神经认知科学领域的各种技术,比如ERP(事件相关电位)、核磁共振成像、近红外光谱等等。新技术的学习固然重要,但研究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技术终归只是技术,并不是所有习得研究非得要用某些技术手段,任何时候好的研究问题、好的研究视角更为重要。当然,研究者也不必排斥新方法、新范式,因为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可能会使旧的研究焕发新的活力,促使研究者发现新的问题,拓宽研究思路,因此应该以更开放更积极的心态对待新技术。 常辉(上海交通大学): 二语习得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初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发展十分迅速,跨学科特点也越发鲜明,有语言学视角、心理学视角、社会文化视角、教育学视角等,每个视角都有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例如,目前基于形式语言学的二语习得研究都在探讨接口知识的习得与加工,把以前的普遍语法可及性研究向纵深方向进行了拓展,并与心理学结合。心理学视角的二语习得聚焦在二语习得与加工的心理认知和神经认知机制上,通过眼动仪、ERP和fMRI等先进设备探讨一些艰深的前沿问题,从而探索人类大脑的语言运作机制。这些问题包括:1)二语词汇和一语词汇是否存储在双语者大脑的同一区域,双语者对它们的提取是否通过同一个机制?2)二语习得者对规则词和不规则词的存储和提取是通过单一机制还是双机制完成的?3)二语加工机制与一语加工机制是存在质的差异(即加工机制不同)还是量的差异(即加工机制相同,而加工水平或者说加工自动化程度不同)?二语习得的普遍失败是否是由二语加工机制与一语加工机制存在质的差异造成的? 作为中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者,我们除了紧跟国际潮流做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的研究外,还需要注意研究的本土化,并为推动汉语习得研究和建设语言习得理论做出贡献。这些本土化的研究不仅是国家需要的,而且往往也是语言习得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例如,我们需要研究开设学术英语课程学生所需的英语水平,翻转课堂、慕课和微课应用于教学的效果,学习英语的起始年龄对英语水平的影响,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微观研究,可以为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我们也需要更多地关注中小学的英语学习问题,为中小学英语教学提供更多的指导。我们还需要加大对留学生汉语习得和中国儿童汉语习得的研究,前者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汉语的世界地位和传播中国文化,后者可以让家长更加清楚孩子的汉语发展,还可以用于中国儿童语言障碍的诊断和康复。同时,这两方面的研究还可以推动语言习得理论建设,因为目前的语言习得理论大都是基于英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提出的,很多不适合汉语(Yuan 2010,2013,2015;Zhao 2011),通过汉语习得研究,我们可以修补,甚至推翻目前的一些语言习得理论,提出新的语言习得理论。总之,世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汉语习得研究。 最后,我非常赞同袁博平教授的观点,目前的二语习得研究都在向纵深方向发展,经典的研究问题未必不是热点,但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更加精细地研究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