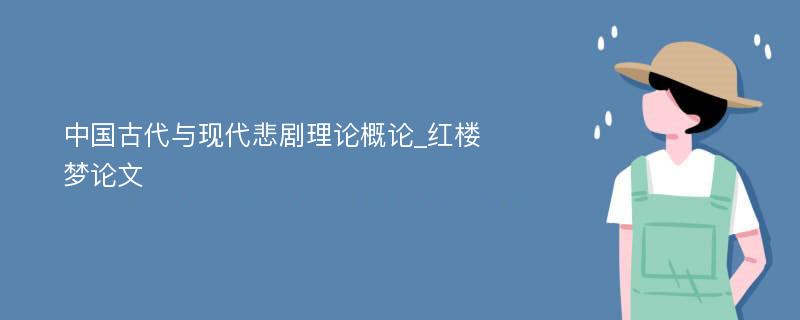
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近代论文,悲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古代戏剧学文献里,没有出现过“悲剧”这个词,但这并不表明我国古代没有悲剧,也不表明古代戏剧学家对于悲剧没有认识。只要从实质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我国古代的悲剧理论自有其特色,也自有其价值,值得认真进行总结。至于近代王国维论悲剧,则带有中西文化相互撞击和融汇的特点,但其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需要进行探讨。
一、凄——悲剧的动人力量
以“凄”来概括悲感,古已有之。《楚辞·远游》:“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文心雕龙·诔碑》:“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若可伤。”这里所说的“凄”,都是一种悲痛、悲伤的感情。人们常说“凄恻动人”,文学艺术作品如能给人以“凄恻”之感,就自然能够“动人”。
在戏剧领域里把“凄”与“动人”联系起来的,当首推元末的高则诚。他在《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的《水调歌头》中说: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
在同一出的《沁园春》中说:
堪悲。赵女支持,剪下香云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筑成坟墓;琵琶写怨,迳往京畿。孝矣伯喈,贤哉牛氏,书馆相逢最惨凄。
高则诚这里所说的“乐人”、“动人”,实际上涉及喜剧、悲剧的不同审美效应。在高则诚看来,悲剧的艺术品位,与喜剧相比,是要高出一筹的。至于“堪悲”、“惨凄”,便是他对悲剧的“动人”力量的具体说明。
明中叶的王世贞进一步阐发了高则诚的意见。他在《曲藻》中说《拜月亭》不如《琵琶记》,其原因之一是“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反过来说,歌演时能“使人堕泪”,正是《琵琶记》的长处之一。《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一的《前贤评语》中选录了王世贞的一些评语,重点也是探讨《琵琶记》的悲剧效果问题。如《南浦嘱别》一出,赵五娘舍不得蔡伯喈离去,所唱〔五供养〕曲中有:“有孩儿也枉然,你爹娘倒教别人看管。”王世贞评曰:“此语参人情按世态,淋漓呜咽,读之一字一泪,却乃一泪一珠。”《宦邸忧思》一出,蔡伯喈思念父母和妻子,所唱〔雁鱼锦〕曲中有:“几回梦里,忽闻鸡唱。忙惊问,错呼旧妇,同候寝堂上。”王世贞评曰:“这般恍惚心绪,似梦似醒,若有若无,舌底模糊道不出处,却写得朗朗凄凄,真乃笔端有舌。”《乞丐寻夫》一出,赵五娘描画公婆遗容,所唱〔三仙桥〕曲中有:“纵认不得是蔡伯喈昔日的爹娘,须认得是赵五娘近日的姑舅。”王世贞评曰:“苦口苦心,凭三寸笔尖写来,自足碎人心肠。”《两贤相遘》一出,写赵五娘上京寻夫,与牛氏邂逅的情景,王世贞评曰:“幻设妇女之态,描写二贤媛心口,真假假真,立谈间而涕泣感动,遂成千载之奇。”这几处悲剧情境的设置,有的是因为亲人之间的生离,如《南浦嘱别》:有的是因为亲人之间的死别,如《乞丐寻夫》;有的是因为思念亲人的愿望与这种愿望不能得到满足的矛盾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抑和痛苦,如《宦邸忧思》;有的是因为一个人的痛苦遭遇及其在另一个人的心中所激起的深切同情,如《两贤相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对《蔡母嗟儿》一出的评语:“《琵琶记》当以《蔡母嗟儿》一篇,为霓裳第一拍。看他语语刺心,言言动骨,绝不闲散一字。半入雍门之琴,半入渐离之筑,凄凄楚楚,铿鍧镗鎝,庶几中声起雅。 ”这里所说的“雍门之琴”的故事见汉桓谭《新论·琴道》。雍门周给孟尝君弹琴,他先和孟尝君拉家常,谈到孟尝君抗秦伐楚,终招祸患,谈到人生无常,年华易逝,直谈得“孟尝君喟然太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门周抓住这一时机,“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叩角羽,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渐离之筑”的故事见《战国策·燕策》。荆轲将入秦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这两个故事都具有悲剧色彩,这说明我国古代悲剧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对于这一点,古代的戏剧学家们是有所认识的。
在王世贞前后,也有不少学者,从“凄”的角度,来认识悲剧的动人力量。前如陆容《菽园杂记》:“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介优者,……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后如吕天成《曲品》评张凤翼《祝发记》:“境趣凄楚逼真。”清代如朱彝尊《酬洪升》:“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这是说《长生殿》以“凄绝”为特色。秦湘业《梅花梦题词》:“漫将苦调谱哀弦,雨妒风欺萼绿仙。自古还魂本无术,从今读曲益凄然。”这是说张道《梅花梦》读之令人“凄然”。杨恩寿《词余丛话》则说吴伟业《通天台》“凄惋”。至梁启超《小说丛话》,也说《桃花扇》是“一部极凄惨、极哀艳、极忙乱之书”,“一部哭声泪痕之书”。可见,悲剧应当具有令人生“凄”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二、怨——悲剧的情感冲突
与一些戏剧学家从“凄”的角度来探讨悲剧的动人力量同时,也有一些戏剧学家侧重从“怨”的角度,来探讨悲剧的情感冲突。
《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一的《前贤评语》中选录了徐渭的评语:“《琵琶》一书,纯是写怨。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儿子,赵氏怨夫婿,牛氏怨严亲,伯喈怨试、怨婚、怨及第,殆极乎怨之致矣。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琵琶》有焉!”所有这些“怨”归结到一点,就是蔡伯喈的应试和再婚,这就是《书馆悲逢》一出中,蔡伯喈所唱的两支〔解三酲〕中所说的:“我只为其中自有黄金屋,反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我只为其中有女颜如玉,反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不管高则诚的主观愿望如何,从剧本所表现的内容来看,对科举、对丞相、甚至对皇帝的“怨”确实是相当突出的。所以陈继儒评点《琵琶记》,在总评中引述汤显祖的话:“从头到尾,无一句快活话。读一篇《琵琶记》,胜读一部《离骚经》。”李贽也看出《琵琶记》中有“怨”,只是他认为怨得还不深,所以他说:“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焚书·杂说》)
综合以上意见可以看出,古代戏剧学家们认为,悲剧的渊源有二:一是音乐方面的“怨乐”和“哀乐”,如雍门之琴、渐离之筑;二是文学方面的《诗》和《骚》,因为《诗》讲“怨”,《骚》也讲“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离骚》的“怨”。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李白《古风二首》其一也说:“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很显然,《离骚》可以称为一首“怨诗”。与此相仿,明末的陈洪绶在评点《娇红记》的时候,把这部悲剧也称为“一部怨谱”。他在评第五十出《仙圆》时说:“泪山血海,到此滴滴归源,昔人谓诗人善怨,此书真古今一部怨谱也。”
对于《娇红记》这部“怨谱”应当有一个完整的理解。正如《离骚》这首“怨诗”既包含“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又包含九死未悔的执着一样,《娇红记》这部“怨谱”中王娇娘、申纯这两个悲剧人物的性格中也包括着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二人“自花前相见,既订姻盟,中间几遭间阻,抱怨而终”(第五十出《仙圆》),另一方面二人对爱情生死不渝,早就立下并始终坚持了共同的誓愿:“今生枕边,来生石边,做的个鸳鸯同冢心欢忭。”(第三十一出《要盟》)对于这后面一点,《娇红记》作者孟称舜是更为强调的,他在《题词》中说:
天下义夫节妇所为,至死而不悔者,岂以是为理所当然而为之邪?笃于其性,发于其情,无意于世之称之,并有不知非哭之为非哭者而然焉。自昔忠臣孝子,世不恒有,而义夫节妇时有之。即义夫犹不多见,而所称节妇则十室之邑必有之。何者?性情所钟,莫深于男女,而女子之情,则更无藉诗书理义之文以讽喻之,而不自知其所至,故所至者若此也。传中所载王娇、申生事,殆有类狂童、淫女所为,而予题之节义,以两人皆从一而终,至于没身而不悔者也。两人始若不正,卒归于正,亦犹孝已之孝,尾生之信,豫让之烈。揆诸理义之文,不必尽合,然而圣人均有取焉。
孟称舜认为,青年男女中有很多情深者,尤其是青年女子,她们的感情更常常自然而然地达到深挚的程度,而当她们的这种感情与现实世界产生矛盾冲突并且处于不可调和的态势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这里孟称舜用以比较的孝己、尾生、豫让三人,都是悲剧性人物。孝己,传说为殷高宗武丁之子,以孝行著,因遭后母谗言,被放逐而死。《庄子·外物》:“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尾生,为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男子。《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豫让为春秋末晋国智伯门客,智伯为赵襄子所灭,豫让自残以谋刺襄子,最终被执自杀。这三人都是在和客观现实的冲突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不惜以身相殉。在孟称舜看来,王娇娘、申纯二人的悲剧性格,与孝己、尾生、豫让三人正相一致。这也可说明,“怨”不仅反映了与现实的矛盾,也包含着对现实的抗争。
三、悲——悲剧的哲理思考
还有一些戏剧家更进一步,对悲剧所包含的哲理蕴进行了思考。孟称舜的朋友卓人月(1606—1636)在《新西厢序》中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阐述。
第一,悲剧最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定局”。卓人月说:“天下欢之日短而悲之日长,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长,此定局也。且也欢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后。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也!”卓人月认为,就现实生活的全体而言,总是悲比欢占优势,死比生占优势,而且最后的归宿必然是悲,是死。因此他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是违背生活的“定局”的,只有悲剧才能准确地反映这一“定局”。这种“忧生之嗟”,古已有之,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到辛弃疾的“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莫不如此,只不过卓人月把它发挥到极致,并且由于他身处明末衰世,因而其感受特别凄惋而已。
第二,悲剧最能体现“风世”的目标。卓人月说:“夫剧以风世,风莫大乎使人超然于悲欢而泊然于生死。生与欢,天之所以鸩人也;悲与死,天之所以玉人也。第如世之所演,当悲而犹不忘欢,处死而犹不忘生,是悲与死亦不足以玉人矣,又何风焉?又何风焉?”在卓人月看来,所谓“风世”,最重要的是要使人对于悲欢、死生有一种超脱的态度。不仅身处逆境,要能够正视那现实的悲与死;就是身处顺境,也不能因留恋欢与生而忘记了那作为根本结局的悲与死。最可悲的,是身处逆境,面对悲与死而不自知,却还要去留恋那虚幻的欢与生。这在卓人月看来,无异于饮鸩止渴。而悲剧,就是消除毒害、唤醒世人的一剂良药,它对于人生是特别有益的。
第三,悲剧最能“脱传奇之窠臼”。这里的“窠臼”,指的就是大团圆的结局。卓人月说:“崔莺莺之事以悲终,霍小玉之事以死终。小说中如此者不可胜计,乃何以王实甫、汤若士之慧业而犹不能脱传奇之窠臼耶?余读其传而慨然动世外之想,读其剧而靡焉兴俗内之怀,其为风与否,可知也。”他指出,唐人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都是悲剧结局,读后能使人产生超脱之想;而据此改编的《西厢记》、《紫钗记》都是大团圆结局,因此便不能起到“风世”的作用。二者相比,他对《西厢记》更不满意:“《紫钗记》犹与传合,其不合者止复苏一段耳,然犹存其意。《西厢》全不合传。若王实甫所作,犹存其意;至关汉卿续之,则本意全失矣。”他认为《西厢记》第五本是关汉卿所作,而他最不满意的正是第五本的大团圆结局。他之所以要创作《新西厢记》,原因正在于此。今天我们虽然不能见到卓人月创作的《新西厢》剧本,但它是以悲剧结局,却是没有疑问的。
卓人月是一位李贺式的文学奇才。他与李贺一样,也是早夭的。综观卓人月一生,有两大不幸:一是母久病而父久不归,“留母与子相拊循,如处长晦久失晨”〔1〕。其中原因如何,已不可明了; 二是屡挫科场,未遇于时,“六战文场毛羽摧,曾无一个解怜才”〔2〕。 因此其“生平遭遇,惟苦无乐”〔3〕。这样的人生经历, 再加上他的深邃思考,便铸成了他的悲剧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就人生观而言,不免有消极的一面;就艺术观而言,在当时却足以震聋发聩。曾经有学者断言,中国人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感受不深,所以中国没有悲剧,在中国,戏剧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卓人月的存在,恐怕要为这一论断提供一个例外了。
四、苦——悲剧的永久回味
说到“苦”,自然会联想起《琵琶记》第二十一出《糟糠自厌》中赵五娘听唱的〔孝顺歌〕:“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的确,悲剧有一种令人咀嚼不尽的苦味,这一点明人多已言之。如吕天成《曲品》评《窦娥冤》:“境最苦”,评《琵琶记》:“苦乐相错,具见体裁”,评《教子记》:“真情苦境,亦尽可观”,评《分钱记》:“苦境可玩”,评《合衫记》:“苦楚境界”,评《双珠记》:“情节极苦,串合最巧,观之惨然”。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紫绶记》:“描写苦状,阅之令人酸楚”,评《双杯记》:“直传苦境”,评《寻亲记》:“直写苦境,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到了清人,更进一步集中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苦戏”、“苦生”、“苦旦”等一系列概念。
就今天见到的材料看,最早提出“苦戏”这一概念的是由明入清的杜浚(1611—1687)。他的《变雅堂诗集》中有一首《看苦戏》的诗:
何代传歌谱,今宵误酒杯。
心伤情理绝,事急鬼神来。
蜡泪宁知苦,鸡声莫漫催。
吾生不如戏,垂老未甘回。
同时的诗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1615—1673)的《定山堂诗集》中有一首和诗,题为《观剧偶感同于皇(杜浚字)作》:
乾坤同白首,涕泪且深杯。
欢入笙箫变,晴看雨雪来。
盘涡天一折,裂石鼓三催。
痛久疑忘味,心伤谏果回。
两人所谈的都是“苦戏”。杜诗说,剧中人物悲苦的感情心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黯然神伤;戏剧演到紧张之处,气氛阴惨,有如鬼神叠现。龚诗则形容戏剧情境由欢突变为悲,仿佛晴天陡降雨雪,又仿佛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得天柱折,地维绝。末句更强调悲剧不仅看的过程中使人惊心动魄,更难得的是看后仍使人感到如谏果(橄榄)一般回味无穷。可以看出,二人对于悲剧的艺术感觉都是相当准确的。
和杜浚、龚鼎孳同时的宋琬(1614—1673)创作的杂剧《祭皋陶》是一个悲剧。此剧据《后汉书·范滂传》,写东汉末年名士范滂(字孟博)遭陷害入狱,狱吏按例要囚徒拜祭狱神皋陶,范滂拒绝拜祭云:“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在他的带动下,全体被捕名士一致罢祭。按宋琬任浙江按察使时,曾因受人诬告而被捕入京,系狱三年,他作此剧可谓有感而发。当时人杜陵睿水生曾作《祭皋陶弁语》云:
……余家藏书不备,尝就余所见,集成《史泣》、《史笑》二书。若以传奇家例论,则《史笑》多净丑,《史泣》多苦生。其间尤痛心酸鼻,不能已已者,莫如东京之范孟博,南渡之岳鹏举。鹏举之事,既已广被乐府,独恨孟博未遇奇笔。一日,客有授余《祭皋陶》四出者,余惊喜读之,大约以辛辣之才,构义激之调,呼天击地,涕泗横流,而光焰万丈,未尝少减。作者其有忧患乎?其有忧而无患乎?夫无孟博之忧患,决不能形容孟博之真气,使千载之上,宛在目前。至于如此也,亦足见杂剧之功伟矣。
《史泣》、《史笑》二书,我们已无从得见。但可以推测,《史泣》所记载的,多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和事件;《史笑》所记载的,多为历史上的喜剧人物和事件。杜陵睿水生在这里以《史泣》、《史笑》二书比拟戏剧中的悲剧与喜剧,是有道理的,因为悲剧的确是多泣,而喜剧的确是多笑。他还指出,悲剧的男主角多为“苦生”。他认为历史上有两位人物,最适宜塑造为这样的“苦生”。一位是宋代的岳飞,其悲剧形象已先后见于《精忠记》、《精忠旗》等剧。另一位是汉代的范滂,其悲剧形象还是首见于这部《祭皋陶》杂剧。因此杜陵睿水生认为《祭皋陶》的创作是很有价值的。他还指出,要把“苦生”的形象塑造成功,首先必须善于体察、善于表现其忧患意识。这一见解,也是值得重视的。
五、悲剧的近代阐释
从十八世纪起,中国的悲剧开始引起外国人士的注意。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汉学家普雷马雷(汉名马约瑟)翻译的《赵氏孤儿:中国悲剧》,收入迪阿尔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一七三五年在巴黎出版。这一剧本是根据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杂剧翻译的。 从目前接触到的材料看, 这是西方人用“悲剧”(法文tragédie,意同英文tragedy)来称呼中国“苦戏”的首例。其后几十年内,《中华帝国全志》又陆续出版了英文版、德文版、俄文版,而《赵氏孤儿:中国悲剧》亦随之传播更广。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在热河行宫观看了为皇帝祝寿的演出。他所写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记叙道:
戏场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
这是外国人士根据自己的观剧感受提出中国戏剧中有“悲剧”的较早一例。
稍后,英国汉学家戴维斯(汉名德庇时)将马致远的《汉宫秋》译成英文,题为《汉宫秋:中国悲剧》,于一八二九年由伦敦东方翻译基金会出版。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外国人士开始注目于中国的悲剧,也有中国学者尝试引进西方的观念,用以研究中国的悲剧。王国维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
王国维在光绪三十年(1904)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主要依据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学说,阐发了以下悲剧观:
第一,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的结合。人的知识与实践这两个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只有“美术”(按: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因其非“实物”,故能于人“无利害之关系”,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人对它也就“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种“艺术之美”,因其能“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故能减轻人类的苦痛,因而也就优于“自然之美”。
这种“艺术之美”又可以分为优美、壮美两种。何谓优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何谓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则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无论“优美”还是“壮美”,都能“使吾人离生活之欲”,因此都是“美”。在文艺作品中还有一种“眩惑”,其作用能使人“复归于生活之欲”,因此“眩惑”与“艺术之美”不能并立,非但不能疗救人世的苦痛,还会使其加重。
用以上标准来衡量,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一绝大著作”。因为“《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特别是因为《红楼梦》所写的解脱,不是“非常之人”的解脱,而是“通常之人”的解脱,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故其特点为“悲感的也,壮美的也”,就是说,能充分体现“艺术之美”的。
第二,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由于剧中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这三种悲剧中,第三种感人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第一、二两种。因为人们在面对第一、二两种悲剧的时候,“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就是说,这两种悲剧,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还是可以逃脱的。第三种悲剧则不然,“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所固有”。就是说,这种悲剧是必然性的,不可逃脱的。因此当人们面对第三种悲剧的时候,“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按照以上的标准,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属于第三种悲剧。他就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分析道:“贾母爱宝钗之婉\,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宝玉之病; 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在宝玉、黛玉爱情毁灭的悲剧中,有关的每个人的行动都有其确切不移的理由,据此,王国维认为“《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又谓“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壮美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可见在王国维看来,“艺术之美”中的“壮美”常常是与悲剧、特别是与第三种悲剧相联系的。
第三,悲剧的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是统一的。王国维首先引亚里士多德之说,“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按:今通译为‘净化’)”。悲剧的这一价值,王国维称之为“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王国维又谓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极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悲剧的这一价值,王国维称之为“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王国维认为,对于悲剧来说,“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是使人向善;“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是言其美;“示人生之真相”,是言其真。可见在王国维看来,悲剧是最能体现真、善、美的完满结合的。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戏剧中悲剧的评价,就是依据以上的悲剧理论,并且常常是在与《红楼梦》的参照中进行的。同样是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王国维这里所批评的,就是所谓“大团圆”结局。他认为《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都是典型的“大团圆”结局。又说:“《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通过以上的比较,他得出结论说:“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他还进一步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虽同具厌世解脱之精神,但程度又大有不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知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因此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小说、戏剧中,只有“《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戏剧中是没有真正的悲剧的。
王国维的这种看法,在他对元杂剧进行系统研究之后,有所补充与修正。
在一九○八年所著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指出:“白仁甫《秋夜梧桐雨》,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
在一九一○年所著的《录曲余谈》中,王国维又指出:“余于元曲中,得三大杰作:马致远之《汉宫秋》,白仁甫之《梧桐雨》,郑德辉之《倩女离魂》是也。马之雄劲,白之悲壮,郑之幽艳,可谓千古绝品。”
王国维两次提到白朴的《梧桐雨》,均以“悲壮”评其特色,则心目中以其为悲剧无疑。
在一九一二年所著的《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更进一步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王国维此处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是片面的,但他对元杂剧中悲剧的分析却极有见地。他在这里提出元杂剧中悲剧的特点有两条:第一条是屏弃了“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如《汉宫秋》中的王昭君自投黑河而死,《梧桐雨》中的唐明皇、杨贵妃也没有在天宫重圆,《西蜀梦》更是关、张双双死难,刘备也痛不欲生。第二条是悲剧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如窦娥甘愿替婆婆认罪,韩厥、公孙杵臼为救赵氏孤儿甘愿献出生命,程婴则甘愿献出亲生骨肉,等等。这后一条实际上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因此是深得悲剧之精神的。
由上述可见,王国维对于中国古代戏剧中悲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并且是逐步接近其本质的。
注释:
〔1〕卓人月《蕊渊集》卷四《腊月二十四日寿母篇》。
〔2〕徐士俊《雁楼集》卷二十二《哭卓珂月》。 按珂月为卓人月字。
〔3〕《蕊渊集》卷一《哭赋》眉评。 以上三条均转引自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中之《卓人月:一位文学奇才的生平及其与〈小青传〉之关系》。
〔4〕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见《坟》。
标签:红楼梦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桃花扇论文; 西厢记论文; 读书论文; 戏剧论文; 王国维论文; 梧桐雨论文; 汉宫秋论文; 琵琶记论文; 娇红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