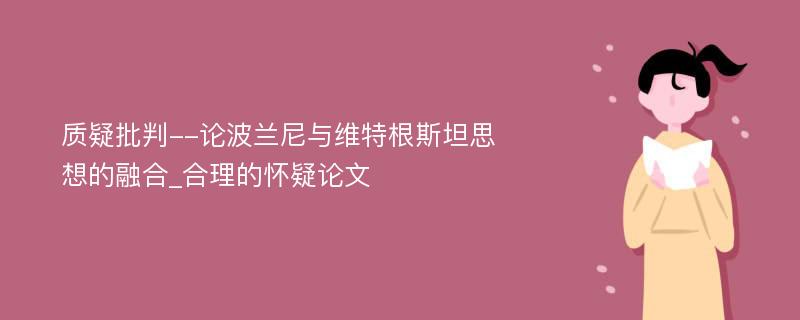
怀疑之批判——论波兰尼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会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波兰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兰尼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倾向是颂扬批判理性而贬抑我们认识中的非批判因素。波兰尼用“批判哲学”一词来概括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把笛卡尔、休谟、康德、密尔、罗素等人看做是批判哲学的代表人物。波兰尼充分肯定了批判哲学的历史功绩,但他认为,批判哲学一味地强调批判理性,而看不到非批判因素对于形成和持有知识的积极作用,在理论上未免失之偏颇。为了克服批判哲学的不足,波兰尼提出了“后批判哲学”的课题,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之一。
怀疑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机能。近代批判哲学极力推崇怀疑,鼓吹普遍怀疑原则。波兰尼在反思批判哲学的过程中,洞察到了普遍怀疑原则的悖谬之处,进而对怀疑这种认知机能作了深入的认识论分析,试图阐明其本性。
与此相关,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实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那就是,在怀疑这个论题上,波兰尼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存在着某种思想的会聚(convergence)。有意思的是,这种会聚不仅表现为两人的思想颇多可相互发明之处,而且表现为两人的相关思想提出的时间也相当接近。维特根斯坦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半时间中(1949-1951年),通过对摩尔在《为常识辩护》及《外部世界的证明》中提出的一些命题的讨论,阐发他对知识和确定性的看法,其中包含了他对怀疑问题的深刻洞见。后来出版的《论确定性》一书(1969年),集中反映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这一侧面。(cf.Wittgenstein)与维特根斯坦相比,波兰尼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开始得要早一些,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比较集中的是在他1947年接受了阿伯丁大学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之后。1951年,波兰尼作了第一个系列的吉福德讲演,该系列10个讲演的核心就是怀疑和信念的关系问题。(cf.Scott and Moleski,p.218)次年(1952年)他作了第二个系列的吉福德讲座。《个人知识》一书(1958年)就是在这两个系列讲座的基础上写成的。
本文试图阐明波兰尼的“怀疑之批判”(the critique of doubt)的主旨,彰显其洞见,揭示其盲点,并辅之以对维特根斯坦相关思想的讨论。笔者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对怀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普遍怀疑原则的悖谬本性
最能体现批判哲学之精神的是普遍怀疑原则。自从笛卡尔提出普遍怀疑的口号以来,休谟、康德、密尔、罗素等都主张,要避免谬误、确立真理,必须诉诸怀疑。(Polanyi,1958,p.269)问题是,普遍怀疑原则能否成立?
后批判哲学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普遍怀疑原则。波兰尼认为,只要把普遍怀疑原则的逻辑贯彻到底,就能看清其悖谬本性。在《个人知识》中,波兰尼考察了人类意识中的两种颇具典范意义的情形,即知觉和语言。波兰尼认为,在我们对事物的知觉中,包含着关于事物本性的信念。为使我们的基本知觉(比如视知觉)能够正常地发挥功能,我们必须遵照“一个过程,该过程体现了整个意蕴体系,该体系是我必须无涉批判地(a-critically)①加以承诺的”。(Polanyi,1958,p.296)关于语言,波兰尼说,“言语只能无涉批判地获得,在某种特定语言中的言语实践,总是接受了该语言所设定的关于宇宙的某种特定理论。”(ibid,p.295)因此,如果我们把普遍怀疑原则贯彻到底,拒斥一切未经证明的信念,就意味着要放弃迄今所接受的所有言述体系和所有起作用的知觉,结果必然是一种虚构的“纯洁心灵”(virgin mind),其基本特征是麻木(stupor)、低能(imbecility)。
在此,我们看到了普遍怀疑原则的吊诡之处:人们倡导普遍怀疑原则的本意是追求真理,但是按照该原则自身的逻辑,又会导致麻木和低能。显然,这不是普遍怀疑原则的倡导者所期待的,但它却是该原则所必然蕴涵的。简言之,普遍怀疑原则由于其自身的逻辑会导致荒谬的结论。波兰尼总结道:“我们可以不断减少我们有意识接受的东西,以至于零,使我们处于麻木的状态。任何给定范围的意识看来都包含了同样范围的无涉批判地接受的信念。所以,全盘怀疑的纲领崩溃了,它的失败昭示了所有合理性的信托根源。”(ibid,pp.296-297)这段话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论证的两方面的理论意蕴:否定地说,它瓦解了普遍(全盘)怀疑原则;肯定地说,它揭示了任何意识的信念内容和所有合理性的信托根源(详下文)。
对怀疑的考察也是《论确定性》的一个重要主题。维特根斯坦批判的矛头所向是“错误的怀疑图景”(Wittgenstein,§249)。维特根斯坦所谓“错误的怀疑图景”是指“无尽的怀疑”(ibid,§625),或者“怀疑一切的怀疑”(ibid,§450)。不难看出,这就是波兰尼所批判的普遍怀疑(或全盘怀疑)原则;两人质疑的是同一个对象。
众所周知,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突出风格是注重实例导向的分析(case-oriented analysis)。如上所述,波兰尼认为,普遍怀疑原则按其自身的逻辑会导致麻木、低能这样一种荒谬的结局。在揭示错误的怀疑图景的荒谬性上,维特根斯坦和波兰尼颇有类似之处,但是,由于他对实例的敏感,他比波兰尼更细致入微地刻画了错误的怀疑图景的各种缺陷。这些缺陷的程度各不相同。以下,笔者将按严重程度(由轻到重)将各种缺陷作一番排列,旨在表明:在《论确定性》中存在着一个对错误的怀疑图景的细致的逐级主义的批判(gradualistic critique)。这一批判能够强有力地支持波兰尼对普遍怀疑原则的批判。
维特根斯坦指出,在有些情况下,毫无限制的怀疑是空洞的、毫无价值的。试想一个学生怀疑历史的真实性,甚至怀疑地球在一百年前是否存在。对此,维特根斯坦的评论是:“在我看来,这种怀疑似乎是空洞的。”(ibid,§312)再看另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不可能怀疑我没有登上过月球。我怎么能够怀疑这一点?首先,我上过月球的假设是毫无价值的。从它不能推导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用它来加以说明。它和我的生活毫无联系。”(ibid,§117)
在有些情况下,怀疑是没有意义的。“怀疑会逐渐丧失意义”(ibid,§56)。试想如下教和学的情景:“学生不听任何解释,他不停地用怀疑来打断,比方说,怀疑事物的存在,怀疑语词的意义,等等。教师说:‘不要打断我,按我告诉你的去做。至此,你的怀疑没有任何意义。’”(ibid,§310)
更严重的是,毫无限制的怀疑会导致一片混乱,会瓦解我们理智生活的基础。维特根斯坦说,“什么东西能够使我怀疑在这里的这个人是我已认识多年的N.N.呢?在这里,怀疑看来会裹胁一切并使之陷于混乱之中。”(Wittgenstein,§613)“也就是说:如果我在所有方面都遭到否定,并且被告知这个人的名字不像我一直所知的那样(在此我有意用‘知道’这个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丧失了作判断的基础。”(ibid,§614)维特根斯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怀疑会导致愚蠢(half-wittedness)。“如果有人对我说他怀疑他是否有一个身体,我会把他当作一个傻子(a halfwit)。”(ibid,§257)“‘在我刚吃过中饭这一事实上,我不可能犯错误。’因为,如果我对某人说‘我刚吃过’,他会觉得我在撒谎,或者我暂时犯傻了,但他不会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此,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的假设根本没有意义。”(ibid,§659)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看法,即毫无限制的怀疑有时意味着愚蠢,接近于波兰尼对所谓“纯洁心灵”的描述:对我们在知觉和语言中无涉批判地接受的东西加以怀疑,将导致麻木和低能。
但是,维特根斯坦对普遍怀疑原则的批判并不止于此,他认为错误的怀疑图景还有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他看来,在有些情况下,怀疑不仅意味着愚蠢,还意味着非理性,甚至更糟,是一个精神问题。维特根斯坦说,“理性的人不会有某些怀疑。”(ibid,§220)“当我们说,我们知道如此这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任何理性的人处在我们的位置上也会知道它,而怀疑它是非理性的。因此,摩尔也不会仅仅说,他知道他如何如何,任何有理性的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也同样会知道这个事情。”(ibid,§325)怀疑摩尔在《外部世界的证明》和《为常识辩护》中所声称知道的那些自明之理,被看做是非理性的,因为只有精神有毛病的人才会怀疑这类事情。“如果有一天我的朋友想象他在某某地方已经生活了很久,等等,我不会把这称作是一个错误,而会称作是一个精神困扰,也许只是暂时的。”(ibid,§71)“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所有的计算都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依赖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他的理由是错误总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他疯了。”(ibid,§217)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我们可以说,如果某人试图贯彻普遍怀疑原则,那么,他不仅会陷入愚蠢,而且会濒于疯狂。显然,后者越出了认识论的范畴,已成为病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了。
错误的怀疑图景的悖谬性质最明显地体现为如下事实,即它会取消怀疑本身。维特根斯坦对普遍怀疑原则的自毁特征(self-destructive character)作了十分明确的表述:“如果你试图怀疑一切,那么你将不能怀疑任何东西。”(ibid,§115)“怀疑一切的怀疑将不成其为怀疑。”(ibid,§450)“无尽的怀疑甚至不是一个怀疑。”(ibid,§625)
以上,笔者试图将维特根斯坦对错误的怀疑图景的批判,诠释为一个逐级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批判不仅能够呼应波兰尼对普遍怀疑原则的批判,而且能够强化、深化、细化这种批判。
二、怀疑的信托品格
波兰尼和维特根斯坦都区分了合理的怀疑和不合理的怀疑。普遍(全盘)怀疑作为一种错误的怀疑图景,属于不合理的怀疑的范畴。那么,什么是合理的怀疑?作为一种认知机能,怀疑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怀疑作为一种认知机能,和信念相对峙。近代批判哲学对于怀疑和信念这两种认知机能的抑扬取舍,态度鲜明:“在哲学的整个批判时期,一直被视若当然的是:对未经证明的信念之接受是通向暗蔽的大道,而真理是经由怀疑的羊肠小道而被逼近的。”(Polanyi,1958,p.269)“这里存在着一种断裂,由此,批判的心灵否定了它的两种机能之一而完全依赖于剩下的那一种机能。信念的名声被彻底败坏,除了某些特许的机会(比如人们还是被允许持有和申明各种宗教信仰),现代人丧失了把任何明确陈述作为他自己的信念来加以接受的能力。”(ibid,p.266)一味地推崇怀疑,和一味地贬抑信念,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普遍怀疑原则是批判哲学一味地贬抑信念的理智倾向的必然结果。贯彻普遍怀疑原则的思想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刨去我们思想意识中的信念内容的过程。
然而,普遍怀疑原则的悖谬本性提示我们,近代批判哲学对怀疑的本性、对于怀疑和信念的关系的认识,远未达至正见,与事实本身还相距甚远。在此,值得追问的是:在与信念隔绝的情况下,怀疑是否可能?
如上所述,波兰尼认为,普遍怀疑原则的崩溃昭示了所有合理性的信托根源,把我们的思想引向了信托纲领。所谓信托纲领,简单地说就是以信念为基础来理解人类经验。按照信托纲领,任何意识都有信念内容,所有合理性都有信托根源,怀疑作为人类的一种认知机能当然也不能例外。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深刻地揭示怀疑的信托内容,阐明了怀疑的信托品格(the fiduciary character of doubt)。在波兰尼那里,信托纲领贯彻于认识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乃至社会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蕴。但是,考虑到近代批判哲学一味地推崇怀疑、贬抑信念的思想背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揭示怀疑的信念内容,阐明怀疑的信托品格,对于后批判哲学来说是一项最关键、最核心的工作。
波兰尼在不同层次上论证了怀疑的信托品格。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对任何明确陈述的怀疑,只是意味着要否定该陈述所表达的信念,而赞成暂时未被怀疑的其他陈述。”(Polanyi,1958,p.272)为了阐明这一主张,他分析了两种形式的明确怀疑(explicit doubt),即矛盾式怀疑(contradictory doubt)和不可知论式怀疑(agnostic doubt)。
以“我相信p”为例,这里p可以代表“行星按椭圆形轨道运行”,或者“人都是有死的”等等。对此,我可以说:“我怀疑p”。这句话可以理解成“我相信非p”,这就是所谓的“矛盾式怀疑”;也可以理解为我否定有充分的理由在p和非p之间作出选择。后者又可分为两种情况: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我相信p是尚未证明了的”,又可理解为“我相信p是不可证明的”,这就是所谓的“不可知论式怀疑”:前者是一种暂时性的不可知论式怀疑,后者则是一种永久性的不可知论式怀疑。
矛盾式怀疑的信托内容是明显的,它否定了原初陈述所表达的信念p,而肯定了与之相矛盾的信念非p。原初陈述和矛盾式怀疑处于同一信托层次上。不可知论式怀疑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无论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不可知论式怀疑,都没有对p之可信性(credibility)、即可信或不可信作出明确的断言。然而,不可知论式怀疑也有其信托内容。“它意味着接受某些关于证明的可能性的信念”。(ibid,p.273)“我相信p未被证明”或者“我相信p是不可证明的”,预设了对某个框架的接受:在此框架中,p可以说被证明了或未被证明,是可证明的或者不可证明的。在不可知论式怀疑中,原初陈述和不可知论式怀疑处在不同的信托层次上,后者所接受的信念在逻辑层次上深于前者所接受的信念。
除了分析矛盾式怀疑、不可知论式怀疑的信托内容,波兰尼还在更深的层次上阐明了怀疑的信托品格。他说:“通过探讨比如表达在我们语言中的以概念框架的形式出现的信念,我们可以进一步阐发作为一个原则的怀疑的限度。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信念是由我们习用的语言所决定的,我们用该语言来诠释我们的经验,来建立我们的言述体系。我们正式宣称的信念能被认为是真的,归根到底只是因为,我们先在逻辑上接受了一套特定的语汇,我们与实在的所有关联都是由此建构的”。(ibid,pp.286-287)这里,波兰尼触及了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信念,它们渗透在我们的语言中,表现为我们的概念框架,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这类信念构成了我们一切智能活动的终极基础:“默会的同意、理智的激情、共享一种习用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加入一个志趣相投的共同体:这些因素影响了我们对事物本性的看法,我们依赖这种看法来把握事物。任何智能,不管多么具有批判性和原创性,都不能在这种信托框架之外起作用。”(ibid,p.266)(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最后这句话堪称信托纲领的典范表述。波兰尼在此强调,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我们习得了语言,成了共同体的成员,获得了关于实在、事物本性的根本信念。只有在这类终极信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接受或者怀疑某个特定的信念。这种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中的概念框架,作为我们最深层次的信念体系,构成了怀疑的最后的信托根基。
通过渐次深入地挖掘怀疑的信托内容,波兰尼阐明了怀疑的信托品格。怀疑不能在信托纲领之外起作用,这正是合理的怀疑的本性所在。波兰尼说:“限于‘合理的怀疑’——这是法律和怀疑哲学的特点——揭示了怀疑的信托品格。要求怀疑必须是合理的,就意味着得依赖于某些不能合理地加以怀疑的东西——用法律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道德的确定性’。”(Polanyi,1958,p.274)合理的怀疑的要求不仅适用于法律和怀疑哲学,而且适用于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领域,是一个普遍的认识论要求。如果说,普遍(全盘)怀疑因试图剔除所有的信念内容而陷于悖谬的境地,那么,合理的、健康的怀疑就是一种具有信托品格的怀疑,是在信托框架之内展开的怀疑。
波兰尼对合理的怀疑的本性的上述认识,和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甚为相契。《论确定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怀疑来自信念之后”。(Wittgenstein,§160)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命题可以看作是对波兰尼的“怀疑的信托品格”这个术语下了一个精彩的注脚。试述如下。
维特根斯坦对错误的怀疑图景的批判,蕴涵了他对怀疑的正面看法。他在不同场合提到,错误的怀疑图景不是我们的怀疑游戏。(ibid,§154、255、317)那么,肯定地说,我们的怀疑游戏是什么样的呢?它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合理的怀疑(reasonable doubt)。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合理的怀疑有什么特征呢?
合理的怀疑需要理由。“我们的怀疑有特定的理由。”(ibid,§458)“如果有学生不相信:在人类有记忆之前,这座山就已经存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说,他的这种怀疑没有理由。”(ibid,§322)“这么说,合理的怀疑必须有理由。我们也可以说:‘理性的人相信这一点’。”(ibid,§323)合理的怀疑是我们的怀疑游戏,这样的怀疑需要理由。
在合理的怀疑中,当我们质疑其他东西的时候,理由是我们所依赖的东西,所依赖的东西通常是不受怀疑的。“怀疑的行为和不怀疑的行为。只有有了第二种行为,才会有第一种行为。(ibid,§354)“当我们要检验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已预设了某种东西是不受检验的。”(ibid,§163)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在历史学中,我们也许会检验关于拿破仑的故事,但我们不会去检验,是否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基于错觉、伪造等等;在科学当中,为了用实验来检验某个命题的真理性,我们预设了如下命题的真理性,即我所看到的那种仪器确实是在那里,如此等等。(cf.ibid,§345、346)
怀疑不仅以未被怀疑的东西为前提,而且以不能怀疑的东西为前提。此处的“不能”是在逻辑的意义上说的,这一层意思是维特根斯坦着重强调的。如上所述,合理的怀疑需要理由,但是,提供理由的活动会有个终点。(ibid,§110)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检验、解说、辩护、证明等。(ibid,§164、189、192、204、212、563)在此,我们触及了怀疑的极限。提供理由的活动有一个终点,这一事实表明,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我们会“在某一点上完全没有怀疑”(ibid,§375),或者说,“在某个地方,我必须从不怀疑出发”(ibid,§150)。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怀疑的缺席是我们的语言游戏的本质。”(ibid,§370)在此,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怀疑游戏的终极基础:“怀疑本身只能以超越怀疑(beyond doubt)的东西为基础”。(ibid,§519)
在我们的怀疑游戏中,不能怀疑的东西像枢纽和轴一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质问和我们的怀疑依赖于如下事实,即有些命题是免于怀疑的(exempt from doubt),可以说,它们正如其他东西围绕着旋转的枢纽。”(ibid,§341)“我并不是明确地认识到那些固定的命题的。我后来发现它们正如一个轴,物体围绕着它旋转。说这个轴是固定的,不是说有东西把它固定住了,而是围绕着它展开的运动决定了它的固定性。”(Wittgenstein,§152)枢纽的隐喻和轴的隐喻表明,有些东西是怀疑的根据,但本身却免于怀疑;这些东西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图景(Weltbild/world-picture)。构成世界图景的东西十分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概念框架,它是我们关于世界的基本信念,我们用它来理解世界。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图景,其作用与波兰尼所说的渗透在我们的语言中的概念框架相类似,都是指我们关于世界的根本信念。
世界图景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它是“我所有探究和断言的基础”(ibid,§162),它是“一种继承而来的背景,在这背景上我区分真和假。”(ibid,§94)它是“我们思想的脚手架”,它“赋予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我们的研究以形式”。(ibid,§211)怀疑作为一种重要的认识活动,就是在根本性的信念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我们的学习经验之中:“在孩提时代,我们学到了各种事实,比如,每个人都有一个脑袋,我们信任并接受了这些事实。……我相信我有祖辈,我相信那些表现得像我父母的人确实是我的父母,等等。这一信念也许从未被表达过;甚至它确实如此这种思想本身也未被思及过。”(ibid,§159)“孩子是通过相信成人来学习的。怀疑来自信念之后。”(着重号为笔者所加)(ibid,§160)“我学到了大量的东西,并且在人类权威的基础上接受了这些东西。然后,我发现,有些东西被我自己的经验确证了,而有些东西则被否证了。”(ibid,§161)和波兰尼一样,维特根斯坦强调,人是通过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获得关于世界的根本信念的。通过学习,儿童掌握了人类的语言游戏。在拥有了世界图景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探究,包括怀疑。在这样的脉络中,维特根斯坦引出了“怀疑来自信念之后”的结论。这个结论与波兰尼的“怀疑不能在信托框架之外起作用”的主张,何其相似乃尔!
如前所述,波兰尼通过渐次深入地挖掘怀疑的信念内容,阐明了怀疑的信托品格。笔者认为,在维特根斯坦的上述思想中,实质上也蕴涵了这样一种思路。
如果我们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路做一个思想实验,就能够阐明这一点。如上所述,维特根斯坦认为,合理的怀疑依赖于理由;如果我们对这个理由作合理的怀疑,就需要第二层次的理由;如果我们再对第二层次的理由做合理的怀疑,就需要第三层次的理由,如此等等。但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样的思想实验不能无限地做下去,因为提供理由的活动有个终点。如果我们用波兰尼的术语,把各个层次的理由看做是同一层次上的合理的怀疑的信托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的世界图景,就是我们的怀疑活动的终极的信托根基。
可见,从维特根斯坦的理路出发,我们也能像波兰尼那样,渐次深入地揭示怀疑的信托品格。
总之,在合理的怀疑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波兰尼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会聚。“怀疑来自信念之后”的命题和“怀疑的信托品格”,可谓异曲同工,在义理上若合符节。
三、“无涉批判的”和默会怀疑
至此,我们对怀疑的讨论还只限于明确怀疑,即对明确陈述的怀疑。随着默会维度(tacit dimension)被引入认识论,怀疑的图景就变得复杂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尼发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怀疑,即默会怀疑。
默会怀疑的发现和“无涉批判的”(a-critical)这个术语的发明密切相关。为了阐明默会怀疑,让我们先从“无涉批判的”说起。
在波兰尼哲学中,有四个相关的术语:批判的(critical)、非批判的(uncritical)、无涉批判的(a-critical)和后批判的(post-critical)。前两个术语是在哲学中被广泛使用的,后两者是波兰尼的独创。对某种东西持“批判的”态度,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对它进行“自由和公开的考察”;相反,“非批判的”是指信念、信任、对传统和权威的接受等认知态度。“后批判的”一词,正如本文开头所表明那样,反映了波兰尼对其哲学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自我理解。那么,“无涉批判的”又是指什么呢?
在《个人知识》中,在区分了明确的、言述的知识(explicit/articulate knowledge)和默会知识/认识(tacit knowing/knowing)的基础上,波兰尼说:
系统的批判只适用于言述的形式,我们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进行这种批判。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批判的”或“非批判的”这样的术语应用于默会思想过程本身,正如我们不会谈论批判的或非批判的跳高或跳舞的活动。默会行动是用其他标准来判断的,因此被认为是无涉批判的。(Polanyi,1958,p.264)
波兰尼主张,我们把“批判的”和“非批判的”这两个术语留给明确的、言述的知识。为了表明默会知识和明确知识有种类的差异,他创造了“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来描述它。
“批判的”、“非批判的”与“无涉批判的”之间的对峙,在《人的研究》(1959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在那里,波兰尼是这样来区分明确知识和默会知识的:
两类知识之间的本质的逻辑差异在于如下事实,即我们能够批判地反思某种被明确地陈述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反思我们关于某种经验的默会意识。(ibid,1959,p.14)
在波兰尼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一种明确知识(如一张地图)作一番批判的检验,是因为它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同时它又对我们有所言说,告诉我们某种信息,令我们倾听。(ibid,p.16)波兰尼认为,对明确知识的这种批判的检讨可以重复进行无数次。“这种类型的批判过程,可以数小时乃至数月、数年地进行下去。我可以任意次地通读整个书稿,逐句考察同一个文本。”(ibid)然而,对于默会知识来说,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种构成行动的知识或者内在于行动的知识,默会知识对于行动者来说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它与行动者是一体的。而且,对默会知识的检验不能重复进行,每一次检验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进行。总起来说,在波兰尼看来,如果我们把对明确知识的考察称作是“批判的”,那么,我们获得和持有默会知识的方式是“无涉批判的”。(ibid,p.17)
如何理解波兰尼刻意创造的“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在我们的概念地图上,它处于什么位置?从字面上看,“无涉批判的”似乎超越于“批判的”与“非批判的”之间的二分。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笔者对“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提出以下两点看法。
首先,“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背后的基本直觉,是对我们认识活动的非批判的、信托维度的承认。所以,在很多场合,波兰尼所谓“无涉批判的”,其含义就是“非批判的”。波兰尼创造这个词的动机,是要批判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知识观、科学观。客观主义、实证主义作为批判哲学的一种形态,其基本特征是无视人类知识的非批判的、信托的品格。但是,在波兰尼批判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早期阶段,这个词并没有出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个人知识》第三部分第八章第264页。在他的早期著作如《科学、信仰和社会》(1946年)和《科学信念》(1950年)(ibid,1950,pp.27-37)等中,波兰尼讨论了科学的信托成分,那时他用的术语是“非批判的”。对我来说,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来自《个人知识》一书本身。在第四章第三节中,波兰尼讨论了传统的传递:在那里,他用“非批判的”来描述学徒对师傅的态度。(cf.ibid,1958,p.53)然而,当他在第264页引入了“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之后,在该页的注释2中,他就主张用“无涉批判的”来替代“非批判的”。(ibid,p.264)作出这个调整的原因是,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中,默会维度已被引入了讨论。显然,在这一语境中,“无涉批判的”(“a-critical”)的涵义,就是“非批判的”(“uncritical”)。可见,尽管波兰尼明确宣称,“批判的”和“非批判的”只适用于明确知识,默会知识则超越于“批判的”和“非批判的”,因而是“无涉批判的”,但在很多场合下,当他用“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时,他的实际所指正是我们认识活动的非批判方面。上文在讨论波兰尼对普遍怀疑原则的批判时,笔者引用了波兰尼几段话,其中他就用“无涉批判的”来描述我们意识中的非批判的、信托的维度。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在这些语境中用“非批判的”来取代“无涉批判的”,我们不会丧失什么东西。
其次,“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是误导的,因为它模糊了如下事实,即默会认识也是可加以考察、检验和反思的,或者更直接地说,可加以批判的。波兰尼说:
我只能在行动中来检验我对某个熟悉的地方所拥有的一种心灵地图,这就是,我切实地把它作为我的向导。如果我迷路了,我就能相应地改正我的思想。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改进非言述的知识。我一次只能以一种方式来看待某物,如果我对自己的所见有疑惑,我所能做的就是再看一次,这样也许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了。非言述的智能只能通过一次次地采取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来探索自己的道路。(Polanyi,1959,pp.16-17)(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此,一幅心灵地图被看做是默会知识的一个实例。从这段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默会知识是可以检验的,它可以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它是能够加以纠正和改进的。波兰尼在此强调的是,考察默会知识的方式不同于考察明确知识:我们只能用行动来考察默会知识,而且每次只能以一种方式来检验。从这里所说的内容来看,很难得出结论说:默会知识是超越于批判的。我们所能说的只是,默会知识与明确知识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批判的。因此,当波兰尼说默会知识是“无涉批判的”(超越于“批判的”和“非批判的”)之时,他在客观上制造了概念混乱。“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遮蔽了默会知识的批判维度。
和波兰尼相比,维特根斯坦学者似乎更为直截了当地承认了默会知识的批判方面。维特根斯坦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哲学有深刻的影响。在时下关于默会知识的讨论中,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批维特根斯坦学者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挪威的维特根斯坦学者格里门(Harald Grimen)认为,默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它也能够接受批判。当然,默会知识接受批判的方式不同于用语言来表达的知识,它必须依赖于活动或实践的质量来加以批判。(格里门,第72-73页)公平地说,波兰尼也有这个意思,但是,他那含混、无用甚至误导的术语“无涉批判的”,模糊、遮蔽了他的洞见。
简单地说,笔者的看法是,波兰尼的真实意图不是要否认默会认识的批判方面,而是要提醒人们关注一种不同形态的批判。这一点为以下事实所证明,那就是,他进一步讨论了默会怀疑,这是他所发现的一种新的类型的怀疑,不同于明确怀疑。如果说,默会认识真的是“无涉批判的”(即超越于批判或非批判的),那么,“默会怀疑”这个术语将是一个语词矛盾。
如上所述,明确怀疑是对明确陈述的质疑,那么,在波兰尼看来,默会怀疑是指什么呢?
为了说明两类怀疑的差异,波兰尼区分了以下两个陈述:“雪是白的”和“‘雪是白的’是真的”。前者是一个描述性陈述,后者被波兰尼称作是一个信心陈述(accreditive statement)。波兰尼说:
因为“‘雪是白的’是真的”是指言说者作出的无涉批判的断言行动,它不是一个描述性句子,不能成为明确怀疑的对象。人们只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说出该陈述。如果这种断言可能缺少完全的自信,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被看作是言说者对他自己的断言的怀疑。这将是一种默会的怀疑,一种非言述的犹豫,正如一个射手犹豫地扣动扳机。(Polanyi,1958,p.280)默会怀疑是指所有启发性努力中内在的疑虑、非言述的犹豫。“一个启发性冲动,总是对其可能的不恰当性有一种感觉。它之缺乏绝对的确定性可被描述为其内在的怀疑。”(Polanyi,1958,p.280)
波兰尼认为,默会怀疑和明确怀疑有种类的差别。关于默会怀疑,波兰尼说,“我们用来证明或否证一个明确的陈述性句子的检验方法,不能应用于我们的行动。因此,不可能在怀疑明确陈述的意义上,来怀疑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声称所做的事情)。”(ibid,p.285)两种怀疑之间有种类差异这一事实,完全契合我们上面得到的结论:默会知识和明确知识接受批判考察的方式不同。可见,默会知识和明确知识都能够被怀疑和批判,但是它们被怀疑和批判的方式不同。
尽管有种类差异,默会怀疑和明确怀疑还是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在谈论宗教的怀疑(religious doubt)时,波兰尼指出,“对我们赖以展开信仰的言述框架作明确的批判性检验,可以加强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在怀疑,以至于完全摧毁我们的信仰。”(ibid)在此,我们看到默会怀疑为明确怀疑所强化的一个实例。它典范性地发生在宗教中,但并不限于宗教领域。波兰尼指出:“这一框架的引发理解(即按照服从上帝来理解自身)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它的构成因素的各种陈述的说服力。同样地,一组细节引发(以这些线索为基础的)启发性洞见的力量,将依赖于作为线索的这些事实的可靠性。因此,对作为事实的线索的怀疑,可以动摇建立在它们之上的体系的内在证据。明确怀疑会强化对我们的接受的内在怀疑,以至于使它成为一种完全的拒绝。”(ibid,pp.285-286)在所有启发性活动中,默会怀疑能为明确怀疑所加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考虑放弃“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因为一方面,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术语,我们不会丧失什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也许会遮蔽某种重要的东西。在我看来,有了“批判的”和“非批判的”这一对概念,波兰尼就足以完成其后批判哲学的理论目标。波兰尼无意于否认默会知识是可以批判的,但是“无涉批判的”这个术语在字面上却有此意味。他的真正意图是想表明,默会知识接受批判的方式不同于明确知识。按照这样的思路,波兰尼发现了默会怀疑。和明确怀疑相比,默会怀疑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怀疑(deeper doubt)。(ibid,p.272)波兰尼对默会怀疑的阐发,他对默会怀疑和明确怀疑的关系的讨论,拓展并深化了我们对怀疑的理解,虽然简略却极有启发性。我的直觉是,“默会怀疑”这个概念很有生发性,对这个论题的深入讨论在认识论上将是富有成果的。
简短的结论
总结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波兰尼的“怀疑之批判”是在划分明确知识和默会知识的认识论架构中展开的。相应于两种知识的划分,波兰尼分别检讨了明确怀疑和默会怀疑。在明确怀疑的层面上,波兰尼揭示了普遍怀疑原则的悖谬本性,阐明了怀疑的信托品格。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则从不同的进路出发,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默会怀疑的发现是波兰尼的一个贡献。如果说,“怀疑的信托品格”这一表述很好地阐明了明确知识层面上怀疑和信念、“批判的”和“非批判的”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默会怀疑,我们则会提出相关的问题。如上所述,笔者认为,波兰尼的“无涉怀疑的”这个术语是误导的,应该放弃。在清除了这个障碍之后,让我们来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默会知识层面上的“怀疑的”和“信托的”、“批判的”和“非批判的”的关系?
如上所述,波兰尼对默会怀疑的讨论十分简略,因此,在他那里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成答案。以下,利用波兰尼、维特根斯坦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维特根斯坦学者的思想材料,笔者拟对这个问题做一番试探性的讨论,提出一个方案,就教于方家。
正如冯·赖特(von Wright)指出的那样,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景具有一种非命题的、实践的品格。(Wright,pp.178-179)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实践”概念,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维特根斯坦学者阐发“默会知识”概念的最重要的灵感来源。(cf.Johannessen,1988,1990)他们区分了强意义上的默会知识和弱意义上的默会知识。前者是原则上非语言所能尽因而需要用行动、实践来表达的知识,后者则不是原则上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在波兰尼的哲学中,既有强意义上的默会知识,也有弱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本文的着重点是强意义上的默会知识,即体现在行动中的知识。(参见郁振华)
维特根斯坦认为,以世界图景为基础,我们的行动是确定无疑的。他说,“如果我们曾依信念的力量而确定地行动,我们还要疑惑:有很多我们不能怀疑的东西吗?”(Wittgenstein,§331)“我知道这是我的脚。我不能接受任何经验来证明与之相反的东西。——那也许是一个感叹,但是,从中能推导出什么呢?至少,根据我的信念,我以毫无怀疑的确定性行动。”(ibid,§360)维特根斯坦进而强调,这种确定性是最高程度的确定性:“如果有人像摩尔那样说,他知道如此这般的事情,他就道出了某事对他而言的确定性程度。重要的是,这个程度是个最大值。”(ibid,§386)
以世界图景为基础的行动具有最高程度的确定性,在笔者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的默会知识的非批判的、信托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针对各种具体行动的默会怀疑。而且,笔者认为,对于默会怀疑,既可以从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考察,也可以从第三人称的视角来考察。波兰尼把默会怀疑看做是启发性行动中内在的疑虑、非言述的犹豫,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视角。不难看出,上文所述他对默会知识的检验方式的特点的刻画,也蕴涵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和波兰尼不同,当格里门强调默会知识也是可以批判的时候,他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他强调从行动的表现和后果来对他人的默会知识作批判的考察(格里门,第72-73页)。
这是笔者对默会知识层面上的“批判的”和“非批判的”、“怀疑的”和“信托的”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笔者愿以这个简略的试探性方案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注释:
①“无涉批判的”是波兰尼的一个重要术语,下文将作专门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