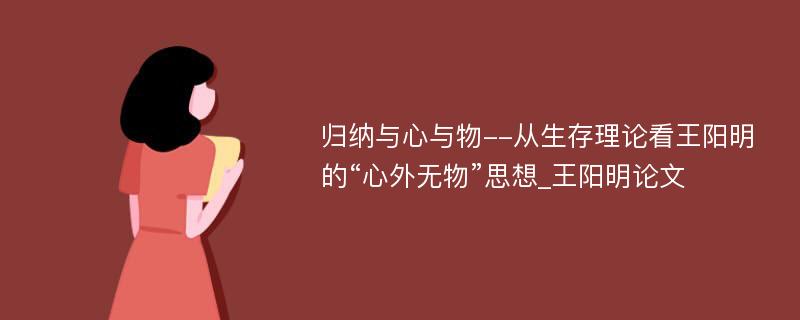
感应与心物——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的生存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感应论文,思想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3)02-0052-007
一、意之所在即是物:心物循环论
“心外无物”并非一个认识论命题,而是有着其更为深刻的内涵。王阳明不可能不认识到物的客观实在性,但他关注的焦点不在此,他要追问的是:物与心如何获得各自的规定性?
首先,王阳明认为只能就物谈心,反对外物求心。作为存在者的物,是一切存在得以澄明的现实境域,是我们必须预先承当的。作为儒者的王阳明,对此的承当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突出表现在王阳明十分浓厚的、作为一生的孜孜追求的仁民爱物思想。可以说,上至天地,中至黎民百姓,下至草木鸟兽瓦石鬼怪,无不是儒者关爱的对象:“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上》)。对于王阳明而言,建功立业,是实现这一理想;著书立说,是宣传这一理想,从而一切外物求心的道路都成为不可能。“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传习录·中》)在王阳明看来,这正是辨别儒佛的关键。他认为,儒家“仁爱及物,比之释迦则又至也”[1-p292]。换句话说,“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随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传习录·下》)。
但是,承认物的客观实在性却并不意味着把“心”和“物”的共同现成存在设为前提。王阳明不可能如康德那样认为“我们外面的事物的存在”是尚未证明而应该得到证明的。[2-p30]毋宁说,王阳明思想本身违抗这种证明,认为心和物在其区别及联系中一向已经是其所是了,而无论任何样的证明都是后起的和片面的。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阳明侧重从心上说物,声称“心外无物”。于是,心也就不是什么现成的东西:“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传习录·上》)。能不离所,所不离能,即能即所,能所互生,心物也就在这一循环结构中相互争斗相互转让而复生了。“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争斗转让之复生的“窍”(Gap,裂隙),便是作为“人心一点灵明”的“意”。
“意”的“裂隙”义,首先表现为王阳明早年所提出的“四句理”:“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不难看出,身心知物都环拱在意的周围,须通过意来展示其本身,意成为这一复杂关系的“环中”。(注:正如陈来先生指出的那样,江右以前,王阳明把诚意看成大学八条目的核心,诚意也就成了他讲学的宗旨。(参见《有无之境》第6章,人民出版社1991)王阳明的不同弟子都同时(正德十年即1515年前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徐爱、陆澄、陈九川等对其作了大致相同记录。(参见《传习录》第6条、78条、201条等。)可以说,王阳明正是以“超以象外”的方式捕捉着这一“裂隙”,以回应裂隙本身的召唤。如此这般,阳明再三遭到误解或不理解也就成为意料之中的事。)
第一,就归意于已发而言,王阳明同于朱熹。王阳明认为,“心之发动处谓之意”(《传习录·下》),“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答罗整庵少宰书》,《传习录·中》),“意者其动也”[1-p243],“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意是心之发心之动,心体因意才得以呈现。其次,“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传习录·下》),“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1-p217],意必应物而后动,物因意才可能存在。第三,心物之区分在意这里变得模糊,它们的联系成为最重要的:“意之所用,必着事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在这里,以外部世界的存在与我的对待为其信念的“自然观点”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套用布伦塔诺的话来说,现在我们关注的既不是意识活动中的“心”,也不是作为主体对象的“物”,而是心和物“之间”的神秘。
但是,绝不能将“意之所在便是物”等同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甚至也不能联系到马克斯·舍勒的“价值的意向性”理论。因为无论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还是舍勒的精神现象学,都仅仅把“意”局限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内,没有看到除了认识论或价值论的功能而外,“意”还有多方面的功能向度。下文我们将看到,王阳明的工夫和本体思想,使意的功能向度得以全方位地张显,从而也就于根本处区别于他们二者。
二、物即事也:行为工夫论
大体说来,王阳明论心物关系有三个层次:一是心物循环论,将一切有关心物关系的“自然观点”悬置。二是行为工夫论,以事为物,消心物于不“积”之实行。三是生存本体论,于“感应之几”处为前二说建立最后之根基。无疑,在这三层次中,生存本体是根,无它即无前二者。但行为工夫却是王阳明的“立言宗旨”,即讲学目的之所在,因而也就成为重中之重了。
徐爱所录《传习录·上》有一条曰:
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事,无心外之物。
此条上文已有所摘录。显而易见,王阳明讲“四句理”的目的首先在于“事亲”。也正如陆澄所录,“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传习录·中》),心外所无的物,首先是事亲孝亲这样的道德—伦理行为物。正是在此“道德—伦理行为物”上,工夫才有其下手处。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物,强调至善,强调克己正心诚意致良知等等,无非是要人于此处着力,为善去恶、改过迁善。也即是说,此处条理节目虽然繁多,但其实只有一事一物:“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其实只是一事。……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大学问》)。它要求戒惧于有善有恶的“意之微”,在心物“之间”的事上磨炼,贞定如一。对于此“道德—伦理行为物”意义上的工夫论,学者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说。
虽然对于儒者而言,事父之孝是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等等的根,(注:《传习录·上》陆澄所录一条云:“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杆生枝生叶。”又《答聂文蔚》释孟子“尧舜之道,孝弟而己”云:“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从这两条可以看出,道德伦理无疑是儒家的立教的根本,但要说它是儒家立教立法的全部,则不能成立。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儒者其实是不乏形上关怀的。)但是这却绝不意味着王阳明即事所为的物单单是指道德—伦理行为物。如果我们仅仅到此为止,那么可以说,我们还未能窥得王门心学的门径。毋宁说,王阳明所指的物更应该是一般行为物。
所谓一般行为物,即人饱含着生存的情感,以自己的全部投入到自己生存的世界之中,从而使世界和自己的存在同时得以澄明。这里的“人”,首先是整体的,但也可以说是肉体的,是道德的伦理的,更是认识的、审美的、情感的、实践的和创造的,但靠所有后者的存在方式的综合却并不能得出前者的存在。也即是说,“人”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现成存在物,他本来已经知道他的世界,“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他是与他的世界在“事”中为一的、一并来到的。在这种意义上,王阳明同意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传习录·上》)。
于是,心物亦有了众多的向度。自己、他人,甚至整个世界,都在“物”的范围之内,都是“明觉之感应”;“心”则更为突出,“喜怒哀乐与思与知觉,皆心之所发。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1-p146]它意味着,在一般行为物处,心性合一,性情合一,心物合一,甚至连遮蔽与无蔽亦合一:“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答陆原静书》,《传习录·中》)。“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传习录·下》),这是众多无滞无积的生存可能性,是心物最原始最积极的规定性,而无论其清浊善恶本真非本真。人的生存,就是依于其一般行为物,不断地让这些可能性从身边一闪而过,不断地抓住这一可能性或抛弃那一可能性,抓对此可能性或抓错彼可能性。换句话说,人本己上即此一般行为物,即自由地为自己的存在而自由生存的可能性,即“必有事焉”。此即真正意义上的“工夫”,不须人为、与时俱化而无有积滞:“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答聂文蔚》,《传习录·中》)正所谓:人道运而无所积,故众事宁!(注:《庄子·天道篇》云:“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答陆原静书》曰:良知之体“本自生生”,“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良知之体本自宁静”,无“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而善恶自辨”。(《传习录·中》))
但是,一般行为物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漫无目标,“必有事焉”也绝不意味着毫无定向。生存的可能性向来已经注定要将人和物捆绑于某种可能性而非那种可能性,这即是工夫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工夫本身呼唤一种决断,一种不思善不思恶而善恶自辨的决断,因为无论是道德—伦理行为物,还是一般行为物,都自然有其“头脑”:良知。“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同上)良知不仅仅是道德伦理的,毋宁说,它是工夫本身的“定盘针”,是一般行为物本己的“指南针”,是决断的内在依据,是对可能性的本真领悟,是定向与非定向的争斗,是宁静与喧闹的嬉戏。如果说,上文的分析多注重“必有事焉”之非定向的、率性而为、物各付物的一面,那么我们将更多地把其定向的、修道而行、克治省察的一面留待下文讨论。其实二者是区而不分的。
三、感应之几:生存本体论
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问题是王阳明工夫理论的中心问题,王阳明与他的学生曾就这一问题反复辩难。如事上磨炼与静坐的问题,必有事焉与勿忘勿助的问题,戒慎恐惧与何思何虑的问题,集义与不动心的问题,存心与定气的问题,有情与无情的问题,动与静的问题,已发与未发的问题,有善有恶与无善无恶的问题等。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于工夫理论本身,这些问题将很难说清楚。而且若王阳明的工夫理论只局限于此,那么它也只能是飘忽不定、游荡无限的,最终将不成其为工夫。我们说,王阳明的思想无疑有其形上姿态,有其“头脑”,有其“根”,(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王阳明对“头脑”和“根”这两个字眼之偏爱。无论是孝根、灵根、命根、性根、病根还是学问头脑、工夫头脑、良知头脑等等,王阳明都欲直指本体。晓得本体,则头脑即根、根即头脑,二者无间,工夫“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传习录·下》))它就是王阳明的生存本体论。所谓生存本体论,也就是对行为工夫论的一种奠基,以便寻找出一般行为物的原始根据并最终确立之。我们认为,于“感应之几”处即有王阳明的生存本体思想在。
《传习录·下》有一条所录云: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鬼神万物尚在何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刘宗周云:“此一条颇近宗门”。其实并非如此。这一条正是王阳明心学的“千古不传之秘”,其生存本体论的秘奥全在于此。这里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心物之感应是人本己的生存结构,它无时无刻不在。有感应则为人,无感应则人为死人;有感应则物各付物,无感应则人与物同时归于遮蔽。因而,这一感应不可能与《史记·天官书》所说的“先形见而应随之”之感应为同类,它只能是“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传习录·下》)之感应。第二,这一结构决不可能从经验中抽绎出来,它只能是既定的天生的。生存结构的天生性不同于认识之先验性,它在此处虽隐而不发,但王阳明于《五经臆说十三条》中将其合盘托出,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诚发见也。皆所谓‘贞’也。观天地交感之理,圣人感人心之道,不过于一贞,而万物生,天下和平焉,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1-p978]这也就是《易·系辞下》所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论语·阳货》所言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第三,在人类的这一生存结构中,感应一定是有定向有主宰的。人的“灵明”即良知可以说就是主宰人的一切生存行为的机能,正如本能是兽类控制活动的机能一样,二者同样具有与其生活目的相适应的自然结构。毋宁说,良知就是这一结构本身。如此一来,良知就彻底从道德伦理的狭窄定位中挣脱出来,成为人的整个生存活动本身的良知而具有了无限丰富的创造性。第四,正是由于其天生性,这一结构在来源上具有了严格的纯粹性,不能于其中搀杂任何经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便即是百神感格,便即是万物复生,从而成其为最值得人敬畏和听从的东西。第五,“一气流通”是感应的最终根据,亦是人的生存的必然事实与最终理想,感应即流通、流通即感应也。这一观念与其说是王阳明对其前人特别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张载的虚空即气说及道家的元气元神元精说等的继承和发展,倒不如说它已经成为王阳明那一时代儒道两家的共同观念。第六,“几”乃离无出有、明暗转化之发生机制,(注:《易·系辞下》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孔颖达《正义》曰:“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周敦颐《通书》亦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中国古人对“几”的重视,不胜枚举。)不可以具体、现成的生存行为反对感应之不受局限的作用和价值。第七,对于这一结构特别是良知的定向主宰机制的干净明晰之表述,也就成为生存本体论的任务而尤显重要了。
先看《传习录·上》之一条:
侃去花问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侃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曰:“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首先必须强调,此善恶问题已远远超出了道德伦理范畴之外而成为良知的主宰定向问题。此问题在古人看来即“性”的问题。我们姑且把其它往圣前贤有关于此的言论置于一旁,再来看王阳明师生的一段问答: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先生曰:“然。”(《传习录·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单纯地看此段话,很难理解。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可以从性上讲,亦可以从心上讲,均是就本体上说。刘宗周则认为无善无恶只能从性上讲而坚决反对从心上讲。在他看来,心关系到成德的问题,若从心上讲无善无恶,则工夫无下手处。由此而下,刘宗周认定“四句教”不是王阳明本人说的。对于后者,学者多有驳斥,刘说不足为据,此不论,至少我们不能因某些东西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认其为不存在。我们说,王阳明以上两段话是讲人的生存活动的结构即感应的,则“四句教”也就不能脱离开感应来讲;若抛开刘本人的立论宗旨而言,刘宗周将无善无恶限定于性上,也就是因为没能看到这段话与感应之说的联系而不能理解这段话。于是,我们就有必要将上两段文字与“四句教”结合起来作一分疏。
所谓“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天泉证道与严滩问答两盛事都围绕它展开,而它又引出多方争论,我们在此且都不去理会。结合以上论述,我们说,所谓“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指心物感应之几是天生的,是人的本己结构。它浑无罅缝,“运而无所积”。人于此处只可听从感应的召唤而视听言动略无执滞。这里不仅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超出一切分别相,甚至亦离言绝象,喧闹但绝不失其宁静。而所谓“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有善有恶意之动”,是指欲观花而花善草恶,欲用草而草善花恶,是善是恶全凭一时感应之机缘:如山中看花,未看则心花同寂,看时则花之颜色顿时灿然,善也。但若执定认为花善草恶,则感应“运而有所积”,此即“皆从躯壳起念”,便有个物在外心在内而将善恶捆绑于物感上,使二者因不相联属而共同窒息,此即“气拘”,即“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然而,感应是人本己的生存结构,是人最值得敬畏和听从的,它一有所息则良知一定当下呈现其息:这就是“从源头上说”,就是良知当下呈现,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既知其息,则此呈现也就是回归感应的开始;“气拘”只能以对感应的应合来消除,一定之善一定之恶随之亦无,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即“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
有了这样的分流,我们就容易理解王阳明的那些貌视截然相反的话。比如,他一方面说“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人”(《传习录·下》),另一方面又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同上)。这里,人们对于是非的判定无疑是其生存活动的“大规矩”,而良知据以判定的根据则是心物感应之积与不积本身,良知存乎人而人却一无所有。同样,严滩问答之四句亦可由此得到很好的解释:“有心俱是实,无心俱上幻”。就四句教的后三句立言,是说良知实有定向主宰功能,工夫在于严格依良知之提醒而随时应答;而“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就第一句来说,认为除过感应之外天下别无事,生存本体只是一个生生不息而已。一言以蔽之,王阳明对于此类问题的回答从来不“执定一边”,或许,这正是因为他“及时”领悟到了感应本身“无有内外之间”的要求。
如此一来,工夫全在对感应之呼唤的应答上,良知的定向主宰功能也就表现在对“是否应答了”的评判及“要应答”的无上命令上。人之生存活动对此呼唤有警觉而应答了,则良知判定这一活动为对、为是;否则,判定为错、为非。是则好、非则恶,而好了恶了反过来又意味着已有所判定有所呈现。可见,是与非全在心物感应之“运而无所积”还是“运而有所积”上看,除此而外良知别无他事人生别无他事。由此,人之生存活动便生生不息:“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四、余论
1.关于王阳明的生存本体论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不可否认,人类之生存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但这些共同是以差异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仅举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为例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中国向来不乏生存论思想,对人生天地间这一现象的思考,是中国思想令人敬畏的执著处,周孔老庄皆然;而中国所缺乏的是存在论思想,对于实在的最终本性,对于宇宙的本性,对于作为存在的纯存在,中国人是不去多认识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天地神人说对我们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但是,至少我们不具有西方传统中高度发达的认识论思想,严格意义上的客体和对象意识,因而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将我们这里的生存论等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更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我们的生存论来批判并拯救西方的科技理性。假若说,海德格尔是与我们相通的,而我们一定要依从海德格尔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恰恰是对象化的思维认识论思想,而不是相反。
2.关于内在的道德性。若曰仁义内在于心,是;若曰人之性是善,亦是。但若说良知灵明即是此内在于心之仁义,又是创生实体,则非。这里的问题是,人的生存是以道德性为前提呢?还是道德性以人的生存为前提?从意之所在说物,与从良知明觉之感应说物,是同一的。没有一个寡头的良知明觉,它只是人的生存结构之中的良知,只是对感应的共鸣。对于感应的应答,即是至善,一切道德上的善恶是非分别,只能是感应后事、感应中自然事。“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传习录·下》)这样,内在的道德性方才有个根基,不言道德而道德自成。否则,便成“理障”,便成“拔本塞源”。一言以蔽之,“良知”并非在心中,而是在感应中。
3.关于王学的分化。本源处即在析意之所在之物与良知明觉感应之物为二,执定一边,或失于敬畏或失于洒脱。
[收稿日期]2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