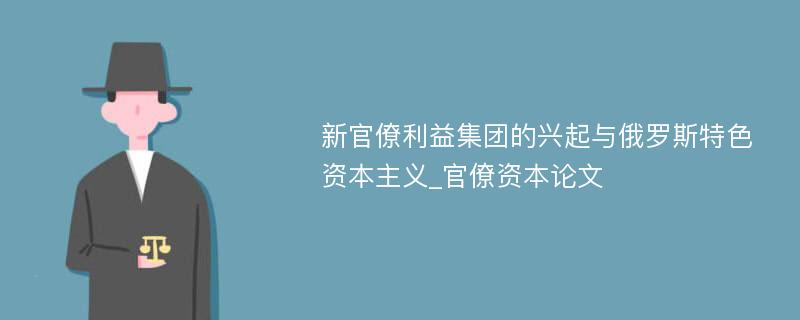
新官僚利益集团的崛起与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官僚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利益集团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当时正红得发紫的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经得意洋洋地吹嘘,以他为首的7家私有寡头企业控制了俄罗斯经济。但风水轮流转,10年之后,当别氏等寡头或流亡海外,或被捕入狱,或改头换面之后,俄私有商业寡头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普京执政后崛起的新的克里姆林宫利益集团。
官僚利益集团取代商业寡头
早在2005年7月,俄《独立报》就刊发过一篇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文章,称普京的7名侧近人士控制着近2200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俄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实际上,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经济就开始向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回归,越来越多的俄高层官员同时出任国有或者国营大公司董事长等要职,直接介入对国家经济的管理。
普京当局认为,俄政府高级官员到大型国企兼职,既是政府履行经营国有资产的责任,也是保障国企忠实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组织措施。据统计,目前普京权力核心圈内至少有10名高官共同控制着俄罗斯最大也是最赚钱的国有或国营大公司,从而在垄断本行业的同时控制了俄的国家经济命脉。俄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的市值一度排在世界第三,曾高达3000多亿美元。副总理茹科夫出任“俄罗斯铁路”公司董事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是“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总统外事助理普里霍季科任“战术火箭武器”公司董事长。总统助理伊万诺夫是主要的防空系统承包商阿尔马兹-安泰公司和“俄罗斯航空公司”董事长。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兼任“石油管道运输”公司董事长。交通部长列维京担任“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公司董事长。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担任“俄罗斯钻石”公司董事长,也是俄第二大银行——外贸银行的董事长。农业部长戈尔杰耶夫同时也是“俄罗斯农业租赁”公司董事长。俄工业与能源部副部长列乌斯是“石油产品运输”公司董事长。此外,前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是俄最大的电力公司“统一电力”的董事长。
在总统的行政部门中,有11人先后兼任6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12人还分别是公司的董事成员。另有15位高官担任了6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并分别享有各大公司的24个董事席位。
通过这些高官,俄政府实际上掌控了主要的经济命脉。随着国际市场原油、天然气和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这几家俄罗斯国有或国营大公司的利润也迅速上涨。据初步统计,2005年和2006年,俄国家控股的公司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资本总量、运营收入和纯利润都呈现较大的上升态势,如“天然气工业”2006年头9个月收入增加了75%,纯利增加了81%,资本总额现高达2260亿美元;国家控股77%的“俄罗斯钻石”已经控制了俄97%的钻石生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也上升至25%;99.9%股份属于俄政府的外贸银行2005年资产上涨57%,利润增加35%。普京侧近人士掌控的国有或国家控股公司总资产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接近俄2006年GDP的50%。
对于这一强大的政商势力,俄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称呼,较为流行的一种是“新官僚资本”,也有人称之为“国家财阀”。根据美国高级管理学校教授法齐奥的调查研究,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00个公司中,共有35个国家出现了高官或议员兼任公司的董事或经理的现象,涉及公司达600家,而这其中尤以俄罗斯的官商现象最为突出。据统计,美国7124家企业中,直接或通过亲属与政府部长或议员构成关系的只有14家,占0.2%;英国7124家企业中有154家,占7.17%;被认为国家调控较强的法国914家企业中与官员关联的只有20家,比重为2.19%;德国840家企业中13家与政界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占1.55%;而俄罗斯入榜的15家企业中有5家属于官办,占30%。在资本市场中,俄官员参与的企业的资本总量占86.75%,远高于美国的4.94%、法国的8.03%、德国的1.2%和英国的39.02%。考虑到法齐奥教授的研究是基于2000年前的数据,显然近年来俄高官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力在进一步加强。
俄出现新官僚利益集团的原因
如果说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行动中,国家财富基本被少数的寡头集团控制和瓜分的话,那么在普京执政后,俄又重新进行财富分配,使其从旧的利益集团手中转移到新的利益集团手中。从俄国内形势发展看,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内俄政商关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俄的国家经济命脉正日益被由普京总统周围的亲信和重要幕僚等高官组成的新利益集团所掌控。可以说,新官僚利益集团的崛起已经成为俄国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普京式发展道路的一大特征。俄新官僚利益集团在普京时期横空出世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俄罗斯存在由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历史传统。俄国历史上具有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及其权力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均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政权及其活动是俄罗斯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是俄国历史的神圣遗产。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写道:“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具体到政商关系上,千百年来,在俄罗斯由国家发挥主导作用,商业服从并为国家意志服务是一种常态,叶利钦时期的金融寡头坐大并在其执政后期操纵国家事务的现象才是历史进程中的插曲。新官僚利益集团的应运而起与俄推崇国家调控的经济思想有着很深的关系。
第二,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模式的转型对俄政商关系模式的变化有决定性影响。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叶利钦时期推行的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导致俄国力下降,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法律和秩序失控。俄整个社会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在转型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由此产生了以国家利益名义加强政府行为能力的动机,民众对调整叶利钦时期搭建起来的寡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强烈不满。以平民主义风格治国的普京针对国家发展的现状和社会民意的需求,开始对经济体制作大规模调整,目标是“让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使俄经济成为“可控制的市场经济”。
第三,新精英阶层要求对政商关系作出新调整。转型理论认为,精英在一个社会的转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决定转型的界限,安排它的进程,控制它的结果”。叶利钦时期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权力资本化以及资本对权力的重新回归,导致了社会政治制度向私人产权和政治多元化方向的发展。随着普京的崛起,其周边形成了新的精英集团——强力派,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并未能从叶利钦的私有化进程中获取经济利益,而新的政治地位促使他们寻求相应的经济红利,从而引发了内部新旧精英的分裂,同时伴生着国家对经济的再度控制。
第四,普京的私有化战略和经济民族主义潮流的混合作用。普京并未放松私有化的进程,其执政以来俄每年被私有化的企业都有两千多家,规模和速度都不小。普京认为,尽管私有化存在种种问题,却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重新国有化可能引发更多问题,同时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增强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民族主义回潮促使普京重新思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并最终决定将产权改革的重心转向公司治理和企业重组,要求对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企业保持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而中小国企则应通过私有化甩掉经济包袱,为发展和壮大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国企提供资金。2004年8月,普京以总统令的形式确认了对巩固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企业及股份公司名单。而普京侧近高官所介入的企业无不属于此类企业。
对新官僚利益集团的两种看法
对于普京治理下的新官僚利益集团现象,俄国内外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基本看法。
一种是亲克里姆林宫的立场,认为普京的这种做法保持了国家对战略经济产业的控制,从而保障了本国的经济安全,并增进了俄的稳定与秩序,是俄近年来和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普京的执政权力支柱之一——“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弗拉基米尔·塔拉切尔对普京近臣代表国家对战略企业进行监管表示坚决支持,他强调说:“我们欢迎外来投资,但是国家必须在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拥有控股权。”俄分析家斯坦诺娃娅强调,“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说法,国家希望由可靠的人来领导这些公司,这些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会与上个世纪90年代那批老板完全不同,他们会代表国家的利益。”从全俄舆情研究中心等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俄民众对国家加强对战略产业的控制普遍加以肯定,并呼吁对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结果进行清算。可以说,普京通过高官对经济加以控制的做法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但俄国内的“民主派”和西方国家则对这种现象予以了严厉批评。俄著名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雷西塔诺夫斯卡娅认为,俄罗斯的“重新民族国家化”进程在继续,政府正逐步收回一切其认为具备战略重要意义的产业控制权。俄国家杜马的独立议员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认为,“普京让俄罗斯倒退了数百年,回到了君主与个人绝对集权的阶段。我们回到了让国家和私人企业在一个体制内共生共存的时代。”普京前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认为,俄罗斯的国有企业,一方面追求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另一方面还要满足国家寡头的个人利益并遵循腐败的“潜规则”。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强调,普京主政多年的结果是把政治权力和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这是一种逐渐扩张的新封建主义秩序,它威胁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
纵观俄罗斯转型以来的经济体制现代化改革进程,就会发现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另一种是自上而下,依赖政府的角色。2003年之前俄罗斯主要采取第一种模式,依靠科技创新,私人领域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但到了2003年之后,石油收入的快速上涨,使政府意识到石油收入不能控制在私人手里,于是加大了政府对石油行业的控制力度。很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这两种选择对俄来说,两种必选其一。不过,正如俄前经济部长亚辛所指出的,很难说俄罗斯经历的政策是完全排除了第一种模式,采取第二种模式。实际上俄罗斯对经济体制的现代化改革模式是一种国家由上到下控制经济占主导的混合模式,新官僚利益集团的崛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新官僚利益集团现象的“支持派”,还是其反对派,都有偏颇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俄政治和商业的联姻尽管招致非议,但国有公司习惯于承担国内外的政治任务,成为俄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之一,比如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俄推行新的对独联体政策方面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这些大国有或者国家控股企业的崛起,俄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底气进一步增加,这无疑拓展了俄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空间。显然,普京当局并不会因为国内外的批评而轻易改变现在的做法。而随着普京政权于2008年的交接,俄政商关系的现有模式在后普京时代可能会续有发展,新官僚利益集团作为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要素将继续存在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