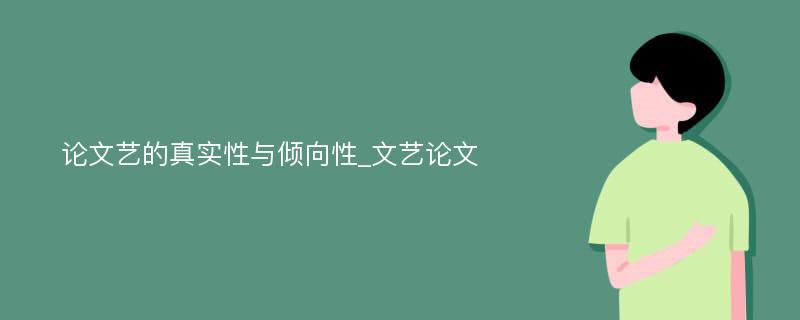
再论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性论文,真实性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此有重要的论述,我国学界也对此问题有过集中的探讨。什么是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二者的关系如何,这个看起来十分清楚的问题,由于外部世界的变化,人们所处历史语境的不同以及个人理解上的差异性,却常常模糊难辨。这就导致了在实际创作中,有时为了文艺的真实性而忘记倾向性,有时为了文艺的倾向性而不顾真实性,有时甚至对文艺的倾向性存在表示怀疑,所有这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背道而驰的。在文艺活动日益繁荣备受重视的今天,重新讨论并厘清这一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主要观点见于他们所写的一些文艺通信中,这些通信评价了拉萨尔的历史剧《弗朗茨·封·济金根》、考茨基的长篇小说《旧与新》和哈克奈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具体是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85年11月26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8年4月初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而在恩格斯给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写的两封信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文艺的倾向性、真实性以及典型性等现实主义的文艺问题。除此之外,在其他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对文艺的倾向性或真实性等问题的相关论述。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他们关于文艺的倾向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肯定文艺的倾向性。恩格斯说“我绝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1]其次,认为倾向性越隐蔽越好。恩格斯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2]“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3]恩格斯还认为,不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4]再次,十分强调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性描写。“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5]“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品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6]因此,恩格斯说:“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7]又次,正是在以上主张的基础上,指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方法,即典型化的创作方法。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8]“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9]以上这些基本构成了马恩经典作家关于文艺倾向性、真实性及典型化创作的主张,也是他们关于“现实主义”的基本见解,这些见解同恩格斯所谈到的“三融合”原则,即“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0]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倾向性需要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来展现和完成,而不能概念式或抽象式的硬性塞入。倾向性无须特别关注,只要创作者将精力执着于细节,执着于情节个性的真实与生动,执着于艺术的“典型化”塑造,那么倾向性便可以“自然地流露出来”。可以说,关于真实性与倾向性关系的统一与一致,是以典型化基础之上的真实性描写为前提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反复肯定了文艺的真实性的重要价值,他们之所以特别推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些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1]真实性、倾向性以及有关典型塑造的相关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内容,之后的各种现实主义理论都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或发展的。 由以上论述可知,文艺的真实性、倾向性及其关系等问题,是一个并不陌生而又内涵界定比较明确的命题。然而,由于受各种现实环境、政治因素、个人喜好等所制约,真正将二者做出比较正确的理解,并在实际创作中合理运用,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把握艺术表现的真实性,以及如何把握作品思想内涵的倾向性,在创作主体的创作意识和实际创作中,往往并不会如理论本身所界定的那样清晰明了。 新时期之初,关于要真实性还是要倾向性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1978年初彭立勋就在《关于文艺的倾向性和真实性——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学习札记》一文中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真实性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和艺术真实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是我们战胜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锐利武器”。[12]而1979年杜奋嘉的《艺术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则从理论上阐明了“艺术真实性与政治倾向性是文艺作品中两个互有联系,但又不能混为一谈的概念”[13]这一基本事实。1980年以后到19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有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一讨论。 从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关于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真实性与倾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如王之望就认为,“文艺真实性、倾向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即文艺真、善、美相统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对无产阶级文艺的一贯的和基本的要求”。[14]这也是大部分理论家所认可的观点。二是认为二者虽然有统一性但仍需要在实践中具体检验。如陈育德、严云受就在承认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相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不是纯理论性的问题,在一部作品中两者是不是统一的,怎样统一的?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精神境界?这都要由客观社会效果来检验。文艺是反映生活的,又反过来给生活以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15]由客观社会效果来具体衡量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从创作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这与第三种观点,即强调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是有相通性的。陈涌认为:“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他认为,“不能认为真实无情地揭露我们现实的矛盾和问题,揭露现实的阴暗面便会丧失社会主义的立场,便无法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同样,不能因为要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坚持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便认为只有歌颂光明,至于揭露我们现实的矛盾和问题,揭露我们现实的阴暗面,和社会主义立场、方向是不相容的。问题不应该这样理解。”[16]四是认为倾向性应该存在于真实性之中。刘冲一指出:“倾向性之于真实性,并不是作家任意外加的,而是生活本身固有的。重要的是作家能否自觉地认识它,能动地反映它。”[17]陈涌也强调了真实的生活与倾向性的固有关系,他认为,“我们要求的是艺术的真实性和社会主义倾向性的一致,但社会主义倾向,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本来存在的,我们作家的社会主义倾向应该看作是现实生活本来存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一种反映和提高,又转过来融汇到艺术创作中去”。[18]这种强调通过真实生活来表现倾向性的观点,在许多理论家那里都有共鸣。对照以上相关讨论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基本都是一致的。 1985年以后,由于大家在认识上已经比较一致,加之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与影响已逐渐占据理论的主导地位,关于文艺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的讨论也就越来越少了。进入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大力推行,已使人们不再将文艺的道德与政治书写当成必然的内容,艺术上的追求与创新在金钱的助推之下也已显得无足轻重,作品的真实性和倾向性被人们抛在了脑后。上天入地,胡编乱造,虚无历史,解构传统,只要能吸引眼球,只要能创造效益,没有什么内容不能写,没有什么底线不能破。 今天的许多文艺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在内,有的不讲真实只讲倾向,有的过于追求真实而忽视倾向,既不能很好地处理真实和倾向的关系,又不能真正理解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创作真谛。笔者认为,近年来在创作倾向上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想,是文艺创作的重要病症之一,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里对此作一专门讨论,以引起注意。 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应该传播主流思想,但倘若背离艺术创作规律,忘记了艺术如何化人的真谛,恐怕就会走上滑稽可笑的境地,更遑论对正确思想的传播与引领。2014年推出即备受诟病的网络季播剧《盗墓笔记》,就属于这一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盗墓笔记》本是网络作家南派三叔创作的系列探险悬疑小说,自2006年在网上连载以来,获得百万读者狂热追捧,南派三叔也因此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超级畅销书作家,2011年更是以158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位。借此东风,2015年6月12日,网络季播剧《盗墓笔记》也在“稻米”们千呼万唤下闪亮登场。然而与小说所引发的狂热相比,该剧却出师不利,非但没有受到原著爱好者的追捧,反而招来了众多网民的质疑。在该剧中,出生于盗墓世家的男主角吴邪被塑造成为一个文物的誓死守卫者,总会不厌其烦、随时随地向身边的人宣讲“把文物上交给国家”的理念,以至于很多观众纷纷呼吁“不如把编剧上交给国家吧”。 这种现象在近年来的文艺作品、影视剧创作中绝非个案,一系列的抗日神剧都在不断地试探着观众的底线。诸如“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隔空打人”、“自行车反物理制敌”、“全裸女敬礼”等剧情的设计,与其说是在警醒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激起人们的爱国情怀,不如说是在颠覆真实、哗众取宠、戏耍历史。在这些剧作中,充斥着一种过于绝对的正义无敌。这些雷人剧情,让本来真实的历史事实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实,让生动鲜活的抗日故事反而变成了消食取笑的娱乐资料。与上述现象如出一辙的,还有201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类节目。被称为2015年春晚“反腐三驾马车”的《投其所好》、《这不是我的》、《圈子》三部作品,创作者的初衷是好的,然而播出之后之所以褒贬不一,就在于作品对丑陋的鞭挞方式,对正能量的宣传尺度,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虽然在艺术的政治倾向性没有问题,但由于过分追逐思想倾向的正确性而忽视了在艺术表现上的真实性,对所表达思想的抽象化处理、概念式解读等,都使这些作品难以达到预想的社会效果,不仅达不到弘扬正能量的宣传效果,反而容易引起人们对“正能量”类节目的反感与误判。 不可否认,文学作品应该去歌颂人类一切美好的情感、精神和品德,去揭露和批判落后、丑陋和邪恶;真正有责任的艺术家,也应该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情感。任何作品,都应该表现作者某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或追求,一直以来,这也是有良知的艺术家们所共同遵奉的信条。文艺创作应该具有某种思想上的倾向性,这是艺术的本质规律之一,是任何人都无法违背的。如马恩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必然会在思想观念或行为处事上带有一定的阶级立场,作家也不例外,在文艺创作中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映出某一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就使得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具有某一阶级的思想倾向性。没有一定倾向性的文艺作品是绝对不存在的。由此可见,不管是《盗墓笔记》,还是鼓吹抗日英雄天下无敌的抗日神剧,抑或把反腐进行到底的春节联欢晚会相关节目,它们的确都在传播一种正确和进步的思想理念,都在歌颂人类美好的精神和品格。 然而,如何把一种坚定的立场、可嘉的精神传递给艺术欣赏者,却并不依赖于喋喋不休的说教、过于裸露的表白,或者歪曲事实的浮夸。一味地“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的“倾向性”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容易导致人物形象的扁平化,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一个“完满而富有生气的整体”(黑格尔语),人物的个性被消融到了作家的“主观规定”之中,而成为一个“过于完美无缺”的理想化身或阶级代言人。如《盗墓笔记》中的男主人公吴邪或者抗日神剧中的豪侠们,他们脱离了自己的个性与成长的典型环境,导致这些人物“虽长厚而似伪,虽多智而近妖”(鲁迅语),成为被“炮制的英雄”。二是情节设计的虚假化,由于创作者急于表明立场,再加上本身生活体验的缺乏,在情节的安排上就难免脱离生活实际和艺术真实,表现出创作上的唯心主义倾向,以至于不得不用一大堆矫揉造作的修饰来掩盖并非合情合理的情节发展。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言,“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被人看穿的命运”,[19]甚至会被认为“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20]其三就是故事结局的套路化,为了宣扬心中的理念,而忽视了叙事上的艺术创新。 其实,真正融于生命中的道德情感,会恰如其分地内含在作品的细节中,而不需要随时随地干瘪地说教。那些以一种先在的预设,把自己的主观见解与创作意图强制性地捆绑于作品之中,则必然适得其反。当然,纵观当下诸种文艺怪相,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文艺工作者严重的急功近利思想。为了获得所谓艺术上的“成功”,贪图名利,以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话题作为噱头;甚至有些时候,为了达到某种自私的目的而不惜牺牲作品的思想价值或艺术魅力。如《盗墓笔记》的编剧就坦言,“上交给国家”的设计,仅仅是为了便于影片通过审查。[21]殊不知,这样的做法最终会自掘坟墓,适得其反,既违背了创作规律,又伤害了正面价值的宣传,不能获得观众的喜欢。 宣扬正确的价值观,是文艺作品的天职所在;但过于急功近利的表现方式,急于求成,让主题先行,就不仅伤害了作品,伤害了观众,也最终伤害了艺术。这种被马克思称为“席勒式”的艺术创作,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主观观念出发,以主观的热情代替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观察,以抽象的观念演绎代替对现实关系的真实具体生动的艺术描写,“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22] 伟大的时代带来伟大的机遇,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言,“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23]今天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抓住机遇,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要处理好文艺的艺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切忌急功近利,真正将“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融化在对人民真实生活的了解中和对艺术表现手段的追求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