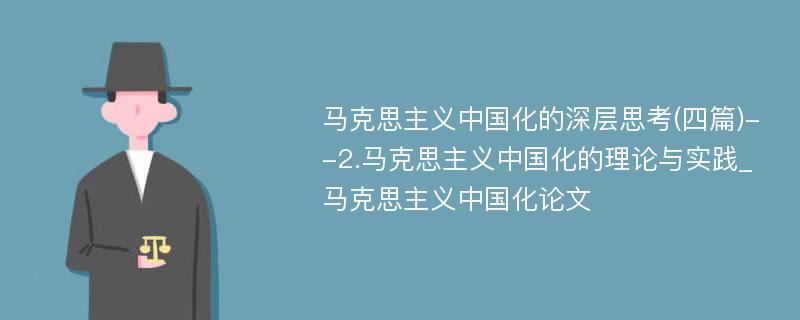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思考(四篇)——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深度论文,理论论文,四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标志着一种思想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实际经历的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实践,这一实践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确切些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不过是这一历史性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因此,中华民族已然经历并且正在经历的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实践,从根本上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讨论,特别是那些字面上的争论,就会是表面的、空疏的、无关宏旨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就是与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和根本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与应答和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的历史性实践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的。关于这种情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概要地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这个概括虽然十分简要,但却是深得要领的。其正确性根本不在于某种属于考据学或校勘学性质的精确性,而在于它揭示出历史的真正客观性的那个方面。只是依循于这样一种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方始被理解为近代中国之历史性实践的一部分,而这一学说之成长起来的本质重要性方始表现为我们的历史性实践的结果。人们当然能够很容易证明: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这里牵涉到的历史之客观性的真正要点在于:必须把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枢纽来把握,因为正是通过这一枢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学说才以实际地参与并开启我国历史性实践的方式客观地显现出来。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也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实践相联系的,并且是作为这一实践的结果而形成和发展的。1938年,毛泽东在他代表中央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给予了原则性的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决不仅仅是单纯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毋宁说,它是承载着历史现实的全部重量的——既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全部经验和教训,也承载着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全部苦难与探索。只要认真地回顾一下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哪怕是只要认真地回顾一下这个历史进程中的若干重要时期,例如红军长征前后的时期,或改革开放前后的时期,我们就能充分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全部历史重量。这个概念决不是空疏的抽象,其历史重量来自于它的实体性内容,而这种实体性内容是由中华民族的近代苦难、由无数志士仁人的艰辛探索、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道路上的不懈奋斗所构成的。离开了这种实体性的内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谓概念讨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空洞无谓的。一位当代哲学家曾经感叹说,在以往的哲学史中居然看不到人类的苦难——这是哲学的耻辱;而这个卓有见地的说法同样适合于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讨论。
然而,确实有一些观点试图完全脱离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便或者用“假设历史”的方式,或者用所谓语文学、术语学或逻辑学的方式来“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以至于最终出现了这样一种概念讨论:它企图以不可能有中国化的太阳和月亮、不可能有中国化的数学和物理学作为论据来指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悖谬。撇开其他的因素不谈,即使仅就理论方面而言,这种所谓的概念讨论连自然和社会历史的一般差别都分辨不清,却试图把作为历史实践一部分的政党主张同荒谬地试图阻止月食到来的“月食党”的幻想混为一谈。这种讨论方式的要害是使概念的实体性内容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仅只留下一个完全抽象的和形式的概念外观。如果以为只有这种抽象的形式——由于它是中立的、中性的、与内容无关的——才是真正客观的,那就大错特错了。黑格尔早就把这种无内容的概念空壳作为外部反思的形式而归入主观思想的范畴,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抽象的形式根本不可能深入到真正的实体性内容中去,所以它只是被用来“随便谈谈你个人的想法罢了”。而德罗伊森则更加尖刻地把这种完全空洞的客观性称之为“阉人般的客观性”。
我们的意思决不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或主题完全不必做什么学术讨论。恰好相反,这个主题上的学术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事实上它还开展得很少,而且开展得还很不充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完全不能脱离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不能脱离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所生成的实体性内容,否则它就不能不犯时代的错误——至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来讲是如此。因为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彻底瓦解了思想、观念、理论等等(也包括学术)的纯粹自律性,并把深入地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规定为自己最关本质的理论取向。很显然,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取消学术,而是提出一个更高的——确切些说,具有原则高度的——学术任务。因此,举例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只有深入到由一定的历史性实践所构成的社会现实中,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由这种现实所规定的理论的需要以及这种需要的程度;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③
不难看出,这里所提示出来的正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而这个基础是以深入到一定的社会现实由以显现的历史性实践为取向的,并且是以依循这一取向而综合全面的历史内容(包括各种意识形式以及文化传统等等)为目标的。同样不难看出,脱离或放弃这一基础的学术研究虽说未必完全没有成绩,但却实际地疏离了历史的真正客观性。在这种情形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就可能仅仅满足于某种主观的、无内容的抽象,甚至流于某种经院式的争论。就这一点而言,蕾蒙·阿隆对萨特和阿尔都塞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说,这两位学者与其说对历史现实感兴趣,毋宁说对哲学的先天条件感兴趣: “他们考察的问题看起来不是马克思的著作或思想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称之为康德的问题,恩格斯可能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可能的?”④
最后,可以简要地概括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应当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既标志着一种思想理论,又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实践。而这种在概念中得到表征的联系,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在现实中展开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在这个历史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彼此呼应、彼此孕育、彼此生成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表现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它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包括“使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与转化,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理论需要之直接成为实践需要时所说的那样:“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⑤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④蕾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9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标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