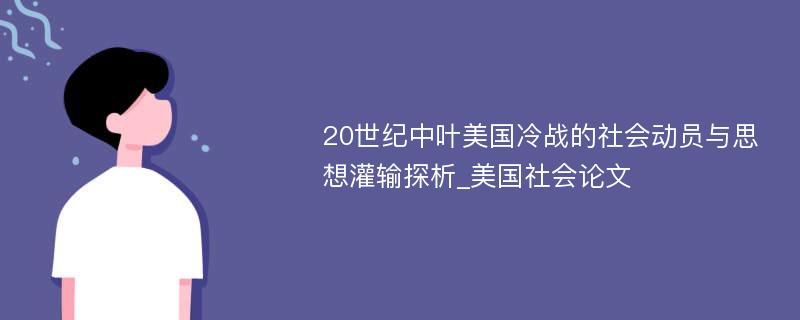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冷战社会动员与思想灌输活动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美国论文,冷战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动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日趋巩固的苏联政权和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危机感受日益加深。这一时期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文件,虽然形式和内容多有变化,却无不渗透一种思想,即要尽量降低战争的风险,同时千方百计削弱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优越于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号召力”。①从杜鲁门到肯尼迪,美国历届总统在公开讲话或内阁会议中均强调冷战是“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②换言之,是意识形态之争。通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较量与思索,美国决策层内部对东西方冷战的性质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进而认定,“在总体战得以避免且共产主义颠覆被有效反击的情况下,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最终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影响人们的态度和立场”。③可见,意识形态因素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冷战进程或大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事实上,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美国进行冷战斗争的工具和目标。 战后国际紧张形势的存在,使美国社会出现了异常一致的反共思潮和对行政机构构建“国家安全机制”的认同,即“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有学者研究认为,1950—1965年间,70%—80%的美国人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在总体上支持行政机构反击共产主义的各种“国家安全努力”。④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种美国国内舆论空前一致的现象多有关注和探讨,但对“冷战共识”产生过程中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联手进行的冷战动员和思想灌输活动则缺乏深入的研究。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战斗的自由”(Militant Liberty)项目为研究个案,通过梳理冷战初期美国在全社会开展冷战动员和思想灌输这一特殊的历史片断,试图说明:(1)“冷战共识”是由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共同“打造”出来的,其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内部风险,二是为了动员美国民众参与到这场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中;(2)“冷战共识”构建过程中的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灌输已经触碰到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原则”底线;(3)不可否认,恐惧和焦虑是美国精英用来整合公共舆论的有效手段,但要理解诸如“战斗的自由”这样的项目产生的根源和运行的机理,恐怕还要触及美国人特殊的安全与危机意识,以及美国文化中的优越感与使命感。没有上述思想基础,就难以解释战后初期美国社会激进保守主义倾向占据上风,以及迫切需要某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根源。 一、“战斗的自由”理念的缘起 正如历史学家熟知的那样,战后初期美国社会又惯性地滑向“孤立主义”,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下降。随着欧洲局势的发展(东欧各国和法意两国共产党及左翼力量的壮大)和1949年“两大冲击”事件(苏联成功试爆核武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发生,美国政府开始担心自己无法集结起有效的力量来应对这场“国家安全危机”。社会精英亦不失时机地提醒行政机构:美国有从内部被颠覆的风险,美苏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战”;糟糕的是,“美国人并不了解世界形势的严峻性”,因此,必须加大对民众的宣传力度,“以便使行政机构应用必要的激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局势”。⑥至少从1948年起,美国政府就与私人基金会、大众媒体、商业团体、社区组织、教育机构、教会与宗教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共同营造一种“红色恐怖”的社会氛围。⑦“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结果而非起因。 与此同时,美国带有优越感和使命感的特殊政治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精英们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的冷战目标不仅是守住所谓“自由世界”的阵地,更要尽一切可能扩大美国价值观念的统治范围,进而完全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达此目的,必须武装美国民众的头脑,并使每一位美国公民都成为冷战的“斗士”。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汤姆·克拉克很早就说过,“那些不相信美国意识形态的人,不应当被允许留在美国”。更多的人则试图论证,在冷战当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承担其责任……只有每个人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自由才能够生存”。⑧上述想法得到美国最高决策者的认同。1953年,美国新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不应该仅仅告诉民众影响我们安全的危险是什么;更应当向其解释我们正为反击危险所做的事情”。⑨其后,在筹备“人民外交”项目(People-to-People Program)时,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这场敌对生活方式之间展开的宏大斗争中,我们美国的意识形态若要取得最终胜利,就必须得到成千上万独立的私人组织和团体,以及美国公民个人的积极支持,通过你们与国外公民间的联络(来传递我们的思想)”。⑩ 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恐慌氛围。应该说,到1953年朝战结束时,美国精英阶层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反击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事业,必须努力让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接受某种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成为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使者。这一时期,在所谓“朝战战俘事件”的刺激下,美国的反共策略变得更加激进,美国社会对于思想灌输有了更大的宽容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动员美国民众、强化美国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战斗的自由”项目并非突如其来,同“麦卡锡主义”一样,它也是美国社会激进反共思潮的产物。 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的一个重要片断。1953年,经过漫长的谈判,交战双方终于就交换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在正式交换战俘时,有21名美国士兵拒绝回到美国。处于冷战对抗的高峰时期,此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在冷战背景下,急于提醒美国民众警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威胁”的美国政治精英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朝战战俘丑闻”由此发酵。在很短的时间内,关于美国战俘在“中共的心理灌输下叛变”的消息传遍美国,所谓“通敌”士兵的数字也由实际上的21人一度被夸大为2300人。(11)媒体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和民众相信,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的被俘士兵最终通敌”。(12)美国国防部在组织调查之后,将这一“丑闻”的出现归因于美国士兵在投入战场前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和心理准备,“美国的家庭、学校、教会和社区没有教会美国公民有关忠诚的责任”,士兵们也没有为应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做好准备。(13)对士兵来说,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或许已经深入骨髓,但却无法言明。所以当他们面临共产主义审讯者时,“很沮丧地发现,自己的美国信仰没有什么逻辑结构”。(14)艾森豪威尔本人对“朝战战俘事件”的总结为,美国青年人并不具有“何为美国,以及美国为何而战……的知识”。(15)“朝战战俘事件”使美国政府内部一直酝酿着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纷纷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战斗的自由”是其中备受瞩目的一项。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初期美国社会由“恐共”、“反共”转到“激进反共”的进程中,军方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麦卡锡主义”的衰落与其将政治矛头指向美国军方有重要关联。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军方亦充斥着赞同激进反共策略的官员。有学者研究表明,美国五角大楼总体上认为西方国家在“共产主义渗透”的威胁面前反应软弱;认为军队在冷战时期应当承担起“道德的和爱国主义的”责任;认为美国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防御共产主义,“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心理上”。(16)自1947年杜鲁门政府创建“国家安全机制”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借机参与到和平时期国家政治与外交事务的决策中。参议员麦卡锡对国防部反共产主义不力的批评和指责,虽然给美国军方带来一定的困扰,但也适时为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推动其决心用爱国主义和强大力量来防御共产主义的侵袭”。(17)这实际上为美国军方在和平时期介入公众生活奠定了根基。 “战斗的自由”理念最早由美国福音派传教士约翰·布鲁格(John C.Broger)提出。(18)布鲁格是一个极端反共主义者,早期负责远东广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的创建与运营,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防部“武装部队信息与教育处”(Armed Forc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主任。与同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各种反共理念不同的是,布鲁格认为美国必须有一套关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简明易懂的准则。这样,思想才能成为有效武器,方便美国各组织和机构对内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为达此目的,布鲁格归纳出一整套“战斗的自由”原则,目的是使“8年级以上阅读水平的美国人都能够掌握这个单一的、简明易懂的意识形态思想的主线”。(19) 1950年,布鲁格与后来出任参联会主席的亚瑟·雷德福(Arthur W.Radford)会面,两人在反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方法上不谋而合。雷德福后来成为“战斗的自由”理念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美国人需要一套概括其生活方式的教义或问答集,以便与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辩论。雷德福认为不只美国的士兵要为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战斗,“处于当前的危险当中,每一个美国人都必须献身于这项事业;必须团结起来反击好战的国际共产主义,以及任何危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力量”。(20)“朝战战俘事件”的发生最终为布鲁格和雷德福两人所倡导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提供了动力。事实上,在没有得到最高决策层同意之前,雷德福已经在其职权范围内开始推广“战斗的自由”理念,并着手开展灌输活动。 根据最终形成的“战斗的自由”文本,“战斗的自由”理念由一系列“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组成,是对自由理想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的标准是要“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实践或者集体展示积极的自由哲学”。(21)“战斗的自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所谓“战斗的”是指,“自由世界”的每个公民要处于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随时宣讲并解释自由的真义。包括布鲁格和雷德福在内,美国精英虽然相信自由意识形态更为优越,但却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活力和动力。为此,“战斗的自由”要做的就是激发自由意识形态的动力,使“自由”成为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有活力、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其二,“战斗的自由”强调“自由”(Liberty)是附带责任的“自由”(Freedom)。布鲁格认为,“自由”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各种“自由”权利,一部分是保证自己和他人实现自由权利的警戒性责任。换言之,“自由世界”的人们不仅享有“自由”,还有强制性的责任保证“自由”的推行。为此,布鲁格罗列出十项基本自由与十项基本责任,并声称这是全世界人民“无论其文化传统,无论其社会风尚”都应当遵守并享有的。其三,“战斗的自由”文本通过对比的方法分析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弱点”,以及“自由世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弱点”;设定了“自由”的基本准则,并号召用一切可行方法积极鼓励那些“欲实现自由的人们”向着这个目标前进。(22) 这本18页的名为“战斗的自由”的小册子极其粗浅地分析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两大思想体系的本质内涵,并简单总结出一系列的原则教条。尽管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不断有人指责其幼稚、可笑,它仍然为许多人认同并接受,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军方对国内外实施意识形态灌输活动的理论基础。(23) 二、公众思想灌输计划的实施 从冷战初期各种危机事件,特别是从朝战结束后的国际舆情和国内政治动向中,美国精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冷战开始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舆论中处于被动境地,这不是由于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够好,或者共产主义更为优越,而是由于美国没有发动有效的反击,“事实上,共产主义……面对有效的反击将毫无抵御能力”。(24)“战斗的自由”的出现适时为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方法和工具。正像布鲁格自己宣扬的那样:它提供了一套有关“自由”的最为简洁的表述方法,“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够很快理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通过热情的宣传和可靠的支持来清晰阐明这一原则”。(25) 从理念走向行动 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为方便冷战政策的推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组建了一个“行动协调委员会”(OCB),专门负责国家安全层面政策的协调与执行,并在实际上承担起反共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的主要责任。(26)布鲁格和雷德福非常清楚他们必须得到“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认同,才能使“战斗的自由”成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战计划,并获得最为广泛的资源和影响力。1954年10月,美国国防部以备忘录的形式呼吁立刻将“战斗的自由”理念转化为行动,“与美国当前实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项目结合在一起……”(27)11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了一份行动大纲并提交给了“行动协调委员会”。这份行动大纲最全面地揭示了美国军方欲将“战斗的自由”理念推广的深度和广度。大纲当中,美国行政机构各个部门都被分派了任务:由中情局负责,分析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并就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弱点、目标和“惯用伎俩”做出评估;由“行动协调委员会”主持,国务院、国防部、美国新闻署、中情局和援外事务管理署(FOA)负责,将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项目和意识形态项目整合到一起实施;由国务院、美国新闻署和中情局负责,就相应的训练和行动项目提出计划,等等。(28) 1954年12月,在雷德福的推荐下,“行动协调委员会”听取了布鲁格就“战斗的自由”理念所做的简况汇报。在当日的会议上,“行动协调委员会”决定由美国新闻署牵头成立一个“OCB特别工作小组”,就即刻将这一理念付诸实施提出建议。其后三个月间,“行动协调委员会”成员机构间就“战斗的自由”项目展开激烈的争论。最终,在总统特别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协调下,“战斗的自由”理念得到部分认可。参谋长联席会议仍被指令承担主要责任,“与相关机构协同实施这一计划”。(29) 美国国防部为“战斗的自由”制定的行动计划纲要表明,该项目的目标是:巩固美国的传统与理想;统一美国的公众舆论;提供一种既支持美国的政策和目标实现,又与其他“自由国家”目标相一致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既为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提供合理性,又要避免美国过早陷入于己不利的承诺中;为“自由世界”的团结和力量确立道德基础,与此同时消除那些关于美国是“好战者、物质国家、利益至上者”的指责。(30)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军方与社会中的反共力量结合,在事实上进行了一次目的清晰明确、方法手段多样、目标群体广泛的意识形态灌输行动。 冷战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计划的实施 从项目实施的难易程度上看,由于有国防部高层的支持,“战斗的自由”项目在军队中最容易推行。事实上,军队的组织模式和动员机制非常便于学说思想的灌输。朝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军方就根据“战斗的自由”理念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名为“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该项目的目的在于,使每一个美国青年,在面临类似朝鲜战争战俘营那种情形时,要坚持下来。(31)1955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要求武装部队的所有人员都要牢记并遵循“行为守则”,以便在战斗中或被俘时的行为能够符合守则规定的标准。从“行为守则”的第一条——“我是美国人,为了我的国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斗”(32)——可以清晰地读出“战斗的自由”原则。 除了现役军人,美国国防部还掌控着庞大的预备役士兵教育系统和军事院校教育系统。从1954年底开始,美国国防部已经指令将“战斗的自由”原则贯彻在武装部队预备役计划(AFRP)、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计划(ROTC Program)、军事信息与教育项目、心理战及其他特殊项目中。1955年,国家陆军学院、空军军事学院,以及其他陆海空军学院和研究机构的课程也加入相关的学习和研究计划。(33)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名为“洗脑”(brainwashing)的研究项目。参谋长联席会议遂与中情局合作,希望不仅可以探索对敌人进行意识形态“洗脑”的方法,同时也可以使美国的士兵在面对类似朝鲜战争那种极端情形时,能够抵制住共产主义“解释”或宣传的影响。(34) 然而,布鲁格和雷德福并不想让“战斗的自由”项目局限于军队系统内部。项目从开始设计就强调要在社区、家庭和学校开展冷战危机宣传,并为美国民众提供相应的培训。因此,在武装部队展开“战斗的自由”训练的同时,美国行政机构通过私人组织、宗教团体、学术机构和互助会等方式“向自由世界……的人们推销(这一理念)”的活动亦铺展开来。(35) 1955年6月,在国防部长威尔逊的支持下,美国国防部召开了一个由商业界、教育界、法律界和媒体精英参与的特殊会议,专门讨论“自由世界意识形态的有利方面”,实际上是围绕着布鲁格的“战斗的自由”理念展开了全面的探讨。(36)威尔逊还亲自出面,邀请其他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探讨“就美国生活方式进行更有效的训练的可行性”。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劳工部、商务部、农业部和美国商会均参与了项目合作。为“战斗的自由”项目准备的宣传材料也提供给这些机构用于他们各自的实地活动,“特别用于强调美国公民训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37) 1957年初,美国国防部与负责可口可乐和通用汽车广告营销的“杰米·汉迪”公司(Jam Handy)签订合约,希望其能以产品宣传的方式将“战斗的自由”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该公司不负所托,很快策划出一套“既可广泛传播,又适合多层次使用”的系列宣传片,名为“为自由而战”(Battle for Liberty)。该宣传片包括7个幻灯片、7卷录音带和7份手册。宣传片的主题涵盖挑战(共产主义)、宗教、经济秩序、教育、公民、社会秩序、法律和规则等多个领域。(38)该公司同时承担起宣传片的推广任务。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宣传活动是在1958年,借着庆祝美国“忠诚日”(39)的时机,该公司与海外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合作,将“为自由而战”系列宣传片送到美国地方学校和社区中心。(40) 20世纪5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美国社会组织、大学和学院,以及各种基金会参与到对普通民众的冷战动员与思想教育当中,形成一种特殊关系下的利益共同体。参联会主席雷德福与著名的保守派教育基金会组织“福奇谷自由基金会”(Freedoms Foundation at Valley Forge)取得联系,借后者推广“战斗的自由”理念。(41)美国军方与私人组织“美国安全委员会”(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出版了《核时代的美国战略》一书。该书极力宣扬美国要与共产主义展开一场进攻性的“持久战”,并且为赢得最终胜利,美国公民和美国政府的领导者都要在“心理战”院校中接受有关“自由”思想的训练。在私人组织的运作下,有1万册之多的《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流通到各公立院校图书馆和社区组织中。(42) 然而,正如“战斗的自由”的批评者频繁指出的那样,美国公众不太接受严肃的灌输活动,因为他们或许不会感兴趣。(43)因此,利用好莱坞电影来渗透“战斗的自由”思想成为项目实施者的又一重要灌输手段。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说过,“最好的宣传就是没有宣传”。(44)对此,美国军方早有深刻理解。1954年美国参联会的米勒德·扬(Millard Young)将军在与加州大学戏剧学系的乔治·萨维奇(George Savage)教授会谈时提到“许多人只有通过戏剧媒介才能被‘打动’”。(45)好莱坞电影无疑是渗透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观念,又不会引发公众反感的最佳途径。中央情报局最早开始利用电影媒介来向美国民众和海外观众渗透意识形态思想,甚至有常驻派拉蒙影业公司的代表。利用所谓“好莱坞公式”,即说服电影导演用影片展现一个“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美国”,中情局把“战斗的自由”很好地融入到其已有的好莱坞行动中。(46)1956年6—7月间,参联会亦派出代表与好莱坞导演及演员们会面,共同商议“如何借助好莱坞电影传播‘战斗的自由’理念”。参加会谈的有约翰·福特(John Ford)、约翰·韦恩(John Wayne)、沃德·邦德(Ward Bond)和梅里安·库珀(Merian Cooper)等知名导演和演员。(47)他们一致同意,通过拍摄电影来“揭示共产主义控制下的社会现状……解释自由世界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极其必要的。(48)事实上,尽管这一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谈不上是为美国政府服务,但的确有助于美国民众反共意识形态的整体确立。 同冷战前期美国社会诸多类似的反共思潮和反共项目一样,“战斗的自由”从一开始就面临各种质疑。然而,美国社会普遍的反共产主义思潮,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需要”,为该项目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一大规模对国内民众进行公开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宣传活动,才在美国国会的干预下逐渐终止。“战斗的自由”没有贯彻下去的原因,下文将详细论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战斗的自由”并非孤立存在,它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潮主导下的众多反共意识形态项目中的一项,其对美国内外决策的潜在影响力仍将长期存在。(49) 三、美国社会动员与灌输活动的特征与禁忌 以“战斗的自由”项目为个案,我们可以一窥冷战时期美国规模庞大的反共宣传与灌输活动冰山之一角。尽管近年来陆续解密的档案文献已经将美国开展的种种“黑色”冷战策略与手段逐步揭示出来,但其对美国民众实施如此广泛而公开的舆论操纵和学说灌输活动,仍然令人惊叹。选取“战斗的自由”为研究个案,除了源于它是冷战压力下美国社会氛围与极端思潮的产物,有一定的代表性;还因为这一理念和项目一直游离于美国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边缘地带,既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广泛支持,又在危机舒缓时遭到质疑而走向衰落。同那些略为温和或更为激进的意识形态项目相比较,“战斗的自由”项目正好可以作为考察危机形态下美国“激进”思潮之界限与尺度的一把钥匙。 “国家意识形态”:从多元到一元 前文提到,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美国需要一个哪怕是非常宽泛界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便于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进行斗争。然而,对于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传播的途径,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 早在杜鲁门执政时期,以保罗·尼采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在起草“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时就已经意识到,为了击败共产主义,美国“除了展示自由思想的优越性之外,别无选择”。(50)尼采及其支持者甚至认为,这意味着必须提出一个与共产主义相对的“美国意识形态”,哪怕这会有损美国社会的多元主义。(51)这些想法无疑是对社会精英的应和。当时,美国社会正就“美国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讨论。有人认为它应当是“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由一系列思想和信仰组成,并带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一个合格的美国人应该能够帮助国家保卫我们珍视的自由”。(52)有人认为它是处于不断界定和确认当中的“美国生活方式”,“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政治生活中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以及经济生活中的私人企业制度,都要被调适以应对冷战危机”。(53)还有人提出了“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的概念,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种生活方式”,(54)目的是消除传统资本主义的一些负面因素。 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由于他对动员美国公民参与冷战斗争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一时期,美国的“意识形态战”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影响来说,都发展到了极致。早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艾森豪威尔就支持哥大师范学院创立了一个名为“公民教育工程”的项目,(55)组织一批知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共同提出了一个“美国自由之前提”(Premises of American Liberty)的列表。数个高校图书馆联合提交了一个用以支持“美国自由之前提”的书目清单,并借助哥大师范学院的声望向外推广。(56)可见,艾森豪威尔在界定“美国意识形态”时,仍然注意保留其多元文化的内涵。受其影响,“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制定“意识形态战”(57)项目时,特别强调该项目并不试图提出一个有关“自由社会”的统一学说,更不会提供一种学说教条。相反,“意识形态战”试图尽一切努力说明的是,“自由社会的原则可以在所有文明中以不同的方式有效运行”。(58)尽管如此,其言下之意已经表明,为了项目顺利推行,美国仍然需要一套有关“自由社会原则”的说教。 事实上,从美国社会特征来说,很难有人能为“国家意识形态”制定一个广为接受的标准,但冷战的压力又使制定这样的标准有迫切的需求。“战斗的自由”提倡的就是一种学说教条。它倡导一元式的、简明易懂的“国家意识形态”,以更好实现“洗脑赢心”的冷战目标。在朝战影响下,它得到决策层相当多人的支持,并被短期归入“意识形态战”项目管理。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意识形态战主张。随意翻查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文件会发现,当布鲁格提出并推广“战斗的自由”理念时,美国社会内部,从行政机构各部门到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都在思考或酝酿类似的建议,甚至美国大学、社会团体、各种基金会和压力集团也不约而同地开出各种激进主义的冷战处方。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个名为“奥兰多委员会”(The Orlando Committee)的地方组织向美国国会提出反共产主义的立法建议,并得到国会重视。(59)“奥兰多建议”与“战斗的自由”理念相似,也是主张要总结出能够与共产主义对抗的一套一元式的思想体系。(60)其时,美国国会充斥着一大批激进反共的议员。他们对行政机构的反共策略,反击共产主义的坚定性和主动性都提出了质疑。(61)“奥兰多建议”很快被国会采纳,并作为“自由委员会”立法提案提交参众两院审议。提案主张,美国以立法形式建立一个“自由研究院”,其不仅要“研究有关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系统知识”,而且要“将反击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手段发展成实用科学”。(62)换言之,如果立法获得通过,美国将出现一个法律上承认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处于冷战对抗高峰期,“自由委员会”提案有大批议员支持,还曾在参议院顺利通过。(63)其后冷战形势发生变化,提案虽然频繁付诸表决,但始终未能再次赢得足够票数。 社会动员与学说灌输:从消极到积极 在战后初期美国的社会动员与学说灌输活动中,还有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是关于打造反共“舆论共识”,以及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途径问题。如前所述,在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看来,他们掌握着有关共产主义的信息资源,公众被普遍认为“缺乏辨识能力”,被视为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可以加以操纵的个体。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认为,动员公众舆论,对于抵御冷战士气消退的风险极其重要。无论如何,“国内舆论必须成为(冷战)战略的一部分”。(64)然而,在这些精英中却始终有关于实施“消极灌输与动员”还是“积极灌输与动员”的争论。尽管没有找到对两者进行清晰界定的文献,但很明显,前者是指一切常规的大众传播与“白色”宣传,后者则是指“黑色”宣传和带有官方色彩的灌输活动。 大众传播是塑造舆论的最佳方式。在这方面,美国政府与新闻媒体、影视媒体,以及教会和社区的合作不可胜数。其中,行政机构与广告委员会(65)的长期合作最为典型。自1948年起,广告委员会就与行政机构、美国私人基金会和多个宗教协会合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美国传统”和“美国生活中的宗教”等主题宣传活动。对美国人来说,记忆最为深刻的应当是“自由列车运动”(Freedom Train Campaign)和“地面观察队”(Ground Observer Corps)运动。前者在美国铁路沿线城市开展了一系列宣传美国历史文献的活动,其目的是“增强抵制内外共产主义宣传毒害的影响”;后者则是一个征召平民志愿者的活动。其假设苏联随时会对美国发动突袭,因此征召50万人组成志愿团队,在美国36个州建立19400个观察站,实施每周两个小时的侦察。当然没有一位志愿者发现真正的苏联轰炸机,但社会恐慌氛围却由此被调动起来,美国政府的民防政策也因此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66)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公民教育”也是有效的传播途径之一。他支持的“公民教育工程”获得卡内基基金会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资助,在美国许多学校付诸实施。(67)当选总统后,艾森豪威尔公开支持广告委员会有关“国防中的公民行动”这一主题宣传活动。在他看来,“灌输”的力量不可小觑。用几个月的时间,通过一个公民教育项目来最大限度地重复有关“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讲话要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完全理解。(68)与艾森豪威尔相同,美国精英非常依赖学校教育来实现其目标。“意识形态战”的项目指南明确表示,“那些因博学多识而备受尊重的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引导美国人民接受和支持那些正确的选择”。(69) 如果说上述活动都可以归为“消极灌输与动员”的话,“战斗的自由”项目则更多地偏于“积极灌输与动员”。在美国政府内部就“战斗的自由”项目展开辩论时,许多机构都认为,已有的或正在实施的“意识形态战”项目在基本策略上与“战斗的自由”理念没有什么不同。(70)它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战斗的自由”项目中包含太多“积极灌输或动员的成分”。(71)美国新闻署曾在其报告中详细列举该机构正在实施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与“战斗的自由”目标完全相同,只不过在项目实施中会“尽量避免暴露出美国官方参与的痕迹”。(72)言下之意,美国新闻署并不反对“战斗的自由”项目,而是反对其项目中提出的那种“公开的”灌输方法。曾在心理战略委员会任职的金特纳(Kintner)在国会作证时亦提到,行政机构内部在推行意识形态进攻战略时,“始终有一些成员争辩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生活方式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其很难被付诸行动”。(73) 与“战斗的自由”项目相比,“自由委员会”提案中的主张带有更为明显的“积极灌输”色彩。它不仅建议“在行政机构内部创建一个独立部门,负责研究并发展出一门综合的反击共产主义阴谋的实用科学,并培训政府官员、普通公民和外国学生掌握这门科学”;(74)甚至建议“创建一个信息中心,负责散布有助于了解共产主义阴谋并击败该阴谋的信息和材料”,而且要“生产并发行各级学校的教材以及其他反共素材”。(75)这实际上无异于公开的洗脑和思想控制。提案在国会拥趸众多已经令人惊讶,最终流产亦在情理之中。 激进反共策略:从宽容到质疑 总体来看,冷战前期美国政府与各社会团体联合推动的反共动员与灌输活动一直游离于美国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边缘。在国家安全危机的旗号下,这些活动得到相当程度的宽容和支持。来自不同方向的相似观念和主张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美国社会整体上处于一种普遍的危机感受之下,另一方面亦表明,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包含培植“激进”思想的成分。然而,时过境迁,当冷战形势趋于缓和,略显极端的意识形态策略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因而遭到强烈的质疑。 冷战前期,美国的反共宣传战和意识形态战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下,由国务院、美国新闻署(1953年以后)、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具体实施的,其长期目标是要“在世界范围内鼓励自由世界哲学与精神的广泛接受”。(76)这样一个庞大的思想工程必然需要美国私人组织和公众的理解和参与,这在历届美国总统的讲话中都有充分体现。NSC68号文件亦表示,为了击败共产主义,必须将“美国人的全部内在能量激发出来”。该文件宣称美国将通过“传统的民主程序”来实现这一目标,即首先为公众提供关于当前形势的充分的信息;接着在公众充分理解当前形势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最后在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出反击共产主义的国家意志。(77)然而毫无疑问,所谓“传统的民主程序”是不可能存在的。保罗·尼采承认,国家意志的形成需要美国民众“巨大的牺牲和严格的纪律”,这将迫使他们“放弃源于自由体制的某些利益”。(78) 在冷战特殊形势下,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战”项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推行得非常顺利,有行政高层的直接支持,有私人组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很少受到外界质疑。事实上,对行政机构实施“意识形态战”有直接约束力的《史密斯-蒙特法》(Smith-Mundt Act),最初并不禁止对美国公众进行宣传,甚至要求行政机构必须将对外宣传的素材和资料提供给国会、出版界、新闻杂志、广播系统等机构使用。(79)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行政机构从事对内宣传战和隐蔽战的活动引发美国社会广泛质疑,《史密斯-蒙特法》才得到修订(1972),明确规定美国对外宣传的素材和资料“不得在美国(本土及属地)传播”。(80) 比较而言,“战斗的自由”项目则触碰到了美国社会更多的政治禁忌。“政教分离”和“军事远离政治”这两项禁忌在冷战早期美国政府构建国家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81)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布鲁格的宗教背景、“战斗的自由”理念中的“新教福音主义倾向”,使该项目从一开始就招致批评。(82)中情局内部一份文件评价说,“它即便不会引发矛盾,也毫无价值可言”。(83)更严重的是,随着“战斗的自由”项目的铺展,军方太过公开地介入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灌输活动,引发了国会的关注。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很早就警告“美国右翼和军方正联合起来,超越其职权范围,塑造美国的公众舆论”。1961年夏,富布赖特向总统肯尼迪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发出一个私人备忘录,谴责“军方人员正从事宣传活动”。(84)其后接受国会质询时,富布赖特说道,“美国一向有一个深厚传统,即在政治事务上教育民众的职能不属于军方”。(85)1962年,美国国会就国务院和国防部涉嫌操纵公众舆论以及在军队中从事灌输活动进行调查听证。(86)“战斗的自由”项目自此走向衰微。 应该说,导致“战斗的自由”项目终止、“自由委员会”提案流产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其触碰到美国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底线”。“战斗的自由”强调唯一的或一元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张对内对外实施“积极的灌输与动员”;“自由委员会”提案则坚持在立法层面上,制定一个“科学的”学说体系,并在全国和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公开的”学说灌输活动。这些观念与美国文化多元性以及固有的“自由”理念相悖;在实践中,两者又对其政策意图和方法手段不加掩饰,最终导致其失败。 四、“安全”和“自由”的迷思 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战斗的自由”将公民责任与国家使命直接联系起来,向美国公民提出了“义务性”的要求,这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引发太大争议。事实上,诸如“战斗的自由”这样的激进冷战策略的产生,既有国际形势导致危机感的外部因素,又有来自美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因素。它们在满足美国民众的安全需求的同时,又迎合了其文化中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因而才能在突破“个人自由”原则底线的情况下,仍然获得生存的空间。 熟悉美国历史的学者大多能够察知美国人特殊的安全与危机意识。美国是一个追求“绝对安全”的国家。由于长期享有战略优势,美国公众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低,对威胁自身安全的敌对力量非常敏感。危机事件能够轻易凝聚国内力量,突破各种规则和传统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早期,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投入巨额资金推动社会科学家研究和完善“(思想)灌输法”。该基金会认为,如果要在未来几十年逐步推进“全球政府”的理念,就要用更为成熟的操控技巧来说服美国人民。而现有的大众传播媒介似乎“在塑造良好公民,或在‘冷战’中塑造积极的民主意识形态方面,并不见成效。”(87)这些研究的成果之一是,“恐惧,无论基于引导还是基于其他原因产生,都会使一个人倾向于屈从精英”。(88)在现实当中,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确经常利用夸大安全威胁等手段来激发美国公众的危机意识,以达成政策共识。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合力营造出多个“差距”恐慌,为美国政府的激进政策特别是飙升的国防预算寻求合理性,如“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卫星差距”、“教育差距”、“威慑差距”、“防御差距”、“技术差距”等。为了推行意识形态进攻战略,美国政府同样提出了“(学说)训练差距”(Training Gap)的说辞,(89)并借助其引发的恐慌发起各种带有激进色彩的反共产主义项目。无论是“战斗的自由”还是“自由委员会”提案,甚至“意识形态战”项目,其推崇的方法和手段都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相悖,却依然赢得了相当多精英和民众的支持。正如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公众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严重危机事件的态度时所总结的,“(其时)大众文化的所有分支都行动起来,似乎它们本来就是政府的衍生品……它们用一种声音说话”。(90)而美国总统小布什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安全与价值观之间的选择是极其现实的,通常情况下,安全是必然的选择。(91)这解释了当代美国为何会有激进思潮生长的广阔空间。 除了安全与危机意识,要剖解“战斗的自由”的思想根源,恐怕还要提及美国文化中的优越感与使命感。至少从威尔逊时代起,美国就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到杜鲁门执政时期,借助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冷战斗争,美国最终确立了“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其自身的优越感与使命感亦被无限放大。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3号文件中,美国政府宣称“他国民众发展并维持其对自身、对自由社会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美国的信任程度”,并且“环境与事态已经将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头衔加诸于美国身上”。(92)无论是广告委员会的宣传活动,还是“战斗的自由”的思想灌输活动,美国精英在打造“冷战共识”时都刻意强调反共产主义这一历史使命与公民责任之间的联系。美国式“自由”是附带责任的自由,不履行保护“自由”的责任就没有权利享有“自由”;必须“教会美国人有关爱国主义和道德领袖的传统价值”。(93)这是“战斗的自由”理念的基本出发点。这种优越感和使命感,正如“战斗的自由”文本开篇所言,“并非新生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美国人所‘信仰、传承和实践’”。(94)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随处干涉的话语中,“自由”与“责任”总会相提并论。1954年,“行动协调委员会”在筹划干涉拉美的行动时,这样论述其行动的合理性,“美国,作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赢得独立的殖民地,出于本能地理解依附者和被殖民者对于自由的渴望。美国的政策是帮助而非阻碍自由的扩散。美国过去是,未来仍然是,政治独立发展的支持者”。(95)21世纪初,当美国仍处于“9·11事件”带来的危机恐慌之下时,“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再度密切起来。小布什总统毫不掩饰地声明:美国的政策是“自信地”使用其巨大的影响力来推进“自由的事业”,因为“我们自由的生存越来越有赖于其他地区自由的成功。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来自于自由在全世界的扩张”。(96) 有学者认为,全球责任、民族伟大和反共产主义,这三个松散的意识形态组合弥漫于战后初期美国公众生活中,是美国社会“冷战共识”形成的主要原因。(97)应该说,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正是借助危机形势,通过激发美国民众的领导意识和责任意识,才处心积虑地打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空前一致的反共产主义思潮,并为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民意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才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需要明确的意识形态敌人和带有威胁性的敌人。它,值得我们付出勇气,可以使我们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团结起来”。(98) 注释: ①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NSC 135/3,“Reappraisal of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Strategy for National Security,” Sep.25,1952,PD00306,Database: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类似的文件还有NSC 20/4、NSC68、NSC162、NSC5422/2等。 ②Harry S.Truman,“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Greece and Turkey:The Truman Doctrine,” Mar.12,1947,in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2846; John F.Kennedy,“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Urgent National Needs,” May 25,1961,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151. ③Department of State,“New Dimensions of Diplomacy,” Dec.5,1960,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Papers of James C.Thomson,Jr.,Box 7,Chester Bowles;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6th Draft,Dec.1960,p.3,http://www.foia.cia.gov/helms/pdf/sprague_report.pdf. ④Milton J.Rosenberg,“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ld War Consensus,”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Mar.1981; Jack L.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255. ⑤利用解密文件对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实施的意识形态战(ideological warfare)进行系统学术研究,在中国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西方学术界也起步较晚。已有研究多将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看作是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没有美国国内的思想统一和舆论偏向,没有美国各组织团体的积极参与,意识形态战亦很难贯彻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学者对美国的内部学说灌输或意识形态灌输活动研究还有很大不足,对冷战前期美国社会整体上出现的激进思想倾向也没有很好的总结。此外,尽管美国有“信息自由法”(FOIA)和比较规范的政府文件解密制度,但对于解密过程控制仍非常严格,这是导致诸如“战斗的自由”理念如何得以贯彻这样的敏感信息仍大部分处于保密状态的主要原因。本文所言思想灌输活动包括从意识形态研究到一般学说在内的项目与活动,已有研究参见Scott Lucas,Freedom’s War: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 Kenneth Alan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2006; Frances Stoner Saunders,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New York:New Press,1999. ⑥Daniel Lee Lykins,From Total War to Total Diplomacy:The Advertising Council,Domestic Propaganda and Cold War Consensus,Dissertation,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1998,p.132. ⑦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如美国行政机构与广告委员会(The Advertising Council)合作,筹划并推出一系列以“增强抵制内外共产主义宣传毒害的影响”为目的的公共广告活动;影视媒体放映《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同谋者》、《红色恐怖》等影片;新闻媒体刊发有关“共产主义正试图瓦解美国”、“苏联发起憎恨美国运动”等消息。 ⑧Stephen J.Whitfield,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p.53-58. ⑨C.D.Jackson and Robert Cutler Discuss,“Age of Peril”Memo,Jul.28,1953,CK3100307104,Database: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Gale Group,Inc.. ⑩James Hagerty,“Press Secretary to the President,” May 31,1956,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http://www.eisenhower.archives.gov/research/online_documents/people_to_people/BinderV.pdf. (11)U.S.Senate,86th Congress,1st Session,“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for 1960: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Readex U.S.Congressional Serial Se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9,p.131; Lori Lyn Bogle,The Pentagon's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The Early Cold War,College Station,TX:Texas A & M.University Press,2004,p.119. (12)U.S.Senate,86th Congress,1st Session,“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for 1960: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p.131. (13)Secretary of Defense's Advisory Committee,“POW:The Fight Continues after the Battle,”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s Advisory Committee on Prisoners of War,1955,p.13,http://www.loc.gov/rr/frd/Military_Law/pdf/POW-report.pdf. (14)Christopher S.DeRosa,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in the U.S.Arm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Vietnam War,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6,p.150; Herbert Elliston,“‘Militant Liberty’:Words and Deeds,”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Jan.15,1956,p.E4. (15)Thomas Alfred Palmer,“Why We Fight”:A Study of Indoctrination Activities in the Armed Forces,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71,Database: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PQDT),pp.32-33. (16)Lori Lyn Bogle,The Pentagon's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The Early Cold War,pp.116-118. (17)Lori Lyn Bogle,The Pentagon's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The Early Cold War,pp.116-118. (18)冷战时期,美国教会和保守派宗教人士大量参与国内政治活动和冷战对外宣传活动。由于美国认定“自由民主”源于宗教精神,而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信仰又迥异于西方,因此宗教团体和教士在美国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19)Christopher S.DeRosa,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in the U.S.Arm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Vietnam War,p.149. (20)George Dugan,“Religion Called Key to Security:Radford and A.E.C.Head Stress Role of Faith in American,” New York Times,Oct.26,1955,p.16. (21)U.S.Department of Defense,Militant Liberty:A Program of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Freedom,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p.1. (22)U.S.Department of Defense,Militant Liberty:A Program of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Freedom,pp.2,4-5,10-11. (23)Samuel P.Huntington,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397. (24)Joint Chiefs of Staff,“Brief of Military Liberty Project,” Oct.22,1954,CK3100082153,DDRS. (25)Joint Chiefs of Staff,“Brief of Military Liberty Project,” Oct.22,1954. (26)Dwight D.Eisenhower,“Executive Order 10483:Establishing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Sep.2,1953,in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60573. (27)Joint Chiefs of Staff,“Brief of Military Liberty Project,” Oct.22,1954. (28)Joint Subsidiary Plans Division/Joint Chief of Staff(JSPD/JCS) Militant Liberty Outline Plan,Nov.5,1954,CK3100092981,DDRS. (29)“OCB Concern with Militant Liberty,” undated,CK3100007586,DDRS. (30)JSPD/JCS,“Militant Liberty Outline Plan,” Nov.5,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0,OCB 091.4 Ideological Programs(File #1)(8),pp.27-28. (31)U.S.Senate,86th Congress,1st Session,“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for 1960: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p.131. (32)Dwight D.Eisenhower,“Executive Order 10631:Code of Conduct for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ug.17,1955,in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9249. (33)JSPD/JCS,“Militant Liberty Outline Plan,” Nov.5,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0,OCB 091.4 Ideological Programs(File #1)(8); John G.Norris,“Plan Aimed to Promote Free World Principles:Concept Sponsored by Radford Already Being Used,”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Nov.22,1955,p.1. (34)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Memorandum for the Director:“Brainwashing,” Jun.7,1956,CIA-RDP80R01731R000300200018-2,Database:The CIA Records Search Tool (CIA CREST). (35)U.S.House,84th Congress,1st Session,“Department of the Army Appropriations for 1956: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p.853; John G.Norris,“Plan Aimed to Promote Free World Principles:Concept Sponsored by Radford Already Being Used,” p.1. (36)U.S.Department of Defense,Militant Liberty:A Program of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Freedom,p.i. (37)U.S.House,85th Congress,1st Session,“Department of the Army Appropriations for 1958: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582. (38)Thomas Alfred Palmer,“Why We Fight”:A Study of Indoctrination Activities in the Armed Forces,p.53. (39)美国“忠诚日”(Loyalty Day)是一个法定节日,时间为每年的5月1日。1921年,“忠诚日”为对抗共产主义“劳动节”而设立,但一直不受重视。直到1958年,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期,美国国会以立法形式加以确认,并明确其目的是为纪念“美国自由的传统”。“忠诚日”由此成为冷战的产物。 (40)U.S.House,86th Congress,1st Session,“Report of Chairman,Robert E.Hansen,National Loyalty Day Committee,Proceedings of the 59th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of the United States,August 17-23,1958”(H.Doc.84,Serial Set vol.no.12190,Session vol.no.9),Readex U.S.Congressional Serial Set,p.202. (41)“Radford and ‘Militant Liberty,’”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Jun.24,1957,p.A2. (42)Walter F.Hahn and John C.Neff,eds.,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Nuclear Age,New York:Anchor Books,1960; Sara Diamond,Roads to Dominion:Right-Wing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5,p.47. (43)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emorandum for the Executive Secretary:Problem of Cold War Planning,” Aug.26,1957,CK3100006492,DDRS. (44)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Power,N.Y.:Public Affairs[TM],2011,p.116. (45)“Letter from George Savage to General Millard Young,” May 7,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0,OCB 091.4 Ideological Programs,File#1 (2). (46)Alan Johnson,“The Cultural Cold War:Faust Not the Pied Piper,” New Politics,vol.3,Summer2001,p.140. (47)Tony Shaw,Hollywood's Cold War,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7. (48)Michael Fitzgerald,“Television Portrayals of Native Americans:From Tonto to Uncle Ray(1949-2006),” Left Curve,vol.31,Spring 2007,pp.129-138,144. (49)从现有材料来看,该项目在美国政府实施的对外隐蔽行动中存在了很长时间。当许多部门认为这个项目已经被“抛弃”时,美国国防部仍在拉美许多国家推行着“战斗的自由”理念。而项目的国内活动也没有遽然中断。布鲁格本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在担任“武装部队信息与教育处”主任,控制着国防部1000多个军事广播电台、电视台和2000多份报纸等宣传工具,足见其倡导的理念并没有遭到完全否定。详见“OCB Concern with Militant Liberty,”CK3100007586,DDRS; Deputy Chief,Psychological and Paramilitary Staff,“Memorandum for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Sep.27,1957,CIA-RDP80801676R001200130013-3,CIA CREST; Jeff Sharlet,The Family:The Secret Fundamentalism at the Heart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N.Y.:HarperCollins,2008,p.202. (50)NSC,NSC 68,“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14,1950,CK3100347913,DDRS,p.11. (51)Lori Lyn Bogle,The Pentagon's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The Early Cold War,p.84. (52)Jennifer Frost,“Hollywood Gossip as Public Sphere:Hedda Hopper,Reader-Respondents,and the Red Scare,1947-1965,” Cinema Journal,vol.50,no.2 (Winter 2011),p.91. (53)Stephen J.Whitfield,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p.53. (5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Report on a 6 Month Trip around the World to Study U.S.Propaganda Overseas,” CK3100207021,DDRS; Robert Jackall and Janice M.Hirota,Image Makers:Advertising,Public Relations,and the Ethos of Advoc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53-54. (55)The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oject,When Men Are Free:Premises of American Liberty, Cambridge,MA:The Riverside Press,1955. (56)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Information Series:Interview with Earl Wilson,” http://memory.loc.gov/service/mss/mssmisc/mfdip/2005%20txt%20files/2OO4will2.txt; Kenneth Alan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319. (57)亦称“学说战”或“学说项目”。由心理战略委员会(1953年后行动协调委员会)牵头,有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国防部和援外事务管理署等部门参与的规模庞大的反共心理战计划。其目的是“有计划地攻击敌对体系的基本意识形态;同时促进我方体系之基本观念获得承认与接受的积极努力”。“Ideological Warfare,Apr.18,1952,Eisenhower Library,Edward Lilly Papers 1928-1992,Box 54.Folder:Doctrinal Programs 1952. (58)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for the Ideological Program,” Nov.23,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0,OCB 091.4 Ideological Program(File #2)(1). (59)该委员会先与“行动协调委员会”联络,建议行政机构成立一个国际培训学院,专门培训来自世界各国的反共领导人。从学院毕业的成员返回各自国家后,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学术组织,尽一切可能对所在国农民、工人、商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牧师等群体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但其建议未被采纳。 (60)The Orlando Committee,“The Lincoln-Petkov Academy and the National Academy Organizations,” Nov.4,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0,OCB 091.4 Ideological Programs(File #1)(8). (61)U.S.Senate,86th Congress,1st Session,“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for 1960: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p.132. (62)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86th Congress,1st Session,H.R.3880,“A Bill to Create the Freedom Commission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b.2,1959,Eisenhower Library,Edward Lilly Papers 1928-1992,Box 55,Folder:Freedom Academy(2); U.S.Senate,87th Congress,1st Session,S.822,“A Bill to Create the Freedom Commission and the Freedom Academy 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9,1961,Eisenhower Library,Edward Lilly Papers 1928-1992,Box 55,Folder:Freedom Academy(1). (63)在众议院仅因时间原因未能付诸表决。U.S.House,90th Congress,1st Session,Report No.1050,“Freedom Commission and Freedom Academy,” Dec.15,1967,Readex U.S.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64)Thomas Alfred Palmer,“Why We Fight” :A Study of Indoctrination Activities in the Armed Forces,p.40. (65)广告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最初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希望美国的媒体精英能够帮助团结美国人共同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争努力中。二战结束后广告委员会进行了重组。冷战时期,广告委员会在美国社会舆论的形成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曾积极促进“冷战共识”的形成,并帮助征召3万美国青年人加入和平队。 (66)Robert Jackall and Janice M.Hirota,Image Makers:Advertising,Public Relations,and the Ethos of Advocacy,pp.49-50; “Air Defense from the Groud Up,” LIFE,Oct.27,1952,p.141. (67)Kenneth Alan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319. (68)“Suggested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Actions Relating to Eisenhower' s UN Address on ‘Atoms for Progress and Peace,’” CK3100318160,DDRS. (69)Frederick L.Anderson,“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United States Strategy:Panel Report,” Nov.29,1955,CK3100447519,DDRS,p.33. (70)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Report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Broger' s Militant Liberty Project,” Feb.11,1955,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1,OCB 091.4 Ideological Program(File #2)(7). (71)“OCB Concern with Militant Liberty,” CK3100007586,DDRS. (72)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Members of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Militant Liberty,’” Jan.28,1955,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1,OCB 091.4 Ideological Program(File #2)(5). (73)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64,88th Congress,2nd Session,” Sep.9,1965,LexisNexi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Digital Collection,ProQuest LLC,2012,p.9. (74)H.R.3880,86th Congress,1st Session,Feb.2,1959,Eisenhower Library,Edward Lilly Papers 1928-1992,Box 55,Folder:Freedom Academy(2); S.822,87th Congress,1st Session,Feb.9,1961,Eisenhower Library,Edward Lilly Papers 1928-1992,Box 55,Folder:Freedom Academy(1). (75)H.R.3880,86th Congress,1st Session,Feb.2,1959,Eisenhower Library,Edward Lilly Papers 1928-1992,Box 55,Folder:Freedom Academy(2). (76)Memorandum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The U.S.Doctrinal Program,PSB D-33/2,” May5,1953,CIA-RDP80R01731R003200050006-0,CIA CREST. (77)NSC,NSC 68,“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14 1950,p.23. (78)Lori Lyn Bogle,The Pentagon's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The Early Cold War,p.84. (79)Public Laws,CH.36,“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 Jan.27,1948,p.10,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77574.pdf. (80)Kennon H.Nakamura and Matthew C.Weed,“U.S.Public Diplomacy: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 Dec.18,2009,R40989,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p.4; Matthew C.Weed,“U.S.Public Diplomacy:Legislative Proposals to Amend Prohibitions on Disseminating Materials to Domestic Audiences,” Sep.21,2012,R42754,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p.2. (81)艾森豪威尔积极支持用宗教凝聚美国民众,并以宗教为武器展开反击共产主义的冷战斗争。在其任期内,艾森豪威尔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美国在处理内部问题和对外关系时要依赖道德和精神力量。“Planning and Programming in the Area of Mo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Sep.4,1953,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Secretariat Series,Box 5,Moral and Religious; Stephen J.Whitfield,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p.88.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文件中明确规定,“要充分利用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来唤起公众警惕冷战的危险。”参见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Memorandum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Defense on Propaganda Activities of Military Personnel,” Aug.2,1961,LexisNexis Congressional Record Permanent Digital Collection,ProQuest LLC,2012,p.14433. (82)“From Kenneth P.Landon to Mr.Elmer B.Staats,” Feb.11,1955,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1,OCB 091.4 Ideological Program(File #2)(6). (83)Deputy Chief,Psychological and Para-mitary Staff,“Memorandum for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Sep.27,1957,CIA-RDP80B01676R001200130013-3,CIA CREST. (84)Sara Diamond,Roads to Dominion:Right-Wing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p.48. (85)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Memorandum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Defense on Propaganda Activities of Military Personnel,” Aug.2,1961,p.14433. (86)Joseph M.Siracusa,The Kennedy Years,New York:Facts On File,2004,p.447. (87)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1954,” New York,1956,pp.207-208,http://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about-us/annual-reports/1950-1959. (88)Jurriaan Maessen,“Documents Reveal Rockefeller Foundation,Actively Engaged in Mass Mind-Control,” Infowars.com,Mar.4,2012,http://www.infowars.com/documents-reveal-rocketeller-foundation-actively-engaged-in-mass-mind-control/. (89)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64,88th Congress,2nd Session,” Sep.9,1965,LexisNexi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Digital Collection,p.5. (90)Jessica Meyerson,“Theater of War:American Propaganda Film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Robert Jackall,ed.,Propaganda,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 (91)George W.Bush,Decision Points,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0,p.169. (92)NSC,NSC 68/3,“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Dec.8,1950,Annex No.5,PD00181,DNSA,p.4. (93)Lori Lyn Bogle,The Pentagon's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The Early Cold War,p.119. (94)U.S.Department of Defense,Militant Liberty:A Program of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Freedom,p.v. (95)Scott Lucas,Freedom's War: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p.224. (96)George W.Bush,“Inaugural Address,” Jan.20,2005,in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8745. (97)John Fousek,To Lead the Free World: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p.2. (98)Danny Cooper,Neoconservat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Critical Analysis,N.Y.:Routledge,2011,p.12.标签:美国社会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布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