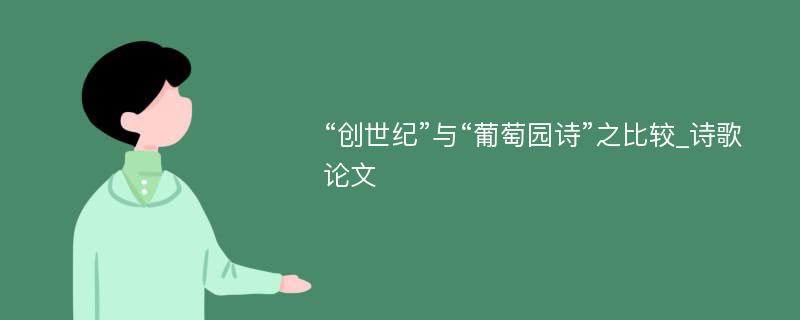
“创世纪”与“葡萄园”诗歌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葡萄园论文,创世纪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繁荣于七八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大景观。无论台湾出现过多少诗歌流派,其现代诗的实践(含诗作品和诗理论),都应视为对整个中华诗歌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在几十年的艰辛漫长的实践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误,有欢愉也有困惑,但不管怎样,每一位有艺术良知的诗人的每一种试验、每一部作品乃至每一轮论争,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积累。肯定,是一种积累;否定,也是一种积累。唯有积累,才有发展,才能飞跃。
“创世纪”诗社和“葡萄园”诗社,都是台湾诗坛有实力和有影响的民间大诗社,他们各有自己的诗歌宣言和旗号,各有一支较稳定的诗人和诗论家队伍,各有自己的出版物,各有自己的领衔人。他们都矢志不渝地实践着现代诗创作,新老结合,以老带新,在各自的旌旗下宣誓、整合,并从不停歇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着。其奋斗精神与创作业绩,让祖国大陆同仁感到十分敬佩和振奋。
笔者曾在《试论“葡萄园”诗歌创作及其理论主张》(注:先后发表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3 期和台湾《葡萄园诗刊》1997年第136期。)一文中, 简明地阐述了个人对该诗社实践等有关问题的见解。现在本文拟通过对两诗社有关问题的比较,着重对“创世纪”诗歌创作及其建树作一番探讨。
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诗坛的最大嬗变,当是以覃子豪主创的“蓝星”诗社和以纪弦主创的“现代诗社”的诞生,以及随后经过重新整合而相继承续出现的“创世纪”诗社和“葡萄园”诗社(这种承续并不是简单的继承或接力关系)。不论他们的宣言、旗号、规模、实践与业绩等有多大不同,他们都十分一致地向世人表明自己是现代诗一派。由此,他们的实践活动,被有的诗论家和文史家视为继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声势浩大的中国新诗革新运动。这一论断,当然有它的现实依据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不能以某种功利眼光和僵化的思维方式,把台湾半个世纪以来的诗歌运动简单划一地判定为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的历史。
“葡萄园”诗社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它诞生之后,根据台湾社会现实和诗坛现状,坚定不移地高举着“健康的、明朗的、中国的现代诗”(注:引自《葡萄园诗论》第094 页文晓村著《我们的道路——〈葡萄园〉二十年回顾兼序〈葡萄园诗选〉》。)的大旗。明确地提出反晦涩、反颓废、反传统、反西洋的“四反”主张。但他们的反晦涩,并不是把诗歌内蕴的含蓄也反掉;他们的反颓废,并不是把诗歌反映人类的一切情绪变化(或内省情感)也反掉;他们的反传统,并不是虚无地割断传统;他们的反西洋,也不是盲目地杜绝西洋。“葡萄园”诗社这一声势浩大的中国新诗革新运动,在当时处于困惑、茫然、混乱的台湾现代诗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冲击波所及,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华诗坛。随后,他们又致力于一系列中华诗歌交流和文化寻根活动,为海峡两岸共同重建中华现代诗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我们可以认为,36年来“葡萄园”诗社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宣扬和捍卫了中华诗歌的民族传统精神,其核心内容就是现代诗的民族魂和大众化。
如果把“葡萄园”诗社和“创世纪”诗社作为台湾现代诗不同流派可以成立的话,如果把90年代之前,把“葡萄园”诗社的“主情”和“创世纪”诗社的“主知”作为他们两大流派主要特征可以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话,那么到90年代之后,他们这些特征已经随着社会现实和诗坛现状的变化而开始了十分微妙的嬗变。“主情”和“主知”已经开始互通互补,逐渐地失去了作为他们主流特征的地位,而被别的新的特征取而代之。“葡萄园”诗人们曾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的作品,不是含有哲学意味的”。(注:引自《葡萄园诗刊》第4期蓝云著《泛论现代诗》。)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就有不少这种“含有哲学意味”的佳构。而所有这些嬗变,探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不论什么原因,都可以最终归结为时代风云变幻。因而任何一种变化,无不带上时代的印记。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重性。“葡萄园”诗社有它的功绩,也有它的缺憾。笔者以为,其主要缺憾有以下两点:
其一,“葡萄园”诗社,不适当地扩大了诗歌艺术的社会功能。他们认为“现代诗决非少数自命为心灵的贵族的特殊宠物”,(注:引自《葡萄园诗论》古丁著《论诗与明朗》。)而主张诗是人类心灵的艺术,“诗的价值乃是在于如何激动读者的心灵,引导读者接近甚至进入诗人所创造的那种崇高优美的境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而与诗人在心灵上发生共鸣。这是诗与其他一切文学价值的所在。”(注:引自《葡萄园诗论》文晓村著《论诗人的觉醒》。)在这里,论者之所论,是从诗的本质属性论及诗的接受美学原理,阐明了诗歌自身的客观的艺术效应。毫无异议,这是包括“创世纪”诗社同仁在内的多数诗人所能接受的观点。但遗憾的是,他们继而又反复强调诗歌必须“美化人生和净化心灵”(注:引自《葡萄园诗刊》创刊号的创刊词(文晓村执笔)。),甚至还认为“当人们感到迷失,不知何去何从时,诗人应该给找出一条出路来”(注:引自《葡萄园诗刊》第4期蓝云著《泛论现代诗》。)。 这不能不说只是一种美好愿望,而不是诗歌文本所固有的自身的艺术规律。它只能被认为是诗人们强加给诗歌的枷锁。诗的审美特征,概括地说就是感悟和共鸣。请读祖国大陆著名现代诗人、诗评家阿红先生的抒情诗《诗的反馈》(注:引自方航仙、苏彦铭编著的《微型文学作品选析》一书。):
一屋子眼睛
一窗棂眼睛
一门框眼睛
黑的眼睛
蓝的眼睛
沉思的眼睛
甜甜的眼睛
蒙着纱布的眼睛
架着眼镜的眼睛
所有眼睛象打开着的
慢镜头,瞄摄着
心灵的图画
所有眼睛,象启动着的
录音机,贪婪地录着
心灵的诚挚
所有的眼睛,象旱了许久的草原
现在每张鹅黄的小嘴
蠕动着,吮着真善美的
醇液……
生命的指,拨响着
生命的弦
微笑诱发着微笑
泪牵引着泪
力搏动力
火种点燃火种
1983.9 沈阳
诗歌朗诵会上
这首诗多层次多角度地写出了诗歌朗诵会的热烈气氛和动人场面,既表形又传神,洋溢着清新的情趣,撩拨着读者的心弦,获得了极致的艺术效应。这就是诗歌艺术自身的魅力,它靠的正是心灵的感悟与共鸣。因此才有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之说。文晓村先生的《桥》也不正是这种以诗论诗的佳作吗?能否写出好诗,是由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技艺水平决定的,绝非诗人的“下意识”所能左右的。假如写诗非得“下意识”地去“美化人生和净化心灵”,那么诗便成为诗人欲达到某种功利的工具了。假如诗还要为迷失方向的人们寻出一条“出路”,那么诗便成为政治。这种诗注定会落入非诗的陷井,这才是诗人的莫大悲哀。不适当地扩大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有碍于“真言”的表达,而这正是“创世纪”诗社所极力回避的“非诗”要害之一。
其二,从诗歌的艺术化手段看,比较“创世纪”诗社,“葡萄园”诗社从诗作到理论都令人觉得其现代意识略逊一筹。文晓村先生曾经强调,所谓“现代”,是指现代的时间与现代的空间。因此,他认为现代诗必须具备“几个普通的原则”:一是现代的语言,二是现代的生活,三是现代的精神。按现代诗的表征要求,这三个“原则”是无可非议的。但就其内涵指向,两个诗社尚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两个诗社虽然都致力于“表现现代现象”(即现代人的生活),但“葡萄园”诗人主要是把目光放在民族本土之上,而“创世纪”诗人主要是把目光投向“世界性”。
第二,两个诗社虽然都致力于表现现代人的精神,但“葡萄园”诗人更注重于表现现代精神中“可贵的一面”(或光明的一面),给人以“生”的希望;而“创世纪”诗人则更注重于表现现代精神中的迷茫、困惑、悲哀的一面,给人以“死”的震撼,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触及灵魂,诗作才更具有力度。
第三,两个诗社都致力于现代语言的革新,但“葡萄园”诗社相当一部分诗作中,“诗到语言为止”的迹象比较明显,而这正是“创世纪”诗人们所极力排除的诗歌语言弊病。“创世纪”诗人认为所有的诗都“应该聆听语言后的真言”(注:引自《创世纪》诗杂志第104 页简政珍著《诗的生命感》。)。这就是说,“语言不是诗歌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诗中,一旦语言的传达完毕之后,它的使命便即刻消逝,而诗意却必须在语言背后血肉型地凸现。”(注:引自《创世纪》诗杂志第106 页余乐敏著《空不空 不空空——诗歌语言的禅喻》。)简而言之,品诗就是“反复品赏语言背后的意蕴。语言‘消逝’,意义‘显现’。这才算完成了由语言物质到诗意精神的审美转化过程。”(注:引自《创世纪》诗杂志第 106页余乐敏著《空不空 不空空——诗歌语言的禅喻》。)语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虽然以上三方面存在着不同见解,但都有其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这是不能苛求的。有分歧,才有比较,才有发展。尽管分歧有趋于统一的时候,但统一是暂时的,统一之后还会有新的分歧,分歧(或不一致)才是永久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诗歌也不例外。
然而,就现代诗本质属性论,其语言艺术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语言的现代化,当是现代诗的首要特征。笔者认为,“葡萄园”诗人们在反对诗歌语言玄虚、晦涩的同时,应当努力增强语言的现代化意识,更广泛更深入地实践和研究现代语言如何“利用文字的功用,将诗人的诗思传达给读者”(注:引自《葡萄园诗刊》第4期蓝云著《泛论现代诗》。) 。这时的“传达”,有两个不同层次,一是“诗到语言为止”,这是浅层次的传达;一是让读者能透过诗的表面语言符号,感悟到语言背后的所谓“真言”(不是真话假话的“真”,而是诗人真正所要表达的意蕴的真)。如果没理解错的话,用传统说法,这就是指含蓄,指诗中的“空白”,即指读者直读不出却意会得到的诗思情感。用简政珍的诗论解释,那就是现代诗中的“沉默”,这种“沉默”才是现代诗无声的最具魅力的语言。这是中国新诗艺术现代化十分重要的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葡萄园”诗社在“四反”过程中,应当克服担心被西方艺术所指染的不良心态,大胆汲取“西洋”现代诗中某些有助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此同时,还要特别警惕思想意识上的自我封闭倾向,要有鲁迅先生30年代所提倡的“拿来主义”的精神和勇气,更广泛地参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乃至碰撞)。只有这样,才能在原有坚实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才能紧跟未来世界多元化多层次文化格局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开拓新的更美好的前景。
上述“葡萄园”诗社之不足,倒成了“创世纪”诗社的优势。笔者认为,“创世纪”诗社的主要建树在于:
他们在倡导中华诗歌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的诗歌创新实践和理论主张,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简政珍的现代诗论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他们不但拓展了中华诗人的思维空间和表现领域,而且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为加速中华诗歌艺术的现代化进程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创世纪”诗社成立于50年代初,可以说比“葡萄园”诗社多走了一段坎坷之途,因此,他们为促进中华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创世纪”诗人们之所以首先提出中华诗歌的“世界性”主张,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他们与祖国大陆的民族文化母体隔断,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勇敢地从旧中国的封闭社会环境中走出来,打开了千奇百怪、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之窗,闯入了西方五彩缤纷的诗歌殿堂。其勇气与举止无不令中华诗坛乃至世界诗坛所瞩目和称赞。二是“创世纪”诗社中拥有一大群学者型诗人,尤其是有一部分曾到“西洋”留学或讲学回归的颇具实力的学者型诗人,从纪弦到叶维廉到简政珍等,他们的一系列现代诗作和理论体系更带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品位和实验性质。他们的所有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告诉人们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忘我奋斗的是中华诗歌的一场重大变革,而中华诗歌正处于一个空前引人注目的转型时期。
因此,与任何诗歌团体一样,既是实验,既是处于中华诗歌的转型阶段,那么所有的实验性作品及其理论主张,就必然带有其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的一面。也就是说,既有它的建树,又有它的不足。
笔者以为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诗歌作品中,意象的怪异莫测和语境的幽深晦涩,甚至不少理论文章也偏离汉语语法甚远,采用了大量的欧化语法,犹如外国语直译文本,广大中华民族大众难以阅读和接受,甚至望诗生畏、望文兴叹。如此艰辛耕耘只赢得少数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赞许,这委实是诗人、诗论家聪明才智令人惋惜的浪费,终于不免造成了作者的委屈和读者的悲哀。
诗歌是让人类神经感应和灵魂震颤的艺术。诗人诗作能引起更多读者的感悟和警醒,从而走向希望,走向光明(不论写丑或者写美,也不论写死或写生),那么它便愈有其审美价值,也就愈能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笔者注意到了文晓村、王在军、余光中、洛夫、简政珍等在长篇史诗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一定要用“功利”来阐释诗歌创作意图的话,那么可以说这就是诗歌艺术的最高功利之所在(当然,这并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伦理、教化的功能)。
由此,笔者认为“创世纪”诗社应当加强民族语言如何在中华诗歌现代化中的表现力和凝聚力的研究与实践。
中华诗歌现代化,只能是在民族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偏离了民族化方向,便脱离了民族土壤(或母体)的根基。毫无疑义,不具备民族特色的现代诗,绝不能视为真正的中华新诗。至于诗歌要不要大众化,现代诗能不能大众化,尚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诗歌是文学品类中最高的艺术,其读者群数比起小说、散文来得少,这是自然的,不足为怪。而有的却认为,诗歌同其它文学品类(如小说、散文、随笔、小品等)一样,应尽量赢得更多读者的阅读、喜爱和认可,越普及、越大众化,就越能发挥其艺术感化作用,它就越具有艺术审美价值。诗歌不应当成为少数“文学贵族”的专利。
笔者赞同的是后一种见解。因此,笔者的结论是:中华诗歌必须走民族化的现代化的大众化的道路,中华诗人应当朝着这“三化”方向努力奋进。
“创世纪”诗社和“葡萄园”诗社,为了创建中华现代诗,都竭尽全力地前仆后继地作出了各自的卓越贡献。大家都是聚集在“中华民族”这面大旗下的炎黄子孙。既然都从事着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就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矛盾对立。当然,批评和论争,是正常的必要的,诚如大陆学者刘登翰等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批评和论争,现代诗的缺陷与失误被进一步揭露,而它的价值,它对台湾甚至整个中国新诗发展的积极意义,也在被逐渐认识。”(注:引自1993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刘登翰等编的《台湾文学史·下卷》第127页。)因此, 目前台湾诗坛的流派、山头、理论、贡献等等,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我们不应当把时间、精力与才智过多地消耗在同一个水平层面的无休止的论争上面,而应当在未来的“对话、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发展总趋势下,重新携起手来,存同求异,取长补短,朝着共同的目标再作新的贡献。
两个诗社都是台湾最具实力的最成熟的中华现代诗歌团体,我们有理由满怀信心地预祝他们,随着21世纪的脚步而顺利地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