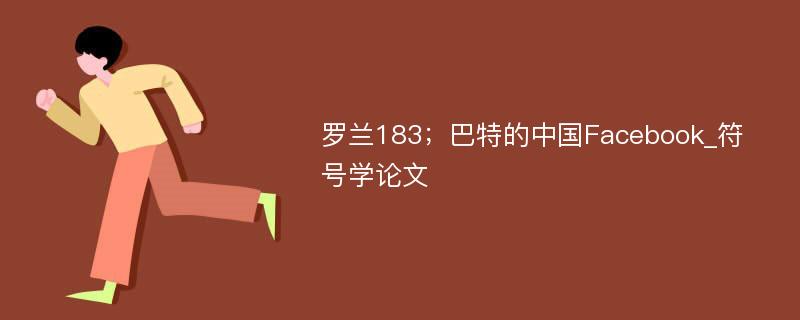
罗兰#183;巴特的中国“脸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脸谱论文,中国论文,巴特论文,罗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脸谱”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符号,中国和西方都有其丰富的样式和谱系。但川剧中“变脸”的绝活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生动地演绎了一个角色的变换或多面性。用这种角色变化来表征他者理论本土接受的复杂状况,是颇为传神的。如果说“脸谱”意味着某种角色,那么“变脸”则代表了角色变化。同一个人物及其思想,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人群中,总会被“变脸”为不同“脸谱”,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当代社会这种变脸更是彰显,因为“流动的现代性”(鲍曼)使得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
与“脸谱”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西方概念是“镜像”。所不同的是“脸谱”着眼于他人的认知,而“镜像”则集中于主体自我的认知和反思。在拉康那里,“镜像”是指主体的自我镜像及其认知①,但稍作拓展,似也可以看作特定主体在他者文化镜面中的歪曲映像和折射。在这个意义上,“镜像”与“脸谱”便有了相通的涵义。它们都揭橥了外来形象在本土文化中的投射、扭曲和变化。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讨论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当代中国的“脸谱”或“镜像”是被如何建构的。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瞥见“脸谱”或“镜像”后面所折射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张力。
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
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以降,许多法国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译介、阅读和研究。萨特、加缪、梅洛—庞蒂、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克里斯蒂娃、托多洛夫……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其中罗兰·巴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其话语的“中国之旅”在本土语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一方面,其著述在法国思想家的汉译作品中种类和数量最多,老辈的萨特或加缪,同辈的福柯或德里达,似无人能与其比肩;另一方面,就其理论的影响或阅读面来说,萨特多限于哲学和文学圈,福柯囿于思想史和社会学界,拉康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影响更狭窄。巴特话语不但是学术话语,同时也是大众阅读的对象,以至于有人说他“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②。
巴特理论的引入最初是伴随着结构主义的译介。据研究文献显示,他的第一篇译文是袁可嘉先生翻译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③。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译介活动出现在1984年,张裕禾翻译了《叙事作品分析导论》(《外国文学报道》1984年第4期)。到了1987年,该杂志在第6期上刊载了巴特的7篇论文,均译自《批评文集》(1964)。他的第一部译著是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符号学原理》。第一部国人选编的文集是李幼蒸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据统计,他的《符号学原理》在中国有4个不同译本,其中以《符号学美学》为书名于1987年出版,印数有3.7万册之巨,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④。
截至2008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巴特至少有20种著作被翻译成汉语(这还不包括许多单篇译文),分别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参与巴特译介工作的不只是从事法语或法国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一些巴特的著作是从英语转译的。这说明,巴特对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影响是多通道的,不仅有法国语言文化这一个源头,而且还有更为广大的英语世界。而英语世界对巴特的理解和解释显然也左右着巴特“脸谱”的中国建构。
巴特单篇论文的翻译就更多了,也比较复杂,这里不再赘述。巴特话语的传播不仅在学术圈,也经常出现在大众传媒上。在个人博客、个人网页、专题网站上,不同的读者依据自己对巴特的理解,将巴特的不同言论语录式地摘引,贴在网上供人阅读。主题各异,理解千差万别。或许我们有理由把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圈系统地译介研究巴特著作;第二个层次是零散而不系统的巴特文章篇章的翻译,既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散文;第三个层次是大众媒体的泛用,只言片语式地加以引用或拼贴。正是由于这样的多层次流布,巴特的中国“脸谱”要比其他法国思想家来得复杂。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其一,关于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9年,这一时期主要围绕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来译介和研究巴特,翻译多为论文而著作不多。李幼蒸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他1984年选译的巴特文选一直到1988年才面世。照他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国内学界与世界学界隔膜所致,其实还有更多的原因⑤。第二阶段是1990-2005年,此时巴特的著作翻译范围扩大,研究也深入到诸多领域。巴特被置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境之中,其影响也超越了其他法国现代思想家。第三阶段是2005年以来,巴特的著作被重译重版,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罗兰·巴特文集》10种,外加传记1种。这就把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巴特的研究也愈加多样化和系统性,其“脸谱”变得更加不确定。
其二,巴特话语“中国之旅”的三十多年,经历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深刻变化。中国接受语境的变化一方面加速了巴特话语的中国传播,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发明”出巴特的中国“脸谱”。这一过程始于学术界,后扩展至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推动巴特“脸谱”不断“变脸”的是极具张力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特别是随着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巴特的中国“镜像”扭曲了,其“脸谱”也变来变去。
“脸谱”一:激进知识分子
从巴特话语“中国之旅”的历时线索来看,显然存在着一个从中立符号学家到激进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这一方面源自巴特理论的庞杂性和角色的复杂性甚至暧昧性,另一方面,它也清楚地标示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投射,巴特读者变化着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以及这一读者群不同代际、专业和背景的“解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之间的解释差异和冲突。
改革开放伊始,经历“文革”十年,百废待兴,学术亟待重建。自中国近代以降的一个反复出现的文化策略此刻重现,那就是“洋为中用”,借鉴外来理论观念解决本土当下问题。于是,国外思想文化的译介掀起了一个高潮,巴特话语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在巴特思想传布的第一阶段,其上场角色基本上是一个符号学者。这里不妨比较一下巴特和萨特的中国接受。萨特当时是如日中天的法国大师,在国内外得到高度赞美和追捧。巴特还只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后来者。但文化的接受过程是高度选择性的,它源自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萨特尽管名气很大,成就卓著,但他那“介入(干预)”的文学观,在刚刚经历“文革”惨痛教训的中国学人看来,已是老调重弹。加上“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这一萨特核心文学观念在中国变得毫无吸引力了。与萨特不同,巴特进入中国视野的是全新的结构主义理念和符号学方法。这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学界的现实需求,因为,符号学对各门学科知识建构来说,是具有变革性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如李幼蒸所说,符号学强调横向理解贯通,它可以“在一般思想层面上打通、提升、深入”⑥。在80年代的背景下,巴特一直扮演着作为方法论革新者的符号学家角色。
从译本和译文的选择来看,最早翻译和研究的文献大都集中在他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上,特别是《符号学原理》。许多单篇译文也多限于他的有关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当时的巴特研究自然也就多集中于这一层面。因此,巴特的初始镜像显然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是创造性地将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运用于文学、文化和社会文本分析的方法论革新者。巴特的这种中国接受的期待视域表明,那时的学术研究需求是,如何引入新的学术方法论来改变政治控制严密的伪学术,颠覆教条主义和政治干预,形成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基于这一视域,对巴特话语的兴趣更多集中于技术性的文本分析方法,而对这一分析的“去神话”的意识形态批判则关注较少。1985年前后出现的“方法论热”,更是强化了巴特符号学家“脸谱”塑造的取向,许多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的译介和著述面世,巴特的多篇论文也被选入不同文集和读本之中⑦。
随着8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文化转变,政治和文化情势变得日趋严峻,经济高速发展并日益融入全球化,两者形成了复杂的张力。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研究观念引发了热烈讨论,新一代学人进入知识生产体制,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开始了第二阶段,其“变脸”出现了。
后现代主义虽早已进入中国学界⑧,但80年代末才真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并引发广泛讨论,这就合乎逻辑地带出了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根基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张隆溪早在1983年就在《读书》上撰文指出,巴特已从结构主义转向了后结构主义,但此前对巴特的研究几乎不关注这一转变,也许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方法论热情暂时遮蔽了这一转变的意义。或许我们有理由认为,巴特经历过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但是,囿于解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论期待视域,巴特只是作为一个带有科学分析倾向的技术性专家出现。相反,借助后现代主义视角,后结构主义理念在巴特话语中变得异常醒目和重要了,一些即使是巴特早期著述中的观点和理念,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加以重新解释。于是,十多年间巴特变换了模样,从一个“中立”的符号学家变成政治取向彰显的激进知识分子。
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引入之外,还有更多的复杂原因。9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风向的转变,特别是所谓“后革命时代”的到来,知识界各种保守主义抬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地形图。消费社会的到来,大众文化的急剧膨胀,不断地消解着原本作为对立面的严肃的高雅文化。一方面,消费社会特有的文化景观占据了日常生活,影视媒体、商业广告、流行音乐、网络文化等悄然成为不可抗拒的现实;另一方面,在精英主义观念遭遇挑战的同时,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策略进入了知识界。尤其是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对巴特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揭示了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另一面,那就是对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批判。这些复杂的原因导致巴特“脸谱”的重塑。
首先,学术界一度幻想的科学的、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研究路径遭到质疑。结构主义符号学那种抽象的、形式化的和繁复的文本技术分析,似乎已经不再能激发本土学者的兴趣。反之,隐含在技术性分析后面的激进观念、批判立场和后结构主义主张,此时便凸现出来。于是,巴特那些尼采式的判词和颠覆性的理论,遂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主题。这些原本被遮蔽的新的“脸谱”元素,逐渐从背景走到了前台,引发了青年一代学者的高度兴趣。巴特的译介是始于“方法论”的技术创新冲动,此时却发生了重心迁移,人们更加关注他的“去神话”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李幼蒸曾指出,巴特学术最具价值的是其文本意义结构分析的技术方面,他认为,这是巴特对中国学术现代化更有用处的一面。但他又指出,与这一分析相伴的是巴特的许多“准哲学性”智慧,反实证论、反实在论和美学乌托邦等⑨。在我看来,假如说80年代人们较多地关注于巴特理论的前一层面的话,那么,90年代以降,后一层面的这些“准哲学性”智慧更引人注目。
其次,随着中国学术越来越体制化,知识生产变得越发沉闷和技术化,新一代学者作为生产者的加盟,导致了生产者之间的代际差异乃至冲突。“60后”和“70后”的学者在成为学术共同体新的社会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有别于上一代学者的知识兴趣和政治取向。他们未曾亲历“文革”,在较为稳定富庶的生活境遇中成长,对“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时代”难免抱有某种激进冲动和革命渴望。尤其是在现实革命难成现实的当下语境中,思想革命和观念激进成为他们的可能选择⑩。比较来说,较年长的学者比较关心巴特技术性层面上的符号学理论,而较年轻的学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则更强调巴特批判性和颠覆性的理论话语。前者厌倦了动荡与革命,所以倾向于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后者期盼新的变革,因而热衷于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观念。由此形成了巴特的两代“解释共同体”的代沟,正是在这个代沟中,巴特完成了从中立的符号学家到激进批判知识分子的“变脸”。
具体来说,巴特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脸谱”,是由如下几个激进话语构成的,它们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受到了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第一个是“作者死了”的宣判。就像尼采宣判“上帝死了”一样具有震撼力,巴特的这个口号极具颠覆性或反叛性,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是对以往文学理论的一种有力反叛。“作者死了”反对的是流行的文学研究观念,即作者在文本意义解释中的权威性。但“作者死了”在巴特那里的意义不止于此,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考量,它包含了对本源、中心或在场等观念的断然否定。进一步讲,巴特的这种观念还突出了其他两个相关命题。其一,高扬文字书写的重要性,贬抑传统的声音中心统治地位;其二,对启蒙自主反思主体的解构,照他的说法,作为现代概念的作者不过是一个“抄写者”而已。这些宣判很有颠覆性和吸引力,人们从中读出某种叛逆性的快感,像尼采宣判“上帝死了”一样震撼,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中人物的话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了,做什么都可以!”
第二个是巴特的文本理论,它与“作者死了”密切相关。巴特的文本理论也可以用类似的宣判句式来表述,那就是“作品死了”。在巴特的理论构架里,文本完全是一个后结构主义的概念,它抛弃了自足的现代作品观。它既不同于传统“有机统一”的实体性作品观,又迥异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甚至法国结构主义的作品观。巴特强调的是解构的、网状结构的开放文本。像上帝一样的作者死去了,粉碎了文本解释的唯一神学根源,这就为更多可能的文本解释提供了合法性。巴特常把编织、音乐等概念比作文本,清楚地标明了他赋予读者以文本意义解释的权利。他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的多元解释更是实践的典范。作者之死乃是读者的诞生,从一个唯一的权威作者到无数可能的读者,从一个确定不移的实体性作品,到网状连结和互文交织的开放性文本,文本意义的解释必然呈现出不确定性、多元性、相对主义的后现代理念。这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实践是极具启发性和煽动性的。特别是巴特关于“可写的”和“可读的”文本的比较,以及他对文本“生产性”和“愉悦”的强调,更加突出了文本的未完成性和读者多元解释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巴特关于语言乌托邦实践命题,也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理论,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今天,巴特的“作者死了”和“作品死了”的命题已成为许多青年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80年代被视为方法论革新的符号学家,在90年代演变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巴特还是那个巴特,只是当下本土语境及其期待视域发生了变化,于是,巴特完成了第一次“变脸”。
“脸谱”二:大众文化鼓吹者
在巴特完成第一次“变脸”的同时,另一个“变脸”也在酝酿形成中。有人把巴特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视为他“晚节不保”的标志,因为“结构不上街”,所以,巴特最终被1968年学生运动无情抛弃。正是由于这一转变,“身体、欲望、文字自乐的嬉戏成为了他的主题……把他带向自我毁灭的深渊”(11)。这种看法显得有点简单化了,却也点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巴特与大众文化的纠缠。在巴特的话语中,从服装时尚到摔跤,从广告到摄影,从脱衣舞到情色话语,这些严肃的萨特绝不讨论的问题,往往都是巴特钟爱的话题。巴特著作的中国接受也充满了戏剧性,据说他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出版时,反应平平,此书后来以《恋人絮语》为题出版,市场反应热烈,甚至引发了巴特“同志”倾向的猜测(12)。显然,巴特中国“脸谱”的不断“变脸”来自多个方面。
首先是巴特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使得他难以归类,就像他的传记作者卡勒所说的,他同时是“多才多艺的人”、“文学史家”、“神话学家”、“批评家”、“论战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享乐论者”、“作家”等(13)。中国学者也注意到巴特的多面性,李幼蒸提醒道,“应该注意到存在有‘两个巴特’:作为理智分析家和作为美学艺术家。对前者而言,我们会惊叹其观念的清晰和准确;对于后者而言,如他对‘快乐’、‘色情’、‘意涵’等词的故意反常用法,连西方专家的读解都难以一致。”(14)
随着中国小康社会的到来,消费文化和景观社会的形态渐次形成,大众文化成为日常生活,在这种深刻变化了的语境中,巴特那种严肃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脸谱”,却又“变脸”成大众文化的捍卫者和阐释者,甚至是大众文化的吹鼓手。导致巴特角色变化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巴特理论话语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给中国解读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在巴特的研究视野中,除了严肃的文学作品之外,更多或更有影响的是他的大众文化话语。从《符号帝国》到《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从《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到《明室:摄影纵横谈》,从《恋人絮语》到《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论》,这些著述探究了大量当代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现象。如果说他的符号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分析还远离人们日常生活和普罗大众的话,那么,这些话题显然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认为巴特比萨特等老一辈学者更具大众亲和力,其话语更有普及性和常识性。用威廉斯的话来说,文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精英主义的文化,把它视为严肃的、高雅的和难以企及的;另一种则把文化看作日常的、普通的,强调大众的日常生活层面(15)。看来,萨特的理论属于前者,而巴特的话语显然属于后者。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巴特著作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法国思想家,成为大众喜爱的读物。特别是他在诸多论述中所触及的那些话题或关键词,诸如“服饰”、“饮食”、“广告”、“触摸”、“照片”、“身体”、“男女”、“欲望”、“旅行”、“爱情”、“建筑”等等,显然是许多信奉高雅文化的思想家不愿讨论的。问题在于,巴特对大众文化话题的热衷,并不意味着他赞美大众文化,其实他的话语中带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有趣的是,在巴特有关大众文化话语的中国式解读中,一方面,那些比较复杂的意义分析被简单过滤了,剩下的是对大众文化本身的合理描述;另一方面,隐含其后的巴特的批判性、去魅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也被普通读者肯定大众文化的期待视域遮蔽了。
其次,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小康已从量化经济指标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媒体文化、景观社会的初见端倪,迫切地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面对的难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毕竟囿于哲学层面的分析和严肃的批判立场而与大众隔膜,巴特的分析话语却通俗有趣,天然地具有某种与大众的亲和力。对巴特大众文化话语的通俗解读所过滤掉的批判取向,往往被某种大众文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阐释所取代。巴特由此被塑造成一个大众文化合法性的阐释者。这种情况只要对网络上关于巴特著述的引语及其讨论稍加浏览,就可清楚地看到。它们与其说是对大众文化的反思批判,不如说是对大众文化合法性的论证。这个巴特“脸谱”更多的是本土读者公众想象力所投射出来的巴特。于是,一个大众文化合法性阐释者的巴特应运而生。
总体上看,作为一个大众文化阐释者,巴特的中国“脸谱”有如下几个相关变体。
第一,情感巴特。在当代中国情感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文化问题的语境中,在谈论和研讨日常情感问题越来越普遍的情形下,巴特扮演了一个情感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角色,其著述和个人经历引发了读者们的兴趣。加上本土读者对法国文化浪漫气质的中国式想象,巴特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法式浪漫情感的担当者。许多解读《恋人絮语》的中国读者,把巴特看作一个对爱情有深刻见解和独特经历的人,其言论被广泛地用于解释形形色色的不向情境和情感。另一些读者则关心《巴特自述》中所流露的同性恋倾向,在其有关自己情感世界描绘的文字中搜寻他的“同志”情结。巴特另一个情感生活的层面是他与母亲长久的母子情,不少人关注两个事实,一是巴特成长过程中母亲不可取代的作用,母亲的离世给他的心灵造成巨大的打击,他在《明室》下篇中专门分析了母亲的照片及其对母亲的记忆;二是巴特受聘法兰西公学时,在其就职演讲时,挽着母亲的臂膀出席。这不同于那些名流和明星的情感生活的煽情叙述,巴特的情感自我倾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话语,它对于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着复杂情感风暴的本土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可资参照的话语世界。更有读者在巴特情感话语的文字中感悟到一种爱情话语的无逻辑性和混乱,并从这些无逻辑性和混乱中感悟到爱情本身的特征。此外,从爱情到情色,巴特许多极富创意的文字吸引了公众的目光。比如,一篇广泛流传并作为书名的文章《脱衣舞的幻灭》,就是一个例子(16)。
第二,影像巴特。巴特对当代视觉文化的阐释,亦有许多真知灼见。当中国视觉文化崛起时,传统的绘画和电影理论显然捉襟见肘,于是,巴特有关图像的种种理论,从复杂的符号学分析到照片的印象描述等,引发了本土读者的高度关注(17)。尤其是今天,随着数码摄影时代的到来,影像的大众狂欢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或者说影像生存成为典型的当代生活方式。从数码相机到手机拍摄,从网络传播到各种视频网站的涌现,直至各种影视作品的恶搞等,使得如何解说“读图时代”的影像变成一个热门话题。影像巴特的涵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巴特提供了一套有关影像解释的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影像巴特还意味着巴特本身成为影像,也就是在各种媒体中频繁出现的巴特照片或影像(18)。在影像巴特的中国“脸谱”建构过程中,巴特的一些文献具有重要作用,诸如论文《广告信息》,著作《今日神话》和《明室》。前两者今天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典范,着重于考量图像不同层次的意义生产,其中贯穿了意识形态批判。相比较而言,《明室》可读性更好,因此晚近的影响也就更大一些。这本书的读者不只是视觉工作者(如画家或批评家),还有许多普通读者广泛阅读和引用这本书,解释种种不同的影像类型。特别是关于摄影的本质,“知面”和“刺点”的理论,对于当下国人理解和解释摄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此,巴特的图像话语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中国大众影像狂欢的某种注脚。
第三,时尚巴特。巴特的许多文化分析著述被做新的理解。许多当代大众文化现象,从流行体系到时装摄影,从埃菲尔铁塔到影星嘉宝的脸,这些作为时尚存在的大众文化现象,都进入了巴特的解释视野。流行时尚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普遍的文化景观,是消费社会和媒体文化的必然产物。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一书,算得上是一部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著作。他关于流行的看法是:流行是由单一循环论证的无限变化决定的,“就像是一架保持意义却不固定意义的机器,它永远是一个失落的意义,然而又确实是一种意义,没有内容的意义。它变成了人类自恃他们有能力把毫无意义的东西变得有所意指的一种景观”(19)。巴特的界说道出了流行时尚只是能指变化而缺乏意义生产的本质所在。在当下中国语境中,人们不大关注巴特的时尚话语关于“意义的失落”、“循环论证”、“没有内容的意义”等关键表述,而对流行时尚的能指变化更为关心,甚至把这种变化本身就看作新意义的生产。这种理解颠倒了巴特对流行时尚的分析,其批判性转而成为合理性的解释,去魅转而成为“复魅”。在如此取向的解读中巴特完成了某种“变脸”,从一个大众文化批判者转而成为一个大众文化的礼赞者。这说明,本土当下语境对于一个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无论文本原义如何,它的接受都有赖于本土语境中的读者及其价值取向。当精英主义的文化观日益让位于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时,当流行时尚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时,当流行时尚的商业阴谋被华丽外观巧妙遮蔽时,人们对流行时尚的认同和接纳,就会把原本抵抗性的话语解读为认同性的话语。这也许就是巴特时尚话语中国式解读的特色所在。
巴特话语的走红原因是复杂的。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比较浅显的原因,即巴特话语的论题及其文风。他那种片段风格,感性描述,活泼例证与形象的比喻,都成了巴特有别于其他严肃艰深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特征之一。他那些引发普通读者兴趣的生动话题,更是召唤着无数可能的解释。总体上看,当下中国存在着两种巴特解读,一种是知识界比较严肃的解释,它凸现了巴特理论的反叛性和批判锋芒,努力把巴特塑造成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在这种解读中,巴特理论话语成为某种“去神话化”的倾向被特别加以强调,而看似自然的文化现象后面不自然的意义也就被彰显出来。另一种则是大众的通俗解读,它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较少深究和系统解释巴特话语,因而更容易形成当下语境价值观和文化取向的本土投射。这种解读与其说是关心巴特说了什么,不如说是意欲“发明”一个中国当下大众文化所需要的巴特“脸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都是真实的,它们折射出中国“后革命时代”消费社会及其文化内部的语境张力。可以肯定,随着这些张力的发展变化,还会有更多的巴特“脸谱”被塑造出来。
注释:
①参见拉康《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②李幼蒸:《总序》,载巴特《符号学历险》,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依据英译文转译的。巴特著述最初有不少是从英文转译,因此,英美学界对巴特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大陆学术界。随着时间的推移,直接从法文翻译的巴特著述逐渐多起来,近些年来巴特著述基本上都从法文直接翻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帝国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影响。
④张晓明:《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
⑤李幼蒸:《总序》,载巴特《符号学历险》,第5页。
⑥李幼蒸:《译者前言》,载巴特《符号学历险》,第5页。
⑦研究巴特的论著主要有,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赵宪章:《文艺学方法论通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胡经之等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收入巴特论文的文集和读本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伍蠡甫等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周宪等主编:《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
⑧美国学者杰姆逊1985年就在北京大学授课讲述后现代主义,此讲稿后成书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⑨李幼蒸:《译者前言》,载巴特《符号学历险》,第5页。
⑩这种取向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得到印证,诸如所谓的“新左派”思潮出现,话剧《切·格瓦拉》的上演等。
(11)参见《我看罗兰·巴特》,http://shenyuwuyou.spaces.live.com/blog/cns!DB433124DF3A1EF4!326.entry,2009.3.14.
(12)Devison Yang:《罗兰·巴特》,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4777&PostID=233709.
(13)参见卡勒《巴尔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就以这些角色为标题,分别记叙了巴特的不同侧面。
(14)李幼蒸:《译者前言》,载巴特《符号学历险》,第15页。
(15)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1-20.
(16)魏萌选编:《脱衣舞的幻灭:外国后现代主义散文随笔》,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7)引起我国学者高度关注的影像理论家及其著述有: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摄影小史》,桑塔格的《论摄影》,伯格的《观看之道》等。
(18)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在巴特的译著的封面上,大多选取了点烟或拿着雪茄做思考状的巴特影像。
(19)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