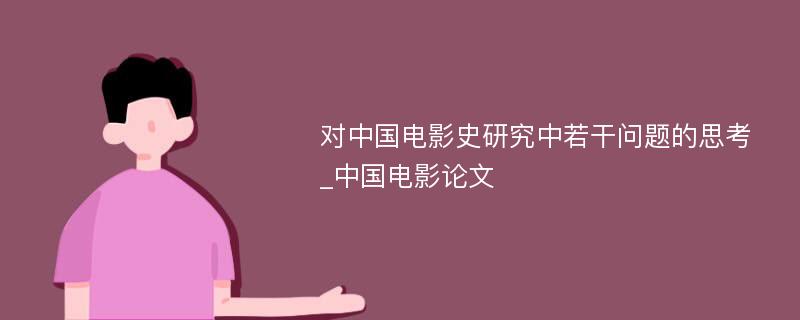
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之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007-6522.2011.04.002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1)04-0011-09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发展,文艺理论界也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既逐步清除了极左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也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由此,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和新的气象,其中电影理论研究和电影批评也同样如此。在此过程中,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也随之有了很大拓展。特别是自从电影理论界关于“重写电影史”的倡导以来,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里勤奋治学,深入探讨,不仅发表了很多颇有新意的研究文章,而且还出版了不少各种类型的电影史著作,其数量和种类都很可观,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对此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就目前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现状而言,若要在现有基础上有更大的拓展和创新,尚有一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顾名思义,电影史研究主要关注和研究电影本身的发展历史,注重总结和探讨电影创作生产的基本规律;同时,还要揭示各种政治思潮、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对电影创作生产的影响,以及各种电影思潮、电影流派的传承关系与相互影响;并对各个历史阶段一些有影响的或有代表性的创作者及其作品进行评介,对各种电影现象进行论析等。为此,它既可以分为电影通史、电影专门史,也可以分为国别(区域)电影史、断代电影史、类型电影史等各种不同种类。
显然,中国电影史属于国别电影史,它既可以细分为中国电影通史、中国电影专门史(如中国电影文学史、中国电影艺术史、中国电影技术史、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理论史、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电影文化史、中国电影美学史、中国电影思潮史等),也可以分为区域电影史(如香港电影史、台湾电影史、上海电影史等)、断代电影史(如中国现代电影史、中国当代电影史、中国新时期电影史等),以及类型电影史(如中国戏曲电影史、中国武侠电影史、中国喜剧电影史等)。窃以为在当下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首先应该确立“打通”的电影史观念。何谓“打通”?以笔者之见,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把中国现代电影史的研究和中国当代电影史的研究“打通”,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应该汲取的主要教训,认真总结其创作生产的基本规律。即使是电影专门史、断代电影史或类型电影史的研究,也要放在“打通”后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梳理、思考和探讨。只有如此,才能较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电影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
就拿中国当代电影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1949年以来的电影创作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而应该看到,尽管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并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中,有一些传统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在延续中有所变化、有所拓展,这就需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综合研究和深入考察。例如,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即是如此。它萌发于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期间,在40年代抗战电影和战后进步电影的创作潮流中得以完善,并相继出现了一批堪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相媲美的优秀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并未中断,而是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并增添了新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实主义传统则被破坏,虚假的伪现实主义作品盛行。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又有了新的拓展。因而,如何看待和论析当代电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就需要在“打通”以后的历史背景下,看其在弘扬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哪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应该汲取的教训,这样才较为全面和深刻。
又如,不少电影艺术家(如剧作家夏衍、柯灵、于伶等,导演艺术家郑君里、孙瑜、张骏祥等)的创作是跨越现代和当代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的创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故对其美学风格和具体作品的评析,也应该在“打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评价和判断,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和全面。
再如,有些电影类型(如武侠片)在早期电影创作中较为兴盛,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创作基本上中断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而另有些电影类型(如戏曲片)的创作则从早期电影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故而对这些类型片的创作生产进行研究时,也需要把前后两个阶段联系起来,在对照中进行探讨分析。
其二,则要把大陆电影发展史和香港、台湾、澳门的电影发展史“打通”,既由此确立中国电影发展的整体观,也便于对两岸四地电影创作生产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探讨和研究。长期以来,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大陆的电影和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电影在各自区域内独立发展,表现出不一样的艺术风貌。但是,两岸四地电影的创作生产又并非完全隔离,而是不同程度地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中发展的。
例如,香港早期电影的发展就明显受到大陆电影的影响,特别是大陆电影人先后多次南下香港,对香港的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陆的“进步电影工作者转移香港后所开展的进步电影运动,不仅团结了广大的电影工作者,并在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这是极有意义的”。[1]反之,新时期以来,大陆商业电影的勃兴和发展又受到了香港电影的影响,特别在商业电影的创作模式和市场运作等方面,大陆电影人向香港电影人学习借鉴了不少经验。而香港回归以后,大陆电影和香港电影又出现了融合发展之趋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因此,电影史的研究就不能忽略这种情况。
台湾电影的发展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陆电影的辐射和影响,近年来不少台湾电影人也注重到大陆来开拓市场,寻求新的发展,这就使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澳门电影更是在大陆电影的直接影响下萌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这种联系是无法割裂的。至于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和澳门电影在发展中的影响与互动,则更加显著。因此,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对此进行“打通”是完全必要的。
近年来,随着华语电影的创作发展,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还应该逐步扩展到华语电影史。华语电影应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及其他地区以汉语为母语创作拍摄的电影。也就是说,除了两岸四地的电影创作之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凡是以汉语为母语创作拍摄的电影均应包括在内,这样既拓展了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范围,也符合当下华语电影创作生产发展之趋势。
其三,要把对电影创作的研究和对电影产业的研究“打通”。过去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较注重对电影创作发展演变的研究,而对电影产业的发展变化不太关注和重视。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研究电影产业的发展,以及探讨电影创作与电影产业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等,均已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也出版了若干电影产业史方面的著作。但是,目前有分量、有影响的成果还不多,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由于近年来民营电影企业日益增多,它们在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日益增强,所以应对它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而这种研究也需要与建国之前民营电影企业进行一些比较和对照,以便从中总结探讨一些经验教训。
显然,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提倡“打通”,就是要树立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发展的整体观,在电影史的研究中充分尊重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演变的自身规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来总结其经验教训,评析各种创作现象、产业现象和各类电影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认真探讨总结各种基本规律。
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领域,我们既要加强中国电影通史的研究,又要加强各类断代史、专门史、区域史和口述史的研究,从而使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更加丰富、全面,并日趋完善。近年来,在这些领域里的研究虽然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拓展,也取得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但无论就其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来看,均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推进,同时,还有一些空白也亟须弥补。首先,就中国电影通史的研究而言,目前还缺少有分量、有深度、有新意的通史著作。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研究课题,因为它包括了两岸四地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史,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大陆。为此,就需要多方组织力量进行合作研究,在广泛搜集和发掘更多电影史料的基础上,以新的理论观点来完成中国电影通史的研究和写作。前几年,由大陆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台湾电影导演李行、香港电影导演吴思远合作主编的《中国电影图史》无疑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有更多更深入、更全面的通史著作问世。至于电影理论界倡导的“重写电影史”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重写”的工作应建立在对电影史料深入发掘、整理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新史料作为支撑,新的观点也难以确立起来。据笔者所知,近几年,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院校已组织了一批博士生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些重要的电影公司(如明星公司、联华公司、天一公司、新华公司、艺华公司、电通公司、文华公司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博士论文。他们在广泛搜集、深入发掘电影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些电影公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其在电影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等做出了一些新的评价。这显然是“重写电影史”中一项颇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同时,在“重写电影史”中还要对过去电影史上因种种原因而被忽视或被遗忘的一些重要的电影艺术家及其作品,对同样被忽视或被遗忘的一些重要的电影思潮、电影现象、电影流派等,均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评价。
其次,应该抓紧开展“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访谈和研究,因为这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无论是对于中国电影史料学的学科建设、对于重写电影史,还是对于深入总结探讨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经验和教训等,它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项工作首先要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抢救一批珍贵的史料。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历程,虽然不少文字资料对此已有所记载,但是毕竟还十分有限,有些复杂的事件和现象至今还模糊不清。不少电影人在献身于中国电影的奋斗过程中,都有一些独特的经历,尽管也有一些人出版了回忆录,但多数人没有留下回忆录。如果这些经历不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和流传下来,则是很大的损失,许多珍贵的史料将会随着人去而消逝。近年来,一些年事已高的老艺术家陆续驾鹤西去,仅以上海而言,新时期以来先后逝世的著名电影艺术家就有赵丹、吴永刚、孙瑜、沈浮、黄佐临、白杨、张骏祥、万籁鸣、柯灵、桑弧、孙道临、谢晋等,他们都是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做出过独特的贡献,也都曾经历过许多重要的事件,如果早一点启动“口述史”的工作,就可以为后人留下很多他们亲历的史料,会有助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今只能留下诸多遗憾了。这几年来,中国电影资料馆已组织研究者开展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访谈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引人瞩目的成果,这是令人欣慰的,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窃以为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由于“口述史”是通过具体的人来讲述的个人亲历的历史,因此,口述对象的确定要做到普遍采访和重点口述相结合。因人力和经费所限,目前中国电影资料馆“口述史”项目组采访的对象均为80岁以上的前辈电影人。以年龄划线当然可以,也是一种较简便的方法,但是,还应该根据电影史上的一些薄弱环节、重要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以及每个人的成就贡献和身体健康状况等,确定重点的口述对象。先确保重点口述,再完成普遍采访。有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或成就贡献突出者,倘若健康状况不佳,即使不到80岁,也可以先采访。总之,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以免留下遗憾。同时,由于电影发展史涉及到创作、产业、发行放映、理论批评、电影报刊出版等多种领域,所以口述对象的确定也要兼顾各个方面,把各方面的史料都能较好地保存下来。
其二,要做到资料的保存和资料的使用相结合。采访得到的史料经过整理后既要很好保存,同时也要重视使用,充分发挥其作用。《当代电影》已设置了专栏发表部分采访实录,但仅此还不够。采访的录像可以制作成若干专题片在电影频道播放,或制作成光碟出售。这样既可以扩大影响,也可以部分解决“口述史”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使用的过程也是对史料进行分析、考证和鉴别的过程。从事电影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或同一事件的其他经历者,均可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辨别,并确定其价值。
其三,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一些电影人去了台湾或香港发展,因此,中国电影资料馆可以和中国台北电影资料馆、香港电影资料馆等单位进行合作,共同开展“口述史”的工作;或取得他们的支持,派人去台湾、香港等地进行采访。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一些电影人移居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如果有可能、有必要,也可以去那里做一些采访工作。总之,这一项目的采访工作不能局限于内地,还要扩展到域外。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将会更加凸显出来。
另外,电影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也应该是电影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新时期之初,中国电影家协会曾组织一批研究者编撰出版了《中国电影家列传》丛书,可惜后来没有延续下去。近年来,已有如夏衍、田汉、于伶、柯灵、赵丹、沈浮、白杨、张瑞芳、张骏祥、秦怡、孙道临、徐桑楚等不少著名剧作家、艺术家、事业家的个人传记问世,其中有的人(如夏衍、张瑞芳等)还不止出版了一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人物传记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电影史的研究。由于电影人物传记(特别是明星传记)拥有较多的读者,影响颇大,所以实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写作和研究。新时期以来,也有部分前辈电影人发表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如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阳翰笙的《风雨五十年》、赵丹的《赵丹自述》、张瑞芳的《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等,都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这些回忆录均有助于深化和细化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故而应该设法动员更多的前辈电影人撰写回忆录,以此留下更多珍贵的史料。由于回忆录的作者和口述史的对象都是前辈电影人,其主要内容也都是对亲历的电影史之回顾总结,所以这两项工作是密切相关而又互为补充的。
中国电影是世界电影的一部分,其发展既受到域外各种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和各种电影思潮、电影流派的影响,也离不开对域外各国电影的学习与借鉴。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电影艺术、电影技术、电影理论批评乃至电影产业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域外各国电影的影响与渗透,“中国电影可谓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艺术”。[2]
例如,在中国电影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中,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影响最为深远,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对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之电影观念与审美情趣的渗透和定型上,而且好莱坞电影的拍摄方法、叙事技巧、明星制、市场运作方式等都对中国电影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早期中国电影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其影响和渗透更为明显。譬如,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技巧就被借鉴运用于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之中,使中国电影的类型日益丰富多样,如警匪片、战争片、伦理片、喜剧片、音乐片、传记片、西部片等,都以较鲜明的类型特点和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形态呈现在银幕上,从而推动了电影创作多元化的新发展,并给观众以新的审美娱乐享受。其次,好莱坞电影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受到了中国电影界的关注,并被逐步引入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之中。当一部又一部用高科技手段拍摄的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时,不仅吸引了众多的电影观众,而且也推动了中国电影技术手段的变革和创新。数码技术、电脑特技等被更多地运用在影片拍摄之中,使银幕的视听造型更具引人之魅力。另外,当中国电影的管理、发行、放映体制开始进行改革,以便更好地适应中国电影走向市场的需要时,好莱坞的经验则成为重要的借鉴和参照模式。因为在长期的市场运作过程中,好莱坞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于是,制片人作用的强化、重视影片的宣传营销等,均在实践中被逐一推行,在此不赘。总之,长期以来,好莱坞电影既是中国电影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也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竞争对手,这种微妙的关系仍将继续。而我们对于好莱坞电影的了解、认识和评价还不够深入细致,而对于其对中国大陆电影所产生的影响,也缺乏足够的系统研究。至于好莱坞电影对香港电影、台湾电影等的影响,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又如,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好莱坞电影产生的影响之外,苏联电影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无论是对在中国放映之苏联电影的大量评介,还是对苏联电影理论的翻译介绍,以及把苏联各种文学名著进行“中国化”的改编后搬上银幕,均成为当时重要的电影现象。这些工作不仅有效地传播了苏联电影理论,扩大了苏联电影的影响,而且使许多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从中学到了新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与创作技巧,发现了电影艺术的新天地。在此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一直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两国密切的关系,苏联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从创作方法到拍摄技巧,从电影观念到理论批评,从生产体制到管理模式,均以苏联为榜样。对于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这种学习借鉴当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消极影响。如50年代上半期,苏联电影受“无冲突论”的影响,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美化,注重塑造“完美无缺的理想主人公”,以至于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盛行,这种创作思潮也对中国电影产生过不良影响。而管理体制的僵化等,也是一种明显的弊病。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应该深入总结的。
再如,除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苏联电影的影响之外,在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和德国的先锋派电影,以及日本、英国、瑞典等国的电影,均在一定时期或某些方面对中国电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电影理论和艺术实践均受到中国电影界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80年代初,当中国电影创作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纪实美学得以倡导和重视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理论和实践便受到了一批中青年导演和理论工作者的青睐,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对真实性的强调,以及采取实景拍摄和非职业演员等手法,均为该时期不少中国导演创作拍摄时所采用。与此同时,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的写实主义理论和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的学说均受到中国电影界的普遍重视,它们和中国电影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追求真实性的思潮合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实美学,并由此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而法国、德国的先锋派电影所体现出来的探索创新精神,也给中国新一代导演以很大的启迪。此外,日本、英国、瑞典等国的电影,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中国电影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认真关注和研究各种域外传入的电影思潮和电影理论,深入探讨其对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理应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方面,近年来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电影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发展起来的,它所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生活与斗争,而观众对象也主要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所以它在自身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也必然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民族风格。可以说,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新之路,始终是同追求民族化和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特色和民族化美学风格的形成,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分不开的。不少电影工作者在创作中十分注重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借鉴,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因为他们深知:“怎样使我们的电影创作一天比一天更为观众所喜闻乐见,怎样使我国有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影片屹立于世界影坛,研究和吸取我国丰富的古典遗产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课程。”[3]对此,我们今天也应该予以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
首先,从电影创作的取材来看,中国的传统戏曲、古典文学作品等,均成为早期电影创作重要的题材来源。且不说第一部影片《定军山》的拍摄就和中国传统京剧相联姻,仅从古代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来看,就持续不断,延续至今。其次,在电影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不少电影创作者或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戏剧、小说的艺术技巧,或因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和为了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力求在影片拍摄中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一定的民族特色。如早期郑正秋编导的影片就十分注重民族形式的探求和适应观众的欣赏趣味,其《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一些颇有影响的影片,在电影的民族化方面均做了一些开拓性的探索。20世纪30年代左翼新兴电影的崛起,大大密切了电影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并使电影在民族风格的形成上有了新的突破,该时期的一些优秀作品,如《渔光曲》、《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影片,均具有较鲜明的民族化印记。40年代是中国电影趋于成熟的时期,以《小城之春》、《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为代表的一批精品佳作,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和表现生活的真实细腻、艺术手法的朴素深沉及鲜明的民族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题材领域得以拓展,表现工农兵的生活给银幕注入了乡土气息,诸如《白毛女》、《李双双》、《红色娘子军》等影片,无论在继承传统叙事文学的传奇性方面,还是在塑造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方面,乃至在借鉴民间戏曲的艺术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对于电影民族化的倡导,则使不少电影工作者更加自觉地从传统的文学艺术宝库中汲取营养,并有机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于是便出现了《祝福》、《林则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等一批在民族风格的探求上成绩更加显著,也更加成熟的作品。80年代以后,较多的电影工作者在注重学习借鉴欧美电影形式和电影技巧,追求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在民族化追求方面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从《归心似箭》、《巴山夜雨》、《喜盈门》、《乡音》、《心香》等一系列颇受好评的影片在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方面继续进行的新探索,及不断取得的新成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至于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表现民族文化特色方面则较为复杂。前期以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等为代表的影片,更多地表现出对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反思,而到了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则成为民族寓言的虚构。此后无论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梅兰芳》、《赵氏孤儿》等,还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乃至其拍摄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大片,在这方面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和表现。尽管有评论者指出陈凯歌、张艺谋等的影片是在西方的文化视域与认同中来表现中国的民族文化,并对此提出了一些批评,但他们执着的民族文化立场,及其影片由此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特色,均显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一种艺术追求。对其成绩和不足、贡献和缺陷等,也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除了电影创作之外,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建设也同样如此。中国有悠久的文学艺术传统,诗论、乐论、画论和戏剧理论都产生得很早,不仅有一批颇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而且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这就为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对象。我们从中国电影史上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中,就不难看出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早期的著作且不说,仅以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郑君里的《画外音》和徐昌霖的《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等著作为例,即能予以佐证。他们都注重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汲取营养,并有机融合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之中。因此,中国电影理论史和中国电影美学史也实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总之,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努力开拓学科领域,不仅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要不断创新,而且研究视角也要更加多元化,这样既能避免单调和重复,也能使学术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电影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得到更快的发展。
标签: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