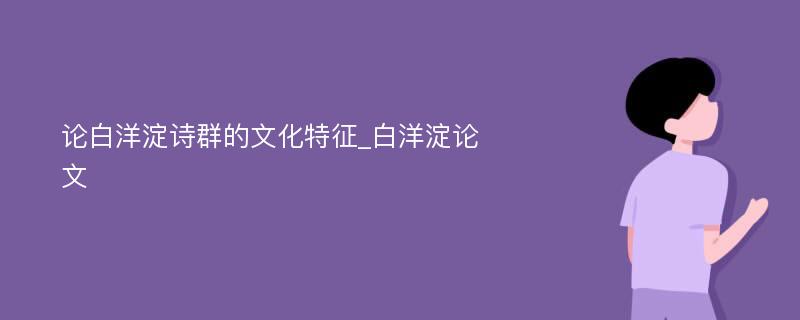
论“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洋淀论文,特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时期,河北省白洋淀成为新诗潮“潜流期”的一个卧虎藏龙之地,这里诞生了一支诗歌劲旅——“白洋淀诗群”,它是伴随着1968年底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出现的一个知青诗人群,有时也被称为“白洋淀诗歌群落”(注:这是牛汉为该诗群的命名。1994年5月6日—9日,《诗探索》编辑部在白洋淀召开“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讨论会上,牛汉认为“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个名字本身很有诗意。“群落”一词,给人一种苍茫、荒蛮、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感觉。)。与当时公开发表的主流文学相比,“白洋淀诗群”处于潜在的地下状态,应归为“非主流文学”,但正是这样的“非主流文学”却客观上成为文革时期真实存在的、更具文学性的文学生态,对重绘当代文学地图,还原当代文学史本来面目构成一种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文学史叙述。“白洋淀诗群”作为一个追认性的命名,只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从时间角度来看,它开始于1969年,形成于文革中后期,1972—1974年达到高潮,随着文革结束与知青返城而在1976年而终止;从地域角度来看,它诞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徐水白洋淀,是插队知青以此为聚集地形成的相对独立的诗歌群体,由于距离北京相对比较近而具有一种形成诗潮的文化优势;从诗人角度来看,它是以北京知青为主(也有个别天津知青)构成的创作群体,如北京知青根子、芒克、多多、依群、方含、宋海泉、林莽等,天津知青白青;从他们的精神履历来看,他们属于“文学食指群”,与他们的启蒙老师食指一样,在“1968年”完成了人生逆转和精神蜕变,都是“六八年人”。“白洋淀诗群”的成员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他们都经历了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身份转变,都从风暴的中心流放到风暴的边缘,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和艺术家庭,多数人曾就读于北京有名的中学,其文学、艺术修养显然比一般人要优越。他们在白洋淀插队时期开始诗歌创作,并写出了各自的代表作,当然,他们的作品主要以手抄或手稿形式流传。
“白洋淀诗群”又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仅仅包括在白洋淀插队落户的知青诗人;广义的“白洋淀诗群”还包括白洋淀的外围成员,他们是“准白洋淀成员”,包括同时期在其它地区(如山西的食指、黑龙江的马佳、内蒙的史铁生等)插队的北京青年(如北岛),留在城里的北京青年,后来聚集在民刊《今天》周围的成员,如北岛、江河、杨炼、顾城、严力、田晓青、阿城、齐简(史宝嘉)等。另外,新时期后的一部分诗人、作家、画家、电影导演等艺术工作者在文革时期都曾与“白洋淀诗群”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流,如画家彭刚、书法家卢中南、作家史铁生、马佳、甘铁生、郑义,电影导演陈凯歌、田壮壮等。许多人虽然不写诗,但通过其他形式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探索不同程度地参与、启迪了“白洋淀诗群”。在一个艺术贫乏的年代,白洋淀养育了一代“离家出走”的艺术浪子。
一、“首都牌跑鞋”:乡村里的城市文化
“白洋淀诗群”是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城市知青诗人群,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介于乡村与城市边缘的知青诗人群。“白洋淀诗群”主要由北京知青构成,是文革时期“北京诗人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北京诗人群为主的“白洋淀诗群”又是一个城市诗人群,代表了一种城市文化。在中国特殊的城乡构成及其经济、文化差异中,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往往有着甚为悬殊的差别。在20世纪60、70年代,尽管整个中国基本处于一种“乡村化”的社会文化结构,城市化的步伐并不激进,整个社会的整体物质水平都不高,但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农村在各个方面(尤其在文化上)还是无法与城市相比。相比而言,北京所代表的是一种“都市化”的社会文化结构,而白洋淀诗群的大多分成员均出生、成长于北京,应是城市(北京)的文化归属。
一个事实是: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中,其诗人构成几乎均以城市青年为主,纯粹的农村青年几乎没有机会加入到这一阵营中。比如北京、上海、贵阳、厦门等城市的青年。城市青年尽管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流落到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但他们与出生并一直生活在农村的青年相比,具有更多的文化便利。在他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实际是把城市文化随身携带到了农村,这种城市文化不但没有被农村文化所改造、同化、泯灭,反而显示出其优越性,并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知识、文化储备。北京作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使得这里的城市青年几乎先天地拥有政治与文化上的先觉者地位,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优先权”,或者说是一种“特权”,这种优先权与特权往往是大多数外省诗人(也包括普通人)所难以享受甚至难以想象的。比如良好的教育,对于黄皮书、灰皮书等的阅读,对于西方音乐与绘画的欣赏,颇为频繁的文学(文化)信息的往来和沟通,群体性的地下沙龙与文学聚会。可以说,在新诗潮潜流期的诗歌演剧中,城市青年担纲主演了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一幕。
白洋淀能够在文革时期成为一个诗歌摇篮,正是因为它有着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文化优势。正如徐敬亚所言:“北京,作为朦胧诗的主要策源地,它从来就没有与外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 与建设兵团、军垦农场(如北大荒)的知青半军事化、颇为严格的管制相比,白洋淀水乡在管理上较为宽松和自由;与其他被流放到更为偏远、落后、艰苦的边疆地区(如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地)的知青相比,白洋淀地区在经济上虽谈不上富庶,但生活温饱不成问题,所以生存的压力较轻,也使他们有余裕的时间、精力去进行艺术探索,而且在文化上,又与1970年代中期(大致在1973年左右)达到高潮的北京地下沙龙(如铁道部宿舍的徐浩渊沙龙)形成互动关系;另外,“白洋淀诗群”中的大部分诗人都是自己联系去的白洋淀,带有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一面。“当时到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无一例外,全是自行联系去的,这表明了在限制个性的大环境中追求小自由的一种自我意识。”[2] 白洋淀美丽的水乡特色,使知青的心灵暂时得到休憩,“当时情形虽然生活困窘,大环境压抑,但美丽的白洋淀,友善的人群,村风的淳朴,使无以为诉的小知青们自然跌入酒神状态”[3]。他们与插队所在地的群众(贫下中农)没有剑拔弩张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他们的地理环境封闭而文化环境自由、宽松且开放,这一点与贵州诗人群大多因为是国民党军官、资本家的后代而成了当时的“社会渣滓”,且不时受到如影随形的政治迫害与歧视,以致精神上承受过于沉重的政治压力明显不同。
白洋淀的地域优势集中体现在北京给予它的文化营养与文化交流上。白洋淀地处农村,但却以开放的环境接纳着来自各地的知青,诗人与后来的“朦胧诗”主将也有较为密切的来往。多多与北岛、江河相识于1970年冬(注:多多在《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载《开拓》1988年第3期)回忆:“我国北岛、江河早在1970年冬便见过面,当时我和北岛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后他与芒克交往密切,还专程去白洋淀会芒克。以后一直到1978年为止,我没有再见过北岛,就我记忆所及,北岛的第一首诗是《金色的小号》。后来我与江河、宫继随有过一个三人游戏的小圈子,常常彻夜交谈。”)。北岛与“白洋淀诗群”往来密切,在1972年就与多多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认识,尤其与芒克交往密切(从1972—1980年)(注:北岛与多多、芒克相识的有关情况,参见刘洪彬《北岛访谈录》中北岛的回忆,载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并在1978年与芒克联手(北岛为主编、芒克为副主编)创办了《今天》诗刊。当时,江河便经常来往于白洋淀与北京之间,与在白洋淀插队的多多、林莽、宋海泉有过很深的诗歌交流。“白洋淀诗群”与北京青年诗人群之间密切的生活往来与文学沟通,构成了一个里应外合的文化(诗歌)圈。“它和北京整个知青群落和‘文革’后一代青年的命运是关连的”[4](p.282)。
白洋淀距离北京很近,与北京的联系非常密切,很多白洋淀知青经常往来于北京—白洋淀两地,各种新的政治、文化信息和思潮很快就会从北京传到白洋淀,在白洋淀造成一种探讨政治形势、进行文学艺术实验的活跃气氛。比如他们与1972年北京的地下沙龙交往频繁,使得第一批诗歌作品最早在这些沙龙中得以流传,实际上是沟通了白洋淀(乡村)与北京(都市)之间文化的中断,构成两地之间互相沟通的文化氛围。北京的知识青年虽然落户在相对封闭的农村水乡,但他们脚下穿着的却是一双外省青年所没有的“首都牌跑鞋”(注:徐敬亚在《王小妮的光晕》(载《诗探索》1997年第2辑)一文中谈到京城文化与外省文化对朦胧诗最初萌发的影响:“这,也是‘崛起的诗群’们在跑道上最初上路时的情景:他们,并没有与北京听到同一声发令的枪响。很多人是在别人抢跑久久之后,才傻忽忽出发的人。他们甚至赤着脚,连一双‘首都牌’的跑鞋都没有”。),这双鞋几乎对他们跑到同时代人的最前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可以设想,在全国都胆小怕事般地蒙昧之际,如果没有早在1970年就开始流传的那两本暗含反叛意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以及后来传达着西方诗智的《娘子谷及其它》、《洛尔珈诗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及复印纸上的《法国象征派诗选》……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歌先锋们,一直到“四五”运动平反时,恐怕也许还在昆明湖的水边像普希金一样忧郁,在皇城的角落里像中学生一样抒情。[1]
同时期的大多数外省青年,不必说在文化控制严密、文学阅读贫乏的文革时期,即使是在文革结束与思想解放运动之间的一段时间空地中,他们的诗歌教育仍然是贫乏和有限的。如徐敬亚说:
在六七十年代之交那沉重的日子里,一本《放歌集》和两本《普希金抒情诗选》,是我唯一、偷偷的食粮。1980年夏天到北京,我和王小妮才第一次从京城那里读到了法国象征派,知道了韩波、瓦雷里和阿波里奈……而从1970年初冬起,上述那些书就在中国文化的中心传播。而那个时候,王小妮正在漫天大雪东北的土房子里读着破旧的中学课本。[1]
在北京文化提供的营养中,书籍阅读和活跃的地下文学沙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外省一般难以见到的“灰皮书”、“黄皮书”等“内部出版”的读物启迪了他们的心智。“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里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5] “灰皮书”与“黄皮书”主要包括两类书籍:一类是马列主义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理论书籍;另一类是中外古今的文学经典名著,其中包括西方各种流派的诗歌,尤以俄苏文学影响为最。第一类书籍的阅读促使他们思想的成熟,加快了对文革时期文化专制“脱魅”的速度;对历史与哲学类书籍的阅读倾向往往带来“思想者群落”的形成(注:比如朱学勤在《思想史上失踪者》一文中记述的文革时期上海青年的地下哲学、历史书籍阅读及其萌发的独立思想者。载《读书》1995年第10期。)。而对文学艺术类书籍的阅读往往相应地形成文学艺术的实验繁盛,更容易成就文学家、艺术家,比如“白洋淀诗歌群落”、贵州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
可以说,“白洋淀诗群”的根在北京,这个根是文化之“根”。北京作为他们的文化后盾,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他们所急需的文化养分,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文化饥渴,使正处于精神与文化饥饿症的一代青年得到补给。白洋淀能够产生如此大规模、群体性、成就相当高的诗歌创作群体,除去个人自身内在的文化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外在的地缘优势,这种地缘优势往往显示了一种文化优势,正是白洋淀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与文化优势,才使它成为新诗潮的一个摇篮。北京不仅是他们物质意义的“家”,而且是他们精神意义的“家”,使他们实现了在离家流浪之后精神与文化的归家。北京—白洋淀之间形成的文化和文学沟通,具有双向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可以从政治与文化专制的包围圈里突围出来,在社会的边缘获得一个相对自由的现实空间与文化空间,最终达到思想的重塑;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剔除与选择中,仍然接受着来自政治文化中心的、未被污染的文学养分和文化底蕴,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仅从文学这一角度而言,可以说,毛泽东所言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1955年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后来这句话在文革中成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流行语录。)在白洋淀得到了某种应验。在对地域因素的强调中,尽管我们不想人为制造或虚构一个新的、极易引起无数误解的“北京/外省”及其连带的“北京文化/外省文化”的二元对立(互补)模式(这种对立,确切地说是一种差异),但新诗潮的发生却在强调着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并且也在不断提醒着这种差异并非虚构。
二、青春的痉挛:知青身份与青年文化的“代际”意义
1969—1976年,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中,一批知识青年的来临,对于白洋淀来说,与其说焕发了诗意,不如说经历了一次“青春的痉挛”。“白洋淀诗群”作为一个知青诗人群,实际上是一个青年诗人群。青年诗人在白洋淀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在白洋淀的时间,大致集中在18岁—26岁之间(注:以白洋淀诗群主要诗人在白洋淀插队的时间与年龄为例:芒克六年,19—26岁;根子三年,18—21岁;多多五年,18—24岁;林莽六年,20—26岁。这样一个年龄段正是他们人生中最富于创新和叛逆精神的时期。)。可以说,这一诗群先天带有“青年文化”特色,而且由这一青年诗群发展演变的“朦胧诗”亦是一个“青春方阵”[6](p.159) 的组合。青年文化是一种富于探索精神的文化形态,青年往往充满幻想,重视感觉,富于叛逆性,容易冲动,走极端,厌恶各种束缚、压抑,追求自由精神和个性独立(注:本文此处对于“青年文化”特征的论述,参考了王富仁论文《创造社与中国社会的青年文化》一文中关于“青年文化”的定位,引自王富仁著《灵魂的挣扎——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白洋淀诗群”的诗歌创作,也从各个层面体现了青年文化的特征。
芒克自然的天性,敏锐的感觉,以及青春的理想情怀和乐观态度,使他具有青年文化特有的浪漫气质,“芒克的诗简隽明亮,散发着青春健康的鼻息和心音。他从个体生命的真切状态出发,白洋淀水乡明朗旷悍的景色正好对应了他自由的心灵。即使那些展示精神颓丧的诗,也丝毫没有知青作品(包括新时期以后的知青文学)惯有的‘落难秀才’的怨气,而是饱满、鲜活、不羁的快活流浪。”[7] 芒克的诗歌体现了青春文化偏于明朗的一面,而这一诗群的其他诗人则体现了青年文化忧郁的另一面,从青春的热情乐观转向青春的叛逆与颓废,在根子的诗歌《三月与末日》、《致生活》与多多的《乌鸦》、《手艺》等诗中得到了张扬。青春期的细腻感伤和忧郁情调在方含的《在路上》、林莽《诉泣》、《凌花》和宋海泉的《海盗船谣》等作品中也表现得非常充分。白洋淀诗群的地下诗歌创作带有一种非功利性的“青春写作”情调,更接近于自然无为的个人化特征,他们没有加入到主流文学创作的规范运作系统,也就不必为主流代言,他们的创作更接近于诗歌生长的原生态。
青年诗人是新诗潮潜流期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整个新诗潮就是青年文化在诗歌领域的反应。王富仁在《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中论及创造社主将郭沫若诗歌的青年文化特征:
郭沫若诗歌中的热情不是老年人那沉静、含蓄的感情,也不是中年人那骚动着的燥热的激情,而是青年人那易燃易熄的燎原烈火。他就用这倏忽而来、倏忽而去的爆发式热情重新组织着眼前的宇宙和世界,给这个宇宙和世界谱上了青春的旋律。[8](p.190)
如果把文中的郭沫若置换成贵州诗人黄翔,那么这一段论述也恰好可以印证黄翔诗歌中的青年文化特征。创作上早于“白洋淀诗群”的贵州诗人黄翔,在27岁(1968年)写下《火炬之歌》,正如郭沫若在青年时AI写作下《女神》一样,同样宣泄了青春的力量和青年人特有的自我表现意识。“白洋淀诗群”中的根子、芒克、多多也都从不同侧面应和了青年文化的特征,比如对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大胆与直率的现实诅咒,自我心灵的真诚抒发,都是青年文化和青春人格的典型体现。
对于年龄的强调,不仅显示文化的生理学意义,同时更显示文化的“代际”意义,也即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意义。事实上,在“白洋淀诗群”向“朦胧诗”过渡之中,不仅是一个新的诗群以及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而更是代表了一代人在历史舞台的崛起,他们作为“第三代群”(刘小枫语)或“第五代人”(李泽厚语)的崛起(注:参见刘小枫《关于‘五四’一代的社会学思考札记》(载《读书》1989年第5期)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471页)。刘小枫全面定义、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断代,他认为“‘五四’一代,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生长,20年代至40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这一代人还有极少数成员尚在角色之中;第二代群为‘解放的一代’,为三四十年代生长、五六十年代进入文化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一代;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为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生长,70年代至80年代进入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称为‘游戏的一代’,即60年代至70年代生长,90年代至21世纪初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李泽厚把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体现了文化学与社会学的意义。尤其在文革之后,整个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们的“代际观念”更为强烈和自觉,以至于青年诗人一旦浮出地表,就立刻暴露出与中老年诗人的对立,而两代诗人的对立根本上是两种文化(青年文化与中老年文化)的对立。新时期以后,“朦胧诗论争”表现了两种文化的矛盾,关于“读懂”与“读不懂”问题,关于创作的“民族化”与“西化”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等等都是论争中的显性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朦胧诗论争”就是青年与中老年、青年文化与中老年文化的一次交锋。
另外,仅就诗歌本身而言,这种“代际”意义一方面显示了他们作为一代人在当代诗坛的崛起,即并不只是某个单独个体的崛起,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崛起;另一方面显示了与同时期的中老年诗人(即新时期后被称为“归来的诗人群”的部分诗人)在创作上的相似性与区别性,这种相似性与区别性也预示了他们在新时期浮出地表之后再一次形成对峙(显性)与沟通(隐性)的局面。
在这里,对于“城市”环境和“青年”身份的强调,并不是有意夸大地域与年龄因素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而试图说明在一种特殊的或者说是畸形的环境中,一些正常环境中平常的力量可能被强化,并“超常发挥”它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能演变为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被放逐的诗歌群落:“互喻”中的诗人集合
“白洋淀诗群”具有群落的性质,但它是一个诗人群,而不是一个诗歌流派。尽管由于“上山下乡”的被放逐命运使他们有了共同的人生经历,从而使他们的诗歌主题也具有了某种相似性,但他们的诗风却并非完全一致的,他们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在当时,他们并非一个自觉的诗学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也不具有诗歌组织的性质,也没有像后来的《今天》诗人群一样,既有自己的阵地,又有固定的文学活动,而且有一个核心人物(北岛),基本上是自觉的“同人”性质的创作集合;“白洋淀诗群”是一个是“诗人”的集合,是一个“诗人”的群落,而不是诗歌流派的形成,但是他们在创作上却是一群“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自觉地、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路径。
如果说中国当代新诗潮在文革初期经过先行者食指、黄翔的逃逸和突围,为新诗潮摆脱“政治专制”的诗歌包围奠定了最初的状态和流向,那么,到了“白洋淀诗群”实际上推进、扩展了新诗潮的河道,一路融纳着不断汇入的诗歌溪流,正向成熟迈进。如果说食指、黄翔是以浪漫主义为主导,融合了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色,只是初步开始了现代主义诗歌的长旅;那么,“白洋淀诗群”已经使兼容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诗风成为主导倾向,从而为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当代的复归和重现作了重要的铺垫。如果说同时期的贵州诗人、上海诗人的群体性还不够显著,诗人的分布也较为零散,规模还较小的话,那么,无论在诗人的数量、诗歌的成就和对“新诗潮”形成的直接、显性影响上,还是在群体性特征与规模上,“白洋淀诗群”都堪称为新诗潮潜流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群体,是中国当代新诗潮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作为一个诗歌群落,“白洋淀诗群”体现了文化的互喻性。也就是说,因为稳定的地理环境,开放的文化环境,他们的创作除了诗群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着诗群内部、诗人之间互相影响的特征。“白洋淀诗群”的这种开放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开放(如各地知青频繁造访白洋淀),而且是文化视野上的开放(如博杂的地下阅读、活跃的地下文艺沙龙等),尤其体现在诗歌写作中的互相影响。“他们相互刺激,相互启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氛围。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诗人都曾与白洋淀有过密切的联系。那儿交通不便,但朋友们的相互交往却是经常的。”[9] 他们中很多人接受了食指的诗歌启蒙,互相摘抄各自好的诗句,不同艺术生态的融合等,使“白洋淀诗群”除具有玛格丽特·米特(Margaret Mead,1901—1978)所说的“前喻型”与“后喻型”的文化特征之外,还具有更加突出的“互喻型”文化特征[10][p.12]。不过,这种“互喻型”的文化特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自喻型”特征。白洋淀形成的是一个自足的文化圈子,一方面他们把追求标新立异的个性和独立性视为青年人的天职,在创作上张扬现代性和个人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诗歌群落,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的阅读背景等,使他们在诗歌主题和艺术手法上也表现出某种一致性或者趋同的倾向,这种一致性和趋同性正是典型的“互喻型”诗学特征和文化特征。另外,“互喻型”的文化特征还有可能在诗歌行为上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引发诗歌行动,比如,“白洋淀诗群”的芒克后来和北岛一起创办非正式期刊《今天》,其办刊宗旨和刊物风格仍然延续了一种“群落性”或曰“同人性”。
但是,一个“文革”的大时代和一个“白洋淀”的小环境,虽然使“白洋淀诗群”必然有着某种共同的经历和情绪,却并没有使每个诗人独立的创作个性泯灭。尽管诞生于共同的地理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中,有着共同的现实与历史境遇,其创作在向现代主义彼岸行驶、靠近的过程中经过了某些共同的风景和目标,但由于个人家庭熏陶、文化修养、个人的美学情趣的趋向不同,他们的各自的诗歌呈现出了“个人化”的风格,在群体性的“同”中又清晰显示出个体性的“异”来。他们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群体性质而混沌了各自的风格,相反,这一诗群在诗歌个性与艺术风格上各具特色,各个诗人在共性中仍保存着面目清晰的个性特征。在这一诗群中,芒克自然而深刻,清新的歌唱交织着深沉的忧伤,更像一个行吟诗人与自然之子,他的诗真正使长久被革命意识钝化的个人感觉回到诗中,重新恢复了生命的各种真实可触的本能知觉。根子以一个末日审判者的无情语调宣告了精神世界的彻底破产,渎神的激情散发着狞厉之美和复仇的快感。多多的冷峻使他更善于揭示出狂欢的历史表象遮蔽下的恐怖真相,他弃绝了赞美与歌颂,更深地传达了“革命化”时代的诸种“震惊体验”。林莽用一支寂寞的画笔写诗,在他自己青春年代的苍白画面上设色,用浓浓淡淡的色彩点染心灵的回声和生命的清愁,有一种静物写生的沉静之美。宋海泉诗歌中刻画出一群“浪流汉”的形象,其“流浪”主题又恰好是一代人“被放逐”的某种人生写照。方含以浪漫主义的“谣曲写作”表达了“在路上”的生命漂泊感。可以说,在文化互喻中,他们是诗人的集合,是独立个体的集合,所以,他们的诗歌写作体现了每个人不同的诗歌“手艺”。
总之,“白洋淀诗群”是在一个特殊的境遇中发展起来的文革“地下诗歌”,而作为新诗潮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白洋淀诗群”以其创作高度把文革“地下诗歌”推向高潮,成为新诗潮在潜流期最具典型意义的诗歌群体,为新诗潮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而它在创作上凸现的个人性和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实验与承续,也为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作为一个生长于城市与乡村边缘的知青诗人群,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不仅对认识同时期其他地域的诗人、诗歌群落有着启示意义,同时也可以观照整个文革地下诗歌与后来的朦胧诗甚至是“第三代诗人”的某些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