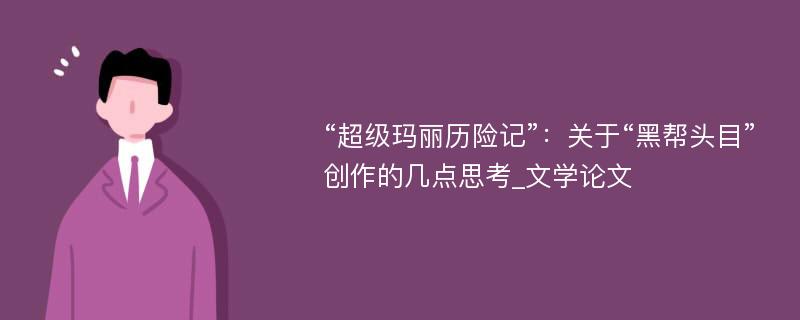
超级玛莉的历险——《匪首》创作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匪首论文,札记论文,玛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一般说,完成一部作品再写创作谈都是不真实的。创作过程如一个水手在狂风大浪中游过大海,一旦上岸,总结成功或呛水的得失未免是事后的分析,对于他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下次游泳的遭遇仍然不可预测。作家的困境在于永远没有熟路可走,前程总是陌生的。如超级玛莉过关,在危机四伏中历险。打熟了前三关,你会厌恶它的平庸,无数刺激的引人入胜的美境诱惑着你,你便不在乎落入深渊跌下火海,或是被千奇百怪的鸟兽吃掉。文学让人上瘾跟电子游戏让人上瘾一样,是人的智慧运动的乐趣和好奇心、冒险欲的亢奋,绝对的得心应手是不可能的,经验都是历险运动的潜意识积累。再高明再科学的战术分析也不能把握一场球赛的胜负,球赛的胜负取决于球员的整体状态、无数复杂的变量因素,也许只因为守门员头天夜晚多打了几个喷嚏,一场球就输了。过程的随机性、偶然性恰恰是情节的精采之处。——就这个意义讲,作家的才气往往在神来之笔,而不在周密思考、细致安排、烂熟构思。一个大气而恃才的作家从不把创作谈当一回事。创作的非理性要求作者跟着感觉走,抛开一切高明理论,不在乎批评家的褒贬。我们往往把用尽可能高的理性层次建设作家,与创作状态的尽可能直觉混为一谈,因而常在两个误区失落——或因缺乏艺术与美学的自觉而直陋浅薄;或因理性干预而理念化。
也许,这便是我写《匪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从文之初,我认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美学追求为目的。因此,我曾不遗余力地抨击打着“乡土文学”旗号的俚俗文艺观。有位著名作家到我的故乡南阳去讲学,阐述自己的乡土文学主张,“我五十年代的作品叙述语言用文学语言,人物对话用土语俗语,到了八十年代,叙述语言也用土语俗语。”什么原因?因为划右派回乡二十年,深得乡亲的温暖与保护(他讲了个把小时摧人泪下的故事),要报答乡亲,必得使用俚俗的语言才能让他们看懂。他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但我问他:你的乡亲文盲很多,即使稍稍识字也难以通篇认读你煞费苦心为他们写的书,那可怎么办?看来这位作家远没有另一位老作家、更著名的作家为农民服务彻底,他在第二届黄河笔会上的发言颇有振聋发聩之功,“这几年我不写小说,因为乡亲们不识字,看不懂,我写电影让他们看。”我倒很想进策,请他不要做作家而做走村串户的说唱艺人。只用在牛屋里扎上脚打梆,乡亲耳不聋,就能为他们服务。这里显然是在讨论如何周到地为乡亲服务,根本不是讨论文学。当沃尔科特(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使用五种语言写作,当同属于第三世界的帕斯(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哈佛、波士顿两所大学名誉博士、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学者的笔写《太阳石》,当莫瑞森(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纽约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兰盾书屋高级编审的目光审视自己的黑人文化,当以写农民乡土著称的塞拉(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痛斥次文学的时候,我们还在与中国的著名作家们讨论文学如何让农民看懂,如果这不是有关文学的荒诞寓言,那肯定是中国作家与世界作家没有共同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类地球上。
我们可以把文学划分为三个领域,可以承认在追求智慧高雅、人性哲理、形式创新的纯文学之外有必要存在表现社会世态、关注人的社会生存、抨击时弊、呼号真理与正义的严肃文学和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通俗文学,但即使以最大限度照顾大众审美的通俗文学,也必须首先具备文学的品性,要求接受者以一定的文化修养,并具有引导接受者不断提高文化修养的功能。如果文学标示一个民族的智慧文化水平,它就不能为局部的甚至恰恰是落后的哪一个阶层服务,它是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财富。纯文学作家应该明白自己的历史重担是民族的知识精英。他的任务是把民族的个性推入人类文化的展廊。有这个志愿,竭尽毕生精力而未必如意,不但可以原谅而且可敬。没这个志愿不可原谅。
我是以危言高论为快感乐事的人,立志把《匪首》写得尽可能雅致些,艺术档次尽可能高些,文化与哲学包容量尽可能大些,这是毫无疑问的。创作准备阶段读了很多野史、禅史、回忆录,研究了一阵子民俗文化、宗教,偶而卖弄一下,便能换来“学者型”和喝采,可见中国乡亲非常容易懵。一知半解故弄玄虚地谈禅说道几乎成为前一阵子最时髦的包装。那时我常想起最多欲放荡的波德莱尔和最富政治激情的三岛由纪夫都是禅的热心爱好者,明白了禅的自欺欺人,常常怀疑煞有介事谈禅的人必然包藏欺世盗名的祸心而泯灭真诚,禅的最有名的祖师不就是用“菩提本无树”的有名的骗人诗句猎取了六祖大师的位子吗?……那时我的确读书入迷,写小说的激情反而随着理性的加浓而逐渐淡漠。是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科技部主任写的介绍混沌学形成、兴起与现状的长篇报告文学惊醒了我。“为什么一颗被狂风摧弯的秃树在冬天晚空的背景上现出的轮廓给人以美感,而不管建筑师如何努力,任何一所大楼的相应轮廓则不然?……我们的美感是由有序和无序的和谐配置诱发的。”一个绳的球,远看是零维的点,近看是三维的球,细看局部是绳——一维的线,再细看,是三维的绳柱,再细析,是一维的麻丝。……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测量船测出的距离与步行测出的距离与蜗牛爬出的距离……英国的海岸线是不可知的。天上的云和涧中的涡流为什么找不到规律而又象是有序?火星上的大红斑、股票的涨落、池塘里鱼虾的盛衰变化……科学家活跃的思维使我震惊,原来高精尖的科学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公式、原理,一项科学发现的突破因素是科学家的直觉智慧,他们的想象力使文学艺术家黯然失色。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不是靠生活阅历和学识积累,尽管这二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激情与幻想,阅历生活,积累学识,都是为了丰富、建设直觉智慧,而不是框限它、磨钝它。作家的佳势状态是天马行空,他一生能达到的高度就是张扬自己的激情与幻想的程度。
我想把《匪首》作为考验我虚构能力、张扬幻想的试验品。
2
选取远离现实的人生故事是因为它可以给我以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和营造虚构世界的自由。那阵子“新写实主义”甚嚣尘上,我因为写了《明天的太阳》,差点被一帮理论家划进这个流派。因为写了系列笔记小说《落叶溪》,又被一位洋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先生)括入汪曾祺、林斤澜一派,称为“改造本土小说成功的范例”。要谋求个人那一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自由,必须躲避。
1、首先得躲开“新写实主义”,躲开乏味的琐屑现实生活,因为它使想象力萎缩。
2、坚决改变《落叶溪》带给人们的传统面目,尤其要抛开超逸散漫的士大夫情调,它太容易使人想到禅。
3、躲开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先锋派浪潮,虽然它的确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唤醒文学的形式意识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一经成为时尚,就有可能批量生产。何况我有我的所长,只有躲开才能显出这所长。
4、尤其难办的是必须躲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用《百年孤独》堵死中国作家最容易走出去的路。中国的民俗文化比拉美更富魔幻色彩,古老神秘、无处不有的渗入民族心理深处的神话传说简直就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灵魂,要概括传达中国文化,道教的影子无可逃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人更依赖直觉,更看重总体动态,而西方人靠分析逻辑、重实证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世界观更接近混沌学。可惜这样足可以震撼世界的文化特征已经被马尔克斯抢先展示。外祖母、干娘、母亲给我讲的神鬼故事不比马尔克斯祖母的故事差,可我再这么讲别人就觉得不过是名作的拙劣仿本。外祖母捐白布扯天桥,让乡亲们上天躲避战乱;公所的曹爷预言县城变乱,预言自己的死期。……所有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只能忍疼割爱。必须拚命在结构、意象、语言上躲着《百年孤独》,不能让朋友说受了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生在马尔克斯之后,真倒霉!
3
中国作家处境的尴尬在于唐宋以降的实用主义文学观经过明清苛繁的文字狱,再经建国以来极左路线的发挥,文学的品性几乎丧失殆尽,人们习惯了文学是政治的附庸,读者要求文学作品必须是对社会政治表明态度的社会思想载体。中国的读者似乎早已忘却了文学对于人的性灵的温柔、愉悦和美的享受。人们更赞赏鲁迅的杂文而对《野草》十分隔膜。明明是写爱情悲剧与人性悲剧的《红楼梦》,必须从中找出阶级斗争才能显出份量,否则就会被认为不过是才予佳人的无聊。一部长篇小说,洋洋数十万言,如果不能让读者读出点沉甸甸的主题,如果不能让读者把握人物的意义、故事的启迪,他们一定会说“这都是啥呀?——没意思!”更可怕的是,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十分觉悟,早已清醒地批判了图解政策配合运动,早已转变了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该是人学的人,在读一长篇时,仍然本能地要求作品必须唤起他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感受、感动、思索的挑战。简言之,他们必须让作家对自己的人物、对自己讲述的故事做出价值判断,如果不是“社会意义”,那就应该是“终极关怀”。总之,文必载道。
这首先是我自己与自己的辩论。
幸亏我读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位教授的小册子。这位洋人对中国典籍旁证博引,论述“文以载道”的演变。原来,“文以载道”始见于魏晋,道,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是宇宙的原理,人与宇宙的关系的理解,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到了唐代才被规定为道义的道,被偷换了概念,成为实用主义文学观的旗帜。“诗言志”,原是主观表现主义,志,个人情致、志趣之谓,并非理想志愿之志。大约一代盛唐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认同,个人自由在文学观上受到限制,也是封建主义体制成熟的标志。我们无法责难中国读者不知道享受文学,几千年尤其近百年中华民族的忧患深重,中国封建主义体制不歇不停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决定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状态,往往统治者一次决策使整个民族几十年陷于灾难,危及两三代人命运。中国人特重口祸文灾,轻易不开玩笑,幽默感被正襟危坐代替,审美享受难免带着罪恶感。所以,肖乾老人在赞扬《尤利西斯》为奇书的同时,又清醒地指出,中国的国情未必适合这样的作品。纯文学在中国也就特别难以生存。以鲁迅的才具,也只能行进于纯文学与严肃文学的交叉地带,阿Q、祥林嫂、孔乙己首先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尽管他是最早使用现代小说技法的大师,你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意识流(《狂人日记》)、黑色幽默(《阿Q正传》、《孔乙己》)博尔赫斯后设主义、荒诞寓言(《故事新编》)……如果说调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最杰出的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学观与现代派的调和者。他以俯瞰超拔的目光、人类文明的目光关照灾难深重的民族,以欧化的艺术改造传统,他不像前几年的“现代派”那样只重皮毛外壳,他在适度照顾中国读者的同时显示自己思想与美学的先锋性,所以,他是中国第一个民族的现代派。
对于中国的文学,力度,仍然是对民族人性状态、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抽象把握。
如果把自己的长篇定位在尽可能靠近纯文学的位置上,就必须舍弃一些作家与读者已习惯的东西才能得到一些新鲜的宁肯是有缺憾的试验成果。
4
我知道我的优势,诸如描写、节奏与节制、感觉性与抒情性,比如人生阅历与感悟,比如书卷气。这些优势是我的巨大障碍,局限我的抽象、粗犷、宏大,既容易限定我在写实领域,又容易破坏作为长篇至关重要的情节结构而流于散漫。
能不能把近代中国溶入中原豫西南的切片?使豫西南的乡土历史、民俗民风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标本?——用具象的富于鲜活人间气息的生活场景,组合出带有隐喻意味的虚构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虽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却已不再是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地域的故事?
问题在于:尽管它已不再是具象的时代的地域,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它又必须让人把握到最真实的历史,民族的历史、乡土的历史。
它必须用活生生的具象的个体生命过程、特殊地域的文化氛围,达到人的生命状态、民族的生存历史状态的最真实的抽象。
再一组逃避:
逃避政治视点,才能达到个体体验的真实。视点是大河中身不由己搏斗挣扎的人,而不是这条河和河的流向。我发现了里尔克的首肯,他说:“这是可能的吗?全部世界历史都被误解了?这是可能的吗,过去是虚假的,因为人们总谈论它的大众,正好象述说许多人的一种合流,而不去说他们所围绕着的个人,因为他是生疏的并且死了?”对历史的正向诠释与反向审视同在一个巷道里,它们只注重历史批判,也就是只注意合流而忽视个人。对于中国的文学来说,跳不出这个巷道就等于永远在套子里,在创新上没意义。
逃避狭义人道主义。人类世界也是一个动物世界,因而才有萨特的存在主义。人文精神、终极关怀在文学里是从人的无奈的异化过程找出慈悲感与怜悯心。《匪首》抹去了所有人的价值判断之后还剩下了什么?——毋宁说抹去了所有的价值判断岂不仅仅是展示生命本能?作家在哪儿?我说,作家在书外。瞧,人们呐,你们朝着自己的人生目的(如果有目的话)竭尽毕生精力去奋斗,去挣扎、踢腾,你们闹腾得整个世界五光十色,你们你逼我我逼你,使时光成为谁也没法把握的涡流。无论自以为高尚的、神圣的、正义的,还是无奈的、不可忍受的……行为在每个生命中都涌动着它自身的价值追求,刽子手老了会得意地向子孙回忆杀人的快感和经历,那是他干了一生的活儿。乞丐会津津乐道讨乞的种种伎俩与无赖相。谁都对自己的活儿自豪,人类世界才成为这种样子。人们呐,读读我的书,瞧瞧你们的德行!就是你们这种德行构成了历史!
逃避哲学分析文化关照。不要昆德拉式的理性视觉和行为提示。希望自己的作品更象一部没有旁白的电影,直接诉诸直观印象。
不用说,它逃避现实主义,也逃避荒诞派和智慧游戏。
5
构思拆白。——这是最要不得的。于读者的自由联想和感受最倒胃口。读者全凭直觉、投入自我才有阅读兴趣。作者把自己的作品解释一番,不但大煞风景而且局限了作品的辐射效应。
如果权当一次随兴所致耳热目赤的聊天,那倒未尝不可。相信读者的审美和智慧,做一次不拘礼节的交流。
那座城是个象征。它是人类集聚群体智慧活动的物质文明的标志。人们创造了它,它又刺激调动着人的欲望,成为劫夺勾斗的罪恶的渊薮。人们最终必然会毁了它,不是因为它的罪恶,而是因为人的无限贪婪。人类最终必然会毁了自己,那时上帝再来,人会得到再造,城也会再现辉煌。
人生都是一个异化自己失落天性的过程。要么被事业或文明异化,要么被本能变为野蛮。兼之的苟苟营营与申的不接受教化殊途同归,季之的现代文明只能使他更软弱。母亲以造物的、大自然的包容养育人类,不管他们贤或不肖。正因为她知道他们必然被异化,知道世界与生命是怎样的过程,她才养育所有的生灵,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是遵循天道。兼之的执著于人生的追求与申的生命本色的蓬勃、季之的理性规范也许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正因为三者不能兼于一身,人性的缺陷才使人类在不断追寻着宗教般的梦想。荞麦,就是这梦想的博大与善良的良智的底蕴。
在具象的乡土历史的抽象上,母亲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荞麦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典范,也是中华美德的化身。兼之代表着封建主义时代流变的潮头,申代表着强大而不可战胜的农民集体无意识,季之预示了近代中国与世界文化沟溶的可能性。这个家庭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各种势力消长的缩影。——我想通过这个家庭每个人的个人生命过程最真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一个时代。兼之一定要死去,因为以官商为代表从封建体制里孕生出的资本主义带着封建主义的劣根性和资本积累初期的罪恶性,它是强大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阶段的畸形物,终将为历史淘汰。——由于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的强大,这种官商杂种会随着历史的反复而重现,但终究是暂时的,一但资本主义体制确立,官与商都将受到法制的制约。早也是要死的。虽然天虫军的多数还活着,还会不断重演集体无意识,但愚昧本能必将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增强理性,民国的建立把中国的文明推进了一步。季之是软弱的,但他在求索,寻找,他在中国会长久地摇摆、无奈,在这摇摆、无奈的涡流中发展。他是有希望的。他代表着民主与法制,代表着文化溶合和人类和解。他的仁爱思想来自荞麦(中华美德)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他是这本书中唯一具有理性自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所以,他在这块土地上的苍白也便不可避免。
我更想同评论家、读者好好探讨一下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尝试。因为我相信形式即内容。没有艺术新鲜的形式,任何抽象、象征都会化为乌有。我认为文学作品第一任务是让人享受。美,是第一位的。而美又非常具象、直观,没有具体的美的形式,也便不能进入深刻。所以,我很在意读者的直观印象,对我的拆白他们最好不必理睬。
1994年10月20日于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