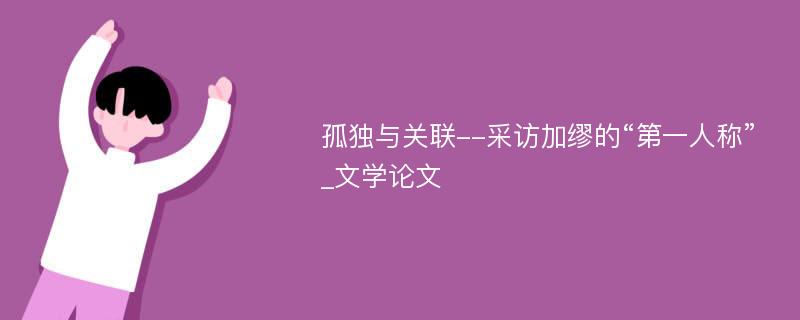
孤单而有联系——关于加缪的《第一个人》的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缪论文,孤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0年1月,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朋友兼出 版商米歇尔·伽俐马。从车祸的残骸中人们找到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那就是加缪的最 后一部小说《第一个人》。在此之前,加缪就曾因他最著名的小说《局外人》和《鼠疫 》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自从《局外人》第一次出版,五十年过去了,它依然是法国本世纪最畅销的小说。199 5年10月,也就是加缪去世35年之后,《第一个人》的英文版终于问世了。加缪的女儿 ,卡特琳娜·加缪被推选来出版这部未曾编辑过的手稿。经整理,它的草稿构成了一部 完整的小说文本,作者的笔记也用来补充说明手稿创作的进展过程。正因如此,读者几 乎无缘得见的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在《第一个人》中得到了展示。这部带有极强自传 性的小说,是加缪对处于世纪之交的阿尔及利亚,对自己极度贫穷的少年时代和没有父 亲的家庭所做的一次深沉的思考。虽然手稿仍未完成,但文本的大部分已具有了加缪特 色的简洁和感性色彩,从而清楚地显示了他最好的作品即将诞生,而过早到来的不幸死 亡却夺走了他年仅47岁的生命。
卡特琳娜·加缪和她的合作者奥拜尔·伽俐马于1995年10月访问伦敦。英国记者拉塞 尔·威尔金森用法语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们讨论《第一个人》的内涵,以使我们在世 纪末可以更好地评论作为作家与政治哲学家的加缪。
(拉塞尔·威尔金森简称“拉·威尔金森”,卡特琳娜·加缪简称“卡·加缪”,奥拜 尔·伽俐马简称“奥·伽俐马”)
拉·威尔金森:在《第一个人》的编辑手记中您说,现在是一个比较适宜接受加缪作 品的时候。您是否认为近些年来加缪已被遗忘?
卡·加缪:他从未被自己的读者背弃过。加缪一直被极广泛地阅读着。在伽俐马出版 社出版的所有作品中他的书销售量最高,而且这种状况已维持了不少年。销售从未停止 过,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说重新发现了他,就是在暗示说这些年他没有读者。这不是事实 。情况是,出版《第一个人》时我对自己说“这将是可怕的”,但只是从批评界的角度 来看是可怕的。我并不是担心加缪的读者,我担心的是评论文章中将会写些什么。
然而有好多迹象表明,今天的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加缪。历史为他们提供了重读加 缪的理由。事实上,人们反对加缪一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性事件,是一件误解。加 缪曾公开谴责过古拉格和斯大林所做的种种清洗。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加缪是对的。在当 时,说苏联有集中营是一种亵渎,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今天我们想起苏联也会记起 集中营,但以前这是不可以的。过去,一个承认自己是左翼分子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这样 想或这样说的。加缪一贯坚持,历史依据标准和历史推理并非应该考虑到的惟一因素, 它们并统领一切,历史对于人的观点总有可能是错的。这正是今天我们要开始思考的方 式。
拉·威尔金森:那么,您是否认为加缪的作品在经历了被知识界孤立的阶段之后,正 逐步得到确认呢?
奥·伽利马:这要取决于不同的阶段。战争刚刚结束,1945年解放时,加缪名震四方 ,为萨特和那一代的所有知识分子所爱戴。一次萨特在美国接受采访,被问及法国文学 的未来,他回答说未来下一个伟大的作家会是加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政治 的而非文学的评判因素介入进来,而从1951年加缪写作《反叛者》那天起,加缪与知识 界的关系破裂了,全部的,几乎是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对他充满敌意。同时,因为 加缪已经不被右翼看好,所以他发现自己已完全是孤家寡人了。
后来在80年代,被人们称为法兰西年轻哲学家的那些人,比如贝尔纳尔和格吕克斯曼 ,他们指出加缪讲了一些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没有人能听得进去的话。他们说,加缪是对 的,而不是那些在萨特影响下渐渐转变了的人,就是说,对共产主义的奉献应该是无条 件的,就像人们在苏联所见的一样。自从那时起,人们对加缪的评价开始转变,并一直 持续到今天。加缪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先前不喜欢他,现在也开始欣赏他。至此,我们回 到文学上来了,加缪一直被公认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拉·威尔金森:这使我们特别关注《第一个人》的出版。这本书将怎样改变我们对加 缪作品的理解呢?
卡·加缪:我们应该记住,加缪没有完成他希望写出的东西——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第一个人》是他最后一部遗作。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因为这本书体现了他的追求以及他整个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苦修克己与感性体验的混 合,体现了他为不能表达自我的人代言的一种心愿。
拉·威尔金森:在写给让·格勒尼埃的信中(格勒尼埃是加缪在阿尔及利亚的哲学老师 ,这些信已在加缪的笔记选集中问世),加缪多次谈到他在《第一个人》写作上的不愉 快。是不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感到有必要去创作一部扛鼎之作?
卡·加缪:他并不是在诺贝尔奖的影响下写作的。对于身为艺术家的他,获得诺贝尔 奖只是一件身外之事。诺贝尔奖来自外界,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一种来自社会的认可 。并且,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写作动力来自内在的需要。对于这部他想写的作品 ,我们不能在仅有它的开头部分的情况下来谈论它。因为他几乎还没写出想要表达的任 何东西,但他需要写。在我看来,如果你看《第一个人》,你会发现它的风格与加缪为 人的方式十分吻合。它与他本人非常相似。
拉·威尔金森: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第一个人》对加缪的思想得出一个更清晰的概念 呢?
卡·加缪:也许不能,因为它只是处在一个粗糙的状态。但是,在这种没有任何艺术 雕饰,也没有任何东西被擦抹掉的情况下,人们反而可以看到更多。或者,与此同时它 呈现得更加真实。我认为他想写一些事情来解释他是谁,解释他与时代强加给他的种种 评判是怎样的不同。他被许多人看做一个严肃的道德学家,但他是在足球场和剧院里领 会自己的“道德”的。这是一些可以感知的东西,而不是仅凭思想传递的东西——那根 本是不存在的。他是通过感觉开始思考的。他无法在艺术手法和文化模式的基础上思考 ,因为对他来说这些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他的道德是“活生生”地感觉到的,来自非 常具体的事物。他的“道德观”从来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传播的。那是他自身的体验, 他思考的方式。有些人发现他关于荒谬的概念非常有趣,而其他一些人则会被他作品中 的太阳、阿尔及利亚和酷热等因素所吸引。
拉·威尔金森:既然《第一个人》是关于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及童年时代经历的, 那么,以往总是把加缪作为法国作家的形象来论述时,他个人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危 机极深的联系却往往被忽视,这不是很奇怪吗?您是否认为《第一个人》会再一次强调 阿尔及利亚对于我们理解加缪的重要性呢?
卡·加缪:我希望是这样。加缪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尽管那里的法国人 因为他的贫困而排斥他,但还是把他纳入法国侨民的行列。从政治观点上说,他推崇联 邦政府。实际上,他认为应该像今天的南非(或者说像南非人正在极力所建设的那个样 子)那样,人口是多民族的,但不同种族的人们拥有同样的权利。他希望阿拉伯人与法 国人,就像生活在那里的其他种族一样,都拥有同样的权利。
拉·威尔金森:您是否认为父亲的缺失以及幼年文化教育上的双重性使得加缪将自己 看做“失根族”中的第一个成员?
卡·加缪:不是在政治层面上。他是“第一个人”是因为他的贫穷,对于人类来说这 一点从来不是太重要。他确实了解阿尔及利亚。他是被自己的国家放逐出来的人,但依 然生活在自己国家的语言之中。孤单而有联系。这不同于那些被流放到一个国家,那里 的语言已不再是他自己的语言的人的情况。对于事情会好起来,他并没有抱太多的希望 ,但他还是希望它朝好的方向发展。阿尔及利亚的暴力事件已发展到了那种程度,以致 那样的暴力一旦产生,将不会再给人以任何的反省余地,也没有斡旋的空间。看看今天 的波斯尼亚,那里的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以及塞尔维亚人,他们制造出那么多的 恐怖事件,以致人们开始产生疑问:在经历各自所做的事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生活在 一起。暴力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仇恨之中。在那里是没有任何反省 和调解的可能性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个人那方面是错的,这方面是对的”;或 是说,“一个人这样是错的,而那样是对的”。而这正是可以使人们,或是使两个人能 够生活在一起的必要因素。只有通过接受彼此的差异,同时也为差异所丰富,我们才能 解决争端。
拉·威尔金森:所以加缪试图生活在一种孤单而有联系的悖论式的境地中?
卡·加缪:我认为加缪感到非常孤单。你可以在他所有的书里看到这一点。“局外人 ”不是加缪,但在《局外人》中却有加缪的一些特征,有那种被放逐的印记。但是他被 流放的地方并不是专指巴黎或其他什么地方,而是由于他的出身,他从知识分子圈子里 被放逐。那是一种彻底的流放。仅仅是因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他处于一种 经常想要从中逃离的境地。在任何时候,你都必须懂得什么是血统,所有的一切都得是 合理化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感到被放逐,体验到了孤单。
奥·伽利马:还有很明显的一点是加缪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中立的”人。因为他是有 使命感的;看看他在抵抗运动中的身体力行吧。他参加了抵抗纳粹主义的战斗。他总是 怀着深厚的责任感投入到对极权主义的反抗之中。人们往往忘了,例如,加缪对佛朗哥 统治时期极端反感,并始终如一。他拒绝到西班牙旅行。他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 为他们接受了佛朗哥的西班牙政府并允许它拥有发言的一席之地。加缪是彻底不妥协的 ,这根本不是中庸立场,这是战斗。他投身战斗并奉献自己。当然,他不是一个存在主 义者,但他是有使命感的。他是一个斗士。他主导名为《战斗》的抵抗运动期刊并非毫 无目的的。
拉·威尔金森:是什么使他的使命感与存在主义者的不同呢?
卡·加缪和奥·伽利马(同时说):他不是存在主义者!
奥·伽利马:他一向拒绝做存在主义者。
拉·威尔金森:孤单而有联系,作为萨特的好朋友却与存在主义信条保持距离,这是 另一个例子吧?
卡·加缪:是的。现在我们开始看清其中的缘由。但通常的情况是只有你直接遭遇了 那些事情,你才能理解它们。每个人都对一个更美好的人类社会抱有很大的希望,而许 多人,包括萨特在内,在开始时都指望共产主义。在人们的理想中,宽容总是占有一席 之地的。但加缪指出,我们需要接纳很多事情,所有的事在被改善之前必须先被接受。 当萨特被问及他是否愿意生活在共产主义政体之下时,他回答说:“不,对于其他人, 它是好的;但对于我,却不行。”他的确是这样说的!所以,很难说他的态度多大程度 上是富于知识分子的理性的。你能想象一个人一面坚决不愿生活在共产主义政体下,一 面却又认为它对于大家都合适吗?这可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萨特却这样做了。
加缪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纯粹的意识形态, 它并不考虑人的具体情况。在经济学中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学想要考虑的是超乎人性 标准的理论,或是作为参数的“人”。如果你不把人抽象化的话,那么最后去撞墙,把 自己撞个头破血流也是不会起作用的。这就是现在加缪为什么更加流行的原因,因为他 总是说“是的,但存在着活生生的人。这是第一要紧的事,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人”。 这就是有联系的含义。
拉·威尔金森:是不是可以说《第一个人》是加缪的经验与哲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呢?
卡·加缪:在已经写成的关于《第一个人》的文章中,提到的是加缪的谦逊,是接受 这些矛盾。去寻找一种解释,那就是死亡。对于加缪,谎言就意味着死亡。这就是为什 么加缪的戏剧《误会》中儿子被他的妹妹与母亲杀死的原因,因为他说了谎。他没有告 诉她们他是谁。她们杀死了他,因为她们并没能认出他来。但是加缪同时也说,强求排 他性就失去真实性。从这一点上,如果你不愿意拒绝关于生活的某些明显的东西,某些 证据,你就不得不接受矛盾。如果你创造了一种体系,你以这么一种途径说“这里有真 理”,那么,你就排斥了所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是说你将扼杀生活。这取决于每个作为 个体的人。他所攻击的并非现存制度。他说:“如果这不错,那就可以更好。”他的目 的是帮助人们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尽可能多地触动人 们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
拉·威尔金森:作为一部为他母亲而写的书,你是否认为加缪对于女性的观念在《第 一个人》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表现?
卡·加缪:在加缪的其他作品中女性出现得比较少,这是事实。她们只拥有分量很轻 的地位。然而,女性在《第一个人》中出现得较多。但不仅是就女人本身而论,它的文 体风格、它的各个构成因素以及他记下的笔记中都表达出更多的女性气质。你可以在这 本书中发现一个真正的爱的故事,一个少年的爱的故事,这也是加缪的第一次。莫尔索 (《局外人》中的主角)和玛丽从未这么重要过。在《正义者》中的多拉和其他剧中的另 一些角色也不是那么为人所知。我觉得对于加缪,母亲就不止于此了。她就是爱,绝对 的爱。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是为她而写的,献给“永远无法读到这本书的你”。并且, “爱”在《第一个人》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加缪爱他从未选择过的那些事物,他以一 种非常实在的方式爱着自己童年的经历。他们的贫穷意味着他们只能考虑该吃什么穿什 么。在他的家里,没有做其他事情的余地。别人是很难想象加缪的感受的。在加缪他们 的生活中,一切都容不得幻想。
法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所以很难说贫穷这一点使加缪的作品显得更 有价值。我宁愿说这使它与众不同。这是必然的,他的处境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自然 ,那些没有这类体验的知识分子将很难理解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使加缪更加宽容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其他人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他们想象贫困, 但他们并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他们对于劳动阶级是心怀恶意的。那是一 种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的视角,也不是萨特所希望采纳的那种方式。因为他们并不熟悉 劳动阶级,他们从未将自己置身于劳动人民之中。他们也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就对此 心怀恶意。加缪对那些陷入贫困中的人则更加靠近。
拉·威尔金森:他的这种靠近是不是产生于他的谦逊呢?这种谦逊可以从《第一个人》 的结尾,他给他以前的老师热尔曼先生的信中看出来。
卡·加缪:这是因为在《第一个人》中他的老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缪不折不扣 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老师。《第一个人》完全是自传性的。他描述的母亲正是我认识的 那个女人,她确实像他所描述的那样。而且这位老师也真的存在。但这同时也说明名誉 对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谢辞中也向他的老师表示感谢 。认可与感激同时存在着。这是要表明他老师为他做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全世界到处 都有像热尔曼先生这样的人。这就是我出版那些信件的原因,为了让他在这部作品中拥 有一席之地。但是我从来都不可能代表我的父亲去行动或思考,去说他可能会说的话, 或去做他可能会做的事。他是一位艺术家,他认为自己是一位艺术家,所以他承担起了 为那些不能或没有机会为自己说话的人发言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