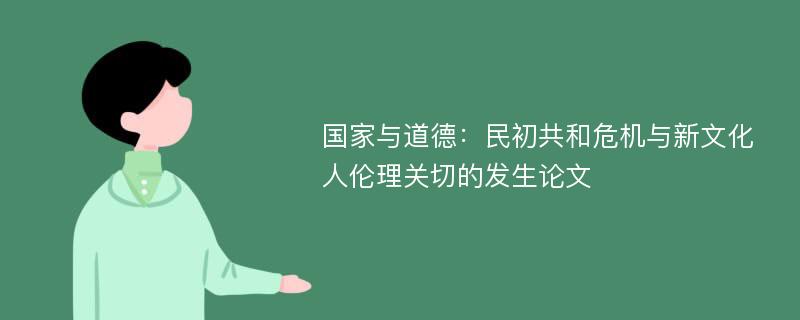
传统与现代
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
季剑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所,北京 100101)
摘 要: 民国初年,知识阶层出于对政治动荡和社会失范的忧虑,普遍陷入到某种道德焦虑之中。道德成为共和国家建设的核心关切,在这种认知背后,是某种国家有机体的观念,由此梁启超等进步党背景的知识分子发展出一种“国性”论述,试图以儒家传统为资源,努力为共和国家建立道德基础;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会,则寻求通过宪法,将孔教确立为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国教。然而,共和国体能否与中国的道德传统有机地结合,共和国家建设是否需要以及需要何种层面上的道德支撑,在张东荪、章士钊等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作为理论前提的国家有机体观念也受到了挑战。而在陈独秀、高一涵等新文化人那里,儒家道德传统成了与共和国体完全不相容且必须被抛弃和否定的对象,与此同时,建立在国民权利基础上的国家观念也取代了国家有机体理论,成为新文化人的主流认识。正是在这一论辩过程中,新文化人的“伦理觉悟”才得以自觉地发生,并发展为对包括儒家道德在内的中国传统的整体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可以理解为对民国初年共和危机中围绕“国家与道德”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的创造性的回应。
关键词: 共和危机;新文化运动;孔教;国家有机体论;伦理关切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共和国体。然而,仅仅依靠一套移植自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足以保证新生的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时人普遍认识到,道德对于共和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这其中既有将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儒家政治传统的残留,也有西方政治学说和国家理论的支持,更有对中国现实的道德状况的忧虑。围绕“国家与道德”这一论题,民初各方知识分子展开了一系列论述,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语境。尤其是新文化人对伦理问题的高度关切,可以看作对这些论述的直接回应。
一
民国肇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都曾提出以传统伦理道德作为国家建设的要素。1912年5月,黄兴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民国初建,百端待理。立政必先正名,治国首重饬纪。我中华开化最早,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立国之要素,即为法治之精神。”[1](P.193)不久,1912年9月,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他强调:“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2](P.3547)11月6日,教育总长汤化龙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也指出,“吾人今日之责任,全在以道德为根本而巩固民国之基础”。[3]
如果说政治人物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主要是基于传统的政教相维的框架,以期实现规范秩序和治理国政的现实目标,那么知识分子的关怀则要更为深远。1912年底,梁启超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问题。他将道德提升到“最高之本体”的地位,认为中国的道德传统构成了“国性”,它构成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存续的基础,今日仍有待发扬淬厉,“夫既以此精神,以为国家过去继续成立之基,即可用此精神,以为国家将来滋长发荣之具”。[4]但这一作为国民结合的纽带和历史传统之依托的“国性”,今天却有失坠的危险,共和国的前途也因此蒙上了暗淡的阴影。[5]
河南省开封市城区农资销售处秦经理表示,开封地区农民开始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磷肥用量减少,更多趋向施用复合肥。她说:“现在农民对化肥价格很敏感,稍微贵一点就不买了。农产品现在不值钱,化肥涨价了,农民不接受。农民的心态是只要有肥料施到地里就行了,不关心化肥品质。”除了农民不接受高价肥以外,渠道商也对厂家调价不买账,一方面现在的铺货量已近70%,而且大部分代理商还有少量库存,需要补货的很少;另一方面,一旦上游厂家涨价,渠道商就不会拿货,因为基层经销商不会买,下游阻力大。
对中国道德传统失落的焦虑,在梁启超周围的进步党背景的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普遍。蓝公武从外来势力入侵、国内变动、物质文明发达、社会生活困难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道德权威失坠的缘由,悲叹道:“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中国之礼教,中国立国之道也,而今皆扫地尽矣,则中国之所与立者,其尚有存乎”。[6]张东荪从法律角度补充了蓝公武的论述,认为除了社会方面的因素外,“今日民德不振,乃法律之原因”。[7]而吴贯因则将道德之堕落归咎于“共和”本身:“盖在纲纪整饬之世,有礼教足以范围人心,有刑罚足以惩治不法,故国民之性质,可以改恶而为善,不至改善而为恶。今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明哲归隐,贼民朋兴,其有能执礼法以相绳者,则彼有民权自由之名词,足以为破坏法律,破坏道德之武器,于是纲纪废隳,藩篱尽撤,遂成为暴民专制之世界”[8],“盖共和之国,不重纲常,不尚名分,惟平等自由之义竞争权利之说,则为一般人所了解。于是民德易漓”。[9]
吴贯因的观点引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共和国体本身就建立在“民权”“平等”“自由”等观念基础上,如果说这些观念会造成道德的沦丧,那只能说明共和国体有天生的缺陷。这当然体现了某种保守主义的立场。然而在另一方面,吴贯因的看法也包含了某种真理性。与中国传统的政教相维的国家体制相比,共和体制似乎只是提供了一个制度的框架,并没有道德教化的功能。传统的伦理道德失去了制度性的依托,其前途确实岌岌可危。事实上,梁启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盖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而数千年社会组织之基础,将翻根柢而动摇”,由于“嬗代之时间太促,发动之力太剧,则全社会之秩序破,非亟有道以维系之,而社会且将自灭”。要维持社会有形与无形的秩序,“非涵养新信条,建设新社会组织,无以致之”。[10]然而,他诉诸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国性”而非“新信条”,而“国性”在共和国体下又自身难保,这一悖论表明为共和国体寻求新的道德基础依然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亟亟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道德基础,并非简单地沿袭传统的政教相维的思维模式,而是有西方的理论资源——“国家有机体”说——作为根据。19世纪末,梁启超在严复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将“群”看作社会政治的有机体的观念。国家作为一种有机体的凝聚,依赖于“公”的道德理想。[注] 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0-76页。梁启超当时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而《天演论》中已经包含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思想。 但梁启超稍晚接触到的德国法学家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1899年4月至10月,《清议报》上就连载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注] 据法国学者巴斯蒂的研究,这个译本是在日本学者吾妻兵治当年的译本《国家学》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的,参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901-1903年间,梁启超在数篇文章都提到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但此时他对卢梭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理论也表现出认同感。大概在1902-1903年间,梁启超转向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11],1903年10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系统介绍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有机体,“国家自有其精神,自有其形体,与人无异”。但国家作为有机体与生物出于“天造”不同,仍是“人力之创作”的产物,其形成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由国中固有之性质与夫外界事物之刺激而生者”,指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性;二是“由君长号令所施行与夫臣民意志所翊赞而生者”,则侧重于制度安排特别是宪政在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12](P.70)。前者对应的是国家的“精神”,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后者对应的是“形体”,即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和宪政秩序。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共同体。
通过到超市、市场调查,没有发现只用太阳能电池板,不接电源就能使用的太阳能充电台灯;网上也没有查到通过简单电路就能有效匹配现有电池板、手机通用电池、普通发光二极管的设计方案。
1903年之后,梁启超基本上秉持国家有机体说来展开他的国家论述,并以此为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申辩。能够与中国数千年传统“精神”有机结合的,只能是君主立宪这一“形体”。他对前者的强调甚至达到了吸纳后者的程度:“当知此君权有限之理想,为我国尧舜孔孟所发明垂教,绝非稗贩之于他国”[14](P.66)。1911年11月,当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大势已去,梁启超仍在幻想实行“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其理由正是“国家为一种有机体,非一时所骤能意造也,其政治现象之变化,必根据于历史”。[15](PP. 43,29)只要仍保留“君主”的象征,中国这个有机体似乎就可以一直存续下去。
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失去了制度性的依托,作为一种游离出来的“精神”,它是否还能在新生的共和国体中安身,这是摆在梁启超面前的难题。但这并没有让梁启超放弃将中国的道德传统安顿到现代国家架构之中的努力,这一任务反而由此变得更加紧迫了。除了借助报刊等大声疾呼外,梁启超还调整了早年反对其师倡导孔教的立场[16](PP. 50-59),转而参与到孔教运动中来。
二
(1)以 DIY为宗旨。当今生活崇尚自由、个性、便捷,因此“DIY”的社会需求便不断提升。通过自己动手亲身体验,把创意灵感变为现实产品。因此,创客空间是知识与实践体验相结合的产物,是亲身实践与创新理念的结合体,是追求开放、共享、创新的 DIY 文化新范式。
为请定孔教为国教事。窃惟立国之本,在乎道德,道德之准,定于宗教。我国自羲炎以来,以天为宗,以祖为法,以伦纪为纲常,以忠孝为彝训,而归本于民。……今日国本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之所不敢为。且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注] 《孔教会请愿书》(孔教会全体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庸言》,第1卷第16号,1913年7月16日。据严复1913年9月25日致熊纯如书:“呈辞乃高要陈氏(按:即陈焕章)所作”,见《严复全集》第8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91页。
请愿书虽然强调孔教的宗教性,但着眼点仍在道德之于“立国”的本体地位,可代表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民初知识分子的共同关切。该项议案经过数次讨论,最终未能获得通过,宪法草案对相关条款的最终表述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第三章第十九条)。[18](P.51)此后孔教会为力争孔教的国教地位,仍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梁启超本人似并未执着于此,在他拟定的《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规定“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之所以列此条款,是因为“孔教屡蒙污蔑,国人固有之信仰中坚,日以摇动削弱,其影响及于国本者非尠”,其中并未牵扯“国教”问题。显然,梁启超理解的“国本”,并非作为宗教的孔教,而是作为中国固有之道德传统的孔教。
不过,借助宪法来维护孔教“国本”的地位,实际上已经说明这一“国本”并不稳固。更重要的是,孔教作为中国道德的源泉,在共和国体的架构中本应安于“精神”层面,一旦牵涉制定宪法这一政治行动,就有越界的嫌疑,考虑到儒教与帝制不可分割的历史,甚至可能会有损孔教的形象。张东荪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孔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之结晶”,自然是中国的国教,然须知“国教非可以强定者也”,“诚以国教非以政治之力而定,乃本于国民自觉心而定耳。是故国教者,社会上之事业,非政治上之事业。往往一语及国教,则连想专制。此误解之由,不可不辨也”,故他认为“近人谋建议案于国会,欲定孔教为国教,且以祀孔配天,此无足为孔子增光,殆亦画蛇添足之类,无足取也”。[19]参与宪法制定的国民党议员谷钟秀明则明确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他针对孔教习惯上已成国教列入宪法不过使之成文而已的说法,反驳道:“且既称孔教习惯上已为国教,即不载诸宪法,于孔教何损,若虑孔教衰微,特以法律之力巩固之,是习惯上已为国教之说根本已失。”[20]所谓“习惯”,义同张东荪所谓的“自然”,均可从孔教形成于历史中的“有机性”这一层面来理解,而如今孔教却须依赖有意识的立法行为来维持不坠,恰恰证明了这一“有机性”的丧失。
此后民国政局的动荡似乎更进一步印证了孔教的尴尬地位。1912年11月4日,宪法草案刚刚通过不久,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11月13日,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停止开会。宪法草案亦束之高阁。此后至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三年多的时间内,中华民国呈现出无国会无议员的状态,共和国体已名存实亡。在此期间,袁世凯颁布了一系列尊孔祭孔的典礼和告令,并于1914年9月28日亲自到孔庙祭孔。[2](PP. 535-538)虽然袁世凯并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注] 关于袁世凯对孔教的态度,参见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60-263页。 ,但他的一系列举动无异于将孔教重新制度化,让人们意识到孔教有与帝制重新结合的可能。如果孔教不止于“精神”,而是侵入到国家制度的“形体”中,它就会直接危及共和国体的生存。《甲寅》的一位作者注意到,“两载以来,故家遗老,辄藉口于国民道德之堕落,欲恢复种种之旧制,谓是可以改良民德,微论其所言者乃等项庄之舞剑,意在于沛公,而不在于陪讌饮也。”[21]语婉而讽,意谓种种恢复旧制之举措实别有政治用心。另一位论者引张东荪为同调,表示“道德之于立国重矣,虽然,此以社会之精神言,而非以政治之作用言”,强调“人之精神藏于内部,必非政治之力所能侵入,故道德由优游涵泳而成,而政治以限制程督为用,执道德主义为政,消极行之,不免空言而无效,积极行之,且有危险之结果”,倡导孔教亦是“执道德主义为政”的表现,将有“流于专制”的危险。[22]后来者记述道,“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的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旧的思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23]虽是后见之明,亦可见旧道德与旧制度之间剪不清理还乱的纠葛。
袁世凯恢复旧制的政治举措,一步步导向帝制运动,这引起了蓝公武、吴贯因等人的警惕。他们一改民国初年热切召唤传统道德的论调,意识到共和国家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蓝公武明确以国家有机体说为依据,断定“古之所谓礼教与近世国家之有机组织不相容也”,他进而对梁启超的“国性”论述也提出质疑,认为“所谓国性者,又空泛而至难解者也”,作为中国道德传统之结晶的“国性”,“在文化未进闭关自守之时,固未尝不可以维系纲纪而范围人心,顾在今日,适足以阻国运之进步文化之发展而已,尚得谓之国性也哉!”[24]吴贯因也对梁启超的“国性”论做出重新解读,指出“国性之为物,不过表示国民一时之心理,原非历代相承成一固定之结晶体”,强调“国性必当时求改良不能作为复古之注解”。[25]
梁启超也调整了自己的论述。他在《大中华发刊词》中虽然仍坚持使用“国性”概念,肯定其“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智术,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其相亲而相扶”,从而“抟捖四万万人为一浑合有机体”的功能,但他已不再强调传统道德的本体地位,也未提及孔教之于“国性”的意义。[26]不久他又撰文,重新阐发了自己对“孔子教义”的看法,他一方面仍认为“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纽”,但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将孔子之言中有关“治国平天下之大法”的部分搁置起来,单单拎出“养成人格”一项,当作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实际上是让孔教退出公共领域,彻底剥离其制度性的层面,让其仅仅作为“私德”发挥作用。[27]针对蓝公武对“复古”的批判,梁启超承认“道德论与复古论相缘。凡倡道德,皆假之以为复古地也”,但仍归咎于少数“居要津之人”,而“吾侪以为道德无时而可以蔑弃,且无中外新旧之可言”,试图通过将道德普遍化,把“旧道德”从政治的泥潭中拯救出来。[28]
基于这种以人民权利为基础的国家观念,章士钊将当时主张国家高于个人的观点称之为“伪国家主义”。[65]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如严复鼓吹的那种“民生所以为国”的声音,在袁世凯专权时期,这种声音代表了官方舆论的态度。章士钊声明,“国为人而设,非人为国而设也。人为权利而造国,非国为人而造权利也”,进而指出“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其方法也。盖人之所求者幸福也,外此立国,焉用国为”[66],我们后面会看到高一涵对这一判断的认同与阐发。当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并引起轩然大波后,章士钊对陈独秀“切身之痛”的“不爱国”之言表示同情和支持,称“吾国之大患,在不识国家为何物,以谓国家神圣,理不可渎”,将其视为“伪国家主义”的表现,这是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的先声。章士钊引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说,指出国家即建立在契约之上,当然可以解散,“解散之后,人人既复其自由,即重谋所以建国之道,再造总意,复创新约”[67],这让我们想起他在民国初年提出的“毁党造党”说,或可称之为“毁国造国”说。国家或解散或重建,完全取决于人民主体性的实践活动。章士钊的国家论述,将“国家”与“道德”这两个民初政论中的核心概念都去神秘化了,消除了它们身上的光环,从而为《新青年》清理出了一个新的文化论辩的空间。
总之,在袁世凯帝制运动造成的共和危机中,中国的道德传统对共和国家建设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民国初年以传统道德为共和国之“精神”的方案已然名誉扫地。那么共和国家应该以什么样的道德作为其“精神”呢?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有论者重新拾起梁启超早年有关“公德”与“私德”的区分:“自泰西学说输入以来,于是乎言道德者有新道德旧道德之分,旧道德之范围在私德,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是也。新道德之注重公德,如爱国心公益心是也。值此世界大通之世,非助长国民之公德不足以立国,社会已承认之矣”。[29]在这里维系国家的不是作为“旧道德”的“私德”,而是作为“新道德”的“公德”,这实际上接近梁启超接受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说之前的立场。但较之依托中国历史传统内涵相对明确的“旧道德”,“新道德”有着更宽广的阐释空间,“国家与道德”的论题,将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继续展开。
三
张东荪的国家观念,深受英国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影响,他曾在论著中多次引用其《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一书,其中有一段话写道:
民国初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曾出台一系列革除旧俗改良风气的措施,这引起了康有为极大的不满,也加强了他对孔教失坠的危机感。他以政教双轨为理据,指出“历史民俗”与“立国之政治无关”,“宗教之事,风俗之源,尤非政府所能干预”。[32](PP. 23,25)在现实的刺激下,作为孔教会的领袖(康有为在1913年9月召开的全国孔教大会上被正式推举为孔教会会长),康有为把孔教提升到“国魂”的地位:
蜡人之机体,有耳目手足,能持行运动,而无心知灵觉,则可谓之人矣乎?若是者,电器之为傀儡者足矣。共和有政府议院政党国民,摹欧钩美,以为政治风俗,而无其教以为人心之本,若是者可谓之国矣乎?……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33](P.16)
国家人格说,乃近世文明之所产,亦近代文化之精髓也。国家之有人格,即是国家之行动,等于国民。国民之有人格与受制限,固不待言,惟国家亦然,此近世国家之真诠也。故近世国家与道德同源,格林亦谓政治上之服从,与道德同其渊源,异乎奴隶,仍保其权于自身。则近世国家,纯为道德之产物,非徒自身有人格,受制限,且必承认国民之人格,其互相交涉之间有一定之规律与严密之径途,各不侵越也。试观吾国何如乎?国家对于国民,素未承认其有人格,国家与国民之交,亦未有一定之径途,独秀君谓如此国家,其何能爱?“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残民之国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吾诵斯言,吾泪如绠。吾国家其真不足爱乎?吾闻人之诟病独秀斯言者众矣。吾亦亟欲驳斥之,然观乎近世国家所以生存之道,无奈其于言外,不能更觅一语。呜呼![注] 张东荪《行动与政治》,《甲寅》,第1卷第6号,1915年5月30日。张东荪有关国家行动之限制的思考,很可能直接源于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第八章“国家目的的性质和随之而来的对国家行动的限制”。鲍桑葵的论述中本身就包含了某种悖论,他认为国家为了促进共同体的全体利益,应该采取行动干预个人生活,这种干预在形式上是积极的,但其目的和效果是消除妨碍美好生活的障碍,因而是消极的,见第195-204页。
实际上,康有为及其领导的孔教运动,已然卷入到民国初年的现实政治之中。康有为对“方今志士,感激于风俗之隳坏,亦多欲提倡道德以救之”表示同情,“然空言提倡,无能为也。必先发明中国教化之美,知孔教之宜于中国而光大之”[38](PP.129,142),所谓光大孔教,自然不止于空言,还要见诸行事。事实上孔教会本身就带有某种政党色彩[注] 1912年7月,康有为在致其弟子陈焕章的信中谈及创立孔教会事:“今为政党极难,数党相忌……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从中可见康有为借孔教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意图。见康有为《与陈焕章书》(1912年7月),《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37页。 ,而康有为除参与推动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外,还提出祀孔祭天的制度设计[注] 关于康有为和孔教会将儒教重新制度化的努力,参见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5-346页。 ,正如论者所言,这些国家制度层面上的诉求,“虽竭力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撇清关系,但客观上却难以区隔,致其政教双轨的制度构想流于虚妄”。[注] 彭春凌《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1页。关于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与孔教会的复杂关系,参见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第264-272页。
平心而论,无论康有为的孔教实践与现实政治——特别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有多么深的瓜葛,至少在价值层面上,他对“共和”仍持肯定的态度。为了协调孔教与“共和”之间的关系,康有为以公羊学三世说和《礼运》大同之义对孔子学说做了“与时俱进”的重新阐释,指出“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31](P.327),甚至将孔子之道发挥到可适用任何时代的程度:“圣人之陈治法,以变万世之变通,非止供一时之行用”[39](P.204)。在孔教的道德内涵方面,针对“或以孔子为旧道德,不能行之于新世”的“今之议者”,康有为强调“新道德、旧道德之名词”皆是谬说,孔子之道德,如智仁勇信、忠恕廉耻等,并无新旧之别。[40](P.332)只是如此一来,孔教既成为普遍的真理,就被抽空了其作为“国魂”的独特性。后来陈独秀即以此否定孔教:“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41]另一方面,康有为理想中的“共和”也并非民国采用的民主共和制,而是他设计的保留君主的“虚君共和”国体。1917年7月他参与清室复辟,目的仍是要建立以溥仪为君主、以中国为国号的立宪国家,“政体虽有虚君,民权仍是共和”。[42](PP.398-399)也许在康有为看来,只有这样的国体才是真正能够安顿孔教之“魂”的“形体”,然而它却不可能实现,孔教终究只能成为“游魂”而已。[43](P.233)
四
1913年8月参与上书参众两院请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还有严复,虽然严复在私人信件中称“孔教会仆亦被动而已”[44](P.291),但从他这一时期的文字来看,在以中国的道德传统为立国之基这一基本立场上,他与梁启超及孔教会同人并无分歧。在1913年的一篇演讲中,他也使用“国性”这一概念,指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45](P.463),观点与梁启超几乎如出一辙。1914年10月,严复向参政院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其中云:
国于天地,其长存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此所由来旧矣。……故近世之言群治者曰:无机之物,则有原子,有机之体,则有细胞,皆为么匿。么匿一一皆有相吸相拒之二力含于其中,此天之所赋也。相吸力胜者,其么匿聚而成体,相拒胜甚者,其么匿散而消亡。国者,有机之体也;民者,国之么匿也;道德者,其相吸力之大用也。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46](PP.475-476)
严复曾提及“斯宾塞以群为有机团体,与人身之为有机团体正同。人身以细胞为么匿,人群以个人为么匿”[47](P.432),显然这里“近世之言群治者”当指斯宾塞,他试图援引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来为他的“立国精神”议案提供理论根据。有机体通过细胞这样的单元(么匿)结合而成,国家作为有机体则依靠国民的结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斯宾塞那里,社会有机体是通过个人之间的自愿合作和交互影响而形成并不断进化的,意识仅仅存在于个人,整个共同体并没有共同的意识。与生物有机体不同,社会有机体不存在调控全体的感觉中枢,不可能设想社会有机体有自己的“精神”与人格。[48](PP.84-131)斯宾塞极力反对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在他看来,社会有机体是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非成员为了集合体的福祉而存在。[49](P.151)这与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大相径庭,而严复这里的表述明显更接近后者。事实上严复对斯宾塞的学说并非存有误解,在1913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严复如此描述斯宾塞的观点:“斯宾塞曰:生物么匿无觉性,而全体有觉性。至于社会则么匿有觉性,而全体无别具觉性。是故,治国是者,必不能以公利之故,而强使小己为之牺牲。”对斯宾塞的论旨领会得相当准确,然而接下来严复在按语中则强调:“至身为社会一份子,则当知民生所以为国,而后种族国土有以长存”,把国家置于更高的位置上,并称斯宾塞“极端主张民权者是也”,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47](P.436)
严复不惜扭曲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突出以道德为源泉的“国性”对于“立国”的重要性,当然出于他对民国“时运”的忧惧。接下来他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而即以此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46](P.477)1914年10月27日,严复的议案经梁士诒、王世澂等二十人联署,在参政院会议上提出并获得通过,当日咨送政府。袁世凯据此于11月3日发布《大总统告令》,认为此建议案,切中时弊,并谕令内务部和教育部及各省按六条办法分别实行。[50](P.475)
康有为对该议案的通过极为兴奋,他在《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一文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鄙人闻之,喜而不寐,距跃三百”[39](P.203),大概这是民国政府办的少数几件让他满意的事情之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立“忠孝节义”作为“立国之精神”的地位,虽未能载诸宪法,但也聊胜于无了。他唯一感到不满的是该案并未提出贯彻实行的根本办法,这办法也很简单,即“尊孔”而已。从康有为的角度来看,道德也好,忠孝节义也好,当然都包含在孔教之中了。
然而在其他人看来,参政院通过这项议案,不过更进一步地证明了传统道德与旧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有论者直斥“严某借此以献媚于总统”,所谓“道德”已成为“一般梯荣沽宠者藉作效顺一人之专用名词”。[29]蓝公武亦指出,所谓“忠孝节义者”,为“古昔封建制信条,乃不适于今日国家之文化”。[24]参政院本身就是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产物。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召集御用的政治会议修改约法,1914年5月1日公布的新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设立参政院,作为临时性的立法机构,严复本人亦是参政院参政之一。参政院通过该议案,本身亦可归入蓝公武所批判的“复古”之举。正是由于受到这些逆共和而动的政治活动的“牵连”,传统道德的形象不断被负面化,但对适应时代要求和共和国体的“新道德”的诉求,也由此变得更加强烈起来。
五
在民国初年围绕“国家与道德”展开的一系列论述中,张东荪的思考尤为引人注目。如论者所述,张东荪“始终将个人道德视为共和政治的基础”[51](P.87),但他对道德的理解却较时人更为深入,也更具弹性。如前所述,张东荪亦对国民道德堕落的状况忧心忡忡,对梁启超等人“以孔教挽回今日道德堕落”的努力亦表示同情与肯定,但又强调“非谓今日道德之救济,仅恃孔教,不过言于生计政治教育之外,而孔教亦为不可轻忽者耳”。[19]孔教固当努力保持,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共和国家的道德基础问题。与梁启超等人相比,张东荪对所谓“国性”“国魂”持一种更为动态的看法,由于时世的变迁和旧道德的瓦解,中国的道德传统已不足恃,“‘中国魂’之说,诚不为无所依据,特不过追思数千年前中国民族所以致兴之道而已,与现今之中国状态与夫国民性质,绝不相同”,仁义廉耻之说,证诸历史,堪为国魂,然而如今“则杳焉无或存矣”。[52]共和国家必须建立在新的道德基础之上,这种道德应该是“应乎时代之道德,所以合群立国之道德,由科学研究而出之道德,非胶柱鼓瑟,谓一民族必有其固有之伦理”[53],他曾把这种新的道德概括为“正谊”,“正谊者,自我实现之方法,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占他人之权利之谓也”,今天要保障共和国体并无他途,“惟促进人民之道德耳。公民之道德在明权利义务之辨,明权利与义务之辨,即在正谊”。[54]
1912年10月7日,陈焕章、沈曾植等人创立孔教会,梁启超亦列名其中。1913年7月12日,由国会选举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开始着手制定宪法。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严复等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17](P.439)《请愿书》写道:
从张东荪的理解来看,“正谊”(rightness)[注] 据《正谊》杂志的封面,“正谊”对应的英译词是rightness,即公正、正当之义。 建立在对权利与义务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西方经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权利意味着一种与自主性相关的、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然而当义务被引入进来作为权利的前提时,权利观念就被道德化了。[55](PP. 105,135-136)义务意味着对国家的道德责任,张东荪的思考以共和国家的建设为出发点,强调公民“一己之义务”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寻求为共和国家建立道德基础的孔教运动中,康有为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就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孔教思想,并倡导建立以基督教为模板的孔教组织。康有为意识到,“方今国争方竞,旧理诚间有不适于时用者。今必当政教分行,双轮并驰,乃不偏弊”[30](P.166),这种受西方政教分离体制之启发而形成的政教双轨的思路,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且欧美各国,政教分离,向不相属。……故其政教并行,已如双轮并驰,一前一却,一上一下,相牵相掣而得其调和也”,“俾言教者极其迂阔之论以养人心,言政者权其时势之宜以争国利,两不相碍而两不相失焉”。[31](PP. 316,327)正因为孔教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无关,故亦可托身于共和国体之下。不仅如此,为了给孔教争取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地位,康有为反复征引英人勃拉斯(Viscount James Bryce)《平民政治》(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一书中的观点,指出美国共和制之所以成功,“盖道德与物质之发明,过于政治,而后能成此大业也”[注]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1912年5、6月间),《康有为全集》第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5页;又见《议院政府无干预民俗说》(1913年2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24页。类似表述在康有为这一时期的论著中所在多有,不一一列举。 ,极力拔高“教”的重要性,淡化“政”的作用。而在中国的语境中,道德当然本自孔教。
英人濮森蒯教授曰:“联想与社会,实同一之构造,今分三段以证之。一曰,凡社会皆不过为个人之精神结合之外部表现而已;二曰,凡个人精神皆为系统中之系统,而此系统实与社会相适应;三曰,社会者虽谓各个人精神所结合而成,然实有实在性,而此实在性,即在精神全体之中也。”濮氏之言,足以证社会意识之存在。社会意识,即国家意识,是故谓国家为意识的结合的混一体,固未尝不可也。[注] 张东荪《论宪法之性质及其形式》,《庸言》,第1卷第10号,1913年4月16日。原文注明这段话引自Bosanquet,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9, p.170。张东荪文中“联想”一词,对应的英文是minds(精神),见[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8页。
鲍桑葵认为,社会是一个精神的共同体,每一个人的精神都是社会精神的表现或反映,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鲍桑葵那里,社会和国家基本上是同义语,都是指一种有机的共同体。按照霍布豪斯(L. T. Hobhouse,1864-1929)的说法,鲍桑葵把“国家看成了我们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认为它是文明生活的有机组织” [注] [英]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汪淑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7页。这本书即是对鲍桑葵国家理论的系统批判。 ,霍布豪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鲍桑葵的国家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批评。从理论谱系上说,鲍桑葵的学说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完全不同[注] 关于鲍桑葵对斯宾塞的批评,见《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第63-64、97-100页。 ,倒是更接近同样源自黑格尔国家学说的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
依据鲍桑葵的国家学说,张东荪一方面认定“国家者,意志结合之产物也”,“为人民意志之结晶体”[56],另一方面又指出“国家有人格,是为法人”。[52]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自身作为行动之主体的人格化的国家,其意志能否与组成国家的人民的意志完全保持一致?如果说“正谊”包含了个人对于国家所承担的道德责任,那么又如何保证国家本身的行动是道德的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鲍桑葵给出的回答非常简单明快:“国家的目的就是道德的目的”,“国家的行动就是维护各种权利”。[57](PP. 204,205)这在理论上当然无可置疑,但张东荪所面临的民初现实却要复杂严峻得多,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
这段话带有明显的国家有机体论的色彩。孔教作为“魂”和“人心之本”,对应的是国家的“精神”,“政府议院政党国民”等对应的是国家的“形体”,两者互不凌越,各司其职,恰如康有为设计的政教双轨架构一般。康有为孔教思想整体上确实表现出道德化的取向[34](PP. 97-101),“盖孔子之道,本乎天命,明乎鬼神,而实以人道为教”[35](P.341),孔教虽然有超越性和神性的一面,但较之佛教和基督教,它的优势主要在于作为“人道之教”的安顿世俗生活的道德力量。然而正因为孔教“言天而不离人”的世俗性,它不可能与政治完全剥离开来。因而,当我们在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表述,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惟孔教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广大无不备,于人道犹详悉,于政治尤深博”[36](P.82),“数千年中人心风俗,政治得失是非,皆在孔教中,融铸洽化,合之为一”[37](P.116)。这些论述显然有违于政教双轨的原则,与传统的政教相维的思路也有别,毋宁说是某种以“教”领“政”的蓝图的表达。[注] 关于康有为民国初年对政教关系的思考,参见张翔《共和与国教——政制巨变之际的“立孔教为国教”问题》,《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2.住房建设和消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房地产发展涉及的行业多、范围广,带动效应明显,对不同行业的带动效应不同(见表1)。
文中所提及的格林(T. H. Green,1836-1882),与鲍桑葵同属英国新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引用的陈独秀的话,出自那篇当时极具争议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这篇文章给张东荪很大的刺激,使得他不得不正视国家为恶这个在民初的中国已然是现实而非理论的问题。抛开文中真挚情感的流露不谈,从论述的逻辑来看,张东荪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人格化的主体本身应受到道德的约束,这是他的理论前提;但他在前面说“国家之行动,等于国民”,着眼于国家作为国民意志之结合体的性质,而在后文中又说国家与国民“互相交涉之间有一定之规律与严密之径途”,则是明明将“国家”与“国民”当作两个不同的人格化的主体了。这里的逻辑漏洞实际上透露出这样一种认知,即在民国的现实政治中,真正作为主体能够行动的那个“国家”,并非全体国民,而只是国民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即是“政府”。在同时期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张东荪亦强调国家与国民之间有严密之分界,互不相越,此乃“制治之根本也”。在专制统治下,国民道德只会日趋堕落,“欲国民进德,必赖自然发展与自然竞争”,此只能“由政府之受制限中得之”。[58]由此可见,政府受到道德的约束,较之“促进人民之道德”更加重要,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前提。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东荪开出了“贤人政治”的药方,最终将共和国家的道德基础寄托在了少数“贤人”身上。
阿里听到这声音,怔了怔,立即停止吵闹。他走近罗四强,把耳朵贴在手机上,站在那里,静静地听,一直听到哀乐完毕。阿里自言自语说:“嗯,姆妈睡着了。”然后就低头沮丧地走进自己的房间,一屁股坐在床上。
六
1914年5月,“二次革命”后避居日本的章士钊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开篇之作《政本》一文带有某种宣言的性质,表达了章士钊对时局的基本看法。有感于民国肇建以来各方势力之争夺与相互倾轧,他提出以“有容”为“政本”:“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59]乍看上去,这像是对政治人物提出的一项道德要求,无怪乎有读者来信批评该文“偏于道德方面,而略于法律方面”,章士钊回应道,不好同恶异正是“法治之精神”得以产生的前提。[60]相对于道德而言,章士钊更看重政治与法制的改进,事实上,他对时人亟亟以道德为虑的思考和言说方式非常不以为然:“徒伤民德之不进,发为迂阔远于事情之论,谓当改造民性以后,始谋政治之改良,而不悟政治不良,即民德不进之唯一症结”,当务之急是谋求政治和法制的建设:“吾国今日之大患,不在伦理之不良,而在政治之不善。不在道德之不进,而在法制之不立。政治者本以济伦理之穷,而法制者即能补道德之不足。”[61]针对道德为立国之基的流行论述,章士钊反驳道:
立国首重道德,此何待论。然立国是一事,培养道德又是一事,不可并为一谈。盖吾人不能虚悬一道德之量,为立国至少之度,不及是焉,即废国不治也。[62]
显然,在章士钊看来,共和国家的建设首先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却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的。重要的是能够见诸实效的政治活动,而非迂阔的道德玄谈。浸淫于英国经验主义的章士钊,把政治理解为在现实中不断摸索和试验的能动性的实践:“盖政治之径途,纡曲错综,不可骤辨。往往今日之发展,昨日乃茫无所知。乙策之成功,非经甲策之失败,将决无其事。故政治之进程,其关键纯在试验,试验一度,即进步一度。”由此,政治制度作为人的实践的产物,其形式较之所谓“精神”更重要。他将制度比喻为“七巧板”,“钧是板也,甲法拼之而未善,安在乙法拼之而亦不善乎?夫近世之政治,所重者形式耳。故国有国体,政有政体,国体政体之争,皆形式之争也。形式不存,即精神不寄”[63],这与当时那种将道德传统视为“国性”“国魂”的主流看法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考虑到这种看法在当时被袁世凯政府利用的事实,章士钊对“道德”和“精神”的贬黜,实有釜底抽薪的意义。
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为梁启超提供了一种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理想中的君主立宪体制结合起来的国家建设方案。换言之,在这一理论框架内,传统作为一种“精神”要素,仍可以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安身,而不会被弃如敝屣,这是卢梭基于自然法和契约论原理的国家学说无法做到的。[注] 关于梁启超对伯伦知理的接受,参见雷勇《国家比喻的意义转换与现代国家形象——梁启超国家有机体理论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渊源》,《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 更重要的是,借助国家有机体说,作为“私德”的传统道德重新获得了正当性。在1902-1903年间完成的《新民说》中,梁启超对道德的看法前后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写于1902年的《论公德》一文批评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所谓“公德”,乃“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这反映了梁启超之前的群学观点。而在1903年的《论私德》一文中,梁启超则强调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为“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此机体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将奚以哉”。[13](PP. 12,132,135)“旧道德”可以起到凝聚和维系有机体的作用,这显然是国家有机体说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章士钊从这种对政治的实践性的理解出发,破除了“国家”的人格性和精神性,在章士钊这里,国家亦不过是人类政治活动的产物而已,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用来满足自身需要和享受自身权利的工具。他对国家的定义是:“国家者,乃自由人民为公益而结为一体,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于他人者也”,“国家者宜建之于权利之上者也”。[64]他特别认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豪斯的观点,曾在《甲寅》上刊载自己翻译的霍布豪斯《民政与反动》(Democracy and Reaction )一书第五章的全章内容(题为《哈浦浩权利说》),并曾多次引用其中的观点。霍布豪斯写道:“夫近世国家之所以高于中古及太古者,以其于人民能力之发展,使得充其量也,以其与人以圆满之自由,而同时复保持社会全体之秩序也。以是近世国家,纯筑之于各种权利之上,而人人之精力,因获由此种或彼种以寻其途而致于事焉。”[注] 秋桐(章士钊)《哈浦浩权利说》,《甲寅》,第1卷第2号,1914年6月10日。英文原文见L. T. Hobhouse, Democracy and Reactio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4, p.127。考虑到霍布豪斯对鲍桑葵的批评,我们会发现章士钊和张东荪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均有其各自的且针锋相对的英国思想脉络,尽管章张两人并未发生直接的论争。[注] 邹小站以章士钊、张东荪、高一涵等人为例,指出民国三、四年间中国思想界受袁世凯专制集权的刺激,开始反思国家主义(包括国家有机体论)的国家观,主张个人自由权利,似没有注意到张东荪的国家观受国家有机体论影响的一面。参见邹小站《民国三、四年间中国思想界对国家观念的表述》,《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4期。
微课热是暂时的,但微课是长期的,教育工作者应当时刻以学生为中心,在微课的设计、应用过程中,应当遵循教育规律,提高学生的主动性,使微课真正为教学、为学生服务[6],如若不然,微课只是一种教学工具,对学习起不了实质的作用。
通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对水库水质进行富营养化评价,汾河二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处于30~50,属于中营养水体。
脂肪失去光泽,偏灰黄甚至变绿,肌肉暗红,切面湿润,弹性基本消失,有腐败气味散出,证明该猪肉已经变质。在冬季气温低,嗅不到气味,通过加热烧烙或煮沸,变质的腐败气味就会散发出来。
七
在《甲寅》杂志上,《新青年》的一些作者已经开始登场亮相[注] 关于《甲寅》与《新青年》的渊源,学界多有论述,较新的研究参见孟庆澍《〈甲寅〉与〈新青年〉渊源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陈友良《从辛亥到五四:欧事研究会、〈甲寅杂志〉与五四知识群体的兴起》,《船山学刊》,2014年第4期。 ,高一涵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我们读高一涵在两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能清晰地发现作者思路的一贯性。1914年11月,高一涵在《甲寅》上发表《民福》一文,直接引用《哈浦浩权利说》中有关国家“建筑于人民权利之上”的观点,指出“国家职务,在致民于各得其宜,不在代民行其职务”。[68]高一涵经由章士钊的翻译对霍布豪斯的接受,确立了他对国家的基本看法。在后来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中,高一涵秉持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强调共和国家作为保障国民权利和发展个人天性之手段和工具的性质:“共和国家,其第一要义,即在致人民之心思才力,各得其所”。[69]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的文章,对章士钊的观点加以详尽的阐发,指出“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国家的终极蕲向(end),仅仅是保护人民的权利,“是故无人民不成国家,无权利不成人民,无自由不成权利,自由、权利、国家,均非人生之归宿,均不过凭之借之,以达吾归宿之所耳”。[70]国家并没有自身的目的,“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71]当个人不再被“国家”定义为“国民”,而拥有了独立自主的“人生”的时候,就获得了更丰富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五四”时期那个有深度和主体性的自我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接受自由主义的国家观的同时,高一涵还对国家有机体说展开了深入的检讨与批判:
3.2 主要临床表现 钩虫性十二指肠炎综合征是由钩虫寄生于小肠所引起的疾病,钩虫性十二指肠炎综合征患者因感染钩虫的数量、时间及个人的身体状况常呈现轻重不一的临床表现。本征多先有胃纳增加而体重减轻,上腹部不适,可有不同程度的隐痛,餐后腹胀。后期食欲不振,可有恶心、呕吐、便秘或腹泻,甚至黑便、柏油样便、血便等消化道出血表现。贫血严重时胃酸分泌减低,可有异嗜癖、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甚至发生嗜酸性脓肿导致肠梗阻表现。钩虫感染轻者可无症状,部分可有贫血、营养不良、胃肠功能失调,重者可有发育障碍及心功能不全[7]。
从这个班结业的学生,因为有前期的培训基础,深受公司重视,累计有二十多名学生在赛德盛公司或在该行业就业。此举为学生打开了就业渠道,校企双方对合作结果都非常满意,双方续签5年合作协议,共同商定保持长期合作。
夫总人类集合之体,而名之曰国家。指人类共同创设之制度,而称之曰国体。是国家为人类所合成,国体为人类所创造,均非自有本体,由勾萌柝甲,含生负性,而自生自长,以底于成者也。近世学者,自伯伦知理(J. K. Bluntschli)以迄韦罗贝(Willoughby)氏,均以国家之起,肇自人类之自觉、感情、意志。而国家有机体说,又为多数学者所斥驳,掊击之至无完肤。[72]
关于国家蕲向一事,至十九棊初叶以前,纷纷聚讼,几为政治学议论汇萃之区,迨近世且有谓为无置论之必要者。又因国家官品[按:即有机体]之说兴,多谓国家如自然物,其生长发育,皆因其有自然主体,主体而外,绝无蕲向之可言。 殊不知国家为人类所创造之一物,其实有体质,即为人类所部勒之一制度,用为凭藉,以求人生之归宿者也。故一国之建也,必有能建之人与夫所建之旨,能所交待,而国家乃生、乃存、乃发达、乃垂久,固非漫无主旨,而自然生成也者。[70]
高一涵大体沿袭章士钊的思路,把“国家”看作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指出它与自然生长的有机体有着本质的区别。高一涵将国家有机体说置于政治学的脉络中考察,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显然下过一番功夫,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把伯伦知理也置于国家有机体说的反对者之列。这里面似乎存在着某种误解,按照梁启超的介绍,伯伦知理已经区分了国家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国家起源“肇自人类之自觉、感情、意志”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中形成一个有机体。[12](P.70)高一涵对伯伦知理的了解很可能并不是经由梁启超,而是通过直接阅读伯伦知理著作的英译本而获得的。因为他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一文,译自伯伦知理的著作《近代国家论》(Lehrevommodernen Stat )第一卷《国家凡论》的英译本The Theory of the state ,[注] 高一涵在文中译为《原国》。 该书与梁启超译介的《国家论》并不是一本书,而且在高一涵留学的大正日本也没有日译本。[73](PP. 211-213)高一涵的译文译自该书第一章第六节,总体而言相当准确。应该说,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也包含了某种自由主义的成分,如他承认现代国家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个人并没有完全被国家吸纳,而是独立地发展自身;国家作为目的并不能涵盖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等等。[74](PP. 58,259-265)凡此种种,都是高一涵在译文中极力发挥的观点。然而总体上而言伯伦知理是一个国家有机体论者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高一涵的译文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近世国家,自拟人身,举其精神、肉体,而一以贯之(精神即民族精神,肉体即宪法也)。”[注] 高一涵《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英文原文见The Theory of the state , p. 61。这是国家有机体论的经典表述,高一涵却未置一词。
森川裕贵推测高一涵在《新青年》上提及伯伦知理,是受到了美国政治学家迦纳(James Wilford Garner, 1871-1938)的著作《政治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的影响。[73](P.213)在这本书中,迦纳把伯伦知理看作国家有机体说“最极端的鼓吹者之一”(one of the most extreme advocates of the organic theory),同时对该学说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批评。[75](PP. 58,63-65)如果高一涵确实读过迦纳的著作,想必应该了解他对伯伦知理的态度。需要补充的是,高一涵提到的韦罗贝(Westel W.Willoughby,1867-1945)是迦纳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学家,而且与中国颇有渊源,他曾于1917年受邀担任北洋政府的法律顾问。韦罗贝著有《国家的性质研究》(An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一书,影响颇大,或亦为高一涵所参考。这本书也批评了国家有机体说[76](PP. 35-38),高一涵把作者列入国家有机体说的反对者,倒是很恰当的。
不管高一涵有意还是无意地曲解了伯伦知理,他反对国家有机体说的基本立场是明白的。此外,他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也持批判的态度,特别指出“国家和社会”与有机体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第一条就是“有机体的构成分子,离了全体,就没有独立的生命;国家和社会的构成分子,就是离了全体,也可以独立生活的”,强调个体不依赖于国家和社会的自主性。[77]但他没有意识到在斯宾塞那里“国家”与“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
如果说国家不是一个有机体,那么也就不需要以道德作为维系这一有机体的粘合剂。于是道德就被从“国性”话语中解放了出来,而完全系于个人。事实上,高一涵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否认国家与道德之间的关联。民国初年各方人士都喜欢引用孟德斯鸠“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的名言[注] 仅举以下诸例,以见一斑:“孟德斯鸠谓专制之国尚威力,立宪国尚名誉,共和国尚道德”(康有为《中华救国论》(1912年5、6月间),《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25页);“孟德斯鸠有言,专制国所以维系者在威力,立宪国所以维系者在名誉,共和国所以维系者在道德,斯言谅矣”(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续第二号),《庸言》,第1卷第4号,1913年1月16日);“吾闻之孟德斯鸠之言曰:共和国以道德而立”(张东荪《正谊解》,《正谊》,第1卷第1号,1914年1月15日);“孟德斯鸠曰:专制以威吓为精神者也,立宪以名誉为精神者也,共和以道德为精神者也”(谷钟秀《良心与势力》,《正谊》,第1卷第5号,1914年9月15日)。时人了解这句话可能有两条途径,或是严复翻译的《法意》,或是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民丛报》,第4、5号,1902年3月24日、4月28日)一文。孟德斯鸠的原文,见(法)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42页。 ,连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总统时的宣言书上,也有“共和国重道德”的话头[78]。1918年11月24日徐世昌发布的“大总统令”上,也有“西哲有言,道德为共和国之元气”的说法,引来了高一涵的不满,他考求孟氏的本意,从学理上对这一名言做了细致的辨析:
他[按:指孟德斯鸠]虽说过共和政府以道德为原理,然他所谓“道德”,乃是政治的道德(politcal virtue),即是爱国与爱平等是也,绝不是那关于伦理的道德与宗教的道德(not moral or Christian virtue)。因为近世谈政治的人,稍明政治原理,即明白道德为人类内部的品德,属于感情及良知的范围。国家的权力,仅能支配人类外部的行为,绝不可干涉人类的思想、感情、信仰。[79]
民初时人引用孟德斯鸠的格言时,对“道德”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表述,与孟氏的原意几乎毫不相关。但这种将共和国体与道德联系起来的思考和言说方式,在当时非常普遍,可以说极具症候性。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它反映了人们为共和国家建设寻求道德基础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高一涵的辨析堪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将道德还原到个人精神生活的领域,道德议题不再受到国家话语的支配,而有可能在与“人”和“人类”相关联的更开阔的层面上展开。
八
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出国亡无所惜的激愤之言,引起舆论大哗,《甲寅》“获诘问斥责之书,累十余通”,章士钊却深表同情。[67]陈独秀在文中以一种冷静而决断的口气说道:“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80]这句话透露出的国家观念,与章士钊的基本一致,不过与章士钊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待国家的思路相比,陈独秀显然对精神因素更为看重,这从该文标题就可以看出来。陈独秀把“爱国心”与“自觉心”都视为“立国之要素”。“爱国心”不难理解,“自觉心”正是那种正视国家之恶与国民之愚的理性态度。陈独秀写作此文,也是为了警醒国人。
在日后的人生旅途上,每当我哼起印度尼西亚民歌《鸽子》,就会想起舒曼,想起了我们在学校烧大茶炉的生活,想起西天大海滩一样的火烧云。想起舒曼离开我们的那个黄昏。
不久陈独秀就在上海创办了直接面向青年发声的《青年杂志》。开篇即以“敬告青年”为题,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等六项要求,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某种道德律令。[81]陈独秀还将中国之危境归咎于“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提倡勤、俭、廉、洁、诚、信诸德,似乎与民初的主流论述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82]但不同的是,陈独秀的道德论述带有强烈的动员色彩,旨在从读者中召唤出新的道德主体以建设共和国家,与民初论述中那种从中国传统道德中寻求共和国家之基础的思路完全不同。陈独秀的这一论述理路实际上引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道德革命的走向。[83]正因为诉诸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陈独秀对传统道德完全持否定的态度:“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作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的“儒者三纲之说”,只是抹杀了个人独立人格的“奴隶道德”。[84]在这里,道德作为塑造人格的基本力量,实际上构成了政治的基础。陈独秀由此把“伦理之觉悟”看作比“政治之觉悟”更彻底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因此他以极为斩截的口气断定:“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85]
陈独秀的“觉悟”,应该与他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下经受的现实刺激有直接的关系,旧道德与旧制度之间的亲缘关系已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也印证了陈独秀“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的判断。1916年8月,袁世凯去世后,国会重新恢复。9月,宪法起草委员会继续讨论1913年未完成的宪法草案,孔教会重新提出列孔教为国教的议案,宪法中有关孔教的表述再次引起激烈争论。[注] 关于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上有关孔教的争论以及最后的结果,参见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第199-212页。 陈独秀对孔教入宪问题极为关注,《新青年》的“国内大事记”栏目持续跟踪报道。在陈独秀看来,“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应该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就应该解决。[41]换言之,孔教不只是关系到制定宪法这一具体的政治行动,更牵涉共和国家建设的基础问题,亦即伦理问题。
在把孔教问题当作共和国家建设的基础问题这一点上,陈独秀和康有为等孔教会人士其实分享着相似的关切。陈独秀乐意承认孔教“为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86],“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87]。这是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判断,但因为双方共同关心的立国之基的问题涉及价值的选择,同一个历史事实却会指向完全相反的立场。陈独秀的态度非常明确:“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88],“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89]
但实际上,王维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画家。尽管目前公认出自他手的画作还没有一幅能确定是他的真迹,但这对于我们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真正关注的,是那画中如诗般的意境。
四是调整水的空间分布。以恢复自然片状流态为目标,拆除大沼泽地386km的防护堤及运河,拆除沼泽地公园与大水杉国家保护区的分离堤坝,将阻碍产生片状沼泽地的41号公路的部分路段改为桥梁或设置路下管道。
回过头来看,民国初年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发展出一套“国性”“国魂”等论述,试图将孔教当作抽象的“精神”,安放在共和国体之中。然而孔教和传统道德在民初共和危机中扮演的暧昧乃至不光彩的角色似乎表明,将孔教从帝制中国的历史中完全抽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孔教不可能和共和国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过来还会威胁后者的生存。孔教和传统道德的这种尴尬处境,在陈独秀那斩截明快的论述中得到了彻底的揭示,甚至被推到了极端。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在历史事实的层面上,作为伦理道德体系的孔教是传统政治的基础,是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礼俗和文化之中的精华(就像陈独秀和康有为都认定的那样),那么在价值立场上对帝制的否定就必然导向对孔教的否定,并进一步导向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性否定。正是在这里,“五四”新文化人吹响了全面反传统的号角。
参考文献:
[1] 黄兴:《致袁世凯等电》,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 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一卷(1913-1916年)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 《政党须重道德》,《申报》1912年11月28日,第7版。
[4]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第1卷第2号,1912年12月16日。
[5]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
[6] 蓝公武:《中国道德之权威》,《庸言》第1卷第3号,1913年1月1日。
[7] 张东荪:《道德堕落之原因》,《庸言》第1卷第12号,1913年5月16日。
[8] 吴贯因:《政治与人物》,《庸言》第1卷第12号,1913年5月16日。
[9] 吴贯因:《中国共和政治之前途》(续前),《庸言》第1卷第23号,1913年11月1日。
[10]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
[11] 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2]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3]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4] 梁启超:《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饮冰室合集·文集》,文集之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5]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文集之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6]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8] 陈茹玄:《增订中国宪法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19] 张东荪:《余之孔教观》,《庸言》第1卷第15号,1913年7月1日。
[20] 谷钟秀:《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释义》,《正谊》第1卷第1号,1914年1月15日。
[21] 无涯:《道德进化论》,《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日。
[22] 光昇:《评法治与德治之优劣》,《中华杂志》第1卷第3号,1914年5月16日。
[23] 毋忘:《最近新旧思潮冲突之杂感》,《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
[24] 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25] 吴贯因:《说国性》,《大中华》第1卷第3期,1915年3月20日。
[26]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27] 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道何由》,《大中华》第1卷第2期,1915年2月20日。
[28] 梁启超:《复古思潮平议》,《大中华》第1卷第7期,1915年7月20日。
[29] 惟一:《最近社会之悲观》,《正谊》第1卷第7号,1915年2月15日。
[30] 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10年秋),《康有为全集》第9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1]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1912年5、6月间),《康有为全集》第9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2] 康有为:《议院政府无干预民俗说》(1913年2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3] 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1913年2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4]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35] 康有为:《孔教会序》(1912年9月),《康有为全集》第9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6]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年3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7] 康有为:《覆教育部书》(1913年5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8]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1913年7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9] 康有为:《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1914年12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0] 康有为:《致教育总长范静生书》(1916年9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1]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42] 康有为:《丁巳代拟诏书》(1917年7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3]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4] 严复:《1913年9月25日致熊纯如书》,《严复全集》第8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45] 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全集》第7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46] 严复:《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严复全集》第7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47] 严复:《进化天演》,《严复全集》第7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48] Ernest Barker,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from Herbert Spencer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5.
[49] 迈克尔·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曾一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50] 《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编者题注,《严复全集》第7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51] 高波:《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52] 张东荪:《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谊》第1卷第7号,1915年2月15日。
[53] 圣心(张东荪):《国本》,《新中华》第1卷第4号,1916年1月。
[54] 张东荪:《正谊解》,《正谊》第1卷第1号, 1914年1月15日。
[55] 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56] 张东荪:《中国共和前途之最后裁判》,《正谊》第1卷第3号,1914年3月15日。
[57] 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58] 张东荪:《贤人政治》,《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号,1917年11月15日。
[59] 秋桐(章士钊):《政本》,《甲寅》第1卷第1号,1914年3月15日。
[60] 章士钊:《人治与法治(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2号,1914年6月10日。
[61] 无卯(章士钊):《迷而不复》,《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
[62] 章士钊:《救国本问(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63] 秋桐(章士钊):《政治与社会》,《甲寅》第1卷第6号,1915年6月10日。
[64] 秋桐(章士钊):《国家与责任》,《甲寅》第1卷第2号,1914年6月10日。
[65] 秋桐(章士钊):《自觉》,《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
[66] 秋桐(章士钊):《复辟平议》,《甲寅》第1卷第5号,1915年5月10日。
[67] 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
[68] 高一涵:《民福》,《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69]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70]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71]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72]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73] 森川裕贵:《高一涵思想的形成——以“五四”前后为中心》,《政论家的矜持:章士钊、张东荪政治思想研究》,袁广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74]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0.
[75] James Wilford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10.
[76] Westel W.Willough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896.
[77] 高一涵:《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78] 《中华民国大总统莅任宣言书》,《时事汇报》第1号,1913年12月。
[79]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80]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81]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82]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83] 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84]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
[85]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86] 《通信》(陈独秀复俞颂华),《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87] 《通信》(陈独秀复常乃惪),《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88]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89]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State and Morality: Political Crisi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Genesis of Ethical Concerns of New Culture Intellectuals
JI Jian-qing
(Institute of Culture Studies,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Concerned about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social chao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tellectuals were widely caught into moral anxiety. Among them morality was commonly recognized as a core iss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publican state. Behind this notion was the 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 which was drawn on by intellectuals with background of Progressive Party, including Liang Qichao, to develop the idea of “national nature”. They made effort to base republican state on a moral foundation with Confucian tradition as its resource. Meanwhile, Confucian Society led by Kang Youwei sought to establish Confucianism as national religion vi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However, the problems that whether republican state form could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moral trad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publican state needed the support of——if any, what kind of——morality, aroused wide controversy among such intellectuals as Zhang Dongsun and Zhang Shizhao. The 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 as theoretical premise was also challenged. Whi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New Culture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Chen Duxiu and Gao Yihan, Confucian moral tradition was totally incompatible with republican state, hence had to be abandoned and rejected. As a result, the conception that state should be based on rights of citizens,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 got popular among New Culture intellectuals. It is precisely in this argumentative process that the “ethical awakening” of New Culture intellectuals was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into the overall denial of Confucian moral tradition. In this sense, New Culture Movement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creative response to a variety of arguments centering around the issue of “State and Morality” in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Key words: Republican crisis; New Culture Movement; Confucianism; the 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 ethical concerns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9)04-0024-15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9.04.003
收稿日期: 2019-04-16
作者简介: 季剑青,文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民国北京都市文化方面的研究。
(组稿编辑:吴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