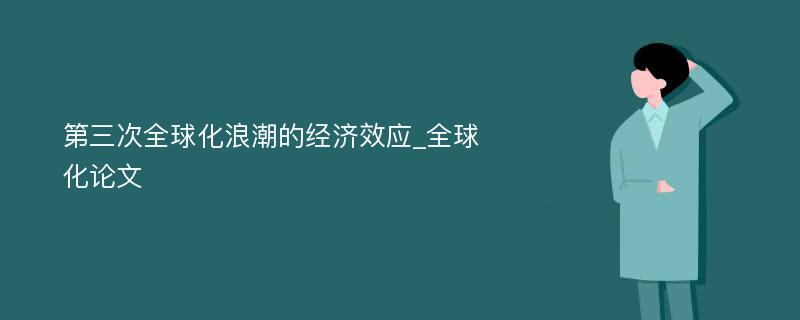
第三波全球化的经济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超越了“相互依赖”,成为理解世界经济变迁和国际政治转型的重要范式,并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向各领域知识谱系渗透的“话语霸权”。“没有人否定全球化业已成为迅速扩散的理论文献的主题”。(注:Jemes H.Mittelman,"Globaliztionan Ascendant Paradigm?"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March 2002,pp.1-14.)全球化发展了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物质主义的认识论,并深受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青睐,迅速形成了一股盛况空前的全球化研究热潮。
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宏观层次来看,全球化对资本流向、产业结构、收入分配、阶级关系、劳工权力、国际权力、环境政策、跨国移民乃至国家主权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进而也必然重塑国际政治格局。然而,全球化影响的微观方面仍不甚清楚,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双刃剑”分析范式,即不论政治、经济或社会领域,全球化总是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后果。“双刃剑”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分析范式,其不足之处在于过分笼统,难以全面揭示全球化的“灰箱”。
在全球化文献中,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更加关注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就收入和工作安全而论,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面对经济变化和技术进步已变得特别脆弱。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开放和一体化,它会塑造新的赢家和输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ck)宣称:“加深的一体化暴露了(社会)沿着一条断层线划分的两个集团,一个是拥有技术和流动性的适应全球市场的集团,另一个集团没有这些优势,也不能察觉市场的大肆扩张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危害。”伍德(Wood)认为,南北贸易对北方国家非熟练工人造成了损害,造成他们的工资减少和工作流失,“北方国家的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苏珊·科林斯(Susan Collins)关注“美国工人的生活及前景正在恶化,工资降低,工作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威廉·克莱因(William Cline)对此给予了回应,他指出“美国收入分配和工资不平等的显著增长”可能刺激保护主义的政治学。(注:Ethan B.kapstein,"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2,Spring 2000,pp.359-384.)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在《1996年总统经济报告》中承认,“贸易可能对工资不平等产生负面影响”,并担心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引发政治上对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的强烈抵制。
对全球化的负面评价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多数学者对全球化引起的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效应表示忧虑。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样充满矛盾和悖论,少数发展中国家驶上了全球化快车道,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日益边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似乎正在形成“南方国家中的北方”这样一种重新分化的新现象。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集团来说,全球化在财富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上都有利于欧洲、北美和日本组成的所谓“三方集团”(G-3),这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马太效应似乎仍然是描述全球化所扮演分化角色的时髦用词。
上述情况表明,在理解全球化这个极其复杂的客观历史进程时,“双刃剑”分析虽然有用,却远不能揭示其实质和全部意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利弊问题,从经济层次来说,它至少产生了四种效应,即减贫效应、边缘化效应、马太效应和社会倾销效应。
一、全球化的减贫效应和边缘化效应
一般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4年,先进的交通运输系统、通过谈判降低关税壁垒等,提高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戏剧性地增加了商品、资本和劳动诸要素的全球流动。结果,世界出口以每年8%的速度递增,相当于世界平均收入增长的两倍;流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外国资本以3倍于平均收入的速度增加。第二波全球化出现于1950-1980年期间,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一体化。(注: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Globaliztion,Growth and Poverty:Building and Inclusive World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4.)在GATT框架下,北美、欧洲和日本通过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恢复了贸易关系。由于普遍推行进口替代政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停留在初级产品出口水平上,并且拒绝外资渗透。第三波全球化(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仍在发展之中。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狂飙突进为第三波全球化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选择向外资开放边界、对贸易开放市场以及改善投资环境等政策措施,导致第三波全球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由于第二波全球化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因此它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与之相比较,第三波全球化被称为“金融全球化”,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圈可点。第三波全球化的不同之处表现为:首先,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选择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其工业化速度明显加快,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其次,其他发展中国家(如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独联体国家等)却越来越被边缘化,人均收入不断降低,贫困随之增加;第三,在第二波全球化中并不重要的跨国移民和资本流动在第三波全球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了清楚地说明全球化对减贫产生的促进作用,世界银行给发达国家贴上“全球化国家”的标签,发展中国家则被划分为两组:“较全球化国家”和“最不全球化国家”。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加入了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较全球化国家”在第一波全球化中只是作为世界经济的外围存在,未能真正进入世界经济的中心;在第二波全球化中,由于多数较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和赢得民族独立,它们普遍从意识形态上对第二波全球化采取了否定和抵制态度。然而,在第三波全球化中,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战后以来国内经济政策的相继失败,这促进它们选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由于经济改革和融入世界市场,较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逐渐取得了成功,其发展速度从70年代平均2.9%增长为90年代的5%。第一、二波全球化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不可与第三波全球化同日而语,第三波全球化最大的亮点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大约30亿人口受全球化所赐恩惠摆脱了贫困。究其基本原因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顺应了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首次成功地利用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赢得了竞争优势。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制造业仅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25%,而1998年上升到80%。中国、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达到81%。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出口基本与世界水平持平。服务业的成长也反映了“较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波全球化中取得了成功。上世纪80年代初,商业服务业占全球富国出口的17%,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9%,在第三波全球化中,富国服务业出口比例增长到20%,而“较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份额却翻了一番,达到17%。(注: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Globaliztion,Growth and Poverty: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2.)
随着主要发展中国家日益深入地嵌入一体化,这些国家更深地卷入了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资本市场,经济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
在第三波全球化中,外资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多拉(Dollar)和克雷(Kraay)发现,投资总水平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重要的是其他因素,如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等。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减贫的前提。以中国为例,1978-1994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增长9%,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13%。由于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赤贫人口总数迅速减少,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正如一些学者所评论的,“这个国家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成功之一”。(注:David Dollar,Aart Kraay,"Spreading the Wealth,"Foreign Affairs,Vol.8,No.1,January/February 2002,pp.120-133.)
大多数穷国被归为“最不全球化国家”类型,这些穷国的经历基本上是反全球化的。“最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三波全球化浪潮中彻底地从全球化国家中分离出来,完全被边缘化了。大约20亿人口没有全面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包括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原属苏联的一些国家。这种边缘化效应的后果是,“最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波全球化中其人均收入实际上下降了。全球化导致“最不全球化国家”边缘化的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资本的逐利性。大多数边缘化国家不能吸引国际资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与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不是通过吸引外资而是通过资本外逃实现的,到1990年,资本最稀缺的非洲地区约有40%的财富为大陆以外所有;二是“最不全球化国家”日益增加的内战风险阻吓了外国资本。内战风险在“较全球化”的发展中地区日益减少,而在非洲却日益增加。非洲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而内战地区初级产品出口往往成为叛乱分子的财政来源,因此非洲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生产实际上潜藏着巨大风险。由于资本高度关注风险系数,因此大多数全球资本仍然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只是全球资本市场的较小部分,即使这部分资本的国际分配也不均衡。在第三波全球化中,一些国家获得了大量外资,而另一些国家则一无所获。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报告,1993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占全部外资的39%。其中80%的外资流入了十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其它国家依次是新加坡、阿根廷、墨西哥和马来西亚。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1993年非洲国家吸收的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外资总额中所占比例减少了5%,1996年非洲所占比例更是猛降到3.8%,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低点。(注:[美]詹姆斯·米特尔曼著:《全球化综合征》,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二、全球化的“社会倾销”效应
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波全球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也是较为突出的。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全球化造成了劳资双方截然不同的处境和立场,有可能引发最为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经济冲突。其中,“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是全球化向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提出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在美国,“社会倾销”一度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护身符,日渐式微的孤立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企图利用它借尸还魂,环境保护组织和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力量则趁机推波助澜,致使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议程在西雅图险遭不测。美国劳工组织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坚决抵制西雅图会议和NAFTA,其根源并不仅在于他们对有关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关注,而在于他们对经济全球化对就业、工资和环境带来消极后果的深刻忧虑。
“社会倾销”是近几年在反全球化和抵制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队伍中流行起来的一个口头禅,意指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造成工作机会从高工资、高保障的发达国家流向低工资、低保障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不发达国家)。它的极端意义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商品出口将低劳工标准和低环保标准“输出”到发达国家。从生产全球化来说,全球化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跨国公司为了规避福利国家过重的税收负担、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严格的环境标准,把工厂从母国迁往发展中国家,从而造成母国在相应岗位上就业的工人集体失业;从贸易全球化来看,全球化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导致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工人大量失业。发达国家的工会和环保组织据此抱怨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向发达国家输出低劳工标准和低环保标准。
工作流失论(或产业空心论)是社会倾销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顾名思义,这里是指工作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工作机会就开始外流,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电视制造业整体流失,钢铁业日薄西山,汽车制造业受到冲击;工业界数百万待遇优厚的稳定工作消失,为低薪的服务业工作所取代;教育和技术水准最低的工人薪资开始下降。随着科技兴盛,服务业工作逐渐减少,教育和技术水准稍高的员工待遇也逐渐走下坡路,他们被迫和非技术工人争夺最低劣的工作。美国很多高薪而技术层次较低的工作,现在已经自动消失或转到外国去了。英国经济学家伍德认为,与第三世界国家贸易,对第一世界国家低技术劳工大批失业的影响比科技更大。他说,就整体而言,贸易使第一世界国家对低技术劳工的需求减少大约20%。其他国家在需要较高技术的制造业领域竞争力的增强,会使这种冲击变得更为强烈。“愈来愈多证据显示自由贸易确实可能带来严重损害,而且可能弊大于利,这对崇尚自由贸易的美国经济学界正造成强烈冲击,其严重性有如宗教危机。”(注:[美]理查德·隆沃斯著:《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96-97页。)资金、贸易和科技正互相结合,彼此推波助澜,共同消灭工作,降低薪资。美国作家埃伦哈特说:“美国老百姓注意到,过去20年美国失去了4000万个工作机会,并断定绝对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他们看到美国许多大公司把大部分生产作业搬到第三世界国家,并相信他们赖以维持家计的宝贵工作已跑到泰国和斯里兰卡。”(注:美]理查德·隆沃斯著:《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第98页。)因此,美国劳工阶级在1993年反对国会通过NAFTA执行法,其主要依据就是罗斯·佩罗所说的“吸吮效应”。一俟NAFTA正式启动,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会被墨西哥“吸吮”过去,因为墨西哥的劳工和环境标准要比美国低很多。
许多学者对工作流失和结构性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唐宁(John Dunning)认为,发达国家失业率呈上升趋势,是因为一般人缺乏以新技术或技术革新为特征的生产系统所要求的那些技能。格累德(William Greider)将结构性失业同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联系起来,指出“工作流失导致失业”,因此失业完全是由于跨国公司跨境生产和贸易所造成的。在这种全球化风暴中,“最大的输家便是劳工。不管是工会的会员,还是一般的工薪族都是如此。在世界上,虽然人们的工资总的来说有起有伏,但工人们在这场全球经济中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他们对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和雇佣条件方面的控制。”(注:杨伯溆著:《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213-214页。)
工资趋同论。由于跨国公司选择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投资建立工厂,导致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下降,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上升,最终造成二者逐步趋同。美国工人普遍担心其薪资会“中国化”或“墨西哥化”。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如果一种商品或服务能同时在低薪国家和高薪国家制造,两地薪资差距将逐渐缩小。随着美国钢铁业转移海外,印度和巴西钢铁工人的薪资逐渐提高,美国钢铁工人薪资却不断降低。虽然目前两者尚未相等,但如果现有趋势继续下去,就会发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趋同。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柏利斯(Gary Burtless)对此评论说:“如果这些假定是正确的,那么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活动,将使两国劳工的薪资趋于平等;如果接受要素均等化理论,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大多数墨西哥人来说是好消息,对美国和墨西哥拥有相同技能的那些劳工,却是坏消息。”美国工会和劳工集团认为,全球化是劳工收入降低和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因而对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贸易自由化议程一概加以抵制。“因为在全球化经济下,那些缺乏技术的工人,现在必须与数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亚洲人竞争。”(注:[美]理查德·隆沃斯著:《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第11页。)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劳工和许多知识分子对NAFTA和WTO这类超国家机构十分反感和强烈抵制的原因。1997年9月,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主持的“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测验”发现,尽管经济运行健康,多数美国人仍反对扩展贸易。一个绝对多数,即54%的美国人反对NAFTA扩大到拉丁美洲。贸易扩展仅得到多数年轻人(18-29岁)、受过高等教育者(研究生学历)和高收入者(年收入逾75000美元)的支持。(注: William A.Lovett,Alfred E.Eckes,Jr.and Richard L.Brinkman,U.S.Trade Policy:History,Theory,and the WTO,M.E.Sharpe,Inc.,1999,p.104.)
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召开期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赶去进行了抗议示威活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相反,美国的跨国公司对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和双边主义的自由贸易谈判格外青睐。在乌拉圭回合中,跨国公司自始至终扮演着“垂帘听政”角色,实际上,以GATT和WTO为框架的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程度地反映了跨国公司的利益诉求。发达国家的劳工阶级在这场零和博弈中无疑成了输家。
三、全球化的马太效应
全球化造成的“马太效应”涵盖着两个层面:一方面,全球化造成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加重了国家内部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对称。“自80年代初,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肯定已形成了。”(注:David Johnston,"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Found Substanfially Wider",New York Times,5 September 1999,p.14.)对外贸易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日益暴露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面前。由于全球化的分配效应,全球分配结构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次变化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劳工。以美国为例,从里根时期到克林顿政府,美国整体所得的90%集中于收入最高的20%阶层中。198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男性工人薪资为收入最低10%32人的3.2倍;但到1995年,这个差距扩大到4.4倍。1980-1995年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0%工人的税后所得增加了1.7%,收入最低的10%工人税后所得却减少了9.6%,而中等收入的员工实际所得减少了3.6%。(注:[美]理查德·隆沃斯著:《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第78页。)上世纪90年代,除了最上层20%工人外,其它劳工薪资不是减少就是毫无增加。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马太效应。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世界经济可以划为四类:需要经济、充足经济、多余经济和奢侈经济(注:“四种经济反映世界贫富悬殊”,《参考消息》2004年10月24日,第3版。)。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生活在需要经济之中,因为他们甚至得不到充足的食物。在某些局部地区(社会),由于不平等有所减少,充足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多余经济依赖于技术的日臻成熟和完美,以应付难以餍足的现代消费主义。财富、名誉和金钱则意味着一种奢侈经济,正是这种奢侈经济操纵着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需求经济阶段,而奢侈经济的幽灵却在欧美日游荡,二者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反差。美国CEO的年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416倍。(注:Jay Mazur,"Labor's New Internationalism,"Foreign Affairs,Vol.79,No.1,January/February 2000.pp.79-93.)而比尔·盖茨等4人的财富竟高于42个国家、6亿人口的GDP之和。(注:“四种经济反映世界贫富悬殊”,《参考消息》2004年10月24日,第3版。)
第三波全球化无疑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成长,但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却是不成比例的。一小撮国家及跨国公司垄断游戏规则并掌控着世界市场。跨国公司是第三波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全球100个最大经济体中,竟然有51个是跨国公司。(注:Jay Mazur,"Labor's New Internationalism,"Foreign Affairs,Vol.79,No.1,January/February 2000.pp.79-93.)而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来源于发达国家。可见,由国民财富体现的国家权力差距依然是巨大的。“在经济总量上,没有几个国家有望挑战中等甚至较小的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即使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可绝对差距如此之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会消除。”(注: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5页。)
目前,发达国家的学者普遍关注全球化引起的国家内部分配不平等,以致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世界经济论坛前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等都宣扬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危害论”。然而,对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影响更大的却是全球化扩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首先,过去积累下来的国家间不平等现象非但没有因全球化而消除或减缓,反而日益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4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CDP为高收入发达国家人均CDP的2.4%,后者是前者的43倍,而1994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6%,后者是前者的62倍。(注:李建军、田光宁:“经济全球化中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许多因素表明,第三波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中的马太效应有着内在联系。第二,目前缺乏一个进行有效全球治理的机构及其法律。由于全球化促使技术愈来愈复杂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进一步扩大,马太效应造成的后果堪忧。全球化对单个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有益的,印度、中国和墨西哥经济迅猛发展就是例证,这些国家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降低。全球化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边缘化和挑战,意味着它们将从“全球化国家”和“较全球化国家”中彻底分化出来,“全球化国家”和“较全球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以“最不全球化国家”的边缘化为代价,这是第三波全球化引起的巨大的政治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最终将会影响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
标签:全球化论文; 第三波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边缘化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