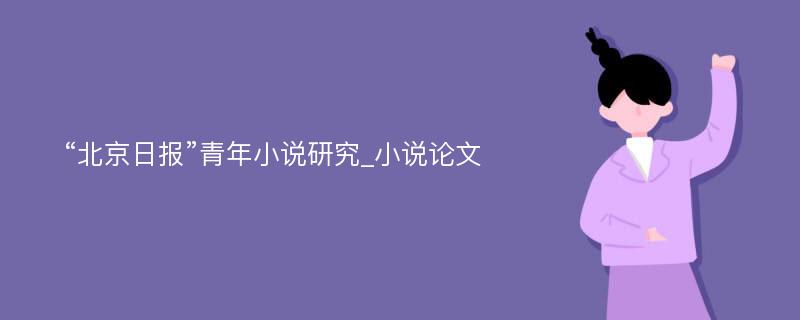
《京报副刊》青年题材小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报论文,副刊论文,题材论文,青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伏园主持下的《京报副刊》十分重视对新文学运动的推动,在周氏兄弟等人的大力帮助下,《京报副刊》积极投身到文学活动的建设中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小说方面,由于“五四”后围绕文艺副刊而产生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青年学生,所以关注青年的情感婚姻、学生校园生活以及妇女问题就成为这个时代小说创作中的不变主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人的觉醒,对灰色乏味的校园生活、荒唐堕落的青年学生的描写一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下的作家们所注重表现的。向培良的《挂号信的运命》描写了一个不安心求学、日日盼望家中寄钱来供自己挥霍的青年学生的灰色生活。文章中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心理描写,但是却用白描的手法通过细节刻画出一个堕落青年的灵魂。黎锦明的《一场试验》则在描写一群学生在考试前的群像的同时,通过第三人称“他”的视角来表现当时学校考试制度的混乱,并且通过对“他”在考试中这个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描写刻画出了一个在学校中得过且过、吊儿郎当的学生典型。最后“他”因为考试作弊而被检举出来,但是别的学生“有公然抄书而没有察觉的,还有被察觉而故不声明的”。作者寥寥几笔就把当时教育状况的无序和混乱表现得十分透彻。
在对青年学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作者的笔触饱蘸着同情伸向了青年学生远离故乡、深入社会后所遭遇到的世事百相、人情冷暖。焦菊隐的小说《会见》讲述了一个穷困的学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向同在北京的远亲借钱的故事。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将一个因为贫困而沦为社会零余者的青年人是如何在经济压力下被迫向社会富裕阶层低三下四、委曲求全的场景生动刻画了出来。作者利用借钱这个情节线索来贯穿全篇,通过主人公借钱前的无奈心理、借钱时的忍气吞声、借钱后屈辱的感情叙述把青年在经济压迫下的人格扭曲以及社会上虚伪的人际关系刻画得细致入微。许钦文的小说《叔父》则更是用讽刺的口吻直接揭露了虚假的亲情关系、社会环境对一个青年人的伤害。一个名叫伯棠的青年人为了继续求学而投奔自己的叔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可是在衙门做事的叔父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想把伯棠介绍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来做女婿,借此巩固自己的职位。由于伯棠坚决反对,他就把伯棠赶出了家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伯棠不得不参军并在军阀战争中屡获升迁,五年后伯棠又和他叔父见面了,在伯棠虚伪地与叔父应酬的同时,叔父也大讲自己当年赶伯棠出门的一片苦心:“孟老夫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我深悟此理,所以硬着头皮……。”① 文章就在这样一种颇有喜剧色彩的场景中闭幕了。这篇小说生动地揭穿了披着脉脉温情外衣的人际关系的假面,阐明了一个青年人即使可以挣扎着逃出家庭中的罪恶和虚伪,也必然会被社会的大染缸所吞噬。许钦文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社会的受害者得势后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改造这种社会关系,反而继承了当年吞噬自己的恶势力的习性。
青年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是《京报副刊》小说中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在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小说中,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是包办婚姻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妇女与家庭的关系问题。
在有关包办婚姻主题上,《京报副刊》的小说作家已经表现出了与“五四”时代作家的不同之处。“五四”时期以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为代表的爱情小说,是全力抨击以家庭父权残害青年婚姻自主、扼杀人性的包办婚姻之罪恶的。“五四”时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所以才会有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中对自由结合的热烈向往。可是如果“新”本身存在着内部脱序的状态,那么矛盾迟早会暴露出来。在二十年代中期婚姻自主的观念已经注入到青年人思想之后,由自由恋爱相结合的婚姻关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那就是如果男女双方只是在婚姻结合方面是自由的,在家庭内部关系处理上仍然摆脱不了传统思想观念的话,一旦男女双方面临家庭问题的时候,双方或一方就会对包办婚姻产生一定的幻想并进而否定自由结合的婚姻。许钦文的小说《“原来就是你!”》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文本。小说中男主人公高益三在喝茶的时候偶然看到朋友志忠的姐姐,“觉得她的身材不长不矮的刚好,肥瘦也很适度,露在发簪下红润而且鲜明的皮肤实在可爱”变由此爱上了她,并且再三托人去提亲。这个女子却认为“婚姻的事须由交际中形成,自己做主,不能由父母代订”,益三由此更加认为这个新式女子是值得自己爱戴的。后来益三去教书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现在的妻子,他们自由相恋而结婚。可是婚后不久益三就对自己的妻子产生了诸如“不要像煞有介事的太有趣,我原是把烂番薯当作何首乌玩的呀”的想法。而他的妻子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他,所以双方家庭生活中争吵不断。在一次争吵中他的妻子不经意地说:“照现在看来,从前我实在是在做梦,以为婚姻必须自己做主,好像只要自己做主一定是美满的了。唉,如果嫁了那个姓高的,难道还会比现在更坏。唉,我实在是辜负他的热情,他即经再三的要媒人来恳求,又屡次另行托人来说好,而且爸爸妈妈也都已对了他,只是我独唱高调,我说什么婚姻须由交际中形成,自己做主,不能由父母代订,毫不知道变通。现在,好!”② 经过双方一番言论才发现原来他现在的妻子就是志忠的姐姐,双方不约而同地说到:“原来就是你!”这篇小说是颇有几分喜剧色彩的,同时也是十分有象征意味的。双方都是以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准则才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家庭生活中,女方对男方在经济上依赖,男方把女方当作“玩物”。这说明,男女双方如果在家庭观念、思维模式等方面仍然是传统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仅仅是在婚恋结合方面的自由并不能保证婚姻生活的幸福。这就是这篇小说意味深刻的地方,也是相比“五四”时期仅仅要求婚姻自主的一种思想进步。这篇小说的意味就在于,作者通过幻画出一个潜在的包办婚姻的同时,让现实中自由恋爱的婚姻最后与幻画出的婚姻合二为一,“原来就是你”这句话深刻地表示出了两种婚姻模式的殊途同归,那种表面是新而内里仍然是旧的婚姻模式的虚假性,这样的恋爱自由导致的婚姻实在也比包办婚姻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封建思想不打破,任凭表面上的革新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益三与他妻子虽然逃避了父母的包办,却最终逃不过头脑中封建思想的“包办”。如此,许钦文的这篇小说就把罗家伦在《是爱情还是苦痛》中的思想命题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同时,即便是包办婚姻,我觉得在当时的历史境遇内也要分别对待,不能一概抨击。对那些从乡土中走出来进入到城市的读书人来说,包办婚姻在自由恋爱的社会氛围内自然是应该大力批驳的,可是对那些农村的青年人来说,身处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现实下,根本被剥夺了同异性接触的机会和权利,如果在不改造社会现实、不改造人(也包括受到封建礼教严重毒害的青年人本身)的思维心态的前提下对他们空嚷“婚姻自由”我觉得是根本行不通的,是变相地剥夺了他们爱情、婚姻的权利。因为对他们来说,包办婚姻可能是通向爱情的唯一道路。在青年男女有了极大的人身自由和接触机会的今天,批驳包办婚姻是必然的,可是我们不能把当下的理性带入到需要“同情的理解”的历史情境中去。对那些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人来说,正是因为他们有了部分的“自由”所以才有了“恋爱”的要求。试想当时那些在农村的青年人,连“自由”都没有,哪里来的“恋爱”呢?我们在承认文学家对“包办婚姻”罪恶的描述中确实有相当的一部分是真实世情写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文学家人为建构起来的,把它当作封建社会扼杀人性的一种象征物来刻画的,甚至有的作家只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罢了。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包办婚姻”(尤其是在农村)真的那么万恶不赦吗?我认为不应该那么绝对。我们姑且不谈“包办婚姻”是不是绝对的不幸福,要知道,自由恋爱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城市中得风气之先,有自由才有了自由恋爱。而在当时的农村,历史的惯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男女接触机会极少的情况下,包办婚姻往往提供了双方爱慕的一个渠道,虽然不是自由恋爱的,但是谁又能肯定说就不幸福呢。我们不能把今天的“幸福”观念强加在当时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头脑里,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启蒙暴力”吗?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包办婚姻是好的,而是想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表达社会转型期内婚姻形式的社会丰富性和历史多样性。
从“五四”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包办婚姻不幸福的文学叙述都是建立在“城乡对立”模式的基础上的,基本上是一个男子进城上学后反抗农村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包办,而那些被包办的女子对他们来说仿佛是一生的负累。我们当然要指出这是觉醒了的人对婚姻的正当要求,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也会有现代“陈世美”会借助于“自由恋爱”的幌子抛弃当年恩爱的发妻。同时,这样的“城乡对立”借助于简单的地域文化差异抹杀了历史语境中婚恋问题的复杂性。从许钦文的小说《“原来就是你!”》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对不是高嚷几句“自由恋爱”就能解决青年情感问题的,如果启蒙思想不是系统地影响并改造青年人的思想观念,那么单一的婚姻自由的要求往往会造成“思想脱序”的状态,也就是说结婚是自由了,可是家庭生活还是笼罩在传统思想“故鬼重来”的阴影之下。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对包办婚姻,尤其是农村的包办婚姻进行重新认识。《京报副刊》上俞闻樵的小说《往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本。这篇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讲述了“我”要上中学以前在农村的一段情感经历。“我”大姐的朋友士俊姐经常到“我”家来玩,她出于女生的矜持很少理“我”,“我”也嫌她“太骄傲了,少有礼节”,可是“后来我得到消息,我家内将要替我订婚了;我对方的主人是谁呢?就是日前常来的大姐的朋友士俊姐。”如果是一个启蒙作家写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写“我”怎么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以及自己的不幸,可是作者却没有这样处理情节,他充分写出了一个农村青年人思想的复杂性,“我”是这样想的:“我素来是主张晚婚的。由我的见闻所得:凡人订婚以后,总是要有若干苦恼的。所以我平日正立意于求学一途,不愿发生外务,徒来乱我心思。但是现在突然有这样的消息来了,那么,在我必定是要坚决抗拒的了。可是当时事实上却又并不是如此,——平日坚定的主张,已即时沉淀了,而是更满心希望着事情早早地成就。这是什么缘故呢?连我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后来竟能如我所望了,当时认为这是我生来最满意的一件事。”③ 后来两人果然如愿以偿,结为伴侣了。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我”离家上学后两人的相思之苦,尤其是尝到爱情甜蜜的士俊姐对“我”因为怀念而落落寡欢以至于染病的细节描写也十分动人,最终“我”接到了士俊姐去世的消息而晕倒了。作者就是让情窦初开的“我”和士俊姐通过包办婚姻而结合,并由此揭示出婚姻结合的形式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感情的实质。对包办婚姻主题这样的情节处理在启蒙者齐声控诉包办婚姻的罪恶的“合唱”中显得特别另类,我们能说这样由包办婚姻而产生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吗?我们能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吗?如果我们能对当时农村的青年人多一点同情的理解,那么或许会对包办婚姻也有区别对待、具体分析的必要了。同样的,许钦文的小说《幻恋》描写了一对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农村男女的包办婚姻的故事。男主人公亨斋托人去梁家提婚,而梁家也准备把梁家三小姐许配给亨斋,他们所受到的新式教育只不过在双方衡量的天平上放下了等量的砝码而已,后来由于亨斋家庭的败落,这桩包办婚姻也落空了,可是亨斋却始终怀想着那个从未谋面却在自己心中栩栩如生、穿着学生装的女生的影像。许钦文的这篇小说本来是要批判以人钱交换为实质的包办婚姻的虚假性的,可是,他的小说中男主人公对女方的怀想却是具有了男女感情的意味的,亨斋的感情无疑是纯洁的、善良的。许钦文或许也没有想到,他的小说已经溢出了他创作的意旨。农村青年人对异性的向往和热恋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包办婚姻给他们提供了恋爱的可能和渠道。
妇女与家庭关系方面的小说也是《京报副刊》中关于青年婚恋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中国青年的家庭、婚姻问题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妇女解放问题。向培良的小说《依违》讲述了一个受到家庭束缚的新式女子的苦恼与觉醒。作品的女主人公芸芝本来是一个进步而活跃的新式女子,但是琐屑的家庭生活把她慢慢地打磨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她的先生叔均是一个钻营职务的公务人员,但是她对此却一无所知。终于,她以前几个女同学对她的拜访燃起了她要重新生活的渴望,与此同时,她也终于认清了丈夫的虚伪丑恶、把妻子当作附属品的真实面目。于是她在惨淡现实中忽然觉得:“青年时代的志趣同毅力,突然在伊胸中燃烧起来了。伊觉得叔均那么卑劣同使气,已经不能再同居下去。伊又想到伊自己也是一个人,也在学校里读过书,并不是毫无能力,非靠丈夫吃饭不可的,为什么要受他的侮辱呢?但是伊一想到几年来家庭的生活,两重笨轭,把伊的精力都消耗尽了。自己的能力全部退化,几乎变为家庭的寄生物,不知道能否自立,又踌躇不决。”④ 但是最终她仍然决定了,她要跟同学去办学校“教育人并且教育自己”。她在给自己丈夫的诀别信中说:“去了,我要自己开展我的生活去了。这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权利,我不愿意无论什么人代我负责!”⑤ 她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可是当她踏出家门口的同时,自己的儿子却哭着叫妈妈,“一听到这里,由一种看不见的力立刻抓着伊。使伊立定了。”想要走出家门的觉醒女子,她可以舍弃婚姻和家庭,勇敢地投入到改造社会、改造自我的征程中去,可是她却难以割舍亲情和母子之爱。作者最后感叹道:“上帝呵,这力如今绕住了芸芝了,伊到底能否自脱呢?”⑥ 作者就是把芸芝放在理性与情感的煎熬之中来指出妇女解放的困难所在。向培良的这篇小说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不禁让我们想到了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都是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都是呼喊出“我是我自己的”时代强音,但是向培良却通过芸芝儿子的哭声来牵绊住芸芝出走的步伐,这无疑是对中国妇女解放复杂性的一种深刻的认识。对于旧式家庭的恨可以让她决然出走,可是母爱、亲情却限制着她们自我解放的决心。向培良在这里活生生地刻画出了一个徘徊于亲情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女性的形象。
袁嘉华的《零落》也是一篇很有悲剧色彩的小说。新式女子淑荃由于新婚之后丈夫就出国留学而独身一人,在婆家她受到轻视和冷落而无人诉说,她出于寂寞给海外的丈夫写信谎称自己得病了,丈夫是回来了,但是却跟家人一起埋怨她的幼稚与无理。丈夫走后,她去一个乡村学校教学,在那里认识了同样处于孤独中的有妇之夫——男教员张先生,两人同病相怜并最终产生了感情。后来随着婆家的冷淡和丈夫的漠视,淑荃终于难以忍受下去了,并最终在婆家的软硬兼施下与丈夫离了婚。可是,她的爱人张先生却受困于家庭的负累,几番努力依旧难获自由身,最后,淑荃实在看不到任何希望了,“一种苍茫凄切的情绪永远透着她的眼中淋漓的泪滴,她觉得从前砥砺不平的悲怀现在已经化成一片白茫茫的空虚了。”⑦ 小说就在这样的悲剧色彩中戛然而止。如果说向培良小说《依违》中的女主人公是受到了母子亲情的困扰而难以走出家门的话,那么淑荃就是走出了封建冷酷的家庭后却无所依托的女子形象的典型。冷酷的社会和灰色的生活带给她的只有创伤和仇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恶劣的心态下,女子解放的任务显得更为急峻了。毫无疑问,改造社会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和唯一途径,这也是《零落》这篇小说思想上的深刻所在。
综上所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京报副刊》上,有关青年题材的小说相对于“五四”时期已经产生了很多文学异质性和多样性。如果我们用一种“同情的理解”去理解这些历史语境中的异质性,我们会有新的启发和收获,可能帮助我们破除以往文学史叙述上的简单化和“启蒙暴力”倾向。
注释:
①许钦文:《叔父》,《京报副刊》1925年5月24日,第6版。
②许钦文:《“原来就是你!”》,《京报副刊》,1925年1月31日,第5版。
③俞闻樵:《往事》,《京报副刊》,1924年12月18日,第4版。
④⑤⑥向培良:《依违》,《京报副刊》,1925年4月10日,第5版。
⑦袁嘉华:《零落》,《京报副刊》,1925年8月21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