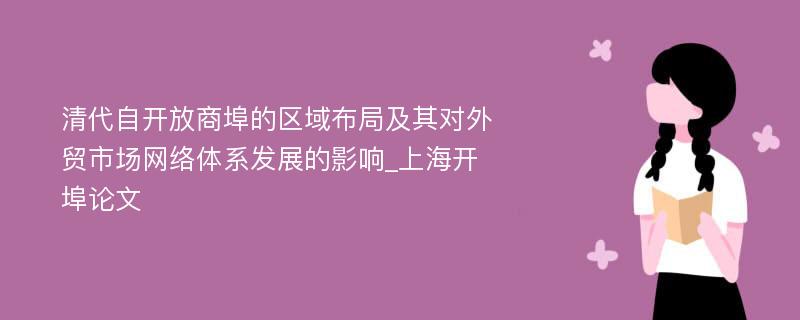
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埠论文,其对论文,地域论文,体系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季中国政府惩列强之侵略,思有以制之,从戊戌年开始,在其国祚尚存的最后14年里,于既有的通商口岸之外,主动开辟埠头35处。这些埠头当时被称为“自开商埠”,以区别于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条约口岸”。首批奏准自开的有岳州、秦皇岛、三都澳等埠。以该三埠开放为起点,自开商埠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鉴于学术界对自开商埠研究甚少,本文拟就此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所论涉及面甚广,或有不周延之处,敬祈高明諟正。
一、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与类型
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学者说法不一。孔庆泰选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列入“商埠年月表”且标明属于清季“自开”的商埠有武昌、岳州、长沙、常德、湘潭、三都澳、鼓浪屿、南宁、昆明、济南、潍县、周村、吴淞、海州、秦皇岛等15处(注:《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严中平所编《鸦片战争后所开商埠表》中可以划归“自开”的商埠共12处,较之孔庆泰的统计少了长沙、常德、湘潭、武昌等四处,多了广东的公益埠一处(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8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朱新繁《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一书的统计为17处,较之孔庆泰的统计多了南京、河口、思茅三处,少了吴淞一处(注:朱新繁:《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第180—187页,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的统计为16处,较之孔庆泰的统计多了奉天的葫芦岛和南京两处,少了吴淞一处(注: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第16—20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此外,被学者列为“民国元年以前自行开埠”的通商口岸还有江苏的浦口、天生港以及广东的香洲三处(注:王树槐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8)第84—87页,1984年6月版;何志毅:《香港开埠及其盛衰》,《广东文史资料》第46辑第9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第68页附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博士论文,1995年印制。案:杜文承姜涛先生借阅,谨此致谢。)。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若不作考辨,但以“榜上有名”为断,曾被学者列为晚清“自开商埠”的城镇为23个。其中,南京和长沙不是“自开商埠”不应再有争议。河口、思茅则系依1895年6月20 日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之规定开放,其不属于“自开商埠”亦不难断谳。真正容易引起争议的只有吴淞、浦口、公益埠、葫芦岛四处。吴淞系一业已奏准“自开”的商埠,分歧在于是否正式开埠,即是否宣布“开张”与实际做生意之分别。宣布“开张”已否虽不得而知,生意则已经在做了。因此,称吴淞为“自开商埠”并非毫无理由。浦口、公益埠、葫芦岛三埠之争议则系因“改朝换代”而起。盖此三处开埠之议均起自清末。葫芦岛系1908年由东三省总督奏准开放,但事情几经周折,直到1914年方由北洋政府之国务总理熊希龄宣布开埠。公益埠是由两广总督张人骏于1908年批准开埠的,然其开办时间却推迟到了民国元年(注:葫芦岛、公益埠开埠的情况参见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8页“商埠表”,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浦口开埠之议始于1900年,系英、德领事提出要求,由两江总督刘坤一负责筹办,嗣因庚子事变而延误;1910年开埠事再度提出,并由地方官议决就浦口既有之市场扩充推广,建立商场,拟就《浦口市场局暂行章程》, 并由黄思永负责发行公债; 但直到1912年8月, 商埠才最终建成(注:浦口开放的情况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民政部档案,全宗号509,案卷号209,档案名称:“两江总督咨送浦口士绅建立自辟市场简章及有关文书”。)。显然,该三处商埠均处于跨越“朝代”的特殊地位,若以议决建设商埠的时间为断,则三处均属于“清季”自开之商埠;若以设关开埠的时间为断,则三处又应当划归“民国”。考虑到经中央或地方政府批准开埠之后,多数商埠的内外贸易便已经开始,商埠的存在也因此成为合法,而商埠的建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殊难找到某种业已建成的标志,加之许多地方设关开埠的时间无法考证,我们认为,以获准开埠的时间作为选择判断的标准更加合理,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这一选择判断标准能够得到认同,则在上文提到的23处城镇中,除了南京、长沙、河口、思茅四处,其余19处均应属于清季“自开商埠”。这些商埠除葫芦岛外,均位于“关内”,加上1905年底清政府在属于“关外”的东北地区主动开放的16个商埠,清季“自开商埠”的总数应不少于35个。兹将清季“自开”之商埠列表如下:
表1 清季自开商埠一览表(注:资料来源: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8 页“商埠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王树槐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第85—86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二编;漆树芬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第16—20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朱新繁著《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第180—187页,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等等。)
省别商埠名批准开埠时间实际开埠时间
湖南 岳州 1898年4月24日 1899年11月13日
湘潭 1905年7月
1906年3月16日
常德 1905年7月
1906年7月2日
湖北 武昌 1900年11月18日
山东 济南 1904年5月15日 1906年1月10日
潍县 同上 1906年1月1日
周村 同上 1906年1月
江苏 吴淞 1898年4月20日
海州 1905年10月24日 1921年
浦口 1910年
1912年8月
天生港 1906年7月
福建三都澳 1898年4月24日 1899年4月28日
鼓浪屿 1902年11月21日
广东 香洲 1908年5月24日 1909年
公益埠 1908年
广西 南宁 1899年1月30日 1907年1月1日
云南 昆明 1905年5月11日 1910年4月29日
直隶秦皇岛 1898年4月26日 1901—1902年之间
奉天凤凰城 1905年12月22日 1907年6月28日
辽阳 同上 1907年6月28日
新民屯 同上
铁岭 同上 1906年9月10日
通江子 同上 同上
法库门 同上 同上
葫芦岛 1908年
1914年
吉林 长春 1905年12月22日 1907年1月14日
吉林省城同上 同上
哈尔滨 同上 同上
宁古塔 同上 1910年1月
珲春 同上 1910年1月1日
三姓 同上 1909年7月1日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905年12月22日 1907年5月28日
海拉尔同上 1910年1月
爱珲 同上 1907年6月28日
满洲里同上 1907年1月14日
省别 备注
湖南
湘抚奏准
同上
同上
湖北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
山东
袁世凯等奏准
同上
同上
江苏
总理衙门奏准
地方官主持
署两江总督周馥奏准
福建
总理衙门奏准
兴泉永兵备道奏准
广东
由"绅商"主持
由粤督批准
广西
广西巡抚奏准
云南
滇督奏准
直隶
总理衙门奏准
奉天
以下各口岸除葫芦岛外,
均系依据中日《会议东
三省事宜》条约附约规
定由中国"自行开埠通
商"
东三省总督奏准
由上表不难看出,清季“自开商埠”星散各地,地域分布颇为宽广。如果依照商埠所在城市的行政级别来区划,则可分为省会级、府厅州县级和乡镇级三类。依据自开商埠自身的特征,又可以区分为普通自开商埠、免税自开商埠和临时起下货物的“招呼口岸”三类。若从主权归属的角度审视,则又可以分为完全由中国筹议自开和条约载明由中国“自开”两类。
普通自开商埠的特征较为明确,即强调权自我操。这是由清政府批准开设的通商口岸;商埠区由中国方面划定,中外商民均可按照有关章程在其中租地建造,投资经营;埠内不设租界,所有警政、行政、司法事务,均由中国自办,工程事务,由中国派出的海关监督会同税务司办理。曾经参与民初开埠事宜的梁士诒认为,自开商埠与条约口岸的区别在于:“在自开商埠,我国得有行政权,内外人民同受支配,而课税可照内地办法,一体征收,此其显有区别者也”(注: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上),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第58辑第164页,上海书店影印本。)。 总理衙门提出的“自开商埠办法”咨文,亦强调了主权的归属问题,文曰:“自开商埠,与约开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该处商民将来所立之工程局,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应统设一局,不应分国立局。内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之官员,并该口之税务司,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以示区别而申主权。”(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最早的自开商埠如岳州、秦皇岛、三都澳在建设之初,便已形成这些特征。清末新政期间开放的口岸大多仿效该三埠,但因后起故,有所借鉴,成绩往往更加显著。
免税自开商埠亦具有自开商埠的一般特征,只是在税收上享受了某种程度的优惠政策。香洲即属于这类自开商埠。该埠于1908年开放,次年由粤督奏请“暂作无税口岸”。然事情颇多曲折。九龙关税务司在查复此事时,谓商埠之盛衰,全恃地势之得宜与否,非关乎有税无税,并称若作无税口岸,与它处办法歧异,难免开“漏税之门”。广东劝业道会同布政司、粤海关税务处在复核此议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振兴埠务,保护商业,招徕华侨,挽回溢利,非先明定该埠为无税口岸,不足以资提倡而树风声。该税司以商埠之盛衰为与税则之有无毫无关系者,体察情形,殆非笃论。香洲东与香港对峙,北据澳门上游,同是贸易商场,人则一切自由,我则动多束缚,优胜劣败,相形见绌,不能不亟图挽救。该埠倘定为无税口岸,一经宣示,风声所播,国中巨贾竞出其途,海外侨商云集内向,兴盛之机,正未有艾至。(注:《税务处等奏议复增祺奏香洲自辟商埠请暂准作为无税口岸折》,见王彦威、王亮编:《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9第11—13页,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由于广东方面的力争,税务处、外务部、度支部等在议复朝廷时亦以“该埠毗连(之)香港澳门,皆是无税口岸,倘有歧异,相形见绌”为词,建议朝廷“恩准香洲自辟商埠暂作为无税口岸”。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奉旨“依议”。然而所谓“无税口岸”,也只是税收范围较之其他口岸有所限制,并非完全免税。税务处的奏折对此作了明确说明:
所谓免税者,亦非全无限制。譬如内地生货运至香洲,制成熟货运输出洋,只完内地生货之税,毋庸再完出口熟货之税;外洋生货运至香洲,制成熟货销售内地,只完内地熟货之税,不必先完进口生货之税。所有内地海关厘厂,仍照章完纳,与港澳事体相同,于饷课不虞亏短,洵属有益于商无损于国。(注:《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9第12页。)
清季经旨准以“无税口岸”形式对外开放的自开商埠仅香洲一处,但在开办之初,申请暂时免收关税的还有济南(注:济南开埠之初,袁世凯、周馥等奏请暂缓设关收税云:“开埠之始,首重招徕,议将税关暂缓设立,所需各项经费,先由华官自行筹备。”所请获朝廷批准。引文见《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1905年。)。 只是济南未获准辟为“无税口岸”,虽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免收关税之实,却无“无税口岸”之名,不宜置诸此类商埠之列。
临时起下货物口岸的英文名称为“Port of Call”。斯坦利·莱特(Stanley F. Wright )在称“西江起下货物之埠”时, 用的便是“West River stages or ports of call”(注:Stanley F.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WM.Mullan & Son (Pub.) LTD., Belfast,1950,p.895.)这一名称。中国学者或称之为“过口埠”, 或称之为“访问口岸”(注:华民编:《中国海关之实际状况》第 1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出版;前揭杜语文,第29页。华民将这类口岸视为有客货则停,无客货则开之非正式商埠,或介于条约口岸与非条约口岸之间的一种商埠,这与杜语将之列为自开商埠类有所不同。)。我以为,若照英文直译,则称做“招呼口岸”更为相宜。属于这类口岸的“自开商埠”有南通的天生港。该埠开放之议起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刘坤一遵旨筹划南通自开商埠之时,后因故而寝。光绪三十二年,署两江总督周馥奏请“通州天生港自开商埠”,其具体办法是将该港建成“可以起下货物之不通商口岸”。通州在籍绅士翰林院修撰张謇亦因海州自开商埠,函“请将通州一埠一律举办”。事情以是再次提上政府议程。外务部、户部在议复此事时认为,周馥奏请天生港“既开埠而仍不通商,为向所未有之办法”,究竟利弊如何,尚须预为揆度。经外务部致电周馥查核,同意援照“大通六处办法”,关房关栈,暂时不建,以省用度,三五年后,酌度商务情形,再行设关开埠。所谓“大通六处办法”,系依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第三款之规定,将长江沿线的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处非通商口岸,试以“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外务部认为,天生港亦系沿江地方,与大通六处形势略同,自可准华洋各轮来往停泊,上下客货。但考虑到该埠与江海关、镇江关相距不远,若开作商埠,其关税一项,恐致此盈彼虚。故议定“所有天生港一处,应只作为起下货物之口岸,以通航路而兴商务,不必预筹开埠通商”(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558—555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然而“起下货物”之口岸亦每作成生意,由是天生港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自开商埠”。
若按照商埠所在城镇的行政级别来划分,属于省会城市的有武昌、济南、昆明、吉林省城、齐齐哈尔5处,属于府厅州县级的有岳州、 湘潭、常德、南宁、潍县、海州、香洲、三姓、宁古塔、爱珲、凤凰城、铁岭、新民、辽阳、长春、哈尔滨、法库门、通江子、满洲里、海拉尔等20处,属于县以下村镇或居民聚居点的有秦皇岛、三都澳、周村、吴淞、浦口、天生港、鼓浪屿、公益埠、葫芦岛、珲春等10处。
“自开商埠”有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主动对外开放的,也有依照条约规定“自开”的。岳州、三都澳、秦皇岛,济南、潍县、周村、昆明、南宁、武昌、湘潭、常德、吴淞、海州、鼓浪屿、香洲、公益埠、天生港、葫芦岛、浦口等19埠属于前一种类型。虽然其中湘潭、常德、南宁、鼓浪屿等埠有“外人索开”之因素掺和其间,但未载诸条约,故均可列入前一类“自开商埠”。1905年东北三省开放的16个商埠,则系依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之规定而开放。这16个口岸是否为“自开商埠”颇有争议。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均视之为“条约口岸”,但也有视之为“自开商埠”者,彭雨新教授即作如是观(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所列“民国自开商埠年月表”,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所列“商埠表”,以及朱新繁、漆树芬、华民、张洪祥等人的著作,均未将东三省1905年开放的城市置诸“自开商埠”之列。彭雨新先生则反是,在国内学者中率先肯定此16城市的“自开商埠”地位,并对其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详见彭雨新:《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载章开沅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第195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彭先生虽然没有申述理由,但我以为其判断是正确的。因为若是拘泥于条约,该条约已载明该16埠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注:《分议东三省事宜·附约》,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340页。), 则据约称之为“条约口岸”的理由并不充足。况且,东三省开埠之议早在庚子年间便已由张之洞等中国官吏奏陈朝廷,日俄战争期间,主动开埠的主张更是通过各种官方渠道提出,虽然外人有所要求,但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并非被动接受。更为要紧的是,东北三省所开商埠包括警政、商务管理在内的一切行政权都掌握在中国政府委任的官员手里,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这一切,都是通常意义上的“条约口岸”所不可能具备的,因而,将该16城市确定为“自开商埠”,更能揭示其丰富的政治、经济内涵。
二、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
从地域分布上看,在清季“自开”的35个商埠中,分布于沿海的有秦皇岛、海州、吴淞、三都澳、鼓浪屿、香洲、公益埠7处, 分布于沿江的有武昌、岳阳、浦口、天生港、南宁5处,位于内陆的有济南、 潍县、周村、湘潭、常德、昆明6处,东三省先后开放的17处(1905 年所开16处加上1908年开放的葫芦岛)“自开商埠”则属于“关外”型。
这些“自开商埠”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特征,值得研究者注意。
其一,清季“自开商埠”大多分布在沿海及沿边省份,沿江及内陆省份的“自开商埠”数量较少。在上列35个商埠中,东三省及云南、广西这类边境省区所开商埠有19个,加上位于海口或沿海省份在陆路开设的10个,则位于沿海、沿边省份的自开商埠多达29个,而沿江及内陆省份“自开”之商埠仅有6个,数量差别,殊为明显。
形成这一地理分布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从单纯做生意的角度来看,沿海、沿边省份的许多城镇都处于外国商品来华的“入口”处,在这些地方开埠做生意,自有其便捷之处。特别是沿海地区,在海禁已经不复存在的晚清时期,风气大开,华夷共处,彼此已见惯不惊,而已经开埠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尚未开埠地区的官民,更是表现了极大的吸引力。在这些地区开埠通商,既有天然形胜的便利条件,复有为内地难以比拟的社会人文条件。一些地区(如广东香洲)的开放,乃绅民倡行于前,官府认准于后,这与内地一些口岸(如湖南常德)虽经官府奏准举办,绅民仍借端反对适成鲜明对照。
此外,沿海、沿边省份尚有较为发达的交通条件。位于海口的商埠自不待言。其他沿海、沿边省份的“自开商埠”大多位于铁路、公路的干线或交汇点上,南来北往,十分方便。例如东三省的“自开商埠”,便大多位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昆明商埠位于滇缅铁路中国一方的起点上。济南则是胶济铁路的始发站。周村虽处于山东腹地,但亦南通沂蒙,北接黄河两岸,胶济铁路开通之后,更是成为内地商品货物输往青岛、烟台的中转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位于广西腹地的南宁,虽既不通火车,也未濒临大海,但陆路及内河航运亦极为便捷。按总署之说法,南宁地势“山环水抱,虽闻有浅水滩流,而通汇左右两江,河身深阔,上控龙州,下通浔梧,又为云贵两省必经之路”(注:《总署奏遵议广西南宁作为中国自设口岸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36第25页。), 自为开埠通商的绝好处所。便利的交通以及优越的自然及人文地理条件,是形成清季“自开商埠”特殊的地域分布状况的不容忽略的原因。
然而清季“自开商埠”明显向沿海、沿边省份倾斜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因为如果强调交通便利及文明“开化”程度,则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不低下,但是沿江一线的“自开商埠”却只有武昌、岳阳、浦口、天生港四处。这不仅与沿海、沿边众多的“自开商埠”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也与沿江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即便沿江已经存在六个条约口岸,也远远没有达到市场饱和的程度。至于广大的内陆地区,县及县以上市镇数以千计,其中不乏货物辐辏,商贾云集之所。然而,除了由沿海、沿边省份在本省腹地所开商埠之外,真正在内地“自开”的商埠只有常德、湘潭两处。这种状况若仅以地理的因素来作解释,显然缺乏说明力。
鄙意以为,清季自开商埠特殊的地理分布状况与其说主要是因于客观的自然及交通条件,勿宁说主要是因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清季“自开商埠”,主政者显然有借开埠对外通商,缓解面临的财政危机这一经济层面的考虑,然而经过认真权衡,他们普遍认为,对外开埠通商,沿海与内地,利弊得失是不一样的。对此,刘坤一曾经做过明确的表述:
广开口岸之旨,原欲杜侵占,第多一口岸,于税厘即增一漏卮,于国币即多一份费用。通盘筹计,沿海择要开口利多害少,沿江、内地多开口岸实属有害无利。盖内地与沿江断不虑有侵占,而于华洋杂处、制造皆有大损。且内地开口,沿途经由之地皆隐成口岸,且内地名虽开通一处,实则沿江海而至内地开处均与口岸无异,所损尤大,而于商务未必真有利益。……湘中先开岳岸,创办极限。若再深入内地,则目前之开办与夫日后之弹压保护,其难更可想见。(注:《江督刘坤一致外部英使所开邮政圜法及口岸情弊请饬盛宣怀切实与辨析》(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50第20页。)
刘坤一深感忧虑的也正是在朝诸公所芥蒂于心者。这在外务部就察哈都统诚勋奏请张垣开埠事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可以清楚窥见:“惟开埠通商事关交涉,虽自辟稍可保主权,而内地究不同口岸。当此治外法权尚未收回之时,多一商埠即多一纠葛。”(注:《外部奏议复察哈尔都统诚勋奏请开辟张垣商埠折》(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清季外交史料》卷215第11—12页。)为了避免“纠葛”,清政府在允准沿海、 沿边省份广开商埠的同时,却又尽量避免在内地开埠通商,这是内地“自开商埠”数量偏少的主要原因。
其二,清季由中国政府主动开放的商埠大多为不甚重要的中小城镇,因而这种“开放”的作用也势必受到影响。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借鉴有关“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施坚雅就19世纪末中国社会所做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施氏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而提出了区域系统研究法,据此将中国划分成9个相对独立的大区, 每个大区均有“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分,并依经济及人口状况划分为8 个等级。下表是施坚雅按照其等级结构理论而制作的。
表2 中国城镇在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分布状况表(1893年)(注:G·W·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第15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本文在引用此表时,删除了“合计”栏中的百分比数值。)
在经济等级结构 核心地区
中所处级别数量 百分比边缘地区合计
全国性大城市6100%
6
区域级大城市
18
90.0%
2 20
区域级城市 38
60.3% 25 63
中等城市 108
54.0% 92 200
地方级城市360
53.8% 309 669
中心性集镇
1163
50.2%11562319
中等性集镇
3905
48.7%41068011
一般性集镇 13242
47.8%
14470
27712
合计18840
20160
39000
在经济等级结构各级城市\集镇人口平均数
中所处级别 核心地区
边缘地区
全国性大城市 667000
区域级大城市 217000 80000
区域级城市73500 39400
中等城市 25500 17200
地方级城市 7800
5800
中心性集镇 2330
1800
中等性集镇 690450
一般性集镇 210100
如果我们将施坚雅提供的不同等级城市的人口指标,与表1 所列35个“自开商埠”的人口作一番观照,就会发现,没有一个“自开商埠”够得上“全国性大城市”或核心地区“区域级大城市”的资格。按照行政级别,清季“自开商埠”中最大的城市应为济南、武昌、昆明、吉林省城和齐齐哈尔,但这5个城市的人口指标都达不到21.7 万的水平。 在1906年,济南、吉林省城、齐齐哈尔的人口统计数都是10万(注:参见姜涛著:《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40页表13—1“20世纪初叶城市人口的估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据毛承霖纂:《续修历城县志》称,济南“商埠新埠”之时,城内三个区人口总计为53904人, 城外三个区人口总数为84779人,商埠四个区人口总计为32306人(见该县志卷4,“地域考三·户口”)。合城厢区及商埠区人口, 济南开埠之初人口为86210人,较姜涛先生的统计数尚少13790人。)。同年昆明人口的统计数为4.5万,1909年冬季人口调查的结果, 昆明城内外九区男女丁口总计为9.18 万(注: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近代人口史料》(1909—1982)第2辑上第5页,1987年3月印行; 〔美〕德·希·帕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39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武昌城人口最多,1911年初的统计数据为18.24 万(注:《湖北武昌等十一属六十八州县城议事会议员姓名履历(清册)》所附人口表,转引自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第65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但也没有达到施坚雅为“区域级大城市”所规定的21.7万的人口标准。这5 个省会级的商埠大抵均属于“区域级城市”的类型。即便考虑到昆明、吉林省城和齐齐哈尔所处之地理位置,亦至多只能列入“边缘地区”“区域级大城市”的范围(注:案:施氏在划分中国的城市经济区域时,并未将东三省考虑在内,如果拘泥于施氏设计的模式,则清季自开商埠中属于边缘地区“区域级大城市”者,只有昆明一个城市。)。包德威(David D.Buck)教授在论述济南城市史时曾指出,“济南在晚清只能算作一个三流商业城市”(注: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3.)。这种“三流商业城市”的定位,对于其他省会级的“自开商埠”亦大体适用。
多数“自开商埠”属于人口少于73500,却又多于25500的“中等城市”,即施坚雅模式中位居“四流”的城市类型,或边缘地区的“区域级城市”的类型。这些城市包括南宁、岳州、常德、哈尔滨、长春等。南宁在1907年开埠,社会经济因此迅速发展,1912年10月取代桂林成为广西省会,但该城在1910年亦不过60064 人(注:鹤仙:《清末时南宁人口》,《南宁史料》(内部资料)第2辑第34 页。 )。 常德的人口1916年统计为5万,岳州的城厢人口约在2万至3万之间(注: 张朋园:《近代湖南的人口与都市发展》,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33)第28编第547—555页“区域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另据《中国实业志·湖南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四”第99页,民国二十四年初版)之统计,岳阳城厢人口至1933年亦仅为25727人。)。哈尔滨与长春1906年的人口数分别为3万和3.5万( 注:〔美〕德·希·帕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 388页。)。
还有不少“自开商埠”属于“地方级城市”或“集镇”类型。这些商埠的人口一般都在2.5万以下。其地理位置或在中心,或在边缘。 秦皇岛、三都澳、吴淞、鼓浪屿、周村、公益埠、天生港、葫芦岛等均可划归此类。其中秦皇岛、三都澳最具典型性。秦皇岛在开埠前只是一个小渔村,因开平矿务局运煤之需而兴建的秦皇岛港,也不过“栈房三两,代卸钱粮”,规模十分狭小。秦皇岛开埠之后,贡生程敏侯赋诗致贺,留下“荒岛继踵学开通,改良辟作春申浦”(注:君羊:《程敏侯〈贺秦皇岛开埠〉诗注》,见《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第5 辑第 93 页,1991年。)的诗句,其“荒岛”的称谓,应当不是纯粹的文学语言。从人口上看,开埠数年之后,秦皇岛的人口亦仅有5000人(注:〔美〕德·希·帕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390页。), 其属于“集镇”类商埠,应无争议。三都澳在开埠前“除了几间破旧农舍以外,看不到其他东西”,开埠之后,人口渐增,但直到民国初年,该埠亦不过八千人。天生港、公益埠、葫芦岛、鼓浪屿等埠的情形亦大率如此。
清季“自开商埠”在中国城市经济等级结构中序列偏低,与条约口岸的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开商埠”的选择范围有关。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开放“五口”对外通商以来,中国的重要口岸相继被迫开放。截至1898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已多达40余个(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由条约规定开放的口岸大多为经济地位突出、具有开发价值的大中城市。在沿海地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杭州、苏州、烟台、天津、营口等城市早已依约开放,为外国人控制;在长江沿线,南京、镇江、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等城市也已成为外国人从事“自由贸易”的理想场所。在施坚雅模式中列为“全国性大城市”的6个城市中,除了北京、 西安之外,其他4个都是条约口岸;在20个“区域性大城市”中, 条约口岸亦占了相当数量。在沿海、沿江地区,属于这两个级别的可供“开埠”的城市已经不多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没有较大的口岸可供开放。北京系京师重地,须尽量避免华洋杂处,西安地处西北,无交通之便利,不将该两大城市列为自开商埠,也似乎无可非议。但郑州、太原、南昌等省会城市,均有交通上的便利条件,商业资源亦十分丰富,清政府在策划对外开埠通商时,却始终未将其考虑在内。这表明清季“自开商埠”在中国城市经济等级结构中序列偏低这一现象,尚不能单纯以有无较大口岸可开来加以解释。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清政府“开放”政策所具有的特殊指向性。一般认为,“开埠”意味着对西方近代经济及社会文化因子的吸纳,对于“前近代”国家,则意味着近代化的开始。但清季的“开埠”却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由于这里的“开埠”被当成了抵制由外人提出、且在内涵上两者存在交叉关系的另一种“开埠”的手段,因而其表面上的“开关”,实际上已暗含“闭关”的性质,这就必然使自开商埠的实施范围和推进力度上受到某些人为的限制。但闭关锁国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在“门户开放”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新形势下,有限制地对外“开放”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因应之策。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已经多次为学者揭示的政治及经济层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化解之方式,自然是某种体现了传统哲学“执两用中”精义的“中国式”办法,于是出现了清季大张旗鼓宣布商埠“自开”,而所开商埠在中国经济等级结构中地位偏低的状况。
清季“自开商埠”地域分布偏向沿海、沿边,且在城市经济等级结构中级别偏低,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了这类商埠后来的发展。在沿海、沿江“自开”的商埠,多为中小城市,处在条约口岸的“夹缝”之中,求生存已属十分困难,遑论其他!而沿边省份“自开”的商埠,因所属省份在经济上就不具有重要性——这些省区商埠的“自开”,主要是着眼于政治或军事战略——故很难对国家的“开放”,产生全局性的影响。总之,这种在商埠“自开”之初便已形成的畸形格局,既有其不能不如此的成因,又有同主政者之初衷大相径庭的客观后果,研究清季“自开商埠”,不可不对这两方面同时加以考察。
三、自开商埠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确定一个参照系统。由于斯时尚无其他类型的口岸可资比较,将条约口岸作为参照系统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如众所知,1898年中国的条约口岸数已经多达40几个,但如果我们对自开商埠政策实施之前的条约口岸作一番研究,则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外贸市场,它远远没有发育到网络体系完备的程度。
我们且从分析当时中国外贸市场的辐射范围入手进行研究。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需要事先说明。其一,通商口岸不是单纯的外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它同时还是中国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制成品的采购中心,因此,施坚雅在其研究中所强调的外国商品的“销售域”,可能同时又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采购域”。但两者不一定在场域(range )上完全吻合。当中国的外贸仍然保持出超时,很可能采购域大于销售域,反之则可能出现销售域大于采购域的情况。其二,由于存在国内产品的输出,外商的买进意味着中国商人的卖出,因而,通商口岸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内既有的商品市场发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口岸从事贸易活动的场域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传统的商业市场对于外国商品的接纳或排异程度。考虑到这两层因素,我们的考察对象将不仅是“销售域”,而是包括销售域在内的全部通商口岸所从事的贸易活动的“场域”。
划定通商口岸所从事的贸易活动的场域是一项颇为复杂的研究工作。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首先需要确定相邻通商口岸最近距离的平均数。由于两个口岸邻近在多数情况下可理解为其中一个口岸是另一个口岸势力所未及的地区,而该地区尚有独立发展商业经济的潜力,因此该两处口岸直线距离之半,便可作为半径,而通商口岸所在地则是圆心,以此画出的圆,便可视为一个通商口岸贸易经营活动的场域。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全国性大城市”。在1898年以前所辟通商口岸中,属于这类城市的有5个,即广州、上海、天津、 汉口和重庆(注:将重庆列为“全国性大城市”或许会引起争议,但从入川洋货总值来看,光绪七年(1882年),即开埠前10年,渝埠商务报告所显示的数额已达400万两,这使该埠“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 汉口的第四位销售中心”(Commercial Reports,1881—1882,Chungking, 转引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28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据此, 我以为有理由将重庆列为此类城市,尽管有学者更倾向于让苏州入闱。)。这5 个城市构成了分布颇为匀称的5个经济区域即华南、华东、华北、华中和华西的外贸中心。 然而,在这5个口岸城市中, 相邻最近的上海与汉口之间的直线距离也有约650公里,各相邻城市的直线距离的平均值约为850公里。如果将这一数据换算成陆上或水道的实际交通距离,则该5 个大城市中相邻城市的直线距离平均应在1000公里以上。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5 个堪称“中心地”的口岸城市显然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中国的全部对外贸易的重任,在它们之间的广大地区,尚存在着不属于其“销售域”的中间地带,因而我们尚不能单以他们之间的距离的远近来估计其活动场域,而勿宁将次一级的填补其活动真空地带的通商口岸一并加以考察。
1898年之前中国次一级或更次一级的通商口岸有43个,其中还包括新疆、西藏、蒙古境内自成一体,与内地殊少交通的14个。如果将这14个口岸放置一旁,暂不讨论,则有关的口岸还剩下29个,加上5 个中心级口岸,一共有34个。从地理位置上考察,这些口岸中相邻者的最近直线距离相差颇大。广州至三水之间直线距离约为50公里,上海与苏州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80公里,算是所有一般通商口岸间距离最近的两个。最远的可能是天津至烟台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400公里。 其它各相邻口岸的距离远近各异,其相邻者的平均直线距离约为200 公里(注:其他相邻口岸的直线距离分别约为:上海至杭州150公里,上海至苏州 80公里,杭州至宁波130公里,宁波至温州250公里,苏州至杭州125 公里,北海至琼州210公里,台南至淡水150公里,福州至厦门150公里, 九江至芜湖300公里,营口至大连200公里,龙州至北海270公里, 广州至汕头380公里,广州至三水50公里,沙市至汉口200 公里, 汉口至九江180公里,天津至烟台400公里。)。这意味着在两个口岸从事贸易活动条件相等的条件下,平均每个口岸的活动场域的半径不应该超过100 公里。
如果我们将上述条约口岸均画出一个半径为100公里的圆, 并将彼此衔接或相邻的圆用线条连接起来,则可明显地看出,1898年以前中国已开通商口岸的活动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及华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几个地区,对外贸易的网络体系已经大体形成。另外,在渤海湾周遭,虽然彼此距离甚远,但由于海上交通的便利,天津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的三角地带,也初步形成贸易网络。此外,尚有分布在新疆、西藏、蒙古、云南的几个相对孤立的贸易点。
然而,不难看出,未能划为通商口岸活动场域的地区还相当广泛。在中国腹地,与对外贸易没有直接联系的还有湖南、山西、陕西、河南、贵州、青海、甘肃等7个省份。东北地区除辽东半岛之外, 大部分区域都未与外贸发生联系。另外,各个已建成商埠区域之间亦存在明显的隔阻。例如,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渤海三角区之间尚存在苏北和鲁南这一片长度近500公里的空白, 华南的贸易网络与华东的贸易网络之间也存在一个长度约400公里的空白地带。在长江流域,重庆虽已开埠, 但它与中下游相距遥远,很难说它已经同中下游的外贸网络连成了一体。在渤海湾地区,如果从陆路考察,天津至营口,烟台至天津之间亦缺乏必要的货物中转环节。在内陆地区,山西、陕西、贵州、青海、甘肃且不论,就连经济素称发达的直鲁腹地和湖南中部及北部地区,也看不到通商口岸的存在。
造成戊戌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网络体系发育不成熟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需求的因素之外,尚有三层不应当忽略的因素:
一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在中国铁路的里程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通商口岸借以转运其货物的唯有海陆水道。1892年龙州海关税务司曾指陈了这个无可奈何的事实:“大体言之,只要能够的话,贸易均采水路。”(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etc.,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1882—1891,Shanghai,1893,p.661.)将近 20年以后,湖北沙市税务司也作出了一个可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沙市没有铁路交通,在若干年内没有也无所谓,但却是天然和人工水道之辐辏系统的中心。”(注:Ibid.,1902—1911,Vol.1,pp.292—293.)在内陆地区,除了湖南是一个例外,其它没有通商口岸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旧式船只(Junk)及内河轮船难以直接通航的地区。像西安那样重要的全国性大城市,人口众多,商业素称发达,其没有成为通商口岸,显然不能以无外贸需求来加以解释。
二是厘税的压抑和传统商业的竞争。厘金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本属勒索,但在尚未以子口税取代厘税的广大内地,外国商人每每为之裹足,因而它在客观上又为中国商人减少了竞争压力。以故中国商人在厘金和外商竞争之间的选择上常常呈两难窘况,有时甚至宁愿要厘金而不愿与外商竞争。另外,厘金税又是清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在关税和厘金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在某些外贸税收未必超过厘金数额的地区,政府作出舍外求内的决策,实属经济因素使然。开埠之后重庆的情况,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重庆是1891年1 月依照《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规定开放的。然而开埠之后情况却不尽人意。英国驻华使馆官员禄福礼(H.E.Fulford)在开埠一年以后的一份报告中作了如下总结:
到目前为止,重庆的贸易条件整体上还没有受到开埠的影响。这就是说,分发贸易仍然完全掌握在本地商人手中。……在目前的条件下,外国商人能否战胜早已建立并且组织严密的本地商行还是个问题。但是他们可以更深入地推进子口税制度以尽量扩大贸易。迄今为止,重庆是子口税制度的终点站。为了抵制繁重的厘税,应该把子口税制度推广到川省的每一个角落,并深入到川省邻近地区。(但)如前所述,以往这种努力遭到了明显的失败。(注:“禄福礼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1892年4月29日),见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1876—1949)》第87—8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外商在重庆遭遇的情况在其它口岸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外人要将子口税的推广,当成其须臾不敢懈怠的要务。
三是民族主义者的抗拒。一些地区具有贸易的良好地理及资源条件,但绅民排外情绪高涨,亦限制了口岸的设置及贸易的发展。湖南即一显例。其情学者尽知,故此从略。
然而,在自开商埠政策实施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前所述,自开商埠政策实施的时间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14年,其间共“自开”商埠35个。这一口岸数,约当戊戌前“中国本部”(China proper)所开全部条约口岸的数目。加上戊戌以后所开条约口岸,截至辛亥,中国的各类通商口岸总数已多达97个(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张洪祥前揭书所附“近代中国约开通商口岸一览表”,见该书第321—324页。)。这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育。
这一结论的例证是,早先几个通商口岸活动场域范围之外的“真空地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补。其中最明显的是东北地区。1898年以前,该地区只有位于辽东半岛上的营口和大连两个通商口岸。1905年,东北自开通商口岸16处,加上1903年依据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所开放的奉天府、安东,依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开放的大东沟,以及1909年依据中日《图们江中朝界务条约》所开放的吉林4埠, 东北地区的全部通商口岸已多达25个。一个遍及吉、奉两省和黑龙江部分地区的外贸市场网系已经形成。在长江中游地区,原先只有汉口、宜昌和九江三处对外通商,随着自开商埠政策的实施,该地区又开辟了武昌、岳州、常德、湘潭四个自开商埠,长沙作为介于条约口岸和自开商埠之间的特殊类型口岸,亦于这一时期对外开放。这样,不仅湖南这一重要的省区结束了没有通商口岸的历史,而且长江中游地区既有的一条线(长江)上的几个点(商埠),亦因湘省四个口岸的开放而连成一片,长江中游的外贸市场网络由此而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海湾地区,由于秦皇岛的开放,天津与营口、奉天府之间有了一个可以吞吐货物的埠头,这使直鲁经济区同东北经济区在陆上发生了联系(注:秦皇岛开埠之后,虽其贸易范围主要限于山海关、锦州附近及朝阳、赤峰一带,但因该埠为天然不冻港,每年白河封冻之后,天津贸易,多移至此,又与京奉铁路相连,故该埠沟通直、奉地区贸易联系之作用十分明显。参阅陈重民编纂:《今世中国贸易通志》第一编“对外贸易之大势”,第98页,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而直鲁地区本身亦因济南、周村、潍县的开放,将通商口岸由沿海拓展到腹地,扩大了该地区外贸活动的场域。在黄海沿岸,海州的开埠则使直鲁地区与华东地区的贸易联系得到加强。在福建北部沿海,三都澳的开放也产生了类似的作用。《海关十年报告》提供的资料表明,三都澳口岸开放后,闽北地区的货物开始大量地通过轮船运往福州。福州海关的税款则逐渐向北转移,据估计,开埠之初,“三都澳征收的税款有99%是从福州税款中转移过来的”(注:《三都澳海关十年报告》,见《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54—156页,1985年。)。很明显,三都澳开放缩短了华东外贸市场网络与华南网络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另外,在僻处边陲的云南,省城昆明的开放亦使该省既有的外贸市场场域由滇南及边境地区向经济发达的中部地区延伸了至少两百公里。
显而易见,我们在分析1898年以前中国已开通商口岸活动场域时所指陈的一些“空白”及各区域间存在的“隔阻”现象,在大量的自开商埠出现之后,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这种状况,是自开商埠的对外贸易能够在总体上维持一定的规模并在一些地区能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然而,一些结构性的缺陷也开始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口岸分布疏密失当,个别地区商埠的密度偏大。这突出表现在吉林和奉天两省。吉、奉两省原先过于闭塞,开辟通商口岸无疑可以促进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总有些怀疑,在清季,像吉、奉这类经济并不发达,人口亦算不上稠密的省区,在外贸上有没有开放20个通商口岸的必要。以苏、浙两省的人口和土地面积相观照,或许有利于说明这一问题。有关资料表明,1898年,江苏和浙江两省人口总数为3429万人,面积接近21万平方公里,清季开放口岸的总数为10个。以此计算,当时两省每342万人口才拥有一个口岸, 每个口岸的辐射面积(假设已经将该两省全部覆盖)约为2.1万平方公里。 而同期吉、奉两省的总人口为542万人,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 若以通商口岸数20来分别除人口和面积,则平均每个口岸只与27万人口发生直接供求关系,这一数据仅为苏、浙两省口岸同类数据的7.8%, 尽管其可能的辐射面积略大于苏、浙两省,达到了2.6 万平方公里(注:有关人口数据,参阅姜涛著:《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88—435页所附“ 1749 —1898年分省人口统计”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吉林缺1898年统计数据,故代之以1897年的数据。)。事实上,吉、奉两省在经济上对如此众多口岸的需求是在20多年以后的事。清季吉、奉两省的开放,与其说是经济的内在规律使然,勿宁说是日、俄激烈争夺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宣布开埠之后,才会出现一部分口岸在发展路途上步履维艰,甚至形同虚设的状况。
与东北地区广开商埠形成鲜明对照,一些省区在清政府宣布实施开埠政策多年以后,仍然是深藏固锁,没有开放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这些省区有山西、陕西、河南、贵州、青海、甘肃等;另外,像四川这样的具有数千万人口的大省,清季也始终只有重庆一个口岸对外开放。这就形成了外贸市场网系分布于周边和长江一线,而“内陆地区”几乎与外贸无缘的状况。费维恺教授认为,19世纪中国的商业制度,虽然有“高度的传统式进展”,但仍然不能划归“现代”市场经济的范畴(注:费维恺著、林载爵译:《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53 页, 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费氏在作出这一论证时有他认定的“现代”标准。但通商口岸的商业制度是“现代”的则似乎不应该有所争议。从实施自开商埠政策之后中国通商口岸的分布情况来看,尽管某种良性发展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但如果据此认为一个“现代”的商业贸易市场网络已经发育成熟,则显然缺乏依据。研究清季自开商埠史,这一层似不应当忽略。
第二是外贸网络上形成了某些“死结”。如前所述,商埠欲生存发展,须具备一定的“需求圈”作为前提,其“销售域”方可拓展。由于竞争的关系,每两个商埠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避免各自界域的交叉重合。如果两个口岸因距离太近而导致界域严重交叉,则其中一个条件较差的口岸很可能成为该地区外贸网络上的一个“死结”,成为另一口岸发展的牺牲品。 武昌和浦口两埠的情况即可作如是观。 武昌是1900年奏准开放的,但迟至1917年,才由湖北省宪拟具“通商场筹备大纲”,谘由主管各部核算,直到1919年年底委任韩光祚为商埠局长之后,开埠事才初现眉目(注:《内务部经办商埠一览表》(1921年11月1日),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武昌商埠迟迟未能发展的症结在于贸易活动的场域与仅一江之隔的汉口形成了过多的交叉重合,而其起步从事近代商业活动的时间又较晚。如众所知,汉口是1861年依英约而开放的。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武昌奏准开埠时,已经成为中国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到这里来从事商业及其他活动的外国人已多达3千余人(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anford,Callfornia,p.13。此书承马敏教授代为复印,谨致谢悃。),年贸易额高达一亿三千万两,商业繁盛,被誉为“东方之芝加哥”(注:〔日〕水野幸吉:《汉口》第1页,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版。 转引自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第 120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由于长江的隔阻给位于南岸的武昌留下了少许生存空间,但其发展前景显然是不容乐观的。浦口的情况亦类是。尽管占踞了津浦铁路南段起点的有利条件,在一江之隔的省会城市南京已经开埠的情况下,浦口除了扮演货物转运站的角色之外,人们很难在商贸方面对之抱多大期望。事实上,早在筹议开埠时,外务部就曾经批示:“该埠与金陵口岸相距甚近,酌设轮渡以转输货物,亦可期便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民政部档案,全宗号509, 案卷号209,《两江总督咨送浦口建立市场简章及有关文书》。), 对急于在浦口开埠提出异议。该埠后来的发展步履维艰,可谓良有以矣。
四、余论
清季自开商埠政策实施之后,随着口岸的增加,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网系得到了一定的发育。但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种发育还远远没有臻于成熟。外贸市场是一种与国际市场并轨的外向型的商业场域,它不仅承担着向外输出中国传统农业及手工业制成品的职责,而且担负着吸纳外国工业制成品的任务,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在它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中国社会经济对于出入口商品的吐纳能力。然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在传统经济结构中已经运行了不止千年,没有迹象表明,在清朝统治的最后的若干年里,传统经济已经面临解构。既然中国的传统经济几乎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既然这种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内向型的设置,那么,在性质上与之相互径庭,在形式上与之成方枘圆凿之势的外贸市场欲求发育成长,自然也就难乎其难了。自开商埠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此其首要原因。
此外,清政府在制订自开商埠政策时混淆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造成了自开商埠的畸形发展,亦有以致之。开埠通商,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只有把它当做经济行为,才可望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清政府中的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主动开埠可收权操自我之效,但商埠开辟过多又难免导致外国人及外国物质的乃至精神的产品的大量涌入。权衡利害,结果抛出了实施范围极为有限的自开商埠政策。但清末的内外形势已经不是这种多少带有“以攻为守”策略的开埠办法所能应付的了。当时,许多开明人士都认为,全境对外开放已经势在必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实施全境对外开放的政策,历数十年,国以强盛,民以富足。在中国酝酿自开商埠政策之时,一些开明的官绅亦曾提出仿效日本的建议。出使俄国大臣杨儒就曾认为,今之中国,实乃昔之日本,在对外通商问题上,“东邻之成例可援”(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49第6页。)。彭名寿亦主张广开商埠,他在《湘报》上发表文章,以日本明治维新“举全国而口岸之”,商务遂盛,国力遂增,作为通商成效之证明,主张以日本为师(注:《湘报类纂》论著甲下,第28—29页,光绪二十八年刊本。)。盛宣怀在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期间,曾与郑孝胥等人议及“举国通商事”,并提出“将内地各省会一体通商”的建议(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二册,第642—643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二十九日条,中华书局1993年版。)。虽然在今天看来,清末中国未必具备了像日本那样全境对外开放的条件,但当时对外贸易的需求亦非清政府实施自开商埠政策时缩手缩脚的作法所能满足。清政府既要“主动”开埠以示“开明”,又要将开埠之弊害控制到最低程度,自然只能在自开商埠的数量、口岸级别和地域分布上作文章,于是出现了本文所指陈的低水平开放的局面。
不过,清季实施自开商埠政策并非毫无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正面”的或“积极”的作用。清政府既然在对外贸易方面有所建置,并由此提供了某种新的经济结构,其作用与功能就必然有所发挥。事实上,自开商埠政策实施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由于篇幅的缘故,本文的论域只限于“结构”,至于“功能”,只好留待另文再作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