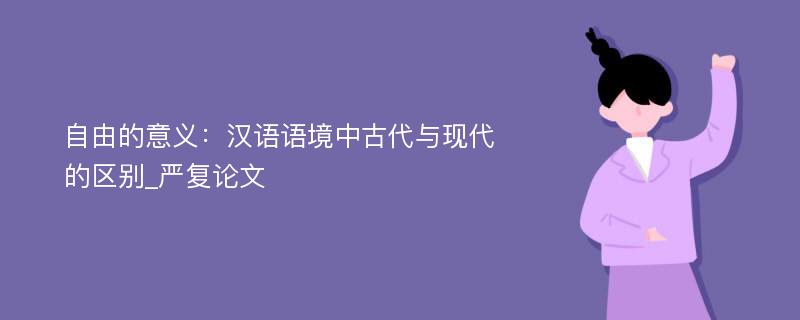
自由的含义:中文背景下的古今差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中文论文,含义论文,差别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严复集》第1册,第2页)八年之后的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自序”中,严复写道:“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同上,第131页)①
严复生活的时代,正如他文章题目所标示的,是一个“世变之亟”的时代。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是西方近代观念蜂拥进入中国的时代,“自由”的观念也从“未尝立以为教者”,转而为“常闻于士大夫”。新观念的传入或者兴起,一定会面临“竺旧者”和“喜新者”的分歧,“自由”的观念在一个“世变之亟”的时代兴起于中国,所面临的分歧尤其尖锐。但是,严复敏锐地看到,新旧人士对于自由的观念虽有好恶之不同,却有共同的误解。正是为了对治误解,他翻译了穆勒的On Liberty,并且译为“群己权界论”,认为划分“群己权界”是理解“自由”的根本,所以在该书的“自序”中特别指出:“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
为什么中国历古圣贤深畏自由,从不立此为教?守旧者为何视之为洪水猛兽之邪说,而喜新者又如何误解了自由的含义?严复以“群己权界”为理解自由的关键,对于自由的观念意味着什么?这些是本文意欲探讨的问题。
一、“自由”的中文词源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自己的思考是在中文的语境下进行的,即使是研究西方思想,也将面临它们的中文表达问题,而一旦使用中文,中文语词的历史积淀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上,第5册,第1322页)岂惟译书如此,研究和论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于自由的观念而言,追索它的中文词源和历史语境尤其重要。自由的观念在19世纪末骤然兴起于中国,固然与“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关系密切,但是,自由热的激发与西学东渐相关,并不意味着自由的语词没有它本土的词源。相反,本文的考察将显示,正是因为受制于中文的历史语境,才有了“竺旧者”对自由的深畏和“喜新者”的恣肆泛滥,而严复宣扬的自由观念由于强调“群己权界”,因此扭转了中文“自由”的传统语义。
那么,自由在中文中的传统语义是什么?严复说:“自繇……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从“自由”的词源来看,应当说严复的理解是准确的。但是严复又说:“自繇之义,始不过自主无罣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这些劣义“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严复集》第1册,第132-133页),这样说就不太准确了。下面的考察将表明,尽管自由最初是一个中性词,但是自由的贬义也是自由初义的必然引申,并非与初义无涉。
下面先考察“自由”的中文词源。
“自由”在中文里出现是很早的,东汉末郑玄(127-200)注《礼记》,三次用到了“自由”。②这说明至少从东汉时代起,中文里就有自由这个语词了。③那么,自由的含义是什么?
《礼记》卷二说:“帷薄之外不趋。”郑玄注释说:“不见尊者,行自由,不为容也。”卷三十五又说:“请见不请退。”郑玄注释说:“去止不敢自由。”还有一个语例与肉食的软硬有关,郑玄的注释是:“欲濡欲干,人自由也。”这里只分析前面两个语例。
“趋”是行走的一种姿态,《辞海》的解释是:“小步而行,表示恭敬。”见尊者要以“趋”的姿态,表示对尊者的敬意,这是礼的要求。但是在帷薄之外,还没有见到尊者,这时步履可以自由:自如地走,不必“为容”,做出趋的姿态。所以郑玄注释《礼记》的“帷薄之外不趋”,就说:“不见尊者,行自由,不为容也。”拜谒尊者也有礼制的具体要求,不能想见就见,想走就走,所以见面要事先提出请求,见面后也不能自己随意离开,郑玄注释:“请见不请退”,称“去止不敢自由”。
这两个语例里的“自由”,都是“随心所欲,自己做主”的意思。见尊者一定要趋,这是礼制的要求,没有见到尊者之前,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走路姿态,这就是“自由”。而拜见尊者,无论是去拜谒还是告辞离开,都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也就是“不敢自由”。“自由”最初出现在中文里,基本含义就是行为举止上的“自己做主”。
那么,什么情况下能够自己做主,什么情况下不能自己做主呢?“帷薄之外”是一个重要提示。没有掀开帘子进入厅堂,是可以“行自由”的,一旦进到“帷薄之内”,就不能自由了,而是必须遵守礼制的规定,该趋的时候趋,该拜的时候拜。“帷薄之外不趋”是一个具体的礼仪规定,也是一个隐喻:“帏薄之内”喻指礼义制度的范围之内,而“帏薄之外”喻指礼仪制度的范围之外。由此也可以说,在礼义制度的范围之内,人的行为必须遵从礼义制度的规定,是“去止不敢自由”的;而在礼义制度的范围之外,就可以自己做主,可以“行自由”。所以,虽然郑玄注释《礼记》时只是用“自由”解释具体的礼仪规范:见尊者应当如何,不见尊者可以如何,但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一个具体的礼仪宣布了一项最基本的原则: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行为方式的事情,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不能与他人有关,一旦与他人有关,就涉及了安排人际关系的礼仪和制度,这时候就必须遵守礼仪制度而“去止不敢自由”,就没有“自由”存在的位置了。
据此也可以说,传统中文里的“自由”是一种“无关系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发生在制度的规定之外,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涉及安排人际关系的人伦秩序。这种无关对象或他者的自由,与庄子的逍遥游有点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发生在“无何有之乡”,不是“人间世”的事情:人们在“无何有之乡”可以逍遥,而在“人间世”则一切皆“寓于不得已”,必须遵循人间世的各种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中文里的“自由”如同逍遥游一样,是一个人独处时候的自在随意,与他人没有关系,与人际没有关系,与安排人际关系的礼仪制度没有关系。“自由”的含义是一个人在人际之外、制度之外、规矩之外的自得自在。
二、“自由”语义的贬义化
追踪“自由”的中文词源,可以看到,“自由”是规矩之外的事情,不能与制度发生关系。那么,如果发生关系将如何呢?下面的分析将表明,一旦发生关系,则这种关系的性质必定是否定性的。用“帷薄之外不趋”来说,就是在“帷薄之外”固然可以“不趋”,可以“行自由”,但是在“帷薄之内”也“不趋”,也“行自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时候“自由”所表达的“自我做主”就变成了擅自做主、为所欲为,甚至变成了恣意妄为,变成了对礼制的挑战。因此,“自由”是不能与制度和规矩发生关系的。
“自由”与制度相互外在的关系,其实也使“自由”与制度构成了相互反对的关系。不能与制度发生关系的“自由”,恰好在提示着制度的态度:制度拒绝“自由”。而“自由”的贬义就发生在不允许自由的制度之下。在史书中,可以看到“自由”与“明制”对举,表达着违背制度的否定性含义。例如,晋武帝司马炎下诏指责王濬“忽弃明制,专擅自由”,吓得王濬上书自辨,称“伏读严诏,惊怖悚栗,不知躯命当所投厝”。(《晋书·王濬传》)这里“忽弃明制,专擅自由”的“自由”,显然是指违背制度,否定性的含义不言而喻。又如《后汉书·阎皇后纪》记载阎皇后的亲戚专权,用了“自由”的语词来描述阎氏“兄弟权要,威福自由”。④《后汉书·五行志》称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天子,却“视之如小儿,百事自由”。其他如《晋书》的“杀生自由,好恶任意”(《晋书·刘琨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晋书·王敦传》)等,其“自由”无不与制度的规范和应当相对立,表达着否定的含义。严复说,自由的劣义“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严复集》第1册,第133页),而据笔者的考察,“无关系的自由”一旦进入关系,一旦涉及制度,其贬义化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对于制度来说,“自由”是一种异己的危害性力量。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富强是全社会高度赞同的一致目标,国家要富有、强大,人民要富足、强健,几乎没有人对此心存疑惑。但是,在一致追求富强的共同努力中,在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和认同方面,却明显存在着差异。严复时代的“竺旧者”和“喜新者”对于“自由”就有分歧,据说现在仍然有人不赞同把“自由”列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如果询问这些对“自由”心存疑惧的人们,探问他们存疑的理由,恐怕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自由”仍然意味着违背制度,意味着不守党纪国法,“自由”的中文传统语义(当然也是传统观念)很可能就是他们对“自由”心存畏惧的潜在心理原因。
严复说中国历古圣贤深畏自由,从未尝立以为教。的确,在传统中文的语境下,“自由”的含义是一个人独处时的自在,是“无关系的自由”,不能与制度发生关系,一旦发生关系就只能是否定性的,在这种语境下,我们的先圣先贤如何可能以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而立以为教呢?而这样的自由又如何能够不令“竺旧者”惊怖其言,并视之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呢?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是以上下有等、长幼有序为社会理想的,这样一个以身份安排秩序的社会确实没有自由的位置。更何况,传统语义的自由本身就不能涉及关系,“喜新者”如果用这种“无关系的自由”强行于社会并据以抗拒秩序,在不能“行自由”的“帏薄之内”执意“行自由”,又如何能够不进入恣肆泛滥的迷乱之中呢?
严复对中文“自由”所表现出来的“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的劣义深感不安,所以在翻译《群己权界论》时,用了“自繇”来取代“自由”。其实,就文字本身而言,“繇”与“由”是相通的,《尔雅·释水》曰“繇膝以下为揭,繇膝以上为涉”,足以为证。就语词而言,“自繇”也不是严复的新造之词,而是历史的旧有之词。《册府元龟》摘记阎皇后的故事,称阎氏“兄弟权要,威福自繇”(《册府元龟》卷三百六《外戚部》),用的就是“自繇”而不是“自由”,《后汉书》用的则是“自由”。类似的语例《册府元龟》里还有。显然,由于“繇”、“由”相通,至少从宋代开始,“自繇”就与“自由”通用了。但是,虽然“自繇”的写法复杂一些,却是一个比“自由”晚出的语词。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解释自己选用“自繇”的理由时说:“今此译遇自繇字,皆做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严复集》第1册,第133页),他似乎把笔画比较繁难的“自繇”当作更加古远的语词,这多少有点不准确。不过,接下来的解释则是有意义的:严复说,西文的liberty是一个很实在的术语,不是拘虚之说,所以“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区别什么?显然是区别于“自由”。传统的“自由”不能进入社会生活,是“虚”的;一旦与制度相关,又将附着“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等诸多贬义,又是“劣”的。严复使用不甚流行的“自繇”来翻译liberty,再加以自己的批语和说明,就是为了克服“自由”的虚义和劣义,而只取“自由”不为外物拘限的初义,由此初义来接引西方近代的“自由”观念,并由此宣示出传统中文的“自由”语义不曾拥有的近代内涵。
三、“自由”语义的近代转化
由于严复及其同代人的努力,到了近代,中文的“自由”增加了它原本没有的新含义。这个新增的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蕴涵了“权利”的含义,蕴含了在社会生活中划分人与人之间权利界限的含义。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上下有等、长幼有序,这种形态的社会关注的是人的身份资格、道德责任,而不在意人的权利问题,传统的中文中甚至没有“权利”一词。“权利”这个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时,“入一权字”并“增一利字”组拼出来的新词,用来翻译英文的Right,⑤后来逐渐流行开来。传统中文没有“权利”一词,因此,中国传统思想从不讨论权利问题,尤其没有从个人出发的权利意识,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是与传统社会的性质相匹配的观念现象。严复等人从西方引进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后,中文的“自由”才成为与权利相关的观念。上文提到,严复翻译穆勒的On Liberty,不是译成“论自由”,而是译为“群己权界论”。他用“群己权界”来规范“自由”,就是为了表明“自由”既是对权利的伸张,同时也是对权力的限制,并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恣意妄为。后来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直接用“权利”来定义“自由”,称“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29页)从严复的时代之后,中文的“自由”才成为与权利相关的概念。
“自由”与权利相关,与权利划界相关。传统的“自由”只能在“帏薄之外”享用,进入“帏薄之内”就是挑战制度,就是作乱。但是,当“自由”拥有权利的含义之后,它恰好就是“帏薄之内”的事情了,因为正是在人际之间才有伸张“自由”和限制“自由”的问题。严复说,如果一个人独居世外,一切活动皆自作主张,无论做什么,自己决定即可,因为不存在他人,所以也不存在禁止和限制的问题。进入社会就不同了,“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严复集》第1册,第132页)
这是对传统“自由”语义的扭转。在传统的语境下只有“帏薄之外”才能“自由”,而严复却说在“帏薄之外”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在传统的语境下,“帏薄之内”是不允许“自由”的,而严复却说只有入群之后,在人际之间才有自由和自由的限定问题。显然,经过了近代思想的洗礼之后,中文的“自由”具有了两种很不相同的含义:一种是传统的语义,指独处时的自得自在;一种是近代的语义,指社会的团体生活中的自由权利和对权力的限制。可以说,畏惧“自由”的人恐怕心里都潜藏着“自由”的传统语义,而伸张“自由”的人未必完全懂得“自由”的近代含义。在严复的时代,“竺旧者”固然畏惧传统含义的自由,而“喜新者”之所以“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恐怕还是没有跃出“自由”的传统含义。
当“自由”初兴之时,其新旧含义明显纠缠在一起,民国初年的政令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民国二年的大总统通令说:“惟民国以人民为主体,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征心理之同……值此邪说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是,国何以立。”(程淯,第36页)民国三年的大总统通令说:“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同上,第37页)该通令一方面抱怨无识者“误解平等自由”,“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另一方面也把自由民主作为正面价值标立起来,作为立国的原则。拿这种原则与现实的实际情况相对照,其间无疑还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尽管如此,立国的基础毕竟变了,不再是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而是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原则。这就表明,严复藉由翻译和评语赋予“自由”的正面含义,已经成为中国走出传统、敞开新路的重要方向了。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人一直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艰难行进,直到今天仍然纠缠在“自由”的传统语义和近代语义之间而徘徊不定。
“自由”语义的古今差别,实际上是以观念的形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制度环境。古代的“自由”与传统的等级社会相关,以疏离社会的姿态表现出某种退避的消极意味;而现代的“自由”积极伸张公民社会的基本权利,是社会正义的当然内涵。在古今的对比之下来看围绕“自由”发生的疑虑和争执,可以说,只有当“自由”完全摆脱了身份制的人身关系,成为公民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公共意识时,人们对“自由”的畏惧和误解才会消除,“自由”的现代意义也才能真正彰显。
注释:
①严复既使用“自繇”,也使用“自由”,二者的区别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②在郑玄的《礼记注》中,“自由”二字出现了12次,其中9次是用“由”来解释“自”,所谓“自,由也”;此外的3例是“自由”连成为一个片语的用法。
③赵岐(约108-201)撰《孟子章句》,也使用到“自由”一词。《孟子·公孙丑下》:“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赵岐注:“居师宾之位,进退自由,岂不绰绰然舒缓有余裕乎?”
④阎皇后的故事是宫廷权力之争的典型故事。阎皇后是东汉安帝(107—125)皇后,“后有才色”,她的兄弟“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汉顺帝当时是皇太子,阎皇后废他为济阴王,安帝死后,又秘不发丧,安排“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称少帝。现在的历史年表上没有这个皇帝,这个少帝在位仅仅200来天就死了。少帝死后,阎皇后的兄弟们又想重玩旧花招,再立一个小皇帝,“太后征济北河间王子,未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后汉书·阎皇后纪》称阎氏“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就是指他们在少帝在位时实际掌握了朝廷大权。这里用“威福自由”来描述他们的专权行为,“自由”的含义显然是否定性的。其他故事也有相似的语境。
⑤《万国公法》于1864年刊行。丁韪良在《公法便览》中说:“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入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转引自赵明,第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