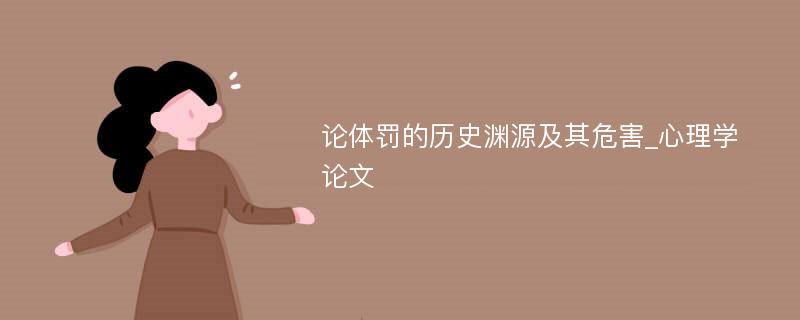
论体罚的历史根源及其危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些学校和家庭中,体罚和变相体罚被当作一种教育手段依然存在,我国早在解放区时就要求废除体罚。建国后,教育部于1952年2 月14日发出明确指示:废止对学生施行体罚或变相体罚。此后,又曾多次明令严禁体罚学生。然而,体罚并未绝迹,在一些学校和地区甚至还相当严重。某些家长或教师体罚学生致残致死的惨案,时见于报端,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有人公然认为体罚在特定条件下“适当采用有积极作用”,有人公开主张“对屡教不改的学生适当体罚,是完全必要的。”在日常德育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对体罚的严重危害及其产生的根源予以剖析,进而使教育者自觉地废止体罚,是当前德育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
体罚在中外教育史上可谓“源远流长”。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类学校中,教师可以用戒尺(即戒方,亦称戒饬)等任意责罚学生。明代中央国学国子监特设由监丞负责的“绳愆厅”,专司对学生的体罚,国子监的监规规定:“在学生员……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诉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充军”。清代王誉昌《崇祯宫词》注:“有犯老师,批本监提督责处,轻则学长以戒方打掌,重则罚跪于圣人前”。《儒林外史·七》载:“本该考居极等,姑且从宽,敢过戒饬来,照例责罚。”可见,体罚在中国封建教育中,早就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教育手段。
在西方教育史上,以野蛮的体罚而著称的“硬教育”,当推斯巴达教育。斯巴达是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以剥削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为生的奴隶主阶级,建立了一种军事教育制度。斯巴达人的法律规定,儿童属于国家,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男孩七岁即被送入“国家教育场”,直至十八岁升入“士官团”,二十岁始服兵役直至六十岁退役。在教育场内,总监有一批助手,称为“鞭打者”。学童四季穿单衣,光头跣足,石块为枕,芦草为席,经常无端受鞭笞,且不许哀号呻吟。这种教育制度,使斯巴达成为古希腊的军事强国之一,以维持其贵族寡头统治,但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则远逊于雅典等城邦。公元前四至三世纪,斯巴提亚特集团势衰瓦解。
文艺复兴前的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学校也普遍流行体罚。桦棒、棍子等体罚工具,成了许多学校必备的教具。近代资产阶级虽然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允许体罚。十七世纪英国教育家洛克一方面反对体罚,一方面认为,如果学生倔强和公开反抗,仍然可以采用体罚。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在管理儿童的方法中,包括体罚在内的惩罚,应当占重要地位。他把整个教育学体系分为管理、教学和训育三大部分。所谓“管理”,就是运用威胁、监督、惩罚等强制性的方法,“克服儿童不驯服的烈性”。迄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里,体罚现象也仍然存在。
剥削阶级及其卫道者,为什么对体罚手段乐此不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教育是奴化教育。他们对学生“终日以冷遇和呵斥,甚至打扑,使他们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鲁迅语),使其不敢破坏旧世界的纲常秩序。社会主义教育是区别于以往任何剥削阶级教育的新型的教育。我国现阶级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的建设人才。教师的神圣职责是爱护学生,教书育人。体罚,严惩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而无助于学生德智体美劳任何一方面的正常发展。体罚,与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任务,与人民教师的师德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必须坚决摒弃与废止。
二
有些教育者在理论上可能也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不应该采用体罚手段。但在实际教育过程中,他们又认为在“特定条件下适当采用有积极作用”,或者把体罚同处分惩罚混为一谈,认为是必要的。许多家长则往往是“恨铁不成钢”,希望棍棒出强龙。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某些领导也认为,体罚固然不对,但管总比不管好,或是怕抓不好挫伤教师的积极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从宏观上看,体罚是一种惩罚。然而,在狭义上,体罚和惩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对是非善恶肯定与否定的认识过程。作为对受教育者的品行进行否定性评价的一种高层次方式,具有惩罚性质的处分是必要的。在学校管理法规规定的程序与方式范围内,处分惩罚的刺激能使受教育者产生条件反射,进而使他们的道德认知和行为规范化、社会化。但即便如此,处分惩罚这种厌恶刺激所产生的负强化,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因此,也必须慎重,不可滥施。
诚然,体罚也是一种厌恶刺激,甚至有时在精神病院里被做为行为矫治的一种疗法。在实现短期教育目标上,它也可能暂时在个别学生身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正确而必要的处分惩罚,是道德对非道德的谴责,是纪律对反纪律的制裁,是理性的合法宣告;而体罚的本身就是非道德的,其动因往往只是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受到体罚或变相体罚的孩子,生理上的创伤自不必说,心理上的损害则更严重。
其一,是对孩子自尊心的损害。自尊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但表现为对个人的自我尊重,而且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权利和人格。它可以成为个人自爱自重的内因,也可以成为个人克服各种困难和自身弱点,努力进取以维护自己尊严的积极行为动机。儿童心理学指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强和生理的发育,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是自尊心的增强。这种自尊心,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分析中,属于“超我”的范畴。作为“本我”和“自我”的对立面,“超我”自拟了许多清规戒律,强迫“自我”遵守,并时刻抑制“自我”的种种反规范、反社会的欲望和冲动。当然,“超我”的堤防可能被冲溃。然而,体罚和名目繁多的变相体罚如打耳光、打屁股、撕耳朵、罚站、罚晒、罚冻、罚饿、罚跪、封嘴、罚自己打自己、罚扫地、罚抄作业等等,恶狠狠地撕裂了孩子脆弱的自尊心。在人格受辱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超我”的抑制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宽容的可能,从而听任非规范行为恣意冲破自尊自律的防线,让“自我”冲动公开释放。他们往往或自暴自弃,破罐破摔;或文过饰非,欺骗说谎;或思想绝望,走向极端,毁物伤人。
其二,是对孩子人格正常发展的损害。许多心理学家的研究都表明过这一点:对儿童缺乏真心实意的关怀和慈爱,将使他们的人格发展不正常。德国当代心理学家霍尼认为,少年儿童有两个基本的需要:安全与满足。霍尼举出一些使少年儿童安全需要受挫的父母或教师行为如对孩子体罚、冷漠、遗弃、厌恶、偏爱、奚落、愚弄、羞耻等,认为如以这些行为对待他们,将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体验,她称之为“基本敌对情绪”(basic hostility)。这样,他们一方面依赖父母师长, 一方面又在内心里抱有敌意,产生剧烈的心理冲突。我们知道,少年儿童无力改变这种不幸的局面,而且在许多文化背景中,孩子对父母师长抱有敌意,往往被认为是有罪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压抑这种敌对情绪。总之,这种压抑仅仅是由无助感、恐惧感和罪恶感驱动的。由于这种压抑,他们的人格发展必然是不正常的。
然而这种“基本敌对情绪”与日俱增,压抑的驱动力却显而易见在日益减弱。成年后,他们的敌对情绪将泛化投射到周围所有的人与物,在暗地里或公开地释放出来,给社会带来种种不良甚至不幸的恶果。
体罚者对此应该负有什么责任呢?
我国心理学家陈仲庚认为,“赞赏和惩罚对一个学生的人格发展是十分敏感的因素”,因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象及自我评价是由别人对自己的行为态度的反映照见本身而产生的”。经常受奖自知向上,经常受罚者往往沦落。批评处分尚且如此,体罚尤然。伴随着肉体痛楚的精神刺激,在日后往往还会不断地被同伴同学有意无意地取笑和挖苦。在被体罚者的内心深处,这颗“臭花生”的味道也永远除之不去。读者都是过来人,孩提时代或许也受过这样那样的体罚,这种体验是可以理解的。经常遭受体罚者,将会严重地被不良情绪所困扰,最终导致各种人格障碍特别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和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少年儿童缺乏父母师长的爱是这些精神病态人格发展的首要原因,而当前存在的各种体罚现象的深层原因,恰恰是体罚缺乏了一个“爱”字。
综上所述,体罚造成的心理损害是严重的,我们必须坚决摒弃废止。
三
在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今天,体罚的又一个危害是造成了流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禁止体罚学生”。因此,体罚不仅不利于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有害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对于体罚者而言还是一个法律问题。
体罚引起流生,其发生机制有必要予以探究。
精神病学家沃帕做过这样的实验:他把一只猫关在笼中,在其饥饿时投入食物。当猫将要取食时,就给以强烈的电击。反复多次,猫就出现强烈的恐惧反应,拒绝吃笼中的食物,而且对猫笼以及实验室环境也产生恐惧反应,力图逃走。这个实验提示我们,当父母师长因孩子的学习或行为问题施行体罚时,孩子不仅对体罚的本身产生厌恶和恐惧,而且对学校的所有学习环境产生同样反应。除了生理需要,一个人最迫切的就是安全需要。受体罚的学生,出于安全需要的本能逃出校园,态度是坚决的。经验表明,这些流生很难动员复学。我们还可以分析,在这些流生原来的道德观念中,教师是至善至美的。当教师扬起拳掌,他就把孩子理想中的偶像击碎了,在极度的失望情绪中,他们一走了之,确实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注意到各类报刊的中缝经常刊登着“寻人启示”,其中有多少孩子是因被父母体罚而离家出走的,虽无统计资料可资分析,但可以想象不在少数。家长明鉴!
从法律、伦理观念来看,体罚难道还不应该摒弃废止吗!
在现实生活中,“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成才”等俗谚至今流传未衰。封建教育流毒影响之深,可见一斑。但是,优秀的教师,合格的家长,教育孩子是不靠棍棒的。我们只能用“爱”去感化学生,只能用真善美去战胜假丑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必须摒弃废止体罚和变相体罚,希望这能够成为广大教育者信服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