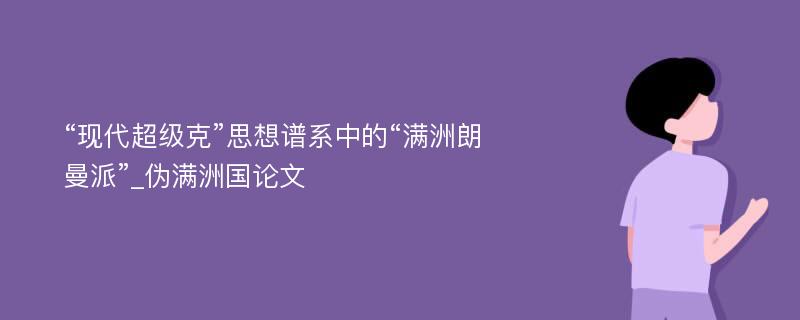
“近代的超克”思想谱系中的“满洲浪曼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论文,谱系论文,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浪曼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第8期《中央公论》“中公读书室”栏目以日本思想史及文化理论著名学者子安宣邦的新书《“近代的超克”是什么》为话题对他进行了专访。当问及竹内好的“近代超克”论与“日本浪曼派”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子安总结道: 战后对于“近代超克”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几乎没有人把它们置于昭和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理解和修正……竹内在战后对“日本浪曼派”进行了重新评价,使保田①反语式的“近代超克”论在战后重获生机,并确立了自身的理论立场。保田将目光投向日本古代以寻求实现超克的基础,而竹内好则诉诸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是在以欧美为榜样率先现代化了的日本身上,而是在“不断失败而又顽强抗争的亚洲(中国)”那里找寻一种反抗的主体性。② 为了填补战时的那一段“空白”,在“日本浪曼派”与竹内好之间、战前与战后的“近代超克”论之间建立起某种前后相承的联系,子安宣邦在梳理的过程中又加入了围绕着“近代的超克”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三次辩论,即1941年10月召开的以尾崎秀实、橘朴为首的“大陆政策十年检讨”座谈会、1941年12月8日召开的以京都学派为核心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研讨会以及翌年7月召开的“近代的超克”专题讨论会。③ 与子安不谋而合,哈卢图尼恩在《为近代所超克》一书中以第三次会议为研究对象,归纳了二战时期“超克”理论的三种类型:一是小林秀雄的观点,主张通过重新发现日本古代文学经典,恢复“原初的情感及感性结构”,从而实现文化重建的最终目标;二是龟井胜一郎的观点,主张通过复兴日本传统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以奠定现代日本文化认同的基础;三是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西谷启治的观点,主张通过以“无我”(subjective nothing)代替“自我”(subjective self),消除主客体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缓解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④ 按照子安宣邦和哈卢图尼恩提供的这份谱系,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时,“近代的超克”都是以日本自身的文化资源作为实现手段,它们“表面上的主题始终是近代-欧洲世界史”。但这一谱系有意识地回避了作为“昭和中心问题”的“中国问题”⑤,让人疑窦丛生:“近代超克”论者将目光转向中国,这种朝着中国的转向真的是直到1959年竹内好正式提出“以中国为方法”才横空出世的吗?二战期间大批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经验对他们当时的理论主张真的没有产生过丝毫的影响吗?“近代的超克”理论是否真如子安所论述的那样呈现出一种跳跃性的发展模式?对于“满洲浪曼派”这样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考察无疑能帮助我们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日本浪曼派”与“近代的超克”的思想渊源 要确定“满洲浪曼派”在“近代的超克”理论谱系中的相对位置,就必须厘清它与“日本浪曼派”之间的思想渊源。早在所谓日本现代“文艺复兴”运动发轫之际的1932年,面对因大萧条而急剧恶化的社会文化生态,时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美学科的保田与重郎就与同年级的田中克己、中岛荣次郎、小高根太郎、薄井敏夫、松下武雄、伊东静雄等人共同创办了“以反抗文学主流、否定文坛一切既有事物”⑥为宗旨的纯文学杂志《我思》(コギト)。1934年,保田又在《我思》11月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日本浪曼派”公告》一文,一个新的致力于浪漫主义研究的文学团体就此宣告成立,署名成员包括保田与重郎、龟井胜一郎、中岛荣次郎、神保光太郎、中谷孝雄、绪方隆士六人,之后又扩大到56人,囊括了萩原朔太郎、佐藤春夫、太宰治等一大批当时已声名显赫的文学家,令“日本浪曼派”成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⑦ 综观“日本浪曼派”的理论观点,可以归纳出这一流派的几大特征:首先,“日本浪曼派”所要超越和克服的近代并不是广义上的西洋文化,而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以“文明开化”为口号的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国家主义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不但给日本带来了“文化的丧失”,还导致日本社会陷入阶级争斗、矛盾丛生的分裂状态。只有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化批判才有可能对这种近代国家体制予以道义上的谴责和系统性的否定:“明治之后我们日本自始至终也未能摆脱落后的俾斯麦式的国家形态……就在国家未能坚守信义的当口,唯有日本文坛却成为现代社会伦理意义最好的守护者。”⑧ 其次,“日本浪曼派”基于日本文化特殊主义的立场与日本近代的差异化体验,对历史决定论和一元的现代化模式提出了强烈质疑。当尼采宣称“我代表了历史所有的名义”的时候,仿佛古往今来一切历史都只是通向现代性的被克服的阶段而已;而通过对所谓“东方的专制”的论述,黑格尔又为异质的东亚社会贴上了“无始无终的停滞”、缺乏“个体精神”和“科学兴趣”的标签⑨,将其塑造为某种“反”历史、“反”现代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过是现代精神的自我演化,而这种现代精神又为西方社会所独有,传统日本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处于历史进步的潮流之外,且终将被现代所克服。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全盘接受的正是这种看似具有普遍意义、实则渗透了西方中心意识的一元模式,在强行移植具有明显差异的霸权文化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不断与自身的历史传统划清界限,最终导致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空前混乱。有鉴于此,“日本浪曼派”才试图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体系,将近代日本置于其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之中来重新加以认识,凭借传统的文化资源以及日本近代化进程的独特经验,引入“新的历史视角”,导入“东洋的他者性”,摆脱黑格尔历史理性的束缚,重新发现日本近代的历史起源,并赋予新的定义。 再次,“日本浪曼派”的“近代超克”论尽管立足于古典文化,却并非以纯粹回归过去为目的,正如凯文·多克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日本浪曼派来说,‘向着日本的回归’是与近代相断绝的不可欠缺的一个要素,它既植根于被称作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历史性之中,又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运动。”⑩“日本浪曼派”显然清楚,回归的憧憬根本不可能实现,经历了现代化洗礼的日本人与同时代欧洲人的共同点要比跟祖先的多得多,而他们自身也同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日本浪曼派”那里,“古典”只是一层“壳”,一种“内容无意义的形式”(11),重要的是如何在“古老秩序开始崩溃,新兴秩序正在建立的关键时刻”将这些民族传统置于近代世界的语境之中加以重组,从而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意义更为广泛的“文化统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克才会将现代称作“日本浪曼派”的父亲,而将文化视为它的母体,“日本浪曼派”的“近代超克”论也因此成为了某种“俄狄浦斯式的空想”。(12) 此外,“日本浪曼派”文化批判的主要实现手段是所谓“诗性精神”,其最终目的是恢复日常世界的整体性,并在此基础之上完成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建。柄谷行人在论及“日本浪曼派”与明治时期浪漫主义派别的细微差别时,指出后者视《万叶集》中所代表的自然为日本真正的浪漫主义的本源,而前者则“与之相反,将《万叶集》的人工及颓废之美作为本源之所在”(13)。由此可见,“日本浪曼派”的立足点并不是现实事物和现实情感本身,而是某种先验的、主观的建构,某种“梦想的产物”,诗歌正是这种“人工之力”最好的载体。在《日本浪曼派》创刊号上,保田与重郎对于诗歌的作用是这样阐述的:“余尝听人这样说,诗歌自远古时代起,自有语言之日起,便为人们在虚空之中营筑精神梦幻。”(14)在这里,诗歌的“纯粹的想象力”和强烈的主观精神被“日本浪曼派”所利用,用来构建一个非现实化的、脱离了历史束缚的空间。在这当中,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各种现代生活的断片通过想象被统合在一起,使得世界的整体性得到象征性的恢复。在先验意识的统摄之下,这一文化统一体作为素材“转化为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象征,成为当下基于共同历史空间意识的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石”,它“既暗示了与古代流传下来的风俗传统之间垂直方向上的连续性,又强调了与别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水平方向上的差异”,为民族文化身份的“创造”奠定了基础。(15)正因为此,诗歌成为“日本浪曼派”主导性的文学体裁,而崇高成为其最高的美学原则。这种崇高体现在作为“反讽”的浪漫文学与“低俗”现实的激烈对抗当中(在二战将政治美学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这一对抗又被表述为“作为反讽的日本”与美英之间的最终决战),呈现出鲜明的悲剧性色彩,并最终按照“死的美学”的原则,以死亡来实现自身的终极形态和对整体性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囿于现实而与“诗的精神”相违背的自然主义写作手法则成为“日本浪曼派”的主要攻击对象。 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卡林内斯库对“美学现代性”和“当代精神”这对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美学现代性”拒绝承认“现实”的合法性,反对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理念,崇尚“人工之力”,将诗人视为“来自未来的先知”,而诗歌是最为“前卫”的艺术形式,美学现代性试图在“想象力”当中建立现代美学的基础,体现了一种对于以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及其所代表的陈腐平庸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全面否定;尽管同样以文学艺术作为关注对象,“当代精神”则“指向另一种现代性,一种理性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包含人类一切合理的、与理性相关的文化遗产”,又将它们作为“不受时间制约”的存在物,按照合理性原则建立等级秩序。通过这种方式,“当代精神”“将反社会的社会化,将反文化的文化化,将具有颠覆性的合法化”,并使自身成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16)根据这一划分,“日本浪曼派”的理论主张显然同时具有“美学现代性”和“当代精神”的特征。它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抗、对于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抨击、对于诗歌“人工之力”和“想象力美学”的强调、对于崇高怪诞(grotesque)等艺术风格的推崇,无疑和“美学现代性”的诉求相一致;但它重新“发现”古典,将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各种文化断片联系在一起以建立起单一、恒定、排他性的文化统一体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最终目标却与“当代精神”不谋而合。换句话说,“近代超克”论所树立的“近代”与“文化”两极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保田与重郎等人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出发,最后却以一种为自身所否定的方式再次确认了现代性的普遍意义,为其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在二战当中,“近代超克”论才会被现代国家机器所利用,沦为替侵略扩张政策张目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其手段与目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为包括竹内好在内的后来者提供了重新阐释的空间。 二、《满洲浪曼》杂志的缘起 那么,“满洲浪曼派”又是怎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与“日本浪曼派”之间有何联系,他们在哪些方面继承和改造了后者的思想观点,伪“满洲国”独特的自然景物与社会现实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审美意识及文学实践?为了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有必要先将目光投向《满洲浪曼》杂志创刊的那一刻。 1938年初,当时就职于“满洲映画协会”的原“日本浪曼派”成员北村谦次郎与同事矢原礼三郎二人萌生了创办一本全新的文化综合杂志的念头。他们找到在“国务院弘报处”担任《宣抚月刊》编辑的木崎龙,又在木崎的推荐下向“满日文化协会”常务干事杉村勇造寻求帮助。(17)在“满日文化协会”的资助下,《满洲浪曼》杂志于1938年10月正式创刊,同人包括属于“日本浪曼派”的北村谦次郎、枰井与、横田文子,还涵盖木崎龙、今井一郎、长谷川濬、逸见犹吉、大内隆雄、荒牧芳郎等一大批在伪“满洲国”各大文化机关任职的日本知识分子。杂志第一辑共分小说、诗、随笔、评论四个部分,刊载作品除了同人创作之外,还包括“作文派”同人(吉野治夫、坂井艳司)、“新京文艺集团”同人(今村荣治、下岛甚三)以及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牛岛春子等人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百花缭乱”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满洲浪曼》创刊伊始,就开始刊登由大内隆雄译成日文的中国东北作家的作品,例如田兵的《阿廖沙》、古丁的《昼夜》、袁犀的《邻三人》、疑迟的《梨花落》等等。按照冈田英树的说法,《满洲浪曼》是“在日本语杂志中有意识地收录中国作家作品的最初的实践者,意义显得尤为重要”(18)。第二辑于1939年3月出版,由长谷川濬担当编辑,还新开设了名为“同人语”的新栏目。同年7月出版的第三辑坚持了杂志原有的体例和季刊的发行模式,同时增加了“文化机关当事者聆讯”特辑,对具有左翼倾向的“作文派”核心成员青木实以及吉野治夫等人进行了专访。这一辑中,另一位“日本浪曼派”成员绿川贡也加入了《满洲浪曼》的创作队伍。第四辑于1939年12月付梓,杂志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的“满洲浪曼”几个大字和对应刊号均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满洲作家撰集”的大标题和“满洲浪曼特辑”的副标题,而原有的诗歌、评论等类别也被一并取消,只保留吉野治夫、长谷川濬等人的小说创作,就此,《满洲浪漫》完成了从季刊向选集的转变,而第四辑也成为伪“满洲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日语小说选。此外,北尾阳三、大泷重直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此时加入了《满洲浪曼》的同人队伍。出版于1940年5月的《满洲浪曼》第五辑保持了第四辑的体例,以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为主要内容,成为一份文学理论专辑。杂志第六辑出版于1940年10月,与第四辑相同,同样以收录短篇小说为主。从这辑开始,杂志的发行机构从殖民官方指定的“文祥堂”变成了私人经营的“新京兴亚文化出版社”,编辑事务所也搬离了之前所在的“满日文化协会”。北村谦次郎将这一变化称作“满洲浪曼的重新起航”,而作为这一重新起航重要组成部分的还有加盟的“日本浪曼派”另一员大将檀一雄。1941年5月出版的《满洲浪曼》第七辑正是以檀一雄的作品《僻土残歌》为题。这一辑作品数量较于之前各期大幅减少,杂志名称也改为“满洲浪曼丛书”,显现出鲜明的文集的特征。在伪“满洲国”殖民宣传机构的打压之下,随着1941年3月“艺文指导要纲”的颁布和同年7月文化统制机构“满洲文艺家协会”的成立,《满洲浪曼》杂志也“突然无疾而终”。(19) 三、“满洲浪曼派”的核心观点与“大陆性”的提出 “满洲浪曼派”的理论观点除了散见于《满洲日日新闻》、《作文》、《北窗》等日本报刊之外,主要收录在《满洲浪曼》杂志尤其是第五辑“理论研究专辑”中。通过对其主要成员,包括被西原和海称作“最能代表《满洲浪曼》杂志风貌的作家”长谷川濬以及身为“满洲浪曼派”灵魂人物的北村谦次郎的相关论述进行深入分析和整体把握,可以归纳出为“满洲浪曼派”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主张。 首先,长谷川濬等人对伪“满洲国”的建立寄予厚望,并极力推崇作为殖民统治合法性基石的所谓“建国精神”中所包含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内容,认为它们以一种具有“独特形态的新的生活样式”打破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藩篱,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体系所依循的功利主义、强权政治的法则,并由此开启了亚洲乃至全人类历史的新的篇章。换句话说,伪“满洲国”及其多元平等的意识形态幻象在他们看来正代表了跨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使他们基于“世界主义的氛围预见了整个人类的危机与动向”,发现了克服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历史契机。自认为“文明的开创者”的他们渴望参与其中,用相伴而生的“莫大的喜悦”去改造无病呻吟的“小市民的劣根性”,去医治“现代人精神的贫困”。(20) 以此为根本出发点,“满洲浪曼派”同人试图通过所谓的“满洲文学”来赋予“建国精神”以特殊的社会历史内涵,并为其找到现实的立足点,使文学创作成为“孕育这种新精神的母胎”。正因为此,他们一方面以创造“雄壮”、“伟大”的“浪漫主义的满洲神话”为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则提出采用一种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来展现中国东北的自然与社会现实,探索其内在本质,从而在此基础之上提炼出与“建国精神”相对应、并使其获得现实象征和具体表述的某种精神内核。可以说,对于“满洲浪曼派”而言,其创作手段是现实主义的,创作目的是诗性和浪漫的,而整个创作过程则是“探求”与“观照”这二者的有机结合。就像北村谦次郎所指出的那样,作家应当以“观察人类的生活方式”为己任,并通过“将生活[的碎片]统一在一起、对其进行观照来产生美的意识”;与此同时,这一“观照”则必须基于对生活的描绘、对现实的表现,并以“为人生”为导向,力求“给生活带来指导意义”(详见「探」:63-64)。 基于这样的认识,“满洲浪曼派”并不排斥客观现实和现实主义,相反,他们对殖民政治的干预以及完全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抱有深刻的警惕,号召作家“回归文坛之外的现实土壤来发掘丰富的个性化的因素”,以客观观察和个性自由来捍卫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因此,“满洲浪曼派”虽然强烈认同“建国精神”的理想主义伪装,却反对将殖民政治凌驾于艺术之上,令后者成为前者的附庸:“[满洲]文学绝不会出于国策考虑而把协和挂在嘴边,也不会为了迎合建国精神而冠以建国文学之名。占据其中心位置的除了我等作为艺术家的灵魂以及对纯化的美的意识的渴求之外别无他物。”(「探」:65)正是在所谓“现实”的基础之上,“满洲浪曼派”不满于空洞的政治宣传口号,从伪“满洲国”“建国精神”出发走上了偏离乃至“质疑”殖民官方意识形态的道路。 在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中国东北的过程中,“满洲浪曼派”认识到伪“满洲国”最为显著的社会现实是处于殖民压迫之下的广大东北人民的赫然存在。正如长谷川濬在分析什么是“满洲文学”“独一无二的形态时”所指出的那样,“依照满洲国的民族构成,占总人口大多数的日满两大民族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领域内,如果没有这二者的协力与合作,满洲文学是无法得以成立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日系文学和满系文学这两个词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满洲文学的独一无二的形态……在这样两大民族紧密结合的精神整体之中,我发现了满洲国的伟大的梦”(21)。长谷川濬之所以肯定身为被殖民者的中国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无可争议的权利,突出他们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他者的融合,以此作为达成“文明重建”的根本途径。因此北村谦次郎把“表明成为一名大陆人的决心,获得完成这项事业所需的热情”视为“满洲浪曼派”的核心使命,将其称作“作为理念的满洲浪漫”,并以之对殖民统治“存在的合理化倾向进行反拨”,含蓄地表达改变不合理的殖民秩序的主观愿望(详见「探」:72)。 “满洲浪曼派”这一跨民族、跨文化的设想,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体现为“对于满人、尤其是满人作家的关注”(「建」:3)。对“满洲浪曼派”来说,这不但出于“环境经验的必然性”,更是“触及满洲文学本质形态的良心的举动”;而古丁等中国作家“对于满人社会的考察”、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描绘,在他们看来,更为身处伪“满洲国”的日本作家提供了“几多的暗示和参考”。同样,朝鲜族、蒙古族作家也被纳入这个“各族联欢的特别的文学聚会”(详见「建」:3-4)。正是在对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的所谓多元文化的憧憬之中,长谷川濬等人想象着由日本《万叶集》、古希腊所代表的古典精神即“伟大艺术精神”在现代的重现。 要想真正与他者相融合,就必须对他者的特性做出深入的了解,在伪“满洲国”特殊的政治历史语境之下,这意味着“满洲浪曼派”需要对殖民地以及被殖民的大多数民众进行某种总体性的把握。与当时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基于“马贼、暗娼、红土、驴马之类的意象”(22)将中国东北与野蛮、落后画上等号或是用“好面子”、“没办法”来贬低深受殖民压迫的中国民众不同,“满洲浪曼派”从自身的利益和目的出发,对中国东北的风土人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颂。在长谷川濬那里,东北大地上那“寥落的群星”、“幽深的密林”、“壮阔的高山大河”以及“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枕山抱河的蒙古草原、三河的哥萨克村落、俄罗斯人的农庄和不知名部落的望楼”无不蕴含着“蠢动的纯粹之魂”,体现了“自然之美的伟大调和”,带给人们“无限的精神食粮”(详见「建」:4-5)。而北村谦次郎则在详细比较所谓大陆美学和日本美学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了“大陆性”这一核心特征,并进而指出了“接近和融入大陆性的历史必要”。按照他的阐释,日本美学发端于日本“明朗、润达”的自然环境,崇尚枯寂、余韵、物哀、幽玄之类的艺术观念,而大陆美学则以“一月的严寒与三月的黄尘”为象征,以“无穷无尽、徒劳往复的历史”为依托,体现为中国东北作家笔下那“永恒的暗色”。当日本美学这种“轻巧、精致”、“感伤”、“以纤细为主”的性格在“大陆的地平线上”遭遇到它那“钝重、暗郁的表情”时,便“不由得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正因为此,北村断言日本美学缺乏“近代文学的社会性、人间性”,无法“构成真正的反抗精神”,同“浪漫主义的本质内容相差甚远”,是“浪漫的邪道”,因此必须从美的意识当中排除出去。反过来,在所谓“大陆性”“悲剧精神”的感召下,日本作家不但要接受中国作家作品中的暗色,更需要放弃原有的文化身份,向他们学习,通过对大陆的自然历史、社会风俗进行文学表现,将外在的风物内化为强烈的“归属”意识,并在此过程中最终“获得大陆性”,“完成[满洲]浪漫的建构”。这一过程被北村形象化地表述为“死的预想”,而日本作家只有像“求死”那样否定自身,将自身作为“一种徒劳”、一种“垫脚石一般的存在物”,才能使个性精神得以融入历史的长河,通过“洗练感性、革新灵魂”,“在[历史的]永恒之名中获得再生的机缘”(详见「探」:74-76)。 在创作实践的层面上,“大陆性”又被“满洲浪曼派”同人具象化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人间性”、“社会性”、“包容性”与“强韧性”。(23)所谓“人间性”和“社会性”是对文学创作回归社会现实的强调。北村谦次郎将现实与美的交融称作“壮大的浪漫”,并以之作为“满洲浪曼派”最高的美学原则。在他看来,“壮大的浪漫”虽被冠以浪漫的名号,却“绝非与写实文学或实体的美背道而驰,相反,正是在写实文学的基础之上,它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24)同样,木崎龙也借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提出“文学必须在日常事物中得到表现”,“现实主义乃是一切文学作品存在的前提”,并着重强调所谓“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生活的斗争意识”。(25) 所谓“包容性”是指对不同风格、题材、世界观影响下的文学作品的兼收并蓄。《满洲浪曼》杂志固然收有不少像长谷川濬的《乌尔顺河》、横田文子的《鸟》之类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作品,更刊登了竹内正一、牛岛春子等左翼作家揭示伪“满洲国”尖锐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创作,而倡导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文坛名宿大内隆雄的加盟,更加凸显了这一特征。这种“包容性”还集中体现在对于中国东北作家作品的接受与重视上。《满洲浪曼》每期都有中国作家的作品发表,并且越到后来所占比重越大(26),涉及作家不但有与“满洲浪曼派”联系紧密的《艺文志》同人,还包括石军、田兵等乡土文学作家,甚至连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袁犀以及日后因“反满抗日”而惨死狱中的王则也被囊括在内。《满洲浪曼》所收录的东北作家的小说作品多以殖民统治下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为主题,隐晦地表达了他们的民族反抗意识,总体基调阴郁、凝重,构成了北村谦次郎所谓大陆的“永久暗色”的文学缩影。正因为此,西田胜才会把这些“满人”作品视为“中国普罗文学的一种展开”,强调《满洲浪曼》杂志由于有了这些作品,带给人们“异乎寻常的沉重感”。(27) 所谓“强韧性”则反映在对于东北壮烈严酷的自然景物以及东北民众受这一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的表现上。例如丘益太郎就借“北满的荒野、呼伦贝尔草原、东疆的密林和热河的山岳地形”引发出对东北人民的“炽烈情感”和“反抗精神”的赞颂。(28)而大内隆雄则用“北方的特质”来代替“大陆性”,强调其所包含的不仅是“广袤雄大的自然的影响”,更是“人类的重压”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深受殖民压迫的劳动者“豪壮且极富韧性的性格”。日本作家不但应该“立足于这块土地所特有的奇谲的自然环境”,更应该“在作品中尽可能多地对劳动者进行描写”,表现“半封建社会带给人们的沉重压迫”。(29)这种对于自然和乡土社会的关注演变成一首首自然之歌和庶民之歌,成为“满洲浪曼派”最为重要的文学表现主题。 但是,绝对不可否认的是,“满洲浪曼派”出于自身需要而宣扬的“大陆性”只存在于他们的碎片化想象之中,绝非对日本占领下中国东北真实现状的真实反映,而且这一“大陆性”既回避了日本殖民统治的血腥残酷,又将所谓“满洲”在地理和历史文化上同中国割裂开来,透露出内里仍是浓重的日本殖民意识形态。在通过战争强行占领中国领土的基础上谈所谓日“满”文学的融合,这种文学创作精神尽管推崇对东北风土人情的赞颂,但以此希望培养出的所谓“归属”意识本质上仍是殖民者的“不义”。 四、从“日本浪曼派”到“满洲浪曼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保田与重郎便开始了他的首次中国大陆之旅。在作为这次旅行随感录的《蒙疆》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首先,我国应当在世界范围内率先与19世纪的一切意识形态相诀别。问题在于,尚未完成19世纪现代化事业的日本文化还要通过亚洲实现更大规模的转向……这一点从我等的民族理念得以表现的那一刻起便为人所知,并被付诸行动……正是“蒙疆”象征了日本此次转向的萌芽。我对北京失望透顶,只有到了蒙疆才重新萌发了这样的念头。(30) 两年后,保田与重郎又在《我思》12月号上发表了名为《关于“致满洲皇帝旗之歌”》的评论,更为直接露骨地将满洲国的建立与他的“近代超克”论联系在一起: 满洲事变以其世界观的纯洁性震撼了我们这个时代一大批青年的内心……事实怎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满洲国明白无误地是在前进。也就是说,满洲国至今仍是法兰西共和国、苏维埃联邦之后第一个出现的另一种全新而大胆的文明理想以及某种新的世界观的表现。在将“满洲国”当作新思想以及革命性的世界观来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日本浪曼派的萌芽状态也从而得以表现。(31) 在这里,正是保田与重郎自己率先提出了面向亚洲大陆的转向:在他看来,伪“满洲国”的建立无疑代表了其心目中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对日本社会乃至全人类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让“日本浪曼派”本身从中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契机;不仅如此,在思想史的层面上,通过将伪“满洲国”作为“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更为纯粹的存在物来加以理解,保田发现了“近代超克”论自我扬弃、改弦更张的可能性。借用广松涉的话来说,就是“保田与重郎一下子从新生的‘满洲国’,从它所标榜的‘五族协和’和‘王道乐土’的建国理念中找到了新的‘文明理想’和‘世界观’以及对于西欧近代理念的一举超克”(32)。正因为此,保田才将目光转向包括“满蒙支在内的亚洲大陆”,期待着在这片土地上构建出一种有别于现代物质文明、充满主观浪漫精神并使主客体关系得以象征性修复的全新文化范式。 在这份期待之中,《满洲浪曼》杂志的出版和“满洲浪曼派”的崛起可以说正是“日本浪曼派”按照自身逻辑发展所形成的必然产物。(33)除了刊物名称(34)、组成人员上的重合之外,北村谦次郎本人也对“满洲浪曼派”与“日本浪曼派”之间的承继关系毫不讳言: 龟井胜一郎曾经将日本浪曼派的决心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诗性精神的昂扬和对当代低俗的现实主义的反抗,二是血统的树立,三是对现代文化人伪装的告发与弹劾。满洲浪曼所包含的精神,并非在派别的意义上继承了日本浪曼派;可以说,既是它[日本浪曼派思想]的泛滥又是它的实践,但我们首先应当从沉默的美德中出发。(「探」:72-73) 对于这段话中“泛滥”一词的含义,日本学者众说纷纭。西原和海认为将“继承”与“泛滥”并置属于“日本浪曼派”惯用的“反讽”修辞手法,含蓄地表达了北村反对“军部及政府从东北挺进华北”,希望“日本的扩张止步于满洲国境内”以免危及殖民统治稳定的想法。西田胜则提出“且不管语言方面使用了怎样的修辞手法,都可以解释为激进地接受‘日本浪曼派’的影响、对其展开实践的意思”(35)。笔者认为,日语中“泛滥”一词除了指水过多而溢出之外,还有不受欢迎的事物大行其道的意思,在引申层面上具有明显的贬义;北村在定义什么是“满洲浪曼”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词,显然其臧否的目标不是自身,而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将矛头指向了作为比较对象的“日本浪曼派”。联系下文这一点表露得更为明显。在提出“沉默的美德”之后,北村又写道:“即使喋喋不休,又能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不露声色地探求永恒的价值,并开始接近并溶解于大陆性这项极其困难的事业。”(「探」:73)通过将“泛滥”、“喋喋不休”与“实践”、“沉默的美德”进行对比,北村的这段文字暗含对“日本浪曼派”“虚妄的美”以及“强行的人工之力”(36)的批判,同时又标示出自身的独立性格。一方面要表明渊源,另一方面要凸显差异,或许只有“泛滥”一词才能如此形象而又微妙地展现出二者之间的暧昧关系。 与“日本浪曼派”相同,“满洲浪曼派”也将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文化表征作为自身的根本出发点。这一点在身为“满洲浪曼派”核心成员木崎龙的论述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体现。木崎用从近代早期直到帝国主义阶段始终“弥漫着的世纪末的烦恼”来指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混沌”、“近代资本主义最丑陋的结果”、“革新路上必须摒弃的障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并强调“目不暇接地变换着色彩”的现代生活对现代人思想意识的侵蚀:各种现代精神病症的文化表征被木崎归结为“达达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新古典主义等等主义的泛滥”,被他斥作“琐碎无聊的派生物”。(37)在批判现代社会及其文化思想产物的基础之上,木崎龙与保田与重郎不谋而合地把“超克”的希望寄托在伪“满洲国”“实现王道乐土”以及“达成民族协和这一宏大理想”的过程中,并将文学实践视为完成这一“超克”最为重要的手段,宣称“唯有满洲文学有巍然耸立于近代混迷之外的可能”(详见「建設」:39)。不只是木崎龙,北村谦次郎也号召“满洲浪曼派”同人“以文学浪漫精神所蕴含的烈烈气概,向现时的流俗提出挑战,以对诗的拥护来抗击似是而非的文化”(38)。而檀一雄更是激情洋溢地宣告道:“过去的诗人和文士大概早已配不上艺文之士的名号。将这类人排除在外,明日的诗人们难道不应当成为‘文明重建的伟战士’吗?”(39)和保田等人一样,无论是木崎龙、北村谦次郎还是檀一雄,这些满洲浪曼派都将伪“满洲国”的建立视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场文明实验,都受惑于所谓“建国精神”中“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意识形态幻象,他们所提出的通过文学的“浪漫精神”来改造现代文明的论调和日本浪曼派宣扬“不受束缚的高蹈的精神”、反对“平庸低俗的文学”的立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其强调“雄大”、“壮阔”之美,并以消解自身文化身份的象征性死亡来实现融入他者的“浪漫的梦”的方式,也和“日本浪曼派”所谓“死的美学”原则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满洲浪曼派”并非西田胜所言的“日本浪曼派的满洲版”,可以说从“日本浪曼派”出发,“满洲浪曼派”最终踏上了一条否定和超越前者的道路。导致这场巨大转变的正是中国东北这一异质他者的客观存在。在保田与重郎对于新的文明模式的畅想当中,伪“满洲国”只是作为某种特定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关注,事实本身无足轻重;同时,它的存在价值完全由日本所决定,占据问题核心的仍然是日本自身的革新与转向,“满洲”或所谓“大陆”只不过是日本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手段”和建构出来的想象物罢了。这也是保田声称“事实本身如何我并不知道”,但“现在满洲国的理想与现实”构成了“一种从世界范围入手改革日本现有状况的思考方式”(40),并人为地将“亚洲大陆”与日本民族理念的表现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大陆”不但由此被边缘化和符号化了,还被保田置入这样一个文明的等级序列中:“更严格一点说,大陆与地形和风土无关(并非某个地理学的现象),大陆是皇军的大陆,是一种庄严的存在,并因此而成为浪漫主义的象征。它是通向新的未来的理想主义的混沌的母胎。换而言之,作为文学母胎的大陆是这一混沌的表面。”(41)通过这样的表述,保田将“大陆”与其自然、民族及社会现实剥离开来,不仅令其沦为一个依附于日本浪漫主义象征体系的空洞概念,而且将它的归属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变成“皇军”的大陆。它被定义为某种原始而混沌的存在物,有待于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皇军”的拓殖,从而摆脱蒙昧状态,真正进入历史的视野,获得走向未来的可能。这种“亚洲/日本=野蛮/文明”的二元对立模式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主导着近代日本与其东亚邻国的关系,在这里也成为以“超克”日本近代为目标的“日本浪曼派”的中国认知论的基础,使这一流派自欺欺人、毫不愧疚地为日本的殖民行径摇旗呐喊、涂抹粉饰。 在“满洲浪曼派”那里,首先占据他们思想中心的不再是日本的发展问题,而是如何“建筑与满洲浑然一体的独特文化”以及探寻“绝非日本文学派生物”的“别样且独特的满洲文学风格和内容”(「探」:78);“与日本传统相关的一切”被视为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侵略”(42),“毫无保留的必要”(43)。不仅如此,“满洲浪曼派”更直接把日本当作资本主义的罪恶渊薮,是应被批判和“超克”的对象。就像西村真一郎所总结的那样:“虽然日本从未隶属于美国,然而由她的文化设施及作为文化产出的流行趋势来看,她所展现的所谓银座风俗恰恰是一种文化殖民地观的体现。”(44)这样的“殖民文化观”反映在文学领域内,就成了木崎龙所说的“川端康成用‘末期的眼’投出犀利一瞥,横光利一的‘纯粹性’闪烁着妖冶的光芒,结果却都迷失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中……沉溺于自我主义只能使对普遍人性的思考在杂音中消退,空留下无足轻重的枝节,对于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确定立足点的他们来说……首先应该怪咎的不是文学评论的贫困或是创作的贫困,而是‘生活’的贫困”(「建設」:41)。日本现代文学“无内容、无气力”的现实,在“满洲浪曼派”看来,只能是像“解剖猿猴一样为人类医学提供示范意义”,而对“满洲文学”而言,“大量吸取日本文学、特别是明治以后文学发展的教训,不假慈悲地将其剔除出去,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批判摄取,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建設」:38)。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及其相关理念同样被“满洲浪曼派”视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病征而遭到批判,而这正构成了他们与“日本浪曼派”之间最为根本的分歧。“日本浪曼派”鼓吹重建“日本的民族性”以克服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危机,保田与重郎在提出“亚洲转向”时,依旧恪守着所谓“民族的理念”和日本中心主义;与这种立场不同,“满洲浪曼派”从一开始便意识到了借由近代民族国家这一模式去超越近代所蕴含着的悖论和风险,进而否定了作为构成现代性意识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45)之重要一环的民族认同。他们理想中的伪“满洲国”及“满洲文化”并非由单一的语言、历史传统及族裔特性所统摄,而是跨民族、跨文化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北村谦次郎才会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将由本居宣长所揭橥、保田与重郎所极力倡导、被视为所谓日本民族精神“神圣图像”(holy icons)(46)的《万叶集》、《源氏物语》及其物哀、幽玄的审美原则定性为“浪漫的邪道”,强调只有将其“感性的一面排除出去”,彻底“融入大陆性”,才能“获得浪漫发展的新的契机”。与此相对应,“满洲”或大陆则不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停滞”和“混沌的母胎”,而化身为能动的历史主体,在克服作为落后历史阶段象征的近代日本的过程中,代表着未来更高的文明理想,成为檀一雄笔下所谓“明日大东亚的预约”。(47) 在这一由“死”到“生”的转变中,“近代的超克”论也通过否定自我、融入他者,实现了对于自身的“超克”。从思想史角度来看,自福泽谕吉开始,日本就已经将西方文明论中“西方/东方=文明/反文明”的差异化结构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先验预设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过来,并套用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在使日本通过近代化“脱亚入欧”的同时,把中国塑造成与文明的日本相对的作为“停滞的亚洲”代表的“否定性他者”。即使在冈仓天心那样的亚洲主义者那里,对于中日拥有“共同的思想遗产”的零星表述也很快被中国文明由于外族入侵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艺术传统、“继承亚洲丰富历史并对其进行一贯深入研究的只有日本”、“成就映现全亚洲意识之镜”乃是“日本伟大的特权”之类的论调所掩盖了。(48)以“近代的超克”为目标的“日本浪曼派”在否定现代社会及其价值体系之余,却仍然吊诡地继承了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亚洲认识图式,这使得他们一方面由于缺乏“超克”的现实立足点而不得不诉诸日本“古典”文化(同样是一种现代观念的产物)和所谓“诗的精神”,将“超克”论建立在“自我想象”的基础之上,造成了“拔着头发逃出地球”的逻辑困境;另一方面又使得处于所谓“混沌”状态的亚洲大陆在“日本浪曼派”后期的理论当中沦为日本实现“超克”所随意榨取的资源和必须牺牲的对象。在保田与重郎“今日初次体验浪漫世纪的日本,一扫悲观的情绪而获得飞跃。就算以征服和侵略为手段,那也是正当而充满美感的”欢呼声中,“近代超克”论赤裸裸地蜕化成了为日本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与之相对,表面看来,“满洲浪曼派”立足于中国东北,通过确立大陆之于日本的文明优势,改写了上述的西方/日本中心主义认识模式,肯定了亚洲/大陆的主体身份,并凭借消解自身、融入他者的论调使“近代超克”论获得了所谓“现实”的实现途径。正是基于这一想象的“现实”,北村谦次郎才会不指名地对“日本浪曼派”否定现实、排斥现实主义文学的立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强调“我们要脚踏实地而不是天马行空地来解释浪漫精神”。(49)出于同样的原因,“能够展现对于现实本质认识”的小说而非诗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受“满洲浪曼派”钟爱的文学体裁。 而“大陆性”所揭示的“中国转向”以及“反抗的精神”等基本原则在竹内好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正是从相似的大陆经验出发,竹内明确提出了“以中国作为方法”、以“中国抵抗的主体性”作为“近代超克”基盘的主张。在此意义上,“满洲浪曼派”开启了竹内好思想的先河,而在历史现实当中,考虑到关内关外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身处北京的竹内好是否受到事实上的影响亦未可知。 五、与殖民主义的暧昧关系 在《日本的殖民主义的“起源”》一文中,柄谷行人以“接近的相似性”来定义日本殖民主义的基本特征:日本殖民者通过突出与被殖民者在种族及文化上的相似性来强调面对西方时二者利益攸关、唇齿相依的关系,从而将被殖民者描绘成殖民事业的自愿参与者,为自身的殖民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50)在这个意义上,以“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为口号的伪“满洲国”建国精神无疑是这种伪装的殖民宣传策略的集中体现。它有意回避了伪“满洲国”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客观现实,虚假地宣扬东亚各民族间的所谓“亲善”与“协作”,并基于所谓“东洋的理想”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否定,将这个傀儡国家(实为殖民地)的建立标榜为一场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政治实验。这一极具欺骗性的论调为“满洲浪曼派”所接受,使他们将“建国精神”作为“近代的超克”的思想表述而加以大力渲染和维护,客观上起到了为伪“满洲国”洗白、为殖民统治张目的作用。 包括“总务厅弘报处”在内的殖民文化机关显然注意到了“满洲浪曼派”对“满洲国”建国精神的接受,因此试图利用《满洲浪曼》杂志来推动殖民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对其最初发展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满洲浪曼》的创刊便获得了由关东军总参谋长小矶国昭、副总参谋长冈村宁次等人担任会长的“满日文化协会”在资金和印务方面的支持。杂志在殖民专制造成的文化废墟中倡导所谓“满洲文艺复兴”,刊登各种体裁、各类作家尤其是中国东北作家的作品,迎合了殖民当局鼓吹“日满亲善”、竭力粉饰太平的需要。(5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川村凑才会将《满洲浪曼》杂志视为伪“满洲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52)。 虽然“满洲浪曼派”的理想主义以及以文明开创者自居的身份意识使其与日本殖民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与之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53),而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伪“满洲国”殖民当局对于文化领域的越发严酷的控制也在“满洲浪曼派”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54),但是,就职于伪“满洲国”各大官方机构、身为殖民既得利益者的《满洲浪曼》同人从未真正反思和否定过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更从未认识到东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对他国主权的公然践踏。中国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在他们笔下始终是失语的,相反,他们将中国东北幻想为一片“全新的天地”,将自己视作扎根这一“新世界”的合法移民,就像受法国大革命影响而流亡北美的法国作家一样,将在这里开创新的历史、新的文明。(55)这种罔顾客观事实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决定了“满洲浪曼派”无法真正了解被殖民者的现实需要,也无法转到真正反抗殖民统治的立场上去。 “满洲浪曼派”既未能触及殖民统治的黑暗现实,又不敢直面东北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真相,其所宣扬的“大陆性”和“反抗的精神”只不过是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之上,显得空洞而虚妄;因此,虽然有着“超克”的愿望,但作为殖民宣传机器特定组成部分的“满洲浪曼派”只能在殖民体系内部寻求现实和话语资源,被其视作指导思想的“建国精神”更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不折不扣的产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满洲浪曼派”对殖民体制的反拨却不得不以伪“满洲国”的存在为前提,在质疑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却使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这一与“日本浪曼派”相类似的理论困境将由竹内好在战后通过对侵略战争的整体性反思加以重新审视和阐发。 ①保田与重郎,日本战前战后时期的右派文艺评论家,日本浪曼派的创始人。 ②子安宣邦「近代の超克は何か」,载『中央公論』2008年第8期,第262頁。 ③详见子安宣邦「近代の超克は何か」,第261頁。 ④See Harry Harootunian,Overcome by Modernity:History,Culture,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91. ⑤详见子安宣邦《日本的近代与近代化论》,收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⑥保田与重郎「日本浪曼派の時代」,收入『保田与重郎全集』第36卷,東京:講談社,1988年,第42頁。 ⑦“日本浪曼派”同人还于1935年3月创办了社团机关刊物《日本浪曼派》,杂志共29期,至1938年8月终刊。 ⑧保田与重郎「ボ一ルドウイイン首相」,收入『保田与重郎全集』第2卷,東京:講談社,1985年,第543-544頁。 ⑨See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troduction,Reason in History,trans.John Sibree,Whitefish:Nabu Press,2010,p.111. ⑩Kevin Doak,Dreams of Difference:The Japan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41. (11)保田与重郎「コギト編集後記」,收入『保田与重郎全集』第40卷,東京:講談社,1989年,第159頁。 (12)See Kevin Doak,Dreams of Difference:The Japan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p.21. (13)柄谷行人『近代日本の批評(昭和篇上)』,岡山:福武書店,1997年,第168-169頁。 (14)保田与重郎「創刊之辞」,载『日本浪曼派』1935年3月第1期,第92頁。 (15)See Kevin Doak,Dreams of Difference:The Japan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p.42. (16)See 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Modernism,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Postmoder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p.91-92. (17)详见北村謙次郎『北辺慕情記』,東京:大学書房,1960年,第66-67頁。 (18)西原和海、岡田英樹、西田勝「満洲浪漫をどう評価するか」,载『殖民地文化研究』2002年第1辑,第9頁。 (19)详见葉山英之『「満洲文学論」断章』,東京:三交社,2011年,第307頁。 (20)详见北村謙次郎「探求と観照」,载『満洲浪曼』1940年第5辑,第65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1)長谷川濬「建国文学私論」,载『満洲浪曼』1940年第5辑,第1-2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本社会习惯于将生活在东北沦陷区的中国人统称为满人,所指非特指满族,而是对东北各族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的特殊称呼。这是日本有意识地将东北沦陷区民众与关内中国民众进行区分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培养当地人所谓的“满洲乡土意识”,弱化他们面向中国的民族认同,其麻醉作用绝不可忽视。 (22)大谷健夫「土地と文学」,收入『満洲文芸年鑑』第1辑,福岡:華書房,1993年,第19頁。 (23)详见逸見猶吉「言葉を借りて」,载『満洲浪曼』1938年第2辑,第175頁。 (24)详见北村謙次郎「時評の詩と真実」,载『満洲浪曼』1938年第2辑,第169頁。 (25)详见木崎龍「文学の表情」,载『満洲浪曼』1938年第2辑,第151頁。 (26)所有汉语作品均由当时唯一能堪当此任的大内隆雄翻译成日文,这或许也是北村等人极力邀请大内隆雄作为同人加入“满洲浪曼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27)详见西原和海、岡田英樹、西田勝「満洲浪漫をどう評価するか」,第9頁。 (28)丘益太郎「自然描写に餓之る」,载『满洲浪曼』1940年第5辑,第114頁。 (29)详见大内隆雄「満洲文学の特質」,载『満洲浪曼』1940年第5辑,第58頁。 (30)保田与重郎『蒙彊』,東京:生活社,1938年,第9頁。 (31)保田与重郎「满州国皇帝旗捧げる曲」,载『コギト』1940年第12期,第37-38頁。 (32)広松涉『「近代の超克」論』,東京:講談社,1989年,第11頁。 (33)《满洲浪曼》的创刊与《日本浪曼派》的终刊在时间上仅相隔了两个月。 (34)同《日本浪曼派》一样,《满洲浪曼》杂志同样用的是“曼”而非约定俗成的“漫”字,以与日本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思潮划清界限。 (35)西原和海、岡田英樹、西田勝「満洲浪漫をどう評価するか」,第5頁。 (36)北村謙次郎「時評の詩と真実」,第169頁。 (37)详见木崎龍「建設の文学」,收入『満洲文芸年鑑』第2辑,福岡:葦書房,1993年,第38-39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建設」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8)北村謙次郎「跋にかへて」,载『満洲浪曼』1940年第6辑,第250頁。 (39)檀一雄「文芸奉還説」,载『満洲浪曼』1940年第6辑,第191頁。 (40)保田与重郎「满州国皇帝旗捧げる曲」,第37頁。 (41)保田与重郎「大陸と文学」,载『新潮』1938年第11期,第65頁。 (42)西村真一郎「満洲文学の基本概念」,载『満洲浪曼』1940年第5辑,第44頁。 (43)富田寿「文学の問題について」,载『満洲浪曼』1938年第1辑,第232頁。 (44)西村真一郎「満洲文学の基本概念」,第44頁。 (45)See Charles Taylor,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2. (46)See 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71. (47)详见檀一雄「現代」,收入《新京風物帖》,長春:流動出版,1942年,第2頁。 (48)详见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收入『明治文学選集·38·岡倉天心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第8頁。 (49)详见北村謙次郎「跋にかへて」,第249頁。 (50)详见柄谷行人「日本殖民地主義の起源」,收入『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殖民地』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80年,第57頁。 (51)“满洲浪曼派”一方面否定殖民当局所提倡的日本文化之于伪“满洲国”的“指导性作用”,并将殖民宗主国的文化传统视作“超克”的对象加以排斥,另一方面则把被殖民者的民族特性奉为“浪漫精神的正道”,试图放弃自身原有的文化身份、融入殖民地社会。这样的观点主张使得在殖民官方操控的“满洲文艺协会”成立后不久,《满洲浪曼》杂志便因“过分宣扬艺术自由”而被当局勒令终刊。 (52)川村湊『文学から見る“満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第50頁。 (53)从一开始,“满洲浪曼派”对于“建国精神”的吸收就是有选择性的。在1932年3月1日出台的伪“满洲国”“建国宣言”当中,除了“王道乐土”与“民族协和”之外,还包含有“顺天安民”、“门户开放”的内容,前者带有“君权神授”的意味,后者与经济殖民有关,这两点都被“满洲浪曼派”有意识地过滤掉了(详见塚瀬進『満洲国“民族協和”の実像』,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年,第67頁)。 (54)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坚持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干预成为“满洲浪曼派”的共识,而所谓“现实批判精神”更显示出他们对殖民专制的不满,他们在小说作品中对殖民地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委婉的揭露和讽刺。与此同时,北村谦次郎也一直在寻求其他的资金和出版渠道以摆脱殖民文化机关的掌控。《满洲浪曼》第六辑改由兴亚文化出版社而非此前“满日文化协会”所指定的祥文堂出版正与北村的努力直接相关。 (55)详见丘益太郎「自然描写に餓える」,第110頁。标签:伪满洲国论文; 东北文化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长谷川论文; 万叶集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