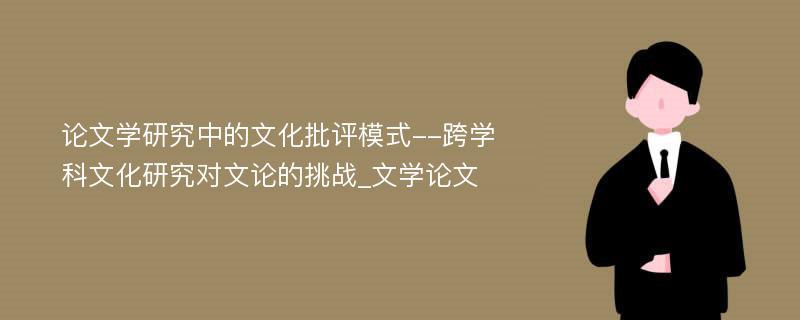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模式”笔谈【四篇】——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批评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由于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参与能力与文化批判功能的丧失,已经引起当代批判理论家的极大担忧。人文科学理性化的结果是对于特定而狭隘的学科“领土”完整的一味死守,它通过把统治性文化的批判者们加以隔离的方法帮助统治性文化的再生产。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蜕变为相互隔离的“专家”,他们在“学术自由”的旗帜(所谓“专家们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下把自己捆绑在限制他们的批判权利的学科话语藩篱中。(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 in tellectual sandoppositional 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and Gita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历史,理论,实践》(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 Newyork,1995.第647页。)学科分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之间产生严重隔阂。这些学科中的学者丧失了就其共同关心的公共性问题进行其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的能力。
本文力图要表明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根本旨趣是一种“解放的旨趣”(哈贝马斯语)。用吉罗克斯等人的话说:“在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一个社会的矛盾的知识分子缺席的情况下,统治性的文化就会更加有效地继续再生产自己的最坏的影响。而且,缺少文化批判的领域,抵抗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就没有自己的声音。”(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 in tellectual sandoppositional 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and Gita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历史,理论,实践》(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 Newyork,1995.第647-648页。)
一
上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文化研究对于西方传统人文科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这种挑战同样也是中国的人文科学者面临的真实问题。文化研究的挑战首先来自对于传统人文科学学科划分的质疑。一个没有疑义的共识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跨学科性或反学科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线。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就已经定下基调。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正如特纳(G.Turner)指出的:“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注:G.特纳(Greame Turner)语,参见C.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0页。)与传统的正规学科不同,文化研究并不拥有、也不寻求一种界线明确的知识或学科领域,它是在与不同的机构化学术话语(尤其是文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话语,以及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分析学的话语)的持续碰撞中,也是在机构化话语的边缘、交叉处开花结果。
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的知识探索领域。当然这并不否定特定的文化研究派别在特定的时期或出于特定的原因自我封闭化与僵化的可能。学术研究总是存在向典范化或正规化方向发展的动势,在今天这个学术机构化已经成为无可逃脱的历史命运的时代就尤其如此。而且任何一种知识或理论,尤其是像文化研究这样知识领域,它不可能不提出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尺度,哪怕是临时性的与可以修改的。文化研究总是在后现代式的绝对的相对主义、非本质主义(从而无法形成自己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与本质主义的僵化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在绝对主义、必然论、决定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但正如霍尔指出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在选择一种理论或立场、观点的同时,必须坚持一种理论的开放视野,“坚持这点是文化研究绝对必要的。至少,假如它仍欲保持为一项批判的与解构的计划时必须如此。我指的是,它一直是自我反思地解构自己;它一直需要在理论化地前进/回归运动上发生作用。”他还认为他“对理论(theory)本身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不断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这也意味着文化研究必须来自各方面的向外在的影响开放。(注: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思想》,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
二
在现代的大学或专业研究体制中,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分门别类的、学科化、系科化的,于是习惯性地,进入这个体制的大部分人文学者或文科学生,都把学科的划分看作是“自然的”分类范畴,仿佛这种划分是“必然”的、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把一个学科与一个“客观的对象”等同起来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首先,一组特定的客体可以是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文学中的同一个文本,比如《诗经》,既可以被文学研究者加以研究,也可以被历史学家加以研究。其次,某一学科研究的特定对象在该学科的发展历史上并不是保持不变的。虽然“文学”一词现在的指涉对象是小说、诗歌与戏剧等虚构性的文本,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现代的建构,“文学”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在历史上是变化不定的。(注:参见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英国文学的兴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特定时期在某个学科名义下被研究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自然的”对象,而是一个人为建构的场域(constructedfield),这个场域本身就是通过学科的实践建构起来的,因而带有相当程度的任意性。而且是与权力密切关联的。福科的著作已经出色地表明:作为一种社会控制与社会组织战略的规训(discipline)出现于西方古典时代的末期,并在现代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而现代的学科建制正是“规训”之一种(discipline一词在英语中兼有“规训”与“学科”的含义)。具有悖论意义的是,“规训/学科”技术的特点是它具有同时实施规范化与等级化、同一化与分殊化的能力。现代的学科建制既是一种分化(允许并制造差异)也是对于差异的控制。学科建制因此是对话语的限制。成为一个学科的一部分意味着提出特定的问题、使用特定的术语系统、研究一个限定的对象。学术机构通过各种等级化的奖励、惩罚、排除等机制而强化了这些限制。
作为一种批判语言,文化研究必须揭示学科体制背后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利益一权力机制,揭示学科体制如何生产统治性文化并将之合法化。这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它必须抵抗包含在业已确立的学科与系科中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种政治经济利益往往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隐蔽在特定的、由学术体制确立的知识一理解模式中,隐蔽在科学真理与审美价值的评估系统中(参见布迪厄的有关研究)。特定的知识—理解模式与“真理”评估系统绝不是像它自己声称的那样是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被它赋予真理与审美价值的陈述绝非仅凭自己的客观真理性或审美价值而成为主导的科学或美学话语。在它的背后有来自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强大支持。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揭示学术体制所确立的“真”或“美”的评估—筛选—奖惩系统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的大学文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所有被纳入教科书的作家或理论家都被整齐地安放在一个等级化的序列中,这个序列似乎是一个以中立公正的审美与艺术价值为标准建立的客观自然的科学评估系统。但是实际上这个序列不可能是客观自然的,而只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包括利益驱动)中建构的,因而维持这样的一个序列也就是维持自己的文化资本、社会地位乃至政治经济利益。正因为这样,对于这个序列的颠覆与重组(比如移动“大师”与非大师的位置、中心与边缘的位置)所引发的不仅是文学上的震动,而且是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震动。
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中等级化的学科秩序的建构虽然是人为的、与特定的社会语境具有历史性的关联;但是它总是力图排除自己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存在着与学科的专业化相一致的不断增强的自主化、正规化趋势。这种正规化只有借助权力才能成为可能。
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兴盛的跨学科文化研究(比如大众文化研究、族性研究、性别研究、妇女研究等),就是产生于对人文科学的学科化以及由之导致的公共性与批判性的日渐式微的强烈不满。它意识到:最重要的问题恰恰被遗忘在僵硬的学科边界划出的空地或裂隙中。文化研究要找回的正是这些被遗漏的问题。但是应当记住的是,由于在学术界内部没有坚实的替代传统学科结构的方案,结果是某些文化研究运动悖论式地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学科才能得以立足。这样,虽然这些运动开始于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但当它们获得比较成功的时候却又退出激进的批判。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学科化,必须对自己进行持续的批评性的反思。
三
在现代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可以典型地发现学科化如何导致包括教师与学生在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丧失。大学的文学教育为学生提供进入被建构为“经典作品”的文化资源库的入场券。当然,“经典”在界定方面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它能够适度综合“边缘”文本或“边缘”作家,但同时,这种灵活性并不能改变基本的等级化的学科建制格局。现代大学中都有所谓的学生“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参考书目又经常被分为“一般的”与“重要的”)。必读书目上所开列的都是一些自《诗经》或柏拉图以来的经典著作,它们代表了一种文学的规范性标准,所谓“文学能力”就是通过这个标准得以评价的。因而,文学教育中的学科规范是以一种等级化组织为基础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文本与作家被安排在这种组织中。某些此类的对象(比如收入中小学或大学语文教科书中的作品)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最好”的,因而代表了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本质。人文科学教育的这个规划(project)事实上是意识形态地建构并起作用的(比较一下9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与70年代的教科书,这一点昭然若揭),它总是生产出严重的意识形态效果,而其所划定的“经典”反过来对学生产生意识形态的规训效应(学科即规训)。通过学习那些被赋予特权的支配性经典文本,学生才可获得在特定的文化中作出特定的行为所需要的文化资本(以文凭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学生似乎增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能力(获得体面的职业,作出与主流相一致的真理陈述或审美判断,等等),但它无疑削弱了学生质疑经典的批判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研究并不仅仅以倒转特定的规范或等级秩序为目的,它并不是简单地把原先处于边缘的文本“扶正”为新的经典,而把原先的规范或经典文本打入“地狱”。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从奴隶到将军”式的报仇雪恨。一个新的等级体系的设置仅仅是重复了传统的关于文化的等级逻辑。文化研究所对抗的实际上是等级化的文化象征观念与逻辑本身。真正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应当建立在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与逻辑上,即认为文化对象事实上是历史地、相对地安排的,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文化研究要把文化作为一套具有历史具体性的行为或实践加以研究,这套行为或实践是活生生的、变化不定的,是一个过程,一个不能通过“储存室”的意象加以固定的过程。(注:参见: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第651页。)
通过阐明文化事实上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文化研究可以保证它自己的政治有效性。学生可以通过文化研究而得知被推荐给他们的所谓“必读书目”并不是天经地义地非读不可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经典的;而他们实际上热衷于阅读、却又被教科书排除在“必读”乃至“参考”之外的文本也不一定是什么“文化垃圾”。“经典”本身也是一个变化着的系统,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原来的经典可能不再是经典,而一些原来的“文化垃圾”倒可能成为经典。文化研究通过相对的而不是等级化的观点来看待新出现的、因而常常是非典范的文化产品,它鼓励对于统治性的教育与政治实践的前提进行质疑,而不是努力去迎合预先决定的、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文化价值定位。这样的实践建立在对于传统人文科学研究的种种学科前提的扬弃之上,它是批判性的自我意识的前提,也是对于支配性的学科体制进行有效抵抗的先决条件。(注:参见: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第651-652页。)
四
如上所述,以文化为对象的人文科学学科总是按照“正规科学”的模式形塑自己,它给学生的印象是一种文化具有一种内在的特征,其特定的结构可以通过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加以描述,它认为文化是已经形成的而不是处于转化的过程中。
这一点在文学理论教学中的体现就是:文学理论教科书总是乐于总结文学的所谓“一般规律”、“本质特点”,似乎存在一种一般的文学艺术活动,从中可以概括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在创作论方面,学生被告知文学创作存在所谓“一般规律”,创作活动必然遵循几个固定的“阶级”与“过程”。而没有看到不同个性、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在具体的创作活动中根本不理会什么固定的“阶段”或“过程”;在欣赏论方面,文学理论教科书同样热衷于总结所谓文学欣赏的“一般规律”,比如认定真正的文学欣赏一定是或应当是有“距离”的,审美活动是无功利的,而没有看到文学欣赏的方式实际上取决于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比如普通大众在欣赏大众文化的时候就是非常投入(不超越)的,是高度参与的(经历过在体育馆举办的流行歌手演唱会的人对此当无异议。英国著名传媒理论家约翰·费斯克对此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更何况距离说与审美的无功利说本身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理论,它本身就体现着一定的阶级与社会阶层的利益与趣味,我们没有理由把它普遍化为一般的欣赏规律(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对此有入木三分的剖析);而在作品论方面,文学理论教科书在划分文学种类及各个种类的特征时也存在严重的机械化、教条化现象,好象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都具有超历史、超民族的普遍本质似的。
在这些被人为建构的“普遍规律”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元的与绝对的真理观与认识论在起作用,一种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的答案。尤其严重的是,当这些“普遍规律”在学校中被体制化为僵化的教条以后,就会成为压抑性、排他性的知识与话语霸权,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形杀手。
如果说教科书化的文学理论在理解文学的性质时存在严重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倾向,那么文化研究抵制的正是这样的倾向,在这方面,它恰好可以发挥解构的功能。文化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de-historized)、非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学科实践,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反对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
五
与自然科学相似,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结构以生产专家为目的。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阻止了各学科中的专家把他们的知识与公共领域相联系。学科化的研究要求专家们只关注少数几个与其专业相关的专门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远离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争论。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待文学研究,就必须认识到,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是一个解放工程。这个工程如果脱离与公共领域的联系将是不可思议的。必须从政治(广义的社会政治而不是狭义的党派政治)的角度看待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功能。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要既在大学之内、也在大学之外重新形构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不只是文人(personofletters),也不只是观念的生产与传播者,知识分子也是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中介者与桥梁纽带,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的合法化者或解合法化者,他/她本质上起到的正是一种政治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并进而把有机知识分子区别为“保守的”与“激进的”。保守的有机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提供道德的与知识的引导,认同统治阶级的权力关系,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宣传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提供经济、政治与伦理形构的基本原理;而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则尝试为被压迫阶级提供道德与知识上的引导,提供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不可缺少的教学法的与政治上的技巧,帮助他们参与并领导集体斗争。(注:参见: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第653页。)但是,葛兰西的观点虽然有助于形构文化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即创造抵抗性的知识分子,但葛兰西却过于机械地把“保守”与“激进”的划分纳入僵化的阶级分析框架,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产生批判的知识分子(即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而实际上,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任何抵抗压抑性知识与实践的群体中产生,并能够与任何这样的群体合作。正如吉罗克斯指出的,“‘有机的’一词并非专指那些把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的革命动力的知识分子。”(注:参见: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第653页。)
但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巨大启示性在于弥合知识分子哲学(知识分子自觉地建构的思想体系)与大众哲学(常常表现为“常识”或民间习俗)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抵抗性的知识分子总是发现自己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他们一般在学术机构(比如大学与研究机关)内生存,而这种机构在产生统治性的文化中常常起到核心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反抗机构,并为学生提供与机构以及社会中其他霸权角色进行斗争的反抗性话语形式。西方的文化批评家经常提醒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学术机构的收编能力,它能够把哪怕是极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安置在一个体面的任职系统内,并赋予他们以机构外的知识分子不能想象的各种“好处”。从而这个任职系统也就成为充满诱惑的罗网。这就导致了机构内的批判性学术活动一般总是偏离与具体的政治运动的关系,结果是,激进的批判理论蜕化为学术杂志与学术会议的不痛不痒的点缀(比如福科、乔姆斯基、赛义德等激进的批评家在西方成为媒体与大学中的明星,它们的言论似乎正好证明西方学术体制的强大的“收编”能力)。
真正以批判为宗旨的文化研究必须抵制这种形式的学术与政治收编,其最主要的方法是鼓励批判的知识分子自觉、积极地把自己的批判融入公共领域的重大讨论,从而把校园内的政治与校园外的政治、把学术政治与社会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工程对于拓宽大学以外的理论与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他们必须发展学科体制与学术奖惩体系以外的运动,呼应葛兰西关于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的观点。它鼓励抵抗的知识分子在许多围绕意识形态斗争而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就是说,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参与对抗性的公共领域之中的重要性。由抵抗的知识分子所实施的反学科的实践如果只有大学校园内的听众,那么它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力。反学科的批判实践应当更加广泛地发生在公共领域。就文学研究与批评而言,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尤其应当积极关注新出现的、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比如大众文化),认真地而不是情绪化地分析它们的意识形态效果。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批判的知识分子应当放弃知识,更不是倡导反智主义,它的使命是把人文知识再政治化(repoliticize),把我们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看作是社会实践的生产而不是对于社会实践的被动描述,把我们在教室中发出的声音扩展到公共领域。
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意味着它不能像现在这样局限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反学科化与反机构化总是紧密关联的。虽然大学的学科结构在近期不大可能消失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但是我们不能把文化研究固定在这种结构中。反学科实践的最重要目的是促发激进的社会文化变迁。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安于大学为他们设置的角色,他们应当在大学中发展出具有大学之外的政治影响力与冲击力的反学科实践。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形式,文化研究应当形构一种对抗性的公共领域。
这样的一种任务要求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抵制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现代学科体制,并揭示这个体制的建构如何与社会劳动分工相互勾连、如何妨碍了社会劳动分工的消除。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并帮助生产这种分工。文化研究需要发展出一种可能性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知识将被视作与大学内外的斗争动力相关的集体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必须发展出一种对抗性的话语与学科的实践,以便处理遍及各种表征秩序、对抗性的文化经验模式以及不同的未来观念的斗争,显然激发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兴趣不可能在传统的系科中发展出来。大学的结构是与压制知识分子的批判关怀的那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