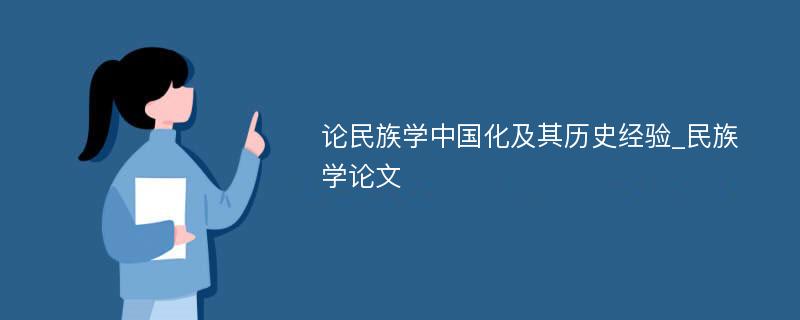
论民族学中国化及其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5)03-0086-05
站在学术舞台的视角观察,人们应当注意到:在人类多元文化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时代 格局下,既是适应全球化趋势中与国际同行对话沟通的需要,也是出于更好地服务于国 家发展的现实目的,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民族学学界讨论的 热点问题之一。民族学中国化的历程昭示我们,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确是一 个老话题,同时又是一个新课题。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来考察,还是看作一个结果去追 寻,民族学中国化问题常议常新。在民族学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中,总结民族学中国化历 程的基本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却也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薄弱领域,尚未见专门论 述,本文就此谈几点粗浅认识,这不仅将有助于深化对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而且有利 于民族学中国化的新的实践推动。
一、民族学“中国化”的界定及其肇始
传统民族学是研究各个民族的社会及其文化的学问,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中 国民族学最早是西方民族学(或称文化人类学)传入的产物。192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12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 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和比较的学问的观点。如果从这时算起到今 天,民族学作为学术概念出现在中国已有近80年的历史。民族学本非中国土生土长的学 术理论,而由西方传入,“因而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依 赖于中国化。”[1](P277)
那么,究竟如何界定民族学中国化?它的涵义是什么?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今天, 每个热闹的讨论时期,学术界都没有对民族学中国化概念的涵义形成公认一致的界定和 表述。这是一个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深化对民族中国化问题的理性思考,首先必须回 答这个问题。认真考察民族学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历程,比较分析各家之说,经过进一 步理性深思,作者认为应当这样理解和界定民族学“中国化”概念的涵义,这就是:立 足于中国国情,在充分了解、比较和吸收西方民族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民族学 研究和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探索和构建中国独特的民族学理论体系,并在服务社 会的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丰富和发展。理解这一概念要进一步认识四点:(一)民族 学是舶来品,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只有充分介绍、认识、比较和引进西方的民族 学理论,在中国才会有可“化”之物,开放中的引进是民族学中国化的基础;(二)民族 学“中国化”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它既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 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实践活动,基于社会需要的实践活动是民族学中国 化的内在动力;(三)民族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 历史阶段上具有不同内容及其表现形式,而且呈生成、完善、丰富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最成熟的表现是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充实和发展。不同历史发展 时态上的不同表现是民族学中国化的历史特征;(四)民族学“中国化”是相对于民族学 学者而言的。离开了民族学学者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参与,民族学“中国化”就失去了存 在的最根本条件,因而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学“中国化”也可以理解 为中国民族学学者对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进行的“中国式”介绍、吸收、改造和创新 的实践过程。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建构过程,民族学“中国化”具有鲜明的开 放性、实践性、历史性和主体性特征。理解上述观点,对于中国民族学学术创新、实践 推动和学科建设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西方输入的学术幼苗,只有适应东方中国的环境和土壤才能生长和壮大,长成参天的 学术理论“大树”。中国学术界提出民族学“中国化”,可以视为学者们对于源于西方 的民族学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文化自觉,这种学术文化理论究竟生于何时?民族学 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起始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燕京大学执教 的吴文藻先生是倡导和主张民族学“中国化”的代表人物。吴文藻为在中国建立“比较 社会学”的基础,“1940年开始主编《社会学丛刊》,在该丛刊的总序中,提出借鉴功 能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实现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1](P283)同时 ,他组织民族学调研队伍进行实地调查,创办刊物《社会学丛刊》,着手进行民族学中 国化的实际创建工作。有学者更明确提出,“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最早是由我国著名民 族学家吴文藻先生于30年代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提出来的。”[2]“吴文藻先生早在30年 代就提出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要使人类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植根于中国土 壤之上。”[3](P189),对此,有关学术史实这里不一一列述。
笔者认为,民族学“中国化”和提出(或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有 着显著差别的概念。民族学“中国化”和提出民族学“中国化”在时间上不是同步的, 而内涵上也不完全是一码事。民族学“中国化”强调的是民族学在中国生长和发展的历 史的过程,而提出民族学“中国化”是一种认识观点,强调的是对民族学“中国化”的 历史过程的自觉意识。前者是自在的历史,后者是自觉的历史。民族学“中国化”作为 既在的过程状态,可以产生于这种认识提出之前,也可以是一种将在的趋势形成于这种 认识提出之时或之后。民族学“中国化”的肇始之时并不等同于提出民族学“中国化” 的主张之时,事实上要早于学者们明确提出民族学“中国化”主张的时期。
因为,民族学产生于西方,是舶来品,故才有所谓的“中国化”问题。中国“化”要 有可化之“物”才行,不然“化”什么呢?没有对象,没有依据,就不会有相应的过程 。因此,根据前述关于民族学中国化涵义的界定,笔者认为民族学“中国化”以民族学 传入中国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民族学“中国化”的起始时间开端于民族学传入中国 的时期,也即指民族学从传入中国之时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这个时间在20世 纪初。民族学传入中国开始“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学“中 国化”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1903年7月底,北京大学堂官书局出版发行由著名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的《民种 学》一书,从这时算起,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并实际上开始“中国化”已有百年历程。
对于民族学中国化(本土化)百年历史的反思与研究,民族学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历来 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分期及其内容,而忽视了不该忽视的重要方面,即这个历史过程—— 民族学中国化(本土化)的百年经验的总结。
今天,民族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总 结百年来民族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回答民族学中国化进一步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无 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学术开放,国外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充分介绍与传播,为民族 学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
1840年之后,中国被迫进入了近代历史。伴随一代代有识之士寻求救国强国真理的努 力,西学东渐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大趋势,学术被迫开放,西方和俄国的人文—社 会科学纷纷被介绍与传入中国,其中包括国外的民族学知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学、民 族学学术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在有识之士寻找社会变革思 想的历程中选择和接受了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自地主阶级改 良派、早期维新派、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五四时期的新型 知识分子,不断地从西方社会学说中寻找社会变革的思想和理论,其中作为西方民族学 理论基础的进化论思想影响最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思想巨匠接收并传 播民族进化论的理论和观点,为民族学理论的传入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康有为的《大同 书》、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章太炎的 《訄书》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成就;(二)欧美、日本和俄国的民族学家、传教士、探 险家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学调查与研究,是国外民族学介绍和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美国的汉学家罗克希尔对蒙古、西藏的调查;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对华北诸省的调查; 日本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对辽东半岛和西南诸省民族以及我国东北的调查;俄国人类学 家史禄国对我国东北地区诸民族的调查等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国外学者在中国进行的 早期民族学调查与研究,尽管有各自的目的,但在客观事实上介绍了国外民族学的理论 与方法,初步记录和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状况和问题,其成果至今仍不失学术上 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同时,这些调查与研究也启发了我国的一些民族学学者对本国民族 及其文化的关注。例如,日本人类学创始人鸟居龙藏于1902年7月到1903年3月对我国西 南诸省进行田野调查,考察了湘、黔、滇、川境内的苗、布依、彝、瑶等民族的体质、 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诸方面情况,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 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介绍了如何运用人类学知识比较研究民族问题,在中 国民族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长期的影响,其著作至今仍是民族学/人类学者研究中国西南 诸民族必读的参考书;(三)20世纪初期,中国较早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一些学者翻译介 绍了大量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并开始撰写介绍民族学的早期作品。例如 ,前面论及的林纾和魏易合译的《民种学》;林楷青译的鸟居龙藏的《人种志》;陶孟 和译的德国人类学者米勒·吕尔的《社会进化史》;而陈映璜、孙学悟、顾寿白等学者 分别撰写了《人类学》(1918)、《人类学之概略》(1916)、《人类学大意》(1924)等, 尝试研究介绍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正是这种学术开放背景下国外包括民族学(人类 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大量介绍与传播,为民族学中国化的肇始提供了必要的 学理准备。
三、有一批学贯中西,把西方理论同中国民族研究的实际相结合,在调查和研究实践 中进行学术创造的学者群体,这是民族学中国化不断推进的根本动力
追溯民族学中国化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学在中国传播、生根和发展的内在推力 ,就是在于各个主要发展时期都有一批学贯中西,又能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学术创造的思 想大家和学者群体。以民族学在我国创立时期为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8年前后, 大批学者赴国外留学,接受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术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其 中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孙本文、黄文山等在美国学习,杨堃、凌纯声、卫惠林等 在德国学习,陶孟和、蔡元培、俞颂华等在英国学习,林惠祥则在菲律宾大学师从美国 导师学习。他们在比较系统地学习国外民族学知识和理论后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相继 回国,运用所学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从事少数民族实地调查,进行学术创造,取得了具 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诸如颜复礼、商承祖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29) ,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林惠祥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等,推动 了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及其中国化进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得到初步发展,理论和方法上开始形成 不同特色,有所谓“南派”和“北派”之称。“南派”以西方进化论和美国历史学派的 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的民族史志材料,从而分类说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情况,故又 称“中国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林惠祥、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等,在民族史 志研究上取得了颇有影响的成果;而“北派”主要受功能学派的影响,强调理论,重视 应用,运用功能学派理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本土方法论,以吴文藻、费孝 通、林耀华为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推出了《论文化表格》、《江村经济》、《金翼》等 具有国际声誉的学术创新成果。学者群体的培养和形成,是民族学中国化不断推进的根 本动力。
四、确立和坚持把握时代脉搏,紧贴国情实际,回答现实问题的民族学中国化的价值 取向
近代以来,救亡、图强、富民是中国一代代志士仁人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上,民族学工作者紧紧把握历史主题和时代特 点,贴紧国情实际,积极回应社会现实需要,通过服务社会实现自我发展。新中国建立 前,在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时代要求下,民族学工作者运用掌握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展开对我国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的调查与研究,逐步认识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提出改 造中国的设想和方案,使人们看到了民族学服务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作用;新中国建立初 期,为了建立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在政府 组织下开展空前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 调查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民族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体现了新的时代价值,其中 国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费孝通为杰出代表的民族学家, 紧扣我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巩固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发展,以及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要 求,卓有建树地开展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取得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民族社会发 展理论、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理论、小城镇建设理论等一批划时代的成果,标志着民族 学中国化跃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中国国情,积极回应现实社会需要,是民族学中国化不断 发展的宝贵经验,是民族学中国化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新世纪,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 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坚信,在服务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民族学中国化一 定会更加大有作为。
五、着力处理“四对关系”,力求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模式
从具体意义上说,民族学“中国化”的历程是中国民族学者文化自觉的心路历程和文 化批判的实践历程。正是中国民族学者不断的理论探索及其实践活动推动着民族学中国 化的进程,体现着中国民族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民族学者在这个历程中确立了自己的 “理论——实践”的研究范式,从而形成了民族学“中国化”历程中的一条重要的本土 方法论经验,这就是着力处理“四对关系”:
(一)田野调查与文献史料运用的关系。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传统的最基本的研究工作方 式。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流传的大量典籍保存记载有各个民族的文献史料,是研究各民 族的不可缺少的民族学材料,这是民族学“中国化”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方法论条件。蔡 元培先生早在他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中就论述了《四夷列传》、《诸番志》 、《真腊风土记》等文献中民族学材料的价值;民族学“中国化”历程中,民族学者借 助中国历史典籍中民族学资料无比丰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研究工作中始终注意田野 调查与文献史料运用相结合,在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上创造了许多成果。典型例子之一, 如潘光旦先生对湘西北土家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他借助大量可信的历史资料,结合实 地调查,“从自称、虎与生活的关系、白虎神崇拜、语言中的虎和鱼等名词的解释、姓 氏等五方面的论据说明巴人与土家的源流关系”[4](P445),归纳分析得出土家是古代 巴人后裔的结论,说明土家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 工作,是民族学中国化进程中历史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其中形成 的关于民族识别的理论和方法是对世界民族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就是学习、吸收和借鉴别人的成果并在新的实践中运 用和检验。创新,就是总结前人的实践经验,经过抽象,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继承是 基础,创新是在基础上的发展。民族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坚持注意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 关系,在继承中创新,通过创新实现发展。可以说,民族学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中国民族 学继承与创新的辩证运动的过程,是我国民族学学术缘脉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
(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民族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生命所在是它们应用实践性。民族 学的历史及其价值极具说服力地证明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检 验并发展理论。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既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概 念定义的四个特征的理论,又不是机械地拘泥于四个特征的框框,而是与我国民族识别 调查研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民族意识判定方法,发展了斯大林的民 族识别理论。这是民族学中国化进程中体现我国特色的历史经验。
(四)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一直是民族学中国化进程 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本土化就是开放、吸收、创新和服务,而国际化就是我们要置身于 国际语境和学术发展的趋势中,立身于国际学术交流与沟通的舞台上。本土化不是固步 自封,与世界对立,而国际化也不是“西洋化”,失去自我。没有本土化,国际化就变 成毫无意义的空话,没有了自我;而没有国际化,本土化也失去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不 会有真正的本土化。我们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而应该统一起来。在民族学中国化的历 程中,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往往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处理得较好的时期,例如 30和40年代前期,50年代前期、80年代以后至今,反之,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处理不好 的时期,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就遭遇不顺,典型例子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期,民族 学中国化历程处于停滞状态。应当确认的是,在民族学中国化历程的推进中,妥善处理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无疑是一条仍需坚持的成功经验。
总之,民族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民族学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必 由之路,理性地理解和总结民族学中国化及其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民族学中国化 的更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