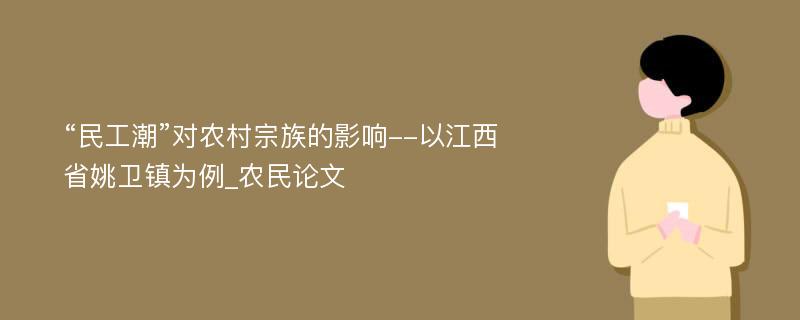
“民工潮”对农村宗族的影响——以江西姚圩镇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江西论文,为例论文,民工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当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迁之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与传统的户籍制度的松动,曾经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地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大量的向城市流动,成为引人注目的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称之为“民工潮”。我们认为,“民工潮”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它给中国农村宗族的变迁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特别重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我们在江西新余市姚圩镇调查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这里的“农民工”在深圳特区建立了“深圳一条姚圩街”;21世纪之初,这些由深圳返乡的“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姚圩一条深圳街”,两个“一条街”鲜明地折射出“民工潮”对农村宗族变迁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它改变了农村宗族的社会结构。
一、“民工潮”加速了农村宗族的社会变迁
在姚圩镇劳务输出的进程中,农村宗族与地方政府的互动角色由依赖家族到依靠政府,体现在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0年代末——1995年):这时期的姚圩镇人外出务工是自发的,靠家族成员的介绍,某个家族有一个人先出去打工,紧接着亲帮亲、友帮友,就是本族的一群人。20世纪80年代末姚圩镇蒋家村蒋某在深圳当兵转业就留在深圳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先是蒋氏家族的人,然后是全镇人,他们通过亲友帮带,到1995年,姚圩外出务工人员已经达到5000多人,且多在深圳创业。这时的劳务输出是处在无序的状态,家族处在主要地位,而政府则是处在次要的地位。“民工潮”的产生使乡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工”对血缘关系的依赖显得更为突出。第二阶段(1996——2000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姚圩镇人外出务工的数量越来越大,自发的、无序的状态显然不能适应“民工潮”的要求,于是姚圩镇党委和政府适时介入,因势利导,把驻深办事处改为驻深党支部(后由新余市委在此基础上组建流动党委)。这时期党支部的职能更加突出,就是逐步探索出一条“流动有序、管理有章、异地有家、建功立业”新路子。这时期政府职能发生了变化,将办事处仅仅落实计划生育工作变成为“农民工”的五项服务,即就业服务、宣传教育服务、生殖保健服务、法律维权服务、生产生活服务。这时期的特点是,农民外出务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这时期是姚圩“农民工”回流时期,外出务工人员致富后不忘家乡建设。正在这时,姚圩镇党委和政府适时引导,给予宽松政策,提供优美的投资环境。几年来,先后有310人回乡投资,创办各种经济实体53家,最大的有新余市金马广场、金叶广场、金融房地产和姚圩镇日发车辆40班跨省市的长途汽车站、葛根加工厂、日供水200吨的自来水厂等,解决就业人员856人。在姚圩镇开辟了一条新街道,由深圳务工返乡农民经商开店、摆滩设点,人们称之为“姚圩一条深圳街”。这里的农民富有了,家家户户奔小康,全镇7273户,有6100户建起了3-4层的小康楼,其中有34户高标准的小康楼,小轿车十几部。这些小康村,房前屋后有绿化、村内村外有亮化、路面广场有硬化,周围环境有静化。在这期间,政府在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回流中起着主导作用,盘活了回流人员的丰厚资金,推动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民工潮”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和宗族的价值观念。第一,血缘关系在劳务输出初始阶段起着重要作用。姚圩镇第一个劳务输出阶段主要是以自发的方式实现的。自发的劳务输出是指输出的劳动者个人或数人在没有他人和组织的帮助下,自己确定和前往输入地寻找就业机会的过程和形式。从姚圩镇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期可以看出,血缘关系在劳务输出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可见,血缘关系在劳务输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地缘关系在劳务输出的全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发现,地缘关系对首次外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起着重要的牵动作用。由于外面的世界、外部的赚钱机会、用工需求通过快信、电话、电报传回输出地,这些信息的受益者首先是局限或优先于直系或旁系的亲戚,但家乡很快就有更多的人也能够分享早期外出者传回来的信息。于是村里的农民就沿着早期外出者的足迹输出到外地。由于多数外出打工者都没有外出的经验,因此在早期外出打工的人回家过年或探亲之际跟着出去,这成为江西农村劳务输出一种最常见的模式。这种通过地缘关系所实现的劳务输出,是一种依托非正式组织的劳务输出形式,是劳务市场正规组织发育不完善时期农民所能够依赖的劳务输出途径。应该说,以地缘为纽带进行的劳务输出,在推进江西老区劳务输出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三,业缘关系在劳务输出的后阶段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劳务输出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我们发现地缘关系演化成一种业缘关系,尤其是当劳务输出后所从事的工种和工作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时,业缘关系就比较容易与地缘关系结合并成为输出的主要渠道。业缘关系有多种表现形式,比较简单的一种是行动的老乡将想出去的老乡带出去,并负责介绍到自己所在的企业,向带出去的每个人收取一定的劳务费,这种费用数量不等。通过业缘关系实现的劳务输出,主要集中于建筑、采矿、建材、服务等方便分包和计件的行业。虽然业缘关系相对于地缘关系对劳务输出来说是一种进步,但它仍是一种非正式的劳务输出组织方式。
二、“民工潮”改变了农村宗族的社会结构
“民工潮”群体,包括亦工亦农者和只具农民身份的纯粹工人。这是一支“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扮演着农民与工人双重角色。这支队伍规模空前,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仅江西的姚圩镇现有外出务工人员11218人,占全镇人口的37.8%,占劳动力人口的74.6%。
“民工潮”改变了农村宗族的社会结构。第一,内族外迁。20年来,在姚圩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许多族民纷纷外迁。早在深圳特区创业时期,姚圩镇蒋家一名男士在深圳当兵,转业后安排在深圳工作。适逢改革开放、建设深圳特区之机,他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堂亲表亲先后介绍到深圳打工。紧接着是姚圩镇的乡亲好友陆续到达深圳,一个个洗车行、饮食店,一个个娱乐城、电子行在深圳创办。据统计,1990年姚圩镇外出务工人数为4976人,1995年发展到7422人,到2004年已经达到1.4万人,占全镇人口的三分之一强。仅在被称为“深圳姚圩一条街”的深圳罗湖区春风路就聚集4000余名姚圩人。它对农村宗族的社会结构调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二,外族内迁。姚圩镇的农民有1/3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有些农民在外创办自己的企业,已经不再回乡种地了。有一个村庄从1982年到1998年抛荒土地就达百余亩。该村干部为了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抛荒问题,于是请来了贵州的打工族。从1998年起,先后就有苗族、京族、仡佬族、布依族和彝族等5个少数民族共12户、66人迁居该村,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相对独立的“贵州村”。第三,家族企业发展。“民工潮”带来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必然变化,推动了家族企业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农业和产品加工业为支撑的新型企业,它带动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拓展了城乡市场,搞活了农产品的流通。从姚圩镇外出务工回流的农民投资家乡建设中可以看出,这些“农民工”把发达地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回家乡,把本家族的人组织起来,开办起一个个现代企业。
“民工潮”的作用、贡献是巨大的,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将是深远的。当代中国城市以及以之为主导的社会的急剧转型,通过游离于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农民工”群体传递给广袤的乡村,使他们自己和家乡被迅速而彻底地裹进这种以城市为主导的变革之中。城市的现代文化使乡村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家庭、宗族关系受到新的挑战。从而使以血缘为核心的乡村亲缘文化和以宗族关系为框架的乡村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时伴之以越来越快的农村城镇化步伐。可以断定,宗族文化和宗族结构正处于冲击下的解构状态,同样也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