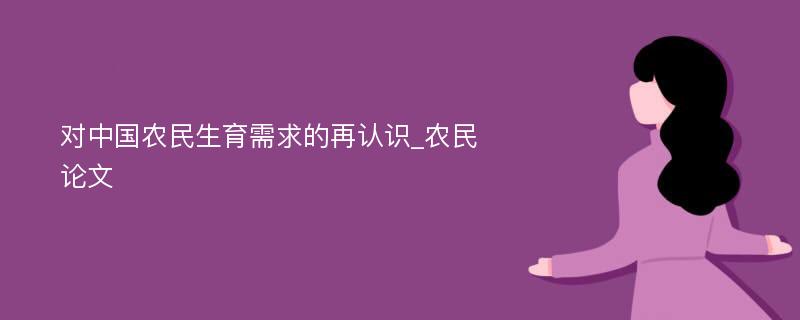
中国农民的生育需求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中国农民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寻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基础,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1996年春第六次中央计生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各级领导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人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的依归)。而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关”的中国农民的计划生育问题则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瓶颈”。要摆脱“瓶颈”制约,就需剖析其主体——农民自身的生育需求。
一、理论研究的现状
在探讨农民的生育动因、生育偏好、生育数量、生育时间问题上,理论界观点各异,侧重有别,真(合理性)假(欠缺合理性)互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一)有人从生育行为的角度入手,指出有三大理论取向即“效用最大化”解释;“社会——文化”解释;“风险最小化”解释。
(二)有人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依托,提出了农民生育的需求层次结构理论,认为农民的生育需求依由抽象到具体,由内隐到外显的顺次,包括五个层次:1.终极意义需求;2.情感需求;3.继嗣需求;4.社会性需求;5.生存性需求。
(三)有人从中国农民生育需求变化的角度出发,从现实生活的需求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的生育需求及其变化的模式替代。
(四)计划生育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论。一种从分析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环境因素着手,认为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环境的软约束性,传统旧习惯环境的误导向性,社会福利环境的弱保障性,经济严惩环境的负效应性和劳动生活环境的欠安定性(杨善麟)。另一种从农民在计生问题上的心理障碍的角度考虑,认为农民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1.传宗接代的心理;2.逃避过关的侥幸心理;3.怕政策变的心理;4.观望攀比心理;5.多生孩子与国无害的心理(李俊国)。
综上,每一种理论都以在不同层面上的合理性而各树一面。我们的始因并不在于对每一种理论本身进行剖析,而在于从中受到启迪,以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管哪一种理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从人自身和外在于人自身的彼岸世界来探究农民的生育问题,对外在于人自身的彼岸世界的研究颇多。而对人自身的研究则表现为欠缺。按照心理学的需要满足过程与行为的关系(刺激→需要→动机→行动)。
研究农民的生育问题最为棘手的不在于生育行为本身,因为生育行为本身展现给人们的是生育控制的困难现状,而在于探寻促使行为产生的动因——利益刺激,在农民的生育问题上更直接地表现为农民的生育需求,所以揭示农民的生育需求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及其内部框架结构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民生育需求的框架构建
农民的生育需求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多变的、相互交错的、动态的系统化过程,无论是需要层次理论还是需求的因素理论都难以对农民的生育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需要本身具有无限性、相关性、重复性、竞争性。然遵循社会科学发展的两大趋势——抽象化和具体化,农民的生育需求是否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一块是基于农民自身的生育需求(也可称为内生需求);另一块是基于外在于农民自身的彼岸世界而产生的需求(可称为外生需求)。然后再在两大板块的内部再细分。
(一)内生需求。人作为主宰世界的主体,其行为必然受其内在的动因的支配,而动因又源于自身的需求,这种需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归宿吸引着每个人潜力的外露。农民的生育需求在这方面表现为农民自身沿着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轨迹实现着需求的满足和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具体表现为:
1.永恒意义上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自身的再生产在农民的生育需求中的反映。无论是称为“生殖崇拜”,还是“种子信仰”,都是通过“种”的繁衍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永生”观念所内化于农民自身的需求,从而与社会物质过程的“无限性”相统一,整合为社会再生产。
2.文化价值实现需求。既有内化于农民自身的传统生育文化惯性所形成的需求,例如:“多子多福”、“早生多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等;也有作为人的价值实现的需求,做人要挣个“面子”,自己能“做”出人来。从而证明自己具有社区规则所认可的做人资格,也经受了一次次生育的成就体验,这也是基于攀比心理产生的需求的一种表现,别人(能)生,我也(能)生;还有基于自身的义务和责任所产生的需求,“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等等,随着近年来寻根问祖风的掀起,更强化了农民的这些需求。因为中国的子女观是反馈型的,而西方则为传递型。
3.慰耦情感的需求。“子福”、“续梦”、“消费享受效用”等构成农民的“生育幸福观”,晚年可尽享“天伦之乐”,通过成就体验而获得满足感,从而倍感人生的伟大,自己的辉煌,在微笑中走向“极乐世界”。
4.生理性的需求。这是基于人的本能而产生的需求。事实上,性的需求和生育的需求是相关联的,生儿育女更多的体现着农民的本能性需求。
(二)外生需求。人自身与“彼岸世界”(也可称为大环境或身外万物)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需求,更多地体现了“社会人”、“经济人”的需求趋向,是人自身受“彼岸世界”的感染而衍生的需求,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明显地有决定于内,受制于外的双重性。这种需求同样由不同的层面构成一个整体,具体为:
1.文化氛围层面上的需求。这里的文化非内化于人自身的文化精神,而是存在于彼岸世界的文化背景。即在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氛围中产生的共识性,明示性,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生育需求。
(1)继嗣需求。在农民的二元观念世界里, 总希望今生多子多孙,香火不断,来世免做“孤魂野鬼”。中国农村(甚至城市),在继嗣的规则上实行男性单系偏重,所以,生男构成了农民长期稳定的生育需求。这种历史形成的需求观根深蒂固,构成了计划生育的最大障碍。日常听到这样的对话:“听说你媳妇生了?”“是的。”“男还是女?”“男”。“恭喜,恭喜,有福气。”“女。”“也挺好。”“其实,女孩孝顺,省心。”也许我们会从这段对话中悟出点什么来。
(2)伦理性需求。这是基于传统人口伦理观念。 小农意识而产生的需求。什么“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早生多生”、“多子多福”等等形成了农民早生、多生、生男的需求模式。
2.社会层面上作为“社会人”的需求。主要表现在:(1 )期望获得正面性评价的需求。在一个信息共享的社区范围内,每个农民的举动都会受到来自周围的达到共识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正面评价为农民所期盼,尤其是对生育的评价,以免众口酿成人间悲剧,象“断子绝孙”、“绝后”等咒语胜过利剑。
(2)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支持的需求。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 分工协作决定了农民在血亲姻亲构成的相互交错的社区网络中寻求支持的可能性,生育使农民具备了这种资格;家族内外的矛盾、冲突与纠纷,天灾人祸的频繁发生,刺激了农民的生育需求。
(3)社会安全保障性需求(或风险缓解或消除需求)。 “养儿防老”,劳动力供给问题在生产力发展的现有条件下,只能依托于现实的劳动力,再加之“孤老”现象的负效应,再次反复刺激着农民的生育需求。在宗族矛盾发展过程中,经常性的族外争政权,族内争族权表现为计划生育上的争生育权。再加之社会秩序的间断性无序状态,强化了农民的生存压力。总之,劳动生活环境的欠安定性使农民将希望寄托在生男孩和多生孩子的生育行为上。
3.关于“效用最大化”解释的说明。中国的农村主体——农民,由于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其经济意识,经济头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经济人”所为,经济分析方法在农民那里不是自觉性的,并不排除少数农民的完全经济化。所以,这种解释还不能形成农民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因,当然,经济因素正在走向农民。基于此,本文认为“效用最大化”解释在分析农民生育需求的变化时,可以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内在动因源,将产生巨大的左右农民生育行为的能量。本文将这种解释仅仅看成是影响农民生育需求的外在因素,这样,方可避免“效用最大化”解释的缺憾。
综上,农民的生育需求的内容是非常庞杂的,可以有不同的层面,每一层面又可细分为次级的层面,其划分标准因不同层面而异,但不管怎样区分,其中的任何一个子层都难以说清农民生育需求的全部,只有在宏观上划分为内在和外在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在二级层面上显露出从抽象到具体,由内隐到外显的生育需求顺序。内在需求和外在需求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形成一股来自分层需求的不同作用力形成的合力(即动因),使我国农民的生育需求表现出特有的风格;在生与不生中选择生,在生育偏好上倾向于早生,多生、男孩,至少子女构成中需要有一个男孩。这可以从广大落后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得到证实。
三、农民生育需求走势展望
上面是对于一般农民的生育需求框架所做的理性的静态分析,实际上,这一框架中的每个层面的需求都是一个变量,这些变量共同促成了农民生育需求变化的可能性。要使农民的生育需求发生变化,最关键的是要转变农民的生育观念,用文明健康的新型生育观念代替传统的旧观念,事实证明,农民的生育模式开始从早生、多生、生男的传统模式向晚生、少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模式转变,当然,少生不是一切,要通过少生来促进优生优育优教,力求把解决现已存在的人口数量规模问题与解决远期的人口结构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我国农民的生育观念、生育需求、生育行为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至于这个阶段需要多长时间,其发展趋势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量之间的互动作用形成的两种反向的力——拉力和推力的较量。
(一)拉力——一股不可低估的寒流。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及,以抛砖引玉。
1.传统文化形成的生育需求惯性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其改变决非短期所能奏效。
2.属于农民本能意义上的需求,同时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有需求。如性、生儿育女的需求,具有永恒性,持续性,已经硬化为人的一种固定需求模型。
3.对生育的数量和质量关系的歪曲理解,即将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错误地理解为正相关关系,从而使家庭经济环境的约束性软化,认为“添丁如同做饭加碗水”、“养娃不算饭钱”等,往往表现出重生轻育,重数量轻质量。
4.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使农民陷入越贫困越要生,越生越贫困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例如长江流域的贫困问题非常严重,地区间贫困差异悬殊。1993年九省一市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44%,其贫困县人口约占全国的50%;其乡村人口占全国的46.35%,其收入低于300元的乡村人口占全国的59.2%。
5.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漏洞百出,堵塞乏力,以至目标需求与现实控制结果相差甚远。表现在:经济严惩环境的负效应刺激了农民的生育需求,治标不治本的目标式生育政策的多变性,缺乏连贯性减弱了其信度,也滋生了农民逃避过关的侥幸心理;执行过程中的“三假(假手术、假证明、假鉴定)”行为人为地提高了人口的生育率,使目标控制与现实操作差距拉大,刺激了再生育的欲望。
(二)推力——一股不容乐观的暖流。表现如下:
1.社会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影响着农民的生育需求的变动轨迹。
(1)农业生产的现实劳动力的换位——妇女、 老人从事农业生产,强壮男劳力离开农业转而从事非农产业,打破了“农业生产离不开男劳力”的神话,从而相对降低了对于劳动力体能的需求,使农民在配置家庭资源的过程中减少了投向生育的比重。同时,也增强了现代农妇的角色意识——吃苦的半边天,农业的主力军。这在一定程度上冲谈了生男的偏好。
(2)农村妇女在非农产业的就业空间拓宽, 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参与水平,也就提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从客观上促进了生育偏好向“少生优育”的倾斜。随着世界范围内女性的崛起,亚洲新一代女性专业人员,政界人士、公司总裁、企业经理们已赢得经济上的独立,是以与男性同事相配。从而给亚洲女性带来了最宝贵的财富——选择权。这种在的世界趋势(或背景)为中国农民的生育需求的变化创下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即使对数百年来女性角色僵化不变的某些地区,也送去了进行自我选择的青春气息。
(3)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比重在东西方的持平, 使中国的农民开始从西方女性身上得到启迪。独身主义,少生或不生的生育观念促使中国农民走向自身的解放,争取平等权。
(4)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目的由增加家庭劳力、 传宗接代转向增加家庭乐趣,感情需要等(赵景辉),而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民工潮”的兴起,促进了城乡信息沟通,使城市现代文明对广大农村产生了辐射和示范效应,对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产生了乘数效应,从而使农民的生育需求向城市模式逐步转化。
2.妇女自身在其解放中对社会做出的认可性贡献将排除妇女生育需求转化中的障碍。
(1)青年妇女积极参与经济创收活动,使其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从而在“阴盛阳衰”的呼声中改变着现代女性的形象;大批女强人的出现使妇女的角色认知定型化——女人可以为男人能为之事,其生育倾向因无暇顾及而大大弱化。
(2 )“女儿孝顺”的生活体验使人们对养老送终的希望寄托由单一男性模式向男女性双向模式转化。再加之青年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使农民对于子女的依赖性减弱,从而也就弱化了其生育需求。
3.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和适度发展可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尤其是针对独生子女户和无男双女户存在的困难及计划生育户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产生的各种后顾之忧所开办的计划生育保险的发展和完善,农民会逐渐从生育构成的壁垒中解脱出来,而成为一个不断完善和日益发展的人。
4.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具有正面引导作用。
“少生快富奔小康”的富裕之路,男到女家结婚落户使农村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典型事迹对广大农民转变生育观念具有强烈的示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