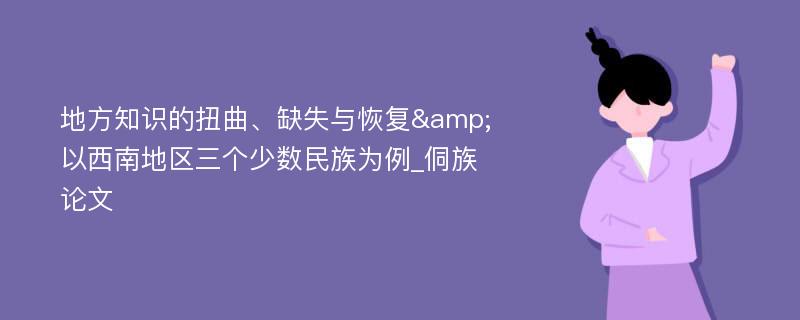
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以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南地区论文,为例论文,少数民族论文,缺失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5)02-0062-05
一、研究假设
民族文化的结构极其复杂,并具有适应于所处环境的禀赋。早年学术界对文化的生态适应研究较为深入,很多结论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但目前人类社会所面对的事实是:生态危机在世界各地频繁露头,这就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具有适应能力,那么为什么还会有生态危机出现?要回答这一疑问,笔者认为,前人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仅关注于民族文化的生态适应,而忽略了民族文化的社会性适应。以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和彝族为例,他们的传统文化原先曾高度适应于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生态智慧和技术技能体系。近500年来,中央王朝为了巩固西南边防而采取了一套稳定的文化政治策略,强化对这些民族的直接统治。各民族为了适应这一文化政治变动,不自觉中导致了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变形、扭曲和缺失,表现为所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从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社会性适应复杂多样,地方性知识的蜕变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民族间的文化政治互动没有关联,但如果将这种变动纳入文化的社会性适应去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其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扭曲和变形,正是族际互动过程中民族文化进行社会性适应所导致的后果。
将民族文化理解为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复杂体系,在人类学研究中由来已久。“适应”是一切自组织复杂体系共有的本能。因而,文化的适应同样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早期的摩尔根和莫斯,其后的斯图尔德、萨林斯,晚近的拉巴埠、格尔兹都对文化的适应做过有创见的论述。但他们的论述大都是着重于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较少地论及文化对所处社会环境的适应,特别是对多元民族并存复杂社会适应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然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单独应对所处的生态环境,它还必须应对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因而文化的社会适应应当是文化适应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当指出的是,前人较少论及民族文化的社会性适应,并不是他们的认识与理解有缺陷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去支持这一领域的探讨。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加上社会背景的变化速度要比生态环境的演化速度要快得多,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肯定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又很不相同,以致于在田野中所观察到的文化事实到底是适应何种社会背景的结果,也就无从加以分析与论证了。
有幸的是,中国的各民族可以为这一研究空缺提供具体生动的研究对象,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有三:一、中国有丰富可凭的系统文本记载,足以支撑这一课题的研究;二、中国历代政府所执行的民族政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以致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对这一政策所作出的反馈,其因果关系较为明晰,容易加以界定;三、中国各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作用与结果,无论从少数民族还是从汉族方面都可以在文献查阅与田野调查中获得可凭的证据,只要把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的作用理解为汉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那么中国将是探明民族文化社会适应的最佳场所之一。本文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将我国西南地区近500年的历史过程作为探讨民族文化社会适应的对象,希望揭示作为汉文化代表的中央王朝采取一套连续、稳定的民族政策作用于西南各民族时,在不同的民族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后果,以便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文化社会适应的某些特点,丰富和完善民族文化适应的内涵。
为了使研究的对象与结论更其具体与明晰,本文仅以各民族生态知识与技能的传承完整程度为分析重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格尔兹、拉巴埠已经做过了很多基础性的铺垫,这里仅是将他们的思路与方法延伸到中国的西南各民族中。为了揭示文化社会适应能力的复杂性,斯图尔德将文化的内在结构理解为多层次的夹心蛋糕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观念,这里也将借用这一模型去解释同一种社会政策在不同的民族中可以导致不同的后果。萨林斯将文化的流变理解为特殊进化与一般进化的复合,对本文的探讨发挥了重大的启迪作用,我们可以发现萨林斯所说的一般进化往往是族际互动导致的结果,其主要内涵体现为文化的社会适应,而萨林斯所说的特殊进化则是民族文化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导致的演变,其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文化的生态适应。当然,文化的社会适应和生态适应两者间也可能相互渗透。凭借这一理解,文化适应的复杂性可以得到较为生动的说明。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同一种政策的作用下不同民族间会产生很不相同的后果,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民族间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同一种政策不会均衡地作用于特定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而是有选择地作用于其中某一层面,结果就会使得这些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与技能,有的传承完好、有的残缺、有的部分保存、有的严重扭曲等等。据此可知民族文化的社会适应机制极其复杂,适应的办法和后果往往与原先的预料不相吻合,如果顺着这一研究思路,可望进一步揭示民族文化社会适应的具体调适过程。
二、民族文化的社会适应背景
中国西南地区生息着30多个民族,由于这些民族分别适应于范围不大的区域生态环境,长期以来这些民族很难聚结成较大的军事同盟与中央王朝抗衡。同时,由于他们的生计方式与中原汉族差异甚大,其物质产品不容易为中原汉族所利用,因而中央王朝对他们既难于直接统治,又无力影响其原有生计方式。这就导致了十三世纪以前的中央王朝对他们的统治基本停留在名义上,仅仅要求各族头人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稳定边疆,确保中原汉族地区免受战火威胁。
13世纪中期,兴起于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汗国,凭借精锐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穿越青藏高原东部的崇山峻岭,偷袭云南获得成功,实现对南宋政权的弧形包围,并最终将其并吞,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大变动。之后继起的汉族政权不得不调整对西南各族的统治政策。
14世纪中叶,明朝重新统一全国。吸取南宋王朝灭亡的教训,沿袭了元代开创的土司制度,强化对西南各族的统治。虽然允许各民族头人世袭统治其领地与人民,但他们的职权、职务和统治办法都受到了中央王朝的控制。各民族头人还得上缴一定的赋税,听候中央王朝的调遣。一旦时机成熟,中央王朝就会借机将某些土司罢免,将其辖地变成中央直辖的省、府、州、县。这一过程先后持续了500余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残存的各族小土司才最终被彻底罢废。
正是这一套持续稳定的边疆统治办法对西南各民族文化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外在作用力,西南各民族文化对此都作出了各不相同的社会性适应。适应的结果就是造成了相关民族文化的演化。由于文化所包括的内容极其复杂,因而我们不可能对民族文化的演化内容作全面的探讨。本文仅针对各民族文化中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发生的变形、扭曲进行探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同一民族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存在差异,其社会性适应也各不相同;对同一民族文化施加影响时的作用点不同,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传承完好程度也会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各民族文化发生扭曲缺失以及由此派生的生态灾变并不是中央王朝施政的初衷,而是各民族文化在社会调适过程中造成的后果。这就揭示了民族文化社会性适应的难以预测和复杂性。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西南的各民族近500年来的文化变迁是探讨民族文化社会适应的理想对象。
三、地方性生态知识的流变
中国西南部地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生态系统复杂多样,与此相应的是这里生息着30多个民族,他们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分别利用这些自然资源。通过世代的经验积累,他们对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建构了一套能够高效利用和有效维护生态资源的技术和技能。这些构成了各民族所特有的地方性知识系统。
近500年来,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控制力的加强,以及随之而来的汉族移民不断迁入定居,导致了这一地区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变。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各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传统的生产技术和技能发生严重变形甚至失传,无法按原样继续执行。随着利用方式的改变,特别是采用了不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汉族资源利用方式,造成了这些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式与所处生态环境相背离,导致生产效率大幅下降,生态环境随之恶化甚至发生灾变。
进入20世纪后,这里的生态恶化已经酿成了严重的灾变,相关地区各族群众的生活也陷入贫困。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对策,着手治理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并竭尽全力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找到合理的生态资源利用方式,这就需要仰仗当地各民族群众的地方性知识。为此,必须将在历史上发生严重扭曲甚至缺失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复原,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才能从中归纳出既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里,仅以侗族、苗族和彝族的地方性知识扭曲、缺失和复原为例,希望以此说明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如何帮助这些民族复原其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使其更好地为他们的发展服务。
在古代,侗族先民生息在沅江和都柳江流域的下游,以游耕的方式种植水稻,并辅以渔猎为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侗族先民被迫溯江而上,进入中上游的山区生活。在这片新的栖息地,90%的土地是低山丘陵,能够开辟为河滩稻田的土地不到5%。侗族居民为了适应这一环境巨变,不得不高度密集利用河谷滩地的土地资源。他们通过使河流改道的办法,在河滩地密集地建构了稻田、池塘和灌溉网,以此多层次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以稻米及鱼类满足食物供给。山地丘陵则用于生产原木,并通过天然河道漂运到汉族地区换取现金。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完善了林木生产技术,这一技术体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每公顷林地的年积材量可以高达30-50立方米,种下的树苗8年即可成材。与此同时,他们在林地实行林粮兼作。无论是间伐,还是主伐,山地的植被覆盖率常年超过75%,可以有效抑制水土流失的发生。因而这是一种可持续运作的资源利用方式。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土地使用权承包到家户,土地资源的人为切割使得林业生产必须的“长周期、全封闭、综合利用以及土地大面积使用”四个前提条件无法满足。因此,传统的利用方式受到了干扰,不仅综合产出能力降低,而且水土流失也开始加剧。有幸的是,政治权力主要影响的是侗族的生存环境,侗族地方性知识系统所受到的扰动十分有限。侗族居民对于相关的技术技能仍然能熟练掌握。只要为其创造适合林业生产的社会政治背景,并辅以适用的现代科学技术,他们完全可以找到可持续运作的资源利用方式和有效的管理模式。
在古代,苗族先民生息在喀斯特山区的疏林灌草地带。这样的地带一般位于山顶或土层极薄的陡坡地段,他们依靠游耕和狩猎采集为生。为了使用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他们建构了一套能通过地表植物物种和植物的生长态势判断土层厚薄的技术。凭借这一技术技能,他们能在高度石漠化的山地上找到苗木的最佳立地位置,使种下的苗木快速成活和郁闭成林,以便再次实施刀耕火种。
他们所生产的粮食品种多而单种作物的产量少,加上他们所生产的粮食不符合政府规定的纳税用粮规格,因而古代的封建王朝对他们抱有歧视和偏见。在政治权力的驱动下,这种歧视和偏见也在社会中扩散开去,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这对于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传承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不少苗族居民放弃了传统的资源利用办法,仿效汉族大面积毁林去建构连片的梯土或梯田。然而,在喀斯特山区地表土层很薄,地下溶洞伏流众多,大面积开垦梯土很容易打穿地表和地下溶洞间的缝隙,诱发严重的水土流失。这一过程在经历了200多年后,到了20世纪中期,不少苗族的栖息地严重石漠化。在最严重的地段,岩石和砾石的裸露率超过70%。这样的生态灾变加剧了当地苗族居民的贫困。当前,只有少部分苗族居民还较为完整地掌握传统地方性知识,他们成了当地生态恢复的宝贵人才。
中国政府目前正大力推行生态恢复和建设,具有这种地方性知识的苗族居民可以使用最简单的工具,花费最低的成本在三年内使已经高度石漠化的山地恢复为可以利用的连片疏林草地,条件稍好的地段甚至能发育成茂密的森林。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为数不多,需要通过大力宣传和推广苗族的传统生态知识,才能加快生态建设的步伐。在这个实例中,由于政治权力主要作用于苗族的观念形态,因此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严重受损。要全面复原其地方性知识,还需要作大量的艰苦工作。
在历史上,生息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连接地带的彝族是一个农牧兼营的民族。他们的农田和牧场均实行轮歇交替使用,在同一地段实施混合耕作。他们的畜群也实行多畜种混群放牧。由于他们的生息地山高谷深,因而放牧要随季节变化上下转场。夏天在山顶放牧,河谷种植作物,冬天则转移到河谷滩地放牧,山顶种植越冬作物。这一套地方性知识和技能能确保当地长出的各种草本植物或灌木均能得到有效而均衡的利用,并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地表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80%。这里的流水侵蚀和重力侵蚀十分严重,但凭借这一套知识体系的运作,可以做到高效产出和生态稳定两全齐美。
随着中央权力的深入,彝族的地方势力被消灭,依靠武力保证土地连片占有,并对其配套使用的条件不复存在。传统社会政治组织无法发挥原有的社会功能,牧场和农田交替使用的生计方式也无法继续执行。同时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彝族居民不断扩大农田而压缩畜群,在20世纪初达到了顶点。不过,由于政治权力主要作用于彝族的社会组织层面,因而彝族的传统地方性知识虽然受到冲击,但却没有完全缺失。一旦所需的社会背景得到改善,地方性知识体系很容易全面恢复。当前,中国政府积极推行生态建设,彝族居民很快地扩大了自己的畜群,并在农田中混种牧草。水土流失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彝族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改善。
2004年,中国政府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倡导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这十分有利于各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复原和运作。
事实证明,中国的西南地区自然背景与生态背景复杂多样,只有凭借多样并存的生态知识,去分别利用不同的生态资源,才能确保资源利用与生态维护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会成为可能。生态环境蜕变的原因并不单是利用过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利用方式上的失误。只要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受到人们的肯定而得到推广运用,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中国西南地区的生态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全面解决。
四、结论与讨论
斯图尔德高度看重生态背景对民族文化建构的作用,因而他将与所处生态环境相关的文化要素合称为“文化内核”,它们构成了文化的最基础层面。为了保证文化的稳定运行,在文化内核之上各民族文化都会形成社会组织层面。之后还会建构一个更高的层面——精神生活层面。于是,民族文化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蛋糕”。考虑到文化内部的极端复杂性,结合本文重点探讨地方性知识的需要,我们将他的文化结构模型作了一些修改。具体的说,就是在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层面之间插入科学技术技能这一层面,两种结构模型如图所示。本文探讨的要点正在于通过观察各民族文化的科学技术层面演化,去分析外力作用下文化的社会适应机制。
精神生活层面
社会组织层面
文化内核(基面层面)
斯图尔德的文化结构模型
精神生活层面
科学技术技能层面
社会组织层面
文化内核(基础层面)
本文拟构的文化结构模型
500年来,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并没有对各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施加均衡的影响。对侗族而言,主要是对其文化基础层面施加了影响;对彝族主要是对他们的社会组织层面施加影响;对苗族则主要作用于该民族的精神生活层面。结果,三个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表现为三种很不相同的情况。侗族的地方性知识不仅高度适应于稻田耕作,而且在山地林业生产中也获得了新的适应能力。彝族固有的传统社会组织解体后,所传习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虽然有些残缺但还基本完整。苗族则不然,其地方性知识体系遭到毁灭性破坏,大部分地方性生态知识缺失,而且仅存的部分也发生了扭曲,失去了系统性和完整性。据此,可以作出这样的总结:外来力量或外部社会环境对文化各层面所施加影响的位置越高,相关民族文化的传承受到的破坏越大。
至于外来的同一作用力为何会作用于不同的文化层面,则与相关民族的固有文化特点相关联。众所周知,从10世纪以后,汉文化已经高度适应于稻田耕作,稻米生产成为国家的立国之本。而侗族也是以稻田耕作为主要生计方式,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作用就表现为向侗族地区移民、屯垦,征收稻米作为赋税。同时,为了利用侗族地区的森林资源而鼓励其进行林木生产以满足汉族地区需要。因此中央王朝统治政策的作用点就集中于侗族文化的基础层面。这是两个民族固有文化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
彝族的传统生计方式是农牧兼营,牧场和农田的领有和稳定使用需要依靠武力去达成和维持。中央王朝不仅需要彝族提供军马,也要借用他们的武装力量。因而在最初是支持他们扩张势力,实现对周边民族的统治。但在彝族地方势力难以驾驭时,又不得不对其实施武力镇压,将其领地纳入中央直辖的行政编制之中。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改土归流”的实质所在。因此,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主要作用于彝族的社会组织层面。由于在文化结构中,社会组织层面处于科学技术层面之下,因而尽管由此诱发了频繁的政治冲突,但彝族的生态知识和技能蒙受的冲击并不大。
苗族传统实施流动的刀耕火种,生产的粮食产品种类多,单类产量少,因而社会组织规模也很小。无论是他们的物质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对于中央封建王朝的价值都不大,因而中央王朝将其视为“化外之民”,将大部分苗族地区视为“生界”,暂不纳入行政统治。对于纳入统治范畴的苗族居民,也一般施行减税或免税,仅在需要时征发其徭役。长期以来对苗族地区的搁置政策,并没有形成有利于苗族文化传承的环境。相反,这种搁置背后所隐含的贬低和歧视,在长期影响之后,造成了苗族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困惑,从而造成苗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严重扭曲和缺失。这里的歧视和贬低直接作用于苗族文化结构最上层的,即精神生活层面,因而在精神层面一旦受损,位于下层的科学技术层面当然要受到巨大的冲击。
本文讨论的重点虽然是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传承,但其结论却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比如,这一结论提醒我们,采用同样的手段去保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中肯定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同一性质的经济活动移植到不同民族文化之中,产生的经济成效也会各不相同;在不同民族地区推广统一的生态维护措施,也不能指望都会形成良好的效果。理解了文化互动后果的复杂性,并深入探讨文化的社会性适应的复杂和多变,对人类社会的协调肯定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希望学术界更多地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使我们对文化适应的认识获得更加深入的了解。
标签:侗族论文; 苗族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中国少数民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彝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