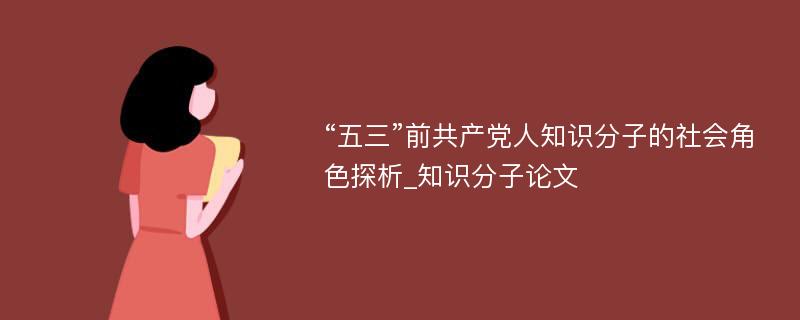
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共产党论文,角色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过去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多数偏重于整 合性的总结,或试图梳理出一套超越时间的“知识分子”概念,或建构一个逐渐走向“ 正确”的知识分子观念的形成过程。(注:相关专著有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 克思到邓小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施平:《知识分子的历史运动和作 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李子文、傅长禄等:《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的历史轨迹》,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相关论文有魏积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三次大 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2期;胡卓群、高睿:《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演 变及今后知识分子政策的展望》,《江西教育学报》1990年第2期;刘青:《党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理论的形成及其丰富与发展》,《东岳论丛》1994年第2期;李新社:《我 党知识分子工作的历史回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1期;隋云:《论中共三 代领导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2期;黄秋 富:《我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历程与经验启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 年第4期;刘吉:《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学术界》2001年第6期。) 这些研究当然有其重要的价值,不少具体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或已获共识,但这样 的研究方式多少显露出研究者预设目标的痕迹,有时也可能会掩盖历史现象本身所具有 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更重要的是,与中共对世界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其他认识一样,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知 并非一个抽象、清晰而固定的概念,它更多地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 论进程,随着中国外部环境和内部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重新认识和不断修订;另一方 面,作为认知对象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本身也未必“稳定”,与其所处的中国 社会一样处于发展变动之中。这样,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及其相应的政策,固不乏相 对稳定的一面,但也有不确定和争议性的一面,总体上的确呈现出一个“与时俱进”的 发展进程,而且仍在发展变动之中。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曾发生过多次摇摆 ”,薄一波认为,“这中间有客观上的各种原因,也有我们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中的失误 ”。(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第517页。)其实,“多次摇摆”的特点同样呈现在1949年以前中共的知识分 子观念和政策之中。在中共成立初期,亦即中共基本意识形态的形成期,党内对于知识 分子的认知就已经百花齐放。(注:遗憾的是,专门探讨这一时段中共知识分子观念和 政策的研究成果迄今并不很多,已见的有齐鹏飞:《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的理论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欧阳正宇:《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知识 分子问题的认识》,《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但既存的论文都偏于言简意 赅,不够具体;前引专著中多少都包含这方面的内容,中共领导和重要人物的传记性研 究之中往往也有一些相关的论述,可以参阅。)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急剧变动的年代,不过短短10年间,就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 久即有五卅运动,紧接着是改变中国统治权的北伐;这三大事件可以说件件打下了历史 的烙印,为所有史书必载必论。对身临其境的中共党人来说,这些改变历史的剧变接踵 而来,必然影响他们对各类事物的认知。当时就连中共所追求和正在从事的中国革命的 性质、任务和道路都还在不断重新界定和澄清之中,那些相对次一级的问题更不能避免 歧异和争论。(注:例如,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观念,是在中共内部 逐渐确立起来的,早期曾有“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和“实际上”的“殖民地”等不同表 述。参见陈廷湘:《创建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在中共成立初期,由于其成员的特殊性,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的 关联恐怕比后来更加密切,这成为中共早期一个必须处理的紧迫问题。对于这些自身就 是读书人的党员来说,对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澄清既是理论的探索,也是个人的 亲身经历和体验。(注:“经历和体验”,即汤普森(E.P.Thompson)使用的experience ,这是其对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参见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 形成》,钱乘旦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年。)实际上,在中共党内,知识分子 是一个后来才确立的称谓,早期更多使用的是“知识阶级”。(注:在多数早期文献中 ,“知识阶级”或“知识分子”多写作“智识阶级”或“智识分子”,本文使用的材料 既有保持原样的,也有一些材料经后来整理已经改为目前的用法,为保持一致,以下引 文均改为目前用法,特此说明。)
对当时的中共党人来说,知识分子是否为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先驱,以及 知识分子是否是一个“阶级”(或中国是否存在一个“知识阶级”),是得到全党(那时 党员数量不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希望凸现早期中共党人在探索知识分子与中国革 命关系时的群体“经历和体验”,即尽可能呈现当年寻求共识过程中不同观点、主张的 竞争和辩难。同时,也希望能对过去党史研究那种基本就中共论中共(涉及背景也多仅 及共产国际)的倾向稍作突破,把中共思想观念的发展置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演变的大 环境中进行考察。
一 引论:劳工神圣和学生的兴起
依照今日的概念,早期的中共党人自身基本都属于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分子这一群 体的认识以及制定党的相应政策,是与当时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思想、社会和政治变化伴 随而共生的。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倾向不能不事先稍作处理,一是清末以来、特别是五四 前后读书人的自我反省;一是五四运动后学生作为一个社会力量的明显兴起;以下即对 这两个问题进行简单考察。(注:在当时环境下,中共党人对知识分子的思考还受到不 少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共产国际和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就非常明显,而列宁关于殖民地 半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思想也直接影响着中共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位,这些因素将另文探 讨。)
(一)劳工神圣:读书人的自我反省
近年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最根本的社会变迁是“四民社会”的解体,在此 基础上出现了读书人的边缘化,而与之伴生的则是一种读书人自我形象的转变,也就是 王汎森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注: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 边缘化》,收入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第33—50页;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 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191—241页;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275—302页。本节论述特别受到王汎森先生文章的启发。)
早在清末,倾向于立宪的梁启超和主张革命的章太炎就曾互相指斥对方不道德。先是 梁氏在1904年历数革命党人的不道德行为,说当时那些“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数豪 杰,皆以道德信义为虱为毒,而其内部日日有杨、韦相搏之势”;对他们而言,“割断 六亲,乃为志士;摧弃五常,乃为伟人;贪黠倾轧,乃为有手段之豪杰;酒色财气,乃 为现本色之英雄”。(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饮冰室合 集·文集》之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40页。此条材料以及本文第一 节中许多材料,均承罗志田老师提示。)稍后章氏提出,戊戌维新失败至少部分是因“ 戊戌党人之无道德致之”,并列举“康党”受贿的劣迹。(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 》,1906年,收入张相、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北京:三 联书店,1963年,第513页。)
以梁、章二位在当时的影响力,这样的争论对读书人的形象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若 双方“道德”都有问题,士人的整体形象自然也就成问题了。更重要的是,章太炎将当 时中国人依职业分成16种:农人、工人、稗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 、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 之第次亦十六等”。且两者成反比,职业和知识愈高,道德水准愈低。(注:参见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86—287 页。)
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日益加剧,不仅梁启超指责“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 ,在民为蠹,在国为蟊”;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 是读书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注: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 )、林懈:《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均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 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 社会与学术》,第230—232页。)结果,士人的自定位逐步下降,大体可见一个从“四 民皆士”到“四民皆工”的表述谱系,且这里的“工”就是后来所说的工人。(注:详 细的论述参见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79—284、289—290页。)
1918年11月16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演说中重申“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这 一观念,并明确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他界定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 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 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 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他举出的非劳工是纨绔子弟、官吏、 商人、顾问、议员,正因有别于这些人,认识到劳工的神圣也就是作为“劳工”的“我 们”认清了“我们的价值”。(注:蔡元培:《劳工神圣》,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 》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页。)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 庶民的胜利》说,一次大战是“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 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重申“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 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而“凡是不做工而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 盗式的民族在新世界里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 当一个工人。诸位啊!快去作工呵!”(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 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0—111页。)尽管两人的表述未必是 有意识的配合,仍呈现出当时北京上层读书人的某种“共识”。
这一劳工神圣的主张正是清末以来知识分子自我反省思路的自然发展。陈独秀在1920 年5月也对劳工说:世界上“最有用最贵重”的人,不是皇帝、做官的和读书的,其实 “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因为人们吃、穿、住、行都靠做工的人,“都不是皇 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因此,“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 ,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能把社会撑住”。他正式提出将古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 于人”一语倒转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并鼓励“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 治、军事、产业”。(注: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 演说》,1920年5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135—137页。)
几个月后,陈独秀在广州又说,“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 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他希望广州青年“做 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注: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1920 年10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86—187页。)在对劳动者继续赞美的同时,他也 将“学生”和无产劳动者并列,这就提示出五四运动后一个新的倾向,即学生作为一个 社群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劳工神圣”主要是思想方面的新倾向,而“学生兴起”则 是社会方面的转折,有必要进行简略的考察。
(二)五四后学生力量的兴起
本来劳工神圣是与读书人无用的观念相随而共生的,学生虽然从清末起逐渐产生从士 大夫中独立出来的意识,但其作为读书人的一部分,仍大体分享着“读书人无用”的社 会形象,地位不一定高:叶德辉在戊戌前后即曾指责当时办新学堂已30年,结果却是“ 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长期管理北洋学堂的严复在1918年也承认,他在该校培养出 的“弟子无得意者”,仅伍光建等一二人稍可,“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注: 叶德辉和严复语皆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 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199—200页; 本节的讨论受该文启发较多,关于“学生”的独立意识及“读书人无用”的观念,并参 见同书第217—218、230—232页。)
学堂与人才的疏离意味着学生也受“读书人无用”观的牵连,但“五四”后情形则大 不同。杨荫杭在五四运动的次年即观察到“学生无事不管”的现象:“他国学生出全力 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注:杨荫 杭文刊于1920年12月20日《申报》,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 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第237页。)到五四运动两周年时,瞿世英也注意到,“五四运动一起,大家都来‘欢 迎学生爱国’。因此成功太易,学生都变成趾高气扬,以为学生万能,无论什么事,都 有‘舍我其谁’之概”。(注:瞿世英:《五四与学生》,《晨报》1921年5月4日,第2 版。)
他们所说的“学生无事不管”,其实主要是指学生对政治的积极参与,这也正是当时 学生力量的主要体现。如果说上面两人对学生参与政治多少有些保留,一般认为已经“ 落后”的梁启超在几年后的五四纪念日对学生说:“青年们啊:你要干政治,请你别要 从现状政治下讨生活,请你别要和现在的军阀党阀结缘。你有志气有魄力,便自己造出 十年后的政治土台,在自己土台上活动。”(注:梁启超:《学生的政治活动》,1925 年5月4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8页 。)
北伐前夕的梁启超不但怂恿学生“干政治”,而且倡导他们和“现状”决裂,进而创 造出自身的政治舞台以开展其政治活动。这是何等的激进!胡适后来指出,五四运动学 生群体对政治的兴趣提高,正有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各政治力量的鼓励:当时从国共两党 到梁启超所领导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予希望 ”,正因为“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人人对政治 都发生了兴趣”。(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5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3年,第184页。其实胡适自己也一直影响和试图“争取”学生,参见罗 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
胡适的观察大体准确,曾在国民党内负责青年工作的朱家骅后来也曾说:“五四运动 以后不久,青年运动的本身,又趋重于政治活动。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都在‘谁有青 年,谁有将来’的观念之下,要取得青年的信仰,来领导青年。于是青年运动,变作了 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于是青年也变作了获得政权的一种手段。”(注:朱家骅:《三民 主义青年团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1942年,收入王聿均、孙斌编:《朱家 骅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357页。)这里所说的“青年”, 应该不是泛指,而是指读书的青年,很能印证以学生为主的边缘知识分子已渐成当时中 国政治活动的一个主要力量。(注:关于边缘知识分子的界定及其在中国政治活动中的 作用,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 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35—237页。)
此前曾以《庶民的胜利》一文号召“人人变成工人”的李大钊,在五四运动约半年后 又写下《知识阶级的胜利》一篇短文,后者的篇幅虽然不能同前者比,其肯定的口气却 不亚于前者。文章说,“‘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 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在新的形势下,李大钊“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 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注: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李大钊选集》,第308页。)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来“证实”知识阶级的胜利,当年那些知识精英对“劳工神圣”的 推崇可能还会继续发展;正是“五四”赋予并“证实”了知识阶级作为“民众先驱”的 地位,李大钊并将此作为对知识阶级“意义”的界定。当然,作为先驱的知识阶级还必 须“忠于民众”,这与陈独秀把“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并列为“好到无以复加”的社 会阶级,大致是共同的思虑。这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对于理解中共早期对知识分子的 认知极具参考价值。
学生是否属于时人口中的知识阶级(或稍后的更流行的知识分子)?当年并无十分清楚的 界定,李大钊在1920年显然是持肯定态度,多数时人也基本是混同使用的。到中共成立 好几年后,中共党人逐渐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思路,才开始对“知识”的社会 载体进行进一步的区分,比如大学的师与生后来就逐渐被区分对待,而小学教师则往往 类同于广义的学生,但中学教师似乎处于两者之间,归类比较含混。学生的政治作用非 常重要而社会分类又相对模糊,直接影响到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政策。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言,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牵涉到其阶级属性问题。当年不少人是将知 识分子算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这进而牵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 (包括后来才区分清晰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所有这些理论问题在五卅运动前大致可以说仍属“发展中”的探索阶段,那时中共的 意识形态仍在形成之中。朱文显先生注意到,中共的早期文献中,可以看到有“知识阶 级”、“知识阶层”、“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等各种提法。“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 ,也有以上几种提法混用的情况”。(注: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 平》,第230页。)这一现象很能说明中共对知识分子定位的摸索状态。
二 责任和地位:早期中共知识分子观的探索历程
自陈独秀提出把“无产劳动者和学生”并列为最佳社会阶级的观念后,不少中共党人 都在探索知识分子或知识阶级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问题,且基本 上都与陈独秀的这一表述相关;说的通俗一些,即两个“最好”之中何者更好。一般而 言,对于“地位”的看法比较歧异,其间也曾出现特别强调知识阶级政治地位的观念, 即把学生置于无产劳动者之前;对于“责任”的看法则更具共识,即无论如何知识分子 都具有唤起和组织劳动者的责任。
(一)中共一大以前知识分子责任的提出
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相当能体现陈独秀把“无产劳动者和学生”并列 为最佳社会阶级的观念。报告说:“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 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这些“ 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 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这一倾向“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因此, “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以 “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二是要打消读书人“想成为学者进入知识界的 念头,促使他们参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进而“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 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2—13页。)报告的最后目标与前述北京知识界 向往成为工人的倾向相通,也就暗示了知识分子似乎有着某种先天不足。到底是知识分 子还是劳工才是引导社会的力量,即使在那时的左倾读书人中,也并不是很清楚,其中 一些人很可能同时有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而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让两者结合起来。
从前引李大钊的表述看,他在五四运动之前谈“庶民的胜利”时向往成为工人,此后 在谈“知识阶级的胜利”时则更提倡知识阶级的先驱作用。他在1921年2月又对青年说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 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注: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 月,《李大钊选集》,第146页。)同年3月,李大钊在一次关于俄罗斯革命的演讲中说 ,俄国“做革命中心的人,是工人、学生和爱自由的贵族们”,而农民革命却很难实现 。他引用了俄国文学家屠格涅夫关于“真正革命精神,只能存在于知识阶级的少数人” 的见解,认为“俄国改造社会的使命,就在少数的知识阶级肩上负着。无论如何,俄国 革命决不能靠全体的农民。少数知识阶级应该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理中”。他 进而说:历史上“少数人作牺牲,多数人享幸福,几乎成了通例。作牺牲的人多半是知 识阶级的人,知识阶级的责任真是重大,真是要紧!”(注: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 去、现在及将来》,1921年3月,《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460—461页。)
早期中共组织成员施存统也在这年春天提出,“在支那实行社会革命,最有力量的人 ,是无产阶级和兵士;然这两种人,现在都是无觉悟的,不懂社会主义的”,需要“有 觉悟的学生”到其团体里去宣传,“等到无产阶级和兵士相信社会主义的多了,然后三 者团结一致,利用机会,猛然干起社会革命来”。由于学生的“环境比一般无产阶级和 兵士好,所以就容易发生觉悟,容易感受社会主义,也便容易为社会牺牲”。尽管学生 本身“没有什么力量”,但“一加入其他团体之中,就很有力量了”。当时中国“能够 做宣传者的,大概只有学生。无产阶级是要学生去宣传的,兵士尤其是要学生去宣传的 ”。没有了学生,“无产阶级和兵士,就不能在同一主义下面联合起来”。故“学生诸 君底责任是很重大的。没有学生诸君,社会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他重申,“学生诸 君底责任真重大呵!”(注:C.T.(施存统):《我们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原载《共产 党》,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以下简作《“一大”前后》)(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9—281页。)
李大钊和施存统的年龄属于“五四”时师生两辈人,两人几乎在同时分别强调“知识 阶级的责任”和“学生诸君底责任”,大致所指皆是与其年龄层次和身份相近的读书人 ,而其“责任”也都在以思想或主义灌输、宣传到工农民众中去。因此,说当时中国共 产主义者中一些人有着类似的共识,或不为过。
当然,那时也有相对看轻读书人的见解,如蔡和森就指出:“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 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 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 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 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他要“大声唤破这种迷 梦”,因为“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薰坏的改造家 ”的理想学说,“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故社会革命与他们“全无干涉 ”。(注:本段与下段,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蔡和 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5—79页。)
但蔡和森是认为应把全世界分为无产和中产两阶级,即“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 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就中国而言,他“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 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 级的候补者”。既然中国的“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 即中等之家——次之”,故“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可知蔡和森那时的思想还 有些含糊。从其后面的界定看,前面那些“中产阶级学者”似应属于他所谓的“无产阶 级的候补者”。如果真是如此,读书人倒是很快就会实现李大钊向往的“人人变成工人 ”的目标。
不论从清末以来中国读书人自我反省的内在理路,还是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观念看,知识分子的先驱地位,都不无使人疑虑之处,故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中,就提出要“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注:这 是《纲领》的英文本内容,其俄文本语句是“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 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参见《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大”前后》 (一),第6—7、9页。)实际上,在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如何 看待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其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也颇有意见分 歧并曾引起争论。(注:这一争论在各种党史论著中都已提及,本文不再申论。关于争 论具体内容,当事人的回忆不尽一致,但大体都认可有此争论存在。参见刘仁静:《回 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回忆党的“一大”》; 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 题》,均收入《“一大”前后》(二),第113—117、207—216、286—287、375—376页 。)
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共一大上就被提出来,充分显示了它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而这 一问题一开始就出现了观点上的明显分歧和激烈争论,则预示着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 极端的复杂性。此后,围绕着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判断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党内出现长期的争论。虽然争论的具体内容、提出问题的角 度、表述意见的方式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都可以在一大前后中共党人 表述的各种观点中找到某些思想脉络上的相关性。
(二)中共一大以后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辩论
1922年6月,在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向少年中国学会提出的提案中,谈到了知识 阶级在中国的三条道路。提案说:“知识阶级在中国,只有三条道路。第一是替治者阶 级的丑行做知识上的盾牌,替治者阶级用深渊的学识,解释,辨护他们的一切罪恶。第 二是不干涉政治,任军阀残暴而不敢抵御,自己却以‘到民间去’安慰自己,间接延长 军阀统治的寿命。第三是引导少数觉悟的民众在各种事业中与军阀代表的黑暗势力奋斗 ,唤醒国人的同情。”他们的提议当然是走第三条道路,即引导民众建立联合战线,用 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注:黄日葵、陈仲瑜、邓仲解、刘仁静、李大钊、沈昌: 《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收入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 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从提案提出建立联合战线这点看,他们的 主张应该已参考了共产国际在1922年初召开的远东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精神。至少在同 年7月的中共二大会议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正式被中共确立为中国民 主革命的指导原则。两次会议的共同精神是中共要从事“国民革命”,导致了后来支持 并参与国民党事业的决定。(注: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30页。)
很可能与这一基本倾向有关,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国焘1922年底在《向导》周刊上 发表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比较系统地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 文章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 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中国完全是个农业国;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而中国农夫又“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他们“ 没有政治的兴趣”;而由于近代工业不够发达,资产阶级和新式工人的数量和势力也都 有限。(注:本段与下三段,参见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 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98—100页。)
面对官僚、军阀和更主要的帝国主义这些革命对象,“因为农人资本家劳动者都还没 有势力,所以这极少数的知识阶级在过去十几年间便为革新势力的先锋,而且他们仍然 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知识阶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 的政治经济状况造成的”。同时,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也能证明“知识阶级在 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特别五四运动“差不多完全为知识阶级所倡导”,不仅导致 中国拒签巴黎和约等结果,更“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真不亚于辛亥 革命”。
五四运动“最足为知识阶级势力的写真”,此后“他们渐能左右舆论;近来之非基督 教运动、裁兵运动、民权运动等,均足表现他们的势力”。但现在却较前“消沉得多” ,其“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为文化运动的声浪所迷惑”,不少人“相信社会改造只需 要书本上的学识和教育能够成功”,结果“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们赶回课堂”, 使“他们现在所研究的学问除了做他们自己的装饰品以外,与中国民众是无切身利益的 ”,甚至他们自己的“肚子都不能弄饱”。
既然知识阶级“自己也天天在压迫之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又造成他们在政治上 的重要地位”,他们“不可摆脱的责任”就是“切实参加解放被压迫的民众的运动”。 而且,“那时常被土匪杀戮,军阀蹂躏的农民,正等着知识阶级去率领他们出火坑;那 些压迫在外国人之下的上海唐山等处的工人们,现在是不断的向他们呼救的”。真正以 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爱国者,就应该到乡村、工厂、商店去宣传,“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 切的政治奋斗”。若知识阶级“能够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更能百折不回的努力”, 中国的革命就会得到和土耳其一样的胜利。
这应该是自李大钊提出知识阶级为民众先驱以来最为全面系统地肯定知识阶级“政治 地位”的表述,尤其开头那句中国人民中“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一语更是非常 醒目。然而,张国焘文中工农群众那嗷嗷待哺以待知识阶级去“率领”的形象既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阶级观念,也与当时提倡“劳工神圣”的中国读书人那种自我反省的 潮流不甚吻合。刚从苏俄返回的瞿秋白于1923年初在《向导》上发表《政治运动与知识 阶级》一文,部分修正了张国焘的观点。他说,五四运动以来,“看看是只有‘知识阶 级干政’,学生运动;失败是学生的失败,教育的摧残。实际上却大谬不然,政潮学潮 的根源远得多呢”。(注:本段与下四段,参见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向 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第147—148页。)
瞿秋白分析说,二十年来中国的宗法社会制度和“半自然的经济”在帝国主义入侵下 逐渐崩坏,造成了“卖国派专制派与爱国派民治派”之间的争斗,后者包括农民阶级、 工人阶级以及代表“纯粹中国的工商业”或“真正的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的商人阶级 。“双方营垒内部,正在‘阶级分化’的过程中,又各自有消长”。五四运动“不过是 此斗争中一大高潮,一大激战”。而五四运动之所以“独能成一大高潮”,即因学生和 知识阶级的作用。他同意胡适的话:“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 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
接下来他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式的环境里,——那 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现在不由得他不成为社会 赘疣——高等流氓,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这是旧的知识阶级;那‘欧风 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 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前者中官僚 最重要,是“专制派的镖师”;后者中“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民治 派的健将”。
然而“知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社会中两种政治倾向 的冲突反映出两种经济制度的倾轧:“政客不过是军阀财阀的机械,代行帝国主义侵略 诈骗的野心;学生不过是劳动平民的利器,表显中国经济要求独立的意识”。则“政客 和学生不过是双方之‘辅助的工具’”,双方各有其主力军:“一方是军阀的兵匪,一 方是平民群众”。一旦辅助的工具“不中用时,主力军就非亲自出马不可”。
瞿秋白承认,“在生产制度尚未完全发达至有绝对平等教育之可能时”,知识阶级“ 往往立于代表社会文化的地位”。但恰在这一点上,新旧知识阶级是共同的,即他们藉 以代表文化的“知识”都来自“劳动平民的汗血”。正因此,知识阶级“应当对于劳动 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学生应当更坚决而不畏缩地做“平民的先锋”。
张国焘和瞿秋白的文章表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已进入理论思考的阶段。一般论 者都比较重视瞿秋白关于平民群众是“主力”而学生只是“辅助工具”的见解,但这一 工具本身又有做“平民先锋”的责任,说明他多少分享着李大钊、施存统和张国焘关于 知识阶级“责任”的看法。其实瞿秋白更大的贡献可能是最早也最明晰地把知识阶级分 成两个部分来看待,而且在正负双方都只是辅助工具而非主体;类似的看法后来不断得 到重复,尽管后出的表述在用语上或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瞿秋白的看法已隐 伏着知识分子并非“阶级”的端倪。
(三)谁是先锋:知识分子与劳工的关系
同时,由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已进入实施阶段,中共领导人更感觉 有必要厘清革命的主力和先驱的问题。陈独秀在1923年4月正式提出,“必须认定劳动 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实际上,“此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劳动阶级不但是重 要部分,已经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了”。他对“知识阶级诸君”呼吁说,不能“单靠你 们决战的舆论和学生运动来打倒军阀”,因为“你们离了工人贫农的劳动群众便没有当 真革命的可能”。但他承认,“你们当中富于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的分子,自然在革命 运动中恒站在指导地位”。(注:陈独秀:《怎么打倒军阀》,1923年4月,《陈独秀著 作选》第2卷,第440—441页。)
劳动阶级成了“先锋”,而知识阶级却居“指导地位”,这种似乎在张国焘和瞿秋白 之间而稍偏向瞿的见解,也已显露出转变的征兆。几个月后,陈独秀明确指出,“知识 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其特性在于“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 独立的阶级”,因而“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摇动”。(注:本段与 下两段,参见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1923年10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第541—542页。)他并未明确这里的“知识阶级的学生”究竟是特指知识阶级的一部 分还是也泛指整个知识阶级,如果是后者,这可能是中共领导第一次指明知识阶级其实 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
不过,陈独秀特别说明,正因为学生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 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且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更有特殊状况,幼稚的各社会 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他认为,中 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除了少数知识阶级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饭穿衣生儿 子的行尸走肉……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尽管当时青年也是态 度各异,“真正醒觉挺身出来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
在陈独秀看来,“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的,这是何等危险!”这使他 与上述多人一样看到了青年学生的责任:“这班青年学生愈为一班行尸走肉所厌恶,他 们的责任愈加重大!”且因国情的区别,他们“责任的轻重,与欧、美、日本的学生迥 然不同”。故中国青年学生“第一要明白他责任重大,而不可自弃,这是因为国民中只 有学生比较是醒觉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 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在“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有着与欧美学生 不同的“特别职任”,即“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 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
如果说这次陈独秀关于“知识阶级的学生”实际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的提法还 有些模糊,在这年年底所写《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他进一步明确其原 来的分析适用于整个“知识阶级”。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 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 ;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注:本段与下三段,参见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57—564页。)
陈独秀再次提到了中国的特殊:从阶级观念看,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中国”;从历史 看,居于四民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 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中国的“知识阶级特别发 达”。在西潮冲击下,“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 。近年来,“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 ,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 ’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
他重申,“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 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故有时比纯粹资产阶级更易于 倾向革命。“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 ,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 地位”。但他也注意到,如果“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时, 他们也可能“放弃革命态度”。这提示出该文写作的特别背景,即中共当时正执行共产 国际决议准备加入国民党为领导的国民革命。
按照陈独秀的理解,“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 迫之下”,“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是“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 ,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而在“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 法社会的旧壳内”,同时“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 势力也都尚未强大”,体现出“一体幼稚”的共性。比较起来,“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 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故“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 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共内部和以后党史研究中都曾引起争议,争论主要在于对中国革 命的性质和工人阶级的认识。(注: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陈独秀稍早已从人类进 化的角度进行阐述,大体和本文一样,试图从理论上论证中共参与国民革命的正当性。 参见《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 446—452页。)就知识分子观而言,应该是陈独秀确立了知识分子没有经济基础因而不 构成一个独立阶级的基本观念。由于当时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尚未形成,最高领导人的意 见似乎也只是不同见解中的一种而已,故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的见解并未立刻被 大家所接受,甚至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注:到1925年6月,周恩来还在反对“知识阶级 ”的提法。他说:“中国有句话:‘知识阶级’。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也是工具,他 不生产,同时也不是掠夺别人生产而成为自己的生产的。完全不是个阶级,只可说他是 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参见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1925年6月,怀恩选编:《 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4页。)而 知识分子也已由“劳工”的“指导”者变为“各阶级间”的“连锁”。
大约同时,担任中共青年团领导的刘仁静仍在强调中国青年学生所负的“责任”。他 说,为中国独立而战的事业“不能不希望中国的青年学生”。因为“中国的青年们是中 国最有希望的一代,他们的活泼与勇气,他们的少成见而能观察事物真相的气质,都是 使他们多负解放中国国民的指导责任”。故“群众不明中国政治经济的状况与其乱源, 学生会有唤醒他的任务;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为恶的罪状,学生会有揭破及攻击的任 务”;学生会要“努力使全国国民大多数得受教育,将禁锢他们思想,阻遏他们行动的 旧习俗的枷锁一齐解脱”;更应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尽教育群众之责”,并“归结 到披露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罪恶暴行之一点”,以“使农民工人通同组织起来以临当前之 大敌”。简言之,“中国的群众不是不知革命,只是缺乏知识者去引导他们”,故“中 国青年学生们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注:敬云(刘仁静):《学生会的任务及其组 织》,1923年10月27日;《怎样打倒外力的侵略》,1923年10月30日;《中国革命之前 途》,1923年11月17日。均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 以下简作《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5、77—78、81页。)
另一方面,邓中夏则认为青年团“须绝对注重青年工人运动,相对的注重青年学生运 动”。因为学生“无经济与阶级的背景,故利害观念不一致;而且所受教育,皆资产阶 级的教育,其观念为‘德谟克拉西’主义,为‘自由主义’,为‘安那其主义’;其心 理为‘发展个性’,为‘反对束缚’,为‘好名’,为‘趣味’,为‘怯懦’,为‘怕 死’,五光十色,无样不备,这些皆与吾人主义与革命精神根本冲突”;而“青年工人 则无青年学生之病”。(注:邓中夏:《讨论本团以后进行的方针》,1923年6月,《邓 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从1923年底起,他以系列论文讨论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农民、兵士三种群众,但 与前引诸位对于“责任”的观念一样,他也主张这些“主力”仍需要读书的“我们青年 ”去宣传和组织。在他看来,当时“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 觉和组织起来”,即因“我们青年只在文章上和电报上空嚷,并未到这三个群众中去做 宣传和组织的工夫”。故青年应该大家都“到民众间去,完成我们重要的光荣的使命” 。他甚至明言:“我可敬畏的青年呵!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几天 后,他又对“亲爱的青年们”补充说,中国革命的重担,“我们挑着不可放下呵”!(注 :按邓中夏所说的“青年”或“我们青年”,当时更多指学生或“知识青年”,如他说 “打倒满清的‘辛亥革命’,是我们青年干的;打卖国贼的‘五四运动’,也是我们青 年干的”。参见邓中夏:《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1923年12月 8日;《论工人运动》,1923年12月15日;《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1923 年12月22日;《论农民运动》,1923年12月29日;《邓中夏文集》,第39、41、44、51 页。)
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知识分子不是阶级的观念已经非常明晰地提出。基本上,到192 3年底,工人、农民为中国革命主力的共识已经达成(即使在陈独秀说工人阶级只是革命 的“重要分子”那篇文章中,他也说到商人、工人、农民已“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 ”),但既然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肩负着唤醒主力的“责任”,或起着陈独秀所说的“ 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甚至一肩挑着“中国革命的重担”,则其在革命中的主导地位 并未受到太大的挑战。
到1924年2月,李大钊提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 无产阶级。”(注:李大钊:《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1924年2月,《李大钊选集 》,第499—500页。)虽然这是为纪念二七罢工而说,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但此语由过 去希望“知识阶级作民众先驱”的李大钊说出,终提示出某种态度的转变。如果工人阶 级或无产阶级逐渐既是革命的主力也是先锋,知识分子又居于何种地位呢?
(四)做革命的民众仆人
周恩来在1924年2月分析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敌人和友人,他列举了五派“中国国民运动 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第三派的知识界“自从五四运动后,顿呈活气,中间虽因 受新文化运动中的恶影响消沉了两三年,但近一年来又复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 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他相信工人阶级“终将为国民革 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但其最先列举的“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却是海外华侨。(注 :周恩来:《革命救国论》,1924年2月,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3—446页。)此时他虽最肯定工人阶级,但似乎寄希望 于以后。
两个月后,恽代英在讨论“革命的基本势力”时明言:“我们所应当依赖的,必须是 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他同时明确地表达了“知识阶级不能依赖”的看法: 由于知识阶级“欲望是大的,虚荣心亦比较利害”,故其既有“特别肯为国家与国民的 利益努力”的一面,也有“很容易被诱惑,很容易被收买”的一面。“他们自己没有经 济上的地位;虽然他们在恶劣的政治经济中间,亦要受许多窘迫,然而他们并不一定与 统治阶级的利害相冲突。他们有时受了军阀或外国势力所豢养,亦会变成他们忠顺的奴 隶”。(注:本段与下段,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1924年4月20日,《恽代 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9、504—505页。)
恽代英承认,历史上“凡倡导革命的人,每多出于中产之家”。因为他们比农工多受 教育,“所以他们的知解与想象力,都比较的发达”。同时其“所受生活的压迫,有时 与农工不甚相远。这使他们中间气质厚重的,不能不感觉革命的必要。在这些人中间, 每可以产出几个革命的好领袖”。但“能成为强有力的革命领袖”的仅是少数个人,却 不可能“化他们全阶级成为革命的”。在革命势力已经得势时,他们也许会“全阶级随 风而靡”;此时也只“可以利用他们”,而“不能靠他们做基本势力”。同时,不能因 为中产之家产出几个革命的好领袖就“忘却农工群众而迷信他们个人的力量”。革命领 袖“最大的事业,便是去唤醒而组织农人、工人”,只有这样,“才可以得着切实的革 命力量”。
这一关于革命领袖和农工群众的关系大体仍类似李大钊所说的先驱与后盾的关系,但 已明显偏向后盾一边了。不过,那时中共内部似仍存在主要做读书人工作的倾向,恽代 英感觉有必要说明:“我们现在努力的对象,不单是知识阶级;光是知识阶级的觉醒, 不会做出怎么了不得的成绩来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便是这个意思。我们 现在要向田间去,要向农民社会里去,要使一般农民觉醒;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 业便是哪一天成功。”(注:恽代英:《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努力?》,1924年4月27日,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11页。)
同年6月,李求实仍肯定青年学生是“革命的酵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今后的革 命必须建筑在民众的基础上;大家都知道在目前能负这个使命而且负到民众间去的,只 有我们青年学生”。但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必须“切实地以民众为中心,对于民众表示 着‘我是为他们而革命’,而且还叫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亦只是为自己而革命”。他强调 ,“我们革命中青年在今日所应持的唯一态度”是认识到“我不是一个革命的知识者, 我只是一个革命的‘你们民众底仆人’”。(注:匪石(李求实):《革命中学生应持的 态度》,1924年6月14日,《六大以前》,第142—143页。)
李求实的观念中仍隐约可见前述各位所说的学生之“责任”,但“革命的酵母”加“ 民众底仆人”似乎已比瞿秋白所谓学生一身兼平民的“辅助工具”和“平民的先锋”略 逊一筹,更远不能与邓中夏提出的青年学生一肩挑着中国革命的重担相比。到1924年11 月,邓中夏自己的观念也有所变化,他仍然看到知识阶级因自身所受经济压迫而“趋向 于革命”的一面,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 革命之中心人物,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便是其证”。(注:本段与下段,邓中夏:《 我们的力量》,1924年11月,《邓中夏文集》,第98—102页。)
但这些知识阶级为革命中心的例证皆是已逝的“历史”,其实已提示着“现在”和“ 将来”未必如此。邓中夏斩钉截铁地说:“老实说罢,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 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他不点名地反驳了陈独秀这一 “笃信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家”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论在数量上和在质量上都还很幼稚 的“理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 国民革命的领袖”。同时,无产阶级还要“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 成一个革命的力量”,以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这样, 似乎“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也由无产阶级来承担了。
张太雷的看法略不同,“在过去的历史和现时各殖民地上的国民运动”中,他“看见 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常常积极地参加这种运动,并且他们亦是这运动不可少的分子 ;他们并且是常居领导这种运动的地位”。中共或青年团“要使他们知道没有农民工人 的参加,国民运动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有指示给他们怎样到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宣传 和组织的责任”。他也注意到知识阶级无独立的经济基础而可能常反革命;不过,青年 学生就“比较富有革命性一点,其中往往有少数参加革命运动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尤 其殖民地上青年学生,格外地趋向于革命”。(注:本段与下段,张太雷:《中国革命 运动和中国的学生》,1925年1月,《六大以前》,第228—230页。按与此文内容基本 相同而题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的文章曾于1924年7月发表于《少年 国际》,收入《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55页。)
尽管青年学生也不能免于知识阶级的动摇性,但“证之各国先例,在无产阶级运动刚 开始的时候,青年学生常常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他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去唤醒他 们起来奋斗和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正在起头,并且中国农民的觉悟还很少,所以能够得到一班中国知识阶级来做‘往民间 去’的运动”,则“对于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大有补益”。尤其“现今中国目 前的政治运动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运动;所以我们有极力领导中国学生参加这运 动的必要”。张太雷还承认学生在国民运动中常居领导的地位,在当时共产党人中可能 是最正面的了。
到1924年底,彭述之提出:“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虽然是混合各阶级的力量而进行 的,然而必得有个主要的进步的阶级作中坚,作领导者,才能使各阶级的意识比较集中 ;各阶级的力量集中,不致为某一反动阶级的私利所乱,才能引导革命的势力到目的地 ,彻底的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他看来,“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 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 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注:本段与下段 ,参见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新青年》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第1、13—14页,本文所用是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彭述之注意到中国国情的特别:与欧美资本社会里知识阶级“常是反革命的”不同, 中国知识阶级“除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军阀所雇佣,资产阶级所役使以外,差不 多都有几分浪漫的革命性,它们大概虽是资产阶级的心理,但它们实受帝国主义的侮辱 (在知识阶级看来),受军阀的冷视(军阀不用它)与摧残(如学校学生和教职员之要求教 育而被打被驱逐甚至被杀就是),所以它们也很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很赞成国民革命 ,并且有时还很激烈地参加革命”。但即使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深的“知识阶级之左 派”,也“必然要受工人阶级之领导,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底下去活动”,才可能推翻帝 国主义与军阀。(注:不过,彭述之在1927年5月的具体表述似更正面一些,其中“反革 命”的成分从这次的“一部分”改为“极少数”,而“学生和中小学的教职员”的倾向 革命则得到更多的强调。他指出了知识分子有其特别的长处,故“中国的知识阶级在中 国革命中便自然而然占了重要的地位,有他特别的使命”。参见彭述之:《中国革命的 根本问题》,1927年5月,《六大以前》,第779页。)
在中共当年的认识中,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多阶级革命,在这样的 革命之中也只有工人阶级是领导者,这一提法后来发展成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观念 。这样,谁是先锋的问题或不再重要,或改变了含义:如果是作为被领导的先锋,就是 另一回事了。
(五)五卅前后的新变化
国共合作的大政治形势影响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认为 ,中国解放运动的进程“要求我们与劳动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之关系日紧一日。因此 ,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 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注:《(中共四大)对 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9—380页。)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明显将“革命的知识 分子”置于比“有政治觉悟的农民”更优先引导的位置,会议特别指出:“殖民地运动 中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注:《(中共四大)对 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6页。)
然而,过去青年团的“大部分同志不明白学生运动之意义与重要,以致学生运动策略 多有错误”,结果是“学生运动的无进步”。其实,“学生在目前政治运动中,是重要 的推动力”;而“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注:《(中共四大)对于青年运动之 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68页。到1926年1月,中共中央仍认为“ 过去全国学生运动,完全由团负责指挥,这是我们过去看轻学生运动的错误”,故“以 后各地学生运动由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 告》,192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页。)几年前李大钊提出的把 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主张被确立为学生运动的最要目的,但学生仍是宣传者 和组织者,工农的地位得到充分凸显,而学生的主导作用也得到肯定。
总体看,中共四大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似比前引一些中共骨干的看法尚 更积极正面,且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或者意味着中共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初步形成 共识。后来的发展表明,在确立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中共既强调发展工人党员 ,也要求继续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入党。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对其 北京机构未能吸收更多读书人表示了不满:“北京是中国知识阶级之大本营,在北京实 际的政治运动,我们不能不看清知识分子是目前的最大动力。北京方面未能得着相当数 量的知识分子党员,乃是一个缺点。”(注:《京区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1册,第496页。)
不过,五卅运动以及省港大罢工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注: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1926年1月,《瞿 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3页。)尽管中共也 从五卅运动中看到学生的力量,如1926年7月的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在民 族革命运动中,革命的学生算是一种重要的成分,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可以看出。 ”但会议也明确了学生重要性的位次:“今后‘国民的联合阵线’,工人农民之次,便 算学生是重要成分。”(注:《学生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2册,第221页。)这与中共四大把“革命的知识分子”置于“有政治觉悟的农民”之 前又已不同了。
正是五卅运动实质性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彭述之在1927年5月即说“从 辛亥革命起,经过‘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革命 中所表演的作用,都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他们“在每次的运动中差不多都站在革命的 前线、先锋、领导的地位”。但接着又说,“就是在‘五卅’中,虽然工人已经起来站 在领导地位,但上海及各地的学生,是站在革命的左线,与工人合作”。(注:彭述之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1927年5月,《六大以前》,第779页。)两说关于“五卅 ”显然有些矛盾,可知前面或是习惯性的表述,一旦“工人已经起来站在领导地位”, 学生就成为“合作”者了。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瞿秋白指出:“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 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根据瞿秋白的论述,罗志田先生指出:这 使五卅运动显出分水岭的意义,“正是‘五卅’体现出的划时代转变把‘五四’推入已 逝的往昔”。(注: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 003年第4期。)在大家争言阶级斗争的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得到凸显,后来的中 共党人基本都要区分知识分子中革命与不革命的部分,其中革命知识分子仍可能具有先 锋的作用。
三 余论
如本文开头所说,中共早期对知识分子的认知,颇有不确定和争议性的一面。出于中 国特有的国情,即陈独秀所说的长期居于四民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五 四运动后学生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无产阶级最具革命性的观念在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确立是有个过程的。同时,从清末开始的读书人自我反省,以及民初逐渐得到 推崇的劳工神圣的倾向,为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阶级,革命主力甚至革命先锋的观念 埋下了伏笔。
也许因为革命领导阶级的问题已经解决,部分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不再与无产阶级形 成一种竞争关系,因其具有新的含义而基本为中共所接受。1927年春召开的中共五大指 出:“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 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 合在一起。”这里似隐约可见陈独秀关于无产劳动者和学生是“好到无以复加”的社会 阶级这一早年观念。“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亦即“阶级性不确定者”在工农 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已得到确认。(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 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96—97页。)
中共主要领导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继续肯定知识分子“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 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他认为,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19 35年的一二九运动,都是“明显的例证”。当然,他也指出对知识分子应区别看待,其 中“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在此基础上, 毛泽东断言:中国“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 是不能成功的”。(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 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36、613页。)
一般多看到工人作用的五卅运动,在毛泽东眼中却是知识分子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的 显例,与1926年中共扩大执委会把革命的学生算作五卅运动中“一种重要成分”相比, 其地位似更高,这再次揭示出当年知识分子在中共党内的潜在重要性。北伐前夕中共曾 试图退出国民党,所持的一个理由即“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实质上是知 识分子反对派”。(注:参见古比雪夫(季山嘉)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信》,1926年1月,转引自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 》2003年第4期。)而曾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的米夫稍后也认为,“中共机会主义”的 社会根源即因“共产党领导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都是那些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时加入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底代表”。(注:米夫:《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28年6月,《六大以前》,第974页。)
尽管米夫的表述有其特定用意,他的观察似不算错。瞿秋白曾说:一方面中国无产阶 级“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 、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 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 ”。由于革命实践的急切需要,“‘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 义者的情形”。他自己从1923年回国后就一直在“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 注: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2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其实“以狗代牛”恐怕不仅指知识浅薄,它同时也有社会的含义,即无产阶级的“思 想代表”本身的社会存在并非无产阶级。这一思想和社会的特殊结合对多数早期中共党 人来说恰是他们的个人经历,处处证明着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思 想和社会的不同步使得中共党人容易反求诸己,他们不能不常常看见、反思、甚至激烈 批判知识分子那“软弱”和可能“动摇”的一面。(注: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恽代英主 动要求接受下层阶级的监督:“如要问我亦会有时‘出卖’救国事业么?我决不昧着良 心嘴硬,我每到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便总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为要保证自己 ‘不卖’,亦只有努力求党的纪律加严,下层阶级监督力量的发展”。详见恽代英:《 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1925年7月,《恽代英文集》下卷,第687—688页。)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李大钊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陈独秀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