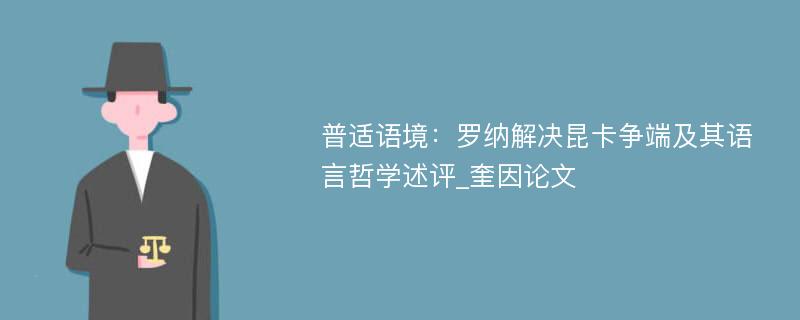
万能的“语境”——劳纳对“奎卡之争”的解决方案及其语言哲学特点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语境论文,之争论文,哲学论文,解决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瑞士哲学家劳纳(Henri Lauener,1933.7 —)现为瑞士伯尔尼大学哲学研究所主任。他的名字可能还不太为中国哲学同行们所熟悉,但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在瑞士而且在欧洲和美国已受到广为关注。近几年劳纳一直关注分析哲学中被称为二十世纪哲学家们的“职业病”的“意义与指称”理论,尤其是发生在奎因和卡尔纳普之间的有关论争,并提出了自己的严谨的、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根据劳纳的《本体论问题》〔1〕和《为何要区分分析与综合陈述?》〔2〕这两篇文章介绍劳纳对“奎卡之争”的分析及其解决方案,并对这一方案中体现出来的劳纳的哲学思想即他的语言一元论思想加以评述。
(一)
为了便于理解劳纳的思想,我们先对“奎卡之争”作一个扼要介绍。
对于科学语句是否可以分为理论陈述和经验陈述的问题,在分析哲学中被称为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区分问题。“奎卡之争”的焦点也就在于,卡尔纳普坚定不移地主张分析与综合的严格区分是可能的;而奎因却给予否定的回答。由于卡尔纳普认为,陈述句的意义部分即分析陈述可以不依赖陈述句的事实部分即综合陈述而存在,因而他在《意义与必然性》中从形式语言的构造上精心区分了指称式的上述两种不同的用法,并通过所谓“分析确定内涵”构造了他的所谓纯粹内涵语言(如S[,3] )〔3〕。这当中,卡尔纳普对分析真又作了区分, 一是逻辑真,它被定义为在所有状态描述中都成立的语句;另外还有一种所谓内涵同构或“同义”问题,它是比逻辑真更强的分析真,但它在卡尔纳普那里仍然可以还原为逻辑真。([3],p.59)(注: “内涵同构”被卡尔纳普看作谓词指称式的分析真。但他将其建立在以状态描述为基础的分析真上,实际上要求事先能判断状态描述的谓词指称式是否同义。这是语义问题而不再是如逻辑真那样的语法问题。因而卡尔纳普将“内涵同构”还原为逻辑真问题受到奎因的病诟。按卡尔纳普的定义,逻辑真原本并非仅指语法真(重言式),但卡尔纳普的解释却似乎仅限于语法真,而且又提出“内涵同构”问题,即语义真,这就使逻辑真的内涵缩小了。)就在这里,奎因找到了反驳的突破口。
奎因对卡尔纳普的逻辑真没有提出异议,比如“没有一个未婚者是已婚的”是必然真的。但他对卡尔纳普建立在“内涵同构”基础上的“同义”概念提出了异议,比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并不是必然真的。奎因指出,卡尔纳普的状态描述的分析性标准仅仅适用于那些不含有像“单身汉”和“未婚男子”这一类非逻辑同义词对子的语言,(卡尔纳普自己在提出“分析确定”时也认为它是仅仅与逻辑指称式分析等值的指称式,而谓词如“单身汉”、“未婚男子”则属于非逻辑指称式),([3],p.88)否则, 对一个含有非逻辑指称式的状态描述进行真值分配就会出现比如把“真”分配给“约翰是单身汉”而把“假”分配给“约翰是未婚的”这样的情况。因而“同义”问题在卡尔纳普那里并没有解决:本来“同义”概念要依赖于分析真,然而现在分析真则要依赖于“同义”概念。这是一个循环。因此,卡尔纳普想把内涵与外延严格分开,仅仅依靠语言规则来确定“分析真”、“同义”、“内涵”等概念是徒劳的。
为了回答奎因的质疑,卡尔纳普在《意义与必然性》第二版增补部分提出了所谓“意义先设”(meaning postulate)概念。 卡尔纳普认为,他是在一个形式语言而不是自然语言基础上来讨论分析问题的。因而他就完全可以在约定主义的立场上来人为地规定上述的非逻辑指称式之间的关系。例如卡尔纳普说,对于下述两个公式:
(1)BaVBa和(2)Ba→Ma
而言,(1)式是逻辑真,即它在任何状态描述中都真,或者说,不论“B”具有什么经验含义,它都为真。而对于奎因提出质疑的(2)式,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意义先设P[,1], 即规定它在语义层次上的非蕴含关系,并且也在任何描述状态中都真:P[,1]“(x)(Bx→Mx)。”那么它就变成分析真的。([3],p.224)但卡尔纳普认为,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假设B=单身汉,M=已婚的,但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断定P[,1]即“所有的单身汉都不是已婚的”是经验上真的, 就要根据人们怎样实际地确定“单身汉”(B)和“已婚的”(M)的经验意义而定。(卡尔纳普因此而发展他的归纳逻辑。)如果有人在实际使用这两个词时,其经验意义总是不相容的, 那么,P[,1]在他那里就是一个成真的综合陈述。总之,分析问题包括同义问题是一个语义上的约定而已;而综合问题则要取决于经验意义。
然而,奎因对卡尔纳普的这一方法同样提出了质疑,他的问题是,在上述的“意义先设”和经验意义之间进行严格区分究竟是否是可能的?([2],p.132)这就是说,一方面,一个实际的经验意义的表达事实上是依赖语言的,以至于上述的P[,1]既是例如某个形式语言L中的语句(分析陈述)也同样是这一经验意义的表达式(综合陈述)。如果是这样,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呢?另一方面,意义先设(x)(BxMx )的真值并非直接受某种经验事实的检验,而是受所谓“全理论”的支配,这样所谓意义先设受经验的检验就成了问题。在奎因的整体主义观点中,由于语言和理论一起作为一个唯一的整体出现,从日常用语到高度发展的科学语言都只是在一个整体中连成一片,因而受经验检验的只是作为整体的语言和理论。为了对付这种漫无边际的整体主义,卡尔纳普提出所谓“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的区分,即“外部问题”是对形式语言变元的整个定义域(即范畴)提出存在问题,而“内部问题”则不涉及变元的整个定义域。([3],p.206)如语句(ヨx)(Hx∧Mx)在“内部问题”中就意味着我们已接受了一个“事物世界”(the world of things)作为框架,这里比如是“人”的世界。 因而该语句即“存在某个人且不是已婚的”对于这个框架内的经验描述而言是综合的;而对于其中的语义系统而言则是分析的。但该语句在“外部问题”中,就依不同的哲学选择而有不同的回答了(这时该语句变为(ヨh )—Mh)。比如实在论者给予肯定的回答,而在唯名论者那里就是假的。因为前者认为有“人”存在,而后者认为并不存在“人”,只存在“张三”“李四”等等。这样,整个语言框架也就以不同的参照系而不同了。(“外部问题”是在元语言层次上的“综合”问题,劳纳意识到这实质上是一个形而上学实在论问题而予以否定。具体见下文。而卡尔纳普则认为这只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但是奎因总是有理由。他认为这一区别对于一个只含有唯一变元类的语言来说,就不复存在了。比如我们假定我们的语言只有唯一的自然数这一个类,那么所谓“外部问题”比如“存在一个数,它大于1 和小于2”是与“内部问题”如“存在x,如果它是自然数, 那么它就大于1和小于2”是同样假的。(即“(ヨn)(1<n<2)”与“(ヨx)[Nx→(1<x<2)]等值)。也就是说, 在这种只含有唯一变元类的语言中,“外部问题”可以毫无区别地转变为“内部问题”,反过来也一样。([2],p.134)这样卡尔纳普想用“内外”之分来支持“分析与综合”之分的作法还是被动摇了。
上面只是对“奎卡之争”的挂一漏万的概述。这一争论还在不断趋向复杂化和技术化,而且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卷入其中。应该看到,“奎卡之争”不只是一个语言或逻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哲学问题。劳纳也正是在这点上把握了“奎卡之争”的实质,在较高的哲学层面上而不是从一些语言或逻辑的技巧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二)
对于劳纳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我们应首先从两个方面把握其哲学内涵。
第一,从劳纳在《为何要区分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中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相对论思想,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奎因的《本体相对论一文对劳纳的影响是基本的。劳纳本人也多次提到奎因这篇文章。《本体相对论》所表达的主要观点就是与语言相结合的相对主义的本体论观点。劳纳在这里获得的灵感就在于:由于相对主义是对某个特定的语言系统而言的,因而这种语言不是如在卡尔纳普那里建立在“语形——语义”(或广义的“语义”)基础上的一般形式语言,而只能是一种“语境”——一种与语用学相结合的完全具体的语言。
只有这个“语境”才能是真正“相对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基础。劳纳说:“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本质上依赖于它在语境中的使用,因此只是像卡尔纳普那样简单地注意到语形上和语义上的规则是不够的。我们此外还需要语用学的规则,它根据特定的目的来规定表达式的用法。”([2],p.135)(对“语境”概念的分析见下文)。在语境如Ln中的所有语句相对于另一个语境L[,n+1]而言时, 它们就从分析陈述变为综合陈述,而且这一区别是绝对清晰的。事实上,当卡尔纳普提出“内部与外部问题”时,正是对奎因《本体相对论》中的这一思想的让步以及对自己当初的“一般内涵语言”的纠偏。但是,奎因的失误在哪里呢?由于奎因本人并不满足于《本体相对论》的那种多元论的本体论思想,他在后期就日益倾向一种唯一的、无所不包的语言——全语言(或全理论)(注:按照陈启伟先生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中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的观点,奎因的本体论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唯名论到概念论,又倾向于共相实在论的过程。劳纳在《为何要区分分析与综合陈述?》一文中,将奎因的立场区分为早期的相对的语言本体论和后期的全语言本体论。按笔者的观点,奎因哲学中的这一严重矛盾主要来自于他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并且伴随他的整个哲学历程。这就解释了令陈先生“颇感困惑”的奎因在后期关于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主张抽像共相的实在论者”的表白。但本文仍按劳纳的看法行文。)。劳纳称之为极端的整体主义。它违背了当初的相对论思想而重新寻找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并同时走向自然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劳纳就坚定地站在卡尔纳普的约定主义以及奎因早期的相对论思想一边,指出奎因这种极端整体主义实际上导致了诸如“物理实在论”之类的形而上学。由于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只承认某个唯一的语言,所有的语句都只对于它而具有意义,而所有与之竞争的其他语言都被消灭殆尽,因而语句的意义也就不可能有相对于其他语言发生质的变化的可能,其结果是分析与综合陈述的区分只能降格为“量”的变化。因而劳纳认为,奎因与他的主要区别在于:“奎因假设了一个单一的、普遍的语境;而他则允许界线分明、多元的语境,它有利于多元化世界的观点。事实上,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也可看出,当奎因用这种极端整体主义对卡尔纳普关于经验含义与意义先设之间的区分问题提出质疑时,卡尔纳普又用“内部与外部问题”作为一种相对主义武器来抵挡奎因。而当卡尔纳普试图在语义层次上对分析与综合陈述作出绝对区分时,奎因又用相对于一个语言系统的统一意义理论来使之受挫。因此,不论是卡尔纳普还是奎因,他们的失误都在于偏离了他们自己提出的实用主义的相对论。因而劳纳吸取了他们的教训而牢牢地把握住彻底的实用主义。但要达到“彻底”,劳纳还必须采取另一个步骤。
因此第二,在奎卡之争表现出来的问题中,劳纳敏锐地注意到,他们二人都没有真正解决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既要以负责的态度解决它,又不能落入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窠臼。卡尔纳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建立语义规则,以便使一切存在都是可检验的。但是这一方法有两个致命的缺点:一是概念如“电子”等等都是直接依赖于语言的,它们只是以非常间接的方式在经验描述中被保证,因而我们事实上无法最终检验它们是否存在(这就是奎因提出经验含义与意义先设之间严格区分的不可能性);二是卡尔纳普把采用某种语言与实际上相信它(以及它所包含的那些被约定的“事实世界”)区分开来,这被劳纳视为是在本体论问题上“赖账”的表现,是极不负责的。而在奎因那里,由于他不满意于多元的相对主义本体化,因而本体论问题就只有在极端的整体主义的“全理论”中被最终确定。比如“物理实在”:它本是一个“全理论”,但由于它是一个“唯一”,因而就等同于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抽象物。(这就是卡尔纳普所批评的将“外部问题”与“内部问题”的混为一谈。也是劳纳所批评的自然主义态度。)除此之外他只能求助于某种主观的意义来源如“行为主义”、“前理论概念”等等。因而劳纳说:“由形而上学实在论导致的棘手问题,是不能通过把基础建立在语言上,或者把基础建立在科学全理论上来解决的。”([2],p.135)前者是卡尔纳普的方法;后者是奎因的方法。为了克服奎卡二人的缺陷,劳纳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放在语言的内部来解决,而把语言之外的实在论(本体论)彻底排除掉。这样,卡尔纳普的经验含义与意义先设都是语言内部的差别,采纳某种语言也就等同于相信它所包含的“事物世界”,同时奎因的唯一的“全理论”的实在也被否定了。
劳纳认为,要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实用主义相对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也就是解决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区分问题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就是建立以“语境”为核心概念的实用主义的相对先验论哲学。
劳纳接着阐述了他的“语境”概念,并分析了它的特点。他说:“按照我的实用主义的相对先验哲学,我们必须赋予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我们对其想要描述和解释的世界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概念结构。借此我们就可按不同的语境来这样规定一定的本体论,使得存在物及其基础部分仅仅相对于所运用的理论而存在”。([2],p.136)(重点句即黑体字由本文所加)很显然,劳纳的“语境”概念已经将上述奎因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和卡尔纳普的“内部—外部”之分兼收并蓄了:整体的单位不再是“全理论”而是“语境”,“内外”之分也只相对于不同的“语境”而言。劳纳用“语境”概念不仅试图解决“奎卡之争”,而且试图彻底解决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劳纳大致从下面四个方面分析了“语境”的含义。
第一,“语境”概念将所谓“实在”完全排除在语言哲学之外。劳纳说:“我的先验方法的特点是,它要求真理概念建立在语境上,因而对于‘真’则作为纯粹的内部概念来处理”。([2],p.137)劳纳这是针对奎因的自然主义的“实在”观点而言的,这种观点即使断言别人的本体论都只是语言内部的一种承诺,但认为其自身的理论却仍然具有外部真理。劳纳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存在一个与奎因在概念上完全不同的理论,那么二者之中究竟何者为“真”呢?如果奎因不相信有一个中性地被给予的事实能够检验理论,他就只有承认这两个理论都是真的(即实在的)。正因为这个两难问题,奎因就从早期的“内部观点”渐渐变得犹豫不定了:他不得不提出所谓“前理论概念” (pre-theoretical notion),它基于说话者说话时的肯定或否定(意向)。(比如:“雪是白的”是真的仅当:雪应是白的!这是所谓“单词句方法”(holophrastic approach)。 )奎因的这一倾向在戴维森那里发展为极端的“无根的实在论”。〔4〕 劳纳对奎因的这种解决方案表示不满。因为奎因的“前理论概念”仍然是“实在论”的残余。劳纳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干净彻底根除语言的“外部真理”,而不是去寻找一个来代替另一个。他说:“我认为,考虑到所有这些令他们越来越棘手的困难,我主张这样一个方法,在这个方法中彻底排除有关外部真理的问题,并且只满足于内部概念。”([2 ], p.137)这样,在一个语言系统中,所有根据语境(它本身是语言的)而进入语言的公理、定理等都被作为(truth by fiat )先验的即分析的命题,而由于这一“先验论”不同于康德的绝对先验论而只是与语境相关,因而劳纳称之为“相对先验论”。
第二,“语境”是完全具体的和多种多样的。“语境”需要语用学,因而在不同的理论中,同一个语项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意义,比如“火箭”一词对于一个宇航专家来说其意思就非常不同于一个外行。这种不同是因为“语境”对语言系统的选择和描述有非常具体的内容,这与卡尔纳普的形式系统是不同的:“语境”要求给出有关行为目的的陈述,有关作为前提的背景知识的陈述,有关被接受的理论及其逻辑或数学知识的陈述,有关设定的本体论(变元的值域)的陈述,有关谓词词库及其外延的陈述,甚至语言的时间上的确定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完全具体的规则。这似乎十分接近奎因的“全理论”(如上所述,事实上劳纳受到奎因“全理论”整体主义的影响),但是劳纳认为在他与奎因之间唯一的和结果完全不同的区别在于:奎因只设立一个唯一的“全语境”,而他自己的哲学则允许一个多种多样的、彼此之间严格区分的语境。后者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图式。
劳纳认为,在奎因那里,由于语言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而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设的语言都成了一个全语言的内部问题。这些不同的语言互相连续地、量变地连成一片,哲学家如果要描述这样一个全语言,就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者”。劳纳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认为应该在严格区分的各种不同的语境基础上采用一个被限定了的整体主义方法,即根据实用主义原则确定语言行为目的,这个目的给出一个相对的语言整体——语境。因此,劳纳说,如果奎因曾把“全理论”看作一只永不靠岸的、只能自我翻修的船(纽拉特(Neurath)语), 那么他自己则把语言看作一个由多艘根据不同目的而建造的船只组成的舰队。([1],p.90)
第三,“语境”说对分析—综合问题的相对论解决。劳纳认为,通过一个语境的确定我们就解决了分析—综合的区分的问题。对某个语境的内部而言,一个语境不仅服从一定的目的,而且也实际上接受了相应的逻辑和语言上的规则,这些规则将相应的指称式视为分析的,或者只是从分析到综合之间的某种量的区别。这种被特定的语境所决定的分析,就是劳纳的所谓“相对先验论”。但对不同语境而言,由于分析只相对于特定的语境,因而同样的指称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时是分析的有时是综合的,这是一种严格的、质的区分。因为分析真理不再是如奎因所讽刺的那样用一个“精神的望远镜”在一个“意义博物馆”里搜寻到的,而是完全由语境生产出来的,因而句子是否是分析的(抑或是综合的)就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语句“不存在同时是红的和绿的表面”在心理学语境中是综合的,而在日常语言中则是分析的。脱离具体的语境则很难对此作出判断。劳纳强调指出,这样一种关于分析的看法与柏拉图主义的存在物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即使逻辑和数学也不是什么纯分析的领域,比如公认的经典一阶谓词逻辑并不是因为它具有客观的(即一成不变的、纯分析的)真理才被广泛使用的,而是仅仅因为它对许多领域都十分实用。
第四,“语境”说主张直觉主义约定立场。“语境”是约定的产物,因而约定如何起作用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涉及到劳纳方法的基础。奎因曾在《约定真理》中认为,逻辑是不能靠约定来支撑的,因为约定只是一种定义,它只能重新表述真理,而不能证明真理。逻辑在约定之前就是具有意义的,否则我们就陷入了自我循环:逻辑是靠约定来建立的,而约定又靠对逻辑的理解来进行。奎因是这样来理解约定的:“对所有x,y和z而言,如x和z是真的,而且z是在‘如果p,那么q’中x 替换p和y替换q的结果,那么y真”,用公式表示:
(x)(y)(z){x∧z∧[z←→(p→q)∧x=p∧y=q]→y}
奎因要表明的是式中的两个蕴含式的意义:如果我们对(p →q )中的“→”不理解,也就无法约定{…→y}中的“→”的含义。
然而劳纳认为,“约定”并不是像奎因理解的那样“从逻辑到逻辑”而起作用的,约定起作用是以“从直觉到逻辑”的方式进行的。他说:“语义学的每一形式都以在元语言层次上的一个关于逻辑项的直觉理解为前提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实际上能够通过所谓语境定义在对象语言中准确地规定对它的运用。规则的表述必须能够使意向含义的重要特点得到反映。”([2],p.139)这种“从直觉到逻辑”的方式不像定理那样从一定的前提推出结论,而是作为一个暂时接受的规定,它产生出语言字面的真相。联系上述第二点,可知这种直觉就是一种完全具体的约定。这一直觉把奎因讲的循环给排除了。(事实上,奎因的“逻辑意义在先”是与他的整体主义相矛盾的。)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劳纳在实用主义基础上接受了卡尔纳普的分析—综合的区分,而克服了卡尔纳普只着眼于语义规则的做法;同时他也在限定的意义上接受了奎因的整体主义思想,而克服了其对分析—综合区分的否定倾向,从而创立了他所谓的实用主义的相对先验论的语言哲学。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将外部的“实在论”彻底排除,而代之以他的“语境”概念,并让“语境”承担起本体论的重任。他说:“在我看来,我所主张的观点具有这样一个优点,这就是它在一般的本体论问题上较好地与我们日常看法以及与我们直觉的期望相吻合。”([1],p.92)
(三)
我们看到,劳纳在解决分析—综合难题时,一方面要拯救本体论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坚定地从语言中彻底排除“外部问题”。要完成这两个本来互相矛盾的举措的根本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改造对语言的看法。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变化。
奎卡二人不论在分析—综合问题上有多大分歧,但两人最终在只相信经验实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卡尔纳普除了在《意义与必然》中严格区分分析即语言内部的命题与综合即语言之外的命题外,在《真理与确证》〔5〕 中又明确区分了语言内部的“真理”与语言外部的“确证”用法。所有这些“分析—综合”、“内部—外部”和“真理—确证”的区分等等,都为了一个目的:把语言建立在经验实在的基础上,并受后者的检验。(上述两分法的后者都是指向这个经验的实在世界)。而对于奎因来说,尽管他早期对语言态度带有强烈的本体论色彩(这对劳纳的哲学有直接影响),但他的经验主义立场使他仍然把语言与实在(本体)区分开来。他之所以最后求助于“行为主义”、“前理论概念”和“泛物理主义”等等,并且只承认建立外延的语言系统,都说明了他的经验的实在立场。当他在说“人之使用语言和概念,犹如戴上一副有色眼镜,永远不可能看到客观实在本身”〔6〕时, 我们感到的则是他对那个“客观实在”的难以忘怀,正如康德对“物自体”的钟情一样。因此不论他与卡尔纳普有多么不同,他们的区别只是两个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卡尔纳普要在语义层次上区分分析(语言)与综合(经验);而奎因则要把语言作为整体来同经验相对照〔7〕。
而劳纳与奎卡二人则完全不同。在《为何要区分分析与综合陈述?》和《本体论问题》中他都把“语境”与本体论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更相信——在承认我们关于分析的范围内接受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可以说是语言问题,但同样可以说是本体论的接受问题”。这后半句话原是奎因说的,但劳纳却是在不同于奎因的意义上引用此话的。他接着说:“(这一观点)也许决定了他(奎因)更强的唯名论倾向,但其中也许同样有理由去寻找,为何他坚定地站在变元值域的‘实在意义’立场上,而反对‘赖尔意义’。”([1],p.91 )这些话是令人深思的:劳纳不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实在论吗?他为何又再三强调奎因所具有的实在主义倾向呢?下面我们联系劳纳的两个步骤来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经验的语言化。这是劳纳对奎因整体主义的直接发展。“经验”一词在奎卡二人那里是第一性的、独立于语言意义的。奎因尽管打破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但他仍坚定地站在经验主义立场上。然而“经验”一词在劳纳那里是从“语境”中派生出来的,它不再独立于语言意义。他说:“检验的任务只能由观察句完成,但观察句的使用已经由如下方式专门化了,即出现在观察句中的理论词项已经被认为具有了指称功能”。([2],p.140)这样,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即经验对于语言或理论的检验作用(不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蜕化为一种如他所说的纯粹的“语言内部问题”;从语境内部产生出的句子又作为“经验检验者”来检验语境。这实际上是不同语境之间的假检验。
第二,语言的实在化。如果我们联系费希特、黑格尔等是怎样把康德的那个彼岸世界“物自体”取消掉,而代之以思有同一的精神主体(“自我”、“理念”,它们同时也是实体),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劳纳是怎样将语言代替经验实在,并且将语言自身实在化的。在奎因的著作中我们必须区分他对于语言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实用主义的语言本体论(实在论)态度,这是他在对象语言中采用的语言观。在《从逻辑的观点看》和《本体论的相对论》中,这种语言观是具有代表性的。它的特点就是它只能针对别人而不能自指。上述劳纳引用的“本体论的接受问题”和“实在意义”等就是奎因在他的对象语言中的实在论语言观。然而奎因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观,就是他的经验实在论的语言观,这是他在元语言中采取的立场。(注:实际上劳纳在《Why ……》一文中多次提到的奎因的“自然主义”、“行为主义”和广义的“物理主义”等等,就是奎因元语言中的术语。)奎因在许多地方对这两种语言观作了区别(尽管他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如他在《论何物存在》一文中说:“本体论的争论趋向于变为关于语言的争论,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我们一定不可匆忙作出结论说,什么东西存在取决于语言。”([7],p.16 )因此奎因尽管说本体论问题是约束变元的值(对象语言),但却认为“实际上要采取什么本体论问题仍未解决”(元语言)。前者是关于“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关于“什么东西存在”的“另一个问题”。([7],p.15)然而,劳纳悄悄地取消了奎因这两种语言观的区别。他接过奎因的对象语言却把它发展为一种元语言,即把语言内部关于某物的承诺直接等同于某物自身。劳纳排除了语言的外延的实在,实际上就把语言的内涵本身(即意义)当作唯一实在的东西。这就是语言的实在化,即与现象(就是语言)融为一体的实在(尽管劳纳不喜欢“实在”这个词)。因此,上面劳纳强调奎因的语言的“实在意义”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这种实在化的现象即语言。指出这一点是本文的主要结论。由于在劳纳那里语言升格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物,它是第一性的,因而在它之中出现的所有个体、属性、命题真值乃至直觉和逻辑等等都是语言(语境)的派生物而已。所以他说“通过语境的确定我们就创造出一个现实的片断(a segment of reality)。”([2],p.136)
通过上述两个步骤,劳纳创造出十分类似于莱布尼兹的单子的实在——语境;单子之间互不相通,每一语境之间也须有严格区分(这是分析与综合之分的根据);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实体,每一个语境也都是一个实体;每个单子都是完全具体的,每一个语境也是完全具体的;在单子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在语境之外也没有任何东西;单子是一个精神实体,语境也是一个集直觉、经验、理论直至逻辑、数学和哲学(本体论)等于一身的精神实体。它是一个万能的唯一实在。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给劳纳的哲学冠以符合他的观点的名称,这就是语言一元论。这一名称比他自称的“实用主义的相对先验论”更合适、更明确。由于一元论必然表明本体论,因而劳纳的哲学也是语言本体论(实在论)的。他的哲学鲜明地代表了当今西方哲学中与主体相联系的、抹杀现象与实在之区别的唯心主义思潮〔8〕。
标签:奎因论文; 本体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语言哲学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