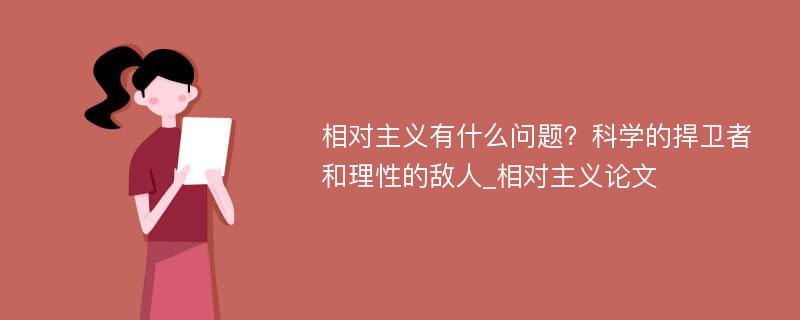
相对主义错在哪?——科学卫士与理性的敌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卫士论文,错在论文,敌人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丹(注:拉里·劳丹(Larry laudan),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是少数几位对“后现代科学元勘”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从其早期的著作《进步及其问题》(1977)、《科学与价值》(1981)、《科学与相对主义》(1990)到本文所评的《超越实在论与相对主义》(1996),体现出他对相对主义批判的一贯立场,特别是《科学与相对主义》一书,认度为是批判相对主义的经典作品。)的《超越实在论与相对主义》一书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了大肆渲染,出版商称这本书“为拒绝实证主义的错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没有使理性的敌人感到有所帮助或使他们感到舒服”。此书虽然在1996出版,但从此书内容可以看出,劳丹为攻击我们这些“理性的敌人”已经足足准备了21年。此书攻击的目标是布鲁尔(注: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其名著《知识和社会意象》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科学社会学家,从而将研究从默顿式的体制社会学转向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一般是以各种社会因素(如科学家之间谈判与协商的修饰学,科学家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等)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制造”,并把这些外部的因素视为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因素,结果就显现出相对主义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趋向。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为各种各样的反科学思潮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引起了科学卫士最为激烈的批判。)的《知识和社会意象》(1976)。但自1976年以来,科学元勘(注:“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是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词,其基本的内容是指从社会的维度去研究科学,它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STS、女性主义科学观、后殖民主义科学观、生态哲学、科学与技术的经济学、科学伦理学、等。就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还包括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其中某些研究已经走向极端,表现为(1)科学的意识形态化;(2)极端的相对主义。这种极端的趋向被称之为“后现代科学元勘”。正是这种极端的倾向引发了“科学大战”。)(science studies)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当前的科学大战(注:“科学大战”(Science Wars):1996年,“索卡尔事件”后,在全球学术界出现了一场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大论战。它通过遍及全球的新闻媒介广泛报道,已经引起了大众的注意,涉及到对科学的本性、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科学方法、科学技术与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众多科学家(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等)纷纷投入保卫科学和理性的斗争,而后现代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却不断地借助于“外部的社会因素”来“解构”科学和理性。这场仍在进行的论战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人文的大冲突。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深刻、影响面如此广泛的论战。)中,格罗斯、莱维特(注: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是美国维吉尼亚(Virginia)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罗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是美国罗格斯(Rutgers)大学数学家。两人合写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1994,1998)拉开了科学保卫战的序幕。)与索卡尔(注:艾伦·索卡尔(Alrn Sold),美国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1996年他在著名的《社会文本》文化研究杂志发表一篇诈文,然后自披其诈,引起轰动,此为“索卡尔事件”,触发了“科学大战”。)之类的科学卫士对我们进行了猛烈攻击。这提醒我这些“理性的朋友”的攻击只不过是劳丹以来的那种过时了的学术攻击的一个翻版。
让我们以劳丹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开始。在实证主义时期,科学知识被视为随时间而逐渐积累。根据这种观点,知识的日益增长的事实就成为毫不含糊地测量科学进步的可靠基础。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托马斯·库恩(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科学革命的结构》是现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并对人类文化的其它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范式的理论,特别是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理论对相对主义及反科学思潮具有一定奠基性。)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后,这种观点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库恩比较了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历史的:科学史不应被理解为事实的积累,而应理解为一系列革命性的突破。这些突破不仅联系着理论上的重大革新,而是还被理解为事实与现象上的重大变化。另一个是哲学的,革命前后,格式塔式的转变让使科学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不同的科学世界包含着不同的事实与现象。
库恩的观点在另一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注: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是最具有反叛精神的美国科学家哲学家。从其成名作《反对方法》到《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和《告别理性》,再到其自传《虚度此生》和遗作《丰富的后果:抽象的神话与存在的丰富性》,他的一生都为破除科学的“理性神话”,取消科学的权威地位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因此,在“科学大战”中他受到了科学卫士的激烈批判。)那里引起了共鸣,在其著名的《反对方法》一书中,他与库恩一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关键在于他们向科学的合理性发出了挑战,如果革命前后的科学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那么看来就很难理解科学家在革命前的理论与事实与革命后的理论与事实之间,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因此,至今为此一直被视为颠覆不破的科学进步的客观真理,已经受了的严重的挑战。库恩革命标志着科学哲学的重大转变,但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会视这些变化为进步。类似地,这意味着科学知识并不简单地是相对于反映世界为真,而是相对于范式或理论为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库恩与费阿本德就直接被纳入相对主义之列。
科学、理性与进步的职业卫士强烈地反对这种相对主义。那些视科学进步那怕持一点怀疑态度的人都被归于错误的一方,并被邪恶地冠以非理性和被指责为“暴民统治”,正如拉卡托斯所指出的那样。因此,那种企图表明库恩与费耶阿本德陷入错误的哲学著作,事实上是属于早已过时的哲学传统之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人们能够发现在科学史中连续与毫不含糊的进步。
这种攻击的标准线索是围绕着过时的“科学方法”而展开的,伟大的方法论学者是卡尔·波普与拉卡托斯,而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是劳丹。劳丹在《超越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一书中确信,尽管实证主义存在着错误,但我们不能屈服于相对主义。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发现某些超革命的科学方法,某些准则,借助于它们,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能够被评价,即使自然事实看来随着这些理论而发生变化。这种方法的祈祷将能够确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但事实上,劳丹从来没有给出这类方法的准确描述,而是经常谈论着他与库恩与费耶阿本德争论的老调:解决问题的数量是方法的关键,这一早已过时的观点,认为如果某些理论比它先前之理论解决了更多的问题,那么它就是理性上进步的。
劳丹的观点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人们能够通过数一数“问题”,就足以信服地支持了劳丹与反相对主义者的判断吗?人们对于什么是一个问题,什么不是一个问题,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更不用说一个问题的解决。欧文·汉兰维(Owen Hannaway)在《化学家与世界》这本书中,发现很难说服16世纪的帕拉塞尔学派的化学家奥斯瓦德·克罗尔(Oswald Croll),使他相信与他同时代的拉瓦锡已经解决了近代化学的基础问题。事实上劳丹自己都承认“众所周知,实践中的方法论学者不可能在科学方法能够得到确保贯彻的条件上达到一致,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被接受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所有这一切使人们感觉到并没有什么好的理由,使人们能注意到方法论学家能够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工具”(126)。所在这一切表明真实世界并不像劳丹所想象地那么简单,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它。
这里我考虑科学大战,我相信科学卫士已经注意到了劳丹反对相对主义异端的战斗,劳丹的书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对相对主义来说,并没有什么具有挑战性的令人信服的反驳被表现出来,尽管几代哲学家一直紧紧抓住这一问题不放。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在10年前都已经认输了,转而讨论其它的问题(如生物哲学的问题)。在学术领域内,反对“理性敌人”的斗争已经消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大量相同的这类过时的论战突然再次全面地爆发出来,这次科学家作为先锋,但不是在学术领域内,而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上。我们得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论战中去吗?或许我们应该这样做。就每一种情形而言,也许下面的评论是恰当的。
就哲学家已经输给了相对主义来说,人们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担保科学家不会陷入相同的境地?答案很简单,哲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的弱智,还没有聪明得足以胜任这项工作(不象科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哲学家至少也做了同样的工作,作为一种试图反驳其对手的前提,他们会真诚地讨论他们的案例,研究他们的对手的立场,尽可能地重述其内容。在科学大战中,我们可以发现没有一位科学的卫士精通认识论。他们模仿脱离语境化的引语,夸耀他们反相对主义信心,歌颂他们反相对主义的口号——“证据与论据”——但却提供了很少的证据与论据。为了挖掘一些相对温和的与不过分的例子,在否认我对粒子物理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时,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注: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berg),美国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曾因在基本粒子和场论方面的工作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美国国家科学勋章。他在《终极理论之梦:寻求自然的基本定律》(1992)一书中,对社会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皮克林的著作《建构夸克》进行了批判。随后两人在《纽约时报》上展开了论战。在科学大战中,他以着彻底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立场,对各种后现代科学元勘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是介入科学大战的最活跃的科学家。)草率地得出了一个武断的断言:“我肯定感觉到我们正在发现物理学中某些真实的东西,但这些发现并不需要我们涉及到那些允许我们发现的社会——历史条件”(Dreams of a Final Theory,188)。看来,如果我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许我也会像温伯格一样,忽视我的著作《建构夸克》中长达四百页的历史证据与论据。对我来说,与哲学家一样,温伯格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代替论据时,科学卫士提供了精神病学的评价。温伯格再次谈到了“优越性(因激动,恐惧等产生的)颤抖”(Dreams of a Final Theory,189)。一位假想的人类学家可能会同情对幻觉的崇拜,暗示科学元勘的人物从有关科学的相对主义那里获得了同样的颤抖。这种感觉一直被科学卫士本能地采用,从一种劳丹式的学术争论到曲解的讽刺。
劳丹看到了由相对主义所产生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技术的,要求一种对科学方法的概念的详细阐述。但在许多哲学家反对相对主义的抗议声的后面,在科学大战的中心,常常是某些不同的和更为难以理解的东西——一种视相对主义认为科学知识只不过“仅仅是一种建构”,从无中生有中编造的故事。温伯格说我“只是根据时髦的变化的联想,如从短裙子变到长裙子”(188),来描述粒子物理学的历史。这一点是的确需要注意的。
如果像温伯格一样,你相信,当代科学知识是“与客观实在1-1对应”(New York Review of Books,8 August 1996,14)。温伯格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相对主义的判断正好相反,科学与自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一种时髦的变化”。但如何你的观点与我们的不同,你必须在总体上反对我们,而不应该借用这种过时了的实证主义立场。库恩、费耶阿本德与20世纪70年代的哲学发展并没有足够地应付这一问题,如库恩理论作为格式塔转化的思想并不能够被解读为对我们(人文学者与思想家)尽到了其职责。如果你不喜欢分子生物学,就去创造一个新的格式塔!但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从那以来,科学元勘已经进步了。考虑下列情形:
当我研究基本粒子发展史时,发现(在文字上)实验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后,我才意识到科学仪器的不可通约性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旧物理学中,仪器只是设计用来记录最普通的基本粒子现象;在70年代的“新物理学”中,新仪器被设定筛选出有利于非常稀有事件的现象。伴随着这种实验的物质程序的变化,是一种理论上的变化:旧物理学解释的是有关作为“基本要素的夸克”,“矩阵的靴带理论”“雷琪洞”等,而新物理学却抓住了稀有的新物理学数据,现在已经成为夸克、胶子、玻色子与统一场的“标准模型”。新旧物理学现象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它们是不同的世界,是不可通约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注意到这一特殊的案例中,物质的与解释性实践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相关的证据本身,如20世纪70年代前的中微子实验确信中性流不存在,而1973年后的实验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所有这些内容都收集在我1984年的著作《建构夸克》之中。
这些说明了什么,首先在现代科学的中心领域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相对主义的论题:基本粒子世界的知识在历史上是相对于我们使用的仪器,新旧物理学之间的这种不连续的戏剧性断裂已经改变了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对我持批评态度的物理学家,包括温伯格也不否认这一事实。例如在我的故事中并没有格式塔的转变,在物质世界中存在着制造事物的机器与仪器领域,这些制造明显是因我们对理论的理解而产生的。因此,本能性的反对相对主义的科学卫士应该发现这里没的什么可挑剔,相对主义不需要否认在科学知识与其对象——物质世界之间的构成性与相互间的联系;也不需要否认对科学中的证据与论证的构成性角色。只需要记住的是它们是情境性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按照劳丹的观点:它们只不过是根据某些横跨时空的方法论标准来看,新物理学可能是合理的。这里最恰当的例子就是各种统一场理论,科学的目标是这样的统一,因此物理学家可能正确地从一个世界进步到另一个世界。
人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回答这一观点。首先,将会对它产生出问题:(1)历史上来说,统一看来并不是科学的共同目标(如,它不是劳丹首选的反对相对主义的堡垒)。(2)如果统一是科学的特殊的目的,那么只有某些物理学分支才能被称为已经制造了进步,其它科学完全不是科学的。(3)在1945年至1970年间,粒子物理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取得进步,然而,统一并没有出现,那么什么是这种进步呢?当然(4)在我研究时期,当我与100位杰出的粒子物理学家谈论它们的研究计划时,他们告诉我有关他们特殊利益与意见,各种可能的资源,事物进入这一领域内的方式的那些似乎真实的和有趣的故事。没有一个人声称已经进入了新物理学,因为这是方法论上完美的研究。这看来是对进步的一种否认。
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让我们停止如此强烈地反对相对主义。让我们考虑这些信息:人们能够把粒子物理学史(与许多其它的理论研究的发现)视为一个令人着迷的现象。也即,对我们来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挖掘世界,正如对世界来说,也存在着众多方式来控制我们。我们采用这一领域中的力学,世界就像这一力学所表现的方式;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引导我们,我们就有这些权力,而以另一种方式引导我们,我们就具有另一些权力。一种方式给予我们旧物理学,而另一种方式给予我们新物理学;一种方式给予我们炼金术,而另一种方式给予我们化学。这种明确的表达表面上看来滑入了“仅仅是建构”的相对主义形式,但实际并非如此。粒子物理学家不得不承认他们制造旧物理学工作时,需要处理某些他们所处的文化地域中的某些特殊的东西,在特殊的语境中才能制造知识。同样需要处理的是制造知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的力量与物质的力量相互之间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这对新物理学也适用,对化学也一样,甚至于对炼金术也一样。
当然,这会带来无数的问题,如我们怎么样样比较新旧物理学?(或许我们应该引入某些现实的,而不是传统科学哲学中能够统摄一切现象的超验的规范)。又如何比较炼金术与化学?(炼金术与化学都是其自身物质、观念与社会生活形式,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好的,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是坏的)。当不同文化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时,介入与相互结合的,又会发生什么?事情肯定会是困难而有趣(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的新版本中浮现出某些很好的思想)。但除非我们放弃跟随劳丹进入死胡同的方法论,否则我们不可能解开这一谜团。科学卫士把科学元勘的学者想象为头脑简单的、怀疑论上无足轻重的人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淫秽的传播媒介正在玩耍着羞耻我们的把戏。科学的创造力自身正在窒息,因为,标准科学模式的创造者不能够想象在这一模式外的世界。他们也不允许考虑科学的文化维度,而这些维度对科学的发现是不可缺乏的语境。如伽利略反对当时公认的观点与他眼睛所见到的东西(太阳围绕着地球转),伽利略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并帮助改变了世界,这不仅是科学意义上,而且还是社会意义,道德意义上,政治意义上,技术意义上与经济意义上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伽利略是费耶阿本德心目中的英雄。
这对伽利略来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件,他不得不与神职的思想警察做出艰苦的斗争。科学大战表明思想警察仍然在控制着我们。不过现在他们穿上的便衣,迁进了新的办公室,但他们缺乏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