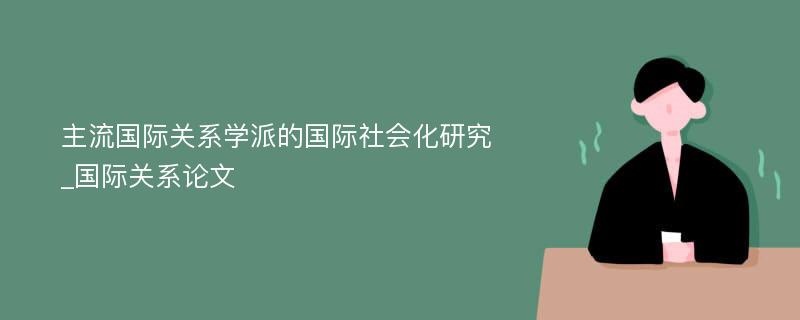
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国际社会化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派对论文,主流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社会化作为世界政治中一种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对于发展关系本位和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①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中,国家被视为国际环境中最重要的行为体,而国家内化规范如同于个人的政治社会化历程,转入国家的行为之中,这就是国家间的社会化历程。因此,不少国际关系学者将国际社会化称为国家社会化,本文的国家社会化均指国际社会化。国家间的政治社会化,是在稳定国际体系的前提之下,国家经过社会化的历程,将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的内涵予以扩散。国家社会化是凭借国家之间所酝酿的观念或是规范,通过互惠、模仿、游说和建立信任的方式进行互动,最终达成规范的内化,建构出国家间学习的模式,从而推动新兴国家融入国际制度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运作。本文通过厘清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于国际社会化的不同认知,从而寻找出可供分析的脉络,并结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对国际社会化研究的意义及不足进行分析。
一、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于国际社会化的定义
斯米尔芬尼格对国际组织与国际社会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国际社会化是一种过程,也就是,引导一个国家朝着将国际环境所建构的观念与规范予以内化(internalization)的过程。”②根据该定义可知,国际社会化包括四种概念上的要素:(1)社会化是指一种过程而非结果。也就是,行为者将观念与实践给予内化的过程。(2)内化是指将所采取的社会观念与实践导入行为者认知与行为的意识之中。其中,内部惩戒机制(internal sanctioning mechanism)能否有效制止脱轨的偏好成为破坏规范的行动,以及获取资源的资格界定,就成为关键所在。③(3)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社会行为者,都是团体性的行为者。不同于决策者个人的社会化,国际社会化一般是指国家的社会化,其行为主体乃是国家,对于国际规范与观念的内化,是通过国家内部制度化的决策过程与其惩戒机制的运作来进行。(4)社会化过程的实质内容,主要是以观念与实践的概念推展为要,而社会化的核心功能在于社会秩序的重新建构与扩散。当然,通过制度化的机制来建构上述内容,至为关键。
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性主义学者也论及了对于国际社会化概念的看法。沃尔兹从“结构”(structure)的观点来分析“体系”(system)的概念。沃尔兹认为,结构是一套限制的条件,间接地影响体系内的行为,结构通过行为者的社会化以及行为者之间的竞争态势来塑造。而通过社会化的作用,一方面降低多样性(variety),另一方面促使团体中成员通过规范达成一致性的标准,也就是,通过社会化使得国家行为者涉入体系的范畴。④身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者基于追求权力与生存的压力,致力于符合成功的规范。
因此,沃尔兹认为,国际社会化是一种自发的、非正式的以及无意图的过程。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间不但变得相似(alike),更基于成功地实践社会化内容而达到涉入国际体系的功能。⑤国家的社会化进程如同个人的政治社会化历程,在其所处的环境系络中(国际环境)渐进地完成。
伊肯伯里和库普乾借用了斯格尔的相关定义,将社会化视为一种规范和观念从一方向其他方传递中学习的过程。他们引入了葛兰西式研究方法,将社会化视为国家精英内化霸权国家阐述的规范和价值,最终被社会化到霸权国或者其他领导国家所建立的群体中。这种霸权秩序开始就有应然的特性。⑥
因此,伊肯伯里和库普乾将社会化概念定义为一种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行为者将规范与观念传递给其他行为者的过程。至于如何传递,他们提出三个假设来解释上述观念与规范的传递方式,⑦其媒介主要是霸权国通过次级国家的精英阶层来完成此一历程。第一个假设,即社会化发生的时机在于国际社会爆发动乱,例如,战争、国家内部产生政治危机、国家分裂后重新建构统治权威以及当性危机的形成,当国际社会与国家内部形成不稳定的情势,将会诱发有利于社会化进行的条件。在国际层次方面,霸权国建立一套有助于建构其利益的规则,来促成稳定;而在国家内部层次上,危机事件制造出让精英阶层达成重组政治类型的新规范,借以弭平争端。第二个假设乃在于精英阶层对于霸权国规范的接纳能力,即次级国家社会化的历程。规范最初根植于民众之间,能否将其扩散至精英阶层,将直接冲击国家行为的效果。即便前述的政治重组,也必须通过机制的运作,使规范能由大众进入精英阶层,让这些规范的运作获得媒介的传递。第三个假设则是指当社会化展开之际,此一过程唤醒权力的强迫性行为。其中,物质的诱因(material incentives)激发出社会化的历程。而物质的诱因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是奖励的承诺来改变行为者的政治或经济层次的动机。霸权国通过惩罚或是奖励等手段,迫使次级国家接受规范,借以展现权力的效益,进而达成社会化的历程。
国际社会化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芬尼莫和斯金克则将国际社会化定义为积极的机制,通过国际体系规范的约束力,并结合惩戒机制与象征性的同侪压力达成规范的内化。⑧国际社会化被视为一种引导新成员国采取国际社会所偏好行为的过程。他们通过国际规范建立的三个步骤来说明社会化的过程,其中,第二个步骤——规范的普及(norm cascades),社会化、制度化成为最主要的机制。在国际政治的系络中,无论双边或是多边的关系,社会化包括外交的赞扬与谴责,并通过实质的惩戒与物质的动机来强化。当然,国家并非是唯一的社会化媒介,规范倡议者的网络与国际组织也是社会化的媒介,通过媒介对于目标行为者施压,使其采取新政策、法律与签署条约,借以实现国际标准的目标。⑨
当然,社会化意指个别国家的观念转变以及如何将国际规范内化到国家内部的制度结构中。芬尼莫认为,国家社会化意指持续进行且存在的认知与社会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国际的互动所建构的国家认知与利益来进行的。在国际环境的场域中,国家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进行学习。此外,在芬尼莫和斯金克探讨国际规范建立的第三个步骤中则提出内化的过程来阐释。通过法律、专家以及官僚组织结构作为内化过程的行为者,其动机在于遵从国际社会所建构的规范,而以惯例与制度化作为主导的机制。
奥德森认为,国家社会化意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内化规范的过程。规范的内化有三个不同的过程。⑩第一,国家社会化是行为个体观念的转变,含括法官、企业领导人、政客、学生以及公众成员基于认知与社会心理学途径所衍生的态度转变。第二,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性的,通过国家内部行为者实施政治压力与游说迫使政府服从特定的国际规范来进行。就实施政治压力的层面而言,利益团体、立法者以及法院都扮演着内部惩戒机制的角色。而在游说的场域中,个别行为者与团体中的个体,被国外的案例所激励,成功地将政策转化至彼此的认知之中。第三,规范的内化主要取决于规范能为国家内部制度结构提供获益的大小,包含法律的内化,以及官僚行为者被委以戮力推动特殊规范创建的制度化工作。
切克尔认为,社会化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而规范与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传递,最终形成规范的内化。如何达到上述的目的,他认为还需通过国际制度和规范的运作与实践来进行。就实际经验来看,时空背景提供社会化运作的条件,例如,后冷战时期的欧洲,通过大规模的计划开展,使得国际规范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欧洲社会的结构,形成特殊的区域规范。这些规范提供影响政策的设定并建立相关机制,从而开启国际社会化的历程。
就理论层面而言,切克尔是依建构主义的途径来分析社会化,短期的观察重点在于新规范如何致力于国家内部媒介的行动,特别是由非政府组织或贸易联盟等机构对于国家决策者施压所形成的社会异议(social protest),以及来自于知识群体与国家官员的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则是长期通过研究人权规范的建立来分析国际社会化历程的。(11)再就方法论而言,探讨国际社会化的研究者必须明确说明一套可操作化的议题——如何认知社会化的历程?有何相关经验性指标可以借鉴?哪些指标被视为是有利的资料?思考其构成条件的范畴,这涉及社会化的机制在何时以及何种条件下能运作。
二、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社会化的研究
经典现实主义一方面关注自助体系内寻求权力的驱动,另一方面也强调历史偶然因素的重要影响。例如,摩根索没有排除国家内化群体规范的行为从而将其视为国际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欧洲君主惧于违反规范招致惩罚从而不得不考虑行为规范现象的消失表示惋惜。(12)他还指出权力和利益的定义依赖于特定文化背景,行为体如何被社会化后以合法的方式寻求合法的利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13)摩根索接受权力和利益具有文化的偶然性的逻辑,表明了他承认世界政治中权力政治的驱动并非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学习的结果。然而,此后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并没有将社会化用于解释权力和利益的变动。
新经典现实主义反对结构现实主义对于还原理论的批判的同时,指出权力与利益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对于解释国家行为和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也坚持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寻求自身利益和安全最大化是国际互动中普遍和不变的事实。(14)这种逻辑本身存在缺陷,它接受外部世界主体间性的解释,由于“解释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本身可能存在断裂现象,因此偏好和观念可能影响对于现实世界的判断,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实力的不平等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也不再具有决定性。此外,该理论也没有解释偏好和观念的来源,因此它没有包括社会化相关理论。
新现实主义将社会化解释为无政府体系下寻求安全的国家,在自助环境中采取均势行为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15)但是这种概念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日常社会科学研究中同质化过程并不等同于社会化。沃尔兹从群体心理学引用了相关理论表明群体内互动能够使得个体成员产生集体意识(collective mind),(16)但是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互动,沃尔兹放弃了集体意识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挑选(select)和竞争(competition)。沃尔兹认为,效法和竞争导致了国家行为的相似性,通过互动使得国际体系内不效法最成功国家的自助和均衡行为的行为体将被剔除出国际体系,从而使得剩下的国家都秉承权力政治的行为方式制定政策。(17)由于该理论对于国家是否必然附带权力政治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它对国家是否有意识寻求均势结果或者只是无意识下产生的体系平衡也无法作出解释,也就是它对无政府状态下社会互动是否导致效法或者模仿也不能作出必要解释。新现实主义夸大了国际社会的压力对国家同质化的影响,由于各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并不总是为争夺稀缺资源展开竞争,而各自行为的驱动也大不相同。20世纪以来,国家衰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那些没有采取自助和均势政策的国家并未消失。(18)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一些国家并未采取均势政策,但是也没有被剔除出国际体系,它们的决策行为仍然不同于国际体系内所谓的“成功国家”。国际体系比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下均势具有更强的变动性和复杂性,这些新兴国家通过倡导一系列诸如裁军、主权平等和反对侵略的规范确保了自身的生存。
第二,多数社会化概念的运用指的是偏好形成或者变革的过程。儿童社会化包含了儿童通过与家庭和社会组织的社会互动形成对于社会的和物质的喜好。政治社会化通常指的是青年从父母或者同龄人那里习得的政治取向和偏好。然而,对于新现实主义,社会化似乎与偏好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从微观经济学引入相关概念和推理逻辑,经济学模式通常将偏好视为稳定因素,不同的环境约束了行为体获得偏好结果的能力。因此,新现实主义认为,物质结构是制约国家行为的关键因素,国际社会化仅仅是行为体忽视权力均衡机制付出代价后,所采取的更为自觉的行为。这也意味着国家对于物质结构中哪些是成功者或者失败者及其原因等方面获得更强的敏感性。行为体准确解释这些信息的过程并没有伴随自身身份或者对于国际体系本质理解的变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能称为社会化。(19)
第三,新现实主义的社会化仅仅朝单向演进,即围绕权力政治规范行为的集中,排除了体系层次社会化朝非权力政治方向发展的可能。然而,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缺乏外部物质威胁或者刺激下国家遵循规范行为的案例比比皆是,表明了国内和国际体系规范的结构同样能对行为体发挥社会化的功能。(20)这也对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和无政府是否是通过社会化影响行为体的唯一因素提出了质疑。况且,权力政治社会化的进行并不依赖结构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由国际体系和单位层次内权力政治规范塑造的。(21)
三、契约制度主义关于国际社会化的研究
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关注国际关系中社会化的过程。该学派采取了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指出社会互动能够改变的偏好、利益或者基本的安全哲学,这些都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它们在塑造模型时通常将这些因素视为固定的,认为制度内的社会互动对身份或者行为体几乎没有影响。(22)制度内的社会互动并不影响行为体的身份和偏好,其身份和偏好通常与它们加入制度之前的身份和偏好相似。这些行为体的特征也并不影响到制度的特征,一个真正有效的制度原则上应该反映合作问题,而不是行为体自身的本质,因此这些特征对于行为体身份并不产生任何影响。制度化频繁互动为其他行为体提供了新的信息,但是对于行为体的基本偏好没有影响。不论社会互动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不会对潜在偏好产生影响。发生变化的只是寻求这些偏好的代价和收益。
制度主义低估了国际社会化的影响,该学派在解释倾向规范行为时突出强调了动机的重要性。制度内的合作基本上从以下三种主要路径进行:
第一种路径是联系。纳什均衡规律表明合作中不满意一方往往倾向于采用武力威胁或者承诺获得博弈中更有利的结果。(23)游说仅仅是通过外在积极或者消极的手段改变不满意一方对于得失的衡量来确保合作的安全。在博弈理论中,游说既没有改变行为体的潜在期望,也没有改变行为体的基本观念或者博弈运作达成的共同认知。
第二种路径是制度引导行为体遵循规范。制度能够引导行为体遵循规范是因为行为体担忧自身的声誉。行为体声誉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与其他行为体进行合作的可能,因此,行为体首先必须获得合作的声誉,特别是在代价高昂环境下的合作更需要行为体有着良好的声誉。建立值得信赖声誉的驱动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遵循规范和倾向国际社会的行为。(24)但是这种建立声誉的观点至少有个主要问题。正如弗兰克指出,这种声誉对于理性的观察者而言决不是可靠的或者值得信赖的。(25)行为体寻求声誉的目的在于能够为其他成员国所觉察。如果这种行为不能为其他成员国所理解,那么将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旦这种行为目的是使得其行为被众所周知,那么其他的成员国将会怀疑其是否的确是高昂代价的行为。减少这种怀疑的唯一方式是使其他成员国信服其行为是无法事先清楚计算的。因此也出现一个悖论,最值得信赖的声誉是建立在自动、情感、非控制性和非衡量利益的基础上。因此,为了减少组织内的不信任和冲突,组织在社会互动中必须向其成员灌输一种深层次的、值得信赖和理所当然的反应。规范的社会化最终成为可信声誉的基础。
第三种路径是制度通过信息交换来引导合作行为。制度内的互动能提供影响手段、设定目标、其他行为体的偏好以及因果逻辑的理解的新信息。(26)这种信息有助于减少其他行为体承担义务可信度的不确定性,有助于行为体的期待围绕着合作的结果集中。信息影响的仅仅是行为体寻求固定偏好下关于战略环境的观念。通常信息影响偏好是通过对精英阶层的影响,某些战略失败的信息能够导致部分精英对于寻求其利益定位的支持,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利益定位。契约制度主义者是如何对待制度内部信息的?目前的研究仍然比较模糊。信息很少具有争议性,它能够直接消除不确定因素。新信息的内容似乎无需解释。为什么制度要减少不确定性?这主要由于新信息中包括的偏好具有不确定性。如何使得这些信息具有可靠性?通常契约制度主义强调信息供应者应承担的成本。但是契约制度主义对于解释何种情况下新信息将影响偏好、观念和战略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等方面没有相关的理论解释。此外,信息的社会环境似乎无关紧要,或者至少对于代价的共同定位及信息可靠性最重要的因素是无法解释的。拜尔森将观念作为现实经验研究后指出:决定建构观念的多种历史社会关系是如何过滤新信息的,尚未有相关的研究。
事实上,同样的信息被不同地解读,这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来自于人们喜欢的信息(信息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或者贬低其他的信息。(27)例如,经济交易中的价格协商,人们交换关于自身偏好和底线的信息存在极大不同,主要取决于交换方是否是朋友,假如采取欺骗行为,朋友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而陌生人则代价相对比较低。(28)即使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面对面的谈判更可能使得谈判双方受益,因为这种行为能够使得诚信规范进一步增强信任和推动信息共享。因此,社会环境对信息如何有效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关键因素。
社会化对于契约制度主义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假设制度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规范、习惯和条约能够约束行为体的理性选择的协调博弈占据重要地位,那么双方达成共识的社会与历史根源就更应该受到重视。制度主义也承认共识是共享文化和社会经验的产物。但是,国际关系中这些共识的起源并非其关注的核心内容,制度主义并没有对谈判和制度内达成共识的微观层次内容进行解释。从本质上讲,共享文化和社会经验有助于行为体在平衡中进行选择,但是制度主义学派并未对这种选择进行物质外化分析。假如有学者认为双方的共识和契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不同的本体论对于共识的稳定具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共识的社会起源问题更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建构主义本体论认为,多个行为体之间长期连续的活动导致社会结构环境的变化,反过来影响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界定。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社会契约和共识能够通过非激进和非线性的方式进行演进和变化。的确,契约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本体论的差异是导致前者为何对偏好变化不感兴趣的原因。建构主义本体论为相对不稳定的偏好打开大门,更加重视偏好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和规范性社会环境。
其次,契约制度主义承认新现实主义的社会化过程具有滞后性。假如契约制度主义为了解释为何行为体关注绝对利益和共同利益是建立国际制度的必要条件,从而接受新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和安全最大化的假设,那么,它们将不得不承认新现实主义社会化研究是不完善的可能。不是关注不完全社会化可能导致制度内逆社会化的过程,而是契约制度主义更强调国内政治变革、外在技术变革和多种问题的出现,以此解释关注绝对利益和共同利益。
最后,有趣的是契约制度主义采用制度的定义非常具有社会学的韵味。从制度的意图到影响,如果制度得到有效实施,那么同社会化国家过程非常相似。马丁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套约束国际进行合作与宪法精神的规则,预先给定国家行为可接受的方式和为不可接受的行为方式提供解决方案。”(29)该定义意味着多数有效制度能够使成员国内化预先规则或者给定的方案。国家应当长期放弃从因果进行衡量,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正义性来确定自身的行为。否则,所谓预先给定的行为仅仅是是否奖罚的事情,而不是是否被接受的问题。(30)
国际关系自由学派也将国际社会化引入自身的本体论和认知论中。国际关系自由学派的杰出代表安德鲁·莫拉夫克斯克(Andrew Moravcsik)认为,通过身份建构和社会互动改变利益与偏好是可能的。但是,他批评了建构主义在规范扩散过程中忽视了国家和次级国家的分析。此外,莫拉夫克斯克还特别强调建构主义忽视了规范从国际体系结构向国内层次扩散过程中偏好是如何形成和分配的问题。(31)他承认国际规范扩散能够导致内化,而国家间内化的变量是先于国家和次级国家身份之间运行的。另外,莫拉夫克斯克还运用了社会学的语言,为探究社会化提供了可能:国际关系自由学派试图综合分析寻求自身利益行为体决策迈向合作或者冲突集中的环境。(32)一种社会环境体现了价值与观念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但是这种行为集中产生的根源并不明确。他指出,对于自由而言,合作的形式、内容和深度直接取决于多种行为体之间社会互动形成的偏好问题。(33)偏好是如何影响预测合作或者冲突行为的集中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他接着强调偏好是在改变跨国社会环境的反应中变化和跨国文化环境中特殊价值地位有助于每个社会界定其内涵。(34)莫拉夫克斯克将价值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与偏好的变革联系起来,但是他对于国家间社会偏好或者社会身份是否在国家或者国家间层次建构的问题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莫拉夫克斯克认为,“自由理论对于社会身份起源没有自身独特的理论,社会身份的形成主要源于历史的积累或者国家行为的建构,同时也无法解释它们是否最终能够影响观念或者物质因素。”(35)国际关系自由学派对于国际社会化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规范的扩散需要通过国内制度的过滤,而国内制度又是集中偏好和制度政策的实体。关于偏好的社会起源、内容和建构的解释都被国际关系自由学派所摒弃,因此,对于偏好来源于何处,国际关系自由学派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反思主义对国际社会化的研究
(一)建构主义对国际社会化的研究及其不足。
建构主义将社会化视为核心概念。建构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认知和利益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产物。认同和利益并非外生于体系,而是内生于其中。社会化不仅与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相符,而且对于解释主体间性的结构如何改变行为者的认同和利益相当重要。亚历山大·温特把社会化定义为“互动的普遍特征,通过互动,认同和利益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结构和行动者相互建构的微观机制。他们把社会化看成是导致规范内化的过程,从社会化中可以管窥到规范的演进。国际社会化诱导国家从原来规范的破坏者成为规范的遵从者。正如奥努夫指出的那样,社会关系把我们建构成为了社会化动物的“我们”。(36)建构主义对于国际规范的形成与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确性逻辑上,因此,倾向规范的行为及其内化被视为是必然的过程。对于何种规范被施动者内化及其方式和程度等问题,克拉特奇维尔和鲁杰认为,应当将国际制度视为行为体期望集中的社会制度,主体间性集中产生的过程问题也由此出现。社会制度的形式表明行为体经历制度内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加入制度前后集中的程度是不同的。(37)虽然建构主义学者也对社会化做了一些研究,但是主要集中从社会制度主义的角度分析价值和实践从宏观层次进行扩散,衡量全球规范的现状与地区实践之间的关系。(38)芬尼莫的研究突破了这种关系,着重分析了国际规范施动者是如何以新兴的国际规范和实践“教育”新成员和建构其国内制度和程序的。成员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这些规范和实践,甚至它们有些不符合成员国的物质福祉和安全利益。
目前,建构主义对国际规范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并非相当清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建构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了社会制度主义的认知论。
建构主义忽视从微观层面对社会化的分析。(39)该学派认为,国际体系层面的施动者能够将新的规范理解灌输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中,因此,国际制度内的行为体遵循国际体系的规范和价值也是必然的。研究忽视社会化对于单位层次影响的程度、规范竞争的程度、规范滞后,以及国际规范作为施动者如何“教育”单位层次的国家理解、处理和解释这些规范等问题。这造成因果机制研究的不足。因此,单位层次的行为体是如何接受正义性逻辑和采取倾向规范的行为的相关研究仍然相当薄弱。这种忽视是令人诧异的,假设建构主义者关注的是多种行为体的反思行为:如果在规范扩散过程中存在这种施动者,那么多种行为体在接受“教育”后,这一互动的微观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个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体系的规范影响成员的行为是既定的,无需进一步解释,这一关于社会化的研究存在重大缺陷。
社会规范结构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国际制度及其内部成员国之间的互动能够将最重要的国际规范传递给新成员国,新成员国通过自身身份对这些国际规范进行过滤。协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制度之间互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和实践互动不断的重复也可能改变国际制度最初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许多建构主义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但是忽略了第二步,即国际制度是如何将国际规范教育给新成员国以及它与国家实践内容之间的关系。准确而言,第二步是决定国际社会化是否有效产生影响的关键。虽然国际制度内的行为体处于相同的制度环境内,但是它们对于自身的利益和行为认知却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第二步的关键是分析世界政治中社会化在微观层面是如何运作的。
第二,建构主义开始关注社会化的微观层次和社会互动的建构影响,且主要集中在游说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借鉴的是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它认为,可以通过对规范理解进行非强制性的沟通以达到行为体内化规范的目的。但是,并非所有规范的社会化都是战略谈判,即使是战略谈判,也必须有共同规范的基础和确立能够被接受的稳定的核心议题。因此,对于社会环境的界定与为何某种行为应当被避免的问题应事先达成共识。谈判也并不仅仅是控制外在物质环境强制其他方采取自身期待的行为,这中间包含了通过争论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观念。(40)正如梅尔指出的那样:“冲突各方总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中达成共识和推断出某种妨碍谈判的行为,并应当尽力避免之,从而推动谈判。”(41)
在建构主义看来,游说不仅仅是沟通的行为,而且也是规范性的强制行为。次级国家遵循规范不仅仅将其内化,而且是精英阶层避免大众批评的一种手段。这导致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对于怎样建构信服的论点并没有清晰的论述。此外,沟通行动理论对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要求也相当复杂。建构主义对于社会化问题的研究过于关注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忽视了沟通行动理论中的游说、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化等丰富的传统研究成果。对于这些传统研究成果而言,游说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如何将沟通行动理论运用于解释是否是游说或者强制导致行为体采取倾向国际规范的行为,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沟通行动中如何使其他成员国信服,这个课题的研究有较高的要求。建构主义未能解释制度内成员国如何对共识进行争论,从而使其他行为体对特定的社会现象达成共识。在何种社会或者物质环境下,沟通行动能取得更大收效,这需要社会化双方高度信任和实力均衡。(42)建构主义仅仅依赖身份理论,而忽视权力因素的影响。身份理论指出,当两个行为体相互信赖以至于彼此能接受对方提出的证据、概念和结论,以助于沟通行动的顺利进行。(43)虽然身份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增强行为体理解对方解释的有效性和内化规范的程度,但是,对身份在沟通行为的最初阶段是如何产生的仍然没有阐释清楚。第二,建构主义之所以重视游说,是因为它将游说视为同新现实主义和契约制度主义就社会互动能否改变行为体的偏好和解决其利益问题进行争论的王牌。纯粹的社会化——至少还有两种社会互动方式在缺乏外在物质威胁或者许诺时能够产生倾向规范的行为。这两种社会互动方式分别是社会影响和模仿。社会影响伴随着一系列的次过程,即鼓励、羞辱、地位最大化等,通过相同身份认同的组织对成员在社会和心理上进行奖励,使得新成员采取倾向于规范的行为。模仿是由于新成员无法对收益、手段与目的作出明确的计算,为了适应不确定的国际环境而效仿国际制度内其他成员倾向规范的行为。由于建构主义过于注重游说的作用,从而无法解释倾向规范行为在其他微观层面的手段。国际规范社会化的路径远远不止游说这一手段,也可以通过教育、认知学习和社会环境等手段对行为体施加影响。
(二)国际社会理论对国际社会化的研究。
国际社会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化对于国际社会的产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国际社会化催生国际社会。本文就英国国际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关于国际社会化的论述加以分析。布尔曾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国际社会产生的动力。他首先认为,在古代世界里,土耳其、中国、日本等国家虽然有了与欧洲诸国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只能形成国际体系,而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程度。其国际交往是停滞在一般程度上的经贸交往的水平,两类国家之间并不相互确认“相互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价值观念”(44)。因此,国际社会在具有一定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国际体系条件下存在,如十六七世纪的基督教国际社会,以及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是技术进步、交换关系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产物,其标志则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与义务来互相联系。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而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45)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者国际社会)就出现了。”(46)
布尔关于国际社会的界定有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国际社会是国际体系的继续与发展,二是国际社会必须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支撑,三是国际社会要有理性的契约或者制度安排,四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是国家。以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国际社会学派认为:“一群国家不是简单地形成了一种国际体系,体系内的每一个国家在行动时都必然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反应,而且还通过对话和共识建立起共同规则和制度来指导彼此间的关系,并且在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中实现共同的利益。”(47)这个国家群体其实就形成了所谓的国际社会。布尔的这种界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体现了国际社会理论对于国际社会的深刻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国际社会化在推动共同文化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五、国际社会化研究的意义
国际社会化是国际规范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于社会化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同。国际关系主流学派都承认社会互动能够通过外在的约束力量改变行为体的决策。现实主义将社会化视为同质化,忽视了身份和规范作为国际社会化的核心内容的重要性,无法真正理解国际社会化的深刻内容;契约制度主义过分强调成本和收益,低估了偏好的重要性和社会化的影响;虽然反思主义极其重视社会化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从微观层次对国际社会化进行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国际社会化,更好地将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理论架构起来。
首先,尽管国际体系内规范的转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和外交史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但是,规范内化的问题仍然被众多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国际社会化研究有利于解释国家互动对于国内层面的影响。
其次,国际社会化研究有助于解释现实世界中看似独立和没有关联的现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和因果联系。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规范内化的具体案例研究是有的,如国际人权规范扩散、民主化以及采用科学官僚机构等研究,但是,这些案例在研究国际社会化的方法与概念上仍未达成共识,而国际社会化研究恰恰是为了探求这些现象内在的共同点。
第三,国际社会化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国际社会化的过程与国际政治中的其他现象极容易被混淆。国际社会化并不表示次级国家政策的变化朝着遵循规范的方向发展,它指的是通过国际互动影响国内政策取向从而使得某种政策被接受或者否决的过程。国际社会化的关键环节是规范的内化,而不是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问题不是国家是否遵守规范而是为什么要遵守。
第四,国际社会化内涵本身的模糊有助于从多角度进行研究。社会化含义使得我们更为关注国际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权力和不平等因素。建构主义过分强调国际现实的社会建构,但是忽视了权力政治的视角,国际社会化强调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个体的观念,这有利于弥补以上的不足。然而,国际社会化内涵容易被有些学者误解为新加入国际制度的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指导或者霸权国的同化。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采用了过时的社会化概念。帕森斯社会学理论将社会化界定为社会复制、遵守和灌输共同的价值、个体冲动的社会约束。但是,最近的社会学理论批判这种过分的社会化模式。当前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是如何使得行为体阐述自身期望、共同努力和成为自我导向的行为体。国际社会化决不是将外来的规范通过直接方式强加给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并不意味着同质化一定得支配多元化,而是分析在何种环境下国际社会化的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影响。
注释:
①参阅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②Frank Sohimmelfennig,"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6,No.1,2000,pp.111~112.
③Robert Axelrod,"An Evolution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80,1986,p.1104; James Coleman,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London:Belknap Press,1990,p.293.
④⑤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Y.:Random House Press,1979,pp.73~75,p.128.
⑥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Kupchan,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4:3,Summer 1990,pp.289~290.
⑦John G.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1990,p.284.
⑧⑨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901~904,p.902.
⑩Kai Alderson,"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2001,pp.415~433.
(11)Jeffrey T.Checkel,"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Chapter 1:introduction," ARENA working papers,WP 01/11,pp.2~3.
(12)(13)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Knopf,1978,pp.251~252,p.9.
(14)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Washington,DC,August 28~31,1997.
(15)(16)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p.127~128,p.75.
(17)Joao Resende-Santos "Anarchy and the emulation of Military Systems: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 South America,1870~1930" Security studies 5:3( spring),1996,pp.193~260.以上文献对效法做了详细的介绍。文章将效法和模仿两个概念区别对待,效法包含了有意识地向他国寻求成功的经验,并将成功经验内化作为未来理解世界政治现实的基本准则;模仿则是一种复制特定社会环境下多数行为体的行为,它是一种缺乏意识和寻求功能最大化的行为。
(18)Tanisha M.Fazal,"The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 Norm",paper prepared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an Francisco,August 30-September 2,2001.
(19)温特认为,沃尔兹采用的社会化形式相当奇特。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概念并未包含社会因素,它是物质实力的产物,而不是身份和偏好等非物质因素互动的产物。因此,社会化变成了均势和关注相对权力行为的集合,而不是行为体特征的集合。虽然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化也包含了围绕社会特定模式行为的集合,但是,这种过程是发生在没有物质约束的情况下,行为体将倾向社会的行为内化,并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
(20)Elizabeth Kier,Imaging War: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R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Norms and Deterrence: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Taboos",in Peter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21)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e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Katzen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22)Celeste Wallander,Mortal Friends,Best Enemies:German-Russian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该书对于制度主义学派内部在制度与偏好问题上的分歧作了系统阐述。
(23)Lisa Martin,"The Rational Choice State of Multilateralism" in John Gerard 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24)David Kreps,"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ames E.Alt and Kenneth Shepsle,eds.,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90~143.
(25)Robert Frank,Passions within Reason: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New York:W.W.Norton.
(26)Lisa Martin,"An Institutionalist View: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T.V.Paul and John Hall,eds.,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84.
(27)James Kuklinski and Norman Hurley,It'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in Diana C.Murz,eds,Political Persuasion and Attitude Chang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127.
(28)Jennifer Halpern,Elements of a Script for Friendship in Transaction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41:6,December 1997,pp.835~868.
(29)Lisa Martin,An Institutionalist View: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in T.Paul and John Hall,eds.,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78~98.
(30)艾伯特(Abbott)和斯尼德尔(Snidal)综合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正式国际组织的角色和影响观点,指出国际组织能够帮助国家改变和建构共同的环境及其自身。大量文章关注的是国家利用国际组织在协调和提供信息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有些学者也试图将国际组织视为影响国家利益、主体间性理解和环境的施动者,但是最后这种观点都被放弃了。详见Kenneth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42:1 February 1998,pp.3~32.
(31)(32)(33)(34)(35)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1:4 Autumn 1997,p.539,p.517,p.521,pp.522~533,p.525.
(36)Nicholas Onuf,Constructivism: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alkova,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Armonk,NY:M.E.Sharpe,1998,p.59.
(37)Friedrich Kraochwil and 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 State of the Art on the an Art of the St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0:4 Autumn 1986,pp.573~575.
(38)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Danna Eyre and Mark Suchman,Status,Norms,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Conventional Weapons:An Institutional Theory Approach,in Peter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Richard Price,Reversing the Gun Sights: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min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2:3 Summer 1998,pp.613~644; 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c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39)这类的批评可以参见:Jeffrey 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orld Politics 50(January)1998,p.335.Thomas Risse,Let's Talk,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August 1997,p.2.亚历山大·温特在其代表作《国际关系中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指出:“在社会理论中……虽然能够充分指出文化规范的存在及其相应的行为,但是,对于规范如何扩散到行为体内部仍然缺乏研究。”详见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34.
(40)对于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的综合分析,可以参考:Thomas Risse,Let's Talk,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August 1997.
(41)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6~177.
(42)Michael Rabinder James,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Logics of Group Conflict,paper prepared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Boston,September,1998,pp.7~11,pp.15~17.
(43)Michael Williams,The Institution of Security,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2:3 1997,p.291.
(44)巴里·布赞(英),《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45)保罗·肯尼迪(美):《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46)赫德利·布尔(英):《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11页。
(47)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建构主义论文; 新现实主义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规范分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