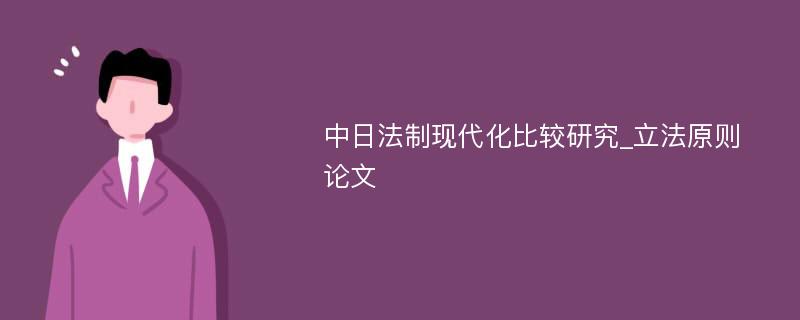
中日法制近代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法制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法制近代化的含义及特征
“法制近代化”是个宽泛而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先对这一概念作一探讨。
首先须明确,所谓“近代化”,指的是哪一历史阶段的现象。从有关论著中可以看到,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按史学界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将近代作为不同于现代的一个阶段,赋予近代化以不同于现代化的含义;另一种则把近代化与现代化合为一体,称之为“近代化”,或“现代化”。(注:如马家骏、汤重南所著《日中近代化的比较》(日本六兴出版1988年版)一书中,就用“近代化”这一概念表示近代以来包括现代在内的历史发展趋势。)笔者认为,这类概念本来就没有如同自然科学的概念那样严格的含义,两种用法均无不可,关键是看研究的对象及研究需要。以本文而言,为了便于将中日两国的法制演进进行比较,以采取第一种用法为宜,因为中国法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情况,如将这一阶段也作为近代化的一部分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既不科学,也无多大意义。因此本文所说的“法制近代化”,仅指前现代阶段的法制演化,而不包括现代。
其次须弄清楚,所谓“法制近代化”,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它包含着人类法制演进中的哪些趋势。从近代主要国家的法制发展来看,法制近代化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法治主义原则的确立。
法治主义是一种以突出法的至上权威性和统治地位为特征的立国原则,虽然在历史上,主张以法治国的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但真正的法治主义无论作为系统的理论还是国家原则,都主要形成于近代。近代以前,由于实行法治所必需的种种条件(如宪政民主、权力分立等)尚不具备,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法治才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法治学说经过欧洲思想家和法学家们的阐释,逐渐形成系统的理论,英、法、美等较早实现近代化的国家相继走上法治之路,制定了作为国家最高准则的宪法,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分权原则,从而消除了临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实现了法的统治。其他后起国家也大体如此。从古代中世纪的君主之治、寡头之治到近代的法律之治,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反映了法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衡量法制进化程度的尺度之一。
2.民意立法机关的出现。
从专制到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这一历史趋势在近代的表现之一,便是民意立法机关的出现。近代以前,除个别国家的个别时期外,最终立法权一般由君主或寡头执掌,立法没有严格的程度。到了近代,随着民主分权制度的出现,议会等民意机关成为行使最终立法权的机关。这是近代立法不同于古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凡是步入近代化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虽然民意机关反映民意的程度因国家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并由此而引起了人们看法上的一些分歧,但这种机关的出现是历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则是不能否认的,它不仅使立法被纳入严格的程序,而且至少使得法律反映人民意愿成为可能。
3.以人权保护为特征的公民法律体系形成。
法律体系的变化是法制变化的重要方面。对于近代法律体系的属性,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概括,诸如“资产阶级法”、“市民法”等等(注:日本学者大都用“市民法”来概括近代法,但在对“市民法”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存在着差别,有的用这一概念来指称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对应,以私有权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为原则的私法,有的用以概括具有这种特征的所有法律。)。其实,如果撇开非法制角度的考量,将近代法概括为公民法,则是较为恰当的。因为近代社会从本质上讲属于公民社会,所有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民主自由等权利,并通过法律结成非政府的社会系统。近代法是与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法律,其内容和作用是反映和规范公民社会的各种关系,应该用“公民法”来概括其属性。公民法的基本特征是保护人权。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宪法及各项公法对公民民主自由权和人身权的保护性规定上,也体现在民法等私法对私权的保护上,各国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的法律体系都有种趋势。有的国家如英国,在步入近代的过程中并未废除原有的法律,但通过制定新法、法律汇编和注释等仍注入了人权保护的精神。可以说,人权保护是近代法律区别是于古代法律的一个基本标志。
4.独立司法系统的建立。
司法独立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历史趋势。近代以前,由于权力分化水平底下,司法系统大都被囊括在混合权力系统中,司法权主要由兼具各种职能的混合型权力机构行使。虽然许多国家都长期设有具体办理司法事务的专门机构,有的国家甚至还曾有过较为系统的专门司法组织,但这些机构并不能构成独立的系统,也不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因为在它们的上面还存在着拥有更高权力的混合型机构,包括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专制王权。从总体上讲,这些机构都是混合权力系统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职能划分上,都不是独立的系统。只是到了近代,随着民主化、法治化趋势的出现和分权制衡制度的产生,独立的司法系统才得以形成。近代各国都曾有过司法系统从混合权力系统中分离出来而走向独立化的过程,从而构成了法制近代化的又一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所说的法制近代化,就是出现于近代的呈现出以上特征的法制演化。需要指出的是,法制的演化是相关各种因素综合变化的复杂过程,其中既有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变化,也有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变化,而后者往往还是前者的先导,因此,我们对法制近代化的考察,不能仅局限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有时需将有关的思想观念也包括进去。
二 中日法制近代化的共同点
中日两国是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并在近代初期有类似的遭遇,两国的法制近代化有许多共同之处。
1.两国的法制近代化,都是由外来的冲击而引发的,而不是自身自然发展的产物。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延续而有着牢固结构的法制体系。这个体系赖以存续的基础不仅是有着较强韧性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有它所根植于其中的深厚的文化土壤。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法制还会延续下去,即使发生变化,也不会离原来的轨道太远。而西方的冲击则从两方面促成了中国法制的根本转变。第一,西方的侵略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压力迫使中国不断地作出调整,从而一步步走上包括改变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改革的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起初并未意识到要变更国家制度,只想靠兴办实业和发展技术来富国强兵,对抗西方,因而出现了以追求“船坚炮利”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才逐渐认识到不改变制度不足以解决民族存亡问题,同样是设学堂、办矿务、制洋器,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从而下决心进行制度的改革。无论是康、梁的变法维新,还是被称为“慈禧新政”的清末变法,都是诉诸于制度的改革。正是这种革故鼎新,变法图存的历史潮流,造成了法制大变化的契机,使法制近代化成为可能。第二,西方的冲击增加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西方近代制度在中西对抗中所表现出的优越性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等人及以后在法制改革中起重大作用的沈家本等,都是在认识到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文明与进步的情况下,倡导和推进中国的法制改革的。
日本的法制近代化,也是西方冲击的产物。日本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受到西方的侵扰,自1853年美国人培理受总统派遣,率船队到达日本,向日本政府提出开放国门的要求后,西方列强陆续进入日本,与德川幕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而使日本丧失了司法和海关主权。对日本近代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摆脱西方的压力而兴起的。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日本法制朝近代方向的转变。一是明治维新中出现的种种改革,包括锁国政策的废弃,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农民身份的解放,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习俗和教育文化的变革等,造成了大规模的近代化潮流,法制作为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要被囊括在其中,改革势在必行。二是西方列强对日本法律的看法和态度,直接引发了法制改革的进行。明治维新发生后,日本政府一直想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来收回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但西方列强认为日本的法律过于落后,与西方法律差别较大,提出须待日本法律与西方法律一致后,方可放弃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权。明治政府为解决修约问题,遂决意实行法制改革,由此开始了日本的法制近代化过程(注:日本学者在谈到日本法向近代转变的原因时,往往强调修约的作用。其实,从宏观上看,修约只是一个具体的诱因,日本近代法制的变化主要是由因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变化所决定的,没有修约问题,也会发生。)。
2.两国的近代法制,都是在引进外国法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在戊戌变法酝酿法制改革时,就表现出了引进西方法律和制度的倾向。当时的变法人物都主张采择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行中国的改革。康有为主张“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注:《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还提出,民法、商法、讼律、 国际公法等,“西人皆极详明”,中国应设专门机构,“采定各律以定率从。”(注:《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谭嗣同也认为, 西方法度政令美备,主张中法“尽变西法”。(注:《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徵》。)梁启超主张参酌西方的议会制度,设立“立法部”。(注:《论立法权》,《文集》卷20。)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仍在延续,民间出现了翻译出版外国法律和法律著作的高潮。据统计,仅见于《东方杂志》广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政译著就有38种。(注: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第369页~371页。)
至清末法制改革,引进西方法制仍是确定不移的原则。清政府明确宣布,要“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注:《清德宗实录》卷498。)。由于当时日本已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因而清政府将日本作为主要模仿对象,同时参考德国、荷兰、法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十余年间,组织人力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并聘请外国法律专家,帮助起草法典。其所订新法大部分以外国法为蓝本。其中主要者如《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仿自日本明治宪法,《钦定大清商律》仿自英国公司法和日本商法公司部分,《大清民律草案》、《民刑诉讼法草案》、《大清刑律草案》等主要仿自日本和德国有关法律。新出现的由大理院和地方法院构成的司法系统及相关制度,也大体模仿日本和德国。
到民国时期,由于政府更换频繁,引进外国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除日本和德国外,欧洲其他大陆法国家和英美等国的影响也很明显。北京政府时期,民事审判曾实行成文法与判例并行的制度;南京政府时期,在民商立法中实行民商合一制,将商事总则规定于民法典中,而关于公司等制定单项法规;在破产立法中破产法仅作程序规定,而有关实体规定则分散在民法和公司等法中。这些做法均与日本和德国不同,而与瑞士、法国及英美法国家接近。总的看来,参考采择的范围有所扩大,显示出在吸收外国法方面趋向成熟。
日本的法制近代化也以引进西方的法制的方式进行。明治以前,在西方冲击的压力下,日本就出现了学习西方技术的现象,明治维新开始后,明治天皇在有名的五条誓文中明确宣布,要“求知识于世界”,(注:[日]高柳真三:《日本法制史》(二),有斐阁1982 年版, 第12页。)把学习西方做为一项基本的立国方针。此后,日本出现了以模仿西方为特征的“文明开化”潮流,其近代法制体系,就是在模仿西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国家制度和立国原则方面,受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等所介绍的西方制度和思想的影响,明治初期就出现了想采取三权分立制度的意向。1868年制定的《政体书》规定,国家由太政官总揽大权,其下设议政、行政、刑法三官。议政官负责议决国家重要事务和制定法律,行政官掌管行政,刑法官掌管检察、审判、警察等事务,三机构长官不能互相兼任。虽然这只是形式上对“三权分立”的模仿,而且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行,仍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以后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和立宪活动的热化,再次出现引进西方国家制度的高潮。围绕着实行何种体制的问题,发生了许多争论,出现了建立英国式立宪君主制和实行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等不同主张。到明治宪法颁布,确定以普鲁士制度为样板而实行天皇集权下的立法、司法、行政分立制,争论才大体结束,日本近代国家体制,基本就是在模仿普鲁士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立法方面,对外国法的引进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明治前期,主要模仿法国法。明治初,政府便组织人翻译法国法,同时以法国法为样板,进行民法的起草。1875年,聘法国法学家波阿索那德为顾问,开始系统进行各项法典的起草工作。1877年,波阿索那德完成了《日本刑法草案》,经内阁和元老院审议并增加了一些内容后,于1880年公布,1882年开始实施。同时还公布实施了波阿索那德负责起草的治罪法。民法起草工作也因明治初仅由日本人起草不成功,而改由波阿索那德主持,于1879年重新开始,除其中涉及民间习惯的家族法部分和财产继承赠与部分由日本人起草外,其余全由波阿索那德起草。主要以法国法为母法,同时也参考了意大利民法等各国立法。该草案于1890年公布,后因引起的争议较大,未能实施。此外,还根据法国法制定了一些单项法规。明治后期,对德国法的继受逐渐增多。1890年公布的商法(一般称为旧商法)和民事诉讼法,1907年公布施行的新刑法,都是由德国人负责,主要以德国法为典范起草的。1899年公布的新商法虽由日本人起草,也基本以德国旧商法为蓝本。此外,在波阿索那德民法草案被搁置后又重新起草的民法和192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受德国法的影响。
在司法制度方面,明治前期也是以学法国为主。1872年,在对明治初的法制改革作出重大贡献的司法卿江藤新平主持下,司法省聘法国人焦尔鸠.布斯凯制定了《司法职务定制》, 建立了由司法省临时裁判所、司法省裁判所、派出裁判所、府县裁判所、各区裁判所组成的司法体系,初步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三年之后,随着实行立宪政体的方针的确定,为了进一步强化审判权,实现审判与行政的彻底分离,又在具有留法经历的井上毅的促进下,以法国只进行法律审的撤销法院为样板,设立了大审院,并制定了《大审院诸裁判所职制章程》、《控诉上诉程序》,确立了以大审院为最高审判机构的独立司法体系。明治中期以后,随着法律系统向德国法方向的转变,司法制度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1886年,为了达到修改不平等约,收回治外法权的目的,以司法省顾问、德国人奥得.鲁道鲁夫为中心,起草法院构成法,于1890 年公布施行。该法以德国1877年法院构成法为蓝本,重新规定了日本的司法体系,成为与明治宪法配套的骨干法律。日本司法制度遂由法国式的转变为德国式的。
3.两国法制近代化中都遇到了引进西方法律与保持本国传统的矛盾,并都因此而引发了立法中的争论。
中日两国是有着东方传统的国家,在引进西方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外来法制与本国传统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主要都发生在对外来法制尚未充分消化吸收的近代化前期。
中国在清末法制改革中,围绕着某些法律的制定,出现了被概括为“礼法之争”的激烈争论。1906年,由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起草的中国近代第一部诉讼法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告成,由于该草案采取了西方的罪刑法定、公开审判等诉讼制度,特别是规定了陪审制和律师制度,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在朝廷交发各大臣讨论时,“各督抚多议其窒碍”(注:《清史稿.刑法志一》。)。 对朝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内阁大学士张之洞认为,该草案背离中国做为立国之本的纲常礼教,“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注:《张文襄公全集》卷69。)不宜颁布。此草案遂被搁置。
后不久,围绕着新制订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又出现了更为激烈的争论。这部完成于1907年的新刑法草案,尽管起草中吸收了一些中国旧律的内容,出台后仍受到猛烈批驳。由“礼教派”主管的学部指责该草案与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相背,力主按礼教原则重加修订。后经修订法律馆和法部修订,加重了对涉及礼教的犯罪的处罚,并增加了体现礼教原则的《附则》5条, 才作为修正案奏交资政院审议。但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在资政院审议前后,又出现了以资政院钦选议员劳乃宣为主的礼教派对修正案的驳难,认为修正案将礼教各条作为附则是本末倒置,要求将旧律中礼教条款直接列入新刑律。对此,主持法律起草的沈家本等据法理进行辩驳,资政院议员和许多大臣都卷入了争论,涉及的问题颇多,最后主要集中在“无夫奸”和“子孙违犯教令”应否科罪,以及子孙对尊长的侵害能否适用正当防卫等问题上。直至清朝崩溃,双方意见也未统一,该草案也因此而未能通过施行。
日本进行近代立法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着民法典和商法典是延期还是按期实施的问题而展开。1890年,在经过长期的酝酿起草后,明治政府公布了由财产、财产取得、债权担保和证据、人事等编组成的民法典,准备从1893年开始实施。同年还公布了商法典。但在法典公布的前一年,就出现了反对按期实施的意见,从法学士会发表《关于法典编纂的意见书》开始,形成了一股由法学、司法和政界人物组成的反对实施的力量。他们从历史法学派强调法律的民族性的理论出发,指责民法典照抄法国民法,没有体现日本的民族性。他们认为,日本应以祖先崇拜和忠、孝结合的国家主义为立国之本,以天皇统治为根本制度,而以法国法为蓝本而起草的民法典基于天赋人权的理论,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不适合日本的国情。有名的贵族院议员穗积八束甚至发出“民法出,忠孝亡”的论断,(注:[日]《穗积八束博士论文集》,有斐阁1913年版,第223页~227页。转引自日本近代法制史研究会编《近代法120讲》,法律文化社1996 年版,第132页。)对民法典进行责难。对此, 主张按期实施的断行派极力反驳,双方发生激烈争论。至1892年,随着延期法案被提交第三次帝国议会,争论的舞台也由社会而移至议会,最后经贵族院、众议院过半数通过,决定对民法典重加修订,延期施行。
中日两国近代立法中出现的争论,表面看来是不同人物间的认识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外来法在本土化过程中与原有传统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是东方国家引进西方法律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中日两国对西方法律的继受,就是在经历了这种矛盾与冲突后才趋向成熟的。
4.两国的法制近代化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不彻底性,且法制系统内的发展不平衡。
第一,在近代化阶段,两国都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国家。中国虽自戊戌变法时起就有人倡导法治主义,但由于国家体制中始终存在着法律所难以制约的权力,法的地位和权威性一直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之下。清末改革时期,仅进行了立宪的准备,宪政制度尚未建立,因而皇帝仍拥有临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和地位。进入民国后,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国家权力被纳入由法律规定的轨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法律中都有关于国家权力的规定,但在军人专政和一党独裁的局面下,这些规定究竟有多大的约束力,是大可怀疑的。从袁世凯“毁法”到“张勋复辟”,法律的尊严不断被军阀的武力所毁坏,而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又宣告了“党治”体制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从来没有实现。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通过1889年公布的宪法,基本确立了以依法审判和依法政为内容的法治原则。但该宪法同时又规定了天皇极大的权力,“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1 条);“天皇为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天皇成为国家元首, 总揽统治权”(第四条)。也就是说,天皇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内阁和议会都是辅佐天皇的机关,在天皇统治下实行权力分立。在天皇与法律的关系上,一方面天皇享有最高立法权,“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第5条);另一方面,天皇根据需要,可以敕令代替法律(第8条)。因而虽规定天皇依宪法条文行使统治权,天皇的实际地位仍超越于法律之上。这种状态下的法治,实际上是介于“韩非子式的法治”与近代法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与真正的法治还有一定的距离。因而日本学者也认为在二战以前,日本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法治,而没有达到实质上的法治。(注:[日]日本近代法制史研究会编:《近代法 120讲》,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第120页~122页。)
第二,两国的近代法律中都存在着带有传统色彩的不符合人权保护精神的内容。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清末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法律中保留了一些旧法中依伦常而同罪异罚的规定,除上文提到的清末“礼法之争”中涉及到的新法中保留部分体现礼教原则的内容外,北京政府时期颁行的刑事法律中, 也保留有这方面的内容。 如1914年公布施行的《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就规定将尊卑亲属关系作为量刑的一个标准,特别是尊犯卑处罚较常人为轻,实际上是减少了法律对卑者权利的保护。到南京政府时期,新制定的刑法对此作了修改,只规定卑犯尊加重处罚,偏重对尊者的保护,较前有所改进。但这一时期颁行的一些刑事特别法,如《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勘乱时期邮政抽查条例》等,具有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民主自由权的的性质。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首先是国民没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按照明治宪法的规定,国民都是天皇的“臣民”,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皆出自天皇恩惠,并且只可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第29条),从而给公民权利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照此规定,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来剥夺公民的民主自由权。1900年为压制劳工运动而颁布的《治安警察法》,1925年针对反体制活动制定的《治安维持法》,以及1938年为适应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需要而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都具有这种性质。其次是国民权利不平等。《治安警察法》禁止女子参加政治性结社;《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妇女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民法规定,女子结婚后,丈夫管理其财产,妻子的经济行为和诉讼行为须经丈夫许可。充分显示了法律对妇女的歧视。
第三,两国都未完全实现司法独立。中国从清末开始建立近代司法制度,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离,但直到1949年,这一过程仍未完成,最大的缺陷是县级审判机构未能普遍设立。清末变法时期,仅在中央和部分省试设了一些近代审判机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省级审判机构普遍设立,但地方县级审判机构的设立遇到困难,绝大多数县仍由行政长官(知事)兼理司法。到南京政府时期,曾计划大力推行县设法院的工作,由于战争的影响,一直未能完成,到1949年全国县设法院仅782所, 约占全国总县数1/3强,其余县除少数设立过渡性的司法公署外,多数仍由知事兼理司法(注:展恒举:《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47页~248页。),历史上延续已久的司法与行政混合的现象没有完全改变。日本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按明治宪法的规定,司法权由裁判所以天皇的名义依法行使(第57条),在法律上司法机构并不拥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二是除普通裁判所外,还设有隶属于行政等其他机构的特别裁判所,如行政裁判所为隶属于内阁的行政机关,作为违警罪即决裁判所的警察署也属于行政机关,实际上一部分司法权由行政机关行使,所以日本学者也认为日本近代的司法独立是不充分的(注:[日]染野义信:《近代转换中的审判制度》,劲草书房1988年版,第152页~154页;日本近代法制史研究会编《日本近代法120讲》,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第113页~114页。)。
第四,两国的近代法制都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即一方面如上所说,在法治和人权保护等方面未完全达到近代水平,而另一方面,在法律种类上却较早地出现了现代立法。中国在30年代初出现了被认为是现代法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和《工厂法》,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陆续制定了《租佃调停法》、《劳动争议调停法》,以及《国民健康保险法》、《劳动者年金保险法》等,法制系统的发展出现明显的不平衡。
三 两国法制近代化的差异
中日两国法制近代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者的进程和达到的程度上。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民族和社会构成复杂,并有着深厚文化积累的国家,完成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其他国家要长,古代两次大转折(春秋战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近代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虽然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无论是文化的调整还是社会体系的更新都远远没有完成。特别是政治上屡次发生政权更迭,且经常出现几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法制近代化,其进程必然是曲折复杂的。
从大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法制近代化大体经历了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改革时期、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等阶段,其间还穿插着南京临时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立法司法活动。虽然从发展趋势上讲,这几个时期的法制变化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都朝着近代化的方向演变,但从具体过程看,却不能不注意其多次出现的中断、退化与反复。
如前所述,戊戌变法时期就出现了关于法制改革的酝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力主实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同时,都提出了模仿西方,建立新的立法、司法机构和制定新法的主张,梁启超和严复等还明确提出应实行法治主义,并对中国的“人治”传统进行了激烈抨击。严复还通过中西对比,阐述了法律应保护天赋人权的思想。但他们的主张还未来得及实施,便随着“六君子”的被镇压而告结束。两年以后,在慈禧决定进行大规模变法时,法制改革才重新被提上日程,而且开始还仅限于与解决中外关系有关的部分,比起戊戌变法时期关于法制改革的酝酿,范围已有所不及。直到1905年清政府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才开始了与戊戌变法时期的酝酿范围大致吻合的较为全面的改革。而清末的改革尚未完成,又因清朝的崩溃而中断。其成果中除已付诸实施的部分,如《钦定大清商律》等新法和新建立的司法审判制度及监狱制度等基本被民国政府所继承外,其尚未施行的草案和未及推行的新制有许多被搁置。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以革命的姿态对待清朝的遗产,不可能完全沿着清朝改革的路径往下走。而以后的北京政府又被军人轮流把持,极不稳定,法制的创设在相当程度上受政治和权力争夺的影响,法制近代化难以正常进展。民国初的十几年里,议会三起三落,宪法几修几废,以至连最主张民主共和的孙中山也暂时停止了对宪政民主的追求,退到了“党治”的路上。立法方面也有波折,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法律,有些到段祺瑞时期便被废除,因而15年中虽然积累了一些成果,但数量不是很多,比之清末10年都略显逊色。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才又有较明显的进展,到1935年,初步完成了以“六法”为内容的近代法律体系。但此后出现的抗日战争,又使法制近代化进程受到影响,直到1945年,“六法”体系才大体完善,近代司法系统大体成形。而南京政府的立法和司法,也并不是在清末和北京政府法制基础上的直线推进,有些立法(如破产法)基本是从头开始,前几个阶段取得的成果,仍有一些丧失。
日本的法制近代化进程要比中国平稳得多。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基本确定了以天皇制度为核心的立宪体制,虽然曾出现过要求进一步实行民主的较为激进的自由民权运动和反对中央政府的士族叛乱,但都未造成政权更迭,更未能动摇既定的天皇体制,从而法制近代化得以在比中国稳定的环境中进行。
综观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可以看出,它基本是一个逐渐展开,步步递进的过程。明治初期,法制近代化尚未完全展开,所进行的改革主要限于两方面,一是按照当时的需要制定一些新法,如《户籍法》、《郡区街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以及关于报纸、出版、集会的条例等;二是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离,建立专门的司法机构。由于这一时期实行的还是天皇集权的体制,民意机关尚未出现,宪法的起草也仅在酝酿中,因而在立法体制等方面还没有实行近代化改革,法治主义也仅是个别精英头脑中的一种理想。到明治中期,经过一个时期的积累,再加上“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法制近代化全面展开,1889年,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第二年,按宪法的规定进行了总选举,并开设了第一届议会,产生了民意立法机关。 各项新法的制定也逐渐展开, 到1899年,基本完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创制,建立了按宪法、民法、商法、民诉、刑法、刑诉等六法编制的法律系统。与行政分离的近代司法系统和有关的制度也于这一时期形成。进入20世纪后,又为适应世界潮流,陆续对民法、商法、刑法、民诉、刑诉等法典进行了修改,并重新制定了破产法及其他一些新法。从总体看,在30年代以前,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是沿着明治维新以来的方向直线发展的,没有出现中断和大的反复。只是在进入30年代以后,由于法西斯统治的出现,法制方面才出现了一些倒退。
由于中国的法制近代化比日本曲折,因而完成同样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要比日本长。如关于近代立法机关,在清末就设立了作为议会前身的资政院,而且资政院在成立后也确曾按接近近代立法程序的方式进行了立法活动,已多少具有了近代立法机关的性质。但资政院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因清朝的崩溃而告结束。此后,曾出现过两届三期国会,存在的时间都很短,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立法院,中国近代立法机关才确定下来。由于按照国民党的理论,当时处于“训政”时期,立法院属于国民政府的下属机构,不由民选产生,与民意立法机关还有差距。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实行后,立法院才真正具有民意立法机关的性质。相比之下,日本完成这一过程要顺利得多,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起算,到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只经过了23年,其间还经历了过渡性的左院和元老院阶段。再如关于近代立法,中国从1900年便已开始了近代法律的起草和制定,直到1945年才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而日本完成这一过程只用了32年的时间。从两国法制近代化的总体情况看,中国的进程明显慢于日本,到1949年中国法制近代化告一段落,所达到的程度仍低于日本。
标签:立法原则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司法行政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德国民法论文; 行政立法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法律论文; 外国法制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