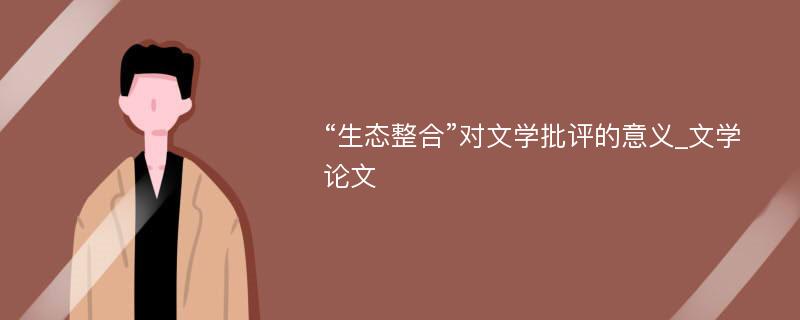
“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生态论文,意义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1)02-0015-05
八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1],提出生态学是否颠覆文艺学的问题。所谓颠覆是指生态学对文艺学相关理念、原理、方法所具有的挑战性和革命性。比如,从观念或言说立场分析:生态学强调以自然界一分子的地位认识自然界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承认自然价值,保护自然价值,抛弃以损害自然价值的方式实现文化价值,做到在自然价值基础上创造文化价值。如今,生态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生态学也已然成为当今的“显学”。可我仍然担忧:我们是否止于借用生态学术语谈论文艺学老问题;是否止于寻找中国古代“本土资源”而没有继续前行,尽管借用生态学术语和寻找中国古代“本土资源”都是必须的、合理的。这里所谓继续前行,是指进一步区分生态学与我国传统“自然观”的联系与不同;区分生态学中不同流派的观点对文艺学的不同影响。正是从这点出发,本文将阐释“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学批评思维方式的意义。
早在2000年,我国生态学家余谋昌先生就指出:生态学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思想,一种方法,以为生态学的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即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道德地位、道德待遇。承认不只是人有价值,生命和自然界也有价值,不只是劳动产品有价值,自然界的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产品也有经济价值。学术界也有人认为生态学在根本观念上具备颠覆性质,断言它将颠覆经典的哲学、文艺学、美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学科[2]。
2010年,王诺在《生态视角的人文社科研究之关键问题》[3]里就“生态批评”这个“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进行说明,他认为“生态批评”“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为“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整体的还是人类中心的。乐黛云先生对这篇论文曾给予高度评价,她说王诺“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区分,指出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环境主义的基本精神只是以人类为中心保护环境。这无疑是生态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这个重大进展的表现之一是充分认识生态整体主义在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学批评思维模式的推进作用。“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任何一个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有中心就一定有边缘,有非中心的部分,有周边环境。……如果不消解中心主义本身,如果依然延续中心主义的思路,我们仍然跳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而是把原来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动物中心主义’到‘生物中心主义’再到‘地球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
王诺得出结论:“生态整体主义是思维方式的一次革命,从中心论和二元论到整体论的革命,它强调整体但绝不预设中心。”我以为,王诺的这个结论是生态批评研究者对10年前余谋昌提出问题的一个回应!回到我的论题,“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观的意义在哪里?我认为其一是文学批评标准的;其二是文学批评思维方式的。
用“生态整体主义”重新看待过往文学史,可能会带来文学史秩序的改变;用“生态整体主义”眼光评判具体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也可能会带来与原先不同的评价,就如同艾略特说的现代作品对传统文学史秩序带来的改变。艾略特说:“一件崭新的艺术品一旦问世以后,它就使我们改变了对过去的作品的看法,那也就是说:它所发生的作用同时影响了它以前的一切作品……在新的作品出现以前,现存的秩序是完整无缺的。一旦有新的因素投入其间,为了保持协调与和谐,‘整个’现存秩序必须改变。每件艺术品对于那些不朽的巨著所形成的‘整个’秩序,本来就是有某种关系、比例和价值存在,现在这些关系、比例和价值势必因而重新调整。这就是新旧之间的调和。”[4]107艾略特说的是现代对传统具有的调整作用,由于对新作品价值的认可,人们会改变对原来作品的看法,那些原有巨著组成的秩序因此发生变化。“生态整体主义”则是因为其思想本身带来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文学批评标准改变了,文学史的秩序当然也随之改变,以对我国传统俗文学的评价为例。
郑振铎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也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说,所谓的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重视,而流传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5]4我国文人对俗文学如戏曲、民歌、小说的系统研究晚至元代,而且文人说到俗文学的时候总还是显得底气不足。元朝的钟嗣成曾以记载金元戏曲作家的传记和作品目录而成《录鬼簿》,这是现存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重要文献,还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戏曲史和戏剧批评著作。但在《录鬼簿序》里作者仍然表现出因肯定戏曲价值而“得罪于圣门者”的矛盾心理,因为我国古代诗文才是正统,惟是独尊。这当然是封建等级观念作祟,但是谁又能否定唯我独尊的面向地球上的一切生命这里面就没有等级观念的影响。
对俗文学的态度与评价涉及正统/非正统、中心/非中心的二元思维模式以及由二元思维模式带来的文学批评标准的正统化。如果从文学这个“物种”以及“生物圈”的宏观视角考察俗文学的价值,考察人就不再是“底气不足”,不再怀有“得罪于圣门者”的愧疚,而是理直气壮地说明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具体作用;俗文学在整个文学史发展中不可或缺。进一步说,我们如果不拆除文学批评“对象”人为等级的藩篱,就不能平等地对待所批评的对象。这个“等级的藩篱”是既定的,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之中。坚守思维方式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就显得非常艰难,而一旦坚守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评判就可能具备颠覆价值。这里,先举一个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英国18世纪晚期奴隶贸易研究的例子。
英国18世纪晚期的奴隶贸易在英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化的作用问题,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否定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海外贸易是欧洲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因素。其理由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海外贸易只占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在英国也只占国民收入的0.54%(1770年),海外奴隶贸易利润对英国资本形成的贡献最多不会超过12%。这就是说,从数量上看海外奴隶贸易对英国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作用是很小的。有位叫肯尼斯·波梅兰兹的学者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阐释分析这段历史,指出是“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而非原始积累使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了最大收益。英国从新大陆(美洲)获得大量“土地密集”(land intensive)的产品(如糖和棉花),从而缓解了英国自身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海外奴隶贸易的“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资本在数量上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它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6]对英国18世纪晚期奴隶贸易对其经济尤其是工业化的作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断语是“微乎其微”甚至是“没有作用”,在生态整体主义者看来却具有“关键作用”!两个判断天壤之别,后者对前者的颠覆作用不言自明。
对俗文学的价值判断也是如此。从文学“物种”以及“生物圈”宏观视角考察,俗文学在文学的“生物圈”内是与纯文学一样、一同存在的不同“物种”,她与纯文学同时生长在文学这个“生物圈”内,两者关系并存、互补,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冲突。我们可以说,从文体角度分析,没有先秦诸侯国无名氏的民谣(风),就没有以后的“采风”机构和从事相关收集活动的人士;没有各诸侯国的“风”,也就没有与风并存的雅、颂体的存在,没有孔子删诗结果《诗经》的存在。风是最早的俗文学之一,她与雅颂并存、互补,是最早的诗体“圈”中的一个“种”类,不可或缺。
在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中俗文学又具有“创作源”和催化剂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后来的文人从广义的俗文学里汲取养分,回归诗歌言志缘情传统,变革原有纯文学体式的发展过程。以我国古代诗歌史里的《古诗十九首》为例。
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和时代存在多种推测,有人认为是枚乘、傅毅或曹植、王粲所作,但均无据可考。学界公认《古诗十九首》为东汉末年非一时一人的文人之作,既是文人之作,可能就与俗文学关系甚微,事实却恰恰相反。《古诗十九首》与俗文学存在密切联系!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赤裸裸的、没有丝毫约束与刻意遮掩的诗歌语言,抒写人生感慨,传达生命信息,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些没有刻意遮掩的直抒胸臆,一方面成为汉代文人的正襟危坐与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有效过渡;一方面也传达出率真而大胆的反叛意味,是对儒家宗法制度的反动,是对温柔诗教的反动,也是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的先声。因此可以说,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体式上由民歌乐府发展而来,同时也秉承了民歌自由真率之传统,为文人诗歌注入了新鲜活力!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李白、杜甫或者白居易个人诗歌创作为例,作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研究,可以写出系列论文,那是一定的,此处不再赘言。本人以俗文学为例,旨在说明评价文学现象时,如果坚持“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坚持“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其结果多半富有颠覆价值和创新意味。
生态整体主义是思维方式的一次革命,重点是要超越“中心论”和“二元论”,上面我说的是如果超越“中心论”,在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因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文学史的原有秩序。这里再说明如何超越“二元论”思维方式的问题,这似乎更加困难。王诺在《莫兰的发展批判与科技批判》[7]里提到莫兰的“复杂思维范式”,认为莫兰的“复杂思维范式”的核心内容是对科技的批判。莫兰指出,“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也愈益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8]87其次,莫兰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缺乏社会责任、人类责任和生态责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既缺少科学的责任性又缺少关于责任性的科学”[8]87,这是莫兰对当代科学技术现状的一个基本判断。莫兰分析了科学家缺乏责任感的根本原因: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的经典科学观念认为,科学从原则上将事实与价值分离,“也就是说从它的内部排除任何伦理学的管辖权;在消除科学认识的主体的基础上建立它的客观性的公设。”[8]87科学把“为着认识而认识”当作自己的绝对律令,只要认识,不计后果。这一律令促使科学把任何戒律、禁忌和责任排除在科学之外,于是,“责任性因此是无意义的和非科学的。研究者从原则上和从职业上来说都是不需负责任的。”[8]87莫兰认为,这种把科学与伦理责任分离的绝对律令,如果说在科学刚刚兴起的时代和受到宗教政治排挤和威胁的时代还有其正确性和时代意义的话,那么,“在科学处于统治地位和威胁着其他事物的存在的时代就不再是正确的了”[8]95,“认为价值判断不适于科学研究活动的思想具有积极意义的时代结束了”[8]94。莫兰进一步指出,与社会责任感分离,必然导致科学不能认识自己,“不能科学地思考它本身,不能确定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不能预见它在当代的发展会导致什么——毁灭、奴役还是解放”[8]104,造成了可怕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还不自知,还不知道反省和自我批判。
其实,莫兰的“复杂思维范式”的思想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中国老子的智慧;一个是现代物理学理论,具体说来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传统物理学在思维方式上带有科学的简单化色彩,是对思维对象进行必要的分割和封闭,把它们压缩成一个简单成分,并排除一切非线性的因素,以获得理想的、理性的、标准化的成果。这里,所谓理想的是指认为观念能够反映现实,认为只有可理解的才是真实的;理性化的则试图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纳入一个一致的、有序的体系,不允许他溢出体系,因为我们需要用理性解释整个世界的存在;标准化就是要求消灭一切怪异的、神秘的、无法简化的现象。从伽利略到牛顿,秩序的地位越来越高,为此我们建立起一条铁的法则,亿万颗星星都按照这个法则运行。
这种认识论上的坚强信念,直到19世纪才受到根本的动摇。到了19世纪,在物理学秩序的中心地带冒出了一小团的无序。开始它们被封闭在瓶中,仅仅得到一点气体,可后来它变成杂食动物,食欲大增,渐渐威胁到整个宇宙——那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它引入了一个“能量耗散”这个新概念。即所有能量的转换,所有利用热能所做的功都必将引起能量的耗散。这种利用热能在转换和做功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逆的能量的省耗也就是“熵”。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个极其专门的知识领域,在此我们不可能进行深入的阐释。应该注意的是它的内涵包括了或者说是引入了有序和无序的概念,即突破了第一定律中有序的限制;同时它还引进了组织与组织解体的概念,因为构成一个系统秩序的是一个能够把各种异质成分组成一个整体的组织。
古典科学
无序——互动(结合)——有序/组织
热力学第二定律
有序/组织——无序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矩形封闭的线条去掉,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图示了:
无序——互动——有序/组织——无序
因此,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人们的认识带来了新的消息
“——在时间长河中有着并将永远有衰退和耗散。
——任何有组织的事物,任何有组织的生物都不可能逃脱衰退、耗散、解体的命运。任何生命都不可能逃脱死亡。
——一切创造,一切发展,生生相息,甚至一切信息都必须付出熵的代价。
——一切生物,一切系统都不可能孤立地再生。”[9]58
在理论思维方式上我们可以引申出这么一个观点:有序与无序的共生。它引进了逻辑的复杂性:必须在有序概念中看见无序;在无序概念中看见有序。甚至可以说极端的无序复合体包含着有序,极端的有序复合体包含着无序。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互补的、竞争的和对抗的。
比较而言,古典科学的思维是线性的、孤立的、有序的;现代科学则将无序纳入了自己的视阈,并且认识到无序的普遍作用;只有将这两种认识结合起来,才可能接近事物存在的本真状况(至少从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上说)。那就是无序——互动——有序/组织——无序的回环不息的运动过程。[10]
我们中国老子的智慧是什么?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看到对立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如《老子》第二章[11]:“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如果我们能辨别美的事物,那么丑的观念也就有了;都能判断出善的事物,那么关于不善的观念也就有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有和无的事物相互生成,难和易的事情互相促进,长和短东西互为显示,高和下的位置互为呈现,音和声彼此相和,前和后的事物连接不断。)“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有道的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不言”的教导;事物兴起而不加干涉;成就了事情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事物成长而不显示自己的才能;功业成就而不自我夸耀。正因为他不自我夸耀,所以他的功绩不会泯没。)
与老子思想不同,简单化思维最突出特点就是“二元论”或曰“二元对立论”。将复杂对象分为两部分,非此即彼。例如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划分。将内容和形式纳入二元对立的范畴,在开展文学批评的时候,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会儿偏重内容,一会儿偏重形式;也容易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变向转换简单认定为是重形式或者重内容、重内部研究和重外部研究等系列二元对立观念的转换。将内容和形式纳入二元对立范畴的文学批评,还容易让批评者随意拿来不同的理论,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既免除“武器的批判”,也“遮蔽”当下问题的特殊性,或者放下正在研究的问题,转而言说另一个所谓的具体问题或者新鲜问题。免除对“武器的批判”,搁置对本土具体问题的追问,使不同问题总是陷入同一个解题层面。没有深入研究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本土具体问题,没有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停留太久的时间,没有将问题提炼成文学理论的命题并继续深入研究,这样的文学批评当然不可能获得理论创新的成果。
当然,“一分为二有个好处,就是使得你对一个笼统的、囫囵的、混沌的那个‘一’做些非常明晰的划分。不能只见其一,不知其二”,问题在于“不能只知其二、不知其三”。这知其三就是“和”,是使对立的双方组合成第三个东西,由对立变成了同一,由二变成了一。如“和面”:“拿一点面粉、一点水放在缸里,面粉是干的,水是湿的,一个固体,一个液体,但是你把它们混合起来,最后形成的东西,它既不是水,也不是粉,同时既有水,又有粉。这就是‘和’的意思”[12]。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对于文学批评者,重要的是看到内容和形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学文本是那个“三”——内容和形式组合成的第三个东西,由对立变成了同一,由二变成了一,即艺术品本身。
由一到二,是将笼统、囫囵、混沌的那个“一”划分为“二”,它带来逻辑及其分析的明晰性,这是传统物理学带给我们思维方式的好处,但同时又带来思维的简单化;如果在简单的二分法中又只强调其中的一方占有中心位置,另一方就只能处在边缘,其作用也将是次要的,这就不仅是简单化,它可能将简单化带到看似复杂的思维过程,比如,从只重视内容到只重视形式,重视的对象虽然有了变化,其文学批评的结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从思维方式上看,只重视内容或者只重视形式两者是一样的,因而具有更大的迷惑性,由此我们可以说“去中心化”比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加困难。由二再到三,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是不同关系组成的“和”——这些不同关系包括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关系组成的“和”,这才是“生态整体主义”对我们的最大启迪。
“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表现在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学批评理论思维方式这两个方面;是对这两个方面可能存在的“中心论”与“二元论”的超越!比较而言,超越“中心论”比超越“二元论”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只有不预设中心,才能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学批评对象;只有将线性的、孤立的、有序的思维拓展到整体论的、复杂性的思维,文学批评才可能具有创新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