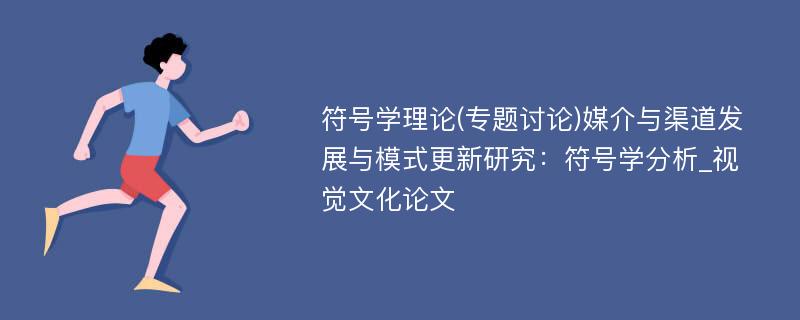
符号学理论发展与模式更新研究(专题讨论)——媒介与渠道:一个符号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媒介论文,符号论文,渠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6-0184-13
一、媒介、传媒、渠道、体裁
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有一系列术语一直被混用,例如媒介、传媒、渠道等。这几个术语非常重要,而且随着电子时代来临越来越重要。所以本文一开始就作一个辨析。
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索绪尔称为能指,也可以简单称为符号。符号文本的文化类别称为体裁,同一体裁往往可以通过不同媒介传送,例如一首诗可以读出来、录音放出来、写出来、印出来。符号依托于一定的物质载体,载体的物质类别称为媒介(medium,又译“中介”)。媒介是储存与传送符号的工具,因此传播学中常称为“传送器”(transmitter)。媒介与载体(vehicle)的区别,在于载体属于个别的符号,例如一封信的载体是信纸上的字句;而媒介是载体的集合称谓,是一个文化概念,例如可以说书信是一种媒介。叶尔慕斯列夫就认为媒介即符号系统的“表达形式”[1]。但是,他又把符号能指称为表达层(plane of expression),因此能指形式往往与媒介混同。
媒介一词的西文medium为拉丁文中性单数,其复数形式为media,意思即“各种媒介”。在当代文化中,media指专司传达的社会体制,中文另译为“媒体”或“传媒”。而所谓体裁(genre),则是文化对符号文本形式的集合分类。
渠道(channel)的定义是“模式化的媒介”(patterned medium),这个定义并不明确。渠道指的是符号信息到达接收者感官的途径,是媒介被感知的方式。从人类的传达行为上分,可以有物质、身体、图像、声音、副语言、语言(包括文字)等七类。西比奥克把渠道分成两大群:物质的(液体的,固体的);能量的(化学的、物理的),而物理的又分成视觉(日光、生物光)、听觉(气体传达的、液体传达的、固体传达的)、电力、热力[2]。这样就有九类细分的渠道。如此分类,实际上过分技术化。例如味觉究竟是固体还是液体的,是物理还是化学的?就不是符号学的研究范畴,符号学只满足于说味觉是一种渠道。
渠道应当用接收者感知的器官来分,因此有视觉(以及光谱外的红外线、紫外线)、听觉(以及动物能听到的超声波)、味觉、触觉(以及附属于触觉的热觉、“电觉”)、嗅觉等五类。人类文化使用最重要的渠道是视觉与听觉,而视觉比听觉重要得多:人类收到的符号信息80%来自视觉。
以上这些区分很细微,不容易弄清楚,一般研究者也无暇细分。本文讨论理论符号学,不得不尽量区分清楚。实际上区分是必要的:渠道是作用于感官的物质介质,媒介往往是符号传送的社会性构造,一种媒介可以社会化为一种媒介。以书为例:视觉是一种渠道,文字是一种媒介,书籍出版业是一种传媒,而小说或历史是体裁。
这里最容易混淆的是渠道与媒介:渠道是感觉方式,只能延伸而不可能改变其根本范畴。例如电子技术延伸储存戏剧演出,但是最后依然要让人看见;而媒介是指符号传达的物质方式,电子技术是文化变迁中的重大动力。有人认为在人类文化中,文字、图像、言语、影视技术、电子技术、身体、表情,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远比嗅觉等储存传送的信息量大得多,不能再称为媒介,而应当称为渠道。更多的学者坚持语言文字是单独的渠道。这当然是对的。但渠道依然必须是感觉性的,不能因为文化变迁而改变。
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媒介不是中立的,媒介本身不是符号过程中的可有可无之物,媒介的性质直接影响到符号传送的可能结果,即影响到意义解读。符号表意总应当与适当的媒介配合。例如情书最好手写,不用电脑打印;情歌最好曲调柔软婉转,不用重金属摇滚;情诗最好不用江阳韵。
媒介本身有时候就会成为符号,例如刺绣的针法可能比所绣的内容更有意义;一幅书法或泼墨山水,首先强调其笔法画艺,至于写的是什么字、画的是什么景色,倒是其次的事。因此,媒介是符号表意的成分,有时是符号最重要的部分。对书画意义的解释,往往不是针对书画的内容,而是针对工具的运用。著名艺术理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甚至认为现代艺术的特点是“节节向工具让步”,让媒介载体代替内容成为艺术的主导成分。
媒介就其功能可以分成以下三种:
(1)记录性媒介。即能保存符号的文本。例如远古的岩画等图像,古代的文字书写与印刷,现代的电子技术。记录性媒介造成文本的过去性,这种媒介造成的文本是成品,如读者已经无法改变小说的结局。
(2)呈现性媒介。往往用于表演,如身体姿势、言语、音乐、电子技术等。呈现性媒介造成文本的表演性、当下性。呈现性媒介是一次性的、当下进行式的,如果用于表意(例如台上演出一个故事),会让接收者觉得后果不明,因而出现强烈的“戏剧反讽”,接收者有干预冲动,一如在对话中听者与说话者可以互动。
(3)心灵媒介。心灵媒介是组成幻想、梦境、白日梦等的载体,它们往往被认为是符号表意的草稿,符号发出者大量的表意意图最后并没有形成表意,成为自我符号。心灵媒介形成的往往是“文本草稿”,但是人能够表现的只是大量草稿的冰山一角。
媒介与技术有重要关联,媒介与技术的结合,造成人类文化的巨变。动物符号行为绝大部分只能是超短距的。人类的五个渠道中,触觉至今是超短程的,嗅觉与味觉也比较短程;听觉、视觉以前是短程的。现当代的电子技术使呈现性媒介可以轻易地转化为记录性媒介。媒介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五官得到延长。符号信息的发出、传送、接收,就可以克服时空限制,越过大跨度间距相隔,落到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人类文化之所以成为符号文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被媒介技术改进了的渠道,保证了文化的表意行为能够被记录、被检验,保留给后世,这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最重要保证。
可以说,渠道属于生理感觉,媒介属于物质文明,而体裁从属于文化实践。因此,媒介似乎与意识形态不直接关联,很容易被另一个文化接受过去;而体裁则是高度文化的,跨文化流传时会发生一定的阻隔。摄影术媒介的普及推广并不难,任何文化很难抵制技术上的进步,而“婚纱照”体裁的接受就会出现文化阻隔,不会跟着摄影术走向全世界。
二、多媒介文本的联合解码
许多体裁可以由多种媒介构成。例如连环画是一种由图画与文字两种媒介组合而成的体裁;电影这种体裁,其中包含连续的图画造成的动态影像、声音、音乐、文字、语言等多种媒介。多媒介体裁(multi-media genre)看起来是现代技术的产物,实际上自古以来一直有:歌曲是一种从人类文明开始时就有的体裁,其中的媒介有语言、音乐以及演唱者的身姿;中国画经常有文字(印章、提款)配合,可以说是图文媒介结合的最早例子;至于小说配插图,则是世界各民族通用的做法。戏剧据说有13种渠道,是一种复杂的媒介体裁。当代电子传媒更容易做到多种媒介混合,例如电影的表演、特技、音乐、声音等,可以分别录制然后剪辑拼合,这就让电影进入工业生产流程,也造就了这个现代“奇观”体裁。
一般说来,多媒介配合能够使表意更加明确、丰富。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与席勒《欢乐颂》配合之完美,已经让人不可能想象没有合唱乐曲如何终结。20世纪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出现,曾经使不少电影从业者认为,电影艺术会因为过于接近戏剧这种强势体裁而走向穷途末路。雅柯布森否认了这一说法,并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写出《电影在衰落吗?》一文,认为多媒介将使电影艺术焕然一新[3]。
也有人翻过来思考,认为媒介越多艺术感染力越强。例如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坚持认为歌剧是一种“集合艺术”,是最理想的艺术门类,感染力的强度,与同时在观众感官上起作用的渠道数目成正比。事实上,我们只能说媒介多能增加表现力,却不一定能保证艺术的优劣,毕竟艺术优劣不全靠于媒介的品质。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戏剧演出花样百出、舞台华丽,而艺术水准却很平平。
符号文本的这个多媒介拼合过程也发生在信息接收者头脑中。由于多媒介文本的各个媒介表意不一定对应,因此解释者不得不对各媒介传送的意义分别进行解释,然后综合起来。例如戏剧说话与表情不一致,歌曲的词与曲调不一致,音乐的曲调与标题不一致,电影的画面与对话互相不一致,这时候如何解释就成了需要斟酌的事。
对多媒介文本作联合解释,往往需要弄清究竟何者是主媒介。经常有一个媒介是主导性的,其他媒介围绕着辅助它,否则如果媒介信息之间发生冲突,解释者就会失去综合解读的凭据。一般而言,主媒介是由体裁的文化程式决定的,体裁不变,主媒介的定位不变。究竟何者为主媒介,并不取决于某个媒介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媒介表意的清晰程度。在各种媒介汇集的体裁中,主导媒介往往是文本中连续、不间断的渠道,这个媒介往往构成主线,其他媒介因为间断而只能为辅。
电影中的主媒介一般是镜头画面,因为画面是连绵不断的。在电影的多媒介竞争中,镜头表现的动态画面成为主媒介,语言、音乐、声响等为辅。由于电影艺术的超熟发展,电影观众的充分成熟,媒介的反讽张力更为复杂而有趣。美国电影《雷格坦音乐》(Ragtime),其中的女主人公已经不爱她那个伪君子丈夫。当丈夫对她说:“我得离开了。”女主人公说:“别把我一个人撇下。”她说这话时,特写镜头显示了她的表情冷淡。因此观众可以体会到女主角的实际意思是“走你的吧!”人物说的语言与人物表情画面意义正好相反,而画面传达的是正解意义。如此安排,人物的心理和文化处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能够很细腻地表现出来。
在歌曲的多媒介表意中,主媒介是歌词,歌词决定歌曲的意义解释。《社会主义好》无论怎么唱,哪怕用摇滚风格来演唱,都是颂歌。但是电影《盲井》中几个矿工把词改了,就变成讽刺歌曲。2007年风靡一时的歌曲《香水有毒》,曲调非常优美,歌手胡杨林唱得也很动听,但是春晚进了大名单,在三审时还是被拿下,因为歌词有“爱情不专一”的暧昧倾向[4]。可见,音乐之优美改变不了歌词的主导意义。
网上的“超文本”经常同时使用文字、图像、音乐等多种媒介。如果接收者解释三者背后的发送者意图不一致,那么到底何者为主导媒介就成了一个问题。陆正兰讨论过网络诗歌媒介不一致形成的张力,“《拳击》一诗,画面上是拳击手,充满了力量和攻击性”,而主媒介则是文字,深思人类心中的野蛮,音乐缓慢而忧伤,这样各媒介之间便出现反讽与对立:人类以竞技和娱乐的名义发泄兽性。“三媒介不必合一,不合一的效果更好,实际上复杂意义只有在多媒介冲突中才能出现。反过来,各媒介运载的符号文本之间,产生发人深思的张力,更能挑战性地运用各媒介的优势。”[5]
有时候多媒介信息冲突会产生非常微妙的效果。英国电影《滑门》(Sliding Door),女主人公赶回家发现男友正在有出轨行为,室内放着流行音乐。看到两个人在匆忙遮掩,女主人公说:“我从来不知道你喜欢Elton John的歌。”男友说:“有时候也喜欢。”这个对话与场面完全不沾边,更加凸显画面上的尴尬场面:男的“喜欢”的当然不是某个歌手。对话与视觉场面完全不相配,而反讽细巧的“英国式幽默”就由这种不一致而产生。
三、通感
表意被束缚于某种载体并不是符号本质的要求,因为意义本身并不是物质的。摆脱载体的束缚成为人类使用符号时很难摆脱的一种冲动。一般的符号表意追求效率和准确性,这种冲动往往不显;艺术符号着眼于符号过程,因此在艺术中出现各种逃脱载体限制的努力,符号学把这种情况称为“跨符号系统表意”(transsemiosis)。但是此种情况可以分成两种局面:“通感”是跨越渠道的符号表意,而“出位之思”是跳出媒介体裁的冲动。两者截然不同,不可不辨。
钱钟书于1962年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通感》一文,他的雄辩和广征博引,尤其是大量中国文学的例子,使中国学界折服。通感也成为广为人知的文学手法,而且似乎是中国文化本有的诗学范畴,不是一种西方传来的观念。实际上许多符号学的基本范畴,无关乎中西,是人类文化共同的表意方式。
“通感”(synaesthesia)在心理学上称为“联觉”(aperception),是跨越感觉渠道的表意与接受,其机制与“内模仿”可能有关。通感的普遍存在,说明不同渠道的符号之间可以互相比较。莫里斯称之为“感觉间(intersensory)现象”,即“像似符号”的发送与感知、接受落在两个不同感官的领域中。通感是跨感觉渠道的表意,是跨越性像似符号,但是各种渠道之间哪怕可以进行比较,也无法表现出来。
在人类文化的表意实践上,通感是用语言写出两个渠道之间感觉的比较,而不是两个渠道的直接比附,因此通感往往被视为一种特殊比喻,即修辞问题[6]。例如,可以说某种声音(类似视觉上的)“明亮”,某些声音(类似触觉上的)“锐”或“钝”,可以说有的笑声“尖利”,也可以说夏威夷衬衫的图案(类似听觉上的)“喧闹”。
从心理学上说,通感似乎是精神异常的结果,往往是遗传所得的特殊能力。医学家发现有自闭症(autism)的儿童经常表现出此种能力,也有一定比例的成人能以一个以上的感觉感知某个刺激,也就是大脑的“跨区域激活”(cross-activated)。有人认为这种异常能力是才能,有人认为是畸形。纳博科夫的小说《才能》(The Gift)把通感者描写成超越世俗经验的天才(类似的小说有Jane Yardley的《Painting Ruby Tuesday》,Wendy Mass的《A Mango-Shaped Space》等),但是女作家格拉斯(Julia Glass)的小说《The Whole World Over》则把她的通感主人公看成病态。社会生理学的统计数字竟然从1/20到1/200 000不等,可见人类多多少少有一点“通感异常”。
通感只能用语言作二级表现。语言描写感觉,本身不是通感。但是语言能同时描述几种感知,而一旦相比较地记录或描写跨渠道的感觉,就自然形成“跨渠道比喻”。除了语言,其他符号体系能否描述通感?理论上说不排除可能性,但实际上找不出例子,因为关于任何渠道的符号的讨论必然要用语言,既然很难用图像讨论图像,用图像讨论声音就更难。这就是为什么在艺术家中诗人最得益于通感。著名的例子有: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苏轼“小星闹若沸”都是听觉修饰视觉,杜甫“晨钟云外湿”是用触觉修饰视觉。其他艺术家并非没有通感,只是他们用语言机会少,表现得也比较少。画家称红黄为“暖色”、蓝白为“冷色”,是视觉与触觉的相同。音乐家认为音调有色彩,例如贝多芬认为b小调是“黑色的”,似乎完全是主观感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与斯克里亚宾关于音乐色调曾有争论,但是他们都同意D大调黄色、F大调青色、降A大调紫色。这些就很难与专业之外的人交流。
通感在佛教哲学中被称为“六根互用”,六根是五种感官加上“意”,“意”的对象是“法”,这很接近所谓“概念比喻”。“互用到”“六根”,就超出感觉,进入了超越感觉的感觉。所以通感不只是基于“感觉可以像似”,而是可以发展到非感觉,某些成语如“秀色可餐”、“大饱眼福”,用的是味觉,描写的却是概念。《乐记·师乙》中描写音乐“如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如端,如贯珠”,都是把符号表意的渠道跨符号系统地扩展到概念范围。艾略特称赞玄学派诗人能够“像嗅到玫瑰一样嗅到思想”,应当也是属于从五官到“意”的通感。
四、出位之思
通感是跨越渠道的努力,主要表现为一种语言修辞手法;而出位之思是对另一种体裁的仰慕,是在一种体裁之内模仿另一种体裁效果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风格追求。两者似乎都是摆脱符号载体的倾向,实际上很不一样。
每一种艺术体裁有自己独特的物质媒介,也就不得不受限于这种媒介的表现能力。而艺术总是努力摆脱载体的束缚,试图达到别的体裁能达到的境界。这是艺术家常见的冲动。陆游诗云:“情知言语难传恨,不似琵琶道得真。”
“出位之思”(Anders Streben),原先是德国艺术学家用的术语,“出位之思”是钱钟书的翻译。英国艺术哲学家瓦尔特·佩特在1877年出版的文集《文艺复兴》一书中首先详细讨论了这种现象,他把出位之思定义为艺术“部分摆脱自身局限”的倾向。佩特说:“建筑尽管自有规则……却似乎追求达到图画的效果,而雕塑企图跳出自身的行事的条件而追求色彩。”同时,他总结说,“所有的艺术都追求音乐的效果,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有可能区分形式与内容,但是艺术都想消除这种区分”,而音乐正是最不容易消除形式与内容的体裁。但是,反过来,“大部分美妙的音乐似乎都在靠拢某种形体,某种图画品质”。佩特警告说,不要把出位之思视为“仅仅是比喻”(mere figure of speech)[7]。而究竟应当视为什么,他没有说。
追求其他体裁的效果是艺术符号表意的一种自然趋势,体裁是载体、渠道、媒介这些符号文本的物质形式的文化程式。符号表意依靠体裁,但是艺术本性是追求新奇,受体裁限制总是很不舒服的,因此艺术家很自然地追求超出体裁限制的表现形式,以出奇制胜。
出位之思不太可能明显地出现于非艺术的体裁中,因为非艺术的符号表意要求效率与准确性,这就必须在体裁范围内充分利用程式的优势。如果要追求某种超越此体裁的效果,就干脆换一个体裁。例如发电子信者,如果要传送文件图像(例如需要签字),与其在电子信中发挥出位之思,还不如去发明扫描器和图像传送技术,形成一种新的体裁。
因此,佩特举的例子都是艺术家的跨体裁“仰慕”,有意混淆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只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表意方式,并不是真正进入另一个体裁。他所说的“部分摆脱”,用词极为准确,如果真正跳出体裁,例如诗真的做成绘画,即所谓具体诗(concrete poems),反而受双重限制,鲜有成功。因此电影追求绘画效果、器乐追求非乐音(自然音)效果、建筑追求舞蹈效果等等,只能偶一为之,做的人多了,反而无新意。
也有同一时期的各种艺术体裁共同追求某种效果的例子,如十七八世纪的巴洛克风格,建筑、音乐、美术共同追求装饰画的效果:在建筑设计上加上过多的雕饰,浮夸的结构;音乐追求豪华、夸张动势,讲究低音复调、上旋律和低音旋律之间相互制约;而诗歌也追求富丽典雅、遣词造句繁复、音韵格律复杂。
有时候两种体裁之间还表现为互相仰慕,例如象征主义诗歌对音乐有异常的兴趣,超现实主义诗歌则刻意追求绘画效果。19世纪法国的印象主义音乐深受象征主义文学和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总是试图取得“描绘”效果。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管弦乐作序曲《牧神午后》,就是试图模仿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同名诗歌,它的音色与风格都渲染出在炎热的太阳下昏昏欲睡所出现的种种幻觉。马拉美在欣赏《牧神午后》演出后说:“这首乐曲发挥了我的诗的感情,它记录的景象比色彩所能做到的还要生动得多。”马拉美可能是在回敬恭维,但他也可能是真心的,因为文学家一向钦慕音乐的境界。
文学对音乐的仰慕,例子更多。例如在结构上文学对音乐就有诸多借鉴。海伦·加德纳认为:“由四首诗组成的《四个四重奏》,每一首都分成了五个部分,而这五个部分都有自己的五个乐章,有引子、呈示、展开、再现、结束,结构完全对应贝多芬作品132号的《A小调四重奏》,就连诗歌中的意象不断重复、变化,也类似音乐中的不断再现和变奏。”[8]艾略特这种模仿有点表面化,明显是佩特说的“比喻做法”,有的作家做的则比较细腻。米兰·昆德拉的《笑忘书》被很多评论家称为“音乐思维的小说”,是用音乐的变奏曲和复调手法写出来的。米兰昆德拉曾为小说艺术提出三点纲领,其中有两点就和音乐有关。他提出应创造一种“彻底剥离”的新艺术,运用省略、浓缩的技巧来揭示世界的复杂性。他自己说,这个观点来自捷克音乐家雅那切可的启迪,“小说摆脱小说技巧、小说言语表边的自动性,使小说增强其密度。”[9]他把可以写成七部小说的材料包容在《笑忘书》中,全书用音乐中的对位方法将“笑”与“忘”,两个主题在各部分变奏发展。
应当说,“出位之思”常常只是艺术家的意图,符号文本中很少能充分体现这些意图,解读时更不容易体会“出位之思”。熟悉音乐的罗曼·罗兰,借他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口说:“他们(法国音乐家)不用文学做拐杖,就寸步难行!他们勉为其难地描写的主题,简直幼稚可笑,不是果园,就是菜园,或是鸡窝……他们满怀信心地在乐谱上写些有韵或无韵的诗句,就像小学生或没落的小报记者一样。”[10]
但是罗曼·罗兰自己用文字描述音乐,也不高明。请看这一段:“他生命的音乐已经融成了一片光明。空气、海洋、土地,都成了交响乐。意大利多么善于用天生的艺术才能来指挥这支乐队啊!……这是五光十色的音乐,一切都是音乐,一切都在歌唱。”[11]这不是罗曼·罗兰的错,文字描写音乐很难不笨拙,刘鹗《老残游记》写明湖居听梨花大鼓那样的技巧,足以令大部分作家汗愧。
艺术家也都明白符号文本的体裁规定性是难以跨越的障碍,出位之思只能偶然一试,着迷于此只能自露其短。但是文学史和艺术史依然充满了类似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德国电影《罗拉快跑》明显是模仿电子游戏,一次不成功可以重新起头再来一次,直到达成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是难得见到的出位之思的成功妙例。在当代文化中,小说与电影模仿电子游戏的“多选择”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形式手段,在《黑客帝国》、《香草天空》等影片中甚至成为核心主题,成为艺术与现实之间应和的基本点:当争夺意义的控制与被控制成为艺术中主人公想弄清的主要困惑,那么现实究竟是意义表达还是被表达的意义,就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