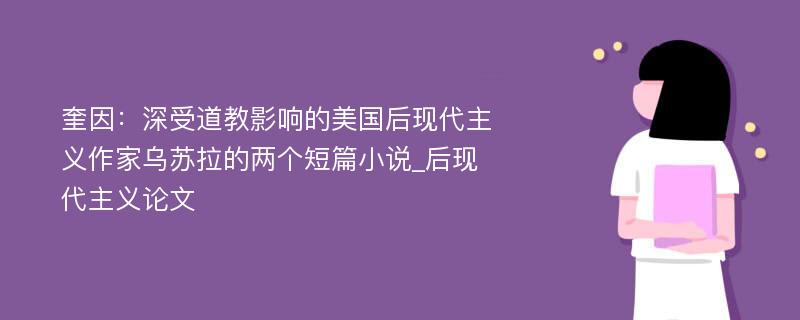
深受道教影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女作家厄秀拉#183;勒#183;魁恩——兼评其两个短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女作家论文,美国论文,短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2)05-0003-07
厄秀拉·勒·魁恩(Ursula Le Guin,1929— )是把科幻小说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结合得 较多的美国当代小说家。她往往利用科幻小说的写作素材来探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经常 关注的人类的生存状态问题,尤其是女性的问题。她在科幻小说中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使 她成了批评家眼中与弗吉尼亚·吴尔芙并驾齐驱的“女祖先”和为科幻小说的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的“女领袖”。(注:Elisabeth Sherwin,“Meet the High Prietess of S cience Fiction”,July 27 1997 gizmo@dcn.davis.ca.us.)她在小说创作手法上也做 了多种探索和大胆尝试,不仅创作了幻想小说、科幻小说、现实主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 等小说,而且还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解构思想和戏仿、拼贴等手法,创作出了一系 列浸润着后现代主义写作特征的社会科幻小说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科幻小说(cyberpunk) 。此外,她在思想意识层面也极为大胆,与众不同。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不是 基督教徒,而是信仰中国道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美国作家西奥多·斯特金(T heodore Sturgeon)在1989年《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厄秀拉·勒·魁 恩:“害怕民主会发展成独裁;赞美勇气、毅力和冒险精神;对于语言,不仅热爱和讲 究,而且在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了探索,也许称之为交流。但是,最重要的是,厄秀拉· 勒·魁恩几乎以奇异的方式考察、攻击、解密、记录和披露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注:Paula Geyh,etc.eds.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A Norton Anthology (New Y ork,1998),pp.519-520.)这也许是对厄秀拉·勒·魁恩较全面的评价。
厄秀拉·勒·魁恩192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她的父亲是现代人类学 的奠基人之一,母亲是个心理学家和作家。勒·魁恩1951年毕业于腊德克利夫学院(Rad cliffe College),获学士学位,并于195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她主要研 修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奇文学,尤其是法国的传奇文学。毕业后,她于1953年 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去巴黎学习一年,并分别于1968年和1975年再次获得该项资助去 伦敦呆了两年的时间。1953年她与历史学家查尔斯·勒·魁恩结婚,并最终在俄勒冈州 的波特兰市定居下来。
勒·魁恩是个多产作家,到目前为止,她已发表了80多篇短篇小说,2个散文集,10部 儿童读物,几卷诗集和16部长篇小说。她的著作已发行了300万册,这使她成了北美大 陆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她不仅著述丰富,而且还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雨果奖 、纳布拉奖、卡夫卡奖等多项大奖,使她在美国当代文坛牢固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道教思想的影响
勒·魁恩虽然从未到过东方,却对东方的哲学和宗教非常感兴趣,对中国的道教更是 情有独钟,道教思想构成了她思想意识中的重要一维。她认为道教是“一种和佛教交织 在一起的古老的神秘主义,实用而且是无神论的。它先于上帝而且超越了上帝”。(注 :Le Guin,“Summer Reading”,Mother Jones May/June 1995,v.20,no.3(p.34.).)她 不仅从14岁起就开始阅读老子的《道德经》,而且还对不同的译本进行了研究和对比, 并于1997年出版了她自己编纂的《道德经》译本。由于她不懂汉语,因此她的译本只能 说是解释性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虽然她的《道德经》不能用来作为一种学术 性的参考或指导,但它却是一本通俗易懂而且颇有影响力的关于“道”的著作。有批评 家称它是“宗教文本中最可爱的著作,它有趣、敏锐、亲切、朴实、非常令人震惊而且 永远令人爱不释手”。(注:Review of Shambhala Books:Tao Te Ching,ed.Ursula Le Guin.
道教对勒·魁恩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影响了她的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她对道教 中幽默和温和的特质非常着迷,认为自里根掌权以来,美国陷入了对作为基督徒的无节 制的自我庆贺之中,人们似乎很害怕说任何反对基督教的言辞。这使她很反感,她觉得 她有义务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她说:“我对上帝的思想从来就不感兴趣。它不是我的 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它对我没有太大的意义。那就是道教吸引我的其中一个原因。我在 道教里可以发现一种完全无神论的思想结构,那是一种神秘主义。”(注:Jane Slaugh ter,“Ursula Le Guin”,The Progressive,v.62(Mar.1998),p.39.)这种大胆的叛逆思 想在美国的基督教文化氛围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她因而招致了许多敌人。即使如此, 她仍然义无反顾地痴迷于中国的道教思想。她对道教的两个主要理论最感兴趣,一个是 非主动理论:人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另一个是反作用力的相对性理论: 两个反作用力是相互依赖的,它们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平衡。这两个反作用力分别由阴和 阳来代表,它们由黑、白两条涡流形成的圆圈来表示。它们互为生成和结束。道教的这 两个主要理论在她最早创作的《土海三部曲》中就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土海三部 曲》包括《土海术士》(1968)、《阿图安的坟墓》(1970)和《最远的海岸》(1972)3部 小说。它们是勒·魁恩对幻想小说所做的最早尝试,也为她带来了许多荣誉,囊括了包 括纽伯里银质奖章以及由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颁发的4项年度儿童图书奖。这些作品深得 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在美国风靡了20年的时间。土海是勒·魁恩虚构出来的、在气候上 与美国很相似的一个地方。这3部有关土海的小说总的来看都是关于青少年心理成长的 故事,其中都浸润着浓郁的道教思想。其实,道教作为她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 几乎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有意无意地得到了体现,形成了她作品的底蕴。
二、科幻小说的特征与女性主义解构思想的融合
勒·魁恩不仅在幻想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她还尝试了多种文学题材的创 作而且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其中,她的科幻小说给她带来的影响和荣誉最大。她 的长篇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1969)、中篇小说《世界的语言是森林》(1973)和短篇 小说《离开欧米拉斯的人们》(1974)分别获得当年不同体裁的雨果奖。她的短篇小说《 孤独》等还曾获得过纳布拉奖。雨果奖和纳布拉奖是美国奖励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这 两个奖项的获得使她经常被列入科幻小说家的行列。对于这种身份的界定,她本人并不 十分满意。其实,这种对作家的狭隘归类是极为不妥的,尤其是在后现代的写作氛围里 。后现代主义小说“种类混杂”的写作特征打破了文学体裁的严格界线,使各类体裁都 有机会出现在同一个文本中。我们可以在长篇小说中看到单独成篇的短篇小说、诗歌、 戏剧对白和音乐简谱等。我们还可以在探讨人类生存问题的严肃小说中看到侦探小说、 科幻小说、哥特式小说等亚文学体裁的影子。正如伊哈布·哈桑所说:“在这多元的现 时,所有的文体辩证地出现在一种现在与非现在、同一与差异的交织之中。”(注:Iha 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70.) 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很难给作家贴上一个准确的类别标签。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不同文学体裁间的融合最为突出的就是科幻小说 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融合。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我们就已经可以在某些科幻小 说家的作品中,开始看到一种日益增长的对于后现代主义写作特征的接受,也就是说, 出现了一种科幻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化”倾向。同样,后现代主义小说很大程度上也在 经受着来自科幻小说的巨大影响。正如布莱恩·麦克黑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发现后现 代主义小说正在从已经‘后现代主义化’了的科幻小说中摄取素材,而科幻小说也正在 采用已经‘科幻小说化’了的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创作模式。”(注:李维屏:《英美现 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第457页。)因此,科幻小说与后现代 主义小说出现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态势。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传统科幻小 说中常见的主题,如星际间的互访与战争、时间旅行、高科技所带来的乌托邦世界等只 是它们的故事背景和氛围。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地球上的未来世界,更感兴趣的是科技革 新所造成的社会和体制方面的后果而不是科技革新本身。也就是说,这些“后现代主义 化”了的科幻小说和“科幻小说化”了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都更倾向于后现代主义者本体 论的创作观念而不是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中的认识论观念。如威廉·巴勒斯的《新星快车 》、唐·德里罗的《拉特纳之星》和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等后现代主义小 说里都有科幻的因素,但是这些小说又都超越了传统的科幻小说的主题。勒·魁恩在这 方面的尝试尤为突出。她像其他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一样在她那虚构的未来世界或其它星 球上建构着她的乌托邦,而女性则是这个乌托邦的主角。
勒·魁恩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深受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影响和促动。她认为女性 主义理论为她提供了写作指南,她可以不再像男人那样去写作,而是像女人一样自由地 进行写作。的确,6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行为在理论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指导。 弗吉尼亚·吴尔芙鼓励女性作家“杀死屋里的安琪儿”;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女性 写作的“符号学”理念;露丝·伊利格瑞提出了“女人腔”的主张;艾莱娜·西苏则明 确发出“描写身体”的号召。这些主张和号召的宗旨都是希望女性作家从女人自身的体 验出发,建构自己的语言模式,扰乱和颠覆作为父权制象征的男性话语范式,从而颠覆 数千年来根植于文本中的父权话语的合法性,瓦解父权制,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蕴含 的二元等级对立结构,用美杜莎的笑声来震毁男性象征秩序,结束女性被束缚的缄默历 史。(注:陈本益等:《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第381页。) 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内核也是要修正或颠覆权威,主张废除元叙事,消解权力语言、欲 望语言和欺诈语言结构,从而解构人类生存中那些基本的“天经地义”的规约和文明中 一些特定的禁忌以及社会体制中等级秩序的内在基础。因此,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 义理论一拍即合,它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带动之下,在文学创作领域掀起了女性创作的 高潮。而在创作实践中把女性主义的解构思想通过科幻小说进行出色表达的作者恐怕是 凤毛麟角。勒·魁恩便是其中的一个。
勒·魁恩在1973年的一次访谈中就曾经表示了她对科幻小说中女性问题的关注。她说 :
一个早期伟大的社会人士说,女性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是那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相当可 靠的表征。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科幻小说中女性非常低的地位应该使我们反思一下科 幻小说是不是文明的。(注:Jane Slaughter,“Ursula Le Guin”,The Progressive,p .36.)
的确,在传统的科幻小说中,我们很难找到女人的身影。我们也很难找到真正用女性 的声音和体验去写科幻小说的女性作家。在人们的意识中,女性似乎与科技无缘、与太 空无缘、与幻想无缘。用勒·魁恩的话说,科幻小说“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的,而且是 非常反女性主义的”。(注:Ibid.,p.36.)因此,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推动之 下,在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氛围中,勒·魁恩创作了许多浸润着浓郁的女性主义颠覆思想 的小说,其中,长篇小说《黑暗的左手》和短篇小说《她消除了它们的名字》(1985)是 最出色的。
《黑暗的左手》是个典型的关注两性关系的小说。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叫做“冬季” 的星球上,大概内容是这样的:世界联盟要增补一个叫做伊丘门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 负责教育、文化交流和贸易方面的事务。因此它的外交使节勒利·埃被派到“冬季”上 去,目的是要让“冬季”加入伊丘门。在这个星球上有两个主要国家:卡海德和沃果里 因。卡海德有点像俄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国家没有战争,权力关系通过威信、尊严 和地位构建起来,但是国王却是个疯子般的人。它的人民信奉黑暗的神秘性。沃果里因 有点像封建君主制国家,它好战,具有侵略性而且官僚作风严重。那里的人民团结,驯 服,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它们否定黑暗的神秘性。这个星球上进行的一种生物实验使 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体验到不同性别的生活状况。大约每隔一个月的时间,当人们进入到 一个“克默”状态或一种性兴奋状态时,他们就有可能或者变成男性,或者变成女性。 这种性别的转换是绝对偶然的,无规律可循的。因此,这个月是男性的人们到了下个月 就有可能变成女性,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这种试验的结果使“冬季”这个星球变成了 双性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存在以男性为中心或者以女性为中心的权力话语或 统治体制,也不可能存在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以及道德、永恒等价值观念。一切都成 了不确定的暂时存在。因此在勒·魁恩的这个文本中,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政治和文化 根基被彻底地动摇和颠覆了,那种建立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c ism)基础之上的阴与阳、黑暗与光明、文化与自然、理智与情感、灵魂与肉体、主体与 客体、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被有力地解构了。《黑暗的左手》可以说是勒 ·魁恩对于女性深切关怀的体现和对于建构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最为大胆的设想。然而 ,她在书中描写的卡海德和沃果里因这两个社会却都有点偏执狂倾向。这似乎又流露出 她对双性人世界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思考和担忧。对此,她曾在1995年的一次访谈中表达 了她的遗憾:“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认为双性人可能是偏执狂。在对女性主义研究了 20年后的今天,我可以想象出一个双性人的社会应该是相当不同的,应该比我们这个有 明显性别区分的社会有趣得多。”(注:Jonathan White,“Coming Back from the Sil ence”,Whole Earth Review,n 85 (Spring,1995):76 (8 pages)pages.)她认为,那种 认为性伴侣一定是异性的看法是幼稚的。她很后悔自己在《黑暗的左手》中作了性行为 应该是异性间行为的暗示,这无疑是对同性恋者的一种声援。无论如何,她在《黑暗的 左手》中所进行的大胆构想是对现代社会中男性权威和元叙事的一种嘲笑和颠覆,也是 道教思想中主张阴阳相融以达到平衡的理念的一种表征。
如果说《黑暗的左手》是勒·魁恩借助于科幻小说的素材所进行的一个关于两性问题 的思想试验的话,那么《她消除了它们的名字》这个短篇小说则是一个对人类起源神话 的嘲弄,对几千年来根植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男女二元对立等级秩序的有力质疑和解 构。用勒·魁恩的话说,这篇小说是对亚当和夏娃故事的颠覆。勒·魁恩用戏仿的手法 对《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故事进行了重写。戏仿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常用的一种写作 技巧,他们在作品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对古典文学名著的 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的、扭曲变形的、嘲弄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和滑稽 可笑,从而达到对传统、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过去的文学范式进行批判、 讽刺和否定的目的。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是创世纪开篇的第一个故事,也 是人们,尤其是西方信奉基督教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它从宗教的角度对人类及其他 物种的起源以及父权制秩序形成的本源进行了寓言式的阐释。亚当是上帝模仿自己的形 象创造出来的,上帝赋予了他许多至高无上的权利,其中一个就是为上帝创造出来的其 他生灵包括他的妻子的命名权。“命名”这个行为在勒·魁恩看来至少有两层涵义:“ 命名”意味着对个体的尊重和一种亲近的情感;同时,它也会在人们之间、人们与世界 之间造成一种疏离、隔膜的感觉。而且,在勒·魁恩看来,命名者对被命名者享有控制 和统治权。因此,“命名”不是一种简单随意的行为,它象征着权力;名字也不是一个 简单空洞的能指,它是主动与被动、统治与被统治等二元对立等级秩序得以建构起来的 途径。关于“名字”和“命名”的涵义问题,勒·魁恩在它的许多小说中都有所探讨, 按照勒·魁恩对于“名字”和“命名”概念的理解,在“亚当与夏娃”这个关于人类的 第一个故事中,亚当就是权力的代表,他给夏娃及其他动物的命名行为就是进行统治、 建构二元对立等级秩序的行为。这个行为本身喻指了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其他动物之间 ,或者说是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对立关系。几千年来,这种等级秩序在 西方的人们默诵《圣经》的过程中已经潜移默化为一种天经地义的社会规约,似乎从来 就没有人大胆地对它提出过质疑。勒·魁恩这个深受中国道教思想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 和非基督徒却勇敢地发出了她响亮的女性主义声音。在《她消除了它们的名字》中,夏 娃成了一个挑战和颠覆亚当的统治权威和他建构起来的等级秩序的女性主义英雄。她首 先说服其他动物放弃它们的名字,去接受一种无名字的状态。她发现动物在把它们的名 字归还给亚当以后,它们之间似乎更亲近了,她自己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更亲密了,横 在他们之间的障碍消失了。他们明显产生了一种想去闻、去触摸、去感受对方的渴望, 因此,夏娃决定也要把她自己的名字归还给亚当。她对亚当说:“你和你的父亲把它借 给了我——事实上,是把它给了我。它确实曾经很有用,但是最近它似乎不那么合适了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它确实曾经非常有用。”(注:引文参阅本文后面的译文。)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他听了夏娃的话后只是心不在 焉地说:“就把它放在那儿,好吗?”然后就继续做他的事情了。这难道意味着亚当的 妥协、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接受?或是勒·魁恩一相情愿的希望?或是她对女性的一种暗示 ?这确实值得人们思考。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则更加耐人寻味。当亚当习惯性地问夏娃, “好吧,亲爱的,什么时候吃晚饭?”时,夏娃却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要走了。和 它们一起。”为丈夫做饭、遵从和维护丈夫的权威是男性文本中所塑造的女性“天使” 形象,也是父权制社会要求女性应当承担的基本义务和责任。然而,勒·魁恩所塑造的 夏娃却放弃了这些义务和责任,并联合其他力量来颠覆她的丈夫亚当的权威。这对传统 的伦理观念是多么有力的挑战和解构。虽然如此,勒·魁恩的夏娃也没有变成男性文本 中的另一种女性形象——阴险刁钻、贪婪自私的“恶魔”。她虽然放弃了亚当给她的名 字,但是她仍对亚当心存感激,对动物充满了友爱和关心。可以说,“夏娃”这个文学 形象颠覆了传统的男性文本中“天使与恶魔”这两个极端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者所 提倡的理想女性形象。
名字既然是别人给的,那么就可以被放弃。权威和秩序是人为建构的,那么也就可以 被解构。没有什么是恒定的、本源的、永远正确的。用利奥塔的话说,广泛的社会主要 准则都是“非法化”的。勒·魁恩对亚当与夏娃故事的戏仿无疑是对利奥塔所谓的“非 法化”理论做出的回应。她通过夏娃对亚当权威的反叛对传统意识中“合法的”、天经 地义的规约进行了质询,对终极真理、宏大叙事进行了嘲弄和消解。
三、梦、拼贴手法的运用与对狂躁、不确定的生存状态的忧虑
如果说《她消除了它们的名字》是厄秀拉·勒·魁恩用戏仿的手法对两性之间传统的 二元对立等级关系所表示的深切关注,那么她的另一个短篇小说《薛定谔的猫》(1974) 则是用梦和拼贴等手法对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所表现的忡忡忧虑。
小说《薛定谔的猫》一开始就以一对正在“零散化”的夫妇摄住了读者的注意力。正 当读者为这对夫妇肢体的零散感到惊愕、迷惑之时,小说的叙述者于半隐半显之中告诉 读者:这是一场梦,或者说这是一些梦的碎片。勒·魁恩用梦的形式来构建她的小说, 可谓用心良苦。她借此巧妙地传达了她想要表达的信息:“不确定性确乎渗透到我们的 行动和思想,它构成我们的世界。”(注: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 ,见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25页。)按照 弗洛伊德对于梦的解释,梦就是潜意识中那些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人在睡眠的时候, 这些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就会冲破自我和超我的约束而闯入意识领域。雅各·拉康在此 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欲望论”也认为梦是被压抑的原始欲望想要进入意识世界的一种 虚幻的、非逻辑的方式和途径之一。这种虚幻的、非逻辑的表达方式被勒·魁恩用来表 达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普遍探讨的本体论问题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它因其虚幻和非逻 辑性而在形式上显得零乱和支离破碎,因其被压抑性而在内容上更显得本真。勒·魁恩 用梦的形式编织起来的记忆残片,使读者在零乱、狂躁之中体会到生的无奈和绝望以及 她对后现代社会人们生存状态的忡忡忧虑。
小说以梦的形式表达了人们不确定、狂乱、支离破碎的生存状态:叙述者不知是男是 女;一对夫妇在“我”的冷漠注视之下顷刻间分崩离析;生活中的一切,如门的旋钮、 电话的拨号盘、刀叉、铅笔、车门等变得灼热烫手;人们的吻像烙铁一般;孩子的头发 摸起来灼热似火;电器和煤气炉会自动找开;冷水管里流出热水来;邮递员突然之间有 了狗的特性;动物有着“狂热的特质”,它们移动迅速,“缺乏在场”。然而,小说中 那只被邮递员称为“薛定谔的猫”却是个例外,它与小说中描写的一切都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它的毛摸起来令人感到凉爽舒适,它的动作缓慢稳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善解 人意。作者似乎赋予了那只猫特别的意义,它象征着存在、理性、秩序和“在场”。然 而,这只猫在小说的最后却在邮递员和叙述者模拟进行的薛定谔的思想试验中不翼而飞 了。
薛定谔是德国的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思想试验,建议把一只猫和 一个装有毒药的容器一起放进一个不透明的盒子中。这个容器被装上锁具,它可以由放 射性的原子衰变打开并放出毒药。那么,一段时间之后,这只猫是活着还是死了呢?根 据古典物理学原理和常识我们可以知道,这只猫一定是要么活着要么死了。也就是说, 答案是唯一的,确定的。然而,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来看,这只猫将会处于一种模棱两 可的状态:活着或死了。只有当盒子被打开,人们看到那只猫时,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坚持量子力学直接解释的理论学者认为存在一个中间态,猫既不死也不活,除非进行 观察,否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确定的。这种理论看似荒谬,实际上则是基于无懈可击 的数学方程,基于量子力学朴实的、自恰的、符合逻辑的结果。
量子理论代表着科学的最大进步。然而量子世界的神奇却使许多包括阿尔伯特·爱因 斯坦在内的科学家都觉得难以理解,他们因此而拒绝接受由薛定谔及其同事得出的理论 结果。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与这个世界玩游戏。”他不承认薛定谔的猫的非真实态之 说,他认为一定有一个内在的机制组成了事物的真实本性。他花了数年时间企图设计一 个实验来检验这种内在真实性是否确实在起作用,但他没有完成这种设计就去世了。
勒·魁恩在《薛定谔的猫》中模拟进行了这个思想试验,当然她的目的决不是像爱因 斯坦那样想从科学实验的角度去验证薛定谔理论的真实性,而是想通过这个试验,根据 猫的状况来验证“上帝是否在与这个世界玩游戏”,即这个世界是不是确定的、有序的 。无论猫是活着或是死了,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肯定的状况。然而在故事的最后,那只猫 却消失了。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打开了盒子,我们仍然无法确定那只猫的状况。它是活 着?或是死了?正如量子力学原理所认为的那样,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这 个想验证“确定性”的试验得出的结果却是“不确定的”。当人们像剥洋葱一样跟随着 作者剥开层层迷雾之后,却发现一个空心,一个虚无。读者原以为在这个狂乱的文本世 界终于找到了一个凉爽、理性的存在物,并且在与叙述者和那个邮递员一样期待着一个 确定的答案时,却像叙述者和邮递员一样在小说的结尾体验到了更加强烈的不确定和彻 底的绝望感。他们只好在“杂乱的星光”和“使舒曼发疯”的曼陀林上的A大调中回味 着丧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理性?秩序?或是希望?
对于“真理”、“理性”、“秩序”、“确定性”等的寻求一直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 一个基本主题。这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目标的确定随着近代社会的到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张 扬。然而,这种情况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便开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20世纪五 六十年代之后,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人类开始彻底反省以往的人类认识历史和 精神历史。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自近代启蒙以来对于“真理”、“理性”等“现 代性”的追求是一种坚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和元叙事的行为 ,应该统统予以消解。他们认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先验的、客观的意义,一切都是 不确定的、模糊的、松动的和多元的。正如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所说:“朝着 模糊和不确定的倾向是当代文明的一种危机。”(注: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 的多元论》,第148页。)伊哈布·哈桑在他的《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一文中也把“ 不确定性”列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本质特征。可见,“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一种普 遍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可以被接受为经验的世界的丧失”。(注:Brian McHale,Post modernist Fiction(Methuen New York and London,1987),p.26.)作为反映时代的一面 镜子的文学家们纷纷扛起了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以各种极端的表现手 法描绘着这一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景观,“黑色幽默”、“戏仿”、“拼贴”、“蒙 太奇”、“迷宫”等是他们常用的写作技巧。他们在雅各布森所谓的“隐喻”和“转喻 ”这两种现AI写作作的两极话语模式之外另辟蹊径,使用一种“矛盾的、并置的、连续中 断的、随意的、极端的和短路的话语”。(注:David Lodge,Working With Structural ism:Essays and Reviews on 19th and 20th Century Literature(Bost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p.13.)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所说的“闪烁”(flickering)效果,一种哈桑所谓的“不确定性”,从而向 读者描绘一种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独有的心理体验。
勒·魁恩在《薛定谔的猫》这篇短篇小说中用追忆的方式把梦境中的碎片串在一起, 这些碎片在内容和形式上毫无联系,在出现的时间上也没有先后的连续性,它们之间互 不衔接,相对独立。然而它们却被勒·魁恩随意地摆放在了一起,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 惯用的形式结构,给读者的审美习惯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产生了常规叙述方式无法达到 的效果。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零散、片断的材料就是一切,反对任何形式的组合结构 。这就是巴塞尔姆所谓的“20世纪所有传播媒介中的所有艺术的中心原则”,(注:Jer ome Klinkowitz,Literary Disruptions:the Making of a Post-Contemporary Americ an Fiction,2nd e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0),p.37.)即“拼贴原则”。 拼贴原则把毫不相干的片断联系在了一起,给读者的阅读体验造成了一种“随意”、“ 短路”和“连续中断”的感觉。此外,勒·魁恩还运用了布莱恩·麦克黑尔在他的《后 现代主义小说》中所论及的“自我消除叙事法”(self-erasing narrative)来达到这种 “随意”和“连续中断”的表达效果,进而强化文本世界和整个“本体领域”的闪烁不 定。勒·魁恩在小说的开头描写的那对夫妇,他们看上去似乎相当强壮的肢体突然间竟 莫名其妙地零散了,女的最后变成了一堆铁丝网状的神经,男的则成了一堆跳着、叫着 的碎片,这一对夫妇就这样眼睁睁地被勒·魁恩“消解”掉了。这个耸人听闻、极端煽 情的场景被描写出来之后马上就被作者“消除”掉了,无论是这个场景或是这对夫妇就 这样无声地消失在这个文本之中,再也没有被作者提及过。而且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精 心描绘出来的象征着理性、秩序和确定性的那只猫也陡然间不翼而飞了。这种叙事方法 在许多后现代主义小说中都可以见到。与勒·魁恩对这对夫妇的处理手法极为相似的是 托马斯·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对泰娄恩·斯洛思罗普的处理。斯洛思罗普被派到 一个叫做“域”的地方之后,由于计划出错,他就“崩溃”、“消散”了。在小说的结 尾,品钦告诉读者斯洛思罗普变成了“一只被拔了毛的信天翁。……消散在整个‘域’ 上了。他是否能再被‘找到’是令人怀疑的……”。(注:Thomas Pynchon,Gravity's Rainbow(New York,Viking,1973),p.712.)此外,塞缪尔·贝克特和缪里尔·斯帕克等 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中也都运用了这种叙事手法。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描绘这 样的煽情场面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读者,使读者对被消除掉的这些场面进行情感投资,通 常是为了引起他们的忧虑、迷恋和兴趣等。当读者被引入这种已描绘出来的世界之后, 作者又把这些世界消除掉,尤其是把被塑造出来的人物消除掉,这样,读者就会感到失 落、不满,他们本能地留恋那些被作者消除的情节和人物,这就加剧了被渴望的在场和 被怨恨的不在场之间的张力,使文本闪烁不定的速度变得更慢。而且这种文本的干扰也 会使整个叙事变得更加混乱和破碎,从而使文本对本体论问题的探索显得更加深刻和贴 切。在《薛定谔的猫》中,那对夫妇消散之后,那种强烈的失落感不禁使我们感到生命 的无常。而在那只猫不翼而飞之后,我们情感上的缺失则更加强烈,因为我们寄托在它 身上的希望以及对于确定性进行验证的可能性也一下子不翼而飞了。也许真如亨利·亚 当斯所说的那样:“生活没有意义,探索也总是以纯粹的虚无空寂而告终,人无处可逃。”(注:亨利·亚当斯:《民主信条的堕落》(纽约:哈泼火炬书局,1969),第251页 。)
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与这个世界玩游戏。”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理 性的、有秩序的,而不是虚构的、混乱和无序的。然而在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 代以后的西方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秩序发生了严重的裂变。尼采说“上帝死了 ”,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和信息时代的先 后诞生,人们发现过去被视为真理、权威和中心的东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威胁甚 至消解。整个世界变得缺乏理性、混乱、疯狂和支离破碎。上帝似乎与这个世界玩起了 游戏。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这个失去理性、混乱和不确 定的世界。勒·魁恩在《薛定谔的猫》中似乎在展示这个世界的同时,还多了一层探索 和验证的意义,然而探索的结果却“以纯粹的虚无空寂而告终”。这个未果的试验只是 加剧了人们不确定和绝望的情绪。也许,勒·魁恩在这里试图表达的是:这个世界本来 就是散乱的、无序的、不确定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试图去解释和验证它的努力只是徒劳 。
勒·魁恩通过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入思考和对小说创作的认真探索,形成了自己在当 代小说创作领域的独特声音。她对中国道教思想中幽默、温和以及和谐、同一气质的迷 恋,使她在许多小说中有意识地解构了人类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等级关系,不厌 其烦地为人类建构着道教哲学所崇尚的和谐、理想的家园。她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 潮的促动之下,有意识地用女性的语言与体验进行写作,在多部作品中为人们勾画了新 型的两性关系,她因此被称为后现AI写作作氛围中科幻小说界的“女权威”。此外,勒· 魁恩还运用了戏仿、拼贴等后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写作手法,对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了 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探讨,因此,一些评论家说她为科幻小说带来了一种“新的敏感性 ”,用一种“奇异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经验进行了解读。
